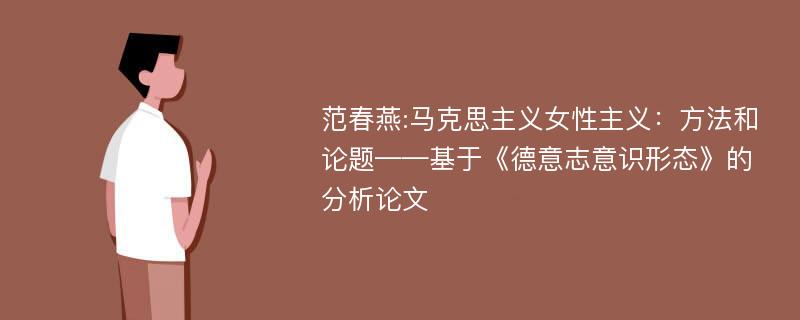
摘 要: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最重要文本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首次全面阐述,不仅为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中脱颖而出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总的方法论原则,也留下了一些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议题。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对经典理论进行批评性阅读的基础上,拓展了其论域,并提出了一种关于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中的“文化转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重新诉诸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硬核”,《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也被重新召回。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家务劳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西方女性主义引用、解读和研究频率最高的两个文本。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那样专门讨论了妇女解放问题,但却被西方女性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视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和妇女问题的奠基之作。这是因为,首先,《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最重要文本之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首次全面阐述,这一“新世界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出女性主义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回答”[1]的总的理论出发点。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原则,也涵盖了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议题,主要包括“两大生产”问题、自然分工问题和家庭问题。再次,尽管恩格斯晚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妇女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讨论,但其中的基本观点并没有超出四十年前和马克思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注]① 比如恩格斯在文中采用了几乎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完全相同的关于“两大生产”问题的表述,对自然分工问题和家庭问题的论述也基本符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论断。参见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虞晖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89页。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方法和论域的基础上,把性别问题引入生产、分工和异化论域,构建了一种以家务劳动为核心、基于性别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后现代主义氛围中的一种文化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又重新回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理论起点,并将其作为构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重要参照,以恢复被文化和话语所遮蔽了的生产议题。
一、经典理论的地平线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从未完整出版过的长篇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种和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见解完全不同的新的哲学观,其中最具颠覆性的见解就是:不是从意识或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去看待人类社会和历史。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成为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讨论妇女受压迫和解放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1.《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理论出发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和旧式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新世界观可以表述为从“现实的人”出发。“现实的人”首先指的是那些有物质需求的个体。“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2]需要构成了第一个历史活动,也产生了家庭。其次,“现实的人”也是社会关系中的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3]再次,“现实的人”是从事劳动实践活动的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4]而从现实的人出发就会得出:历史和政治的核心内容是生产以及拥有不同生产资料的群体之间的不同关系所导致的冲突;历史上的不平等关系并非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是人的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之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如果物质条件不改变,不平等关系也就不会改变。这些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妇女受压迫和解放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妇女受压迫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妇女的解放也和建立在物质条件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相联系。[5]
从现实的人出发,可以很好地驳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性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论,也就是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来看待,认为女性的解放就在于从蒙昧走向科学和理性,从家庭走向社会和公共,通过成为和男人一样的理性人来消除两性差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先驱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浪潮中的西方女性主义者发现,尽管女性已经争得了各种各样的权利,但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地位和命运。通过审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立论基础,他们发现,建立在理性论基础上的女性解放实际上就是要以理性、心智、公共来归化非理性、自然和私人。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悖论,因为女性作为一个历史的和具体的概念,根本无法完成通往普遍理性的一跃。在理性的抽象中,总会存在一种关于“他者”的性别剩余。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理性论隐含的前提就是关于理性和非理性、心智和身体、社会和自然、公共和私人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将男性认同于理性、秩序、文化和公共生活,而将女性与自然、情感、欲望和私人生活相联系,从而天然地构成了对非理性、自然和身体的贬低。换言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试图以理性来抹平性别差异,但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性别主义的嫌疑。
把人的本质视为建立在物质性需求之上的劳动实践关系,不仅能从根本上驳斥普遍理性论,也能排除关于理性和非理性、心智和肉体、公共和私人的二元界分。正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述的那样:“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6]换言之,从生产和实践的视角来看,自然和社会具有统一性。此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也没有截然的区分,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家庭本身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家庭关系就是社会关系(“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7])。
尽管《蒙古的人和神》作者亨宁·哈士纶在20世纪30年代曾造访新疆和静县满汗王王府,书中收录了不少珍贵的历史照片,但是大家心目中还是接受不了这么一幅渥巴锡画像。所以2010年7月在和静县召开的“东归历史与文化”研讨会上安排了一项渥巴锡画像征集活动。与会的好几位蒙古族画家提交了近10幅渥巴锡画像,还有好几幅素描像。画像中的渥巴锡是一位典型的蒙古汉子。宽阔脸膛、两眼炯炯有神,是的,人们心目中的渥巴锡应该这个样子,但毕竟是艺术的创作。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建立在性别分工之上的自然分工称为人类社会分工的最初形式,并把自然分工和真正的社会分工相区分。针对这一点,不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既然在自然分工中已经包含着剥削和压迫的萌芽,那么,自然分工又为什么必须从真正的分工中排除出去呢?把性别分工留在直接性的自然领域,从而把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相隔绝,不仅无法从根本上驳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二元论,对于妇女解放问题而言,也意味着一种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因为如果不把性别分工作为分工的一个例证来看待,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自由对女性而言就会天然地大大减少。仅仅从精神劳动的决定性出发,也会倾向于把妇女在生育、养育和家务劳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归于自然的一边,或者说,妇女只是作为精神发生的自然条件或“容器”而存在。
2.《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奠定的基本问题域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两大生产”原理,也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物质性生产和“生产另一些人”的生育性生产。[8]他们还强调,“两大生产”作为生活的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两大生产”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意义在于:通过指认女性生育活动的重要性,把生育活动提高到了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并列的高度,从而使家庭在个人生产和再生产的意义上获得了理论上的位置。
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提出了自然分工的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分工起初只是性方面的分工,并由此产生了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出现了“真正的”社会分工。也就是说,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作为分工的基础,并不能归于真正的分工即社会分工之列。自然分工仅仅代表着社会分工的萌芽和可能性,“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9]换言之,只有当生产和消费、劳动和享受由不同的人来承担时,真正的社会分工才成为现实。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两大生产和自然分工方面的论述,也给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留下了一些有待讨论的疑问:对自然分工的区别性对待和两大生产原理中所强调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是否存在着矛盾?如果家庭内部的分工不能作为真正的分工来看待,那么这一分工能否作为女性受压迫和屈从地位的根源来进行分析?家庭内部的生育性、养育性和家务性劳动,是否能够归于生产实践范畴?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经典议题的批评性拓展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注]其主要代表包括: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芭芭拉·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伊利·扎瑞斯基(Eli Zaretsky)、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希拉·罗伯(Shelia Bowbotham)、伊芙林·里德(Evelyn Reed)、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等人。的基本特征是:从“现实的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出发,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分工和异化等阶级性议题扩展到了家庭和生育领域,并使其成为一系列性别议题,从而构建了一种以家务劳动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对“自然分工”的拷问
(2) 崩塌发生机制。根据现场调查及遥感影像分析,边坡岩体风化、卸荷作用强烈,沿岩体软弱层和片理面冲沟发育,造成冲沟周边危岩密集分布,在降雨、冻融、地震、重力等作用下,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倾倒式、滑移式、坠落式和滚落式崩塌,落石直径多为0.5 m×0.5 m×0.5 m~4 m×5 m×3 m。
我的脑海萌发出要探索建立一种符合当时农村发展实际,并能充分调动社员生产劳动积极性的新的农业生产办法。核心是使生产的好坏同社员家庭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为了求证这种想法在理论上、路线上的正当性,在政策上的合法性,我有空就往村上大队部跑,找来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报刊阅读,同时认真聆听村里大喇叭播出的有关时政新闻,捕捉社会上流传的各种信息来参考。
鉴于自然分工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劳动关系对于妇女受压迫问题的重要性,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要对经典理论进行批评性的重新解读。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大生产”理论强调的就是生产和实践视角下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不可分,如果将这一点贯彻到底,就能得出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也是不可分的。换言之,劳动的性别分工不仅植根于人的自然需要当中,是满足自然需要的物理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也内含于实践对象的生产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从“发生学”的视角来重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分工理论,认为自然分工不是作为分工的自然“起源”,而是作为分工的理论“原型”,性别分工本身就被回溯性地赋予了阶级维度,性别分工和性别压迫无法规避从阶级分工和阶级剥削的视角所进行的审视和分析。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对经典理论的重新解释并不准确也没有必要,并提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应该致力于拓展新的议题。如温迪·林恩·李曾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尽管有一些类似于“双重关系”的说法,但基本上还是把生产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和具有“深思熟虑目的性”的劳动来看待。[10]结合实践的观点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再强调的正是自然分工的一种非充分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把生育和养育等基于自然分工的活动从劳动实践的形式中排除了,这从后期的一些著作来看更为明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涉及任何基于自然分工的“劳动”,包括生育、养育和家务劳动在内,都被默认为不属于劳动实践的范畴。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分工能够提供一种关于妇女受压迫分析的出发点时,可以直接去建构自己的论域,不必要通过对经典理论的重释来曲意表达。
[1]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94页。
围绕自然分工的争论也引出了妇女异化问题。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异化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分工,既然他们只承认自然分工的一种基础性作用,而不把这种分工作为一种真正的分工来看待,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而言,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基于性别的自然分工究竟还能不能作为妇女异化的根据?
1.“文化转向”和新唯物主义浪潮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不把家庭内部基于性别的分工当作一种真正的分工,不仅不能为妇女的屈从地位提供理论上的解释,也失去了建构一种基于阶级分析的妇女解放理论的可能性。如果被异化的对象只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工人,那么从事家务劳动和生育、养育活动的女性就会失去被异化的资格,妇女的解放就不能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克服来达成,阶级压迫的消亡和性别压迫的消亡就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妇女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也就无法达成一种内在的统一。从另一方面来看,妇女的不可被异化实际上就是承认妇女是内在地被异化的,而且这种内在的异化无从克服也不可救赎。正像温迪·林恩·李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女性的本体论条件不是由她生来的实践能力所决定、而是由她的性别来决定的话,她要么是不能被异化的,要么是已经被内在地异化了的。”[11]妇女的不可异化性与其内在异化之间的矛盾,也使得妇女在资本主义剥削中占据了一个相当奇怪的位置:一方面,她们没有被剥削的资格,另一方面她们看来又是最可剥削的——尽管没有创造性劳动的潜能,但却有一个为妇女特别准备的劳动领域。[12]
结合速冻水饺生产工艺,对所需材料及设备进行简要说明。本研究所选淀粉为山东凯达格兰公司的变性淀粉,以及硬酯酰乳酸钙-钠,抗坏血酸,复合磷酸盐;山东梨花公司生产的水饺专用面粉。所选用的机械设备由番禹力丰公司生产的B20搅面机,哈尔滨田麦公司生产的JBT-100包和式水饺机,海鸥公司生产的DZM-160电动压面机。
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也能够超出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性别本质论。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是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另一个重要流派。相比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承认性别差异(理性可以抹平性别差异),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则是把性别差异本质化,认为性别差异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决定物,从而得出“女性的敌人是男性”的结论。但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看来,男性或女性虽有不同的生物学性别,但同时又都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决定男人或女人本质的,不应只依据其生物学特性,而应根据他们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围绕自然分工讨论的基础上,也致力于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拓展到性别和家庭领域。贾格尔认为,异化不能限定在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中,不仅不挣工资的妇女经历着异化,挣工资的妇女所体验的异化也不同于挣工资的男性工人。异化总是包含着独特的性别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的异化主要表现在她和自己身体的疏离,这和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疏离是一样的。资本对妇女的压迫采取了妇女与所有事、所有人特别是与她自身相疏离的异化形式,妇女作为人之完整性源泉的各种因素都反过来成为导致她分裂的原因。[13]
3.基于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自然分工和妇女异化问题的实质就是从性别视角来考察家庭内部的生产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对经典议题进行拓展的基础上,从正面提出了“家务劳动”的概念,并认为这一概念能够揭示妇女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结构性地位。玛格丽特·本斯顿认为,妇女尽管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推动的平权运动中获得了选举权、教育权和工作权,但她们在从事工资劳动的同时并没有真正摆脱家务劳动,她们承担的毋宁说是双重劳动。而且,尽管工资劳动也使妇女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并不能说明性别之间的差异,只有家务劳动才是属于妇女的劳动,只有从家务劳动入手进行分析才能触及妇女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结构性地位。[14]
在此基础上,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深入探讨了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如家务劳动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家务劳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家务劳动对妇女作为劳动力后备军具有怎样的意义?家务劳动对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具有怎样的意义?
围绕这些问题,这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取得的共识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而言,家务劳动是不可或缺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首先,家务劳动使妇女能够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后备军长期存在。妇女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对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生产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务劳动起到了对工资劳动的平衡和调节的作用,妇女也成为劳动力后备军中最具稳定性的一支力量。此外更重要的是,家务劳动直接贡献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因为家务劳动所提供的准备膳食、清洗餐具、缝制衣服、照料儿童等活动使得劳动者能够面对每一个新的工作日,没有这些不起眼的家庭内部的劳动,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无法正常进行。但是,家务劳动的这些贡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它作为一种无酬劳动本身并没有价值,也就不能在资本主义结构中获得一个显性的位置。家务劳动的“不可见”,就成为妇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遭遇的不平等和屈从地位的根源。
那么,如何使得这样的一种无酬劳动可见并获得认证,从而改变妇女的屈从地位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出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一些不同认识。本斯顿的主张可以归结为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倡议。在她看来,只有把家务劳动从家庭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资本生产的某一个部门的社会性劳动,才能在实现使用价值价值化的同时,消灭家务劳动作为妇女劳动专属领域的“家庭性”。换言之,只有把家务劳动从家庭内部转移到公共领域,才能从根本上取消家务劳动。而科斯塔与詹姆斯却认为,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不能被取消或消灭,恩格斯已经论述过私人的家务劳动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前提,也就是说,在私有制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家务劳动社会化是不能达成的。在他们看来,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就是使妇女的家务劳动至少能够和工人的社会劳动一样得到承认。基于家务劳动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贡献,科斯塔与詹姆斯提出家务劳动不仅是生产性劳动,而且还创造了价值,本身就应该作为资本的构成部分。因此,他们在策略上主张家务劳动的工资化而不是社会化,即由政府和雇主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买单。
三、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转向和重访
第三,资产日常管理变更包主要用于在日常帮助仓库管理人员、领物员等等进行资产信息查询、编辑与修改,例如对资产存放地点的修改调整等等,同时它也会记录每一次的系统维护信息,对每一次的日常购物进行审批检验,实现对高校固定资产基础信息的全面维护。
2.2.3 居民对福州城市林业成效感知差异性分析 就福州市民对福州城市林业综合评价的单因素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5)显示,福州市民对城市森林在各区均匀度,结构布局的乔灌草比例,城市森林覆盖率,噪声,满足市民休闲、游憩、观光等精神需要感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经多重比较后发现,台江区与晋安区、仓山区、鼓楼区、马尾区在均匀度、噪声、精神需要、城市森林覆盖率、乔灌草比例方面差异显著,其他区域的市民在这些单因素感知方面差异不显著。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建立的关于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于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兴起突然中止,他们所主张的以性别关系介入生产议题的路径也在女性主义研究中逐渐淡出。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第三波西方女性主义逐渐远离唯物主义命题,使得一切都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和话语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新一波唯物主义浪潮以回到本体、回到自然、回到身体的名义试图恢复一种非表象、非隐喻的物质概念时,一些以历史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自居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注]主要包括罗斯玛丽·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y)、克瑞斯·英格汉姆(Chrys Ingraham)、唐娜·兰德里(Donna Landry)、杰拉尔德·麦克林(Gerald Maclean)等人。又开始了新一轮对经典理论和议题的重访,试图“将那些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文化政治学漂移,重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视野之中”。[15]而在此过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提出的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产”出发也再次成为思考的起点。
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第三波女性主义逐渐远离了生产议题,转而关注语言、话语和表象。巴雷特把这种趋向称之为女性主义的“文化转向”,认为其基本特征就是从“物”到“词”的转变:一些关于物质性生产和社会结构的讨论消失了,代之以话语分析和精神分析;对女性处境物质条件的拷问,转向了文学批评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对马克思的引用,转向了对德里达、拉康和福柯的引用。[16]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波女性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诉求也变成了一种文化运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或者是一种新的意识。[17]
第三波女性主义的“文化转向”也导致了一系列政治上的瘫痪,一些新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女性主义者过于强调主体性(subjectivity)所造成的。由此,他们提出要重新回到客体和实在,以确认一个不能被观念化的物质性“原化石”的存在,以及一个在话语之外或先于话语的物质世界的存在。[18]在这种“客体导向”(object-oriented)的逆向思维中,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主要沿着三个方向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是后人类女性主义的主张,主要强调从非人类中心主义出发,提出一种活力论的物质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超越性别议题的女性主义(feminism beyond women)。二是生命政治批判,即主张对权力的物质层面而不是文化或意识形态层面进行重新思考,强调身体而非智识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实践性。三是接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传统,试图重新回到生产议题,提出一种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相适应的女性主义分析。[19]
引理 1.3[12] 设{Xni, i≥1, n≥1}是被随机变量X随机控制的随机变量序列, 则对任意的α>0和b>0, 有下面式子成立:
2.对经典理论的重访
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文化转向”实际上折射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反本质主义路向:起初是为了祛除一种经济决定论,主张用政治的和话语的首要性取代经济的首要性,反映到女性主义领域,就是对妇女受压迫问题的讨论不再追问其物质性根源而是采取一种文化性解释。后来,当后马克思主义推出以偶然性、局部性和异质性的身份概念全面取代阶级概念的时候,女性主义也开始全面拒绝一种以性别介入生产议题的分析路径,性别和阶级之间的张力也因为阶级的退隐而不复存在。
在试图扭转“文化转向”的唯物主义重构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主张重新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也就是一种和人的需要和劳动实践关系相联系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硬核”,不同于各种思辨实在论和“客体导向”本体论所说的物质性,而是建立在“主体-客体”辩证关系以及“自然-社会”辩证关系之上的物质性。亨尼西和英格汉姆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一书的序言中主张回到经典理论所提供的一种起始性思考,也就是从作为人类生活前提的现实的个体及其基本需要出发所展开的思考。他们认为,只有从这样一种起始性思考出发,那些被缩减为表象的社会生活才能在现实的层面展开,那些被后现代的文化政治所遮蔽了的生产议题才会浮出水面。在他们看来,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就是要恢复一种以生产为参照的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不平等地位的讨论。[20]
从另一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之名对经典理论的重访并不是一种回归,而毋宁说是一种理论的参照。因为在他们看来,经典理论所提供的一些方法和议题已经被时代的转换所耗尽。比如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当情感、关怀等领域都已经被资本所圈占的情况下,再去讨论家务劳动的工资化不仅已经失去意义,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资本圈占的共谋。他们也不主张在一般的意义上反对文化主义,文化主义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根源,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回到以生产为参照的性别议题,并不意味着完全从文化的上层转向经济的基础,而只能是一种基于全球劳动分工对性别、种族、民族和阶级等问题的交叉性思考。
学生是课本剧的主体,教师却是课本剧的引领者。教师对课本剧的评价可以从学生的表演、剧情的开展、学生的表达、场边情况、道具准备情况多方面对课本剧进行整体分析,让学生从大方向正确理解每一次课本剧的真实情况,从而让学生查缺补漏,在课本剧中全面成长。
注释:
2.妇女的异化
儒家追求尽心而成性,进而到达圣人之境,最终拥有理想的人格。“圣人”始终是儒家所求的理想人格的代称,由此,儒家认可的理想人格最直接的标准就是圣人所代表的概念。而胡宏对此的理解,不仅对许多先贤大儒的众多理论予以了承继,而且还进行了积极的探究,进而使其提出的圣人理论极具个人特色。
[2][3][4][6][7][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514、24、31-32、32、31-32、35-37页。
[5]王宏维:《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性别视域中的演进与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
[10][11][12]温迪·林恩·李:《马克思》,陈文庆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90、91-92页。
陈颐磊说完,从孔守善袖子上褪下黑袖章,给自己左臂套上。其实他心里还打着另一副算盘,面对十万围城,他的此举更多向下属表明自己成仁的决心。
[13]阿丽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孟鑫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14-318页。
[14]Margaret Benst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MonthlyReview, Vol.21, No.4, 1969.
[15][17][20]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s.),MaterialistFeminism:AReaderinClass,DifferenceandWomen’sLiv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1997, p.9, 6-7, 3-9.
[16]雅克·比岱等编:《当代马克思辞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6页。
[18]甘丹·梅亚苏:《有限性之后:论偶然的必然性》,吴燕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7页。
近年来,常州加大力度整合政府、园区、企业和科研院所资源,多方合力共同推动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打造科技人才集聚、创新创业主阵地。截至2016年底,建设市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两站三中心)1 275家,其中省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610家,列全省第四;建设国家级众创空间累计4家,省级23家,市级27家;建设国家级孵化器、加速器累计18家,省级31家,市级74家。全市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为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19]Diana Coole and Samantha Frost(eds.),NewMaterialisms:Ontology,Agency,andPolitics,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2010, pp.4-16.
TheMarxist-MarxistFeminism:MethodandTopics:AnAnalysisBasedonTheGermanIdeology
FAN Chun-y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exts co-authored by Marx and Engels,TheGermanIdeology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elaboration of the “new world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GermanIdeologynot only provided the general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for Marxist feminism, a remarkable school of thought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Second Wave of Western Feminism, but also left behind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including the problems of two productions, natural division of labor, families and so on. Marxist feminism renewed the method and extended the topics based on the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classical theory, and presented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housework. In the late 1990s, Marxist feminism reviewedtheGermanIdeologyagain and tried to recall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facilitate the cultural turn of the Third Wave.
Keywords:The German Ideology, Marxist feminism, housework, materialist feminism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9)03-0011-07
收稿日期:2018-11-30
作者简介:范春燕,女,河南开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蔡永明]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德意志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恩格斯论文; 妇女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