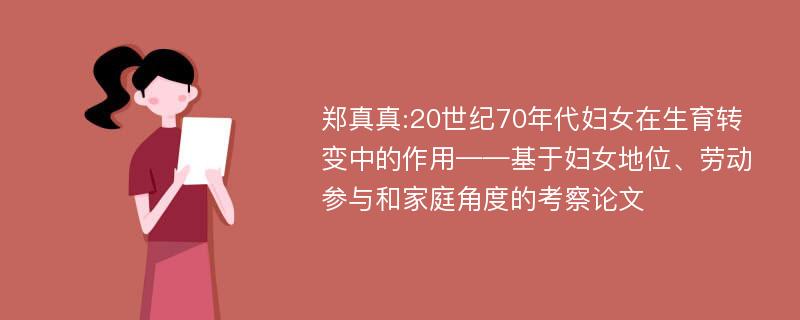
关键词:生育转变;妇女地位;劳动参与;性别角色
摘 要:中国人口的生育转变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目前生育转变已经完成,生育率稳定在较低水平。本文从妇女地位、妇女劳动参与和家庭的角度回顾中国女性在生育转变中的作用。中国快速的社会经济变化对城乡妇女影响巨大,而在家庭和劳动方面的影响则并不同步。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城乡妇女普遍参与集体劳动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为生育率下降做了充分准备,全国范围的计划生育工作则为生育行为改变提供了必要条件。传统家庭性别角色与城乡妇女普遍的劳动参与长久共存,使女性面对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冲突,既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也是当前持续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制定和评价公共政策时,应采取多方位视角,避免将问题简单化,特别在涉及生育相关议题时更应重视妇女的地位和作用。
一、引言:中国的生育转变和相关研究
人口转变是指人口从高死亡率、高生育率向低死亡率、低生育率的演变过程,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是实现人口转变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经历了死亡率降低、生育率快速降低、完成人口转变、生育率再次降低并长期稳定在低生育水平的过程,并于21世纪初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国家开展旨在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城乡倡导“晚稀少”(晚婚晚育、加大两胎间隔、少生优育)的同时,大力推广避孕节育服务。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81年的2.6,此后经过约10年的波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下。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生育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早生、多生、密集生育转向晚生、少生、生育间隔拉长。生育率下降和生育模式变化形成了中国21世纪以来一直稳定的较低生育水平,即使是近年来的两次生育政策调整也没有改变这种基本状况。中国的第一次生育率下降发生在农村人口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年代;长期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发生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时期;而生育政策的调整并未引起大幅度的出生人数增加,且在2018年生育人数明显回落。这三种现象虽然发生年代不同,但是否具有某些内在的联系呢?本文将主要回顾和分析第一次生育率下降,并讨论其影响因素与当前的低生育率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
生育率变化是人口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曾有不少学者从经济角度总结欧洲人口转变和生育率下降的规律。20世纪80年代对欧洲生育率下降的研究发现,仅用经济发展不足以解释生育率的变化和差异,尤其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时有很大局限。有学者总结了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的生育率转变过程,指出并不存在一个导致生育率下降的经济阈值,如亚洲6个国家(中国、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的生育率下降到4.5以下时的人均收入平均约为380美元,而生育率下降至相应水平时拉美国家人均收入接近1800美元。亚洲的生育率下降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个人等因素,政府的政策倾斜包括提供避孕服务和控制人口的压力则对生育率下降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1](PP 299-316)。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早期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分析,特别是讨论生育政策的作用;21世纪以来对中国省级和县级层面的生育率分析,则不约而同地展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下降的推动。但由于宏观指标的局限,尚未能完全理清不同时期的变化机制。已有研究的主要局限之一,是妇女地位相关因素在分析中的缺失,而对生育率下降的简单化解释可能导致对某些已知因素(如政策和经济相关因素)作用的高估。
人口学者寇尔(Ansley J.Coale)曾总结了生育率下降的三个前提条件:(1)婚内生育行为是理性选择,即夫妻之间是可以商议的,而且节制生育为社会规范所接受;(2)育龄夫妇认识到生育控制的社会经济效益,即有限制生育数量的充分理由;(3)育龄夫妇知晓和掌握节制生育的技术,即避孕服务可获得并有能力支付[2](PP 53-72)。其中前两个条件与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在家庭内部事务上夫妻可以共同协商也相当重要,因此妇女地位和自主有关键作用。第二个条件也意味着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的下降。高生育率的下降主要发生在三个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
领导者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占据着至为重要的位置,领导者的决策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作为目标,很多领导者将关注点放在企业生产销售上,忽视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价值。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需要创新,企业领导应该秉持现代化的管理思想,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作用,引进大数据技术,构建信息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领导层应该自主学习大数据知识,掌握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路径、应用策略等,确保大数据技术可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果。同时,领导层应该对内部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做好招聘管理工作,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具备先进性特征。
不同时期的国际研究一致发现,高生育率的下降最先发生在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群中,妇女地位改善和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对生育率下降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内有些应用县级截面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的负相关现象[3][4]。牛建林根据生育率降低的扩散理论,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分析了1975-1998年较长时间跨度的省级生育率变化及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关联,其中包括15-64岁女性的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比重。该研究发现,1990年之前,政策生育率、社会经济变量以及女性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比重与总和生育率显著相关,即生育政策越严格、政策允许生育数量越少的地区,生育率越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城市化程度越高、人口健康状况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地区,生育率越低[5]。不过,迄今为止,与妇女地位相关的指标并未在生育率研究中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已有研究主要是考察社会经济指标与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宏观因素如何影响夫妇生育行为的深入研究相对有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涉及家庭和个人层面(尤其是女性)在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仅依靠宏观指标难以深入分析。
现有关于生育率下降和计划生育的研究中,尽管也涉及女性的经济参与和社会地位,但主要是将计划生育作为外部干预,而妇女地位和妇女生活则被视为受影响的结果。在生育率降低的讨论中,女性作为主体的“缺席”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例如,总结欧洲生育率变化的欧洲生育研究项目几乎未涉及家庭系统和男女两性角色的变化[6](PP 3-14)。对22个国家/地区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项目成败的总结[7](PP 509-543)更为强调和关注政府和精英的作用,而女性即使被提及,也往往是作为项目的对象。但是应当看到,如果没有广大妇女对计划生育的自主需求和自愿响应,这些国家/地区的生育率很难在短时期内下降。中国也不例外。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1971年以后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和此后更为明确的生育政策,妇女的作用极少被提及。国内外有些研究应用社会经济等宏观指标为参考的反事实推演,估计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效应,显然过于简单化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对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和分析也极其有限。因此,有必要将女性作为主角对生育率下降进行深入研究,而不是仅将她们视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被动接受者,从而有利于全面地分析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机制。本文尝试从妇女地位、妇女劳动参与和家庭的角度,分析中国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生育转变中的作用,并希望这种分析视角有助于增强对当前低生育状况的理解和对未来生育率变化的把握。
由表1可以看出,伊利股份的净资产收益率从2012年的23.41%下降到2013年的19.77%,趋势同样变化的还有主营业务利润率和销售毛利率,在2012年到2013年均处于下降趋势,伊利股份2013年三季度净利大幅低于市场预期,仅增长28.6%,而市场普遍预期在60%以上,也略低于37.6%的预期。
二、反思:将女性视角引入生育率下降的分析
回顾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避孕服务的普遍可获得是寇尔总结的生育率下降三个前提条件中最为清晰可见的,即从1971年开始由政府提供、在全国推广的避孕节育免费服务。其他两个条件的形成则需要较长时期且更为复杂,但却是促成广大城乡妇女在政府提供服务后迅速采取避孕节育措施的关键。中国的生育转变,除了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健康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还与其他的国家政策(包括就业和人口流动等各方面相关政策)密切相关,更受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妇女在就业和教育方面变化的影响。农业生产劳动集体化和城乡妇女普遍参与集体劳动,直接促进了妇女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参与,不仅提高了妇女地位和个人收入,而且对降低妇女生育意愿、增强妇女在生育和避孕方面的自主性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城乡家庭的变化与不变,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作用或使这些作用复杂化。以下将聚焦中国女性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劳动参与、有酬和无酬两种劳动的冲突以及女性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从这些方面分析和理解中国人口的生育转变。
对宏观指标的分析也展示了妇女地位提高与生育率下降之间的关系。“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课题组”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评价各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指数以及综合指数的构建(以下简称综合指数)[23]。安徽、陕西、河北、江苏四省据此估算了本省2000年或2004年的市级相应综合指数。本研究选取自然增长率这个人口指标,观察其与综合指数之间的关联。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反映一个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指标,为当年出生人数减去死亡 人数与平均人口数之比。出生人数不仅取决于当年的生育水平,而且受到20年前的生育水平影响,如果20年前的生育水平相对较低,那么当前生育高峰期妇女人数就较少,出生人数也就相对较少。如果当前的生育水平低,出生人数就相对更少。在人口年龄结构没有较大变化的情况下,死亡人数相对稳定。因而低自然增长率不仅反映了当前的低生育水平,也与20年前(即20世纪70-80年代)的低生育水平相关。图1展示了市级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和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除个别点之外,综合指数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综合指数较高的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较低。
(一)两种劳动与生育意愿下降
在人口转变初期,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促成了家庭的生育需求降低,从而驱动生育率下降。而女性的生育观念和态度会直接影响生育行为。基于全球生育率调查的分析发现,在生育率下降进程中,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对促进生育转变起到了重要和显著的作用;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接受过中等教育最为关键[8](PP 31-35)。王丰等最近的一项研究考察了1976年世界各国女性初中在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两项指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的情况与全球趋势一致,即具有较高比例女性受初中教育和较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国家或地区,总和生育率相对较低[9]。不过对于中国而言,1958年以后城乡妇女的普遍劳动参与,是促进生育意愿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基本上在全球居首,由于当时的制度和政策作用,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参与虽然相关,但其影响的主要是从事劳动的性质而非劳动的参与。大部分女性通过从事有酬劳动有了收入,不仅增强了她们的自主能力,而且提高了在重要事务上夫妻共同协商的可能性,包括在生育和避孕方面的协商。与此同时,由于家庭中仍延续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女性是家庭中无酬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两种劳动形成的激励、挤压和冲突,共同促成了女性减少生育数量的强烈愿望。
报纸行业有着长期的发展基础,自身有着独特的优势,比如品牌意识、纸质的触感等。在新媒体时代,由于信息传播的限制较小,在信息的可靠性方面存在较大疑问,而这是报纸行业的优势所在。报纸编辑要充分利用优势,注重对新闻信息深层次的挖掘,突出自身的外形特点和风格。此外,报纸编辑应符合大众的审美特点,注重文字信息和图片信息的排版、设计等,利用自身权威性的特点,形成和新媒体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风格,提升报纸在受众中的影响力。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的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集体化的劳动和分配制度,但在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从农业释放出更多劳动力的进程中,农村女性并没有回到家庭,而是加入了乡镇企业的非农劳动以及稍后兴起的乡—城劳动力流动大潮。有研究从时间配置的角度分析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妇女非农就业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在经济发展处于不同水平的三个地区(上海、山西和陕西),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均抑制了农村妇女的生育行为,就业时间的增加首先减少与育儿直接有关的家务活动时间,而且就业对生育行为的作用强度远大于生育对就业的作用强度[20](PP 114-124)。21世纪根据不同数据来源的多项研究一致发现,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低于非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也相对较低。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降低了劳动力流动成本,沿海地区大量外资的引入产生了巨大的就业机会,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日益普遍,占到全国劳动力流动的40%以上。农村女性的劳动力流动,一方面是生育率降低的结果,即生育子女少的女性更有可能外出打工;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制度,促使农村妇女参与集体劳动,产生了与城市妇女非农就业相似的降低生育率的作用。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改变了农耕社会传统的“男耕女织”家庭分工,《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要达到“七年内每个农村妇女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到120个工作日”的目标,1957年妇女劳动日数达到社员劳动日总数的40%以上,至1965年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者达到70%[14](P 54)。由此可见,当时农村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是相当高的。
但是,农业劳动集体化并没有改变家务劳动由女性承担的传统做法,加之公共服务在农村极度缺乏,女性不仅要和男性一样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而且回家后仍要操持家务、照料子女以及赡养老人。尽管当时的数据资料和相关研究有限,但近年来在全国不同地区农村开展的社会调查研究,通过农村妇女的回忆,为我们理解20世纪70年代的生育率下降提供了可贵的信息。这些研究不约而同地指出,即使有些集体开办的托儿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幼儿照料负担,但农村妇女在白天普遍和男人一样出工,收工回家仍要为全家人准备饭食,只能利用晚上和劳动间歇做全家的针线活[15](PP 94-108)[16](PP 267-289)。白天的有酬劳动和工余的无酬劳动占据了农村妇女的大部分时间,无休止的家务和育儿挤占了她们的闲暇甚至休息时间,使她们感到负担沉重。在现有的记述中,无论南北东西,农村妇女对当时的回忆都可总结为一个“累”字,而且回忆者普遍认为女人比男人更辛苦。两种劳动的冲突是妇女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驱动力。
当外部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推动城乡妇女走出家门从事有酬劳动并有效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对女性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婚姻家庭也在发生变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明显提升,在家庭决策方面具有与男性相当的权力,但女性在家中自主权和决策权的提升与承担主要家务劳动长期并存,至今未变。例如基于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研究发现,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并未因其具有更现代的性别观念和在夫妻资源对比中占优势而减少[17](PP 367-373)。这种家庭内部关系的变与不变,即女性在拥有家庭决策权的同时还需要负担主要的家务劳动,构成了当年生育率第一次下降的推力。有学者认为,集体化时期的社会分配制度、劳动制度及社会性别分工制度之间的失调导致了农村妇女生育意愿普遍降低,为计划生育的开展提供了社会基础[18]。
婴幼儿存活状况的改善降低了农村家庭的生育需求,农村集体劳动、家务和育儿的三重负担抑制了农村妇女的生育愿望。但在生育意愿降低后,相应的避孕节育服务却没有及时跟上,多数农村地区基本无法获得避孕措施,妇女们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方法以减少生育或延长生育间隔[15](PP 158-160)。有研究揭示,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生育的理性控制已经普遍存在于中国家庭之中[19](PP 729-767)。因而不难理解,当1971年全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后,在宣传人口要控制的同时,政府提供的免费避孕节育服务遍及广大农村地区,受到了农村妇女的欢迎,“妇女并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她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与政策结成了联盟,自愿采取避孕措施”[15](P 231);尤其是生育子女多的妇女更有切身体会,她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当时计划生育工作的最坚定支持者[16](PP 267-304)。农村避孕率从计划生育工作开展之前的不到10%,上升到1979年的47.3%[20](P 133)。需要说明的是,这时政府主要是提供避孕节育服务,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行政命令和要求,虽然国家的号召在社区会对育龄夫妻形成节制生育的压力,但可以认为这个时期的避孕行为主要是妇女自主的。有学者曾总结了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时期避孕率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意愿生育率=6.4-0.067×避孕率(N=65,R2=0.69),即在自愿避孕的情况下,高避孕率意味着低生育意愿[21]。如果将此关系应用到中国的1979年,则当时农村的生育意愿略高于3,与20世纪80年代在广东、福建和西部地区农村的调查结果相似[22],已经大大低于20世纪60年代的生育水平(但离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二)妇女地位的提升与生育率的下降
至于几种证明方法,课前都有准备,但不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很多是以前的学生想出来的.课前设想只有思路3和思路4必讲,尤其是思路4,用向量的方法解决问题是一种意识,教材中虽有所涉及,但不够系统,需教师自己去总结.至于其它方法如果学生不提出来,可能略讲或不讲,一切取决于学生的需求.解题方法的呈现要有适当的时机,要有充分的理由,也就是说要讲理.
图1 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1)自然增长率,见国家统计局:《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区县汇总指标)。(2)安徽、陕西、河北、江苏的省辖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见谭琳主编:《1995-200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07页、第422页、第433页、第449页。江苏省为2000年指数,其他三省为2004年指数;从各省对指数的估算来看,有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即省间差异较大),但省内指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观察省内综合指数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之间依然具有明显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图1反映的是不同地区生育率下降的差距和妇女地位相对水平之间的关联,并不意味着未来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会引起的生育率变化。21世纪以来中国各地生育率已经逐渐趋同并稳定在较低水平(即平均一对夫妇不到两个孩子),其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亦会与生育率下降时不同。
文化补充法,简单来说就是对于在电影中被遗漏的一些文化现象做进一步的补充说明。特别是,当归化和异化都无法准确地表达影片里的一些文化现象时,此时就需要译者在适当的时间和位置是上,进行文化的补充,从而使观众可以更好地理解影片中的幽默点以及嘲讽点。
此外,女性受教育程度、劳动参与以及妇女家庭地位都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密切相关,但三种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相互关联却并不相同。关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国内外研究已经反复证实了在生育率下降时期,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下降越早、下降速度越快这一普遍规律。图2应用世界各国的女性初中在校率和总和生育率两个宏观指标,揭示了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田思钰应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分析了女性受教育程度的结构变化在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效应,发现在1941-1964年出生的城乡女性中,所有出生队列皆呈现出受教育程度与终身生育水平负相关的规律[24]。
图2 全球总和生育率与女性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1976年)
资料来源:转引自F.Wang,Y.Cai,K.Shen,S.Gietel-Basten,“Is Demography just a Numerical Exercise? Numbers,Politics,and Legacie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Demography,2018.
至于劳动参与,中国的特点是城乡妇女的高劳动参与在生育率下降之前和下降过程中基本没有改变,高劳动参与为生育率下降打下了基础,但开始下降时间和下降速度则主要受政策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这方面内容已经有学者做过深入研究[5]。
高生育率的下降取决于大多数夫妇生育行为的变化。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20世纪50-60年代的人民健康水平改善和60年代以后城乡妇女普遍参与集体劳动,均有效降低了城乡居民的生育需求,为生育率下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者在较短时期内减少了婴幼儿死亡;后者提升了妇女地位,增强了妻子在家庭中的协商能力和自主权力。但同时由于家庭内部传统性别角色的延续,也加大了妇女兼顾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包括育儿的压力。对应于寇尔总结的生育率下降先决条件,社会和家庭变化为夫妇生育行为改变做了充分准备,1971年开始的全国范围计划生育工作则为这种改变提供了必要条件,在国家号召下广泛开展的避孕节育知识宣传和免费服务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响应,可谓“水到渠成”。经过20年的准备和快速遍及中国城乡的计划生育宣传与服务,中国人口生育率得以在20世纪70年代快速下降。如果没有群众基础,任何政策都很难在短时期内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如果仅有现代避孕技术,而前两个条件不具备,避孕率将难以提高,生育率下降的过程将会非常缓慢。
表1 分年龄组家庭事务决策者(1990年或1991年) (占同龄组的百分比)
决定事务40-44岁45-49岁夫妻共同妻子为主夫妻共同妻子为主生育(农村)84.95.080.26.6生育(城市)79.314.878.015.7从事何种生产51.412.047.511.7住房选择/盖房61.05.858.87.4购买高档商品/大型生产工具70.87.966.39.7投资/贷款57.26.052.88.1孩子升学/职业选择67.77.763.67.9
资料来源:分城乡生育决策,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编:《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北京:万国学术出版社,1994年,第320页;其他家庭决策,见陶春芳、蒋永萍主编:《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第209-210页。
(三)小结
尽管对农村的观察发现,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在妻子当家的家庭里,夫妻双方更容易接受新的生育观念[25](PP 231-232),但有关女性家庭地位的大规模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开展,如1990年的全国妇女地位调查、1991年的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等。如果将家庭决策权力和家务分工作为衡量妇女家庭地位的主要内容,那么在家庭决策权力方面的既有调查结果显示了高度的一致性,即家庭重大事务主要是夫妻共同决策的结果。表1列出了1990年和1991年的两项调查结果,显示在40-49岁的人群(该人群的生育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中,生育决策和决定家庭重大事务为夫妻共同决策或以妻子为主的情况占相当高的比例(见表1)。在家庭事务决策方面,城乡差距不大;在生育决策方面,城市中妻子为主要决策者的比例高于农村。而在家务劳动的承担方面,1990年以来的所有相关调查结果都显示,以女性为主承担家务和照料的状况从未有明显改变。
尸身很快被抢食一空,天葬台上,只剩下一颗孤零零的颅骨,其他部位,一丝骨肉都没有留下。这是最吉祥的征兆,逝者的家人,远远地站在外围,望着台上干干净净的颅骨,笑着,泪流满面。
学习效果:所布置的相同做作业完成情况表明,两个班学生在基础知识部分成绩相近,但在知识运用上,(1)班学生对知识理解更加到位,能以问题为切点自主去探寻答案。
与全球生育率下降规律相似,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首先从城市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开始。中国城市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劳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工农业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为妇女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在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城市中的大多数劳动年龄妇女都被发动和组织起来,到国营单位和街道集体企业就业;20世纪70年代已经形成计划分配机制,城镇劳动年龄女性就业比例达到90%以上[10]。1982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中国城镇30岁以下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超过90%[11],这种女性劳动参与水平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的情形[注]中国在1964年和1982年之间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或全国范围人口调查。改革开放以后的劳动制度变动首先发生在农村。对于城市而言,1982年的普查结果应当最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在计划生育工作普遍开展之前,城市夫妇就已经产生了控制生育的意愿。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城市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高于农村人口,城镇妇女对计划生育服务产生了迫切需求。1963年的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把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列为主要内容之一,当年城市妇幼保健机构开始提供避孕节育服务。1964年城市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下降并低于农村,城市生育率降至4.4且在此后持续下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12](P 15)。中国内地城市人口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在20世纪50-70年代所经历的变化,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极其相似[13](PP 208-238),除了受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合力推动之外,妇女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和就业比例较高也是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不过,在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从高向低快速下降的20世纪70年代,城镇人口占比不到20%,总人口的生育率变动主要受农村的影响。
男女两性在劳动就业方面的相对平等和传统的家庭内部分工长期并存,使女性更多地承受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负担,且一直没有得到缓解。由于家庭中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导致的女性在照料和家务方面的付出,对女性生育决策产生了复杂影响,这是当年推动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无疑对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有重要影响。与此相关的是,由于很多农村社会存在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当生育数量减少时,为了保证家庭中有一个男孩,促成了对胎儿的性别选择和出生性别的人为干预。对于20世纪80年代末持续至今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本文不展开讨论,但需要指出这个问题与家庭中固化的传统性别角色同源。
三、讨论:性别视角在生育研究中的重要性
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口变化特点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数量达到峰值以后负增长并将延续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和负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生育率变化,因而生育率受到特别的关注。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和讨论更应当从性别视角对作为生育主体的妇女给予足够的关注,尤其是涉及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讨论。
当前中国已经处于低生育率时代,与生育率由高向低转变时期相比,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且更为复杂[26],更需要重视从女性的角度研究低生育水平现象,研究女性对于用自己的时间、精力、事业、收入来交换育儿这种“全天候工作”的意愿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用性别平等红利解释低生育率现象[27],认为有些国家能走出超低生育模式的关键,在于较早的工业化发展起始年代和时期较长的性别平等历程,早发展国家更早享受性别平等红利,后发展国家虽然达到了相似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但在性别平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因而不能有效地提升超低生育水平,如东亚和南欧一些国家。也就是说,人类发展指数高并不意味着就自然能将生育率提升至接近更替水平,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
当前中国男女两性在劳动就业方面相对平等,但家庭内部的分工长期保持传统模式。虽然女性的家庭决策权和自主权很高,但她们仍一如既往地承担着主要家务和育儿劳动。近年来这种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例如最近一项有关时间利用的研究显示,与2008年相比,2017年中国家庭内部已婚男性和女性的时间利用发生了明显变化,男性劳动参与率略有上升,而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男女两性劳动参与率差距从9.8个百分点扩大至15.7个百分点;同期对于男女双方都就业的家庭而言,虽然无酬劳动时间均有缩短,但男女两性的差距却在扩大,女性从事无酬劳动时间与男性相应时间之比从2.76上升至3.08[28](PP 87-111)。女性面对的两种劳动的冲突如果得不到有效缓解,不仅对当前的低生育率有重要影响,而且会影响未来人口变化。
回顾20世纪70年代中国生育率第一次下降时期,国家控制人口增长的宏观目标和广大妇女少生的个人愿望相契合,同时由政府提供的避孕节育服务给了她们更多选择,合力推动了当时的生育率下降。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政策和措施,即使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包括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和儿童死亡率下降等,尚不足以对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生育率下降做出令人满意和信服的解释。如果不能将家庭内部的变化(与不变)和妇女地位纳入分析,很可能导致对政策干预和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简单化认识,而忽视了影响生育行为的复杂因素尤其是家庭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因素。认为仅靠政策变化可以直接迅速改变现状,将有可能对未来发展趋势产生错误的判断或误导公共政策的制定。与生育率降低相伴相生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延续至今,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家庭内传统性别偏好的顽强存在,意味着全社会实现性别平等任重而道远。
对于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现有可获得的数据资料有极大的局限。由于历史数据的缺失,只能利用回顾性调查资料综合分析,很难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定量地验证1971-1979年生育率变化和女性家庭地位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说明及时收集可靠信息的重要性,并提醒我们对某个方面尤其是对缺少主流话语群体的忽略(如在生育转变过程中对女性的作用缺乏足够重视)而留下的历史遗憾;另一方面也推动我们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和相关质性研究如口述史研究,超越单一视角和固定模式分析历史上的人口变化。数据缺乏并不意味着历史是说不清的“黑匣子”,更不应囿于数据条件而将历史演变进程简单化。这方面数据和研究的相对匮乏更说明需要摆脱数据和方法局限,进行更为深入和周密的思考,开展更多调查研究,应用更为灵活多样的方法去挖掘,分析和证实这段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化及其多方面的影响因素。
回顾历史,不仅是为了把历史讲清楚,更是为了解释和认识当前。在制定和评价公共政策时,应该采取多方位的视角,避免将问题简单化,例如从社会性别和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当前的低生育率现象[29],还需要关注家庭变迁和性别平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下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在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和项目时,应综合考虑人口变化可能带来的挑战及其对女性的影响、女性在人口变化中的独特作用以及女性面对错综复杂的变化和挑战时的特殊困难与需求,从而制定积极有效的公共政策,为女性提供更多选择,以多种更有效的方式支持女性发展,使她们有能力应对挑战。
[参考文献]
[1]Caldwell,J..The Asian Fertility Revolution:Its Implications for Transition Theories[A].In Leete,R.and I.Alam.eds..TheRevolutioninAsianFertility:Dimensions,Causes,andImplication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2]Coale,A..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Z].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Liege.Volume 1,PP.53-72,1973.转引自:Weeks,J..Population:AnIntroductiontoConceptsandIssues(6thedition)[M].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
[3]蔡泳.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国际经验和江浙的比较[A].曾毅、顾宝昌、郭志刚等.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王良健、梁旷、彭郁.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县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5,(3).
[5]牛建林.从分省生育率看我国生育转变的地区差异[A].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13: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再平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McDonald,P..Fertility Transition Hypotheses[A].In Leete,R.and I.Alam.eds..TheRevolutioninAsianFertility:Dimensions,Causes,andImplication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7]Robinson W.and J.Ross.Edts..TheGlobalFamilyPlanningRevolution:ThreeDecadesofPopulationPoliciesandPrograms[M].The World Bank,2007.中译本:彭伟斌等译.全球家庭计划革命:人口政策和项目30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8]Rele,J.R.and I.Alam.Fertility Transition in Asia:The Statistical Evidence[A].In Leete,R.and I.Alam.eds..TheRevolutioninAsianFertility:Dimensions,Causes,andImplication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9]Wang,F.,Y.Cai,K.Shen,S.Gietel-Basten.Is Demography just a Numerical Exercise? Numbers,Politics,and Legacie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J].Demography,2018.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8-0658-7.
[10]蒋永萍.建国50年中国城市女性就业的回顾与反思[A].彭希哲、郑桂珍主编.社会转型期中的妇女就业[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0.
[11]Maurer-Fazio,Rachel Connelly,Lan Chen and Lixin Tang.Childcare,Eldercare,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in Urban China,1982-2000[J].TheJournalofHumanResources,2011,46(2).
[12]常崇煊主编.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13]Coale,A.and R.Freedman.Similarities in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China and Three Other East Asian Populations[A].In Leete,R.and I.Alam.eds..TheRevolutioninAsianFertility:Dimensions,Causes,andImplication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14]罗琼主编.当代中国妇女[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15]胡桂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西村妇女:1950-198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6][美]贺萧著,张赟译.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7]杨玉静、郑丹丹.婚姻家庭中的妇女地位[A].宋秀岩主编.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
[18]刘筱红、余成龙.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变化:制度系统性调适视角[J].妇女研究论丛,2018,(1).
[19]Zhao,Z..Deliberate Birth Control under a High-Fertility Regime: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China before 1970[J].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97, 23(4).
[20]朱楚珠、彭希哲主编.妇女参与的行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1]Pritchett,L..Desired Fertility and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Policies[J].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94,20(1).
[22]风笑天、张青松.20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5).
[23]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课题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A].谭琳主编.1995-200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4]田思钰.女性教育结构与终身生育率——基于率分解法的结构效应分析[J].人口与社会,2018,(2).
[25]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26]郑真真.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行为及影响因素[A].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6中国人口年鉴[Z].2016.
[27]Anderson,T.and H.Kohler.Low Fertility,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and Gender Equity[J].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2015,41(3).
[28]杜凤莲、王文斌、董晓媛等.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9]计迎春、郑真真.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低生育率[J].中国社会科学,2018,(8).
TheRoleofWomeninFertilityTransitioninthe1970s:BasedonAnalysisofWomen’sStatus,theirLaborParticipation,andFamily
ZHENG Zhen-zhen
(InstituteofPopulationandLaborEconomic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028,China)
KeyWords:fertility transition;women’s status;labor participation;gender role
Abstract:Fertility transition in China mainly took place in the 1970s. A sustained low fertility has been for decades after the transi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women in fertility transition based on analysis of women’s status,their labor participation,and family. The dramatic social-economic changes have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women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China,however the influence to family are lagged behind.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decrease,women’s labor participation in urban and rural,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status,which are pre-conditions for fertility decrease,and the nationwide family planning programme provided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behavior change on childbearing. The coexistence of very high labor participation of women and their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in the family which caught women between paid and unpaid labors was one of the main drivers to fertility drop in the 1970s,and it is also a major determinant of current low fertility. A multi-facet framework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policy so as to avoid oversimplification,and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role of women and their status regarding issues related to fertility.
作者简介:郑真真(1954-),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人口学。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9)03-0005-09
责任编辑:含章
标签:生育率论文; 妇女论文; 中国论文; 女性论文; 家庭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3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