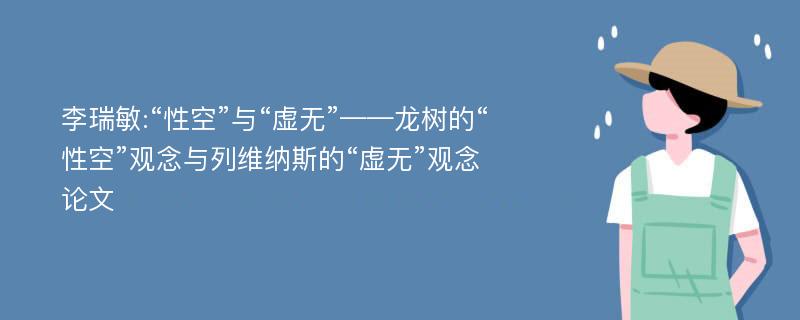
内容提要:“性空”是龙树中观学的核心观念,这一观念与当代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虚无”观念有某种思考理路上的共通性,同时也在共通性之下掩藏着巨大的差异性。本文以“缘起性空”、“中道”与“实相涅槃”勾勒出中观“性空”的基本理论框架,以“莫须有的虚无”、“别于存在”与“为他者的自我”分别考察列维纳斯对“虚无”观念的基本理解,并在行文中对两者进行了依次对比。佛教中观学与列维纳斯哲学基于对差异性的共同强调,在对自我与他者关系问题的思考上也呈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在相似的表面之下佛教思想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依然是根本的。
关键词:龙树中观 性空 列维纳斯 虚无 别于存在
“性空”与“虚无”分别是佛教思想与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佛教义理的明辨水平与对哲学真理的把握程度。而对这两个概念的比较既有助于我们从来自他者的视角理解它们自身的内涵与独特性,也同时将使我们对东西方智慧的共通性有所体会;因为籍由对差异与同一的共在性的明辨所收获到的将不只是悖谬性的不可消除,而也总是意味着发现一种借以理解乃至超越悖谬关系之道路的可能。
龙树中观学的“性空”一举破斥了当时及此前印度思想中“执有”与“偏无”两种理论的不足,以“缘起性空”与“中道性空”的说法将佛教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也开创了历史上大乘佛学研究的热潮。法国当代哲学家列维纳斯在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中以现象学的方式对“虚无”观念在哲学中被理解的方式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与某种程度上的“解构”,他的分析对于解蔽哲学史中通常的“虚无”之理解洞见十足,而他本人对“虚无”独辟蹊径的理解路径尽管以反哲学传统的姿态出现却依然满载着独属于西方哲学的见地。本文试图对龙树的“性空”观念与列维纳斯的“虚无”观念进行比较,其要点既在于澄清“性空”与“虚无”的内涵之别,也在于对“性空”与“虚无”各自所属的概念系统的差异性即它们的“范畴性差异”有所揭示,尽管它们的差异是如此根本,以至于根本没有一个现成的共同范畴可以用以衡量它们。但是龙树与列维纳斯在“性空”与“虚无”之名下所做的某些卓有根本性的思考却又是不无相通之处的,甚至有某种诉求上的默契性。对“性空”与“虚无”的差异与共性的辨析对于理解东西方思想对于彼此而言的他者性与共通性并存的关系,以及对他们是否具有启发出彼此新的可能性的问题进行进一步追问,都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无疑是它们之间的共通性使它们有理解对方的欲望,然而更加确定的是唯有他们之间的他者性才让他们真正蕴含着改变对方之未来的潜能。此外,列维纳斯的哲学有着显而易见的犹太教渊源,在犹太教重视为他人而生活的观念里包含着强烈的对绝对他者①此处的“绝对他者”即包括“上帝”也包括“他人”,在列维纳斯的哲学里,“他人之为绝对他者”与“上帝之为绝对他者”是不冲突的,他从未否认过上帝的存在,关于列维纳斯哲学中上帝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参见列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7-277页。的爱,这在列维纳斯的哲学中有极为鲜明的体现,尤其在自我与他者关系问题上,而这一点与中观学的修行目标“实相涅槃”有着某种思考理路上的亲缘性。不过本文对“性空”与“虚无”的比较最终却仍将落脚于对佛教思想与西方哲学在自他关系理解上于若干共性之下的本质性差异的揭示。
一、“缘起性空”与“莫须有的虚无”
“空观”居于中观学的中心,“观”即是观看的意思,而“所观”便是“空”的义理。中观学的“空观”是贯彻着中道精神的“空”,它本质上既否定“有”也否定“无”,反过来也可以说既肯定“有”也肯定“无”,表现在理论上就是“缘起”与“性空”的相即不离。“缘起论”是佛教的根本思想,因为正确地阐明因果现象就是对人生与世界真相的说明,而中观特色的缘起论便是“缘起性空”。龙树认为释迦提出的缘起论是全面的,既不着重强调“有”也不偏向说“无”,而是“非有非无”或者说“有无相契”的,所以在龙树《中论》的第十五品《观有无品》中有:“若人见有无,见自性他性,如是则不见,佛法真实义。”②龙树:《中论》,见《大正藏》第30 册,第20页上。意思是说,只看见有无的对立与只看见自他之间的对立都是不认识佛法的观点,因为佛法不是混淆有无而是超越有无。对有无的讨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无是因果的首要要素,而因果又是缘起的重要内容,在《中论》第二十四品中有如下“三谛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③同上书,第33页下。在中观学看来“缘起”即进入“假名”,而“性空”又必须依“缘起”,因而“性空”与“假名”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真理的两个不同层面,离开“缘起”谈“性空”或离开“性空”看“缘起”都是无明,始终综合上述两个层面来理解问题才算领会到了中道的精神。所以,中观学的“空观”既在“缘起性空”中得到概括,也在“中道性空”中得到诠释,“缘起空”与“中道空”一起构成了中观学的基础同时也是核心理论。对“缘起”与“性空”之关系的思辨性理解说明了事物在时空经验中的因果实在性与其本质上的不实在性都属于事物的本然性样态,也都是真理性的,而中观学所致力于阐明的实际上正是现象与本质的共在性、不可分性。可见,中观的“空”并不是否定事物的存在,而是要表明事物是“无自性”①此处的“自性”大致包括绝对性、整全性(不可分性)、不灭性三层含义。的,即事物是处于关系中的、没有恒定实体的;但是,中观的“空”又不是相对的,“空”是绝对的空,“空”作为一种客观真理与真理性认识都是“实在的”。所以,一方面“空”是无自性,因为“自性化”往往意味着“实体化”,然而世间万物均处于缘起之中、都是关系的产物,并无不变的实体;另一方面“空”也是一种否定偏见的方式,不但否定“有见”之无明,也否定“无见”之无明,而且与对佛教的通俗理解不同,中观学认为“无见”比“有见”危害更大,如果说执着于“有”是误入歧途,那么执着于“无”便是无可救药了——比如兔角龟毛式的“恶趣空”②“恶趣空”是对小乘部派佛教方广部的“空”观的一种概括,指一种“纯粹的无”或“没有”。便是中观学首要反对的观点,因为这种“空”没有任何意义,一切因果关系都处于绝对的运动之中,一切真理也只能存在于生灭变化的形态之中,离开生灭变化“空”也就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性空”是万物绝对的真理,或者说“性空”这个真理是有绝对性的。
中观之“空”的“非有非无性”不免让人想到西方哲学中的虚无观念。列维纳斯在《上帝·死之与时间》中对虚无在西方哲学中被思考的方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西方哲学从没有接近过真正的虚无,因为哲学一直依据与存在的关系来定义虚无,虚无如同包围着存在之岛屿的大海,总是一再地与存在一同走向更高的同一,比如上帝概念,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等。如此一来,虚无其实就变成了存在的一个特殊阶段或历程,虚无即“非存在/不存在”(non-being),“非存在/不存在”(non-being) 与“存在”共属于“更高的存在”,这其实是对虚无的一种变相取消。③列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87页。列维纳斯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思考虚无问题的方式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被奠定了基础,即存在总是是介于完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纯粹的虚无”(非存在) 与“纯粹的存在”一样都是一种存在的例外状态,然而正如列维纳斯所指出的:“实际上,‘纯粹的存在是纯粹的虚无’ 这一命题有一特殊的同一性层面:这是一种思辨的同一性,它全在于它会变化。存在与虚无是在变化中同一的。对立者的吻合并不是一种行为状态,而是作为变化而产生的。对立者的同时性便是变。”④列维纳斯:《上帝·死亡与时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2页。列维纳斯认为黑格尔与海德格尔依然延续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思考虚无问题的方式,这是一种思想的惯性使然,不过无论黑格尔依据存在来设想的虚无,还是海德格尔将死亡与虚无相等同的思路在列维纳斯看来都不可取,因为虚无既不是“非存在/不存在”(non-being),死亡也并不一定是虚无,虽然死亡肯定意味着某种终结性,但是从死亡与虚无之关联的角度来理解虚无却未必通达。在列维纳斯的理解中死亡并不是虚无,死亡只是绝对的未知与不可能相遇的他者,或者说死亡是不可把握的非主题性的事物,死亡的非经验性与永远尚未来临的他者性使之标示出一种界限,这个界限常被当作存在与非存在的界限,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肯定死亡就是“非存在/不存在”(non-being),在物质上死亡是一堆依然处于流转中的要素,在精神上死亡是不可触碰的绝对未知,归根结底死亡只是他者。①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8-134页。本文将之解读为,在列维纳斯看来黑格尔与海德格尔都把死亡肯定为虚无实际上并没有完成一种哲学上的证明,死亡只是无法被哲学理解以及以哲学的方式被显现但同时也无法消除的现象,将死亡视为虚无不过是哲学的将计就计,死亡只能是个体性的,总体从不会死亡,他们只有变化。然而,死亡与虚无的联姻确乎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一大焦虑之源,列维纳斯指出“虚无挑战着西方思想”,虽然“哲学从未接近过真正的虚无”。②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7页。似乎唯一能够肯定的便只有“虚无是‘别于存在’ 的”,而“别于存在”不可说、“别于存在者”是他者,这等于宣告“关于虚无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未知与陌生交织的暧昧性”,③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8页。除此之外竟别无可言。然而从列维纳斯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提出的原创性概念“il y a”④“Il y a”的意思是“无存在者的存在”,是列维纳斯思考存在问题的重要概念,详见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第63 到73页。中,我们却能看到他对虚无的一种别样地“接近”。
说到这里,《易经》64卦排序的缺陷不言而喻。《易经》64卦排序,从表面上看符合“两两非覆即反”规律,但做出64卦序奇偶(阴阳)综合图,则出现了奇数(阳)偶数(阴)无对称分布规律,杂乱无章,不符合“阴阳就是数量,数量就是阴阳”的分布规律(参见后面图6《易经》64卦卦序奇偶(阴阳)分布无规律),这就是《易经》64卦排序的缺陷之所在!
中观学对本质与现象之差别的“空化”与现象学所追求的“回到实事本身”颇有相似之处。而列维纳斯对虚无的解构与重新赋义也有其实践的或者说伦理的目标,这个目标在一种“为他者的自我”的主体性哲学中被诠释,这也是对“伦理第一哲学”的一种别样表达。列维纳斯所论证的能够为他者主动承担责任的自我,其主旨在于揭示出主体的被动性先于其主动性,主动之主体肇始于被动之主体,宾格之我先于主格之我。其中,“面对他人的自我”之所以是虚位以待的并不是基于道德上,也不是基于心理上,而是基于在“时间上”自我总是位于他者之后的,因为自我之为自我即自我的主体性所在正是源于他人的前来照面,而他人是无端地到来的,对我而言他人总是突然到来的。这里的“时间”可以视为一种关系的表达,时间本身就是由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运动构成的,他人在时间上的在先正是他人在他我关系中的优先性的一种表达,也是他我关系之不对称性的重要原因——我在时间上总是落后于他者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人的无故前来,我就只是潜在地具有主体性,或者说我的主体性尚未落入时空之中。
二、“中道”与“别于存在”
从上面的资料,我们不难看出,得舌癌一定是一个长期的慢性刺激的过程。无论如何,舌头咬伤一个月是绝对不会导致癌症的,其理由是:
列维纳斯的作为人质的“虚位以待的自我”、“宾格之我”、“能够替代他者的自我”、“被他者召唤的自我”等说法其实是极度相似的,①[英] 柯林·戴维斯:《列维纳斯》,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101页。而且更具体地说,列维纳斯所说的为他者之责任的非反思性,即自我并非是在用理性反思出“我应该”之后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的,而仅仅是他者之到来本身所带来的震惊已经足以促成自我的责任,这其实终归是对一种“非反思性的理性”的强调——“为他者的自我”与“实相涅槃”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为他者的自我”试图揭示伦理生活的非知识性,以及伦理处境的非选择性与非反思性;而中观学在自他关系的理解中要求我们首先不对他者做判断,而是回到自他缘起的真实性,因为自他关系永远是在对待相中展开的——至少在涅槃之前如是——所以“进入时间便是亲近他者的唯一方式”,“实相涅槃”一定是在世间的。两者无疑都彰显了他人的重要性,前者以证入觉悟之境来面对他者,后者以承担责任来面对他者,它们都是在存在之中来彰显神圣性的真实存在。可以肯定,中观学在印度思想史上的出现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提出的众生平等观念不是一种空洞的思想,而是饱含着对实体论哲学所导致的种姓制度的理论批评;而列维纳斯开启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哲学反思的新方向,一种反传统的立场,一种将伦理不再定位于关于伦理学的知识,而是以伦理生活的实质内容作为伦理与哲学研究的方向——伦理就是与最挑战自我的那些事情的面对面,就是对如何处身于与他者的关系之中而既不异化他者也不异化自我的一种具有绝对实践性的活动的研究。另外,列维纳斯对差异性的关注使他者在新近的哲学研究视野中得到重视,使哲学与佛学研究的关注点有更多的接近,比如在缘起条件下自我任何单独的趋向都是自利,在中观学看来自利与利他是不可调和的,要利他从而自利,甚至要以他为自来作为达到自利的道路,而以他为自就是列维纳斯的“虚己”,通过利他来利自与主流的西方哲学、伦理学观念即以自利来利他是完全相反的思考方向,在这一点上,龙树与列维纳斯的相遇是跨时空的。
《中论》的主要内容除了独特的“性空”理论之外,就要数对“中道”思想的推崇。如上文已经引用的《中论》第二十四品中的“三谛偈”所表明的,“缘起”与“假名”的统一解释了无论自我还是世界都是诸缘和合而生,所以并不存在某种同一的、不变的实体,但是诸缘和合而生的自我与世界的存在与变迁却又呈现出某种规律性,但是与其说存在着某些作为真理的规律,毋宁说“空”才是所有规律之规律,“空”表明了一切事物都在运动流转之中,因而一切有都是“假有”、一切名都是“假名”,假与空的不离性解释了执取有与执取空任何一端都是不可取的“边见”,只有走向“中”才是化解对立与理解真理的道路,这也是中道的应有之义。在此足见“中道”与“空”并不是两个平行的理论,毋宁说“中道”就是对如何贯彻“空”的方法论探索,龙树比小乘部派佛教对“空观”的深入之处就在于其“有空观而不着空观”的理解角度。所以中观学也可以说是“中道空观”或“以中道观空”,吕澂对此有很好的说明:“ ‘中’ 是从‘空’ 发展出来的,是对‘空’ 的进一步认识,由此而连带着产生‘假’,又综合‘空’、‘假’ 而成立‘中’”。①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可见,中观的“空”不是极端的否定——比如它对持极端否定观点的“恶趣空”是坚决反对的——而是以破为立有所肯定的,它的目的在于用中道方法否定掉不正确的观念,以让正确的观念为之显现,这与现象学研究中通过“去弊”而得“澄明”一样,中道是一种真理也是一种有目标有层次的“去弊”方法,“中道”也同现象学一样是真理与方法的统一。中道之所以将否定作为主要手法,是因为龙树认为用概念认识世界是有限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但是认识又离不开概念,所以最高级别的知识只能用否定法来接近。事物有真相,但是不能分别,所以《中论》不仅对某个概念或观点进行否定,更重要的是选取了若干重要的对立概念进行分析,以展现那些基础概念中就具有的深刻的固有矛盾,如《中论》开篇所说的“八不”:“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②龙树:《中论》,见《大正藏》第30 册,第1页下。对生、灭、常、断、一、异、来、出这八个基本概念的否定,所得出的就是性空、假有、无分别等佛教真理,这段经文也常被概括为“八不中道”。其实除了“有无中道”外,佛教中还有“断常中道”、“无记中道”、“苦乐中道”等,释迦创立佛教时已经提出中道,但是在中观之前的教派中都理解得不够深刻和系统,直到中观学派出现后才将中道作为重要思想并一举将之发展到一个高峰。
中观学对“性空”的思考有其最终的实践目标,这个目标也是大乘佛教修行的终极解脱境界即“实相涅槃”。要理解“实相涅槃”要先理解“实相”概念,“相”一般指“现象”之意,但这里的“实相”是指缘起的“性空”之本质与“假有”之现象的结合,也可以说是“缘起“与“性空”的不离所构成的真相、真理。也可以说“实相”就是世界的非有非无性,是“空”与“有”的共在与并存,它既指事物依缘起而在的真实性,也指事物的本质、状态或性质上的“空”,但是这里的本质不同于实体论的本质,它不具有根本因或本原的性质。更进一步理解,“实相”不但指存在的非有非无性,就连“非有非无”的名相本身也都不过是以诠表“实相”的戏论罢了,它们最终都是认识所暂时借用的“道具”,“实相”终究乃是一种无可言诠的存在之真相,“实相”乃是“无相之相”,是绝对的“相”。“实相涅槃”是中观学独特的涅槃观,“涅槃”是经过一系列的观“空”过程后所达到的一种认识“实相”的境界,这个境界寂灭了一切分别,譬如有无之别、生死之别等。中观素有“涅槃即世间”的说法,就是指“实相涅槃”不离人间、不是与凡人世界隔离的一种生活状态,虽然涅槃只能发生在生死之间,然而涅槃之后便不再被生死问题困扰,这个过程具有不可逆性,因为虽然必须从世间证入涅槃,然而涅槃之后虽不离世间却再也不会回到世间——因为“实相涅槃”即终极解脱与步入无生无死之境。“实相涅槃”表明世界没有实体也没有自性但却有“实相”,而中观主张的修行活动是直接面对关系的,时空中的自他关系始终是“实相”的重要部分,因而涅槃就既包括了智识上的也包括了德性上的,中观派尤其强调涅槃是与世间有关联的一种精神境界,且这种境界既是可追求的也是可能得到的,它就存在于世间之中。大乘佛教常用“悲智同体”来描述涅槃之后的状态,这正是中观的主张即“慈悲与智慧的并行就是觉悟”,对于觉悟者来说世间从此不再有差别——当然也不再有生死,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一种终极性的自由。总之,“实相涅槃”的核心是指一种认识到世间本来面目的精神境界,“涅槃与世间二者无分别”、“诸法实相即涅槃”、“即世间即涅槃”也都表明了涅槃只能作为一种大智的境界、状态而存在,它是凭借“在此岸”而获得的一种“彼岸性”。可见,中观的修行实践目标既不是虚无主义的,也不是相对主义的,它是一种超越的智慧,中观学是一种极尽所思用“双非”的方式空化所有的概念与理论预设,最终达到让现象与本质在意识中进入一种无分彼此的状态从而走向更高的理性,以最终达到与最高之真实的“冥契”——不过这一点都不神秘,反而彰显了理性的高度。某种程度上说,中观学是一种如何直面欲念的知识,它在知识学上的价值非但不是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帮手,相反是对它们的深刻批判。
在各部总长任用部员的时候,由于并无规则可循,全凭总长意志,故而乱象丛生。之初,裁减人员风声先起,各部当差人员皆有不同程度恐慌。交通部裁减了一批告假人员,教育部、内务部、外交部、理财部等亦有为节财而裁减员额之风声,“其中恐慌尤以旗人及守旧派达最高之度,新人物尚能勉强自持,不呈露张皇之状况”。前清部员中旗人、守旧派及新人物面对裁减时各具不同心态,此况既符合人事更迭之际的常理又非常耐人寻味。
“别于存在”与中道思想对理性之限度的反思是有相通性的,无论“中道”还是“别于存在”都在否定中表达了肯定,中道以“性空”肯定了世间“缘起”的真实,而列维纳斯以“别于存在”这一表达肯定了存在的伦理性价值与意义,并且他们都在否定中表达了对一种更高阶的理性的恳切追求。正如列维纳斯所言:“通过一种否定的人类学而隐蔽在主体性中的倾向——寻求一种超验的人的概念,寻求一种先于存在的思想——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或者一种简单的游荡,而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发现这一先于思想之存在一样不可避免。”①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2页。中道思想对否定辩证法的自觉运用与列维纳斯用“别于存在”来解构传统哲学和探索伦理之内涵的方式亦不乏异曲同工之意,不过有相似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选择不等于他们的思想就是相近的,根本性的差异依然在他们对自他关系的理解上显示出来。
三、“实相涅槃”与“为他者的自我”
无独有偶,列维纳斯也喜欢用否定式的哲学表达,尤其是在《别于存在或本质之外》中,其题目中的“别于存在”便已经是他最常用的一种否定表达方式。如果说在《总体与无限》中列维纳斯还是从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异质性的角度来看自他关系的——比如爱欲关系,但是在《别于存在或本质之外》中他不但将重心从对他者性的论证转向对一种新的主体性的建构,也试图尝试一种新的论证他者性的方式,这种论证也将对异质性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英国学者柯林·戴维斯对列维纳斯的著作文本中对否定方法的多重运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的分析十分有见地,以他的论证为重要参考,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列维纳斯的否定式哲学写作:首先,《别于存在或本质之外》的写作方式或者说运思方式充满了实验性,比如大量的连字符以及自创性复合词的使用,再加上对悖论性表达的钟爱使整个作品从语言到意义层面都充满了不稳定性,仿佛它们随时会破裂和自我反对;其次,“别于存在”意在指出某事物不同于存在、不可以用存在范畴进行衡量,其本身的内涵极具模糊性,然而这个表达却在全书中被使用得最多,上帝、虚无、善、恶都曾被列维纳斯拉入“别于存在”的阵营;最后,列维纳斯在该书中分外地强调“说”与“所说”的区别,它们作为语言表达的两个方面互不分离但各自具有重要意义,他在极力表明他的哲学文本不只是一种“所说”,而更是作为“说”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哲学意义——即他时刻想表明他对自己的哲学写作的表达限度有一种异常清晰的自知,他认为承认哲学的有限性是当今时代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①此处相关内容详见[英] 柯林·戴维斯:《列维纳斯》,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101页。纵观整部作品,可以说列维纳斯在“别于存在”之名下致力于描绘的东西正是一种超出了一切经验和认知手段的东西,他用日常语言中最为熟悉的悖论性表达如“与一张面孔相遇,它同时给予和隐藏”、“仿佛空虚是充实,仿佛沉默是噪音”②[英] 柯林·戴维斯:《列维纳斯》,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4页。等等企图让人对熟悉的经验给予一种陌生化、严肃化的关注,以好让其中的矛盾意味充分地被释放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将列维纳斯的表达方式仅仅视为一种对游戏性语言的特别爱好无疑将大大错失他的本意,他有无比明晰的哲学目标,即论证出语言的、逻辑的、知识的限度性,以期证明在人类最为根本的伦理生活中非逻辑力量的不可忽略性,可以说,他实际上是籍由否定理性的限度来肯定“非理性”(感性、情感性等) 的重要性。
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列维纳斯以对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论差异”的反思为切入点来重思存在,其中隐含着一个观点即虚无不是“非存在/不存在”(non-being) 而只是“别于存在”(otherwise than being)。⑤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62-73页。本文将此观点解读为“与其去追问彻底绝缘于存在的‘虚无是什么’ 不如转而接受‘虚无是对超验性的一种经验’”。因为与其将死亡视为虚无或凭借死亡来设想虚无,不如更加决绝地从时间性问题出发来思考虚无。虚无与永恒有某种类似,它们并不是时间的终结,也不完全显露在与时间的关系中,虽然虚无总是、也总要与时间关联起来才能被设想,但是严格说来虚无是非时间的。某种程度上虚无是对“无存在者的存在”⑥详见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莫须有”的,“il y a”就是对“无存在者的存在”或“莫须有的虚无”的一种临近性的体验,然而虚无能、也只能在这样的体验或设想中勉为存在,纯粹的无不但没有还是一种错误的概念或者说一个无意义的追问:“虚无是一种错误的概念,死亡并不等同于虚无”。①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9页。列维纳斯所反对的其实是将虚无与存在进行一种同一化的连结,进而对虚无进行一种时间化的理解,如“虚无是时间性的终结”即死亡。无论“虚无不该在与存在的关联中设想”还是“死亡并不是虚无”都是要力求彰显出虚无的他者性,这种他者性是如此根本,以至于在存在与时间中只能有所体会而无法对之命名或所言太多,甚至以逻辑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虚无只能导致南辕北辙。这与中观的“空”观恰好不谋而合——它们都反对“绝对的空无”或者说“彻底的虚无”,如中观也反对“恶趣空”——但是他们同时都坚持空与虚无的实存性或价值意义,空与虚无都存在于对存在的体验与领会中,就这一点而言空与虚无又是真实存在的。再者,“空观”实为“观”空,观空乃是一种修智,这种修智活动抛却一切预设,始终无所肯定且与万物不离,无论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都与“空“相即不离,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而列维纳斯一再以黑夜、失眠来比拟“il y a”的临近性与距离感的双重纠缠,旨在表明对超验性事物的所有探索其实仍都发生在存在之中,它们是存在的裂隙而不是隔离于存在的某种事物,绝对他者性的存在就是“存在之外”,“存在之外”是对超验性的理智直观,“存在之外”能够给予存在以启发。“空”与“虚无”既不是任何物质实体,也不是任何精神实体,同时也反对用语言、概念或范畴对它们进行任何实体化与肯定型的理解,它们保持自身的方式就是保持完全的超验性,即便它们有时或会在现象中以犹疑闪烁的方式被“体验”,这不同于也更胜于将现象视为显现与遮蔽之双重运作的观点,而是更加正视“被遮蔽”才是最为平常的“现象”,“被遮蔽”乃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共同命运。所以严格来说,“空”不是不存在或没有,“虚无”也不是不存在或没有,它们都是“隐”,而“隐”才是存在的本真之维。
以哲学的方式看,“中道”首先是对排中律的否定,它否认矛盾中的双方有任何一方是必然正确的,而且不但任何一方都有可能是错误的,更重要的可能是他们双方都是错的,对于一种负责任的理解来说,“双非”是唯一可取的方法。从对某个观点的否定到对某个对立性立场的否定,再到对概念范畴的否定,以及对形而上学预设的否定,《中论》以“非”(否定) 来作为接近“中道”的最核心方法,并为此提出了“四句”和“两难”作为具体的运思步骤和技巧。中观学及广义上的佛学研究都擅于运用否定式的推论,而中观独特的哲学深度在于它不只是立足生命体验来反对经验性的虚幻,而是深入到了超验性的虚幻,既反对范畴层面的虚幻,也反对超验法则的虚幻,无论“经验论”还是“观念论”的预设都是它要消解的对象。龙树在《大智度论》卷六中云:“非有亦非无,亦无非有无,此语亦不受,如是名中道。”③龙树:《大智度论》,见《大正藏》第25 册,第105页上。龙树对人们运用概念的方式、对语言的限度都有高度的批判性,即便自身所用的概念也在否定之列,即便用于认识真理的语言也有它的限度。所以,中观是反概念主义的,中道是为了消解人类心理自然而有的概念化倾向,它所强调的不二、无分别不是为了否定事物在时空中的存在,而是为了使认识者更加接近真正完整的“实在”——在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对立的,在该境界中认识者与万物也“无有少分别”。可以肯定,中观学是“绝对主义”的,因为它坚持“不二主义”,“不二主义”在英文中可以表述为Non-Dualism 或Theory Of Non- Two,即它反对任何二元对立的观念,但它却不是Theory Of Nondifference,即“不二”绝对不是“无差别”。
四、结语:觉悟与自由的同与异
虽然佛学与西方哲学高度相异,但中观学与当代的现象学研究却又闪烁出某种思想上的亲缘性,龙树围绕“性空”而建立起的中观学与列维纳斯对“虚无“观念的解构——从对虚无的解构为切入点进而建立绝对他者的哲学——都源自对真理的诘问,也都回归为对自由的某种求索。
“缘起性空”与“莫须有的虚无”都破斥了那种试图以“存在”来同一所有意义的价值取向,他们都饱含着对彼岸性之价值的肯定,“中道”与“别于存在”都是向更高阶的理性进行攀升的方法,他们都以破为立、以否定的方式来肯定存在之意义。“实相涅槃”与“为他者的自我”在宽泛的意义上都是对主体之自由的一种追求,他们共同表明了:自我与他者不是冲突性的存在,在关系之中解脱关系、在为他者的责任中实现自我就是自由的本然之义。并且,步入缘起、进入时间是理解他者与理解自我的唯一方式,因为自我与他者的亲缘与差异无不写录在世间与时间之中——涅槃在人间,神圣性亦只能于存在之中现身。
然而龙树的“性空”与列维纳斯的“虚无”之差异也是巨大的。放在“实相涅槃”与“为他者的自我”这个更具体的视角中来看,前者的目标是觉悟,觉悟的核心是“无我”;而“为他者的自我”是一种新的主体性哲学,“自我”依然是当之不二的主体。前者所强调的无我,从缘起性空到它的不取不舍的实践要求都以无我为终极目标;对于后者,无论自我可以虚至何种程度,即无论如何强调他者之于自我的不可或缺性,自我作为主体可以说仍然位于自他关系的中心。归根结底,觉悟与自由的差别所彰显出的,仍是一个以差异性为根本洞见的思想体系与一个以追求同一性为诉求的哲学系统的极大不同,无论施以如何复杂的辩证性论证他们都总是顽固地一再回到自身。尽管在当今的现象学研究中,尤其是当代法国现象学研究总的来说是走在一条对自身传统进行高度反思的道路上,这一反思从他者、差异到解构等都对否定式思维方式进行了肯定。但是,不可否认它们却依然总是不断地返回到重视同一与整体的哲学道路之中。哲学尤其是其核心的形而上学理论,已然不只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制度,这种制度自希腊哲学开始至今仍发挥着它自身的影响力,依然在展示着它的思想容纳力。列维纳斯对虚无的反思与中观学相接近的趋向在于他们都重视差异与关系,对“空”与“隐”的重要性都有充分的认识,这些无疑有某种思想上的和合性。但是,他们的差异也始终是根本的,中观所追求的觉悟中固然有自由之意味,列维纳斯所力证的自由中也不能说没有觉悟的向度,但是两者的思考与论证仍然都更多地是对彼此之自身传统的一种延续性思考。
By the further analysis,it is clearly to see that Eve tries to change the argument to protect herself.After shirking her responsibility entirely to Adam,she begins to deliberately belittle her pride and independence that she had previously gained.For examples,shesays:
作者简介:李瑞敏,清华大学人文学院2014 级博士生
标签:虚无论文; 纳斯论文; 列维论文; 中道论文; 都是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论文;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佛学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