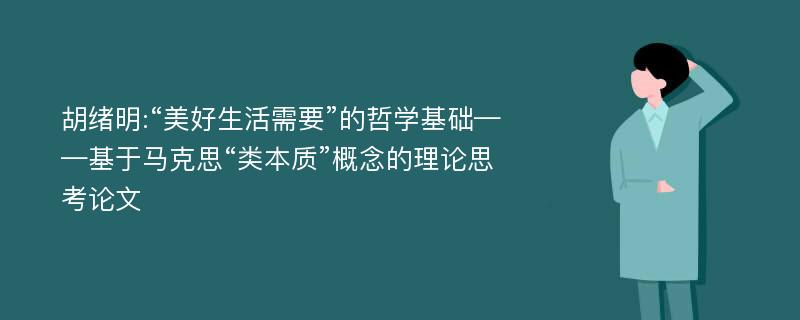
·哲学与文化研究·
摘要:在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概念中,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表征,也是一个超越自然生命的形而上的范畴。“类存在”揭示了美好生活需要的原初动力在于作为人的超越自然生命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存在方式;“类特性”阐明了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内涵在于作为人的表现自己生命方式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类生活”表征着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为我们避免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抽象化、庸俗化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关键词:美好生活需要;类存在;类特性;类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产生的内在动因、丰富内涵及实现路径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重要课题上升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高度并对其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11这些重要论述系统而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我们党为什么要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美好生活以及怎样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一系列重大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和深远的时代价值,其思想的原则高度充分彰显了对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思想作出了重大的创新性发展。本文基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类存在”与美好生活需要的原初动力、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与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内涵、超越自然生命活动的“类生活”与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理论表征三个理论维度,就习近平美好生活观的丰富内涵及其对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展开讨论,旨在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角为深刻理解习近平美好生活观所蕴含的思想的原则高度提供一个学理性的分析框架。
一、“类存在”:美好生活需要的原初动力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民生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党的执政之基的重大的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21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在实践维度上阐明了我们党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性,彰显了习近平美好生活观的鲜明的人民性立场,而且在理论维度上体现了对马克思哲学中的“类存在”概念的创造性发展,深刻揭示了美好生活需要的存在论性质及其原初动力。
气流过山问题是一个传统的气象中尺度问题,它会造成在地形上空和下游的气流扰动,大的扰动能造成飞机颠簸,甚至引发空难,对航空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同时深刻影响着天气和气候变化(池再香等,2011;陈学溶,2013;苗春生等,2017),故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动力气象学发展过程中,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马克思哲学的“类存在”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包括人的生命活动在内的一切存在方式的独特性: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马克思的这一深刻见解——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成果——不仅完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及其对人的抽象、非历史地理解的超越,从而揭穿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2]4的全部真相,而且指证了人的需要的感性特质以及感性需要生成的物质基础;这一深刻见解同时还表明,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因而,任何一种关于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疑问都只能在“历史的一度中”(海德格尔语)方能获得正确的解答。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辩证、历史地批判基础上提出了唯有通过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185“使现存世界革命化”[2]527“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539——才能彻底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科学见解,并将这一美好生活图景的基本要义概括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原则高度不仅体现在对未来美好生活图景的展望及其必然性的科学论证,同时也体现在对美好生活需要之原初动力的独到分析,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概念的重要论述之中。
马克思的“类存在”概念开辟了一条根本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解释路向,指证了美好生活需要的感性基础及其存在论性质,从而为我们解开人类“需要之谜”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架构。质言之,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要义绝不仅仅意味着人对“物的世界”的直观体验,毋宁说,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它始终与“人的世界”本质相关,美好生活需要究竟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条件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156,而只有在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美好生活才直接意味着“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才能真正实现“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2]185。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方式体现为一种“受动”和“能动”相反相成的“类存在”。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2]211作为这种感性—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方式就表现为“受动”和“能动”的有机统一。“受动”的存在方式,表现为人的生命活动、需要对象等方面都要受制于外在于人的客观条件和自然规律的限制;“能动”的存在方式,表现为人的感性活动具有超越性,即人是一种超越生命的能动的存在物。这种“类存在”的双重特性使得人的存在方式本质重要地表现为一种感性—对象性的活动:一方面,人的需要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客观对象,不是直接同人相适合的自然存在;但另一方面,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力量只有在他的对象中方可得以表现和确证,“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210。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人的“类存在”所固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特质,才使得人不断超越作为自然生命个体,而这个超越过程本质重要地呈现为人对现实生活的创造过程,因为“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自身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2]195。
其二,正因为人把自己的生活当作他的活动的对象这种“类意识”,人才具有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特性”。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特性”首先表现在人的活动不像动物那样直接受肉体支配,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这样人的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需要才是全面的,“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2]162-163其次,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特性”还表现在人以人的方式进行活动并积极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唯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需要才是人的需要,需要才真正具有人的本质,需要才是美的。对此,马克思作过非常精彩的论述,“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163
近日,腾讯《一线》独家深度对话58到家CEO陈小华。在陈小华看来,国内互联网行业都是一样的,开始时万众瞩目,然后行业进入洗牌探索期,最后有人发现还有存活的企业在慢慢崛起。陈小华同时分享了自己关于O2O行业的一些感悟,在他看来有的行业适合补贴,有的行业不适合补贴,58到家之所以能够在大浪淘沙中生存至今主要是坚守自己的核心原则。
生活无疑是一个属人的范畴,动物不存在生活,它只是生存。因此,任何一种关于“美好生活需要”的考量都无法绕开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也同样如此。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以“类存在”概念切入对这一带有“斯芬克斯之谜”性质问题的思考。
其一,人是一种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类存在物”,人在对象性的活动中形成感性的需要,并且把这种感性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对象,马克思称之为“类意识”,而人一旦获得了这种“类意识”,人的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各种需要才真正表现为他自己的生命活动。马克思指出,“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但由于“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因而不是“类存在物”,就不可能形成“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的“类意识”[2]162。
二、“类特性”: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内涵
其次,“类生活”是一种超越自然生命的生命活动。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类”,人不仅是一种自然生命的存在,更是一种超越自然生命的生命存在,即表现为一种“超生命的生命”[3]。这是人作为一种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规定中的形而上的维度。这种形而上的本质特性的展开过程实际上体现为人的生命活动所蕴含的意义世界,正是这种意义世界使得人的生命活动不仅仅满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更需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诉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本质重要地蕴含在人的生命活动之中。此外,作为超越自然生命的生命存在,其生命活动的形而上的维度还体现在人还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这种文化性的存在使得人不仅有生活资料等物质性的需要,同时也有艺术审美、民主正义等精神性的需要。人的生命活动所蕴含着的这种形而上的本质特性使得生活本身对人来说就是一个不断超越既定性、追求丰富性的过程。因而,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就绝不能仅仅从对物质财富的片面占有加以考量,而应该构建一种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环境等丰富多元的价值尺度,这些价值范畴的需要构成了人的意义世界,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这种意义世界的对象化过程。正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11-12,因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3)采集精度的协调。由于前期地理国情普查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产使用的数据源(主要是DOM数据)不尽相同和采集方法的不同等因素,使得地理国情数据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平面采集位置存在一定偏差。要实现生产数据库的构建,就必须完全处理偏差问题。处理的基本原则为低精度向高精度靠;低分辨率向高分辨率靠。同时,后续更新生产必须使用相同的数据源。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对现实生活的创造过程实际上就是人自己历史地形成过程,“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2]211。因此,“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519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历史真正生成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阐明了历史的属人性质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性质,并在“历史的一度”中回答了人之所以具有超越自然生命个体,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原初动力在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类存在”。
马克思把人的“类特性”归结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表明探寻人作为一种自然生命体的本质特性是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中生成的,并且人的这种“类特性”的展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因此,人的这种“类特性”不是非历史的抽象概念,人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则完全取决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马克思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2]519-520这表明:一方面,人的生命活动受到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特性”的全部丰富性是生成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人在感性—对象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感性需要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表现方式,并且这种感性需要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不断地追求和创造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因此,对美好生活需要在本质上就体现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的展开过程。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开了人的本质的全部奥秘,从而为我们探寻美好生活需要的原初动力和本质内涵提供了一把钥匙。
正是因为人作为这样的一种“类存在”,才使得人在根本上区别于其他动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作过明确的说明。在他看来,“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2]519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通过揭示人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物质生活的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深刻阐明了人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深层机理:第一,人的任何一种需要都是人自己在从事生活资料的过程中产生的,这表明人的需要生成于人的感性活动,并且人的感性需要受到生活资料生产的历史条件制约,因而包括人的精神需要在内的各种需要都是现实的、历史的感性需要而非抽象的意识活动。第二,正是因为人的需要是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因而人的需要直接表现为人的生活;但因为动物的需要直接是以它的自然生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动物根本就没有生活而只是生存。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证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
三、“类生活”: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理论表征
在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中,“类存在”揭示了美好生活需要的原初动力在于作为人的超越自然生命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存在方式,“类特性”阐明了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内涵在于作为人的表现自己生命方式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只有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从而以“类生活”的方式存在时,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真正得到了满足,人才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类生活”概念本质重要地作为美好生活实现的一个理论表征。
首先,“类生活”表现为一种生产生命的活动。马克思指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2]162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类”,人就是一种“自为存在的生命体”。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的过程在其本质上就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规定的生命的生成过程。人是一种自我创造、自我规定的生命存在,而必要的物质资料是人的有机生命体持存的感性基础,因为人首先是一种感性的存在物;此外,人还需要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性以及生态良好的环境空间等必要的生活要素。因为没有这些必要的生存条件,人的生命活动对人来说就不是真正占有自己本质的过程,进而人就不能真正占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对象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这个意义上,人占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其实就是占有了自己的类本质;反之,人不占有自己的劳动对象,丧失的就是自己的本质,生活仅仅作为一种维持人的自然生命的手段,马克思称之为人的劳动异化。“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2]161-162在马克思看来,以利己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市民社会中的个体生活同“类生活”相对立,因为“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2]30。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作为“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185的“类生活”才能真正实现。
如果说马克思以“类存在”指证了人的存在方式的独特性,并在超越自然生命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生成了感性的需要,那么,人的感性需要的本质内涵在马克思那里则是以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而加以确证的。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162马克思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最后,“类生活”还体现为一种改造世界的能动地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2]163。这就是说,生命原本是从属自然的被动存在,现在变成能够不断地开掘、启动、实现、发挥深藏在自然生命里的潜能,把外在于人的感性客体变成人的感性活动的对象即表现为人的“作品”。一方面,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人能够按照人的尺度创造对象并以人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只有以这种“类特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人的活动才是自由自觉的人的活动,唯有自由自觉的活动才是美好生活的全部真谛;另一方面,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类”,人由于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去创造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样就改变了生命本身的生存方式,改变了生命和外部环境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好生活绝非一个抽象的范畴,毋宁说,美好生活需求的全部丰富性真正生成于人能动地改变世界的感性活动,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520
谣言从“无知”发展到“无畏”,现在又进入到“无耻”阶段,也难怪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网络谣言爆发的时期。从本质上讲,食品安全谣言的“无畏”“无耻”都属于“以谣生利”,在利益驱动下,而且看起来又不需要付出太大的造谣成本,还有什么不能发生?
现行旅游厕所质量等级划分标准为2016年8月颁布实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8973-2016国家标准,替代2003年已颁布的GB/T18973-2003标准。旅游厕所是指:在各类旅游景点、旅游线路沿线、交通集散点、旅游娱乐场所、旅游街区等旅游活动场所聚集地的为游客服务的公共厕所,涵盖了旅游线路中集散地、服务区、餐馆、景区及其他旅游接待场所的公共厕所。新增设的男性、女性通用厕所(亦称第三方卫生间或无性别卫生间)成为新标准中的亮点。
余论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概念中,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表征,也是一个超越自然生命的形而上的范畴。马克思的“类存在”“类特性”“类生活”等关于人的“类本质”概念蕴含着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机理,既揭示了美好生活需要的原初动力,也阐明了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内涵。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为我们避免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抽象化、庸俗化理解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根本政治立场,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创造历史思想的科学把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种提法表明:一方面,把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上升到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奋斗目标的高度,深刻地诠释了“美好生活需要”绝非一个普世价值的范畴,而是一种带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追求的“人民至上论”,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高度地理论自觉和创造性发展。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将“美好生活”简化为纯粹的经验事实或物质表象的做法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立场,都未能在“历史的一度中”(海德格尔语)深刻把握其本质要义,特别是不能真正领会马克思所说的“需要的人的本性”,就是说,都不能深刻揭示需要的人的尺度与人的解放之内在关联所蕴含的原则高度。由此可见,唯有从马克思的思想深处厘清美好生活需要的哲学基础及其内在机理,方能真正跳出旧哲学对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物性”或“种性”的思维藩篱;方能从根本上回答“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一新时代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 高清海:《人的类生命、类本性与“类哲学”》,《长白论丛》1997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B1;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9)02-0026-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关系研究”(16ZDA099)
作者简介:胡绪明,1973年生,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胡运海,1993年生,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圆圆]
标签:马克思论文; 美好生活论文; 自己的论文; 生命论文; 本质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关系研究”(16ZDA099)论文;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