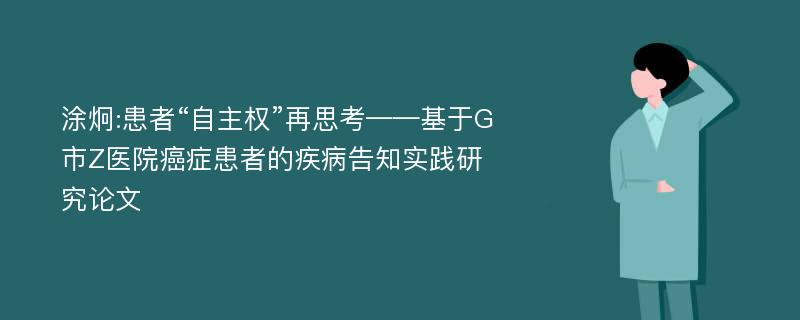
[摘 要]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医疗实践中,广泛存在着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被隐瞒病情的现象。本项研究分别从医生、家属和患者三方的视角和立场来展示疾病告知场景的微妙张力,并反思中国医疗实践中患者“自主权”的概念。首先,疾病告知和自主权具有社会建构属性,是由嵌入在中国医疗场域中的一系列因素,如医疗体制与政策、医患关系、医生的主观态度等共同塑造的。其次,在疾病告知的实践中,“家庭”往往是分裂的,患者与家属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中国疾病告知实践中的症结并非自主权主体由患者转移到家庭,而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由患者移交给了家属,而“家属”并非“家庭”,不一定能代表患者的最大利益。最后,自主权概念中的“知情权”与“决策权”存在分离。不少患者在被剥夺了知情权的同时,不断试图做出有关自己身体和健康的决定;而另一些患者在知晓自己的病情、预后和治疗选择后,依然无法进行自主决策。嵌于医疗体制和家庭关系中的疾病告知和自主权实践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包含着患者、家属和医生在病程中的不断协商、斗争和妥协。
[关键词]疾病告知;自主权;中国医疗实践;医学社会学;癌症患者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
身患疾病,既是个人经历,也是社会性的体验。疾病的发现和治疗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体化经验,而是嵌于特定时代、文化和科技发展背景下的社会产物。在西方国家,患者自主权的概念主要是通过19世纪末期及之后的一系列临床司法案例逐渐确立起来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7年的《纽伦堡法典》、1964年的《赫尔辛基宣言》及在西方社会兴起的公民权利运动和患者权利运动,共同促成了知情同意原则的广泛传播和应用。患者根据本人的价值观和信仰对自己所接受的医疗服务做出自由决定被普遍认为是维护患者个人尊严的重要举措[1]。通常认为,自主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知情权,即患者有权知晓自身病情的诊断结论、治疗方案、预后等真实信息;二是决策权,即患者在知情前提下,不受外力控制而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与治疗相关的决定[2]。在医疗实践中,“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原则反映了患者自主权的这两个核心内容,是保障患者自主权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一般来说,精神正常的成年患者本人是知情同意的权利主体。对于丧失行为能力的患者或未成年患者,知情同意权则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行使[3]。本文重点关注的“疾病告知”是实践知情同意原则和维护患者自主权的首要条件,涉及患者是否,以及如何获得有关自己疾病的信息。
2)针对安全隐患及时跟踪复查,确定完成整改。检查结束后,应立即汇总安全问题,下发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确定整改限期及时跟进整改进度,再次组织复查,对未按期整改者给予处罚,确保整改保质保量完成。
尽管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患者自主权是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医疗系统的价值观,但其在世界各国医疗实践中的贯彻和落实并不具有“普世性”[1]。目前来看,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医疗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疾病告知的模式:“医生主导模式”、“患者自主模式”和“家庭中心模式”[4]。 “医生主导模式”认为具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应该在患者治疗过程中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在是否告知患者病情和其他相关信息的决定中具有主导权。西方社会在相当长的医疗实践历史中一直遵循“医生主导模式”。在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癌症晚期的病人仍然普遍被认为没有能力对自己的病情做出理性的最优判断,或对治疗方案做出合理的选择。医生被赋予了决策权,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们通常选择对患者隐瞒病情,或对真实的病情进行弱化处理[5]。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对患者自主权的理念转变,疾病告知的政策和实践才经历了变革。由此,第二种模式“患者自主模式”,即医生直接向患者告知病情并由患者进行自主选择,开始被西方社会普遍采用。但是疾病的不告知或通过家人间接告知的实践依然在很多社会普遍存在,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南欧国家、中东国家等。在那些家庭和社区观念较重的社会,人们普遍倾向于采用第三种模式“家庭中心模式”,即由医生向患者家属告知病情,再由家属决定是否向患者告知病情。
随着我国医疗体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知情同意的原则被引入中国的医疗体系,相关法律和管理条例都对其做出了规定(1) 1982年卫生部发布的《医院工作制度》中强调实施手术前“必须由病员家属或单位签字同意”。1994年,国务院制定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实施手术、特色检查或患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同年,卫生部制定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进一步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1998年的 《执业医师法》也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2002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2009年《侵权责任法》 更进一步指出,医务人员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情况,并取得书面同意,明确把知情同意作为一项权利写入法律文件。。尽管如此,知情同意原则在当今中国的医疗实践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6]。首先,在面对癌症等重病或绝症时,医生和家属倾向于对患者隐瞒病情[7]。患者身患重疾,却连“知情”都谈不上,更别说“同意”。其次,在医疗实践中存在将“知情同意”简单等同于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的机械程序,且一度规定签字的必须是家属或单位。即便在今天,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依然在“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的规定之后补充了一条“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医务人员将这些规则应用到日常医疗活动中,往往只负责将病情告知家属,获得家属对治疗的签字同意,而是否告诉患者,以及何时、如何告诉患者则由家属决定[8]。这一方面避免了医务人员直接面对患者得知病情后产生的过激反应,也避免了由于患者和家属意见不一致可能产生的医疗纠纷。另一方面,简单而机械的签字制度忽略了知情同意是医生与患者进行充分的交流后达成互相理解的过程,而非仅是白纸黑字的结果[6]。可见,对患者自主权的保护虽然在医疗制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法律和相关管理条例的确认,但在实践中依然遇到重重困难。即使是维护患者自主权的首要步骤“疾病告知”,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在当前中国的医疗环境中,为什么重疾患者难以获得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的充分了解与自主决策的权利?是善意的谎言,还是自主权的错位?本文从医生、家属和患者三方的视角和立场来展示疾病告知的微妙场景,呈现告知实践中不同角色间的张力、冲突和矛盾,并反思中国医疗实践中患者“自主权”的概念。首先,在医疗实践中,自主权的内涵及对其的理解和应用是医疗体制与政策、医生执业环境、医患关系、医疗资源、医生的主观态度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塑造的。因此,我们需要考量其所处社会环境的结构性因素及包含的权力关系。其次,中国患者的自主权虽具有“家庭”属性,但患者和家属时常由于立场和疾病体验的巨大差异而产生对治疗方案的分歧,因此,所谓的“家庭”是需要被解构的。在看似完整的“家庭”参与中,患者与家属可能互为“他者”,主体界限分明。最后,这样的分化不仅造成了家庭内部不同成员间意见和利益的不断碰撞与协商,也表现在自主权内部,即知情权与决策权的分离。田野调查显示,一方面不少患者知道自己的病情却无法自主决定治疗方案,另一方面也有患者在被剥夺了知情权的同时,不断运用各种策略试图夺回对自己身体和健康的决定权。这些争夺的过程显示了自主权具有的时间维度,即嵌于医疗体制和家庭关系中的疾病告知和自主权实践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可见,自主权与其主体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值得做进一步的学理探讨。
患者自主权不是无条件实现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下,由医生、患者及患者家属多方参与决策的行为,其中医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医生严格遵守并有效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疾病告知中患者的自主权就能得到基本的保障,患者家属在其中的作用也会大大降低。因此,中国的医疗实践中,患者自主权的丧失首先与医生的医疗实践行为密切相关。虽然我国从1980年代起就对保障患者自主权的实践(如知情同意)做出了相关规定,但不少医生在医疗实践中并没有直接对患者告知病情,而是选择告知家属。这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造成的,包括医疗体制与政策、执业环境、医患关系、医疗资源、医生的主观态度,等等。
二、研究方法
从上面三个患者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患者与家属对知情权的争夺面临不确定的结果,且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癌症病情的不告知现象在初诊患者或刚入院的患者中尤其明显。然而,随着病情的发展和治疗的推进,一些家属的告知态度会发生变化。很多家属会考虑在特定的时候告知患者,特别是手术前、手术后和临终安排后事的时候。入院后,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患者渐渐对自己的病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很多家属都表示因为瞒不住了,所以向患者揭示病情。即便没被直接告知,患者(如H伯)也会自行猜测病情。正如一位患者(女,57岁,肺癌)表示:“懂的有懂的负担,不懂的有不懂的负担。我妈当时去世的时候就说,其实她早就知道了,一听扩散这种字眼就明白了。你瞒着她,她也瞒着你,知道你是想不让她知道。我妈妈很坚强的。所以我也不怕,不隐瞒,躲不掉的。而且我会上网,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其他患者也提到,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获知病情:与朋友聊天,阅读书籍,观察家人的表情,查看检查结果、化验单和报告,阅读病区走廊的科普栏等。
三、自主权在中国医疗场域的实践及特征
(一)原则≠实践:制度困境、医患关系与医生的主观选择
2.货币政策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表5显示,无论选择M1增长率还是M2增长率,回归结果均显示出一致性。在投资过度的样本组中,MP_L1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假说2a,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问题,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则能有效缓解过度投资。在投资不足的样本组中,回归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值。这验证了假说2b,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缓解上市公司投资不足的问题,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则会使投资不足现象进一步恶化。
首先,医院的制度安排和紧张的医疗资源促使医生倾向于选择不直接向患者告知病情。由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三级医疗体系不完善,患者大量涌入大型公立医院,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Z医院作为全国最大的肿瘤专科医院之一,更是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和东南亚的患者。在此情况下,医院优先将医疗资源配置到治疗性领域和对硬件设施的投入上,在培训医务人员的沟通技术等方面的“软”投入不足。医务人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技能对每个患者的身体和心理状况进行充分了解并实施谨慎、有效的告知[12]。我国对疾病告知的相关规定也并不完善,除了明确知情同意的必要性外,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制度来指导医务人员在什么情况下告诉患者哪些内容,以及何时告知。此外,在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家庭需要负担患者很大部分的治疗费用,因此家属在疾病决策中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医生无法“擅自”决定治疗方案,而需要考虑患者的家庭经济情况并咨询家属的意见。
杰拉德·普林斯叙事理论刍议——以《作为主题的叙事:法国小说研究》及以后作品为主 ……… 杜玉生(2.82)
最后,医生也会结合个人的主观态度、价值观念、工作作风等来决定疾病告知的具体实践。有经验的肿瘤医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哪些患者可以告知病情,哪些不能。这取决于患者的年龄、心理状态、病情等多种因素。Z医院的一位医生在解释门诊中为什么让部分患者去诊室外等候,留下家属单独告知诊断结果时提到,对于病情严重的,特别是晚期癌症患者,或是来自农村、受教育程度低、心理脆弱的患者,怕他们承受不了病情,因此不告知病情(访谈材料L20151016)。然而,当患者的病情发生变化,医生的告知态度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有些医生会在熟悉的患者病情恶化的时候对家属提出建议,让他们尽量在适当的时候告知患者病情,避免留下遗憾。一些护士也会嘱咐家属:如果不告知患者病情,患者术后可能不理解治疗,导致不配合、康复缓慢等问题。然而,笔者接触的大多数医务人员表达出“有心无力”之感,表示他们能做的很有限,建议也往往只针对自己熟悉的患者家庭。即使他们认为告知有利于患者应对疾病,只要家属不同意,他们也很少会主动建议家属告知患者病情。
以上种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医务人员的疾病告知实践。对于医生来说,保护自己和尽可能避免医疗纠纷是非常重要,甚至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但在具体实践中,他们并不是一刀切地“不告知”。在他们眼中,基于患者个体的特征(如年龄、心态、病情)和结构性因素(如阶层、性别、文化程度),使得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适合”获得知情权。对大多数医生来说,具有知情权的个人是那些正值壮年、有文化、心理成熟、经济条件较好的男性。而小孩、老人、女性则被认为是承受力较低的人群,往往成为被隐瞒病情的对象。此外,与医生关系比较亲近、文化隔阂少的患者(例如医疗领域的同行),更可能得到医生有关治疗选择、风险、预后等各种情况“情真意切”的解释。对于病情较轻、早期或预后比较好的患者,医生也倾向于“负责任地”多说一点。这些告知实践受到医生所受专业培训、是否有时间,以及个人价值观和行事作风等制度与个人主观因素的共同影响。
(二)家属≠家庭:自主权的转移与家庭利益的分化
由于医生普遍担忧医患关系存在的风险并区别对待不同病人的“知情”诉求,患者的自主权往往无法得到来自医院层面的保障,而成为医生眼中的“家事”。 家庭一直是中国疾病事件的中心。从病后的寻医问药、对患者的照料、承担医疗费用,到疾病的告知和治疗决策,都围绕家庭这个社会单位展开。现有文献常常认为,在中国,患者被隐瞒病情的原因是家庭取代个人成为自主性的主体。研究者认为,疾病告知实践及其背后的自主原则与本土文化的适配度不足[3,16-19],其中中国特有的“家文化”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认为,患者自主权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嵌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在西方社会,患者的自主权掌握在病人自己手中,这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传统有着密切关系;而在中国和其他家庭观念较重、家庭关系亲密的社会,自主权的主体通常是家庭,而不是个人[20]。但是,在中国的医疗实践中,自主权真的是让渡给了“家庭”吗?如果让渡给了“家庭”,而“家庭”又包含患者,那么各项决定都应该有患者参与,由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协商决定。但现实中,自主权并没有转移到家庭,而是转移给了家属。家属和患者的诉求与决定可能并不一致,亲属之间也因血缘关系和亲近程度的不同而常持不同的立场。这促使我们反思过往研究中过于简单地运用传统家文化来解释医疗实践的做法。
笔者接触到的绝大多数患者都渴望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自己的病情并自主选择治疗方案。基于我国台湾[21]和香港[17]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癌症患者希望被告知他们病情的真实情况。在其他城市开展的一些小规模调查也表明,大多数癌症患者都希望被告知真实病情[22-27]。在我们的访谈中,不少患者对获知自己的病情表现出很坦然的态度:“迟早都要知道的,知道了省得自己一个人在那瞎想”(女,23岁,肺癌);“我觉得教授把详细病情告知给自己,自己心里会更放心一些”(男,30岁,肺癌)。了解自己的病情使患者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减少,也让其可以做好准备应对病情的发展和治疗。家属“重点保护”的老年人在访谈中大多表现出很“看得开”的态度。“当时家里人不愿意说,他们越不愿意说,我就越觉得情况不好,后来孩子就直接告诉我了。他们当时不告诉我也是怕我知道了以后心态不好。我倒觉得生老病死是一个过程,也没什么。”(男,65岁,肺癌)疾病告知给了患者综合各种因素来自主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治疗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把握和安排自己的人生。正如一位患者(P27,女,45岁,乳腺癌)所说:“我特别想了解自己的病情,好做一些计划……像我现在开公司,我要不要放弃公司呢?要不要写遗嘱呢?要不要去公园里面去做那个什么功呢?”患者明确地表达出自主的意愿,而这样的意愿往往和家属对患者疾病信息的隐瞒构成冲突。
首先,在疾病告知中,家属和患者的意愿往往并不一致。家属会根据他们对患者个人情况的了解决定是否告诉患者病情,什么时候告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告知。一位患者(男,60岁,肺癌)的儿子说,父亲血压不稳定,脾气暴躁,情绪也不稳定,所以没向他说明,只是告诉他肺里有炎症。一位代替母亲(女,66岁,肺癌)来看门诊的女儿提到,母亲患病一年半来肿瘤增大了2毫米,她一直没告诉母亲病情。母亲体质不好,有冠心病、高血压,担心她心理承受差。大多数家属在做告知决策时,常常根据他们对患者性格、身体、心理状况的了解而考虑是否告知。很多家属认为,向患者传递复杂的、负面的信息对患者的身体不好,会打击患者的信心。而“无知者无畏”,隐瞒是为了维护患者积极的心态,让患者正常生活。这些判断基于家属对患者个体的了解,彰显了家属对患者的义务和责任,但也常常忽略了患者自身的诉求。
数字化图像处理及3D打印技术可根据CT数据进行骨折部位的真实还原、虚拟复位、复位后评估,从而实现模拟手术,预选内固定钢板,进行钢板预塑形,提供术中钉道导航[7],可制定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为术者实施微创手术提供有效工具。本研究把上述技术应用于SandersⅡ或Ⅲ型跟骨骨折的治疗中,实施经跗骨窦切口跟骨钢板内固定手术,取得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教学督导在听课过程中发现,中职课堂教学以讲授或展示为主,即以听觉型和视觉型为主,而教师讲授并非学生最喜欢的方式,从而导致学生学习动机不强。触觉型与合作型学习风格最适合的教学方式符合现代职业教育课程观,即强调学生的参与和合作,强调个人的直接接触及体验[3]。这也许是中职生喜欢参与式课堂、喜欢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模式的心理学依据。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对木材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天然林面积不断下降,人工林开始增多。杉木是我国最重要的林种之一,具有生长较快、质量和产量较高的特点。但是,逐渐增加的杉木人工林会造成林地肥力降低、水土流失等。为了有效改善这些问题,研究林下植物的多样性十分必要,可以有效改善林分结构,优化种植区域土壤的理化特性,提升森林涵养水源的能力。另外,可以通过人工林的植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实施有效评价,从而为提升并改善植物的多样性提供重要参考指标。所以,本文充分研究了杉木纯林和混交林林下植物多样性的相关内容,为人工林生态系统建设提供参考。
最后,家属的疾病告知中还涉及很多现实因素的考虑,如治疗费用的负担、救治与否的考虑、家庭成员间(经济和照护)责任的分配、(决策中)道德责任的承担等等。尽管转型中的中国家庭在个人遭遇风险和社会保障不足时会出现“再家庭化”的趋势[29],但家庭在为个人风险提供社会保障的同时,其成员之间的互助关系和亲密程度会体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这使得家庭中,特别是扩大家庭中家属的立场往往不一致,利益的落脚点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大家庭如果能对患者提供比较好的支持和照顾,往往更“敢于”告知,也能够较好地应对告知后的安慰问题。如一位患者(男,59岁,肺癌)的儿子提到:“因为之前我和他说了一些话,也跟他说治疗过程中钱不是问题,(告知病情后)他也觉得比较踏实。”另外,家属的救治考虑关系着“道德次序”(moral queue),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老年人常排在年轻人后面[30]195。囿于种种现实的考虑,家属可能觉得不方便对患者进行详细告知,更不愿让患者知道家属的顾虑。此外,在告知决策中,不同的家庭成员意见可能并不一致。有些家属出于情感因素想尽办法要延长患者的生命,有些家属则悄悄算计着老人生死之间经济利益的分配。在看似完整的“家庭”参与中,家属之间因为亲疏远近、治疗理念甚至个人利益不同而争吵不休。有的甚至召开扩大家庭会议(但不包含患者本人)来集体商议。
总体来说,在疾病告知的实践中,家属往往从自己的角度来判断是否告知患者、如何告知以及告知多少。家属对患者病情的隐瞒,既包含了对患者个体情况的考虑,也包含了保护家庭甚至个人利益的考量,其中涉及很多现实因素,如治疗费用的考虑、家庭成员间责任的分配等。虽然相较于医护人员,患者通常会更倾向于依赖和认同家人,但在对待疾病告知的态度上,家属和患者的意志常常相左。以家庭为中心的医疗实践及自主权实践是家长制的[31],事实上由拥有更多权力的家庭成员主导,而极易忽视患者自身的意愿和需求。因此,所谓的“家庭”概念在自主权的分析中需要被解构。中国疾病告知实践中的症结并非自主权主体由患者转移到“家庭”,而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由患者移交给了“家属”,而“家属”并非“家庭”,不一定就能代表患者的最大利益。
(三)知情权≠决策权:患者的斗争与策略
家属对患者隐瞒病情,但大多数患者都想了解自己真实的病情,并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自主权采取各种斗争策略。笔者以Z医院三位中老年患者的故事来呈现患者的视角:
L伯(男,66岁,食管癌)感觉不舒服就到家乡的医院检查。L伯的同学是该医院的医生。检查结果出来后,这位医生悄悄联系了L伯的儿子,告诉他L伯情况严重,为避免他不配合治疗,建议不要告诉他病情,并建议到G市来治疗。从医院出来后,L伯一家与医生一起吃饭,L伯在饭桌上就怀疑起自己的病情,要求直接看检查报告,并威胁说如果不让他知道病情,哪里的治疗都不去。儿子没办法只好给他看了检查报告。L伯表示,作为病人他应该要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到了什么阶段了,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案,以及不同治疗方案可能遇到的问题。L伯觉得病人需要被告知自己的病情,这样才有心理准备,也才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生活。
其次,家属对患者病情的隐瞒,并不一定是完全从患者的利益来考虑,有时也是家属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和适应过程。对于家属来说,思考是否告知患者病情的过程,也是他们去了解癌症,并说服自己接受家人罹患癌症的过程,因此在开始阶段往往选择不向患者说出病情。即使癌症的病情被确诊了一段时间,患者家人也常常不愿主动提起,“似乎放在那不说,大家都忘记了”(女,65岁,食管癌)。暂时躲避疾病、避免谈论疾病是很多家属的应激反应。另一位患者(男,61岁,食管癌)的家属就直接表示:“其实隐瞒病情,不是在欺骗患者,而是欺骗自己罢了。”面对重症,家属也需要时间来接受疾病可能的后果(包括死亡)。有研究指出,家属欺骗患者或在患者面前保持沉默其实是家属在保护自身免于死亡带来的恐惧[28]。
H伯(男,60岁,肺癌)刚住进Z医院时,其女儿在访谈前,专门嘱咐研究人员不要谈“癌”或“肿瘤”,因为父亲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以为是通过手术就能解决的小毛病。H伯自己也说“这样的事知道得越少越好”,看得出他对自己的病情有疑虑,但又害怕知道真相。接下来的几天里,每次研究人员在H伯的病房与其他患者做访谈时,H伯总是认真观察并专心聆听访谈内容,看得出他对自己的病情也有想了解的意愿。手术前两天,H伯的女儿对研究人员说:“(父亲)在家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到了这边变成小孩子似的,我瞒住病情,说什么他都信了。”术后第一天,H伯表示他刻意叫子女不要将所有事情告诉他,他认为知道得越少越好。刚做完手术的他,面对恢复的不确定,心里想知道的或许只是积极的信息。一直到出院前,H伯的女儿依旧没有直接对父亲说过他的病情,但H伯多多少少已经知晓了自己的情况。
第一次在科室见到N伯(男,59岁,食管癌),他就显得很焦急。陪伴他从湖南来G市治疗的儿女不给他看检查报告,也不告诉他具体病情。跟他聊天前,其女儿出来嘱咐研究人员不要说“癌”字,因为他们没有告诉父亲他得的是癌症。N伯认为自己的病是小问题,只是一个月前有几天吃饭时胸腔内有点疼,他认为是家人把小事扩大化了。N伯很想知道之前活检的结果,然后自己决定是否继续治疗。他担心有些治疗本身对身体的伤害更大,认为如果疾病不是恶性的,不用治疗。当了20年村干部的N伯有强烈的意愿了解自己的病情并掌控治疗。他曾当着研究人员的面大声责备儿女什么都不告诉他。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病情,N伯对检查和治疗接受程度极低,抱怨检查太痛苦。过了两周,听科室医务人员说,N伯怀疑所有的治疗手段,坚决要求出院,回老家了。
三位患者的例子表现出患者对知情权的需求并不相同。一些患者希望能够对自己的病情有全面的掌握(包括了解详细的治疗方案),而另一些患者只想知道其中的某一些信息(如自己得了什么病)。患者是否愿意以及多大程度上想了解自己的病情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对自我能力的判断(受过较好教育的L伯的自信)、自我决策的决心(当了20年村干部的N伯对自主的要求)、家庭关系(一直务农的H伯在心理和经济上对女儿的依赖)等。进一步来看,患者对疾病的知晓意愿与他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家庭权力关系有关。患者如果能够获得较多的家庭支持或者经济条件较好,往往能更加坦然地接受有关自己疾病的信息。
以往有关疾病告知的研究以量化研究为主[4,9-11],或是勾勒疾病告知的总体情况,或是试图描述各方有关疾病告知态度和认知的特征,而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长期田野调查中的访谈和观察,旨在更加深入、细致地考察疾病告知和自主权的建构过程中所产生的现实考虑与伦理困境,为了解和分析围绕患者的医疗体验及自主权所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社会关系提供独特的社会学视角。本文的写作基于2014年11月至2016年11月在G市一所三甲肿瘤医院Z所进行的题为“癌症患者疾痛体验”的民族志研究所搜集的田野材料(2)本文中涉及的医院、医生和患者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在此,作者对田野点提供帮助的医务人员及参与访谈的患者和家属表示感谢,也对参与调研的同学黄天瑜、习真、方婵、范卓、张立及为本文提出宝贵意见的学界同仁姚泽麟、程国斌等表示感谢。。研究团队围绕患者的疾病经历和体验,在该医院胸科和泌尿科长期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人员每周前往该医院一到三次,每次停留至少半天,在住院病区和门诊室分别进行观察,并对患者、家属和医务人员进行访谈,最终共形成了约七十万字的田野材料,涉及上百个患者家庭的疾病应对经历和求医历程。其中,涉及疾病告知的典型案例为52个,患者平均年龄50岁左右,男性31名,女性21名。
其次,紧张的医患关系也给医务人员的疾病告知造成了困扰。普遍存在的医疗纠纷甚至医疗暴力让医务人员在日常医疗实践中常常采取防御性措施[13-15]。疾病的不告知、部分告知或间接告知也构成了医生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Z医院一位护士长就明确地说: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告知得听家属的,如果家属想要对患者隐瞒病情,医务人员是不能告知的;如果告知后患者出了什么事,家属会怪罪医务人员(访谈材料Z20150821)。恶化的医患关系让医生在日常医疗实践中采取措施以规避责任,对家属告知病情就是把告知的责任及后果转移给了家属。Z医院一位医生提到一位她相熟的患者(癌症晚期)时更明确表示:“怎么能告诉他只有三个月(预期寿命)!他承受不了,直接跳楼自杀了怎么办?”(访谈材料L20160117)由于担心自己要为告知后可能的不利后果负责,该医生能做的只是告诉患者家属,让他们回去委婉地告知患者病情,并把身后事宜安排妥当。
但病情的变化也可能让一些家属从选择分享病情到后来极力隐瞒,使得患者逐渐失去了知情权。在一次门诊中,一家三口来复查并寻求继续治疗,五十多岁的患者(丈夫)明显了解一年多前被确诊的肺癌病情,他表情担忧,不断向医生询问各种问题。当医生问诊结束开处方时,妻子强行推着丈夫离开诊室,留下二十多岁的儿子在诊室继续向医生打听:“父亲这个情况,又化疗又吃中药,还能活多久?”(访谈材料L20160111)随着病情加重,家属考虑到患者身体情况越来越差,开始对患者隐瞒部分病情。在此过程中,患者也从拥有知情权的个体,到后来被迫失去了(部分)知情权。对于很多家属来说,即使告知了患者病情,是否要将治疗方案、治疗风险、预期寿命、花费等告知患者依然是需要不断斟酌的问题。在癌症早期或治疗效果比较好的情况下,家属倾向于多告知一些;在癌症晚期或病情复杂、预后不好的情况下,家属告知患者病情时则有所保留。有的家庭甚至坚持对患者隐瞒到底,觉得让患者轻松面对生活、没有恐惧地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是最好的选择,无论患者自己是否有意愿知晓。
对疾病知情与否影响着患者行使决策权的可能性,但对患者来说,知情权和决策权并不总是一致的。过往的绝大多数研究未对知情权和决策权做出区分,似乎患者有了知情权就代表他们获得了决策权,或是患者丧失了知情权就一定同时失去了决策权。然而,在实践层面,有些患者获知了自己的病情,却依然无法获得做出独立决定的自主权;有些患者被刻意隐瞒了病情,却依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努力争取着对自己身体和治疗的决策权。例如,H伯主动选择“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在不同的阶段选择性地获取信息,也是行使决策权的一种表现。对N伯来说,虽然直到离开医院都没有获得知情权,却维护了自己的决策权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出院。两位患者都没有获得充分的知情权,却依旧能通过种种方式来争取决策权。相反,在Z医院的临床观察和访谈中,大量案例显示患者虽然拥有知情权,却依然没有决策权。由于受到经济条件限制或得不到家庭的支持,有些患者可能想继续治疗却被迫放弃。与之相反,也有患者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情况下不想继续接受治疗,但家人坚持让患者接受手术之类的介入治疗,甚至在紧急情况下让医生插管抢救,没有实现患者在家安然离世的心愿。同样,患者能否实践他们的决策权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角色有关。那些得到较好的社会支持(医保报销多、工作福利好)和家庭支持(家庭经济条件不错、家庭成员照顾得好)的患者,往往在获得疾病信息后有更多行使决策权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嵌入家庭关系中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并不是无条件归于患者的,常常需要患者自己主动去争取,因此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对患者来说,知情权和决策权并非总是一致的,一些患者没有知情权却依旧试图自主决策,一些患者即便有了知情权却还是无法自主选择治疗方案。细致、深入地观察中国的疾病告知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的分离。二者的不一致也正是中国家庭内部复杂关系和权力斗争的一个缩影。
足球游戏规则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般都会以分组的方式来进行,对场地没有非常高的要求,人数、器材等限制条件也比较少,组织形式一般都会根据不同的条件来做出一定的调整。通过游戏可以使得参与者更多地接触球,还能够更快地掌握相应的足球技术。
四、结语
本文将疾病告知和自主权的建构视为一个社会过程,反思过往研究中对“自主权”的理解,并揭示自主权在中国医疗场域的实践及特征。具体来说有以下发现:首先,患者自主权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嵌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制度中的社会建构的产物。自主权不仅仅是法律条文中的一个概念,而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塑造的,包括医疗体制与政策、医生执业环境、医患关系、医生的主观态度,等等。其次,在疾病告知实践中所观察到的家庭并不是完整、单一的权力主体,患者与家属之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家庭关系是分化的。中国疾病告知实践中的症结并非自主权主体由患者转移到家庭,而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由患者移交给了家属,而“家属”并非“家庭”,不一定能代表患者的最大利益。最后,自主权的两个方面——知情权与决策权在实践中会出现分离,不少患者在被剥夺了知情权的同时,不断试图做出对自己身体和健康的决定,也有患者获知了自己的病情,却依然无法自主决策。嵌于医疗体制和家庭关系中的疾病告知和自主权实践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包含着患者、家属和医生在病程中的不断协商、斗争和妥协。
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人认为,患者获知自己的病情,特别是在病情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做出不理性的决定,如拒绝治疗、自杀等。但是,相关研究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疾病告知对患者心理和生理的伤害并不成立[32]。在国内若干肿瘤医院开展的研究均显示,知情程度对患者的生活质量[33]和社会/家庭状况有积极影响[34]。反而是家属对患者撒“善意的谎言”可能潜藏着诸多负面影响,例如给予患者不切实际的期望,导致家人间的不信任,患者对治疗接受程度低,对治疗的副作用以及术后漫长的恢复过程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而产生更强烈的抗拒情绪。在某些情况下,隐瞒反而会激起患者使用极端的方式来夺回“决策权”。另外,由于无法与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家属需要独自承担日常照料、经济和心理的多重压力。在很多情况下,不告知病情让癌症患者和家属没有为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如死亡)做好准备,从而留下遗憾。在研究人员长期追踪的患者家庭中,有些子女由于没有告诉父母病情,在父母去世后内心深感遗憾,后悔错过了帮家人实现未尽心愿的机会。
患者是否拥有知情权、决策权,是否能够获得合适的治疗以及家属的支持对其疾病体验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每个人都将走过的生命终末期以及生命整体的质量。那么,又该如何在现实条件下保障患者的自主权呢?笔者认为,患者的自主权不应被理解为单纯的“家事”。保障患者的自主权,需要将医务人员重新纳入到疾病告知的实践中来。事实上,有不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供借鉴,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践行的由医生组织的家庭会议模式。当癌症一经确诊,由医生组织患者家属召开家庭会议,了解家属对疾病告知的顾虑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让家属与医务人员达成告知病人的共识,医生进而协同家属一同了解患者的意愿,并将病情和治疗方案等信息根据患者的意愿进行告知(3)胡文郁,“癌症末期病情告知的原則”,引自“中国台湾癌症基金会”(http://www.canceraway.org.tw/page.asp?IDno=1006),2012年9月19日。本文对中国台湾医生组织家庭会议的了解也来自于对台北医学大学蔡笃坚教授的访谈,在此一并致谢。。这样既能减轻家属的精神负担,也能正确地引导病情的告知,让患者有充分的时间掌握和安排自己的人生。而这一切的实现离不开医疗资源的投入和医疗制度的改善,如完善疾病告知和保障患者自主权的法律法规,为医务人员提供更多同患者交流和沟通的时间、空间与培训,引入其他专业角色(医务社工、助理护士等)来辅助告知。此外,在社会层面应建立保障患者自主决策的制度,如生前预嘱的实施。最后,应在全社会积极开展有关疾病告知的宣传和死亡教育,让患者和家属了解自身的相关权益,并能以更平和、理性的态度面对生命中痛苦但必经的旅程。疾病告知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而其合理、有效的实施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关于“名从主人”原则在实施时遇到的问题,李捷、何自然有专文谈到五点对策:一、音从主人;二、音、义从主(即音意结合的翻译);三、音、形从主(即不译照搬);四、形从主人(原文照搬,但发音按目的语读);五、重命名(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译为Beihang University)。[2]这番讨论说明“名从主人”不止和音译相关。
[参考文献]
[1] RATHOR M, SHAH A, HASMONI M. Is Autonomy a Universal Value of Human Existence? Scope of Autonomy in Medical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Western Medical Ethics and Islamic Medical Ethics [J]. Inter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Malaysia, 2016,15(1): 81-88.
[2] BEAUCHAMP T, CHILDRESS J.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3] 董平平,王丽宇. 论中国家庭文化对知情同意原则实践的影响[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 (2): 262-264.
[4] WANG DC, GUO CB, PENG X, et al. Attitudes towards Truth-telling about Cancer: A Survey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Oral and Maxillofacial Cancer [J]. Chinese Journal of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2009, 25(11): 769-711.
[5] SARAFIS P, TSOUNIS A, MALLIAROU M, et al. Disclosing the Truth: A Dilemma between Instilling Hope and Respecting Patient Autonomy in Everyday Clinical Practice [J]. Global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 2014, 6(2): 128-137.
[6] 夏媛媛.从知情同意的发展史正确认识知情同意权[J]. 医学与社会,2007 (2): 44-46.
[7] 曾铁英,李岩,陈英,等. 医护人员对癌症告知态度的调查研究[J]. 医学与哲学,2007(11): 66-67.
[8] 苏银利,李乐之. 医患不同角色群体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态度研究进展[J]. 医学与哲学,2008 (5): 28-29.
[9] FIELDING R, HUNG J. Preferences for Inform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Decisions during Cancer Care among a Hong Kong Chinese Population [J]. Psycho-oncology, 1996, 5(4): 321-329.
[10] 蔡欣怡. “坏消息告知”对病人情绪与生活品质的影响[D]. 台北医学大学人文研究所学位论文. 2010.
[11] SCHWARTSMANN G, BRUNETTO A. Evolution of Truth-telling Practices in Brazil and South America[M]. New Challenges in Communication with Cancer Patients. New York: Springer, 2013: 419-428.
[12] 涂炯,亢歌. 医患沟通中的话语反差:基于某医院医患互动的门诊观察[J].思想战线,2018 (3): 28-36.
[13] 姚泽麟. 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服务的责任私人化与医患关系的恶化[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1): 24-32.
[14] 聂精保,程瑜,邹翔,等. 中国患医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医务人员的观点、制度性利益冲突以及通过医疗专业精神构建信任[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4): 104-114.
[15] 涂炯. 医闹的道义和权力“游戏”[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 (6): 55-66.
[16] 朱伟. 中国文化环境中的知情同意:理论与实践[D].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17] TSE C, CHONG A, FOK S. Breaking Bad News: a Chinese perspective [J]. Palliative Medicine, 2003, 17(4): 339-343.
[18] 土丽艳,郭照江. 知情同意原则与文化背景--中美生命伦理学比较研究之一[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01 (5): 30-31.
[19] 张英涛,孙福川.论知情同意的中国本土化--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知情同意走向[J]. 医学与哲学,2004 (9): 12-15.
[20] FAN R, LI B. Truth Telling in Medicine: the Confucian View [J]. The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2004, 29(2): 179-193.
[21] WANG S, CHEN C, CHEN Y, et al. The Attitude toward Truth Telling of Cancer in Taiwan [J].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4, 57(1): 53-58.
[22] 高柏青,邹德莉,杨力敏. 老年癌症患者病情告知方式与时机的调查[J]. 解放军护理杂志,2006 (10): 43-44.
[23] JIANG Y, LIU C, LI J, et al. Different Attitudes of Chines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oward Truth Telling of Different Stage of Cancer [J]. Psycho-Oncology, 2007, 16(10): 928-936.
[24] 何瑞仙,王映雪,田雅娟,周存杭,王洪燕. 患者及家属对于癌症诊断告知对象意愿调查[J]. 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09 (3): 283-285.
[25] 黄雪薇,王秀丽,张瑛. 癌症患者的信息需求--应否与如何告知癌症诊断[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 (4): 265-270.
[26] 贾艳皊,黄俊波,谢灵英,李金祥. 晚期癌症患者家属的病情告知态度探究[J]. 医学与哲学,2014 (5B): 47-48.
[27] 曾铁英,周敏,冯丽娟,等. 癌症病人对重症病情告知态度的调查研究[J]. 护理研究,2008 (6B): 1522-1523.
[28] CANDIB L. Truth-telling and Advance Planning at the End of Life: Problems with Autonomy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J]. Families, Systems & Health, 2002, 20(3): 213-229.
[29] 吴小英. “去家庭化”还是“家庭化”:家庭论证背后的“政治正确”[J]. 河北学刊,2016 (5): 172-178.
[30] 姚泽麟. “工具性”色彩的淡化:一种新健康观的生成与实践以绍兴醴村为例[J]. 社会,2010 (1): 178-204.
[31] 程国斌. 当代中国家庭医疗决策的伦理策略——一个有关家庭医疗决策的案例研究[J]. 中外医学哲学,2017 (2): 21-41.
[32] HANCOCK K, CLAYTON J, PARKER S, et al. Truth-telling in Discussing Prognosis in Advanced Life-limiting Illnesses: a Systematic Review [J]. Palliative Medicine, 2007, 21(6): 507-17.
[33] 赵丽萍,黄金. 原发性肝癌患者知情状况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J]. 护理学杂志,2007 (6): 8-10.
[34] 罗洁,吴凤英,郑迪. 知情状况对住院晚期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 肿瘤防治研究,2012(7): 855-859.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9)05-0096-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临终医护制度与实践的社会学研究”(17CSH021)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涂炯,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医学社会学。
(责任编辑 卢 虎)
标签:患者论文; 病情论文; 家属论文; 自主权论文; 自己的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临终医护制度与实践的社会学研究"; (17CSH021)论文;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