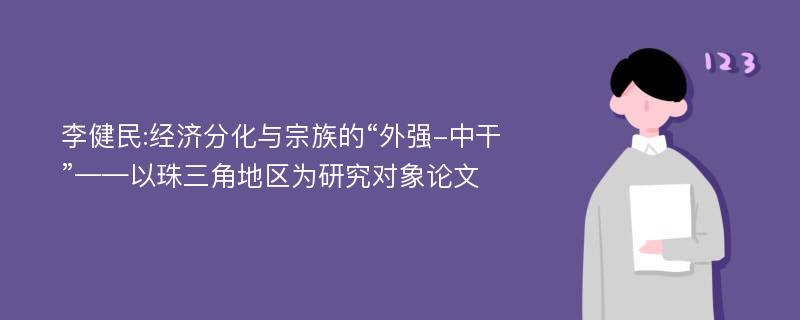
[摘 要]由于特殊的工业化路径,珠三角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初普遍形成“哥哥种地,弟弟进厂”的“一家两制”式分工,从而在家族内部产生“穷哥哥、富弟弟”的差异,割裂了最为亲密的社会关系。这种经济分化进而形塑为一种“不对等格局”,包含人情交换、生活面向、意义世界和彼此期待四个维度,造成宗族内部普遍的关系破碎化。同时,日益注入的资源使宗族得以重建和加强组织的结构和规范,进一步意外性地对内造成激化;但也因为宗族维系的存在,彻底的分裂或原子化得以避免,从而导致了珠三角地区宗族的“外强-中干”这一特殊的动态结构。其结果是走向貌合神离,结构与功能并不一致,甚至产生某种背离。
[关键词]宗族;经济分化;不对等格局;外强-中干
乡村振兴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七大战略之一,同时也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振兴过程中主要将面临什么问题、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是其中的关键。前者往往指向人口外流、文化萎缩、资源稀缺等等,经济落后和原子化严重的西部农村被认为是振兴的重点对象[1-2]。反之,一个简单的预设是,经济发达以及宗族强大的地区则前景光明,被认为是可倚重和动用的资源。按此推论,珠三角农村应该是振兴基础最扎实、发展困境最少的地区。但如果我们仔细进入宗族的内在联结,需要追问的是,宗族内部是否不存在分化?宗族成员间又是否具有充分的能动性?关于宗族的运行机理需要研究者和治理者清醒客观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将构成乡村振兴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当代宗族研究的视角切换
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族不仅是多个家庭和家族结成的组织单位,同时还承担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多种功能,既是制定、执行族规的政治共同体,又是举办公共活动和实行家庭救济的经济共同体,还是一个家族意识形态共同体。其与国家治理中的儒家传统形成同构效应,促成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3]。
20世纪以来,工业化发展与人口流动使宗族遭受连续的冲击,尤其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政策和意识形态层面都对其重点打压。学界对此始终保持关注,有关论争也一直持续,主要包括宗族是走向衰落、蛰伏还是重建,宗族与国家之间保持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宗族对村庄治理和政治现代化存在正面还是负面的功能等。
学界对此有三种主流范式,第一是结构主义视角,将宗族看成一个自洽的整体,注重考察物质和结构形态,即作为组织的宗族;第二是实践主义视角,将宗族看成由多个行动者组成的社会网,注重考察行动、事件、关系等社会实践,即作为日常生活的宗族;第三是文化主义视角,将宗族看成一个中国人的“生命体”,注重考察作为观念的宗族。
(一)结构主义视角:作为组织的宗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取缔宗族,包括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对农村社会实行直接控制,消除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体系;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将家族组织赖以存续的物质要素如族田、宗祠、家庙等予以化解;通过破旧立新的文化运动将家族组织的符号象征如家谱、族旗、楹联等予以销毁[4]。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以组织的幻灭为标志,国家结构性地瓦解了宗族共同体,使其不复拥有作为乡村社区生活核心的支配作用[5-6]。王沪宁更进一步指出,在地主被消灭后,家族文化失去了主要动力,家族组织的治理功能不复存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创造了不同于家族的组织,将农民历史性地纳入跨家族的集体之中,更削弱了家族的功能[7]58-60。
二是网络结构通用化。通用的网络界否是保障现场控制设备与企业管理系统两者之间通讯畅通的关键。通过通用的网络结构,企业管理层能够实现对现场设备的监管,这也正是当前和未来电气自动化所追求的目标。
相反,在改革开放后反而重新生发了滋养宗族的条件,其组织形态与国家治理存在结构性或功能性适配。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重新取代集体劳动方式后,由于正式支持机构尚未建立,同村村民尤其有血缘联系的宗亲家庭成为农户首要的求助与合作对象[8]。人民公社这一国家权威的退出及村委会的设立,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宗族势力的维持和保护[9]。
近十年,大量关于宗族复兴的研究开始兴起,他们判断改革开放后宗族走向重建,这是由于在正式产权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宗族能为农村地区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保护,使后者免受掠夺[10]。同时,在正式组织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其构成村民对公共物品需求的一个替代性组织选择[11]133。也正因为对于宗族组织功能的过于关注,在宗族复兴的讨论中大量的外显性指标被采用,如蔡晓莉[12]、孙秀林[11]143都以是否有祠堂或是否有多个祠堂作为衡量的标准。肖唐镖[13]则将宗族重建的标志界定为宗族的组织机构、制度规范,以及修谱、建祠等宗族活动。其中隐含的预设不言而喻,即制度和结构的重建代表了宗族的实质性归来。
(二)实践主义视角:作为日常生活的宗族
差异化的意义世界同时对应着彼此期望的相悖。富人对穷亲戚已经没有了很高的期待,需要求助时比如借钱、办事、处理纠纷等,潜意识里并不会想起他们。在农业经济时期村民间还有互帮互助的责任乃至必要性,如今无论事实上的能力还是观念上的意义感知,他们也确实都不再“被需要”了。但反过来,观念的力量使穷人仍然保持对富亲戚的期待,遇到困难时首先还会想起他们。进一步而言,这些相斥的期待还建立在各自认同的“正当性”上,即各自都认为自己的期待和要求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
这是因为作为中国农村传统居处形式的亲族聚居,在集体时期并没有遭到根本的破坏,而且对农民流动自由的严格限制,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亲族聚居[14]。其次,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下,人们在个体安全方面实际可以依赖的保护者也只能是传统的关系网络尤其是家族网络[15]42-43。唐军通过对这个时期华北地区的观察,深化了这种发生机制,他发现家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会利用甚或制造某种突发性的生活事件,来扩展自身利益并促成家族生长,包括确认家族结构、彰显规范、明确边界[16],从而实现了家族的蛰伏与绵延[17]。王朔柏等对安徽三个村庄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个观点,其中一个新机制是在以村落为基础的集体化政策下,人们以宗族的非正式网络在正式组织中重新组合在一起[18]。
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宗族才开始真正走向瓦解。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之后,农户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得到肯定,并为家族生长涂抹上了日渐浓重的理性化色彩[16]。王朔柏和陈意新则将之称为“公民化”进程,即改革给予农民经济自主、乡村选举、进城劳动等现代权利,“让农民以法律而非宗法来保障安全,以市场机制而非宗亲合作来实现富裕”。同时民工潮使很大一部分宗族丧失中坚力量,宗族与农民的血缘关系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所取代[18]。遗憾的是,这个视角在解释改革后的宗族变迁时,注意到了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的冲击,但没有如考察集体时期般深入揭示机制,同时在宗族内部经济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也没有很多研究者沿着该脉络后续展开,使其在解释性和影响力上让位于结构主义。
(三)文化主义视角:作为观念的宗族
改革开放后,得益于邻近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的开放政策,以及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珠三角地区充分调动各级积极性,推动“四个轮子”一起转,即市县、乡镇、村、社四个层次共同推动乡村工业化[23]。其中村社两级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充分利用掌握土地资源的优势招商引资,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或将土地出租给投资者,或直接盖标准厂房出租。“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原料在外、市场在外,珠三角的工厂只是外资企业的加工车间,村集体主要赚取土地厂房租金和工缴费[24-26]。
影响更为巨大的是钱杭和谢维扬对宗族的判断,他们强调采取文化人类学的“主位方式”,认为宗族的出现与持续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汉人为满足对自身历史感和归属感需求的体现[20],“中国农民对宗族有一种‘本体性’的需求——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汉人宗族的本体性意义也并非与现代生活概念格格不入,其真正合理的前景,也许应该是逐渐自愿地消除其残余的强制性,在保持自己的本体性需求的同时,将其功能目标尽可能充分地纳入与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相适应的轨道中[21]。不过,文化主义视角在当代宗族研究中并不多见,且对其他路径始终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力。
(四)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和背离:迈向一种整体性视角
上述视角使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到宗族的多个侧面,同时也展示了一些相互矛盾的悖论,计划经济时期宗族既瓦解又蛰伏,改革开放之后则仿佛既复兴又衰弱。对宗族的这一矛盾解释,很可能源于结构与功能的混淆。
这样一种家庭结构的变革叠加经济能力的差异,促成了家族内部兄弟之间更显著的分化。经济能力本身就更强的较小儿子可以摆脱对其哥哥的“反哺”进一步壮大,年长的儿子则仿佛被只身抛入市场经济之中,这促成了兄弟间进一步的显著断裂。由此,每个小亲族内部基本都呈现出“穷哥哥、富弟弟”的格局。
同时,与成员间日常性社会联结相对,强结构与强规范是宗族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正如下文要展开的论述所示,日益注入的资源使宗族得以重建和强化组织,其客观存在很可能对这种已然破碎化的关系造成意外性干扰,从而进一步激化内部成员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但也因为宗族维系的存在,彻底的分裂或原子化得以避免,从而导致了珠三角地区宗族的“外强-中干”这一特殊的动态结构,并带有持续循环的趋势。
总体而言,要揭开当代宗族的“原貌”,只有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找回实践主义视角,并将文化主义贯穿始终,即融合三种视角,结合结构与能动性两方面合理地看待宗族问题,关注结构与行动者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在现代化大背景下,需要引入第四种视角:分化或阶层的视角。经济分化使宗族的成员间产生异质性,进而影响成员间一致性的观念和社会联结,是完全不同于前现代时期的,其与人口流动一样构成了宗族的致命性切割。本文以改革开放后的珠三角地区为例,观察当代宗族在经济分化之下外部结构与内部联结的变迁,以及二者在互动下走向何种样态。
二、珠三角农村的经济分化过程
(一)“三来一补”与经济起飞
文化主义视角同样认为,虽然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使农村中的家族组织被迫解散,宗族仍尚未真正走向瓦解。不过他们依循的解释路径是政治运动没有摧毁宗族的文化观念和深层结构,即实际上农村的家族意识和家族文化并没有消除,成员间的文化性内在关联依然紧密,只不过是由显性状态转入隐性状态。曹锦清等通过浙江农村的调查就指出,宗族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前并未因宗族制度的摧毁而消失,它在农村或明或暗地发挥作用[19]。
不过在当时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企业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三来一补”企业帮助珠三角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吸引外资企业大量涌入,短时期内各种加工制造企业布满在珠三角土地上,使其成为“世界工厂”。外来资本在珠三角设立生产加工基地,获得的部分利润通过工厂租金和工人工资转至珠三角农村。
尽管工厂和企业基本都来自外资,但开始之初这些投资大部分源于从村庄出去的港商。他们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过重的劳动负担,结伴偷渡到香港,改革开放初期重新回来村中办厂,或亲自经营或让留在村里的兄弟操办,因此与村庄还有很多盘根错节的关联。而这样的一群人将直接影响招工的筛选机制与用人方式,从而引起宗族内部一些意外性的变化。
(二)兄弟间的意外性分化
“三来一补”企业给珠三角农村带来了经济起飞,并由于职业收入和出租屋收入相应地带来了经济分化。但经过对珠三角村庄的长期调查发现,一个较少被关注到的现象是,珠三角农村这种分化普遍存在于兄弟之间,这是由于工业化进程之初,招工的筛选机制以及家庭内部兄弟间不同分工所导致的。
当时村里普遍实行工厂定额、村委主导的分配制。港商回村办厂,一般找的是关系最近的亲戚,但人数又不足以支撑工厂运作,且想惠及宗族里的村民一起赚钱,所以找村委组织村里的年轻人进厂打工,他们一般都是家里较小的孩子。长子或年龄较大的由于已经承包了很多田地,一来当时无论什么职业都要将收入上缴给父母,也没有长远眼光看不到进厂打工的明显好处,二来即使想进厂也不能对承包不久的土地置之不理,所以基本都留在家里种地;较小的因为之前没有分田,且还不太熟悉劳作,恰逢工厂兴起的的这段时间便顺利成章地摆脱土地的束缚,或进厂打工,或做些小生意(例如生活用品、服装鞋帽的买卖)。
因此,工业化之初,珠三角家庭普遍实行“一家两制”,即“哥哥种地、弟弟进厂”,从而在一个大家庭之中出现“工农分割”的格局。由于当时普遍不分家,兄弟之间在整个大家庭内只是处于一种劳动分工状态,因此隐藏在他们背后逐渐发生的经济分化在这阶段没有展现出来,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同时由于当时父母权威大,他们通过收取和统筹子女们的收入完成整个家庭的脱贫、改善和置业,从而实现生活发展和经济起飞。
这里面的机制是,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数额与利益呈现出几何式的扩大,涉及金钱和利益的事情已不再是小事和平等的事,也就是数额巨大的“好心事”不再是轻而易举,且富人向穷人要的人情能够还、穷人向富人要的就不一定能还了。这使得社会形成一种非对称的利益格局和结构格局。中产阶层开始给自己划界,差序格局中向外扩散的圈收缩了;而穷人阶层仍然当亲戚们是“自己人”,无论好事坏事首先想到的都是他们。这背后就是“社会”,“社会”让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一切都顺理成章,“社会”在背后推动着他们占富人的“便宜”,小到一顿饭、一份工作,大到几万块、几亩地。在穷人的处事中,依然是传统的一套价值观,在他们眼里,向亲戚要利益不是占便宜,而是分享便宜。中产阶层也并不是不愿意提供帮助,但他们害怕一次次主动的善意帮助变成必须承担的负累,害怕一件想做的事情变成必须做的事情。
情况二:如图5,作△ADB的外接圆⊙E,假设点E与点D在AB的同侧,连接DE、AE、BE,在⊙E中,∠DEA=2∠DBA=60°,又因为DE=AE,所以△ADE为等边三角形,所以∠DAE=60°,因为AD=AE,CD=AD,AE=BE,所以CD=BE,又因为AC=AB,所以△ADC≌△AEB,所以∠BAE=∠CAD=11°,所以∠BAC=∠DAE-∠CAD+∠BAE=∠DAE=60°,又因为AC=AB,所以
(三)资本效应下的阶层固化
随着工厂的积累和大量外来工的涌入,珠三角村民的收入主要分为三项:第一是职业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老板、高级职员以及普通工作者之间;第二是集体分红,一般来源于土地或工厂租金以及集体经营的物业收入,主要体现在村与村之间,村民一般每人一股,差距只体现在家庭人口数量,总体差距并不大;第三是出租屋收入,此类收入体现在土地资本的差异。
隐性价值更需要用心去挖掘。比如拿专题纪录片来说,作品绝大多数局限于从个人角度去审视,尽管我们觉得它的信息价值较高,或者说由于从中可窥见中国纪录片发展轨迹因此具有凭证价值,某些片断可作为当时社会生活原生态的一种记录。又如解放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在判断素材价值时还应注意到主题、画面、解说词之间的关系。
招工的筛选机制导致一个家族内部亲兄弟之间产生了职业分途和资本分化,而这恰恰又对应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分层的两个新规则,更加强化了兄弟间的经济差异。按生产要素分配取代按劳分配之后,首先基于技术和管理要素,职业本身的差别,足以替代勤和懒形成的分化;其次资本要素在分配中开始起重要作用并使差距成几何式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原先种地的哥哥们被迫走向市场,从事的要么是门卫和清洁工等低薪职业,要么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工资远不如在管理层的弟弟们,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积累能通过投资土地和房子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从而导致马太效应,更加固化了“穷哥哥、富弟弟”的格局。
由此,经过在珠三角多个农村的调查,在经济分层上村庄内部普遍形成三类阶层:第一是富人阶层,约占村庄总人口的20%。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一般是与港商老板关系较为亲密,首先进入工厂并随后提拔为高层的一批人,此外还有一些凭借闯劲做生意并取得成功,以及凭借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机关单位工作的,都能积累足够经济资本抢先购置村里的优质土地,拥有三四套出租屋和上十个铺位,年收入能达到几十万元。
第二是中产阶层,约占村庄总人口的50%。他们在限制建房和禁止增高前已经购置新土地,从“种田”到“种楼”,这些土地与分配的宅基地一起被建起了至少一两套出租屋,在2010年左右一栋三层出租屋的租金收入基本能达到几万元,加上一般人均每年至少万元以上的集体分红,他们可以不工作也衣食无忧。
第三是穷人阶层,约占村庄总人口的30%。他们在禁止建宅基地前没有积攒到足够的资金购置新土地和兴建出租屋,现在仍需要做门卫、司机或进厂打工维持生计。这部分人相当一部分是年长的儿子们,正如前文所述,他们在改革初期被迫留在家里种地而放弃了打工的机会,并进而丧失了资本积累和资本投资的能力。
既然带有借代意义的词是很有特点的一类词,借代意义也是很有规律性的意义,那么,词典对这类词进行释义时就应该表现出借代意义的特点和规律,在辞书的编写和释义体例上也应该尽可能地完善和规范。事实上,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总体而言,阶层分化呈现出两个主要原则,第一是跟港商老板血缘圈层更近的人更富有,第二是与之血缘相近(同一个圈层)的情况下由于家庭分工问题,弟弟比哥哥更富有。前一种情况造成家族间的分化,而后一种情形则直接割裂了家族内部,尤其哥哥们对此心里并不服气,因为这种分化是由于工业化初期完全人为的切割,在他们心中没有多少合理性,感觉很“冤屈”。更为致命的是,第二种分化是发生在最密切、最强烈的社会联结之间,这对社会的切割比传统时期家族间的贫富分化更为可怕,因为兄弟的离心离德或大家庭内部关系的松解,是涉及根基式的崩坏,必然带来整个宗族的分崩离析。
三、不对等格局:宗族内部的分化机制
经济的分化不仅单纯在经济维度对宗族产生影响,还会作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宗族成员间一系列的不对等。从社会联结的角度,传统社会可被认为是一定场域内相对均质也彼此对等的存在状态,虽然群体之间有森严的等级和差别,但群体内部的各个行动者是基本同构的;经济分化的后果恰恰揉碎了这种同一性,使原来彼此对等的关系转为一种普遍的不对等,并因此对社会关联形成致命性的改造。
(一)人情交换
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村庄形态仍是基本同质的结构即涂尔干所说的环节社会[27],保持着一种均质的互惠,即今天的帮忙总会在不久的某一天得到被帮对象同样的帮助或回报,就算在借钱方面,借的数额有限,基本都能还。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化才真正将原有的社会形态彻底撕裂,现在是有差异了、纵向的社会形态拉长了,但是大部分人还保留着原有的观念,仍然用旧有的原则处事,这部分人因此被动地或潜移默化地成为一些人口中所谓自私的人。
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普遍的土地征收,原先种地的哥哥们也被迫走向市场,由于已经落下技术基础和社会网络,相比他们的弟弟,只能做一些门卫及司机等工作,如果也进厂打工甚至可能成为弟弟的下属。与此同时,家庭结构也发生变化,原来“工农分割”、密切合作的大家庭开始瓦解成一个个独立的核心家庭,即分家越来越普遍,且一般小儿子们和父母搬到新盖的房子,大儿子们留在老房子。前者是大家庭中父母依靠家庭分工共同积累的资本所建,但最后却未平均分配。分家之后年长的儿子由于普遍收入较低,而且还要住条件较差的老房子,成为了吃亏的一方。与以前分家后兄弟之间都是基本均质的状况相比,如今分家后他们无论经济潜力还是可调动的资源,都反而不如在大家庭中。
总而言之,与传统社会均质的互惠(今天的借钱、帮忙和人情总会在不久的某一天得到被帮对象同样的还予或回报)不同,经济分化后数额巨大的“好心事”不再轻而易举,且富人向穷人要的人情能够还、穷人向富人要的就不一定能还了。人情或借贷成了单向的给予而非互相帮忙。在阶层间不对等的人情交换中,长期处于亏欠状态的中下阶层将交出对他人优势地位乃至权威的认同。
(二)生活面向
由于成长经历的不同,阶层之间不仅在经济收入及相应的社会交换中产生差距和不对等,他们所处的社会网络也不再同质。工业化之前,村民生活面向都在内,必须在村内一起互助合作才能维持生存与生活;而如今,中上阶层由于青年时代开始就投入到工厂或生意上,交际圈往往已经超越家族,建立起各种与同事、合伙人乃至村外人的联系。穷人阶层在中年之前都主要活动于分配的一亩三分地,故还守在原来的老圈子。由此你我还共坐在一张“桌子”上,但已然不在一个“平台”。
“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教育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支柱,是增强教育内源性牵引力、提高教育质量的新契机,应成为高校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新起点[6]。虽然过去几年我国高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方面采取很多有效措施且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容忽视的是问题仍然存在。结合已有研究认为,目前我国高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方面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管理层能力。借鉴 Dermerjian等 (2012)[15]提出的DEA-Tobit模型度量管理层能力。首先运用DEA方法计算企业运营效率,其中产出指标为主营业务收入 (Sales);投入指标为主营业务成本 (Cost)、管理与销售费用之和 (Sama)、固定资产净值 (PPE)、无形资产净值 (Instan)、研发费用 (R&D)、商誉GW),计算如下式:
更大的差别在于,穷人仍然依附于整个家族,尤其依附于家族里的中产阶层,因为处于顶端的富人阶层已经搬离到村外居住,很多主动与村庄的人进行切割,如以各种理由不参与集体的聚会和祭祀。当家族里的穷人仍将自己的前途与发展寄希望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家族时,中产阶层却开始走向另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网络,并能在这个社会网络中较为独立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处于中上层的精英在工作或生意上多有来往,他们有彼此引荐、扩展网络的需求,或者有共同的爱好和指向,能一起去旅游。中产阶层经常和一群富人喝酒聊天,偶尔才和穷兄弟聚聚。
中上层与普通层之间的交往圈有互相分离的趋势。穷人阶层则仍然只在原来的小圈子活动,上层的富人在镇域范围经营起庞大的政商关系网,后者用于交往活动以维系更大圈子的成本通常是前者负担不起的。打牌、搓麻将等他们也很少参与,牌局之大是一方面,聊天时经常谈及的购物、旅游、买房等事情使他们受到很大刺激。由此构成的一个循环是,穷人阶层由于排斥这些象征资本的竞争,交际圈会越来越小,更加不愿意接触。一般只有家族关系能让不同阶层聚集起来,但即使在一起,这种场合下穷人也往往比较沉默,一是早年长期务农的性格不及其他人活跃,二是相对封闭的阅历和经验让他们难以赶上话。他们成了村里“办不了事、说不起话”[28]的人,在参加酒席乃至选举等公共场合中,也变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不太会高谈阔论而是选择沉默寡言。
因此,不同阶层间就业与收入乃至习惯和爱好都呈现出多元化和异质化的趋势,不同层级间村民的互动情境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差者交往时的心态变得异常脆弱。以前村民们互相挖苦取乐是很平常稀松的事情,且往往是“无意识”的,大家不仅不会怪罪,反而感情更进一层,即使偶尔恼羞成怒别人也一笑了之。但是,在收入急剧分化之后,闲聊时一句不经意的玩笑便可能是深深的伤害,在穷者眼里,这种玩笑是鄙视,是不尊重,是富人的显摆和高傲;而在富者眼里,这是穷人心理不平衡,找准机会冷嘲热讽故意出气[29]。穷人与富人在一起说话时的分寸变得难以把握,气氛经常变得凝重。亲戚间的争吵往往是因为众多小事而生发出难以抑制的“气”。
(三)意义世界
经济分化对村庄社会的切割不仅是经济能力和生活面向的切割,对不同个体的意义世界也进行了区隔。分化之前,封闭社区内村庄成员共享一个公共空间以及这个空间之上的意义世界,彼此的意义和价值是相对一致的。由于发展的滞后性,穷人的记忆和意识仍然在村里,与传统类型的取向较为相近;在市场经济中发家致富的富人长大后相当一部分记忆已超然于村庄,两者可能只能共享一些儿时的记忆以及生活世界的情感诉求。不同人群的意义世界逐渐分开,只在生活世界的逻辑有所重合,尤其在经济层面的意义维度中可能已经是“陌生人”。
在理想类型之中,传统中国人的生命意义依托于宗族的延续性,“(族)向各个成员保证,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可以从集团和各个成员个人那里获得援助。贫穷者向‘族’寻求保护,而富裕、著名的人物则从中祈求一个安全装置,以免丧失其社会和经济地位。……‘族’越大、越繁荣、越凝聚,对所有的成员就越有利”[30]78。在此之上,族内的人以“归属体系—传宗接代”的模式体验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家族历史的追溯,以及对“祖先—我—子孙”一体的想象,进而生发出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31],并在祭祀祖先和生养男嗣后裔之中,获得亲属结构中应有的位置,从而实现生命意义的超越。综合起来,宗族对于传统中国人有经济性保障、情感性相依、宗教性超越三种意义或价值。
这三种意义在民国时期和文革时期遭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打击,但普通百姓仍然以独立于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在充满意义的世界里,真正的危机发生于充分的市场化和工业化之后,也即宗族成员被分散性地抛入市场经济。显然,中国人不再是“即使没有像美国人想象的那样发财,但如果他上有父母,下有儿孙,那么其生活同样是满足的”[32],或者仍然把家族的延续与兴盛当作个人追求的价值和意义。但对于穷人而言,家人或宗族仍然是一根“救命稻草”,家族里有人在政府机关当高官或是工厂的大老板,也就是一个强大的宗族能使他们得到安全的确信和生活的满足。
在穷人眼中,依然能感受到许烺光所描述的,“宗族能够满足其成员的各方面需求,包括物质性的保障和社会性的需求,它也就成了成员附着的归属。……在其中他享有某种在这一集团之外享受不到的安全连续和持久的地位,因此他较之其他许多社会的普通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大的确信,从而更能悠然自得的生活”[29]2。但对于中上阶层而言,他们已然不再从宗族的序列中获得经济安全感或安生立命的保证,而是通过自己奋斗得到的资本和在业缘的社会网络中,或者转而依附于大资本或大企业。他们人生的意义也变成挣更多的钱,在和别人的比较中能过更靓丽的生活。
(四)彼此期望
与结构主义关注宗族组织的制度、规范与功能不同,实践主义关注宗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打交道、如何联结以及如何组织起来。有趣的是,两者结论截然相反,后者在对经过宗族的事件性考察后,认为宗族在计划经济时期得以蛰伏与绵延,在改革开放之后反而才真正走向瓦解。
在传统血缘的观念下,血缘地缘内部的“自己人”关系是一种互为义务的社会关联。“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乡约的主要内容[33],相互之间要求提携、帮扶、救济、体谅、宽忍等,在交往中讲究血亲情意和人情面子,讲究做事不走极端、留有余地,这也是前现代时期的生存状态下必须要求的,其历史记忆构成了中下阶层的观念底色。中上阶层也不是完全不认同这种关系,但他们对家族价值的期待已经并不高,也并不期待从中得到多少东西,更多保留的是对情感的皈依。
当期待中的让步与扶持没有如期而至,而且容易被理解为是“占便宜”“依赖思想”,甚至对方以某种道德话语如“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予以回绝时,穷人阶层产生心理落差,阶层间关系破裂的种子也被悄然埋下,公开翻脸只需要再有一个导火索。由于不同阶层村民的互动情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条件较差者交往时的心态变得异常脆弱,社会联结的破裂归结起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所积累的“气”。
随着养蜂产业的扩大,砂仁、花椒、魔芋、万寿菊等经济作物收成的增长,曼来村打赢脱贫攻坚战信心满满。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曼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出列35户133人;2018年计划脱贫出列97户341人,2019年计划脱贫出列3户8人,实现整村脱贫。
四、“外强-中干”:一种特殊的动态结构
如上所述,人情交换、生活面向、意义世界和彼此期待在阶层间构成了不对等的状态,形塑而成为一种“不对等格局”,同时在宗族强大的珠三角地区,这四个维度却又镶嵌在要求对等期待甚至兄长更具权力的宗族场域之中,即当上层与上层的村民结成圈子,中层与中层交往频繁,原有的亲属关系又把不同层级的圈子拴结在一起,从而构成一种强烈的张力。这种张力的结果是,穷人一次次的索取终于使期待不再的中上阶层产生对穷人“自私化”的感觉及相应的抵触行动,而富人的每次拒绝乃至不经意的行为都使穷人产生挫折感并将之归于富人的高傲、显摆及自私。这些情绪化的感觉最终使客观的社会联结产生质变,从而构成宗族内部破碎化的起点。
结构主义隐含的共享前提是,拥有规整性外部结构的宗族必然拥有内部的团结和行动能力,并发挥出相应的外部效应,即理所当然地认为“强宗族”必然是“强团结”。然而静态的结构与动态的能动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的等同关系。“结构限制常常是策略性地运作着;结构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常常是时间性的、空间性的、能动性的、策略性的。类似地,能动者是反思性的,能够在结构限制下重新阐明自身的身份和利益。并且,能够在他们当前的处境中进行策略计算”[22]。杰索普的论断表明,单一的结构性视角可能存有严重局限。相反,文化主义往往脱离于结构,实践主义则经常能看到行动与结构的跳脱与多元,但二者可能都会低估来自组织结构的一致性压力及其社会后果。因此,超越于强弱兴衰的争端,不如说宗族只是在某些维度变强了,在某些维度又变弱了。
(一)破碎化的“强”宗族
不对等格局的张力集中体现在了村民的两类矛盾中:一个是出租屋,一个是借钱。在第一个矛盾中,新建的宅基地上地块位置和面积是固定的,地块之间的通道宽度也有明文规定,但骑楼二层以上凸出来的部分则没有限制,围绕谁家凸得多谁家影响采光等问题,即使五服以内的宗亲也吵得比较厉害,而且恰恰是他们才更可能有交界的宅基地。
就第二个矛盾借钱而言,也更多地发生在宗亲之间,因为一般也只有他们才肯借,且大多发生在穷亲戚向中产阶层亲戚的方向上。由于村里大多数人都已住在了二三十万的房子里,穷人也被迫如此,一是面子或符号资本的竞争;二是不这样做很可能就娶不到媳妇。这样他们不得不向亲人借大笔资金,一栋二十万左右的新房子可能半数以上的钱都是借的,而一般人家只要借个两三万就可以了。
虽然借钱者也是迫于无奈,对于态度较好或者平时关系好的,被借的中产阶级也不会有太大意见,但对于那些觉得“天经地义”,尤其是急着需要他们还钱时态度冷漠的,借钱的事就加剧了相互间关系的败坏。人们开始了不信任和猜度,只有从“好说话”“重感情”的人那里才能较为顺利地借到,而最后这些好人往往成为吃亏的一方,借出一遭却一个也收不回来,一次不借反被记恨。
(1)科学设置各个管理岗位,并妥善限定公路大中修养护人员数量,对下属的养护单位进行有效划分,将公路大中修养护工程中的各项资源进行全面整理,加强配置,构建结构更为合理的公路养护体系。
由此,出租屋与借钱的纠纷致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发生争执和断裂,在宗族内部强整合下形成了破碎化的个人关系,即一个强凝结的宗族内有诸多对兄弟交恶。家庭和家族是整个宗族的根脉所在,同时又是易碎的。诸多兄弟的裂痕进而导致整个家族的,在外壳上看似强盛的宗族也将呈现出外强中干的实质,毕竟作为细胞的诸多私人关系已经崩裂,家庭进而家族间也就难以组成团结一致的宗族。
对对照组提供开腹手术方法治疗。首先,为患者提供硬膜外麻醉处理,取3-6cm的麦氏切口,然后找到阑尾,若系膜相对较为厚,则必须要分次进行结扎[2];若系膜属于正常范畴,则在患者的阑尾根部采用血管钳进行戳孔,在完成带线结扎处理以后,然后再切断系膜;把长度为0.5cm的阑尾结扎线留出来,选择使用碘酒进行消毒处理,之后实行打结操作。最后,将切口进行缝合处理,然后进行消毒包扎,结束手术操作。
另一方面,在成员间日常性社会互动出现失衡的同时,作为组织的宗族与计划经济时期备受打击相比,却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强大,至少在“外观”上展现出一副日益强盛的样貌。这是由于依托于村庄的工业化发展,村内宗族的总体经济条件得以改善。尤其在城市边缘被征地的村庄,得以分享城市快速发展的“大蛋糕”,村民通过分得多套回迁房,一夜间资产达几百万元,多个“土豪村”得以在珠三角诞生。
伴随着各种资源的注入,村集体的资产增值自不必说,这种情况下不仅有人为重修家谱积极走动,各种理事会也逐渐增多,再加上几十年来国家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推动,祠堂也得以在政府与积极者的主导下得到翻新和修缮,并在祠堂前开拓出更宽敞秀丽的广场供举行家宴和婚宴之用,每次举办都显示出盛大的阵势。细分到家族之中,以我们调查的东莞N镇为例,大部分村庄已经对村集体股份确权,家里老人即使去世后股份也会保留,子女们就用老人的股份分红逢年过节一起聚餐,地点和形式往往不尽奢华。同时,在物质条件支撑下,各种规范、仪式、习俗都得以保留和执行,在珠三角地区很少发现有由于个别人的僭越,而过分扭曲和变异,如红白事等人情竞争并不激烈,酒席、建房等不奢侈浪费等等[24]95。
(二)从“外强”长出的“中干”
日益注入的资源使宗族得以保持和强化组织的结构和规范,但对已然破碎化的关系,其很可能造成意外性干扰,并引起进一步的激化。这是因为在强规范之下,尽管人们面对破碎化的亲属关系采取了或怨恨或激进的举措,红白事、祭祀、拜年等家族“聚会”时依然会被聚拢起来——毕竟夫妻双方中总有心软的一方——不去反而才触犯社会的边界。但宗族对建房、借钱等新近矛盾的规范是空白的、缺席的,也就是出现了不损害集体利益情况而损害了个人利益的情况,掩盖了金钱对社会关联的危害。结果仅仅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恶化,踩着边界的人在家族和社会方面仍然不太吃亏,甚至能得到同情,“我穷我有理”。
这样便出现一个悖论:越维护反而越破坏宗族的团结。相互斗气的兄弟或妯娌双方迫于家族的传统和规范必须在对方的红白事上出席,且在拜年、祭祀等活动中见面甚至分工协作,要在外人眼里显得光彩,但家族又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这种情况下的互动反而促成了他们更多的偏见和争吵。
2.3.3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药材样品(编号:S2)适量,共6份,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以岩白菜素峰的保留时间和峰面积为参照,记录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果,14个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RSD均小于3%(n=6),相对峰面积的RSD均小于4%(n=6),表明本方法重复性良好。
图1 从“外强”长出的“中干”示意图
家族“好心办坏事”的意外后果根植于早已破碎化的个体化关系,其实质上镶嵌于一个更深的悖论:宗族性越强反而越容易加深破碎化的个体间关系。与北方小宗族相比,南方大宗族更容易发生借钱的纠纷,因为只有具备强规范强关联的大宗族里才更会借出数十万的大金额,也就是说,这里面内在的机制是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越亲越要借(而且还是借的大数额),越亲越可以不还。
上述两个悖论叠加的后果是一种恶性循环逐渐形成。由于宗族规范强,家族成员间在借钱等方面借人情容易,同时赖人情不还的事情也能倚仗彼此的强关系而经常发生,从而导致众多私人间的交恶。家族面对个人关系的破碎化,碍于家族的“面子”,不想让外人看到内部的离心离德,总是动员他们在红白事、祭祀、拜年等家族“聚会”上继续出席甚至继续合作,但是由于彼此的纠纷无法在家族的场域得到解决,互动的增加反而只会加强彼此的偏见,白眼与争吵越来越多,从而可能会有人呼吁更强的宗族规范或宗族对个人的更多干预,并导向下一轮的循环。
研究同时显示,这些酒店并未将酒店的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纳入考量社交媒体营销的体制中去。酒店经营者更多关注的是顾客的参与度、评级和评价,但不将正负面反馈数量与销售预定数量挂钩。此外,酒店经营者更强调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工具特征。酒店经营者还意识到,社交媒体平台不能只用于扩大酒店客户的覆盖面,还应该作为了解顾客并为他们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工具。最常见的做法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让顾客了解酒店的品牌和产品,并与顾客沟通了解他们的要求。
其中,执行强宗族规范或进行家族感召的人格化载体名义上是家族中的长子,实质上往往是部分仍住在村里或者还与家族交往较密切的富人弟弟。这些在经济场上获得成功的人士,并不想看见家族的凋零,离心离德将让他们感到丢脸,这份个人成就感的追求同时夹杂着自小带有的家族情感,使他们常常背地里支撑着家族的维系,并管理着家族向外的印象整饰,为此甚至在一些场合会责怪兄长在组织家族活动上的“不作为”。例如,节假日聚餐时人来得不齐活,他们“提醒”兄长作为一家之子为什么要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承担过程中又需要怎样的忍辱负重。由于他们年纪轻轻就开始打工或做生意,故思路活跃、能言善辩,往往能用巧妙的话语说得兄长无言以对。
第三,我国已初步建成小康社会,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空前提高,刑罚体系事关国家形象和社会文明程度,应适当予以调整。一方面,刑罚体系总体上要更加轻缓化、文明化。减少、慎用死刑,有利于保障人权,也有利于引导社会尊重生命,消除复仇偿命的陋习;另一方面,刑罚体系局部上还要更加科学化、合理化,避免不同罪行的判罚轻重失当,杜绝同一罪行因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造成“同案不同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刑罚轻缓不等于一味宽纵。对于特定时期社会危害性大、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例如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电信诈欺案件、校园暴力案件应适当加重处罚力度,不轻意适用缓刑和假释,以保持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和打击力。
因此,宗族的“外强-中干”分为“外强”和“中干”两部分,前者指外部规范结构,后者指内部团结能动性,两者之间发生分离且存在动态关系,即强结构、强规范的宗族内部存在诸多破碎化的个体间关系,而一方面这种“中干”是由“外强”意外性导致的,因为在关系已然存在缝隙的情况下,宗族性越强反而越容易产生干扰,如借钱上越亲越要借(且借的数额越大),越亲越可以不还。这种情况下宗族越维护反而越破坏宗族的团结,相互斗气的兄弟或妯娌双方迫于宗族的传统和规范必须在对方的红白事上出席,且在拜年、祭祀等活动中见面甚至分工协作,但宗族又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这种情况下的互动反而促成了他们更多的偏见和争吵。但另一方面,如下文所述,“外强-中干”的另一个方向是,宗族维系的存在很可能也让彻底的分裂或原子化得以避免。
(三)遏制“中干”的“外强”
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伴随的资源注入,宗族在外壳上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强化,这些外在要素尤其包括规范结构虽然一方面意外性地导致个体间破碎化,同时又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持续整合并维持内部的弹性,整体性的宗族不至于完全瓦解为一个个独立个体。也就是说,中产阶层虽然与部分穷亲戚关系紧张但还是会借钱给对方,穷人虽然在族内地位不高且可能处处受气但也没有完全退出宗族的公共领域。
正如上一节所言,部分仍住在村里或者还与家族交往较密切的富人弟弟是宗族规范的人格化载体,并常常依靠灵活的头脑和话语说服兄长们放下个人的恩怨、“顾全大局”,对长子提及“家族责任”,对穷一点的兄弟提醒他们要“顾及恩情”。虽然过度整合会意外性导致相反效果,但也同时激活他们尚存的宗族意识,不至于完全割裂,这种宗族意识甚至还在下一代继续得到灌输和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Fig. 3 is the chip photo of the 245 GHz 2nd subharmonic receiver with on-chip antenna with each circuit block indicated in the figure.
第一,各种仪式的保留甚至强化,如祭祀和红白事等,使得传统是“可触摸的”和“可共情”的,构成一种神圣感染。同时盛大的祠堂外貌与家族聚餐等在潜移默化地灌输一种宗族概念和情结,宗族地位的不断提升也刺激人们留在宗族内部,仍然能保有一种本体性的认同。
第二,宗族的规范虽然缺乏应付新挑战的能力,但仍然构成一种牵制,是阻碍自由选择的结构性变量,有时候人们的行为“不得不考虑它”。相反,在以人情作为社会最主要连接纽带的原子化农村地区容易发生人情的变异,主要表现为人情的周期、规模、金额、对象等方面的总体性变化,其实质是规范人情现象的法则由村落公共规则蜕变为个体偏好,后者大行其道从而直接导致人情的变异[34]。其实质是原子化农村地区缺乏超出个体家庭之上的结构性力量,公共规则因而缺少生存和支撑的土壤。
同时,父母一方为家族的凝聚提供平衡机制。30、40后的一代父母对早年的兄长一辈进行补偿,体现在遗产方面对他们的倾斜等。而60、70后的一代父母,由于改革初期的原始积累以及对出租屋等资产的掌握,父辈是一个有独立能力、能制约子代的实体。他们握有家里的相对主导权,子代仍然有所依赖。不分家逐渐又成为一种常态,以血缘为纽带的体系得以维持。
五、结论与讨论
由于特殊的工业化路径,即依赖外资尤其是从村庄走出去的港商,珠三角农村在工业化之初普遍形成“一家两制”的分工,即“哥哥种地,弟弟进厂”,从而在每个家族内部形成“穷哥哥、富弟弟”的格局,撕裂了最为亲密的血缘关系。这种经济分化进而形塑为一种“不对等格局”,包含人情交换、生活面向、意义世界和彼此期待四个维度,在互相情绪化的感性认识之中使客观的社会联结产生质变,造成了宗族某种意义上的“中干”。同时,日益注入的资源使宗族得以重建和强化组织的结构和规范,对这种已然破碎化的关系造成意外性干扰,又进一步激化了这种“中干”,但也因为宗族维系的存在,彻底的分裂或原子化得以避免,从而导致了珠三角地区宗族的“外强-中干”这一“稳定”的动态结构。
因此,从外在的组织形态看,珠三角宗族依然是强结构和强规范的,甚至在资源注入后生长出一些更为雄厚和先进的物质形式;但在日常生活和能动性方面,受经济分化的冲击宗族内部已然发生了普遍的关系破碎化,同时成员间的意义世界和彼此期待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即作为观念的宗族产生了分野。总体而言,珠三角农村的宗族似乎走向貌合神离,结构与能动或形式与功能之间,并不一致甚至产生某种背离。
不过,将珠三角宗族的研究结论外推到其他地区,可能会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别,需要仔细分辨其他影响因素。温州、潮汕等地宗族同样属于沿海较发达地区,但与珠三角宗族相比,他们内部分裂似乎没有那么严重[35-36],这很可能与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后者在改革开放后以经商为主,面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市场,需要利用社会网络进行自我保护以及经济支持,进而在过程中产生自我强化;而珠三角地区的宗族成员则在工业化之初直接分散性地进入市场,宗族不再如农耕时代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和场所,从而为随后经济分化的切割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对宗族的判断需要分辨清楚什么情景下才真正有效,以及什么情境下宗族才能得到滋养。
同时珠三角的宗族现状也提醒我们,需要反思乡村振兴或乡村重建过程中一些简单的预设,即需要恰如其分地留意宗族这个变量,不能只看高大上的祠堂和族谱等,就认为其已经实质性回归,因为很可能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并不一致,是“外强-中干”的,已难以形成非常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力。在传统社会乃至计划经济时期,宗族构成了历史上的社会基础,决定着村庄乃至上级的政治生态与运作。而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宗族可能已然是虚妄的上层建筑和空中楼阁。由此,乡村振兴将难以把希望全部寄托于此,其对社会的发展可能只剩有限的作用。这些资源在乡村振兴中也并非没有作为,但要尽快细致地修复和保护起来。
[参考文献]
[1]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9
[2]刘合光.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与风险规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27
[3]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Yang C K.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in 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Massachusetts: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59
[5]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6]陆学艺.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7]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8]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中国农村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
[9]毛少君.农村宗族势力蔓延的现状与原因分析.浙江社会科学,1991(2):6
[10]Peng Yu sheng.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4(5):1045-1074
[11]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社会学研究,2011(1):133-166
[12]Tsai Lily,Cadres.Temple and Lineage Institutions,an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The China Journal,2002(48):1-27
[13]肖唐镖.乡村治理中宗族与村民的互动关系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8(6):91-96
[14]李守经,邱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体系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
[15]赵力涛.家族与村庄政治:河北某村家族现象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
[16]唐军.仪式性的消减与事件性的加强——当代华北村落家族生长的理性化.中国社会科学,2000(6):132-140
[17]唐军.蛰伏与绵延:当代华北村落家族的生长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8]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1):180-193
[19]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20]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21]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学术季刊,1993(3):148
[22]Jessop B.Interpretive Sociology and the Dialecetic of Structure and Agency.Theory,Culture&Society,1996(1):11-128
[23]贺雪峰.浙江农村与珠三角农村的比较——以浙江宁海与广东东莞作为对象.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91-99
[24]王晓毅,张军,姚梅.中国村庄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广东省东莞市雁田村调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
[25]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中国城乡及区域发展调查.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27]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8]袁松.发达地区农村的阶层分化与权力实践:一个研究展望.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3):85-90
[29]袁松.生活世界中的村庄社会分层.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0-35
[30]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31]杨华.隐藏的世界:湘南水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华中科技大学,2010
[32]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2001
[33]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4]杨华,欧阳静.农村人情的变异:表现、实质与根源——对当前原子化农村地区人情的一项考察.中州学刊,2011(5):117-121
[35]蔡建娜.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温州模式与发展转型.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
[36]蔡志祥.亲属关系与商业:潮汕家族企业中的父系亲属和姻亲.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2):15-25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nd“External Strength-Inner Weakness”of Clan——Taki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LI Jianmin DONG Leiming
AbstractDue to the special industrialization path,the rural area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generally formed a“one family,two system”division a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elder brothers cultivated farms,younger brothers entered the factories.Thus it brings up the condition of“poor elder brothers and rich younger brothers” within each family,which splits the most intimate social relation.This kind of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further shaped a kind of“unequal pattern”,which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Renqing exchange,life orientation,meaning world and mutual expectation,causing the general fragmentation of relationship in clan.At the same time,the increasingly infused resources enable the clan to rebuild and strengthen the structure and norms of organization,thereby intensify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but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clan maintenance,complete division or atomization is avoided,forming a dynamic structure of“external strength-inner weakness”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s the result,the clan is seemingly in harmony but actually at variance,structure and function are not consistent,and even generates some kind of divergence.
KeywordsClan;Economic differentiation;Unequal pattern;External strength-inner weakness
[收稿日期]2019-04-04
[作者简介]李健民,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董磊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875。
标签:宗族论文; 家族论文; 社会论文; 结构论文; 阶层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