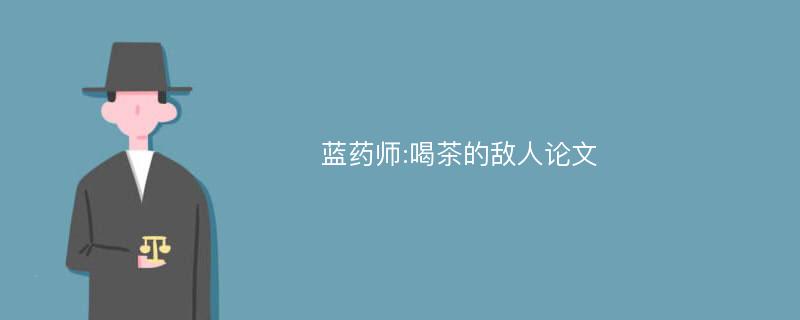
说来惭愧,我喝茶的缘起大半为了附庸风雅。
最早喝茶是高中时,喝的是家乡自制的绿茶,有时还被烟熏过,极便宜。那时总觉得喝茶能拉近些我和“高人”的距离,仿佛魏晋名流、唐宋雅士会伴着氤氲的茶气为我造点虚幻的光环。
我想,只要林强信给我们抛光熟手,无论他怎么指责,甚至拍桌大骂,我也会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然而,我想错了,林强信压根就没有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只是一个劲地和我叙旧,说他一直赏识我,说我是个难得的人才,说我为大发厂作了贡献,功不可没。说到动情时,唏嘘不已。又说虽然你挖了大发厂的熟手和订单,但我能理解,人在江湖,各为其主嘛。我趁机说了一大摞好话,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和诚意。
大学时有一次去班主任家,我利用自己的小聪明,在一群老师同学中我第一个蒙出了铁观音的茶名,收获了老师伸出了大拇指以及一群穷哥们惊诧的目光。我假装深沉地笑笑,吹了吹茶面,宛若西门吹雪,感觉自己雅致极了。
其次是在运营层面发力。企业要持续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并不断根据环境的变化提供越来越好的用户体验。这是实际产品质量与企业的品牌定位无缝对接的过程,因为用户通过实际的产品以及具体服务来感知和判断产品价值,从而形成自己对于相应企业产品的品牌定位。企业要清楚,真正在用户的实际消费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用户实际的品牌感知。因此,对企业而言,实现无形的品牌价值与实际产品的有效对接,是企业在自身品牌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后来工作了,自然开始尝试各种名茶,一半是好奇,一半还是想炫耀。至于口感,我感觉差距并不大。但我总怀疑那是源于自己买的茶还不够贵。有时明明喝得挺高兴了,但一想起这个茶叶价格一般,或市面上有更好的,心里就不是滋味,自然茶水也跟着坏了味道。
因此,我已经不太能心情舒爽地喝茶了,总觉得这茶叶是不是太便宜,这茶具是不是太劣质,这样随便泡着是不是太没有“民国范”。此念一生,便是无边苦海。随便一个茶梗就会变成一只苍蝇。喝也不爽,不喝也不爽。有时明明就想一干而尽,可一想起红楼梦里妙玉的“牛饮”讽刺,赶忙又改成小口品啜,心灵与时间就沉埋在了荒诞里。
茶叶只是喝茶的一小部分。茶叶背后还有茶具。宜兴紫砂壶好,我也花个几百元买上一个,战战兢兢供着,喝茶时都不敢大意,总是轻拿轻放,后来还是打碎了壶盖,心疼了半天。玩久了才知道,这玩意儿跟茶叶一样离谱,没有个万儿八千元,根本买不到真的好的,至于养壶鉴壶更成了一个行业,没个十万八万元你别想入门。至于喝茶的仪态、玩茶的规矩、品茶的学问--统统浩如烟海,丝毫错乱不得。懂得玩这样一套玩具,除了在看到不懂玩的茶友时卖弄几句,在心底找点“我慢”的快感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还得赔上战战兢兢。
后来茶经读多了,发现我们现在的茶道居然可能都是二手货。就这种茶叶直接冲水泡着喝的喝茶方法,居然只是来源于朱元璋这样一个人,一点风雅都谈不上。而明代以前的茶道,所谓的煮茶、斗茶、“晴窗细乳戏分茶”,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种类,都是要磨成粉煎着喝的,真正的茶道就是因为江南名士太文雅太哕唆了,被朱元璋强行废了。现在只在日本“末茶”里残留着些许余韵。我居然发现我这么多年追求的居然都只是权利的阉割品时,顿时产生一种幻灭感,却也突然轻松了。
什么名茶名器,随他去也。什么名士风范,统统放下。此念一起,我好像在一瞬间会喝茶了,我也不再忌讳牛饮之讥,也不再计较茶价云泥之别,茶叶本就是天然之物,长在华山还是衡山谁贵谁贱?茶这个字也就是人在草木之间而已,自然之人又哪有那么多穷讲究,那么多计较?皓月当空,庭如积水,携一本爱读而无用之书,捧一瓷碗,大口入嘴,微汗淋漓。此非周作人的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乎?原来茶道不是刻意去找的,越刻意寻找越不会到来,满心轻松时,它或许会偶尔过来找你。
施密特说得好:“敌人即是你自己问题的化身。”一杯茶,布满了贪、嗔、痴、疑、慢,人若俗物,茶何以堪?有时我们难受,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是在追求幸福,而是在追求比别人幸福。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给他弟弟的《家书》中说:“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饷以热粥,并佐以腌姜。”由此可知,只有自己清寒过,才能了解别人清寒的窘境。范仲淹少时家贫,住在寺庙里发奋苦读。每天煮一锅稀粥,冷凝后划成四块,早晚各两块,以切碎的咸菜佐餐。中国文人与粥,这种不同一般的感情,都由于他们自身的贫苦体验而来。正因如此,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里,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间的冷暖。
摘自《羊城晚报》
标签:茶叶论文; 茶道论文; 是在论文; 企业论文; 自己的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幸福》2019年第11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