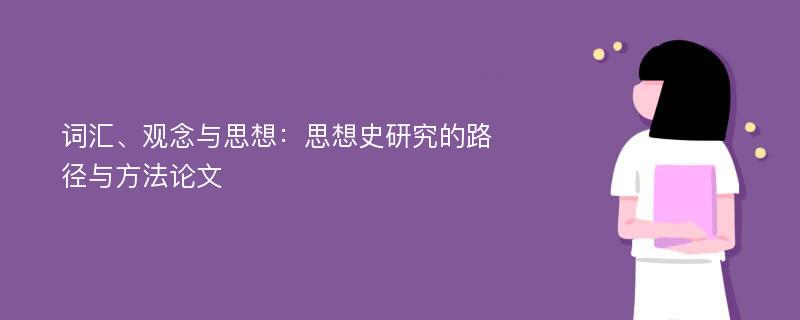
词汇、观念与思想:思想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文/何晓明
近年来,通过对词汇、概念、术语的分析,研究不同时代观念的推演变化,以推进思想史研究向纵深扩展,成为风气,相关成果蔚为大观。我以为,这种学术现象体现了思想史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新变化,值得认真思考。
在词汇、概念、术语辨析的技术层面上,中国传统训诂学的丰厚遗产可资借鉴。周大璞先生的《训诂学要略》引述黄季刚先生的论断:“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周先生列举了释义的经典方法(声训、形训和义训),又揭示了传统训诂学的若干弊端(如厚古薄今、烦琐寡要、穿凿附会、增字解经、随意破字、拆骈为单,等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技术工具和方法指导。思想史研究中涉及的词汇、概念和术语,如天、地、人、道、器、理、气、知、行、本、末、仁、义,等等,既有本义与引申义的联系和区别,更有古义与今义的联系和区别。辨析这些联系与区别,是使研究立于切实基础的必要前提。朱熹讲《周易》的核心意旨:“一是变易,便是流行的;一是交易,便是对待的。”这里的“流行”和“对待”,古今义就大有不同。朱熹讲“流行”,是发展变化的意思;讲“对待”,是矛盾统一的意思。如果没有传统训诂学的训练,就无法把握朱熹思想如此极具辩证光辉的精华。
思想史研究中的词汇、概念、术语辨析不同于传统训诂学的一个重要的本质区别是,它在词语的字面意义之外,更加注重其蕴涵的社会思想内容,即其观念意义。在此层面上,20世纪国内兴起的社会语言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资源。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里论道:“我们的社会语言学将从下面三个出发点去研究语言现象:1,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2,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3,语言是人的思想的直接现实。”陈先生强调,社会语言学探索的两个领域,一是探讨社会生活的变化如何引起语言的变化,二是从语言的变化探究社会的变化。这一认识无疑为我们动态把握词语及其所表现的时代观念的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学理依据。梁启超关于戊戌时代社会流行语言反映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有一段名言:“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这里的“中学”、“西学”、“体”、“用”,本是学术性极强的专业术语,按常理只会在精英小众范围内展开讨论,但在戊戌时代,竟然广泛流行到“举国以为至言”的地步,实在说明,那真是近代史上观念更新、思想启蒙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思想史研究不同于社会语言学的本质区别是,它不是一般地辨析社会变化与语言变化的相互关系,而是试图通过对若干关键词语的考析,厘清人们特定观念形成的来龙去脉,并确定其在民族思想流变的时、空坐标系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从而将思想史的研究提升到更加缜密、精细的水准。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本身的内容”,“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就此而论,如果说社会语言学是传统训诂学与现代社会学联姻的产物,那么,思想史研究中的从词语入手的路径与方法则打通了词语辨析、社会观念更替和思想史探究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
1.3 HER-2、EGR-1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判定 HER-2的阳性结果主要定位于细胞膜或者细胞浆内,其阳性反应表现棕黄色。根据细胞核或者细胞浆染色的深浅以及染色的范围来进行判定,结果判定如下:⑴按照阳性细胞百分数:阴性则0分,阳性细胞≤5%计1分,6%-50%记2分,50%-75%计3分,>75%则4分。⑵按照切片染色强弱来评分:棕褐色表现3分,棕黄色表现2分,淡黄色表现计1分,无色记录0分。免疫组化阳性分4个等级 (计算方法:⑴⑵):0-2分表现为-(阴),3-4分为+,5-8分为++,9-12分为+++。
莱芜山水生态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振兴、实现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杨桂钊委员就对此非常关注:“请问下一步如何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实现精准脱贫呢?”
汉制的真实内核,即暴力与伦理相抗衡的结果,不是暴力的伦理化,而是伦理的暴力化。汉以后的儒学不同于先秦儒学追求平等与责善,而是将等级内化于伦理之中:不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7](下册,P499),而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4](P1158)。暴力与伦理的最终一致,是北魏孝文帝将游牧部落的绝对奴仆制规定于华夏,并在唐律中得到定型与确认。
民主,是《尚书》、《左传》等先秦文献里即出现的古典词语。“天为时求民主”,“天命文王,使为民主”。这里的“民主”,即“民之主”,是君王的意思。数千年后的1870年代,这一词汇被《万国公报》用来介绍美国总统:“美国民主,曰伯理玺天德,自华盛顿为始已百年矣。”就最高统治者这一层意义看,这里的“民主”与《尚书》《左传》的用法相近。但从这“主”是否“民”选,“主”权是否“民”授来看,则《万国公法》的用法显然依据近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现实和政治观念,而《尚书》、《左传》的用法则契合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上古政治现实和政治观念。两者的思想史价值定位,无异天壤之别。
Citizen,更准确的中文对译是国民,公民。从观念层面讲,国民或公民意识的养成,与人们对“国家”意义的现代理解和把握直接相关。梁漱溟说:“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 1899年,梁启超就论道:“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直到1901年,思想激进如陈独秀者,“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这正是近代不同于“臣民”的“公民”意识的肇端。不仅在野人士有此认识,在朝官员同样如此。1907年,孙宝瑄在日记里记载:“前闻荫亭言:我国今日为治,当区民为三等,最下曰齐民,稍优曰国民,最上曰公民,一切纳赋税及享一切权利,皆截然不同。而国家亦须设三种法律以支配之。其有欲由齐民跻国民、由国民跻公民者,必其程度与夫资格日高,然后许之。如是则谋国者方有措手处。余以为然。”朝野上下“共识”的形成,说明思想史上的启蒙时代已经到来。
近代以后,中国的思想话语系统中的某些重要词语之所以会出现歧义纷繁的现象,与这一时期世界文明大冲突、大交融背景下的中外文化互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语言学家萨丕尔提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中国现代思想话语系统里的最基本词语,如:科学、民主、真理、进步、社会、权利、个人、经济、民族、世界、国家、阶级、革命、改良、立宪等,几乎无一不是这种“借贷和交换”的产物。如此一来,由词语辨析到观念厘清之间的学术讨论,由本义与引申义、古义与今义的二维空间,又增加了中义与西义这一维度,成为更加丰厚饱满的三维空间。
如何确证人和自然、人和对象物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海德格尔沿袭“人栖居于世界”的整体存在论构思,进行物的哲学追问也即物的哲学规定性命题探究,遵循“真理—话语—物”的致思路径,据此构造出真理和话语反映物的本质,抑或物的本质归结于真理和话语并最终维系于人的尺度。恰如他在《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中的结论:“‘物是什么?’的问题就是‘人是谁?’的问题。”[5]216海德格尔致力于从物的存在价值推导人的本质问题,不再遵循康德“人是目的”的先验性前提,初步作出了重建人与物之间整体存在关系以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积极尝试。
我们再看“民主”。
下面以“人民”、“民主”二词为例,稍作讨论。
“人民”一词,在中国古籍中出现很早。《史记·乐书》即有“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为臣民的意思,其近义词为氓、百姓、黔首,它与近代意义上“主权在民”,“民有民治民享”等观念中的“民”,意思相差不可以道里计。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其中用“人民”翻译“citizen”。这一用法悄然改变了其中国古义,实际表达了具有近代政治色彩的法治、民权、公民等观念。从古代的“人民”到近代的“人民”,词语本身丝毫未变,但其表达的观念天地翻覆。这种词语与观念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显然只有在思想史流变的研究框架内,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确定的意义。
有论者列举了《万国公报》以后媒体上出现的“民主”的四种含义:1,民之主,指皇帝;2,民主之,指人民支配和人民统治;3,与世袭君主制度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如“民主国”、“民主党”;4,外国民选最高国家领袖。并进一步分析了1864年至1915年间不同含义“民主”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发现第2、第3种含义的“民主”(对译英文democracy)被广泛运用,以中性介绍为主,但负面评价逐渐增多,尤其是1900年以后更甚。1905年以后,革命派的宣传活动声势日盛,立宪派的实际政治操作也渐入佳境,“民主”的使用频率再现高涨。尽管其中负面含义的用法依然占据多数,但终究表明思想史上的不可抗拒的民主时代,已经来临。
吊诡的是,进入现代政治与思想双重意义上的民主革命以来,国人的“民主”观念依然时时发生古今中西之义的混淆。以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为毕生使命,提出“三民主义”理论纲领的孙中山先生,竟然长久地被国人尊称为“国父”,就是显例。而直到21世纪的今天,当主流媒体宣传各级“人民公仆”的先进事迹时,“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类的古老民谣,依旧被用作精彩赞语而津津乐道。如此语言运用的奇观,正说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观念更新、思想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艰难。
近年来,沿着词汇——观念——思想路径开展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当为经典范本。
“封建”一词,“列爵曰封,分土曰建”,本来表示的是古代中国特定时期的政治样态,即封邦建国,以及与之相关的朝政、官制、人身关系、土地制度等。后来“封建”被用来命名从秦朝至晚清的社会经济形态,以表达史家关于历史演化规律的系统观念。这一观念其实已经与作为名词的“封建”本义距离遥远。冯先生考辨这“封建”观念与“封建”名词所指代的历史事实之间说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关系,发现其反映的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关系到学问宗旨、理论建构、价值基准、文本阐释诸方面的重大疏漏与缺憾,因此,对其正本清源的价值和意义,就不仅仅在于还“封建”以本来面目,也不仅仅在于为自秦至清的中国历史阶段寻求一个名实相符、意义精准的称谓,而是在于揭示学界数十年来“积非成是”的认识误区,扫除“约定俗成”的懒汉陋习,让实证与思辨圆融结合的灿烂阳光,长久照耀我们的学术领域、思想世界。
(作者系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教授;摘自《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
标签:思想史研究论文; 《左传》论文; 社会语言学论文; 术语辨析论文; 引申义论文;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