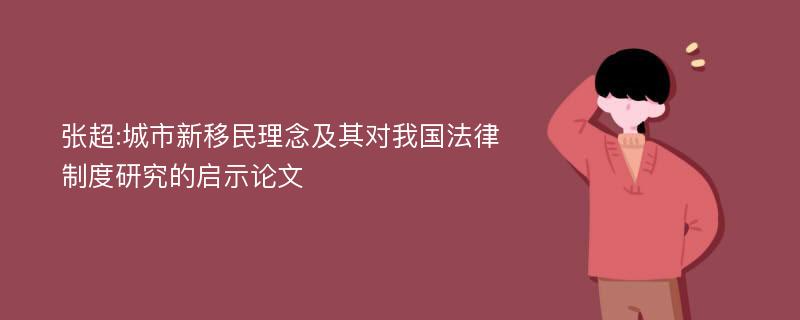
[摘 要]中国的城市化始终处于一种“下城市化”状态,在此状态下,中国的农村—城市转移劳动力很难实现真正的市民化。城市新移民理念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新概念与新思路,对我国相关法律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应从移民视角来看法制;明晰移民身份的界定;探讨移民引起的社会融入问题;加强由城市移民带来的中国传统法律体系变迁研究等。
[关键词] 下城市化 城市新移民 法制
一、下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城市新移民概念的提出背景
(一)中国的城市化与劳动力转移
中国的城市移民研究通常意义上指中国的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rural-urban migration)。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起始于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由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这些过剩的劳动力开始从事一些非农产业。
劳动力转移始终与“城市化”相关。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有学者统计,从1978年到2013年的35年间,中国的城镇人口数量已经从1.7亿增加至7.3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到2013年已经达到了53.7%,而城市的数量也相应的增加,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至2010年的658个,而县城的数量更是激增,从2173个增加至19410个。① Xin-Rui Wang, Eddie Chi-Man Hui, Charles Choguill, Sheng-HuaJia,“The New Urbanization Policy in China: Which Way Forward? ”,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47, 2015, pp.279-284.与此同时,在这种城市化背后,存在着大规模的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这种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存在可以从另一项统计数据中体现出来。虽然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3.7%,但是当仅考虑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时,城市化水平仅为36%。② Xin-Rui Wang, Eddie Chi-Man Hui, Charles Choguill, Sheng-HuaJia,“The New Urbanization Policy in China: Which Way Forward? ”,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47, 2015, pp.279-284.通过计算可知,在城市中大约存在着2.4亿的农村—城市移民,虽然随着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的改革,③有关城市人口的定义,中国统计部门经历了三次比较明显的调整。具体参见:Gene Hsin Chang, Josef. Brada, “The Paradox of China’s Growing Under-urbanization”,Economic Systems, vol.30, 2006, pp.24-40.这些新移民被算为城市人口,但是实际上他们却享受不了诸如受教育权、就业权、医疗和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保险等市民权力。
(二)中国的“下城市化”现象
一般认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现象能够逐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能够形成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体系,① Lewis, W. 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d of Labor”,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no.3, 1954, pp.139-191.但是中国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有的学者将中国的城市化定义成“下城市化”。“下城市化”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Konrad和Szelenyi,指的是高标准的工业化水平并没有引起与之相平衡的城市人口的增加,其中隐含着一种反常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相关关系。② Konrad, G., & Szelenyi, I.,“Social Con fl icts of Under-urbanization”,In M. Harloe (Ed.), Captive Cities: Stud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ities and Regions, New York: Wiley, 1977, pp.157-173.
这种下城市化的水平可以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显现出来。据美国人口参考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PRB)调查显示:截至2001年,全球大约4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之中,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一般都要高于75%。而2001年,据美国的统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36%,这一水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1%。③数据来源于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PRB). (2001). PRB 2001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http://www.data.worldpop.org/prjprbdata/转引自 Li Zhang, Simon Xiaobin Zhao,“Re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Under-urbanization: A Systemic Perspective”,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27, no. 3, 2003, pp.459-483.
对于中国这种下城市化现象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解释。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下城市化水平是中国的发展策略决定的,即通过减少城市化的水平来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中国下城市化现象中隐藏着不可缺少的国家控制和国家导向的发展。有的学者从下城市的起始时间角度来探讨中国的下城市化现象。一般认为,中国的下城市化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前,但有学者指出,实际上中国的下城市化状态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期阶段。④ Gene Hsin Chang, Josef. Brada,“The Paradox of China’s Growing Under-urbanization”,Economic Systems, vol.30,no.1, 2006, pp.24-40.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本应该吸收更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从而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改革开放并没有成为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积极因素,反而造成了中国城市化的滞后。当然这种滞后并不是绝对的逆城市化,从数据能够看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有所提高的,这里强调的只是城市化水平与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性。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张力注意到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那就是:中国城市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城市边界的重新界定相关,这种重新界定主要是通过城市领土兼并临近的土地。⑤ Li Zhanga, Simon Xiaobin Zhao,“Re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Under-urbanization: A Systemic Perspective”,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27, no.3, 2003, pp.459-483.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的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不是通过农村转移劳动力转变为市民,而是通过不断的城市疆域的扩张而连带着将农村人口直接转化成城市人口,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的疆域扩张直接挂钩。从相关调查数据也能够显示出中国城市化的这一特点。在2000年到2011年的10多年时间里,新的城市建设面积增加了76.4%,但是中国的城市人口却仅仅增加了50.5%。⑥ Xin-Rui Wang,Eddie Chi-Man Hui, Charles Choguill, Sheng-HuaJia,“The New Urbanization Policy in China: Which Way Forward? ”,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47, 2015, pp.279-284.中国的下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的增加与城市规模的扩大并不平衡,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是城市规模扩大连带的城市人口的内卷。这种观点背后隐含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有力推手是行政力量:在中国,政治性的城市化推力超过了经济性的推力。
中国特殊的城市化路径还与中国的户籍制度相关,这也是学者们十分关注的另一个城市化影响因素。中国城乡二分的户籍制度一直是解释中国下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因素。中国的户籍制度实际上经历了一种从政策划分依据到人格区分渗透的发展历程。首先,中国的户口制度是一种发展理念。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央政府极大地追求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从而划分了农村与城市的区隔,这种区隔背后的发展理念是用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随后,在这种发展理念的影响之下,户口又成为了一种分配社会资源的机制,这种分配机制将农村人口排除在国家提供的各种社会资源之外。时至今日,虽然中国已经对有关农村—城市移民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但是户籍制度仍旧发挥着作用,现在的情况是,农村—城市移民被允许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仍旧存在着进入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障碍。① Kam Wing Chan,“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Migrant Labor in China: Notes on a Debate”,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36, no.2, 2010, pp.357-364.最后,这种户口的区隔已经成为了一种人格性的标签,这种标签的特性体现在对农村—城市移民的污名化。
中密度纤维板比较热市的产品主要集中在9、12、18 mm规格产品上。中密度纤维板也面临着和胶合板几乎同样的发展困难,那就是原材料的价格疯涨,致使中密度纤维板的出厂价格水涨船高,但是市场价格却不敢调高。据说中密度纤维板销售形势虽然好转,但面临下游生产厂家拖欠资金的问题挺严重。所以总的来看,中密度纤维板市场虽然复苏的迹象明显,但市场资金回笼状态还是不容乐观。
中国庞大的农村—城市劳动力转移与中国的下城市化现象的并存,彰显出了传统城市移民思考路径的缺陷,这种传统的思考路径仍旧没能跳出“城—乡”二分体系。针对中国的城市移民现象,需要一种新的思考路径,而“城市新移民”概念就是这种新思考路径之一。
自营开发城市有关地块.城投未来的关键利润增长点,一定在于做商业区开发、房地产开发、以及其它物业开发上面.
二、城市新移民概念的提出及内涵
(一)农民工的污名化
针对主机系统常见的构件安全质量问题,在制定主机安装缺陷排除措施时,应从实际问题出发,重点解决螺栓松动问题。考虑到主机系统内部机械设备的运转速度较大且振动明显,因此,需要定期检查螺栓安装问题,以免出现螺栓位移的问题。另外,在尾轴偏移导致主机被磨损的问题上,要做好尾轴位置控制工作,将其固定在规定位置上,确保主机系统不受其影响。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学者们研究了大众媒介中所宣扬的农民工形象,分别从电视媒介、平面媒介考察了农民工的形象“污名化”问题。在电视媒介中,农民工形象被塑造成娱乐大众的“小丑”;在平面媒介中,农民工的负面形象也多于正面形象,其中最频繁的再现形象是“受难者”和“弱势群体形象”。⑥刘力、程千:《主流媒体话语表征中农民工阶层的形象意义》,《求索》2010年第1期。媒体中所宣扬的农民工形象加深了农民工的污名化倾向。民众对农村—城市的劳动力移民的印象已经固化为了一群生活在城市的底层、生活条件差、文化水平不高、需要给予帮助的弱势群体形象。
除此之外,有些学者还研究了污名化的称谓对移民群体的身体和心理所产生的影响,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社会污名化和社会歧视经验对被污名化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都会产生直接的负相关性。⑦ Bo Wang, Xiaoming Li, Bonita Stanton, Xiao Yifang,“The In fl uence of Social Stigma and Discriminatory Experience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71,no.1, 2010, pp.84-92.
(二)城市新移民概念的提出
比较城市新移民概念和农民工概念,两者存在着诸多的不同点,这种不同点也彰显了城市新移民概念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可以从对移民的身份定位、移民问题定位和处理移民问题的责任定位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的比较。
针对中国劳动力移民的这种污名化及污名化影响,需要一个新的名称和概念取而代之。近年来学术界频繁出现的“城市新移民”就是其中的替代性概念之一。陈映芳就尝试将农村—城市的转移劳动力群体表述为“城市新移民”,并相应的把他们的权益问题定义为市民权问题。①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确认》,《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朱力将中国的流动人口统称为城市新移民,并根据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的不同分类为不同的类型。②朱力、陈如主编:《城市新移民——南京市流动人口研究报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卢卫在文章中也进一步延伸了城市新移民的概念,认为城市新移民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概念,而是一种新的发展视角,不能将新移民的问题简单地定义成改善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帮助性问题,而是一个城市综合发展和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③卢卫:《居住城市化:人居科学的视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周大鸣认为,“城市新移民”概念最大的理论着眼点在于摆脱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思维,从而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社会。④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移民身份定位 移民问题定位 解决移民问题的责任定位城市新移民 定居居民 城市发展问题 责任和义务农民工 移动农民 社会关怀问题 慈善和道德
就移民的身份定位而言,城市新移民概念的侧重点在于“定居于城市”的居民,而传统的“农民工”的侧重点则是他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城市新移民思路将农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看成是城市的新市民;而农民工概念仍将其看成是外来打工的农民,根本不强调他的定居性和市民性。就移民问题定位而言,城市新移民的思考路径是如何让其享受市民权力,也就是说将其看成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问题;而农民工的思考路径是如何更好地保护其权益,其主要是一个社会关怀问题。就解决移民问题的责任定位而言,城市新移民视角认为其是一种政府的责任和义务问题;而农民工表达的则是政府的慈善和道德问题。
移民群体难以取得个人经营许可权是中国不健全的法制环境导致的,这种不健全的法制对本地居民和移民进行明显的区分。这项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在法制不健全的大背景下,行动主体是如何工具化地处理这种不健全的法制化造成的行为障碍的。这种半合法化的解决途径实际上是通过本地居民、外来移民和地方政府共同强化实施起来的,三者的利益交织在一起。这个案例令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什么才是法律的正当性。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法律的正当性概念在中国的环境下是不适用的,相应的,人们更愿意从工具性的角度来考虑法律。实际上,一些移民遵守法律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法律本身的尊敬,他们违反法律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不好的秉性,他们做出决定仅仅是出于考虑到从事的产业如何为自己获得利润。同时,就法律的实施层面而言,法律的执行并不是简简单单地通过压制或奖励,或者是通过制度性法规的考虑,而是通过一系列细致的规章和零星法条的操作。
(三)作为发展方式的城市新移民
城市新移民概念与农民工概念的比较同时也显示出城市新移民概念作为新的发展思路的意义。城市新移民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指代概念,同时还是一种城市和社会发展新思路。这种新思路主要表现为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发展问题。将移民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方式,这涉及三个层面:空间意义上的区域平衡,时间意义上的代际流动,以及结构意义上的社会重构。这三个层面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即区域平衡促进代际流动继而促进整个社会的重构。⑤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移民所涉及的上述三个发展层面实际上探讨的是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这种新的研究思路完全摆脱了农民工研究的问题化范式,而将城市社会构成变化以及移民与本地居民的结构关系置于研究的核心。⑥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三、城市新移民视角下的法制研究思路
(一) 城市新移民视角下的法制思维转变
1.一个个案,一种思路启发。
从法制角度来促进融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传统的户籍制度改革。
由表2可知,当步长为15时,训练和测试样本的RMSE值最小,网络的预测精度达到最高。所以将步长设置为15。
“让我拍一张菜单,研究上面有什么角色是名存实亡的?”喜欢看侦探卡通的我对儿子说:“应该带放大镜来探索,看看哪样菜色被斩草除根。啊,千万别是你爱吃的肉。”
除此之外,文章还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法律合谋(legal collusion)。这一概念主要表述为:在具有法律歧视的环境下,法律行动主体是如何以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保证自己的权益的。这一案例表明,移民研究能够对法律界的关键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途径,并提出新的法律观点,这种启示也就是笔者提出从移民来看法律发展的出发点。
2.从移民来看法律。
城市新移民概念强调移民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的正当性现象。也就是说,中国的移民实际上是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在这种城市移民的思路下,城市移民相关的法制建设并不仅仅是一种保护移民的法制性机制,而是将城市移民看成是中国法制发展的促成性因素。也就是说,这种视角要求有关移民的法律研究跳出传统的城—乡二分视野,将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中国法制的整体性发展。由此可见,这种城市移民的法治研究视角和上述城市新移民的视角是相似的。
本计划第二天清晨永远离开秦川,可是现在,艾莉突然想在这里多住几天。很显然女人不过将她当成一个试图混进豪宅的女孩——煮咖啡,煮牛奶,洗刷餐具,洗刷马桶,拿不菲的薪水,住豪华的房子……然后,趁女主人不注意,与男主人调情或者偷情——艾莉相信这样的生活对很多年轻并且贫困的女孩极具吸引力。现在她必须让女人相信她是秦川买来的充气娃娃——工厂出来的产品,供男人发泄性欲的玩具。她对他们的生活不会造成丝毫影响。
从移民角度来看中国的法制发展,学者蒋先福已经进行了相应的论述,认为农村—城市的劳动力移民是中国法制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这种城市移民也是联结我国城乡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理想介质。⑧蒋先福:《务工移民与法治发展》,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19页。从第一个方面来说,中国的城市移民促进了中国社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结构转变,在此过程中个人的身份界定也发生了变化,即从身份个人到契约个人的转变,这种个体性的转变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一个社会的法制发展到最后必须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移民所带来的个体性转换为个人的法律自觉创造了条件。从第二个方面来说,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能够调节我国城乡法制建设中的不平衡问题,移民进城务工所受到的法律熏陶也必定能够促进乡村社会中传统法的解体和改进。
从城市新移民的这种角度来看,中国的移民法制建设就不能像传统的对移民的法律文件的规定一样,大多仅涉及保护城市移民的合法权益,诸如保障受教育权、保证工资的发放、保障移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而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移民法律体系,既能保护移民者的权利,又能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脚步。
(二)城市新移民与移民的法律身份界定
在城市新移民视角下,务工移民问题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发展和城市发展问题,相应的,务工移民群体应该将其看成是市民群体,而不应该是在城市工作的农民群体。这种视角要求在法制建设中顺应这种城市新移民概念的思路,将务工移民的法律身份界定为市民。
一项2002年到2007年的对比研究显示,中国移民的劳动力市场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城市新移民的发展方向基本上呈现出移民群体越来越年轻化、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较为稳定和具有较长合同期限的工作的趋势;除此之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这五年的发展时间里,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移民劳动力和本地居民作为人力资本表现了融合的趋势。① Zhaopeng, Frank Qu,Zhong Zhao,“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Rural-urban Migrant Labor Market from 2002 to 2007”,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vol.6, no.2, 2014, pp.316-334.这种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倾向,尤其是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移民与本地市民的人力资本融合,表明劳动力移民已经成为了城市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贡献已经和市民相差无几,这也意味着城市新移民应当具有与城市市民同样的地位,而法律也应该保障这种市民地位。
伴随船舶大型化、交通流密集化等问题,航道的风险管理日趋重要,科学的管理是保障船舶安全行驶的有效途径。[1]在船舶交通流统计的基础上,使用IWRAP模型计算水域的船舶碰撞和搁浅的概率,对于了解水域的安全情况具有重要意义。[2]
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而言,从法理角度,务工移民已经具有了市民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务工移民在城市社会中是一种契约社会的角色。法理上的契约关系的最早提出者是法律史学家梅因(Henry James Sumner Maine),其较为有名的法律史论述是他的“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律演变。在梅因的论述中,身份指的是源自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利和特权的法律关系。在这样的社会秩序里,群体而不是个人才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每个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被缠绕在家庭和群体单位之中。契约指的是由个人自由订立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②蒋先福:《务工移民与法治发展》,第45页。在梅因看来,“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变标志着法制的进步与变迁。梅因的身份到契约的法制发展论述虽然说的是最初的法制发展历程,但是其同样适用于现在的社会。结合农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现实来说,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从法理上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一种从身份个人到契约个人的转换。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和家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种社会中,人仍旧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个体,而是具有某些身份特征。虽然农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身份社会的影子仍旧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一旦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这种身份的个体性就要演变成契约的个体性。在城市生活中,劳动力更多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务工移民这种契约性法理身份也印证了城市新移民概念提出的必要性。
但实际上,农村—城市移民的法律地位是缺失的。“法律地位”是指以法律形式规定法律主体在各种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它是法律主体在不同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综合体现。③唐鸣、陈荣卓:《农民工法律地位的界定及考察路径——一条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思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在法律层面,没有明确的农民工群体的法律地位界定。规范的法学要求法律系统内部的概念准确、权利和义务的边界明晰并且逻辑清晰,这样才能保证法律规制下的个体获得具有法律正当性的各种权益。④蒋先福:《务工移民与法治发展》,第207页。强调农村—城市移民的法律地位,就是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到这部分城市新移民的存在,为他们保有一定的法律主体身份,而不能用一种普遍的、概括性的强势话语把其掩盖在制度之下,忽略对其法律地位的保障。⑤尹奎杰:《农民工法律地位初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影响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的要素较多,主要有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和地质环境因素等。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震和降雨;人为因素包括矿山挖掘时的滥挖、爆破工作对边坡的破坏;地质环境因素包括岩体抗压力、地质构造和抗剪切力等。边坡变形与滑坡的主要原因是地质环境因素引起,而导致边坡变形与滑坡的原因是自然和人为因素。
(三)从法制角度研究城市移民的融合性问题
城市新移民概念要求建立或通过改革形成有利于移民城市融入的法律制度。移民进入城市,或多或少会存在一种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的主要表现就是移民与城市市民之间形成的某种区隔(制度、族群、种族和文化等差异)。城市新移民研究思路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如何消除这些业已形成的区隔,而是在于分析这类区隔机制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影响了城市社会多元文化的构成。⑥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也就是说,城市新移民概念将我们的研究思路转为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移民与市民的融合性问题。相应的,移民法律的建设也是要促进这种城市的融合性。
从城市新移民的角度来看法制的视角来源于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⑦ He, Xin,“Why Do They Not Obey the Law? A Case Study of a Rural-urban Migrant Enclave in China”,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Law School, 2004.可参考文章He, Xin,“Why Do They Not Comply with the Law? Illegality and Semi-legality among Rural-urban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Beijing”,Law & Society Review, vol.39, no.3, 2005.该论文主要研究北京地区外来移民买卖经营许可证的行为。在北京,城市新移民相对于本地居民而言是很难取得个体经营许可证的,这是在城乡这一基本区隔下形成的产物。但是,移民群体们却采取了一种半合法化的途径,即从本地居民手中租赁一个个体经营许可证,将自己的移民身份的欠缺通过非法的“合法化”手段转换实现了移民与本地市民及当地政府的有机融合。通过经营权的买卖,城市移民能够获得经营的正当性,从而避免了由于没有生产许可证而带来的相关执法部门的不定时性的干扰和经济处罚;当地的工商部门能够从这种行为中取得较为稳定的税收收入;本地市民则可以从中取得优厚的租金。
对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移民最普遍流行的称谓是“农民工”。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的称谓是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结合,②刘力、程千:《主流媒体话语表征中农民工阶层的形象意义》,《求索》2010年第1期。“农民”表达的是一种社会身份,而“工”表明的是一种职业。这种称谓实际上是在传统“城—乡”思维模式下的表达。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深化,农民工的称谓已经成为了一种阻碍性的污化名称。针对城市移民的污名化现象,已经有学者分别从社会心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角度进行了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其污名的建构过程。③管健、戴万稳:《中国城市移民的污名建构与认同的代际分化》,《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污名的建构过程首先是一种对话式的表征形态(dialogical representations),它体现了承受污名者(城市移民)和施加污名者(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过程和彼此互倚的对话式关系。在这种对话过程中,直接经验、社会互动和媒体影响成为了污名的直接原因;④管健、戴万稳:《中国城市移民的污名建构与认同的代际分化》,《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当有了直接原因之后,污名的持续还需要另一个社会心理过程才能作为一种符号性的标签存在,那就是锚定(anchoring)。锚定(anchoring)指的是一种规约化和世俗化的过程, 它是用一套既有的规则模式来解释身边的事物。⑤管健、乐国安:《社会表征理论及其发展》,《南京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当一种观念经过锚定之后,就会成为人们思维意识中的类无意识现象。也就是说,之后人们会不加思考的将某种意向强加到其认为符合某一标签的事物之上。拿“农民工”这一标签来说,锚定后的农民工概念将之前人们接触过的农民工的直接经验(农民、底层劳动者、生活条件差、弱势群体等)固定化和无意识化,每当人们接触到移居城市的劳动力时,就会不加分别的将上述固化观念强加其上,哪怕有些移民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户籍制度阻碍移民与市民融入。这种制度性的规定一方面造成了移民与本地市民在各种权利方面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深了市民对移民的污名化倾向,从而进一步拉大了移民与市民的距离。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区分身份的识别制度,更是一种分配社会资源的制度,所以对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有学者认为,学术界过分的看重了户籍制度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阻碍作用,从而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其他面向。这些学者认为,户籍制度单方面的改革根本不会起到促进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户籍制度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基本的造成中国下城市化现象的因素,那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① Li Zhang, Simon Xiaobin Zhao,“Re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Under-urbanization: A Systemic Perspective”,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27, no.3, 2003, pp.459-483.也就是说,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连带着资源分配方式甚至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改变。
1.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新移民的融入。
2.移民法与城市新移民的融入。
促进移民融入的另一个法律途径是设立移民法及单独的移民部门。针对中国大规模的农村—城市劳动力转移,中国政府确实进行了一些有利于城市新移民融入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法律制度多是单部门的政策性行为,很少实现多部门的共同合作来推进其移民政策的实施;其中更缺少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有关移民的专门立法,国务院也没有相关的行政立法。②郑尚元:《“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及其法制依赖——职业移民立法及其展开》,《江淮论坛》2014年第5期。针对这种现状,有些学者呼吁中国应该出台一部专门的移民法,并设立专门的移民机构处理移民事务,同时建立一套完善的移民加入市民身份的审核制度。
仅具有文史哲的知识储备与实践经验二者,还不足以成为优秀的评论家,优秀的评论家还需要一个优良的品质——激进的美学锋芒,即要敢说真话。所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是很难的。我喜欢读画家、书法家的随笔,寥寥几句,甚至有语法错误也没关系,全是一些“活色生香”的句子,生动极了,也深刻极了。
将中国的农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按照移民法律及移民程序来处理,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种促进移民融入的方法也符合本文中提出的城市新移民的概念路径。城乡劳动力转移作为一种移民的策略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城乡”二元思维框架,将有利于中国乡城移民与市民的融合。
环保意识,对损坏的元器件、部件等要妥善处理;成本意识,购置元器件时优先选择性价比高的商家(80%学生达到);
3.中央与地方的法制融入。
另一个由移民的融合性引申出来的是探讨中央和地方法制的融入性问题。融合是城市新移民视角下的主要关注点之一,而在政策和法制层面阻碍这种融合政策执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央和地方政策推行方面的不一致性,而这也需要微观层面的法律研究。有学者指出,如今农村—城市的转移劳动力的法律地位具有双重化格局,③唐鸣、陈荣卓:《论我国农民工法律地位的双重化格局——以国家公民与地区居民为分析框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5期。主要表现:一方面,农村—城市的转移劳动力在国家法制层面上与市民具有同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层面,出于地方财政等方面的考虑,对移民权利的规定与市民却有不同。这种双重化的格局状况不能单从督促地方政府施行中央政府的意见的层面来解决,而应该综合考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制与政策的协调性问题。就城市新移民的子女教育问题而言,中央政府将保障移民子女教育的义务下移到了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为了避免财政负担,对这样的政策持有保守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拨给地方学校的经费中并没有考虑到移民子女的情况,所以准许接收移民子女无疑会给学校的财政造成负担,这就是很多学校接收移民子女的前提条件是缴纳一定数量的借读费的原因。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能够看出,解决诸如移民子女教育等问题必须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当中央将某些政策下放给地方时,并未考虑到地方政府并推进相应的政策跟进。学术界应该细致地研究地方与中央的政策融合性问题,为中央制定后续跟进政策提供参考和咨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央移民法制与政策的顺利实施。
(四)城市新移民与中国传统法制的解体与继承研究
城市新移民视角下的法制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村—城市的劳动力移民对中国传统法制体系的解体和继承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城市新移民与原有的乡村社会还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中国传统城乡二元体系下,这种联系更加紧密。从这种视角来看,城市移民实际上是一个中介者的角色:城市新移民不仅对城市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对乡村社会也具有影响。墨菲的《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可谓这一问题的代表作,其从资源论的角度总结出农民工在外出打工过程中所获得的丰富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对于行动者的行为和传统乡村社会造成的影响。①[爱尔兰]瑞雪·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黄涛、王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从法律角度来说,城市新移民对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已经有学者就移民对乡村权力结构的影响进行了论述。蒋先福认为,务工移民导致了中国传统宗法权威地位的下降、宗族结构的解体以及村落习俗的衰微。②蒋先福:《务工移民与法治发展》,第127-128页。杨力关注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中的新农民阶层,而城市新移民由于受户籍制度的影响被其看成是新农民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这些新农民阶层推动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并着重分析其对乡村司法理论产生的影响,倡导弱化“治理”味道的司法实践,以普适化的乡村法治化轨道取而代之。③杨力:《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这些已有研究能够为我们展示:移民能够为法制研究提供一个有力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我们还能够研究中国传统法制和权力体系的变迁问题,揭示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法律体系移植中的问题与传统法的借鉴等问题。
四、结语
从人类学角度来说,法制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化制度。法制改革不仅仅是法律界的责任,而是关系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促进的作用。对于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制度改革,要以新的理念作为基本思想。因此,移民法制改革始终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哲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参与。
东湖开发区紧邻中心城区,依山傍水。区内地势北高南低,湖泊密布,山峦起伏,再加上外围风景区、森林公园等绿化和水面多达200km2。由于武汉市已经进入2015年“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东湖开发区作为武汉市未来建设的重点区域,应积极响应住建部的号召,开展“海绵城市”的建设工作。
另一方面,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移民法制的改革,应该更加注重法制改革过程中自下而上的方式,寻找一种适合法律多方主体的过渡性制度,调整现有法律制度与固有社会体制的矛盾,在法律实践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9)05-0063-08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岭民族走廊民间信仰的多元互动与区域社会整合研究”(17CMZ04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275)。
责任编辑:王 冰
标签:移民论文; 城市论文; 中国论文; 新移民论文; 农民工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学术研究》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岭民族走廊民间信仰的多元互动与区域社会整合研究”(17CMZ045)论文;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