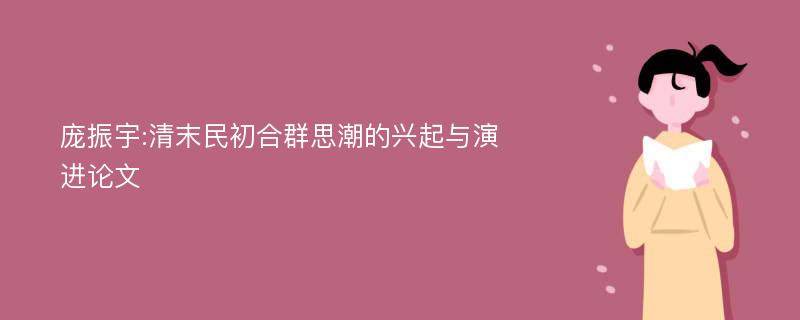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合群立会之说”,合群思潮兴起。20世纪初年,共和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合群思潮的声势更为浩大。晚清政府引入西方社团制度,希冀把合群纳入可控范围之内。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能够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合群仍是改造社会的一个重要思路。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群团的观点。这一时期,合群的主体由社会精英转向工农大众。国民党人亦开始关注和组织工农民众。国共两党对工农民众力量的共同认识,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合群思潮对中国近代社会走向有着重要影响,是实现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助推力量。
[关键词]清末民初;合群思潮;群团;马克思主义;革命
中国先秦时期就有“群”的思想,主要集中在荀子的学说中。荀子在《王制》篇中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并且他还认为,“群”是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社会组织,人欲征服“穷、乱”,首先必须合群。[1]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合群持肯定的态度,并使之上升为人能够异于禽兽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得到政府认可的合群活动主要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对政治层面的合群则加以限制,直到戊戌维新时期才有政治层面的“群”的理论——群学,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合群立会”之说。①目前学界对合群思潮的研究已经取得诸多成果②,但多集中于对清末合群思潮的研究,很少涉及民国成立后合群思潮的演进。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地梳理合群思潮的兴起及其演进历程,并考察合群思潮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
一、戊戌维新时期合群思潮的兴起
清朝初年,刚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清王朝面临极大的政治挑战和社会危机,因此对合群结社活动的防禁措施比前朝更为严厉。顺治九年(1652)、十七年曾两度下令,“诸生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否则“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2](P110)顺治十八年又规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3](P184)这种情况直到清朝末年才有所改变。鸦片战争之后,外敌入侵和国家积贫积弱使合群的愿望通过救亡图存的时代语言表达出来。一些先进之士在西方社会思想的影响之下,认为救亡图强之法在于合群。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卷三十七《礼俗志四》中提到:“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者也。”[4](P911)这里的“社会”就是指由志趣相同的个人结合而成的团体。1890年,康有为吸取从西方传来的政治观点,开始向学生宣传“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5](P19)。从1891年起,他先后在粤、桂等地讲学,认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5](P242)。除了近代民族危机催生合群意识外,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西方式社团对中国新式社团的产生也起到示范作用,并引入合群的政治意识。例如,1887年由新教传教士韦廉臣发起创办的同文书会(1894年中文名称正式改为“广学会”),就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团体,“广学会出版的报刊杂志批评时弊,鼓吹变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变革。[6]
甲午战争之后,合群之论在维新人士大力提倡下,形成颇为壮观的社会思潮。1895年3月,严复在《原强》(发表于天津《直报》)一文中这样写道:“锡彭塞(今译斯宾塞——引者注)者,亦英产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取以名其学焉。”[7](P6)严复借用荀子的概念把斯宾塞的社会学译为群学,表达了中华民族面对列强瓜分应当合群保种的政治主张。同年,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在案语中指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8](P1347)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唤醒民众,强调群体之力在人类生存竞争中的作用,为当时的合群思潮提供了学理依据。
由于学术性的集会比政治性的集会享有更多的自由,维新人士将广设学会作为实现合群的重要步骤。1895年8月,康有为等人倡办强学会。11月,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会先后成立。康有为撰写的《京师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序》和《上海强学会后序》等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合群主张。康有为提出“物单则弱,兼则强”,认为:“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吾中国地合欧洲,民众倍之,可谓庞大魁巨矣,而吞割于日本,盖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也。今者思自保,在学之、群之。”[9](P97)但维新人士公开结社集会,议论国事,对封建统治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因而遭到顽固势力强烈反对。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奏参强学会植党营私,北京、上海强学会相继被封闭。强学会虽然遭到封禁,但是“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至丙申(1896)二月,御史胡孚宸奏请解禁,于是将北京之强学会改为官书局……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谋将上海强学会改为时务报,时务报既出后,闻风兴起者益多,各省志士争(相)醵资,合群以讲新学”[10](P395)。
维新人士在严复、康有为阐述合群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合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们用严复翻译西方社会学所用的“群学”一词,将合群立会之说称之为“群学”[11](P34),并认为中国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自己的“群学”。强学会会刊《强学报》第1号登载的《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一文,认为:“乐群之名,会友之义,先圣所许。后世鉴于小人之党而讳之,是因噎废食、因稗弃禾耳。中国之有会,盖亦古矣。”泰西之所以富强,是因为“外国得我古人乐群之义,安有不强。中国讳言先秦会友之名,安能不弱”。最后,文章提出:“救国之道,莫如敬业乐群、以文会友,能会则大、能会则通、能会则强。”[12]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创立群萌学会,在章程第一条称:“本会以群萌为名,盖因群学可由此而萌也,他日合群既广,即竟称为群学会。”[13](P431)谭嗣同还在《壮飞楼治事十篇》中以“群学”为名大谈合群立会之说,“儒而入会,于是无变书院之名而有变书院之实;释老而入会,于是无变寺院之名而有变寺院之实;农而入会,于是无农部之名而有农部之实;商而入会,于是无商部之名而有商部之实;工而入会,于是无劝工之名而有劝工之实;矿而入会,于是无办矿之名而有办矿之实”,认为“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13](P443-444),他希望以合群立会实现维新变法的主张。
为了排除测试仪器误差导致的测试数据异常,使用了另一套同型号、同生产厂家的机械特性测试仪进行数据对比。经过对比,测试数据仍与初次测试结果相似,证实该断路器本身存在缺陷。
梁启超对合群的阐述最有代表性,表达了这一时期大部分维新人士的主张和诉求。1896年,他根据康有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思想,作《变法通议》。在其中的《论学会》一文中,他认为:“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他提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14](P26-28)这篇文章试图回答如何实现政治整合的问题。随后,他又内演康有为的学说,外依严复的《天演论》和谭嗣同的《仁学》,作《说群》篇。他提出“群者,天下之公理也”,“生而不灭、存而不毁者,则咸恃合群为第一义”。他说:“何谓造物?合群是已。何谓化物?离群是已。……欲灭人之国者,灭其国之群可矣。使之上下不相通,彼此不相恤,虽天府之壤,可立亡矣。”强调了合群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他还通过比较“群术”和“独术”来比较泰西强、中国弱的原因,认为群术是一种有效的治国之术,“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14](P93-94)
合群之说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1897年9月,《知新报》报道:“迩来时局日艰,识时务者,罔不争相淬厉,痛深国耻,以合群之力挽将倒之澜。”[10](P380)1898年2月,《知新报》报道:湖南龙南致用学会兴办,“集思广益,一视同仁,众志成群”[10](P465)。据学者研究,戊戌维新时期有案可稽的学会达72个。[15]这一时期的合群思潮表达了具有维新思想的士绅团结在有为君主周围,以增强社会动员能力的愿望。但是,当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足以支持变法取得成功的社会力量,旧社会势力仍占着绝对优势。1898年9月22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缉拿维新志士。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喋血街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东渡日本,合群思潮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晚清政府在这一时期进行新政改革,也希望把合群结社纳入其可以控制的范围。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会获得合法地位。1906年9月1日,清廷在上谕中称:“著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平和,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24](P128-129)1907年12月24日,慈禧太后懿旨:“著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1908年3月11日,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上奏拟订结社集会律折,请求清廷除了禁止秘密结社外,对其他结社集会应提倡,“其讨论政学,研究事理,联合群策以成一体者,虽用意不同,所务各异,而但令宗旨无悖于治安,即法令可不加以禁遏”。奏折中拟订的结社集会律三十五条,获得清廷的批准。[25]同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26](P59)由此,民间结社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有学者统计,辛亥革命前仅商会、教育会、农学会就有2000多个。[27](P231)这些组织多是在清政府的倡导或许可之下由绅士办理或是以绅士为主体。
二、20世纪初的合群思潮与西方社团制度的引入
戊戌政变后,维新人士仍是合群思潮的有力推动者。梁启超对戊戌维新时期的合群思潮进行了反思,强调“合群之德”的重要性。1901年6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了《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认为,中国“四民中所含小群无数也,然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国民未有合群之德,欲集无数之不能群者强命为群,有其形质无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辈所最当讲求者,在养群德之一事”。文章还阐述了独立与合群之间的关系,“独立之反面依赖也,非合群也;合群之反面营私也,非独立也”,中国需要“合群之独立”。[14](P429)换言之,中华民族只有“善群”“能群”“合群”,才能走上民族的独立富强之路。梁启超还对传统中国的“合群之法”作了理性的梳理并分析中国人不能做到合群的原因。1902年9月16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第十三节《论合群》,认为“优劣之道不一端,而能群与不能群,实为其总源”,合群之义“今举国中稍有知识者,皆能言之”,然仅有合群之表象,而无合群之实举,不但全体国民之“大群”不能合,即使一部分之“小群”也未能合。中国人不能做到合群的原因有四,即“公共观念之缺乏”、“对外之界说不分明”、“无规则”以及“忌嫉”。[16](P693-694)1902年12月,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对《新民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对合群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在于“合群之道”,而真正的合群之道,“当用族制相维相系之情,会党相友相助之法,再参以西人群学以及伦理学之公理,生计学之两利,政治学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开、民气昌,然后可进以民权之说”[17](P506-507)。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组织开展农民工作。《共产党》月刊第3号发表《告中国农民》一文,号召共产主义者及一切革命者“要设法向田间去”,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帮助农民“抢回土地”。[42]如何帮助农民呢?《共产党》月刊第2号至第5号陆续发表有关农民问题的文章,批判否认农村存在阶级分野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号召农民在一个村组织一个“农人会”,在全国组织一个“农人总会”。[43](P159)1921年4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沈玄庐回到家乡浙江萧山县衙前村。经过半年的积极筹备,9月27日,衙前农民协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通过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提出土地“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44](P430)。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组织起来的第一个新型农民团体。衙前附近有80多个村庄也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45]广东海陆丰在彭湃的领导下成立了海丰总农会,随后海丰、陆丰、惠阳三县的农会会员“达到20余万人”。[46](P125)湖南衡山岳北成立了岳北农工会,“会员限于雇农、佃农、自耕农三种”,其他“确可为农民谋利益者”,由农民多人介绍酌量准其入会,加入者达“10余万人之多”。[47](P245)
辛亥革命之后,合群思想有了一个利于广泛传播和实践的政治环境。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地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28](P12)一时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29](P17)。随后,北洋政府亦努力把合群结社纳入政府管理的轨道,颁布了《中央学会法》《商会法》《教育会规程》《农会规程》《林业公会规程》《工商同业公会规则》等法规。民国初年,各类团体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态势。政治社团除了原有的革命、立宪等团体(有的开始向党派转变)外,还出现了反对专制和军阀统治的民主政治社团;经济社团除了原有的行会、商会进一步发展之外,还出现了农、工、商、矿、交通、外贸等业的协会性社团;教育社团从清末的教育会向实践性社团发展。[3](P425)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欧美诸国政治和工运的影响及启发,掀起“工会热”。罗法言等组建了四川省总工会,并得到当时四川都督尹昌衡、张培爵的热情支持。李达寿、常治发起组建湖南省总工会,得到长沙企业界和工人们的积极响应。[21](P46)
先进女性也认识到“合群”的必要性。民主革命志士秋瑾认为女子受压迫的原因是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主张女子通过“学艺”与“合群”取得自立。1905年,她在致湖南第一女学堂的信中说:“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22](P53-54)1906年,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的草章及意旨广告》中说:“本报之设,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22](P31)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秋瑾在为该报撰写的发刊词中称:“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22](P34)秋瑾的好友吕碧城在《中国女报》第2期发表《女子宜急结团体论》,强调:“自欧美自由之风潮掠太平洋而东也,于是我女同胞如梦方觉,知前此之种种压制束缚无以副个人之原理,乃群起而竞言自立,竞言合群,或腾诸笔墨,或宣之演说,或远出游历,无不以自立合群为宗旨。”若在男女间论之,“则不结团体,女权必不能兴,女权不兴,终必复受家庭压制”,因此女子应“急结成一完备坚固之大团体”。[23](P450)
上海、北京在多个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上海在机构养老服务、养老人才、养老产业、行业信用、老年公益5方面优势突出,尤其是老年公益政策创新优势明显,出台了老年教育专项发展规划、建立老年人服务信息管理系统等相关政策。
看到《罪与罚》这个名字自然就会想到《圣经》中的救赎主题,这与作品内容十分贴切。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起名“罪”和“罚”。但是笔者更倾向于于试探性的主题。
与戊戌维新时期的合群思潮相比,20世纪初的合群思潮声势更为浩大,原因是共和知识分子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02年11月,留日湖南籍学生创办刊物《游学译编》。该刊物逐步从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走向革命。1903年5月,《游学译编》第7期刊登《与同志书》称:“亡国灭种之祸迫于旦夕……吾国之人无合群自治之习惯,自私自利,喜独恶群,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虽有公利而不能举也,虽有公害而不能除也。……今日救亡之法,舍合群自治,别无下手之处。”[18](P395、P398)由日本东京浙江同乡会创办的《浙江潮》,是一个革命倾向较为显著的刊物。1903年2月17日,《浙江潮》发表的《国魂篇》称,“新学之士常以合群公德之义提倡奔走而卒无效”,“就不能合群之种种方面观之,则无公德也,无法律也,忌克也,皆是也。而就其归结之总纲言之,则无统一之原质已耳”。所谓“原质”,该作者认为就是“国魂”,即“祖国主义”。[19]“祖国主义何?根于既往之感情,发于将来的希望,而昭于民族之自觉心。”[20]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国内国外发展组织的同时,开始注意工人团体的创建和领导。1906年,孙中山先后派革命党人在香港和广州的机器工人中开展秘密工作。1909年4月22日,以香港机器工人为主体成立中国研机书塾。5月13日,广东机器工人成立广东机器研究公会。中国研机书塾和广东机器研究公会,是革命党人领导的以工人为主体并联合有革命倾向的民族资本家的进步团体。[21](P45-46)
概言之,20世纪初合群思潮的推动者包括前维新人士、共和知识分子和顺应时变的政府统治者。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和民主政治的试行,使合群思潮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发展。清末新政时期的晚清政府和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积极引入西方社团制度,希望合群结社规范化、制度化。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统治并没有能够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遍布荆棘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其中合群思想仍为新的历史时期改造社会的一个重要思路。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合群思潮的转向
五四运动前后,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社团在新的合群思潮中出现。这些进步社团介绍、宣传各种新思想和新学说,一些团体还将自己的主张付诸行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民族复兴典范,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概念和群团思想也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哪里有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32](P446)。群众团体是连接党和群众的“传动装置”。在革命阶段,群众团体广泛联系群众,政党由此拥有革命的群众基础。革命胜利之后,群众团体“站在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协助党和政府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工会、农民组织、共青团及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团体各自组织动员、教育引导和联系服务一定的群众。[33](P368-370)“群众”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但不是一个政治概念。随着马克思主义“群众”概念的传入,“群众”的内涵开始指向“被压迫阶级”,指向“劳动界”。1919年7月,毛泽东提出,农夫“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工人“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其他如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都要联合起来寻求“共同利益”。[34](P373-377)1919年10月,李达在《妇女解放论》中提出:“全劳动界,有合组团体的必要,所以男男女女互相结合起来,对抗那资本家。”[35](P18)1920年7月,恽代英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中把“活动的修养”和“合群的修养”合称为“群众生活的修养”。他说:“我们读书人,多少有些书痴气,总不感觉合群的必要。这一则因为他原从不想做什么社会事业,所以他无需乎群众;再则因为他看不来这些群众种种色色的怪相,所以他不屑与他们相周旋。”但是,“事实的证据,应该可以信平民的能力”,“人家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十几年了,我们到头仍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群众事业,曾经维持得长久”,因此应该注意群众生活的修养。[36](P178-179)这里所说的“群众”是指劳苦平民大众,并提出要相信平民的能力。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a link between lymph node yields and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for colonic carcinoma.
戊戌维新时期和20世纪初年的合群思潮,探讨了群与变、群与强、群与治以及群与会的关系。民国初年,在由探寻改造社会之路的先进分子所推动的新的合群思潮中,“群与强”的话语被放到更突出的位置。而且,合群思潮的影响范围也在扩大。1915年,年仅11岁的任弼时在老师的命题作文《合群说》中写道:“国人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士农工商皆能合群则必能富。富者强之。……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人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30](P10)这说明合群思想已通过教育向青少年普及,以合群求富强。五四运动前夕,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掀起新文化运动。新旧文化思潮的激战,要求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首先组织起来。1919年,《清华周刊》发表王乃慰的《合群》一文中称:“合群,美德也。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先哲有言,良不诬矣。然而,合群之范围则不可不察。同为中国人,则凡中华民国国民应合群矣,然后可以御外侮,跻富强。若一国之中,而一省有一省之合群,一校有一校之合群,南北有畛域,秦楚有径庭,则小团体愈坚固,大团体愈支离矣。……中国之所以弱者,皆未收群策群力之效也。正本清源,当自吾辈始。”[31]作者王乃慰对当时的合群思潮进行反思,思考怎样的合群结社才能使中国能够抵御外侮,真正能够实现国家富强,并且提出要正本清源,由他们这一代新青年担负起历史使命。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派遣维经斯基率领俄共(布)党员小组一行来华,帮助和指导创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7月19日,维经斯基委托陈独秀在上海召开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大会,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并成立包括维经斯基在内的五人领导核心,定名“革命局”,即中共上海发起组。[37]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组织部“在学生中间开展工作,想法设法引导学生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为使革命学生联合起来,组织部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各个城市召集一系列的学生会议。1920年8月17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天津、汉口、南京等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38](P50-53)随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先后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组织。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北京、湖南、广州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相继建立。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把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针对五四运动后打着“工界”招牌的形形色色的工会在上海乘势而起,陈独秀提出建立“真的工人团体”。他在《劳动界》上撰文指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39](P245)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指导下,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在霞飞路渔阳里六号召开。会议提出,目前有五种工会都是妨碍工人的组织,即资本家利用的工会、同乡观念的工会、政客和流氓把持的工会、不纯粹的工会以及只挂招牌的工会。[40](P116)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它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个革命工会。其他地方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开始创建革命工会的活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音》第5期向全国工人提出了四个斗争目标:一,组织工会,专办和工人有利的事;二,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三,增加工人的组织;四,举行游行示威。[21](P80)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并且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41](P4-6)
关于公共图书馆的藏书或电子资源是否能满足该馆读者的阅读需求:55%的读者表示基本能满足;26%的读者表示非常能满足;17%的读者表示不太能满足;1%的读者完全不能满足。对被调查图书馆的总体满意度显示:非常满意的占49%;基本满意的占36%;一般占13%;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读者共计不到2%。由此可见,无论是在资源建设方面还是在总体上看,多数读者还是比较满意的。
关于旅游产业概念的界定,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但共识性的因素主要是围绕着“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等。所以对旅游产业概念可以表述为:“以旅游者为对象,借助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满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吃、住、行、游、娱、购等需求,来实现旅游者精神和物质追求的综合性产业”[3]。
从合群思想的群众基础而言,五四运动前后的合群思潮有了一个新的转向,合群主体由社会精英转变为工农大众。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是扮演中国政治发展主导角色的革命党。致力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人积极组织工会、农会、青年团和妇女组织等团体,同时寻求建设中国新方案的国民党人也重视民众力量。国共两党对工农民众力量的共同认识以及都重视组建工农团体,成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唤起民众和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是孙中山晚年的重要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前后,国民党人也开始关注和组织工农民众。1918年3月,吴稚晖主编的《劳动》在上海创刊,这是全国第一个专门报道劳工运动的杂志。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讲演会中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50](P219)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离粤赴沪,另图根本救国之计。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指示由国民党人主办的《星期评论》,着重对世界与中国的劳工运动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和介绍。1921年,孙中山返粤组织正式政府后,设立专司劳工的部门,并发表了由戴季陶拟定的《广东省工会法草案》。孙中山支持工人运动的发展,造成广州市空前的“工会热”,这一时期他甚至赢得“工人总统”的称誉。[51](P372-373)廖仲恺追随孙中山革命22年,是孙中山晚年最得力的助手。1922年3月6日,廖仲恺在广东第二次农品展览会上发表《农政与农业团体之相互作用》的演说,指出,“苟人民犹是一盘散沙,政府与人民无相互之作用,则民治不能实现,而民国亦徒有其名”,因此实现真正民治“必先使人民自结各种团体”。由于当时中国仍处在宜注重农政的时代,“则农会及其他农业团体,亦应由各地农民自动结合组织,以为介于政府与农民之传导机关”。[52](P158)换言之,在农民个人与国家政府之间应当有农会组织,这样农民才能不再处于分散的孤立的原子状态,才能够有效地制衡政府,保障农民的利益。[53]其他由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闽星》《觉悟》等报刊也都刊出文章,参与讨论劳工组织及劳动问题。
先进的知识分子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妇女问题。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望道认为:“‘女人运动’共有两大类:一是第三阶级女人运动;一是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就是中流阶级的女人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就是劳动阶级的女人运动……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消除‘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平等和不合理。所以第三阶级女人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第四阶级的女人运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因此,为了彻底实现妇女解放就要把劳动妇女组织起来。[48](P78)1921年8月,中共机关刊物《新青年》第9卷第5号刊登了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及章程,肯定了妇女解放是近代“解放历史中的重要部分”,提出中华女界联合会的任务是扩大组织及开展宣传,并规定了具体奋斗纲领。[49](P11-12)改造宣言及章程体现了刚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基本主张。1921年12月,王剑虹在《妇女声》第1期上撰文,明确提出“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有觉悟的女子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的前线,努力反抗一切掠夺和压迫,从根本上去改造社会,建设自由平等的、男女协同的社会”。[48](P94)
四、结 语
中国传统文化对合群持肯定的态度,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团也达到相当的数量规模。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学术社团,东汉后期出现了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民间宗教会社。佛教传入中土后,两晋时期出现了道安僧团、慧远莲社等佛教社团。隋唐时期工商业发达,工商行会组织开始出现。明清时期,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相当普及。明清两代数百年间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各地大量涌现具有同乡会性质的会馆。明清作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时期,对民众的言论和行动均严加控制,因此又出现了一些试图通过抗争改变地位与处境的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3](P23)在中国传统社会,民众在社会生活中需要合群而组织起来时,只要不对统治构成威胁,封建王朝统治者并不严加禁止。中国传统社会里已有的合群意识和潜在倾向,成为清末民初合群思潮兴起的内发性资源。[54](P40)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它就会猛烈地释放出来。
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催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意识又催生了合群思潮。随着西方社会思想、社团观的传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维新时期倡导“合群立会之说”,合群思潮兴起。在合群思潮的推动下,清末的合群结社有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近代志士将西方社团组织上升为西方富强之源,迫切希望在民族危亡关头通过合群来改变民心涣散、一盘散沙的社会现状,并开始建立同志团体,把合群当作改造社会、追求自治、挽救危亡的一种方式;另一种发展趋向是自20世纪初年开始,政府开始引入西方社团制度,并颁布新规制,来改造传统已有的结社,使之获得新生,或者按照西方社团制度建立政府所需要的社团组织。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统治没有让人们得到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因此合群仍是先进分子改造社会、寻求富强之路的一个重要思路,而且共和政体使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从观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合群思想的影响范围也在扩大。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群众”成为被压迫阶级的代名词。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群众概念和关于群团的观点。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新出路就是把劳工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群团观并付诸实施。五四运动前后的国民党人也很重视民众力量,所重视的合群主体,除了精英分子之外,也主要是工农劳动者。国共两党在合群思想上的共同认识,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思想基础。但是,国共两党由于阶级基础不同,对群众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国民党使用“群众”概念时没有阶级性,强调全民性,因此国共两党在合群的实践效果上就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国民党作为以城市精英为主体的政党,也缺乏合适的人才真正深入工农大众之中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在名义上享有对群众运动的主导权,但除了在商民协会、妇女协会之中尚能保持相对强势外,在工会、农民协会之中的影响远逊于共产党。共产党希望在国民革命中以工会、农民协会为主体召开国民会议建立平民民主政权,然后向苏维埃政权过渡。而国民党只是想利用群众运动打倒军阀,并不想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因此掌握军队并且力量强大的国民党在1927年实施“清党”反共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
记者从共建各方签订的《“平安西江”共建协议书》上看到,共建目标主要包括“五个西江”:打造“智慧西江”,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积极推进西江可视化和智能化建设;建设“协同西江”,通过统筹西江沿线各要素和相关职能部门,实现西江一体化发展与管理;建设“绿色西江”,坚持生态文明优先,建立和健全促进西江绿色发展的保障机制,预警、监控与应急体系;打造“文化西江”,通过挖掘和构建西江文化,助推西江文明建设和旅游发展;建设“共享西江”,通过建立健全全方位沟通协调机制,实现西江流域数据、建设、服务共享,互联互通。
清末民初的合群思潮对中国近代社会走向有着重要影响。由于合群思潮的兴起源于近代民族危机,因此清末民初的合群思潮更突出地表现为仁人志士如何建立改造社会、挽救危亡的社会组织,迫切希望改变一盘散沙的社会现实,聚集民气,形成合力,争取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此外,其他社会组织,如作为利益群体聚合的商会、作为地缘纽带的同乡会以及作为灾荒救济组织的华洋义赈会等,也是清末民初合群思潮的产物,它们或由政府所主导或是政府社会治理的补充,同样是中国近代社会向前发展的推动力量。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并综合考虑各指标的可获得性和适用性,本文收集和整理了1970年到2014年176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面板数据。主要变量的选取和统计描述如下。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群学与以群学为名所介绍的西方社会学,名同而实异,“清末群学同名之下,有合群立会之说、社会学和广义社会科学之别”。参见姚纯安:《清末群学辨证——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②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 “群学”》(《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二十世纪初年的 “群学”》(《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虞和平:《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社团的兴起——以戊戌学会为中心》(《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3期);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参考文献]
[1]王兴洲,李鹏忠.荀子的伦理思想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J].东北师大学报,1990,(6).
[2]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中国社团研究会.中国社团发展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4]黄遵宪.日本国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
[5]楼宇烈.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孙邦华.李提摩太和广学会[J].江苏社会科学,2000,(4).
[7]王栻.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王栻.严复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2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1]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M].北京:三联书店,2006.
[12]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N].强学报,1896-01-12.
[13]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1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5]闵杰.戊戌学会考[J].近代史研究,1995,(3).
[16]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2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7]黄遵宪.黄遵宪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8]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0.
[19]飞生.国魂篇[J].浙江潮,1903,(1).
[20]飞生.国魂篇(续)[J].浙江潮,1903,(3).
[21]王永玺.中国工会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22]郭延礼.秋瑾集·徐自华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3]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32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5]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奏拟订结社集会律折[J].东方杂志,1907,5,(4).
[2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7]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8]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第2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9.
[29]傅金铎,张连月.中国政党·中国社团概论[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1]王乃慰.合群[J].清华周刊,1919,(177).
[3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4]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35]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6]恽代英文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7]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J].中共党史研究,1996,(3).
[3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9]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0]共产主义小组: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4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2]告中国农民[J].共产党,1921,(3).
[43]李永芳.近代中国农会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4]陈独秀.新青年:第9卷[M].北京:中国书店,2011.
[45]陈晓蓉.略论浙东衙前农民运动[J].江西社会科学,2003,(11).
[46]郭德宏.彭湃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47]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史料汇编[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
[48]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81.
[49]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0]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1]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52](美)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53]姜义华.为建立“一个正式的民主国家”夯实基础——国民党改组时期廖仲恺民主思想的新发展[J].社会科学,2008,(11).
[54]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9)05-0159-10
庞振宇,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77)
【责任编辑:王立霞】
标签:思潮论文; 北京论文; 中国论文; 组织论文; 西江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论文;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