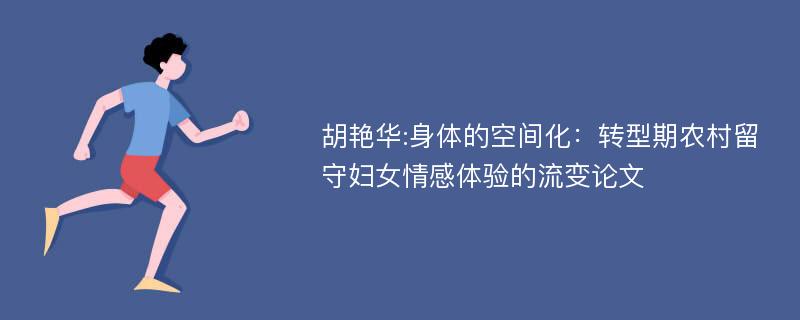
摘要:以湖北Z村的田野调查为例,考察农村留守妇女的情感体验与生活空间的关系,阐释农村家庭两性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历史与变迁。在乡村社会从“封闭的空间—流动的空间—开放的空间”的转型过程中,留守妇女身体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女性情感体验从对传统道德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用主义和本真的依赖。这样一个情感体验流变的过程,不仅是身体在社会空间中的实践,更是凸显出农村家庭中男性主导权力的逐渐式微,家庭关系也朝“稳定—半稳定—不稳定”的方向变化,留守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增强,并逐渐成为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社会政策实践的新主体。
关键词:农村留守妇女;身体;空间化;情感结构
一、引言
农村留守妇女作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群体,国内学者有较多关注,主要集中讨论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1](p28)家庭劳动、[2](p39)生活现状及困境、[3](p73)婚姻关系[4](p130)等方面。国外学者多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关注中国留守妇女的社会福利及其在农村家庭中的社会地位。[5](p186)从已有研究来看,多为横向研究,缺乏历史的时空维度,也很少将留守妇女的情感体验纳入社会结构的框架,因而忽视了其主体性。本文借用威廉斯[6](p48)情感结构的概念,揭示留守妇女社会生活中贴近本体层面且尚难以言表的变化。情感结构类似于一种存在模式,涉及人们价值和信念的选择,与个人的情态和感受相关。不同的情感结构或存在模式之间的差异往往是切实可感的,所以,情感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勾画出时间迁徙过程中所可能感受到的差别,也可用来描述时代变迁在社会成员身上所留下的烙印。这个概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历时的视角去观察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揭示处在空间流变之中的社会体验。[7](p96)
国内最早研究反思性教学的学者之一为熊川武。熊川武(1999)[2]阐释了对反思性教学的认识:“教学主体借助行动研究不断探究与解决自身和教学目的以及教学工具等方面的问题,将‘学会教学’与‘学会学习’结合起来,努力提升教学实践合理性使自己成为学者型教师的过程。”任庆梅(2006)[3]论证了反思性教学、个案研究和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最终认为反思性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教师的创新实践能力。
对于情感的理论研究,国外学者曾经做过不同形式的讨论。社会学家涂尔干将情感视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认为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完全是由理念和情感组成的。[8](p495)韦伯认为理性化的动机和后果都涉及情感的因素。齐美尔则直接分析过诸如感激、羞愧之类的情感现象。[9](p131)特纳在其《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中专门讨论了情感理论,美国社会学会主席马塞曾发表“人类社会简史: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起源与作用”的就职演说,此后社会学主流开始转向对情感这一研究主题的经验研究。从相关经验研究来看,有学者关注美国从事服务工作女性的情感生活、[10](p21)讨论意大利女性经济安全感与生育压力之间的关系、[11](p233)也有从身体的角度研究女性的恐惧感、性别认同与暴力等情感体验。[12](p1826)国内也有学者关注情感研究,如成伯清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国外情感理论的发端和演进做了系统回顾,[13](p42)并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去考察情感结构与社会变迁的关系,[7](p97)也有学者从经验的层面分析情感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14](p19)对于留守妇女情感的讨论大多持心理和问题的视角,如留守妇女独守空房,普遍缺乏家庭安全感,[15](p46)同时性压抑对留守妇女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造成影响。[16](p119)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宏大的情感理论还是微观的经验研究,都忽视了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和微妙的情感体验,而这对我们理解乡村社会家庭结构的历史变迁尤为重要。鉴于此,我们在访谈中将情感与身体结合以此获得一种微观的主体性,同时将留守妇女的情感体验与乡村空间结合来透视一种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从而更完整地阐释农村家庭两性关系和权力的历史与变迁。
本文以湖北Z村的田野调查为例,来考察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的情感体验与生活空间的关系。Z村现有一个村委会,共有五个大组,十个小组,全村均为汉族人。现有住户625户,总人口约2307人,劳动力1270人,其中男性690人,女性580人。Z村是典型的农业村庄,现有耕地总面积为2749亩,以种植棉花、油菜、玉米为主,Z村现在的青壮年男人多出去打工,大部分去深圳、山西、广州等地,以建筑、煤炭、服务业为主,已经登记在案的外出打工者为676人,其中到周边县市务工者为174人,其余均在省城或外省打工,占外出打工人数的74.26%。从村主任口中得知Z村平均每家都有男人外出打工,村子里留守妇女占多数,她们常常在一起休闲,只要参与她们的活动,很容易接触。本研究通过参与观察和个案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将留守妇女按年龄划分为不同的时代,即55岁以上的为第一代留守妇女,35—55岁之间的为第二代,35岁以下的为第三代,收集三代留守妇女的口述生活史作为分析资料。
二、第一代留守妇女的空间化:主体性的消解
空间化具有流动性和共时性特征,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过程与人类活动相互干预形成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力量,它反过来指引、影响与限定人们在生活中的行为与方式。[17](p44)唯有女性情感体验的时间之网能够把断裂点在历史的空间中衔接起来,时间性以生命此在的方式展开,女性的历史将在女性情感和关系的空间里复活,并以这种方式显现历史的另一种延续。[18](p40)人类的任何情感都是具有空间性的。情感的空间化使我们无法将身体置于社会生活之外。人类通过社会活动与流动,将空间变成了一种身体能够感知和把握的存在,也是一个身体和世界共存的一般环境,即德里达所说的身体在场交流的空间。[19](p15)在这个空间中,身体本身具有的物质特性来显示个人情感与社会意义;同时,话语对身体的物质特性进行遴选和凸显使身体具有情感和文化意义。正如在商品化的背景下,身体被阶层化,成为创造身份边界的重要工具。[20](p30)身体与情感的商品化和阶层化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身体与情感的空间化还鲜有研究。正因为社会对待身体和情感的方式离不开社会一般环境即空间的影响和界定,所以本研究用空间化的概念来看不同时代Z村生活空间对留守妇女身体和情感体验的形塑,以及在同一时期关于道德的话语是如何在Z村被传播和实践的。
由于各区铁矿成因类型的不同,组成的主要铁矿物不同,现通过对各类矿床矿区分布情况、矿床规模、成矿特征、矿床成因对比分析,预测下一步找矿方向。
红玉说:“以前忙的时候我老公都会回来帮忙,我们经常见面当然感情不错啦,现在钱是挣得多,但平时都不在家,打电话也就是关心他儿子,都老夫老妻啦,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他蛮肯干在外面蛮辛苦,娃儿读书都靠他啊!说实话我也不是喜欢狗子,我主要是想找个能帮忙做事情的男人,我经常一个人在家里也蛮烦,找个人帮忙有什么错哦,再说这种事情村子里多得是。”
个案:小黄,33岁,10年前嫁到Z村,丈夫小黑在深圳做建筑工,孩子住校,平时和八十岁的婆婆在家。小黄从来不下田干活,她害怕田里虫子多,太阳大不想晒黑,农田就租给别人了,只留下菜园。八十岁的婆婆每天做饭、洗衣、种菜园。小黄几乎不和婆婆交流,觉得没有共同语言。她认为老公挣得钱够花就可以了,也不想出去打工那样太辛苦,现在每天晚上和几个姐妹一起跳广场舞,白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吃完早饭就开始手机上网,老公离得太远也很忙几乎没有时间关心她,所以小黄现在每天都在网上和几个男性朋友聊天,觉得这样能找到心里的安慰,不然就会处于孤独和郁闷之中。婆婆除了知道小黄喜欢玩手机,几乎完全管不了小黄的事情。当然,外面的新信息和国家的新政策,她们也很关注,小黄现在和几个姐妹自发成立了“心理扶贫互助小组”,她说是为了相互之间的心理疏导,也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
相反阿银就不同了,她在四十年前就成了村民口中的“疯婆娘”,常常会在村子里看到她身着鲜艳的绿色绸布衣服,头上别着大红绢花,每天都会从村东头游荡到村西头。只因阿银的男人会很多手艺,在外面做弹花匠和木匠,常常要走村串户,每个月才回家一次。阿银是个讲究的女人,年轻的时候爱好穿着,村子里的人都觉得她和大家穿着不同,有点伤风败俗。她常常去找村东头的染匠给布料上色,一来二去就有人说她和染匠的闲话。最初是阿银的嫂子告诉了她婆婆,阿银的男人回家就将她暴打了一顿,然后把阿银抓到族里的祠堂接受长辈们的审问,因为阿银不承认也不磕头认错,于是就在祠堂跪了两天两夜,期间不时有看热闹的女人过来朝她吐口水,因为没有认错就没有让她吃饭。如果是其他的事情可能会有娘家人过来帮忙说话,但阿银的事情被人们认为是“极不光彩的丢人事”,所以没有人出来帮她。阿银晕倒后再醒来就变得痴呆了,婆家就一直让她住在柴房。染匠也因此被赶出了村子,再也没有回来过。人们都说阿银疯了,因为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但奇怪的是,天黑后阿银永远认得回家的路。
空间化的意义在于空间对人所做的分类。在Z村第一代“男将不在家的婆娘”并不止她们两个,如果将她们的生活轨迹做分类,可以看到两种类型:一类是阿金型,在当时的生活空间中被视为留守妇女“守规矩”的典范,意在告诉人们想在村子里好好生活的,就必须像阿金那样按照族里长辈的要求不断规范自己的言行;二类是阿银型,即“不守规矩的”留守妇女,在当时的Z村,人们从来没有想把他们眼中的“疯子”送到精神病院或者治疗,只要没有暴力行为就不会被锁在家里,往往是让她们自生自灭地在村子里活动,但是如果谁家的孩子不听话或者哭闹,大人就会吓唬说“再哭就让你去跟疯子过”,如果有村子里的女人做出格的事情,就会被人警告“不要做第二个阿银啊”,这或许就是阿银在村子里存在的经验及意义。
从村史的记录来看,在阿金和阿银生活的男耕女织时代,“出轨”事件鲜有发生,Z村几乎没有家庭离婚。村子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局限在家庭成员和亲属之间,族长或长辈所代表的父权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空间中无处不在,并成为一种凝视的眼光和规范妇女言行的道德话语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当权力把身体和情感纳入一种体系化的规训体制中,这种社会空间就成为一个道德空间。而那些“男将不在家的婆娘”无疑成为人们凝视的主要对象,因为想象的目光无处不在,所以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凝视的要求调整并规范自己的身体实践,以压抑的方式指导身体实践,比如阿金型。而阿银型的留守妇女则被作为空间中一种另类的存在,不断地去提示人们要按照既定的规范去指导身体实践,可以无视自身的情感体验和需求,身体成为单元性的封闭之物。这是第一代留守妇女身体的空间化,即父权的凝视转化成一种集体意识指导人们的情感实践,个人的情感遭到忽视,因为身体处于凝视之中,情感也无法自由表达,个人的情感在这样一个封闭的话语空间中没有正面地位。
从全球角度看,西欧、北美、日本三个地区的导航电子地图行业起步比较早,历经十几年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市场正逐步成熟。中国汽车自主导航市场从无到有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且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从国内外技术发展看,当前研究的热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桃花说:“我是蛮相信我家男人的,狗子是老实人,都是被红玉迷坏的!”
三、第二代留守妇女的空间化:身体与情感的亲和
如果说传统封闭的空间和社会制度的安排,赋予个人道德以无比的重要性,那么改革开放相伴随的民工潮使得Z村逐渐转变成一个流动的空间。人们对价值的认定方式开始发生改变,原先的道德判断依据于特定的家族伦常观念,而现在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开放且抽象的市场竞争体系。这种竞争体系将一切事物和行为都置于空间中,同时抽取了一切事物自身内在价值的基石,于是,基于情感纽带的社会团结开始逐渐解体了,[13](p46)人们开始以一种挣钱的能力来判断家庭社会地位的高低,那些留守老人通常被刻板印象地看成无劳动能力的依赖者,[5](p187-204)这样一种话语使得长辈所代表的父权开始在村子衰落。Z村进入男工女耕时期,村民的快速流动,也导致自我定位和认同的参照系统的紊乱。[13](p45-48)Z村传统“三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方式已被“独守空房”所取代,留守妻子与打工丈夫之间聚少离多几乎成了一种常态,双方对家庭的责任感开始被一种实用性代替,“找能够帮忙做事的男人”成为第二代留守妇女“出轨”后的一种借口,并在村民眼里逐渐变得司空见惯起来。[22](p142-144)来看以下案例:
Notes(译者注释):“From the novel Shui Hu, Li Kuei was a peasant rebel. Sung Chiang, the leader of the outlaws, was a capitulationist.”[5]294
V领毛衣适合身材微胖的女生,宽大的V形领和宽松的剪裁,能够很好地掩盖身材赘肉。宽松的款式,穿起来轻松舒适,并且有足够多的搭配空间。可以选择上宽下紧的搭配方法,让微胖体型更显高挑;也可以内搭吊带裙温柔优雅,或是连帽卫衣帅气有范。想要简约好搭,黑色和白色是不错的选择。
在福柯看来,规训的身体是具有缺失感的,保持这种缺失感的一种手段是把被规训的身体置入一种等级体系中。[21](p168)这样家族就成为这种体系的载体,族长或家族中的长辈则代表了一种权力,在其中身体持续地、合理地处于臣服状态,这是封建男权秩序为她们规定的生命本质存在。正如Z村这些男人不在家的婆娘,她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依赖于他人的承认,即在个体化与社会承认之间具有内在的相互依赖性,一旦破坏就会被否定,导致认同或身份的危机,所以她们最好是逆来顺受。而对不愿意接受规训的人,谩骂和否定首当其冲,甚至没有人愿意去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她们的存在破坏了空间中的某种道德持续,对权力形成一种挑战。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忠诚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情感,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有关。[13](p43-45)男耕女织时代的个人处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闭空间中,无论是家庭、邻里、民族还是国家都对女性的忠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并形成一种地方性的共同情感和道德话语,女性的身体和情感也被纳入这种社会关系中。从社会学角度看,无论“阿金型”还是“阿银型”,她们不同的行为和情感经历都表达了生活世界情感体验的各种可能性,但呈现给我们的却是第一代留守妇女主体性消解的状态。在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封闭的社会结构中,道德话语将她们同一种不可理喻的绝对忠诚之间发生关联,并表现出一种无法摆脱的依附性。
狗子说:“红玉是人家的老婆,和我没得关系,我只是有时候给她帮忙,当然是要和桃花过日子啦!”
因此,在跨境电商环境中分析消费者需求亟需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获取真实交易的消费信息,通过电商平台、行业组织、工商业公司、咨询公司等多渠道研究当地消费文化、生活习惯、商品需求等内容,帮助中小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对销售市场做出科学预判,提高新产品上市成功率,进而降低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二是如何将数据变现以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企业需根据数据信息进行客户细分,并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体现在网页设计、文字描述、产品包装、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尽量契合消费者偏好,降低消费者因地理距离产生的感知风险,提高其消费意愿,进而提升海外市场营销效果和市场开拓效率,为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发展提供源源动力。
在Z村待久了,我们发现对于此类事情的处理方式,村民开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理性”和一致性,即当事人通常当作没事情发生一样,而我们所说的“被戴绿帽子的人”或“受害者”采取的态度则是“替自己的妻子(或丈夫)辩护”。对于第二代留守妇女,改革开放前后她们正值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大量向外流动给她们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改变,也推动了Z村原有两性关系的变化,同时被动摇的还有Z村传统婚姻家庭观的价值取向——由封闭空间中的“唾弃+惩罚”到流动空间中的“接受+漠然”。村民现在的看法是“人家两口子的事情,不用我们瞎操心”或“时代变了,年轻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基于村民当前的“理性”想法,打工丈夫回家后是不会有人主动告诉他这些事情的,加上当事人的反应都是无所谓,所以在今天的Z村,因为出轨而离婚的第二代留守妇女家庭并不多,也就是说在第二代留守妇女身上可以看到两性关系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家庭结构基本上是处于半稳定的不确定状态,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她们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和身体实践。
随着生产方式由男耕女织转变成男工女耕,家庭成员从双系结构到单系结构变化,丈夫在家的缺位必然导致家庭功能的部分缺失,家庭也从需求共同体转变成选择性亲密关系,留守妇女可能因为某种互惠而选择与他人发生某种暧昧关系,正如留守妇女红玉找狗子帮忙,这种关系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依赖或理性。在这个身体自由流动的社会空间里,各种话语体系会经历各种转移或变形,传统的父权凝视和道德话语不再适用于情感体验的实用主义,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与情感需求,[23](p125)身体与情感发生联系,是第二代留守妇女身体的空间化。在Z村同样的地理空间中,第一代和第二代人的身体与情感体验遭遇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话语空间,这种话语空间的力量在现实中形塑了留守妇女的社会关系和交往行为。当封闭的空间转变为流动的空间,村落中原有的家族和长辈权力开始衰落,村落共同体控制个人、维持特定秩序的能力削弱甚至开始消失。留守妇女从“被凝视”到“故意忽视”,这种“故意忽视”使第二代留守妇女关注自己的情感需求成为一种可能,并以此指导身体的实践,从而身体与情感产生一种亲和,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对待身体的方式即选择性地亲密关系。
四、第三代留守妇女的空间化:甜蜜的悲哀
第三代留守妇女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在她们生活的时代,留守妇女已然成为一种标签。曾有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男性每年在外时间为10~12个月的比例最高,省外务工丈夫回家的频率最低,半数每年仅回家一次。[24](p110)从Z村外出打工家庭的统计数据来看,仅丈夫在外打工的“男工女耕”型家庭占76.62%,其中丈夫在外省打工者占此类家庭的92.49%,昂贵的回乡路费和“请工”的出现,使得打工者传统的季节性返乡也显得多余,他们一般是在春节期间从务工地返回家乡,在家停留的时间为7-15天。在Z村,许多刚刚结婚的80后夫妻都是共同出去打工,但有孩子之后女方就会回家照顾孩子,家中的老人则继续下田劳动。这种“男人打工—女人看孩子—老人下田”的家庭模式看似稳定,但在情感上却将第三代留守妇女置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之中,个人孤独的困境带来的一种现象就是人们越来越偏向于实际的感受,而持久的和稳定的情感关系,在心灵结构中越来越处于边缘的位置,乃至遭到压抑和遗忘。[25](p70-76)她们每天都花费大量的时间看QQ和朋友圈,因为网络可以轻松地将她们和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整个世界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呈现在她们面前。网络构建的开放空间,让不会玩朋友圈的留守老人觉得自己落后了,而年轻妇女则很喜欢这种时尚的交流方式和体验,可以暂时沉溺其中,不关心生活的理想和目标,更多的是直接关照人本身,或者只在乎个人当下之感觉。[7](p97-99)来看以下案例:
阿金,78岁,看起来很随和,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很标致的女人。阿金8岁到她男人家做童养媳,16岁生了女儿,20岁时生了儿子,在其他姐妹们都生七八个孩子的时代,她终生只生了这两个孩子,因为她男人是船员,总是在外面跑,很少回家,每年只回家一两次,每次只在家里待两三天,从生完儿子以后她就过着无性的生活。但阿金觉得这很正常,一来她在家里没有说话的权力,公婆不让她过问男人的事情,如果她多话公婆就不会让她吃饭;二来在那个时代村子里的人都很羡慕她男人在外面工作,每次回来都给孩子带糖果,而且她男人打扮很时髦,让她觉得很自豪。而她就不敢穿太花的衣服,因为她男人不在家,如果穿得太显眼,就会被村子里的人说闲话,这样传到她公婆耳朵里,她就要被数落,妯娌们也不会理她,那她的日子就很难过了,严重一点可能还要给长辈敬茶磕头赔罪。所以阿金总感觉村子里有很多双眼睛在背后盯着“男将不在家的婆娘”的一举一动,至于她男人为什么回家也不和她亲近,她那时候是既不敢想也不敢问,说出来那肯定就是不守妇道。而她就和村子里多数女人一样平安过到现在。
八月的一天,Z村西头闹哄哄的。走近一看,原来是狗子的老婆桃花(46岁)用菜刀把红玉(44岁)的胳膊砍伤了,狗子已经用摩托车把红玉送去诊所包扎,而桃花仍然怒气冲冲地在人群中叫骂。从叫骂的内容来看,是说红玉勾引她老公狗子,二人早有奸情,最让桃花不能忍受的是狗子最近经常打她,据说这也是红玉唆使的,她忍无可忍所以砍伤红玉。桃花喋喋不休地骂了半小时后,在一群中老年妇女的劝说下,终于收工回家。红玉被砍伤的事情发生后,红玉老公寄了五千块钱要她在家休息,没事情就出去打牌。另外红玉老公打电话警告狗子夫妇不要欺负红玉老实,要狗子赔偿医药费五千,放话说不赔钱就等着挨揍。狗子夫妇经中间人调解协商最后赔偿红玉三千元,此事也算告一段落。现在几乎整个Z村的人都知道红玉的事情,红玉也在公共场合不避讳,比如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炫耀,昨天打牌的钱是私下找狗子拿的,今天桃花出去了刚好晚上要狗子到我家吃饭……。三个卷入此事件的当事人态度也开始心照不宣。
个案:小花,28岁,Z村人,家里有姐妹两人,她是老大,所以父母没有让她出嫁,给她招的上门女婿,丈夫阿红在西藏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家里还有十几亩农田,农活都是小花六十多岁的父母干,小花为了照顾八岁的女儿就在Z村一家超市收银,阿红刚开始出去打工的时候还会每个月寄钱回家,现在只是过年回家才给钱,平时和小花交流也很少。小花觉得阿红可能外面有人,所以她也私下交往了男朋友。尽管父母认为她和阿红可以凑合着过日子,但是小花坚持认为这样的生活很没有意思,说不定哪天就离婚了,也不再让父母过问他们的事情。小花很喜欢QQ,几乎每天都会更新,空间中转的文章基本都是一种私人化情感的表达,比如“有时候,我真想喝醉一回,因为太多无奈。有时候,就是想大哭一场,因为心里憋屈。有时候,就是想疯癫一回,因为情绪低落。……有时候我很累。”尽管常常有情绪化的表达,但每天的生活还是继续,她通过网络也知道了更多信息,常常给家人讲解农村各种新发展,关于精准扶贫的做法她也了解。现在村子里给每家每户都设置了垃圾桶,她就主动邀请几个姐妹参与垃圾分类的活动。她觉得这样做更能体现她们和父母那一辈人的区别,她希望农村能够建设得更好,这样男人就可以不用外出打工了……
在Z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直到人民公社时期,传统是男耕女织,妇女主要是在家里纺线织布,兼做家务,种田则以男劳力为主。据该村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回忆,她15岁就嫁到Z村,她是家里的小媳妇,四十岁之前从来没有上桌子吃过饭,那个时代坐在桌子上的都是家族里的长辈和男人,外出都是男人的事情,村子里很少有女人出门,她至今都没有出过这个村子。她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且同质化的乡村空间里,村子里的人相互都认识,每天活动的都是同样的人。那个时代还没有“留守妇女”这个概念,村子里很少有男人出村子工作,极少数男人在外工作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妇女被称作“男将不在家的婆娘”,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她们就是那个时代的“留守妇女”,阿金(化名)和阿银(化名)就是这样的两个女人。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代留守妇女情感表达的变化,即情感体验转变为一种诚挚开放的本真表达,更加关注自身的真实感受,甚至可以看到一种追求个人幸福和价值的强烈意识。这涉及信息化带来的情感意识的变化,诚挚要求披露的事情必须是真的,本真是说只要是个人的真实感受,什么事情都可披露。这种社会氛围和情感表达所隐含的新规则,实际上崇尚的是做一个赤裸的人,就是所谓的情感族。[13](p43-47)情感族热衷在网络上真实表达自己的个人感受,形成一个开放的释放压力的空间,而村庄中曾经掌握话语权的长辈们因为不懂QQ和朋友圈,几乎无法察觉她们情感的变化,当然更加不可能对她们形成一种感情上的“监督”。
信息化带来的开放便捷也让人们更多关注留守妇女的身体和情感,甚至将其看成一种社会问题。与传统留守妇女身体的空间化不同,第三代空间化带有浓厚的社会结构性色彩,因为它绝不仅仅只是情感的问题,而是集中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问题。留守妇女开始生活在一种开放空间的综合话语中,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对留守妇女的身体和性压抑保持关注,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夫妻分居和性压抑对婚姻关系的稳定构成了一定的潜在威胁;[26](p138)普通大众认为关注留守妇女,其实就是在关注农民工,只有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化解,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和谐,经济的发展才会更平稳;在网络空间则将留守妇女称为“体制性寡妇”,各种吸引眼球似的新闻也层出不穷。由此,家庭的稳定一旦与社会的和谐结盟就形成一种维护稳定的结构性话语,甚至形成了与前两种空间化相对抗的留守妇女互助机构,具有很强的帮扶和制度功能,而政治和社会的眼光就这样结合成为一种新的猎奇式的凝视。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空间中,她们的身体与情感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弱势群体的社会问题,并被不同阶层结构的人群所凝视,而她们自己作为被凝视的主体却习焉不察。
如果仅用道德批判来看出轨事件略显不完整,而“甜蜜的悲哀”不失为当今生产方式下两性关系的隐喻与写照。“甜蜜的悲哀”原是西敏思(Sidney Mintz)《甜蜜与权利》中的概念,曾被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用来讨论西方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宇宙观及其文化观念形态,指的是西方现代性所包含的对人性的双重解释,即一方面认为人有权利从各种外在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认为这种解放与资本主义造成的剥削和殖民主义侵略的悲哀不可分割。[27](p67)正如Z村留守妇女性压抑决绝的方法采用心照不宣的出轨方式,如果将出轨看成是打工者与留守者身体上的解放,那么他们试图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看似对所谓幸福和快乐的追求,同时他们也背负着社会压力;另一方面对配偶出轨的报复心态,也暴露出人性的挣扎与悲哀,而这种悲哀是结构性的社会流动所导致的,是现代性对人的一种剥夺和吞噬,而身体则以特别强烈且非常痛苦的方式承载着社会结构。我们用悲哀一词是因为人们怀有太多的无奈和焦虑,将生活界定为追求幸福的人长期看来无一幸免都是不幸福的。每个家庭在组建的初期都有和谐稳定的想法,外出打工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让未来的生活更幸福美好,但物质生活的满足最终替代不了打工者与留守者精神和身体上的压抑。
1975年8月,中国河南省南部淮河流域受台风尼娜影响造成特大暴雨,导致60多座水库溃坝,近万平方千米受灾,死亡人数则据不同资料从2.6万到24万不等,是目前世界上破坏程度最大的水库溃坝灾难。
五、余论
在Z村,诸如此类的故事还在上演,Z村人对待出轨的态度也透视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追求自我享乐的个人,原本被指责为罪恶道德的缔造者,现在看来似乎变成可以原谅,这就是道德变迁的结果。在男耕女织时期,村子里很少有人从事副业或休闲,外出打工者不多,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空间中,长辈所代表的父权形成一种道德凝视,人们自觉或无意识地都会在道德话语形成的权力中规训自己的身体,而留守妇女的身体几乎被架空为一种沉默的无思想的状态,但共同的田间劳作在家庭成员和夫妻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互动和情感联系,家庭结构和关系都比较稳定。
改革开放之初外出打工的一代人,处在社会流动的早期,男人被卷入辛苦的外出打工生涯中,女性在一开始就被纳入家庭领域,负责照看孩子和田间劳动,男人和女人都被纳入新形式的流动空间,两性关系被重新安排。这样一种两性关系框架,符合“二分的现代性”的准则,[28](p102)在这一框架中,一种新的依赖形式逐渐变得重要起来,那就是女性越来越需要依靠丈夫的收入,与此同时,丈夫也需要她长期在家劳动和照看小孩,才能在打工地正常工作。定期和季节性返乡都为正常家庭功能和夫妻亲密的维持起了补充作用,长辈所代表的绝对父权开始衰落并以一种理性的眼光和话语出现,即留守妇女的出轨往往源于一种实用主义的需要,而家庭结构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徘徊,也就是半稳定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生的一代人,农村劳动力的长期外流使家庭逐渐失去了工作和经济单位的功能,并与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新的关系。夫妻存在长期分隔两地的问题,使得两性情感维系和责任感降低,从而对婚姻的忠诚和家庭责任感都有不同程度的冲击,夫妻更有可能形成选择性的亲密关系。在开放式的网络空间中,人们追求一种本真的表达,留守妇女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和情感,父权的衰落使得道德话语的凝视几乎成为不可能,农村家族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在改变。出轨变得更加习焉不察,这种开放式的情感体验为新的两性关系的形成提供更多的可能,家庭关系也开始变得不稳定。
借助于情感结构,试图把握的是留守妇女正在生动上演和切身感受的情感意识和关系,是一种相互连接而又彼此紧张的鲜活的实践意识。因为情感结构中的核心要素是情感,包括暧昧性、对立—过程效应、情感满足三个方面,故情感的演变逻辑势必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封闭空间中人们可能会
想象或建构一种情感暧昧性,流动空间中的情感体验冲突和理性并存,而开放空间中的情感族更多追求的是一种个人情感满足和价值的体现。我们从历史和批判的角度看到了女性身体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女性情感体验从对传统道德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用主义和本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情感体验开放式的两性关系,这样一个情感体验流变的过程,不仅是身体空间结构的变动,更是农村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动。尽管我们能够看到时代变迁中女性的自主性地位和自我意识的提升,但两性出轨报复的心理长期存在也可能引发婚姻危机,结果是可能导致农村家庭关系的重新组合。在未来可能会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这与追求幸福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那就需要我们去关注特定生存境遇里女性的生命情态,[29](p161-164)同时对乡村家庭伦理做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人们有可能批判理解旧的经验。
RIRI是泌尿外科临床领域中最为常见的病理生理过程之一,肾脏组织的血流灌注丰富,且对缺血再灌注损伤极为敏感,如果术中肾脏组织缺血时间过长,不仅可导致急性肾小管坏死,更可能造成急性肾功能衰竭[5],这是肾移植术后肾功能难以恢复的重要原因,并且与移植肾脏之存活率密切相关。UW保存液的应用虽然已经从几个方面改善了移植后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①KH2PO4作为氢离子缓冲液,能有效减轻细胞酸中毒;②MgSO4、地塞米松具有膜稳定的作用;③还原性谷胱甘肽作为氧自由基清除剂;④别嘌醇可抑制氧自由基形成;⑤大分子量的羟乙基淀粉有效防止细胞间质肿胀。但其保护移植肾脏应对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仍远远不够。
参考文献:
[1]刘巍.西北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来自甘肃省的调查发现[J].妇女研究论丛,2012,(5).
[2]张原.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劳动供给模式及其家庭福利效应[J].农业经济问题,2011,(5).
[3]许传新.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0,(1).
[4]叶敬忠,吴惠芳.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婚姻关系的影响[J].中州学刊,2009,(3).
[5]Tamara Jacka.Left-behind and vulnerable?Conceptualising Development and older Women’s Agency in rural China[J].Asian Studies Review,2014,(2).
[6]Williams Raymond.Marxism and Literature[M].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7]成伯清.代际差异、感受结构与社会变迁——从文化反哺说起[J].河北学刊,2015,(3).
[8][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9]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10]Arlie Hochschild.Emotional life on the market frontier[J].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1,(21).
[11]Francesca Modena,Concetta Rondinelli,Fabio Sabatini.Economic insecurity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The case Italy[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14,(5).
[12]Elizabeth L Sweet,Sara Ortiz Escalante.Bringing bodies into planning:Visceral methods,fear and gender violence[J].Urban Studies,2015,(10).
[13]成伯清.情感的社会学意义[J].山东社会科学,2013,(3).
[14]李林艳.关系、权力与市场——中国房地产业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5]王俊文,段佩君.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留守妇女”问题研究——以江西省井冈山市A镇为例[J].农业考古,2010,(6).
[16]朱潼歆.对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分析与思考[J].河北学刊,2011,(5).
[17]刘怀玉.空间化视野中的全球化、城市化与国家—区域化发展[J].江海学刊,2013,(5).
[18]郭力.网和线:“时间性”与“空间化”——论羽蛇及女性历史叙事[J].北方论丛,2004,(3).
[19]梁国伟,秦霓.网络动态文字与情感的空间化展开[J].文艺评论,2009,(5).
[20]佟新.身体与情感的阶层化[J].文化纵横,2012,(6).
[21]欧阳灿灿.论福柯理论视野中身体、知识与权力之关系[J].学术论坛,2012,(1).
[22]胡艳华.悄无声息的“革命”?转基因作物与一个华中乡村的社会变迁[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23]胡艳华.西方身体人类学:研究进路与范式转换[J].国外社会科学,2013,(6).
[24]黄颖.丈夫返乡对留守妻子家庭的意义[J].妇女研究论丛,2013,(1).
[25]成伯清.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从社群主义的观点看[J].南京社会科学,2011,(1).
[26]吴惠芳,叶敬忠.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
[27][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8][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M].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9]毕光明.《花被窝》:乡村女性的情欲戏剧[J].小说评论,2012,(3).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8-0060-08
作者简介:胡艳华(1979—),女,社会学博士,长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土地流转后农村家庭的社会风险与保障机制研究”(14CSH02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唐 伟 贾晓林
标签:情感论文; 妇女论文; 身体论文; 空间论文; 红玉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土地流转后农村家庭的社会风险与保障机制研究”(14CSH021)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长江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