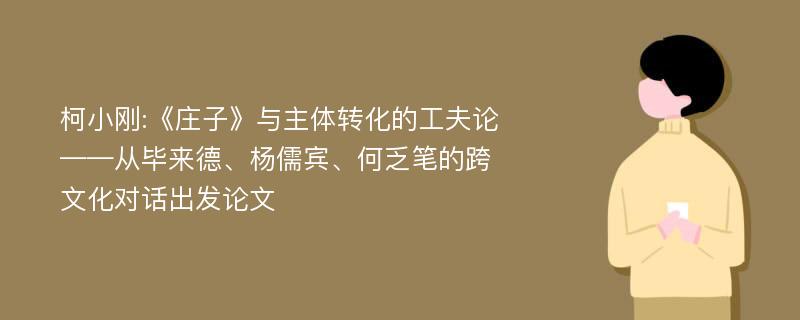
[摘 要]毕来德的《庄子》解读从主体转化的工夫论角度激活了《庄子》的当代批判意义。杨儒宾、何乏笔、赖锡三与毕来德的跨文化《庄子》解释学对话深化了这一进路的《庄子》读解。出于对“气”之为“帝国秩序”的警惕,毕来德的“新主体范式”工夫论中缺少“气化”“物化”的维度,导致“我身主体”不过是对“我思主体”的简单反转。杨儒宾等人提出的“形气主体”“游之主体”“两行主体”则可以弥补毕来德范式的不足。从他们的对话出发,有望对《庄子》形成新的解读,而且这种解读过程本身亦可成为主体转化的工夫习练。
[关 键 词]《庄子》;主体转化;工夫论;毕来德;杨儒宾
在现代理性主体、意识主体、权利主体、劳动与消费主体、体验与娱乐主体的全面危机中,《庄子》的当代批判意义开始凸显出来。在跨文化讨论中,这种意义尤其容易得到展开。近年来,主要由德国汉学家何乏笔(Fabian Heubel)促成的法语庄子学与中文庄学的对话,以及与尼采、福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现象学等思想脉络的对话,围绕“主体的转化”展开了一系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追问,庄子被重新唤醒,与我们同在、交谈,一起面对这个时代的人类生活中最深刻的存在困境。这些困境来自天人之间最原初的吊诡,又在每个时代表现出新的形式。
一、“我身主体”须经“游之主体”的“炮制”
瑞士汉学家毕来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素负盛名,是当代西方庄学学者的重要代表。他从《庄子》中读出的“新主体范式”很可能是疗救现代性疾病的解药。只不过,这味药还需要放到“物”的蒸笼里经过“气化”熏蒸的炮制,才能发挥效能。①“所有已知或未知的官能和潜力之总和”意义上的“身体主体”诚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身心分裂”,不过,却未必能泯除“主客二分”“乘物以游心”,达到杨儒宾所谓“游之主体”。②由于毕来德的“身体”局限于“自身”之内的经验,所以,在他的解读中,庄子的“游”只不过是一种旁观身体活动的“超脱的、静观的意识”[1]104。
林地所有权、使用权与管理权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问题,管理机制仍需不断优化,使林业工作的造、管、用、护更为有机统一。
所以,这毋宁是一种身体版的柏拉图-笛卡尔主义,只不过柏拉图主义静观的是理念(柏拉图本人的思想另当别论),而毕来德静观的是身体的活动;笛卡尔的主体建立于“我思”的省察之上,毕来德的主体则来自“我身”的静观。西方主流思想传统力求心灵不为身体所蔽,才能确保主体的自由;毕来德务求身体不受意识干扰,才能“保障自身的自主性”[1]133。
同样以孤石B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力学分析,孤石受到重力G作用,假设前后两个面近似垂直下接触面,受到的力分别为N2与N1,两个侧面受到的压力大小同为N3,孤石与土的摩擦系数为μ,μ可通过试验获得,外部作用力Fi等。假定孤石B与周围土体的下接触面倾角为θ,边坡倾角为η,孤石倾倒时绕支点E进行,li为E点到周围土体对孤石作用力Ni的力臂,则孤石B的力学平衡方程为:
毕来德所谓“新主体范式”炮制的关键,很可能就在杨儒宾的“游之主体”中。主体之所以能游,诚然是因为“主体的能动性”。但“主体的能动性”又是怎么回事呢?“主体的能动性”显然不是“一个能动的物体或身体”意义上的能动性。主体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物体,也很难局限于身体。它几乎就是“能动性”本身。但它又不是“纯粹理性形式意义上的能动性”,而是一种实存,一种个体性的、具体的、有身体和生活世界的实存。只不过,这种实存方式又不同于石头的实存,因为它总是逸出自身的个体性、如在其外的具体性、浸透心灵和意向性的身体性、超出生活的世界性。主体性就是主体的逸出性。正如杨儒宾所言:
为了说明“未知的官能和潜力”是身体的重要部分,毕来德做了许多非常精彩的描述。他也敏锐地看到,在庄子那里,“虚空与万物之间来回往复的过程,描写的是我们主体的运作”[1]132。不过,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两点之间是通过工夫论意义上的“气”和“游”关联在一起的。在《人间世》的孔颜对话中,孔子所谓“听之以气”就是对“未知官能和潜力”的回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则是为“虚空与万物之间的来回往复”准备的主体工夫。
“兼体而无累”的“气化-物化-两行主体”很可能既不是物质性身体向上进化出来的高级意识功能,也不是超越性的理念或心体向下体现出来的属人心神。这两种观点貌似对立,其实都是一元论的同一性哲学,只是以不同的东西作为同一性的原则。这种同一性哲学很可能是现代主体性危机的根源。而庄子启发我们:“主体”的深层意蕴可能不是任何名词能命名的同一性状态,而是必须通过“听之以气”的心斋工夫体察到“虚待的原初之间性”,然后能游心于所有可能的“之间”,才能在此过程中逐渐打开的境界。
所以,“听之以气”就是听之以“真宰”。庄子的“真”可比诸《中庸》的“诚”。听之以真宰就是“诚者自成”“至诚能化”,因而就是不听之听(“无听之以耳”)、不宰之宰(“无听之以心”)。经由此番“心斋”的修养和转化,主体才能从片面的“有”(“听之以耳”)和片面的“在”(“听之以心”),返回到“有而不在、在而不有”的本来状态,至其真宰而为“真人”“至人”。
《齐物论》结尾的庄周梦蝶寓言也同样指示着“通”与“独”的相反相成、吊诡两行。恰恰就在“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之后,庄子却立即说“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物化”既包含物之相通,也包含各物之独。独然后能通,通然后能独,此之谓化。主体的转化工夫之所以必要,在于主体的不通;主体的转化工夫之所以可能,却正在于主体能独。个体性既是主体转化工夫所要克服的出发点,也是主体转化工夫所要达成的目标。在这个“一而二、二而一”的出发点和目标之间,物之相通和齐一构成了主体转化工夫的主要过程。
毕来德激烈批评“帝国秩序”建立之后的历代《庄子》注疏,希望通过直面文本和自身经验来契合庄子本来的想法。他对于秦以后形成的中国思想概念保有足够清醒的警惕,然而却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帝国秩序”对于“气”的改写,未能通过批判地阅读回到“气”的原初脉络,或者说未能对庄子的“气”“听之以气”。这是个关键的局限性,必将带来“虚空与万物之间来回往复”的滞碍,导致“物”不“物化”而降低为有待解脱的对于主体自由的限制,[1]96,97“游”不“天运”而降为我身之静观。这种“恐物心态”和“自恋情结”的附着点虽然从“我思”转到了“我身”,其为不化之意必固我的“机制”则如出一辙。
具体分项目标为:在教学内容上,将计算思维的培养融入医学院校计算机课程改革,不仅为计算机基础教育提供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更高的目标,也为医学院校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体系提供经验和参考。在教学手段上,开展慕课与翻转课堂混合教学的实践,充分地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深入学习知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开展形成性评价,更科学、客观地衡量学生学习的状态和进度,做好每一步骤的及时反馈,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知识和得到真实的评价,同时,也有利于对课程开设质量进行基于数据的准确分析和科学评价。
杨儒宾以“游之主体”回应毕来德的“我身主体”并不是对后者的反对,而是批判性地补充发展。或者用方以智式的语言说,是对后者的“炮制”。在杨儒宾看来,主体能游的关键在于“形气主体”的“形-气-神三元构造”。通过气的连接作用,不但主体内部的身心之间,而且主体内外的物我之间,都可以形成“互纽”[3]190。这不一定是毕来德所指责的为帝国秩序服务的宇宙论话语,而完全可以是他所提倡的主体自由转化的工夫论话语。
由于害怕曾被帝国语言改造过的“气”再次带来主体的奴役,毕来德宁可把“虚而待物”的“气”解释为无物的“虚空”,从而断绝“虚空与万物之间来回往复”的通道,使得主体转化的工夫实际上无法进行;而基于“形气主体”工夫论的杨儒宾则看到“虚之本体不是明镜意识,而是虚空即气”,是“盈满了气之动能”的虚待主体。[3]192毕来德说“气是虚空”,杨儒宾说“虚空即气”,一近老,一近孔,庄子本人则很可能是两行于其间。
3、肥料混用要得当 叶面追肥时,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叶面肥合理混用,其增产效果会更加显著,并能节省喷洒时间和用工。但肥料混合后必须无不良反应或不降低肥效,否则达不到混用的目的。另外,肥料混合时还要注意溶液的浓度和酸碱度,一般情况下,溶液的pH值在6~7时有利于叶部吸收。
以电影为教学舞台,笔者根据电影内容设计了三个情景,分别是主人公得到神奇遥控器之前的生活(Michael’s pains),得到遥控器之后的生活(Michael’s regrets),放弃人生遥控器之后的生活(Michael’sgains)。具体的教学步骤如下:
综上,针对GarlandⅢ型肱骨髁上骨折患儿的临床治疗方法上,小切口辅助复位经皮克氏针固定的治疗方法用时短,且恢复快,同时可尽少避免并发症的几率,值得临床推广。
观点针锋相对,思想“机制”却如出一辙。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主张心灵或身体,而是“机制”③的转换。不求身心之化、物我同游,而急于以身攻心、以我拒物,既无助于“我思主体”的批判,也妨碍我们跟随庄子一起实践主体的气化-物化工夫。
主体可以说是有而不在,也可说是在而不有。说是有而不在,乃因主体不能没有,但它确实不是可以质测的特殊官能,也不隶属于空间的范畴;说是在而不有,乃因主体是与整体身心的场域共构的,它是场所性质的,但不能为意识所把捉。[3]188
“听之以气”便是这样一种回到“有而不在、在而不有”状态的主体自反工夫。这种主体修养工夫为什么被称为“听之以气”?因为气也是一种“有而不在、在而不有”的东西。气并非一无所有,但它确实是虚的;气无所不在,却并非一块石头那样地实有。 “有而不在、在而不有”既是主体的特性,也是气的特性。这是一种巧合吗?如果只是巧合,为什么《人间世》里的孔子教导颜回修习“心斋”的时候,却以“气”为准?显然,在“心斋”的主体转化工夫里,“气”不是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精微物质”,也不是唯心主义所谓“心灵的发用”,而是“虚以待物者也”。“虚以待物”的“气”正是主体之为主体的深层工夫论词语。
日生东而有西酉之鸡,月生西而有东卯之兔,此阴阳交感之义,故曰卯酉为日月之私门。今兔舐雄毛则成孕,鸡合踏而无形,皆感而不交者也,故卯酉属兔鸡。[注](明)郎瑛:《七修类稿》,中华书局,1959年,第74页。
这意味着,“气”既非片面属身(“无听之以耳”),亦非片面从心(“无听之以心”),而是身心之间的“虚而待物”。“虚”也既不是一种片面属于身心的“主观状态”,也不是片面来自外部世界的“客观空间”,而是人与物之间的“待”。“心斋”的要点可能并不在“心”,而在“虚以待物”的“斋”。所以,在《人间世》的对话里,孔子接下来解释“虚”时又说到“唯道集虚”“虚室生白”。“集”和“生”一收一放,一张一弛,正是“能动性”的深层活动。由此活动而有“主体”之名,非谓意必固我之心或四肢百骸之身也。
“逍遥”这个词在《逍遥游》中的唯一一次出现,可能也在指示日常生活转化的工夫论涵义。在《逍遥游》终篇的那棵无用的大树之下,“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已经不再有鲲鹏寓言的宏大叙事,而只是落脚到一种日常起居的生活方式。只不过,这种日常生活不再局囿于有用性和目的性之中,而是同时超越了大鹏的宏图和斥鴳的小安。一旦注意到这些细节对于主体转化工夫的启发意义,就可以意识到小大之辩的要害可能并不在于小大,而在于转化。 巨大的鲲又有至微的鱼卵之义,也在暗示这一点。
二、“兼体而无累”的“气化-物化-两行主体”
正如何乏笔所指出的那样,“听之以气”需要张载所谓“兼体而无累”的工夫,或赖锡三所谓“气化”和“物化”的两行之“游”。[2][4]“虚待”是体察身心之间、物我之间的“原初之间性”的工夫,“虚以待物”是“兼体而无累”的前提准备,是“气化”和“物化”的两行临界点。“原初”的意思是说,“之间”不只是先有事物、然后有“事物之间”那个意义上的“之间”,而是必须有一种敞开性在先“虚待”,然后才有事物和“事物之间”。“兼体而无累”的工夫是通过“听之以气”的主体转化,浮游于“原初的之间性”,一面“气化”而“磅礴万物以为一”,一面“物化”为事物之间的千差万别。
然而,在这段关键文本的阐释中,毕来德很遗憾地把“听之以气”解释为“自身活动的自我知觉”,未能深入到“气”这个更深层的“未知官能和潜力”之中。如果能深入到这一层,就不会局限于“自身”,而能“同于大通”,达物之情。不能及物,不达物情,所以,正如何乏笔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毕来德对“虚而待物”的翻译中,“物”不见了,[2]“待”也不见了。“气”只被翻译和解释为“完全开放的虚空”,“自身”也“呈现为虚空”[1]84,85。这样的主体比较接近《天下》篇所描述的老子(虽然毕来德对老子持批评态度),“以本为精,以物为粗”,区别只在于把“澹然独与神明居”替换成了“自觉独与身体经验居”。
在这个意义上,庖丁解牛的“以无厚入有间”可能是最基本的“游之主体”寓言。“养生主”所要保养的正是这“无厚”的刀刃,但保养的过程恰恰是在牛骨之间消耗它的过程。孤立的刀刃并不就是主体,只有解牛的“游刃”才是主体。庖丁关于解牛的论述始于“释刀而对曰”,终于“善刀而藏之”,其间从来没有刀的孤立闪现。④所以,对于庄子式的“气化-物化-两行主体”来说,“兼体而无累”的“游于之间”可能是非常关键的活动机制。这也许会指向一种“工夫论的美学进路的政治哲学”。正如何乏笔在与孟柯的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收集本院有完整资料的39例锁骨远端骨折患者,其中钩钢板固定(钩板组)18例,解剖锁定板联合喙锁缝线固定(复合组)21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详见表1,其在性别、年龄、侧别及受伤至手术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美学的领域能成为主体性练习“一”(虚)与“二”(物、多)之间来回往复的场所。难道这不是(未来的)民主政治所不能或缺的启蒙教育?或问,经过对启蒙之辩证的深痛反省之后,庄子和张载各自所描绘的“兼体”修养,是否有助于深入构思新主体性范式下的自律主体,以及当代民主政治所不能或缺的启蒙教育?[2]
杨儒宾的“庄子儒门说”为这种“政治启蒙教育”的设想提供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从庄子本人的时代开始,经由郭象、韩愈、苏轼、觉浪道盛、方以智、王夫之,一直到今天的处境,有些问题和解决的努力可能是持续存在的,虽然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关于“帝国秩序”和“自由民主”的刻板区分,关于“儒家”和“道家”的教条区分,以及关于“气学”(唯物主义)和“心学”(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区分,可能既会遮蔽庄子的本来面目,也无助于现代性问题的解决。 而辩证吊诡的工夫习练可能是庄子式“政治启蒙教育”的第一课。⑤
正如《齐物论》所示,教条化的区分不但不能“避免危险和灾难”,反而恰恰是灾难的组成部分。在《齐物论》中,庄子提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又恰恰是在《天下》篇历述百家之学的前面讲到六经。六经并不是“儒家”的专利,也不是“道家”的刻板对立面。庄子本来就诞生于六经的文化生命和问题脉络之中,在历代注疏的眼界中也并没有完全脱离。六经的多元差异性与庄子的“无端崖之辞”同气连枝,庄子的“卮言日出”直接来自六经的“日新”品格。
六经是六,或者是五,后来又有九经、十三经,从来不是一。在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中,每一部经的篇章字句都一直处在不确定的争议之中。更不必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⑥——经学阐释的大传统是“因时损益”“发明经义”,根据每个时代的具体问题来重新激活经典,保持当代活力,而不是固守教条。如果想要重新激活庄子的“政治启蒙教育”意义和当代批判意义,“庄子与六经”是“炮《庄》”工作的必经步骤。只有经过这个步骤,《庄子》的政治哲学解读才能从其源头重新出发,为深处危机中的现代人类提供“主体转化”的可能性。
余论:从主体转化视角读解《庄子》寓言
从主体转化视角出发,《庄子》里的寓言有望开显出一番新的意义。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工作,本文无法全面展开。下面仅选取《庄子》内七篇中的几个重要寓言,从“主体转化工夫”的角度略作展开,以便落实上面的相关理论分析。庄子寓言往往需要多重反转的阅读,才能略微领会作者“正言若反”的吊诡两行。这种文本解读的过程本身即可以成为一种主体转化工夫的习练。
鲲鹏寓言是《逍遥游》开篇的第一个寓言,也是《庄子》全书的第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在《逍遥游》中有过三重讲述,其中第一重讲述影响最大。实际上,只有在第一重讲述中,才出现了鲲变成鸟的惊人叙述。这是关于转化的直接隐喻。但是,过于直接的隐喻反而会遮蔽寓言所要寓指的意思。真正的转化并不是从一个东西变成另一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自身的转化。在鲲鹏寓言的第二重讲述中(“齐谐版”),鲲就完全没有出现,仅仅叙述了鹏之图南;而在第三重讲述中(“汤之问棘版”),鲲鹏虽然又都出现了,但鲲自鲲、鹏自鹏,并没有写到鲲鹏相变。对于庄子这样的寓言大师来说,这些细节可能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两个细节是“天池”的位置和南冥的永未到达。在第一重讲述中,天池被设定在南冥;而在第三重讲述中,却说北冥即天池。这意味着,天池既是大鹏飞赴的目标,也是飞离的出发点。这是令人惊异的细节,也是意味深长的细节。主体转化的工夫可能并不意味着一种外在地离开和到达,而是内在地转变。人还是这个人,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然而主体却发生了微妙的内在转化。这种转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种持续的工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所以,在鲲鹏寓言的三重讲述中,从来没有述及飞抵南冥之后的情形。这几乎是三重讲述中唯一相同的细节。⑦
因此,“虚而待物”虽然不是意识心和理性自我的主动性(有为),但也绝非盲目顺应宇宙气化和“帝国秩序”的被动性(无为),而是能待物而创生的主体性(无为而无不为)。主体性是能待物而应物的被动-主动性,也是能应物而生物的主动-被动性。 单从主动(“听之以心”)或被动(“听之以耳”)一面出发,都不足以理解主体的实情(“听之以气”)。
鹪鹩、鼹鼠同样是《逍遥游》里出现的小动物。而且,与斥鴳一样,其表述自身生活方式的语法同样由“不过”带起:“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不过,它们的“不过”不过指涉自身的自足,而斥鴳的“不过”却指向一种自大和傲人:“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这意味着,起点的大小对于主体转化工夫而言,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前提。无论大小,要害都在认识自我和感通他人,以及对于自我的持续改变和对于他人的持续感通。自适而不自限,感通于他者而无待他者,道通为一而能独,身为主体而能化,此工夫之谓也。
通与独的关系之于主体转化工夫的意义,在《齐物论》中有更加明确地提示。《齐物论》开篇于南郭子綦的隐机独化,终篇于庄周梦蝶的物化感通。南郭子綦隐机而坐的工夫显现出不同的气象,颜成子游问他为什么不同。令人惊讶的是,南郭子綦的回答并没有描述自己作为工夫习练主体的主观感受和变化,而是竟然开始谈论吹万不同的山林风声。主体的独化恰恰只有在天地万物的感通之中才有可能发生,物论之不齐恰恰只有在吹万不同中才有可能齐同。《齐物论》要齐的并不是差异性,而是差异性之间的“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越能感受差异性,保持在差异性之中,主体才越能认识自己、关心自己、转化自己。这个能感通的真实自我不再是“意必固我”的我,⑧而毋宁是“今者吾丧我”的我。反过来亦然,南郭子綦越能“丧耦”“丧我”,就越能见到真实的自己(“见独”);越能聆听通达无碍的天籁,就越能分辨不同窍穴发出的不同声音。
这是一种精致但贫乏的主体,无法与物同游、与物俱化,只能静观自己的身体知觉和身体活动,成为一个那额索斯式的(narcissistic)身体自恋者,惊异于自己的身体好像是没有边界的,其活动也不是自己能理解的,像毒品吸食者一样。这是一种“唯身体经验主义”,虽然它已超出“感官的经验主义”,达到了“未知官能和身体潜力的经验主义”。出于这种经验主义的局限性,毕来德竟然一再混同庄子的主体经验与毒品吸食者的经验,仅仅根据“经验描述”上的貌似,就把一种主体修养的高级活动机制降低到药物致幻的水平。[1]74-79这将导向一条与庄子貌合神离的歧路。后来的一部分道教徒走上了这条药物依赖的歧路,现代西方有些盲目憧憬“东方神秘文化”的毒品吸食者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主体转化的工夫在《养生主》的“庖丁解牛”和《人间世》的“心斋”中达到了更加直接的寓言表述。面对“大軱”“肯綮”之间的逼仄空间和人间世的两难处境,主体不得不修习自我转化的工夫。工夫的关键并不在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在毕来德所谓“新主体范式”的形成。在庖丁解牛寓言里,牛之为牛、刀之为刀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庖丁之为庖丁的“主体范式”。“庖丁式主体”不再是使用刀这个工具来砍斫牛这个客体的暴力主体,而是杨儒宾所谓“游之主体”。庄子称这样的游叫“浮游”。“浮游”的关键在“气”。所以,“听之以气”的“心斋”工夫成为主体转化的根本。毕来德与杨儒宾、何乏笔、赖锡三等人的争论为什么聚焦于此?良有以也。在他们的跨文化讨论中,《庄子》的工夫论阐释展开了新的面向,值得进一步探索。
1926年,金际珍出生于合肥。10岁左右,她就开始学习刺绣,到今年已经有80多年。她的作品大多与生活、民俗息息相关。乡里的邻居们每逢娶媳嫁女,都会到她这儿讨要两三幅作品。附近谁家孩子出世,也都想请她为孩子绣个肚兜,图个幸福美满、长寿健康的好兆头。“过去普通人家逢上嫁娶、年节等大事时才能绣上一幅,富裕人家平时家中常备着小幅绣品,作为客人来访时的回礼。”金际珍说。
注释:
①物性相炮可为药饵,应是庄子“以息相吹”中的应有之义。《庄子》《论语》、柏拉图皆多对话,亦此义也。方以智名其书曰《药地炮庄》,盖深有得于此者。
②具体详见杨儒宾:《儒门内的庄子》第三章“游之主体”,台北:台北联经出版社,2016年。
要想保证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就应该对电力系统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更新。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有效的措施,相关人员还应该做好记录,在变电站发生安全事故时能够有效抢救并恢复。在我国北方,冬季非常寒冷,电网设备容易在强降雪冲击下,电杆倒塌,造成整个地区电网崩塌。在变电站发生这样的情况下,应该结合相关规范进行及时的处理,把危险降到最低。重点是出现电网断裂的状态下,应该安置警示牌,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封锁,避免出现触电的危险。
③“机制”一词出自毕来德《庄子四讲》(宋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是毕来德解《庄》的关键词。
④关于此点的更详细分析可参拙文“藏刀与藏天下:庄子大宗师与养生主的政治哲学关联”,见收拙著《道学导论(外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庄子式政治启蒙教育”意指“吊诡”与“两行”能力的学习,语出前文所引何乏笔文章。参见拙文“现代性吊诡与当代中国的跨文化古典复兴”,发表于2016年的法兰克福“吊诡现代性”工作坊,见收拙著《生命的默化:当代社会的古典教育》,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⑥王夫之给自己的画像题的对联。参见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见《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院,2011年出版,第73 页。
四大名着是我国文学经典的经典,分别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及《红楼梦》。四部著作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人物及其性格的刻画和所包含的思想内容都是长久以来人们喜爱的,在九寨“嘎花”中就经常被引用。
⑦更多相关的分析,详见柯小刚“中国作为工夫论的政治哲学概念:庄子逍遥游读解”,刊于《江海学刊》,2018年第4 期。
⑧出自《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参考文献:
[1][瑞士]毕来德.庄子四讲[M].宋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德]何乏笔.气化主体与民主政治:关于《庄子》跨文化潜力的思想实验(22)[J].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2(4).
[3]杨儒宾.儒门内的庄子[M].台北:台北联经出版社,2016.
[4]赖锡三.身体、气化、政治批判——毕来德《庄子四讲》与《庄子九札》的身体观与主体论(22 卷)[J].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2(3).
Zhuangzi and “Gongfu” Theory of Subject-Transformation——From the Trans-Cultural Dialogue between Billeter,Yang Rubin and Fabian Heubel
KE Xiaogang
(School of Humanities,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Jean François Billeter’s interpretation ofZhuangzi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ngfu” theory of subjecttransformation has activate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ancient text.Yang Rubin,Fabian Heubel and Lai Xisan’s trans-cultural dialogues with Billeter have promoted the hermeneutics ofZhuangzi on this approach.Because of the precaution against the “imperial order” of “Qi”,Billeter’s “new paradigm of subjectivity” is lack of the dimension of energetic transformation “Qi hua” and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Wu hua”.Therefore,Billeter’s embodied subject is merely a reverse of the Cartesian cogito subject.By contrast,the “subject of wandering” or “the subject of shape-energy” raised by Yang and Heubel cover the shortage of the Billeterian subjectivity.Starting from their dialogues,a new approach ofZhuangzi interpretation could be developed,and the interpretation will serve as an excise of “Gongfu” of subject-transformation.
Keywords:Zhuangzi; Subject-transformation; “Gongfu” Theory; Jean François Billeter; Yang Rubin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 编 号]1003-5478(2019)02-0045-06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19.02.007
[收稿日期]2018-10-18
[作者简介]柯小刚(1973-),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禚丽华
标签:主体论文; 庄子论文; 工夫论文; 之以论文; 身体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道家论文; 《长白学刊》2019年第2期论文;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