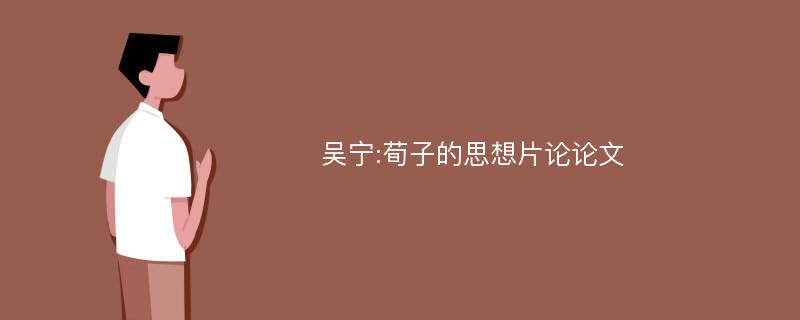
摘 要:在天论方面,孟子所言之“天”为义理之天,具有较浓的形上色彩;而荀子所言之“天”是自然之天,更接近自然主义。在人性论方面,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的行善天性被后天因素压制而不得发挥以至于在现实中有恶的表现;而荀子则主张人心善性恶,认为人的天然欲望不加节制的扩张常常导致作恶。在道德的起源和性质上,孟子认为道德必须是纯粹的,具有明显的反功利倾向;而荀子则认为利欲是促使礼义产生的基础,肯定功利在促进人的道德发展中的作用。孟子和荀子分别使孔子之后的儒家仁、礼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以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对后世宋明理学中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荀子;天论;人性论;道德起源;发展路向
在天论方面,孟子所言之“天”为义理之天,具有较浓的形上色彩;而荀子所言之“天”是自然之天,更接近自然主义。在人性论方面,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的行善天性被后天因素压制而不得发挥以至于在现实中有恶的表现;而荀子则主张人心善性恶,认为人的天然欲望不加节制的扩张常常导致作恶。在道德的起源和性质上,孟子认为道德必须是纯粹的,具有明显的反功利倾向;而荀子则认为利欲是促使礼义产生的基础,肯定功利在促进人的道德发展中的作用。孟子和荀子分别使孔子之后的儒家仁、礼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以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对后世宋明理学中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孟子与荀子哲学思想之异同
对于孟子与荀子之间的关系,如果仅仅将孟、荀作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来概括,则过于简单化了。冯友兰认为孟子代表了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翼,而荀子则代表了儒家的现实主义的一翼,同时指出孟子有左也有右,左就左在强调个人自由,右就右在重视超道德的价值,因而接近宗教;荀子有右也有左,右就右在强调社会控制,左就左在发挥自然主义,因而直接反对任何宗教观念。笔者认为这个概括是很有见地的,本文拟就这几个方面进行比较,以阐发孟子与荀子哲学思想之间的异同及其对后世儒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天论:准形而上学与自然主义
“天”在先秦时代人们的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功能的角度看,“天”在古代扮演了五种角色,分别是主宰之天、造生之天、载行之天、启示之天、审判之天。这样的“天”一直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并且为人间设立了秩序。但是,随着天子失德,“礼崩乐坏”,对“天”的信仰出现了两大危机:造生与载行之“天”由于不再表现仁爱之德而变为自然之天,启示与审判之“天”由于不再保障正义之德而变为命运之天。这两种观念分别以“天”为具象的自然或以“天”为盲目的命运。这样一来,人们既不能从自然中获取超越的理想,又不能从人间复杂的境遇中发现正义的原则,因而陷入精神危机。孔子的“志业”在于把人的命运转化提升为使命,再将它上溯于“天”,重新为“天命”下定义,让人人自觉其内在向善的力量,经由择善而走向至善,以符合“天命”的要求。孔子一方面去除了“天”的神学宗教色彩,另一方面将人的道德实践与“天”联系起来,唤起人们内在的自觉性。孟子在这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不过孟子哲学中的“天”较具动态性和威权性,相对地增加了形而上学色彩,“天”成为人类道德法则及其实现的权威性根源的代称或假定。孟子假定存在着这样一种超越的权威,即道德规则存立所要求的一种因果存在性,亦即其性善和道德学说的形而上学的根据。在孟子看来,宇宙实质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形而上学原则,人性就是这些原则的例证,“天”就是这样一个道德的宇宙。一个人通过充分发展他的禀性,就不仅知“天”,而且同“天”。这种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天”,实际上起着一种象征性作用,它作为义理之基础的权威代表者,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殷商西周时期,天、天命是被作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亲亲之情论仁德,而视天命为一种盲目的主宰力。孔子之后,其弟子和后学力图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贯通,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获得存在论的支撑,另一方面又将天、天命、天道义理化。荀子有取于道家在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观的成分,是“名于天人相分”的自然主义天道观,然而它的理论宗旨却不在于走向自然主义,而在于凸现“天人相分”,然后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人道”学说。
荀子在对孔孟和诸子的继承与批评中别开辟了先秦儒学的新生面。相比于孟子重视对孔子之学的继承,荀子更注重发展孔子之学,其思想更具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对孟子准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倾向的批评也甚为严厉。荀子所言之“天”为自然之天,这大概受到老庄自然主义学说的影响。正如:“皆知其所以成,莫知无形,夫是之谓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即指大自然,它是客观规律并且不以人的主观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为恶远也辍广”在荀子眼里,自然万物,不论是人或是物,皆是天的产物,都具有天性。所以,面对自然,人们要尊重客观自然的规律,而不是人为主观的去改变它。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认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道不会因为人的情感或者意志而有所改变,对人的善恶分辨完全漠然置之。荀子对传统的宗教迷信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吉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种宗教仪式仅仅“志意思慕之情”,是尽人道而非鬼事。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与规律化,“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①《荀子·天论》。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好恶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他把阴阳风雨等潜移默化的机能叫做神,把由此机能所组成的自然界叫做天。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②《荀子·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③《荀子·天论》。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荀子明确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孟子所言之“天”为义理之天,以人性为“天”之构成的一部分,此为孟子性善论的形而上学根据;而荀子所言之“天”是自然之天,其中并无道德的原理。荀子以为,自然界之现象乃自然按照其规律运行使然,其所以然之原故,圣人不求知也。荀子把人看做在宇宙中与天地同等重要的存在,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利用自然提供的一切来创造自己的文化,履行作为人的职责。所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将自然的人与自然的天地齐观,大大提高了人的价值,其“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更加接近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能力,为其人性学说提供了依据。
(二)人性论:性善与性恶
在工业4.0时代,在数字化革命中,人造板加工机械制造商正经历着一个理念的变化:要提供的不能仅仅是机械了,不能只把自己当作制造者,而要协助用户改进他们的企业。Biesse公司声称,已从机械销售者进展到生产率销售者。
人性论在孟、荀的哲学思想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对孟、荀人性论的比较研究不仅仅是区别孟、荀哲学的关键,更是进一步研究孟、荀哲学思想的必经之路。孟子提出人性善,实际上是为了给孔子的道德实践理论寻找依据。他试图回答行“仁”、义利之辨、忠恕之道后面那个为什么“行”的问题。在孟子看来,人性善是天然永在的,其作用却受到外在负面因素的干扰,道德实践者的任务在于主动地排除这些干扰,以使善端得到充分扩充,使人成为“圣人”。孔子的道德理论完全是以道德实践为基础的,其认知基于实证性经验。孟子在这方面与孔子相似,其性善论以经验理性主义为基础,以实证性经验为认知之基,但孟子企图在此之外提供理论性证明。也就是说,孟子以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经验作为人性善的证明,但是他又在经验理性之外提出先验的“天”作为道德规则存立所要求的一种因果存在性的假定,亦即其性善论的形而上学的根据。只有“尽心”“知性”方能“知天”,“知天”方能“立命”,而“天”与人又具有某种同质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所谓人性皆善。孟子所谓性善,在于人皆有仁、义、礼、智之“四端”。“四端”扩充,则能为“圣人”。人之不善不在于其本性与善人不同,而在于不能扩充其“四端”。孟子所说的“端”表示了一种行善的可能性,即天然的倾向可为品德之端,人性可由此不断生发,道德能力遂可在心中育成。因此,孟子的性善论并不是说人性本善,而应该是人性向善,是应然而非实然;如果不能将善端扩充,不仅不能成为善人,甚至可能受到外界的干扰而成为恶人。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要扩充善端,是因为善端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和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孟子性善论的缺点在于忽略了社会性与个人性向的互动关系,以为行为表现纯然来自个人天性,这一点是孟子不及孔子的地方。认为善端能够不受外界影响而自然扩充,就等于把社会当做了理想主义的实验场。事实上,人性是在不断成长的,这与其先天的素质和个性倾向有关,但绝不能期待善端自然地扩充而成为一个“圣人”。对大多数人来说,此天性表现是人性潜能和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善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源于生活,只有在社会生活和交往关系中实现的善才是真正的善。
针对孟子性善论中的不足,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荀子人性论的关键并不在于证明人性恶的事实,而在于他的人性论学说更注重人自身的认识状况、努力状况以及人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使他更自觉地将礼乐作为一种教化手段而制度化。荀子论人性,首先区分所谓性、伪。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之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性是生之所以然者,因而属于“天”。荀子所说之“天”是自然之天,天自有其“常”,其中并无理想和道德的原理,因而人性中也不会有道德的原理。道德乃是人为的,即所谓伪也。荀子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孟子所谓性善,是指人性中本有善端,扩充之即可为“圣人”。荀子谓人之性恶,是指人性中非但本无善端,而且有恶端。人生而有欲,有了欲望就要得到满足,荀子并不把欲望本身当作恶,而是说“顺是”,即对欲望不加节制而任其扩张,最终必然滑向恶的一端。荀子所谓的恶不是指人性中已经包含了恶的因素,因为荀子看到了所谓的善恶并不是一个人的善或一个人的恶,之所以有善有恶,根本在于人如何通过自身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使自己得到实现——“善”就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而“恶”就是个人利益的实现妨碍或损害了他人利益的实现,使人与人的关系处在一种失当的状态。总之,无论善恶都是不能脱离具体社会生活的。人虽然没有善端,但荀子对于人的聪明才力很有信心。人有此才力,若告之以“父子之义”“君臣之正”,则亦可学而“能之”。积学久而成为习惯,“圣人”可积而致也。荀子在教化方面特别重视礼乐的作用,认为这是“化性起伪”、成就善人的关键。
孟、荀的人性论其实是人本经验主义认知的不同侧面的表达。孟子的真正主张是人有行善天性,但此天性被后天因素压制而不得发挥以至于在现实中有恶的表现;荀子则说人的天然欲望不加节制的扩张常常容易导致作恶。两人的直接判断一致:现实的人有作恶的倾向,但通过主观的内外努力可最大限度地增加为善的可能。孟子性善论的实质在于极大地关心行善的可能性,而荀子则更加注重如何积善成善。
2018年将是国际大石油公司的投资拐点年,连续3年的投资下降趋势将正式结束。根据近期各公司公布的年度预算,5家公司2018年合计投资约为1000亿美元,同比小幅增长。涨幅受限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公司仍要确保优先分红,同时投资者对公司的决策制约较大。
(三)治理观:内圣与外王
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其含义两点:第一,礼法并举、王霸统一。他认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①《荀子·成相》。礼以定伦、法能定分,二者相互为用。只是法的特点表现为通过赏罚来维护等级秩序。第二,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称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②《荀子·致士》。荀子以为,礼义是立法的精神,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总之,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是对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未爆杂用的先河。
以往的儒家学者大都把这种外王学的正当性诉诸于天道、天命,很少有人能够从现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源出处证明自己的外王学。荀子的经验知识的立场使他得以面对现实,回到现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源出处。荀子注意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且得以优异于动物的地方,是人能群,即人能组织社会。而人所以能群者,在于分。分即是建立社会等级,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将社会协同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面对自然、战胜自然。分是组织社会的根本法则。而“分莫大于礼”。通过圣人的治礼作乐,将社会分为上下有序的等级,以解决基于物欲的争斗。分的标准就在于礼义,即封建的伦理道德和礼法制度。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人性论出发,荀子提出了“明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以论证礼乐教化之必要性。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那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荀子理欲观认为人有求利求欲之心是性情之必然,因为,人生而有性,有性就有情,有情亦有欲,人生而有欲。荀子认可欲望,认为欲望是人天生就有的,应该尽量满足人的合理欲望,同时,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人就会去求,去自主的争取。但如果这种“求”没有一定的礼制的限度和明确的界限就必然会出现争抢,从而破坏和谐的局面,导致社会混乱。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紊乱的社会局面,但应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和外界财富的有限性,就必须通过制定礼义来分配物资,以用来满足人的欲求,用礼法调节人的欲望。在荀子看来,“人欲”是要满足的,“人情”是需要节制的。并且,荀子为了调养人的欲望设置了礼法,从而达到防止因欲望无穷性而导致出现恶性竞争的纷乱局面,礼的作用就是调养民众、实现生活资料合理有序的分配,从而避免因欲望的无穷性和物质财富有限性之间产生纷争矛盾。
“是啊,他的确……”我转头望了一下,他很安静,又异常沉着,我并不害怕他会伤害我,但最终我还是附和道,“挺吓人的。”
二、荀子与朱熹理欲观的比较
荀子对心理现象的分析还不能完全摆脱经验性的直观描述,其中带有很大程度的猜测成分。荀子的人性学说,虽已触及到人的本质问题,但由于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仍然是抽象的人性论,荀子脱离了人的社会关系来论述人性,而没有看到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其人性学说的目的仍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的,即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做辩护的。荀子从天人相分的立场出发,否定而人性中先验的道德根据。在他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其实质就是人天然有的抽象的自然生物本能和心理本能。荀子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
(一)“人生而有欲”
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中心思想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荀子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贡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荀子思想虽然与孔子、孟子思想都属于儒家思想范筹,但有其独特见解,自成一说。荀子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求其放心”,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二)“天理”和“人欲”
朱熹认为:“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1]56-59意思是说,“天理”即是“道心”,“人欲”即是“人心”,正如《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精,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是“人之一心”中两种“不容并立”的意识,“天理”指的是“天地之性”是以封建伦理纲常为主的包括仁义礼智,人欲是指“计较利害之心”,是人的物质欲望。只有“天理”才是永恒的,而“人欲”是罪恶的一切的社会动乱的根源。“人之一心,天理有则人欲灭,人欲之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因此“天理”“人欲”不能共存,要存天理灭人欲。“理”被朱熹认为是宇宙的根本。朱熹看来,“天理”是人的“心之本然”,也就是一种未受到气禀物欲所屏蔽的未发状态,所以能够遵循其本然之性,且表现的公正,没丝毫人私欲的本然状态。朱熹认为任何人都应该顺应天理,不该存有不合理的非分之想。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他主张的“天理”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为儒家所倡导的,并通过总结百家的“理”“欲”之争中多方观念,认为信奉天理完全的遵守天理才是道德的,在此基础上并提出了“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朱熹认为只有“天理”才是永恒的,而“人欲”是罪恶的一切的社会动乱的根源,而人欲就是其中向恶的方面。朱熹在提出天理并深入研究“理”“欲”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并认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荀子主张尽可能满足人的欲望,即“进则近尽”。人的感官、思维、或者欲望,都是天生秉性的,都是自然的,非人事所能简单改变的,荀子主张应该尽可能的满足人的基本欲望,这就是“天政”。[2]1-7但人除了本性之外,还有人欲,这是情的一种反应。因此,情欲也是人自然天生的本性,也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因此要尽量按照“天政”来使之满足。但人的欲求有无穷性,并不是局限在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是还有其他方面的物质等欲求。面对无止境的欲望,荀子认为:“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人的天生本性要求人的情欲要不断的满足,同时这也是人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也是荀子提出“进则近尽”的理由。荀子主张尽量满足人的自然欲望,但在有限的情况下,物质财富的有限性,应该节制人对欲望的追求。即人追求欲望应根据礼法的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人们所规定的具体的经济条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尽量满足人的欲望。正如:“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但在条件有限不允许的情况下,人则应节制对欲望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
荀子认为情欲虽为人之正当合理之求,但是“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极力反对纵欲,但也不主张去欲、寡欲,而提出节欲。节欲首推心之功用。“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①《荀子·正名》。人性靠“心”的自觉而达于完善。这里荀子看到了理性力量对过度的感情欲望膨胀的节制作用。师法教化和礼义、法度。“伪者,文理隆盛也”。②《荀子·礼论》。“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之礼义法度是改造人性、节制欲望的重要工具,“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③《荀子·性恶》。如果没有师法教化,人只能“隆性”即放纵情欲。荀子更重视礼义作用:“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④《荀子·礼论》。荀子从礼义产生的角度论证了礼义节欲治乱的合理性及重要性。荀子认可欲望,认为欲望是人天生就有的,条件允许应该尽量满足人的合理欲望,同时,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人就会去求,去自主的争取。正如:“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期乱也,故制礼义以分子,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3]132-137但如果这种“求”没有一定的礼制的限度和明确的界限就必然会出现争抢,从而破坏和谐的局面,导致社会混乱。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紊乱的社会局面,但应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和外界财富的有限性,就必须通过制定礼义来分配物资,以用来满足人的欲求,用礼法调节人的欲望。荀子说道:“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他对性的态度是认可的,人生而有性,人生而有欲。认为性是自然本性固有,欲亦是如此:而情生于性,亦是性的内质,而情的感应和体现是欲。因此,人有求利心和欲望是人之本性情的必然的驱使。荀子的理欲观是在人性论基础上建立的,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这是本性所然,无论是天子还是庶民,人人都有这样“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是人之本性所有的,所以不可灭欲或绝欲,是自然天成,不可去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认为,礼义是限制人的欲望的法宝,能够消弭矛盾,获得和谐,然后人人的欲望都可以得到适当的满足。任何强行控制欲望的都是不可行的,强行去除人的欲望的行为,是完全行不通的,违背了自然欲望的规律。人生下来之后都是有欲望的,这是客观世界对人的影响,以及人的情感对客观世界的感应的结果。
三、荀子的体育思想
荀子是在继承儒学的积极入世思想、充分吸纳齐文化中的社会大教育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体育思想的。我们知道,在东夷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齐、鲁文化,虽然地处近邻,可谓鸡犬之声相闻,但从文化形态上看,在春秋以前是有着明显不同的,比如齐文化对于自然神(天神)的崇拜非常重视,鲁文化对于先祖神(祖宗)则更为重视。荀子在战国时期虽然长期生活在齐文化的环境当中,却始终立足于来源于鲁文化的儒学,《韩非子·显学》中说的“儒分为八”其中就包括荀子之儒。荀子的体育思想主要是在齐文化土壤之中对于儒学体育思想的继承或张扬。人的气质修养与品德和身体修养同样关系密切,《荀子·修身》篇就提出了以礼治身的观点,说:“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并且还形成了一套“治气养心之术”。可见《荀子》所谓的“君子结于一”个人修养目标,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尽可能完善的素质教育,换句话说,也就是希望人能够通过后天的知识消化而升华自己的气质水准,这个气质水准不仅包括文化知识、道德品质的后天修养,身体素质的增强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结于一”又是一个过程,保障这一过程顺利进行的办法就是“动静和节”。荀子在这里提到的“礼”,可以理解为规则、规律的意思,人的气血、容貌、言行、思想,其运动过程都应当符合自身的发展规律。按照“动静和节”的办法去运作自身的修养过程,是完善自身气质修养的有效途径。这是之前的孔孟儒学甚至老庄之学都没有系统论述过的。其二,明确提出了运动健身的基本理念。与“动静和节”的气质修养观相呼应,在《荀子·天论》中从军事活动的条件论出发,明确阐述了运动与健身的密切关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这段话的意思主要在于试图确立一种以人为核心而不是以天为核心的行为观念。其中提出的“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的思想值得特别注意。所谓“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就是说,人只要具备衣食等生活条件并且经常进行肢体运动,身体就会强健,天也不能使之生病。所谓“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的意思恰与之相反,如果生活条件欠缺,又不去运动,自然不会有身体的康宁。当然,荀子的这番话本意是为了提高军士的战斗能力,但事实上却揭露出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真理:运动与健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运动可以健身,不运动可以伤身。荀子提出的“动以养生”的观点在先秦体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静以养生”和“动以养生”是中国古代体育养生思想的两个大的思想派别。其三,深刻阐述了乐舞对人的心智陶冶的重要作用。在《荀子·乐论》中首先指出了乐舞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荀子认为,“乐”是人生之必须,其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声音,一是动作。人不能不“乐”,“乐”不能无声、无形,声、形之表现,是否合于“道”,反映的则不仅是个人的品质,更重要的则是对社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他主张要“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从而达到“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的教化目的。乐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呢?《荀子·乐论》篇中做了这样的例证:“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者。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服从。”荀子认为,乐舞对人们身心健康的重要教育作用,一方面乐舞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志意得广”;另一面乐舞可以使人的形体健全生长:“容貌得庄”;同时,还可以通过乐舞活动增强人们的组织、纪律性:“行列得正,进退得齐。”经受过乐舞教育培养的人,既有宽广的心志,又有强健的体魄,还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其素质水平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荀子还把乐舞的教化陶冶功能升华到了移风易俗的高度:“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休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①《荀子·乐论》。荀子的这些论述,核心的论点在于从身心并完的角度来说明乐舞的教育作用,并且从人的社会个体跃升到了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高度。
四、对荀子思想的评价
荀子“天人之分”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的区别,而其“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则是“改造自然的主张”,其学说是控制和改造自然的学说,虽然荀子提出改造自然的理想这一光辉的观点,但是荀子不重视对于自然的研究,没有找到改造自然的有效途径。
人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学乃至中国文化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千百年来,对“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在中国思想史上,先后出现过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超善恶论、性三品论、性善情恶论、性二元论以及性日生论等观点。下面就荀子关于人性方面的思想论述及其成人之途径方面的见解剖析于下。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是人类自我觉醒、自我认识的开始。先秦时期,不同学派的思想家就已经开始探索人性的内容、善恶、标准及其变迁等问题。众所周知,早在孔子之前,晋国的胥臣就已论述过人性问题,但真正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人性问题的却是孔子。孔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相近的,只是后天的习得才出现差别,即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虽没有揭示人性的深层内容,但却为孟、荀人性论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荀子之前,较为系统阐明人性学说的是孟子。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指人与其他一切存在物不同的条件,此条件是人类独有的,是先天具有的伦理道德意识及价值自觉能力。在孟子看来,封建伦理道德发端于人的本性,其目的是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寻找人性上的依据。可见,孟子解析人性,主要侧重于人性的社会功能方面;而荀子所谓的人性,则恰与孟子相反,它是指人生而具有的本能,是人最基本的欲望和要求,荀子的人性理论,也是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寻找人性依据的。荀子人性论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荀子主要从人的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化的角度上去剖析人性,他得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结论。荀子已经看到人的善性出于人为,其实已经表明了人性根本上的虚伪性和伪善性。孟、荀都谈论人性,但他们所谓的人性,既有相通处,又有相异处,他们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性的本质内容,对人性的认识更深入了一层。荀子在人性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批判了孟子的先天道德观念,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人性的动态转换过程以及人性可以通过外在环境条件和内在主观努力得以再塑的思想。在荀子的人性学说中,“性”“伪”是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性”是什么,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新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性者,本始材朴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以看出荀子对“性”做了两条最基本的规定:性是由阴阳相合而生,是人生而自然的,人性本于天道自然。天无情无欲,自然始朴;人性也是纯真质朴,不加雕饰,表明荀子的人性论与其天道自然观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性虽人生而具有,非人力之所能为,然而通过后天的积习修为,可以发生质的转化,这就是荀子人性论中的“化性起伪”观点。从荀子对人“性”的基本规定看,人性中最初不包含任何的道德观念和意识,也不具有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荀子由天然质朴之性得出了“人之性恶”的结论。荀子从人的生理本能、心理意识及社会教化三个层面对人性恶进行了论证。荀子的论据之间带有直观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他用来证明人性恶的种种论据,最终只能证明人性并非自然恶,而是后天恶,即人性若不以礼义来规范引导,必然导致人之性恶。从生理本能的角度看。荀子所说的“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等,都是天生具有的本性,性无所谓善恶。如果无善恶的人性任其发展不加节制,便会导致一系列恶的结果,如争夺、残贼、淫乱等,“从(纵)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凡古今天下所谓善恶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荀子所谓性恶,不是指人性本身,而是指顺纵人之性所出现的结果,人性只有在出现“犯分乱性”时才是恶的,人性之所以恶是因为它超出了圣人规定的度量界限和礼义道德。荀子是要表明:人性具有趋恶的本能,若顺纵人性不予节制,便会出现恶的结果。从心理意识的角度看,“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材,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是从心理对外界的反映上论证人之性恶。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其则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关于“性”的论述是多层面的。其一,荀子在《礼论》中讲到:“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朴”指未加工过的木材,人性就好象原始的未加工过的木材那样。应该说这里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如荀子《礼论》所言:“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也就是说,如果是“文理隆盛”之“伪”加于“本始材朴”之性,当然就能成就圣人之名、天下之功,则性也就能自美。二是,如果是“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的好利、纵欲之恶所加之于性,那“本始材朴”之性当然是无美为恶。所以说,这里所讲的“性”内含善恶两种倾向,但这两种倾向不是由“性”决定的,而是完全由于外界的环境所致,意即人不天生性善,也不天生性恶,荀子是无善无恶论者。其二,“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①《荀子·正名》。“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②《荀子·性恶》。这里的“性”是指生而具有、不受任何外来干预而是其所是的东西,即那种人本来就有的天赋的生物意义上的能力。正如荀子所谓:“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③《荀子·性恶》。也就是说“人性”是自然天成的,不是后天成就的。其三,荀子从情、欲的角度定位“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④《荀子·正名》。“性”乃自然而成,“情”是其本质规定和外化,而“欲”则是“情”的体现。正因为性、情、欲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荀子往往把三者结合起来论述其人性思想。他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⑤《荀子·性恶》。情、欲不仅是人性的表现并且有天然合理性,既然如此,荀子“性恶”观从何而来呢?荀子明确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论证道:“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而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⑥《荀子·性恶》。这里荀子肯定了人之“好利”“疾恶”“耳目之欲”等是人之性,但他突出强调了“顺是”,也就是“从”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即情欲的扩张,当这种扩张达到使“辞让”“忠信”“礼义文理”亡焉,争夺起、暴乱兴的程度时,“天之就也”之合理人性则演化为“性恶”,所以,荀子呼唤师法教化、礼义法度以去恶扬善。荀子之“伪”原初意义上的人性是不完善的,并且有恶向扩张的潜在性。更为重要的是荀子以其关注社会现实的独特视角看到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现状,所以荀子提出“伪”。“伪”即人为。就是要借助人为的力量完善、修正人性。靠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即“心”的功用。荀子讲:“情虽无极,心择可否而行,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⑦《荀子·正名》。从个体角度来讲,自心的体悟和作为当是最重要的。
“理”与“欲”是我国璀璨历史文化长河中重要的一对范畴。“理”是理智,理性,“欲”则是欲望。两者的对立关系,其实也就是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望、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等层面的关系问题,理欲之争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我国古代先哲关于理欲的争辩见解纷呈,我们可以透过理欲之争,可以看出各家各派的思想家的利益观点。这里就选取典型的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来和荀子的理欲观进行对比分析,在对人欲的看法,对人欲的价值取向,对人欲的态度进行对比,以及相同之处对合理欲望的肯定进行分析,通过理论探讨,取其精华,舍弃糟粕。从而达到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各种利益矛盾的目的。对荀子与朱熹理欲观的比较,以达到对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中理欲观的辩证思考。正确处理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合理解决两者之间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正确处理现时代的新的不同主体间不同利益冲突问题。
儒学的核心在仁学,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仁。在孔子看来,德性必须落实到礼,礼的落实又必须有仁心作为内在的基础,“不知礼无以立”。不仅仁建构礼,而且礼对仁同样具有建构作用。如果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孔子,孔子还是更看重价值论。但没有礼,无以体现仁,仁必须落实到礼,这本身就有功利主义倾向。所以说孔子是现实主义者,在这方面荀子更接近孔子。孟子发展了孔子仁学的一面,而荀子发展了孔子礼学的一面。但荀子并不排斥仁学,只是主张以礼来建构仁。孟子及后来的儒家心学都排斥外在规范,过于强调内圣、人的内在道德自觉。在他们看来,由外在规范对人的强制作用而产生的社会秩序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不是建立在人的内在自觉基础之上的。
新款海洋Ocean系列腕表礼赞一切航海元素,天然珍珠母贝表盘于6点钟位置点缀一颗硕大的钻滴。环绕日期显示窗的精美小钻,以圆形明亮式切工钻石勾勒稀世美钻的水滴型轮廓,致敬纯净无瑕的“温斯顿传奇之钻”。
抓住国家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机遇,千方百计多渠道争取资金。精准农业应用系统投资较大,一套精准节水灌溉系统下来要在10万元以上。一是要探索整合财政支农资金方式。统筹安排使用支农资金,围绕发展主导精准农业进行整合,通过资金整合,既有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也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二是拓宽精准农业投入来源渠道。进一步优化农村投资环境,吸引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向精准农业[2]。加快农村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创新,扶持农业信贷担保组织发展,扩大农村担保品范围。加快发展农业保险,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
“人性论”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是一个无法穷究但却无时不在探究的问题。荀子“人性论”的积极价值在于:首先,荀子对“性”的内容的几个层面的阐释丰富了“人性”这一范畴,使人们多维度地探究人性,促进了人性问题的深化和延展,特别是其认识论意义上的人性阐释更是难能可贵。其次,荀子的“性恶”论是和当时特殊的社会现状紧密相连的。荀子基于“性恶”观生发的节欲说和施法教化、礼义、法度的思想有其合理性、现实性,这些思想即便在当代也是十分珍贵的。他的关于“伪”的思想把人为力量界分为主体自我和社会制约两个方面,既看到了人自身的能动性,又强调了社会对人的控制功能,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人的社会属性及其本质存在,只不过这只是荀子“人性论”的潜在思想。荀子的“性恶”论的价值在于:第一,提出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从人的实然层面来看待人性;第二,强调后天环境对人发展的作用。第三,说明礼乐教化的价值与意义,为现实社会的礼乐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荀子的“性恶”论的局限在于:第一,从性恶出发,固然可说明礼乐教化之“伪”的现实必要性,但由于否认了人的道德先验性,圣人治礼作乐的“化性起伪”的教化行为就失去了坚实的存有论根据。第二,把人的先天的自然本性等同于社会道德之恶,没有真实地看到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会性“恶性”之间具有人的意识的造作性。如此将使社会性的“恶行”具有自然存有论根基,以至于“恶”成为了价值的合理性行为。第三,性恶论使人性的超越幅度丧失殆尽,人完全成为社会宗法等级的奴隶。
荀子的理想人格体系分为士、君子和圣人三个层次,在总体人格特征上他强调重智求全,在品质上倡导遵循礼仪。在荣辱观和役物观上,荀子也发展出了自己的见解。荀子的理论对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荀子的理想人格系统,荀子明确指出修身的目的就是要造就理想人格。[4]而所谓的理想人格也不是仅有一个,而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士、君子、圣人。三个层次人格的特点不同:士是最低层次,其最基本的品格就是坚守礼义、辞让、忠信的道德观念,严格地按照礼法办事;君子是高于士的层次,是“法之原,治之原”①《荀子·君道》。,“道法之总要”,②《荀子·儒效》。他是长期积累礼义的结果。由于礼义道德已深人整个身心,所以即使是极细小的言行,也可以作为别人效法的榜样,其“言必当理,事必当务”;③《荀子·儒效》。圣人是最高的理想格,是天下人的最高标准。他是“道”的总汇,是能用礼义这一总原则去统帅一切的人。在荀子这里,理想人格模式由低到高,层层递进,由学习礼义、遵守礼义开始,由浅人深、由低到高,由士开始,循序渐进成为君子,最终成为圣人。荀子把君子的人格总体特征描述为“全”,“全”做事恰到好处之义。而恰到好处,即“中”的原则,一方面是指做事的全面周到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具体在此处,即指做事时要遵循礼。如果君子做事安礼乐利,谨慎而无斗怒,那么做多少事情都不会有过错,“百举而不陷也”。④《荀子·仲尼》。荀子的思想同时兼具“义荣”与“势荣”,沿着以义为重,义先利后的思路,荀子对荣辱进行了界定和分类。“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⑤《荀子·荣辱》。荀子根据对待义利的态度,对荣辱进行区分。义是首位的,做事如果遵循先义后利的原则就会获得荣耀;反之,就会遭受耻辱。故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5]荀子的这种思想一方面揭示了某些人的伪善面目,另一方面又为那些道德高尚、受人诬陷欺凌的人伸张正义。他反对从表面上看待荣与辱,主张深入问题的实质,把荣与辱同人们的德行联系起来分析,这一思想非常深刻。在荀子看来,在对待荣辱的态度上,君子和小人有很大的不同,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作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⑥《荀子·荣辱》。小人做尽妄诞的事情,却希望别人相信自己;做尽虚诈的事情,却想让别人亲近自己;行为如同禽兽,却想让人赞扬自己。而君子,对人诚实可信,所以也想让别人相信自己;对人忠诚,也想让别人亲近自己。[6]对财富名望的追求是所有人生来就具有的共同欲望。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在欲望的诱惑下,是被其牵引还是自己做出决定。君子在物欲面前能够保持清醒,进行利弊的权衡,从而做出正确的决择。这就是不为物所役而能役物的态度,其中体现了人的主导地位。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⑦《荀子·荣辱》。遵守礼义的君子能够役使外物“役使外物”的含义有二种。一是指不被外物所诱;一是指不因外物的得失而使自己心情受到影响,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始终保持心情的平和愉悦。能否做到役使外物,导致了君子与小人的精神境界与生活质量的根本差异。荀子的“役物”的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善假于物”的思想。在自然观方面,荀子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博学才能“知助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的内容、步骤、途径,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学习是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行为。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因为性恶论是荀子的思想特点,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通过学习来不断修行改正自己的缺点。荀子认为学习能够改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智力,荀子否认孟子所说的人有天生的“良知”“良能”,他强调从外界实际事物中学习并且学习的目的是要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性知识去改造客观世界。荀子重视学习以及学习必须“善假于物”、逐渐积累、持之以恒等见解即使在今天对我们的学习也有着指导意义。
荀子的体育教育思想所提出的通过先天的自然条件和后天的教育改造、外在的气质表象和内在的学问修养有机结合而实现各方面素质修养“结于一”,并且要遵从“动静和节”的修养方法、对于运动健身理念的深刻揭示、对于乐舞的教化功能的深刻剖析,不仅在中国先秦体育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在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的发展链条中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近年,我国甲状腺癌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且多见于女性患者。研究数据发现,甲状腺癌为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第3位,以乳头状癌最为多见,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给患者身心造成巨大影响[1-3]。目前临床治疗甲状腺癌多采取手术治疗,效果良好,但手术方案的选择较多,临床并无统一手术金标准[4-5]。为了研究治疗甲状腺癌最佳临床方案,我们特选取75例超声刀手术联合榄香烯注射液治疗甲状腺癌患者与既往75例传统开放手术甲状腺癌患者进行临床对比研究,分析治疗方案效果,现报告结果如下。
荀子兼综道家,调和儒法。在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所理解的道统,就是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传承。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传统,这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也是讨论道统的现代意义。“道”具有一种统序义,并由此形成了道统,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道统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影响了中华民族整个文化的发展和走向。从今天来看,我们应该继承中华民族的道统,如果割断了道统,其实也就制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儒家道统思想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之后,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学说,其中关于天道、地道、人道和中庸之道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在采访的形式上,需要注意好采访的主次关系。在采访开始之前,需要预先设计好使用的采访方式和需要运用到的采访技巧,并根据场合、事件的内容、性质,对采访的问题和模式进行选择,这样无论是对后期协作,还是编辑采访视频都会有更高的效率,并且保证了采访的质量。同时,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设想采访的过程,从采访的前提开始进行准备,保证采访能够环环相扣,把握好采访的每一个细节。并且,采访过程中可能会遇见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被采访者拒绝继续接受采访等。一方面要合理地设置问题和采访方式,保证被采访者能够接受,其次要做好准备,针对事件的性质和可能发生的情况制定处理方案,从而确保采访工作的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1]武振玉.朱子语类:十分[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2).
[2]王寅.荀子论语言的体验认知辩证观——语言哲学再思考:语言的体验性(之五)[J].外语学刊,2006(5).
[3]路德斌.荀子“性恶”论原义[J].东岳论丛,2004(1).
[4]王颖.试析荀子的理想人格理论[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l).
[5]张岱年.孔子与中国文化[J].清华大学学报,1986(1).
[6]龚鹏程.孟子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与影响[J].人文天下,2016(10).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19)01-0039-11
收稿日期:2018-09-10
作者简介:吴宁(1966-),女,安徽桐城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文星)
标签:荀子论文; 孟子论文; 人性论文; 礼义论文; 孔子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邯郸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