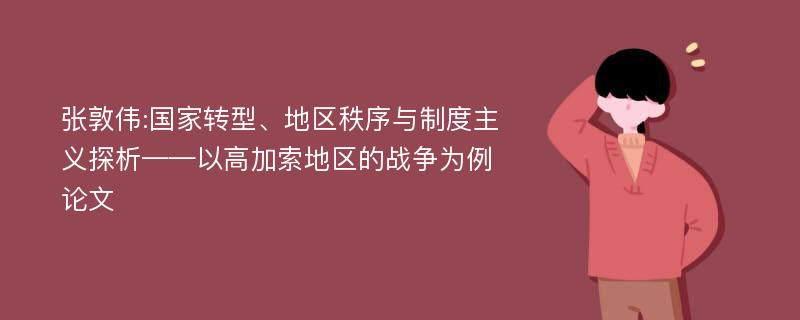
内容提要:随着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各共和加盟国的政治精英们有机会去夺取政权或者争取独立。而苏联的族群联邦主义所留下的历史遗产,也为族群间的分裂与冲突埋下了伏笔。新兴独立国家的治理能力不足,面临着严重的承诺问题与执政危机,不得不诉诸于军队介入来实现管控。在后冷战时代中,高加索地区依然频繁地发生族群冲突与国家内战。因此,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1.传统的冲突理论是否能够解释后冷战时代的国家内战?制度主义在其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2.通过高加索地区的战争案例研究,是否能够进一步地补充与完善现有的冲突理论,并预测国家转型与地区秩序的未来?本文拟采取案例比较的方法分析上述问题,揭示国家转型、制度衰落与冲突爆发这三者之间的因果解释机制。在高加索地区,国家转型造成了制度衰落,进而引发战争冲突,最终影响到地区秩序的平稳化过渡。国家转型与制度衰落为战争爆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窗口,而战争的扩大化与外部力量的介入,又使得高加索的地区秩序陷入一种“冲突循环”的状态中。
关 键 词:制度主义;国家转型;地区秩序;高加索战争;案例比较
在后冷战时代中,高加索地区为什么频繁地发生族群冲突与国家内战,战争进程又如何主导了该地区的秩序转型?这是长久以来困扰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采取案例比较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与解释。本文所选取的5 个战争与冲突案例分别是:俄罗斯国内的车臣战争,格鲁吉亚国内的阿布哈兹争端与南奥塞梯分离争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没有升级为内战的达吉斯坦问题与阿扎利亚问题。尽管每一个案例都依循着各自的运行轨迹,但也有着共同的背景条件,即苏联独特的帝国统治结构。随着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各共和加盟国的政治精英们有机会去夺取政权或者争取独立。而苏联的族群联邦主义所留下来的历史遗产,也为族群间的分裂与冲突埋下了伏笔。由于治理能力不足,且面临着严重的承诺问题与执政危机,新兴独立国家不得不诉诸于军队介入来实现管控。这也进一步地导致了国内局势的恶化与暴力冲突的升级,进而产生国家间的外溢效应。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的两个问题:1.传统的冲突理论是否能够解释后冷战时代的国家内战?制度主义在其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2.通过高加索地区的案例研究,是否能够进一步地补充与完善现有的冲突理论,并预测国家转型与地区秩序的未来?在国家的转型、制度的衰落与冲突的爆发三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因果解释机制,即国家的转型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不稳定性,导致制度产生更迭,进而容易引起冲突。尽管高加索地区的诸多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国家的独立、发展以及衰落,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爆发内战或者族群冲突。首先,族群冲突与国家内战的发生,取决于政治精英的内部分裂程度。其次,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也决定了国家内战的易爆发性。最后,对于国家内战而言,叛乱组织的经济支持同样对地区走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高加索地区,叛乱组织的物质基础往往根植于国家内部的经济掠夺之中。再加上外部力量的干预,国家内战往往会扩大为国家间的战争,从而引发地区秩序的大混乱。
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独立对于高加索地区的民众与精英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自从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后,高加索地区的各加盟国由原先的帝国边境,转化为无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带。摇摇欲坠的苏联政治制度被新的治理模式所取代,高加索地区也开始尝试重塑政权与建构国家。然而,制度变化与国家建设始终是一个冲突性的渐进过程。新旧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族群武装的大规模动员、公共物品的匮乏以及合法性暴力的缺失,使得高加索地区局势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中。从1985年到2005年期间,高加索地区爆发了4 场重要的战争。首先是1988—1994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领土战争,以亚美尼亚人为主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希望从阿塞拜疆国内分离出去,正式取得独立的地位;其次是1989—1993年格鲁吉亚的两场国家内战,分别为南奥塞梯争端与阿布哈兹争端;最后是1994—1996年以及1999—2000年俄罗斯的车臣战争。本文所选取的案例基本上涵盖了上述时间段内主要的国家内战与地区冲突,试图以此来解释在后冷战时代里高加索战争如何形塑了该地区冲突不断、缺乏稳定的政治秩序。
在南斯拉夫联盟地区和高加索地区,包括俄联邦的车臣地区在内,那些主张为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的族群和新国家都发动了成本极高的战争,造成数百万计流离失所的难民和数十万军人和平民的伤亡。如此高成本的族群主义爆发,民主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有卷入战争的后共产主义国家都试验过民主选举以及多无主义政治,除了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之外,其他的战争都不是由族群主义所点燃。简而言之,成功的民主化都延缓了族群主义,而部分民主化在某种情况下推动了族群主义。对于该地区族群主义与族群冲突飙升的起因,学术界的争论从未停息过。长期的民众对立、混居的族群分布模式和苏联崩溃后的军事不稳定,都被当做冲突发生的肇因。然而,斯奈德认为,不同国家的政治条件产生了不同的族群运动方式,然后,影响了族群主义形成的类型。这些模式受以下因素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时机;民主化对精英利益造成威胁的程度;转型期政治制度的性质。
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大部分属于后发展国家。在苏联时代,教育和工业化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前现代社会的部族社会模式特征仍然顽强地保留了下来,由此产生了族群主义迷思出现的可能性。在这些后发展国家的族群主义案例中,政治精英面对大众参与的新兴需求,面对反对派的强烈挑战,通常会自我分裂,然后产生寻求大众联盟的强烈念头,以在政治斗争占上风。在这样的背景下,族群主义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可以动员大众支持并瓦解反对派。被政治和经济变化吓坏的精英集团,如同尽力夺取权力的冒险家,争取把控观念市场,并未因其最终目的而放任族群主义迷思。相反,在另外一些后发展国家中,族群主义温和得多。这些国家面对的公民社会发育孱弱,缺乏官僚的援助,也缺乏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相关案例中,旧政治精英采取了温和的族群主义政策,由于民众的相对惰性与无组织性,因此,旧政治精英认为用强烈的族群主义诉求去刺激他们既无必要也会适得其反。
苏联所留下的制度遗产也会影响到这些后发展国家的转向及其族群主义政治模式。在后发展国家的新兴政治参与和民主制度缺陷之间,产生了一种族群主义强化的潜力。这种潜力如何发挥部分依赖于该国的行政制度以及社会团体如何参与政治的差异。由此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三种:1、按族群分划的联邦国家与单一国家;2、多族群混居背景下的苏联中心国家与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3、官僚制不成熟与庇护政治显著的国家。遵循族群联邦路线的国家大多发生了暴力的族群冲突,其他单一国家则既无分裂也没有族群冲突。因此,当其他因素有利于强化族群动员时,这一族群联邦主义的遗产会极大提高冲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如果曾经属于苏联的中心国家,政治精英则会面临使用武力的诱惑。最后,在高加索地区,国家经济大多是围绕联结不同部族的庇护网络。当苏联解体的时候,高加索地区发生了拥护族群独立和人民自治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由于大众政治被既有的部族庇护网络所绑架,两者之间的竞争利益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得势不两立。
三个高加索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在苏联崩溃后都经过了民主化阶段。在每一个国家,大众的族群主义运动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政治理论。这些大众能量助燃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族群冲突与国家内战。在格鲁吉亚,民主选举出来的族群主义政府与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少数族群的冲突,给俄罗斯的军事介入制造了借口。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战争中,产生了170 万的难民,并有5.5 万人丧生。这些高加索国家在高度的大众参与和低水平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换言之,它们围绕族群组织起来的政治,却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参与制度。综上所述,研究高加索地区的战争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国家转型、地区秩序与制度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问题背景与研究回顾
近年来,国家内战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无论是前沿科学化的定量研究,还是大案例对比的定性研究,目的都是要找出导致国家内战爆发的关键因素。①Walter W.Powell and Paul Dimaggio,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Michael L.Ross,“How Do Natural Resources Influence Civil War? Evidence from Thirteen Cas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1,2004a,pp.35-67.正如不少学者所言,苏联的族群联邦主义将国家领土与族群分布联系在一起,而不同族群之间的历史积怨与不安全感可能导致战争一触即发。②Xavier Raufer,“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Conflict: The Albanian Mafia,” Jan Koehler and Christoph Zürcher (eds.),Potentials of Disorder:Explaining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the Caucasus and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p.62-75.冲突理论认为,下面的6 个风险性因素可能会增加内战的发生几率:第一,低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更容易引发冲突。第二,国家崩溃与治理失败会增加内战爆发的可能性。第三,武装叛乱的资助来源决定了内战能持续长久。第四,旧的战争往往会滋生新的战争,曾经发生过内战的国家很可能会再次面临暴力冲突的威胁。第五,族群地理的复杂性增加了内战的风险。第六,多山的地形地势可能会导致内战的频发。①Xavier Raufer,“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Conflict: The Albanian Mafia,” Jan Koehler and Christoph Zürcher (eds.),Potentials of Disorder:Explaining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the Caucasus and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70.国家内战的频繁爆发,无疑会造成地区秩序的持续波动与冲突常态化。
分别从河南南阳、甘肃天水等地引进大花月季、丰花月季、藤本月季、树状月季等4个类型共计27个品种,主要为嫁接、一年生苗,窖藏,4月初分品种栽植于京韵青风景区。
高加索地区的诸多案例表明,战争的发动并不单纯地取决于对自然资源的汲取,因为叛乱组织里大部分的资金收益都来源于国内的掠夺经济。与世界上其他的多冲突地区相比,高加索也不是最为落后与贫穷的地区。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同样不是该地区分离主义频发的主要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引起了高加索地区中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呢?首当其冲的可能是当地民众的不安全感,即国内社会普遍认为,将来会出现一种不可挽回的经济衰落与国家崩溃。换而言之,民众对政治不确定性的恐惧导致了武装叛乱的发生,而不是出于改变现状的需要。因此,经济低迷与分配不公这两个原因,都不是导致高加索地区国家内战频繁发生的关键所在。
简而言之,本文所采取的案例研究有助于一种因果机制的检验,在促发因素与输出结果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如族群分布、国家治理以及地形因素对于内战爆发的影响等。除此之外,案例研究也能够很好地分析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弥补定量统计方法中普遍存在的“缺失值(Missing factors)”问题。②Nicholas Sambanis,“Do Ethnic and Non-Ethnic Civil Wars Have the Same Caus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quiry (Part 1),”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5,No.3,2001,pp.259-282.最后,案例研究还可以追踪国家内战的动态进程,并揭示在特定环境中族群冲突的不同演化方式,以及国家转型对地区秩序平稳化的影响。
与之相似,尽管大多数的国家内战都发生于多山地带,但也不意味着地形因素与内战爆发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在上述的多场战争中,决定性的战役都是在平原地带展开,尤其是在主要的大城市中。更加重要的是,国家内战不单表现为农村精英与城市精英之间的激烈对抗。与之相反,大部分的武装叛乱都由城市精英与知识分子所共同领导。当然,多山的地形地势在某种意义上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即延缓了政府军的进攻与镇压,为叛乱组织争取布置防御与进行转移的时间。
综上所述,并不是所有的风险性因素,对于内战的爆发都有着一种明确的因果联系。这是因为风险性因素大多内嵌于国内制度与体系结构之中,其影响与作用可能会被中和或者放大。所以,需要把风险性因素放入具体的案例环境中加以考虑,才能够明确不同的风险性因素在内战过程中的实际推动力。除此之外,国家内战的爆发还需要考虑集体行动、民众动员等诸多的问题。所以,本文尝试着将国内制度、体系结构与冲突理论结合起来,重新思考后冷战时代的族群冲突与国家内战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并逐步向外扩大直至形成稳定的影响机制。其中,国家治理能力将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高加索地区的独特政治环境。如前所述,苏联的解体为国家内部的政治精英提供了争夺政权的机会窗口。而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会导致武装叛乱的频繁发生。无论是俄罗斯、格鲁吉亚还是阿塞拜疆,都无法确保中央政府一定能够赢得针对分离主义所发动的战争。
一直以来,学术界似乎在理论上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共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国内冲突的发生与否。与富裕国家相比,贫穷国家的内战爆发风险要更高一些。费伦(James D.Fearon)与莱廷(David D.Laitin)指出,国民收入每减少1000 美元,内战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41%。②James D.Fearon and David D.Laitin,“Ethnicity,Insurgency,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7,No.1,2003,pp.75-90.赫格雷(Havarel Hegre)也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生剧烈变动时,国内冲突时常也会随之出现。③Havard Hegre,et al,“Toward a Democratic Peace? Democracy,Political Change,and Civil War,1816-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1,2001,pp.33-48.1945年以来,世界上的127 场国家内战中,发生在非洲地区有34场,亚洲地区有33 场,而欧洲地区仅有2 场。④Nicholas Sambanis and Elbadawi,Ibrahim,“How Much War Will We See? 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Civil War in 161 Countries,1960-1999,”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6,No.3,2002,pp.307-334.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也反映在苏联政权存在的最后阶段,具体表现为政治合法性的日益削弱与行政管理的逐渐失效,直至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国家暴力手段的垄断。这也标志着掠夺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的机会,最终使其成为叛乱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①Cynthia J.Arnson and I.William Zartman,eds.,Rethinking the Economics of War: the Intersection of Need,Greed,and Greed,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5,p.14.尽管在高加索地区中大多数国家的治理能力都在普遍下降,但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爆发了内战。所以说,一个国家政体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政治危机,还要取决于政治精英的内部结构。通过对以上高加索战争与冲突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家是否会爆发内战主要归结于制度化的权力分配完善与否,其分别体现为以下三点,即:政治精英是否发生分裂,政治精英的动员能力大小,精英联盟的持续时间长短。一旦国内危机失控,也会直接或间接地推动高加索地区秩序的平稳化转型。
二、导致国家内战爆发的不同理论解释
从先前冲突理论的文献综述中可总结出以下六个能够影响国家内战爆发的风险性因素。它们分别是: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存在着历史上的冲突情况,叛乱组织的资金支持充足,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有利于武装叛乱的地形环境。①Jeremy M.Weinstein,“Resources and the Information Problem in Rebel Recruitmen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9,No.4,2005,pp.598-624.Barbara F.Walter and Jack Snyder,Civil Wars,In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12.Stephan Van Evera,“Hypothes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4,1994,pp.5-39.Monica Duffy Toft,The Geography of Ethnic Violence: Identity,Interests and the Indivisibility of Territor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5.Jack Snyder,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New York: Norton,2000,p.43.由此可以总结出以下六种理论,即经济发展论、国家治理论、历史冲突论、叛乱支持论、族群分布论以及地理环境论。这些理论基本上涵盖了冲突理论范式对国家内战爆发的原因解释。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定量化的比较研究还试图通过案例的大数据采集,来系统性地总结出哪些因素的存在会导致社会滋生暴力以及国家爆发内战。与之相反,定性比较研究关注的是小规模的案例分析,以此来揭示风险性因素对于国家内战的爆发到底起着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一)经济发展论
就武装叛军而言,在军事上彻底战胜政府军始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相比于反政府武装的相对弱势,政府军拥有着更多的资源支持与装备优势。在后冷战时代的高加索地区,武装叛军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利用各自国家中政府军的弱点,来实现对现有政权的挑战。新组建的政府军训练不足,也不愿意在复杂且危险的多山地带与武装叛军进行作战。与此同时,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与腐败问题也制约了政府军的及时部署与展开。因而,叛乱组织与国家统治者之间的较量大体上维持着势均力敌的局面。在卡拉巴赫、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等地区,分离主义势力在特定的时间段内甚至还占据着些许的优势。
图2是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城市水系统水—能关系研究的概念框架。在概念框架中,城市水系统的能源强度研究是其他研究的基础,在该基础之上,分析水源类型和条件、水处理工艺、水质标准等各种影响因子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以期掌握造成不同区域或各个水系统能源强度差异的原因,从而有助于节能型城市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管理。然后,结合城市用水水平可以计算城市水系统的能源消耗总量,通过对比分析历史用水数据和不同时期的城市水资源管理实践所对应的能源消耗量,能够揭示城市水系统能耗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以及不同水资源管理策略对水系统能耗的影响。最后,可以计算城市水系统的碳排放量,分析节能减排的途径。
在高加索地区,包括车臣、卡拉巴赫、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在内的国家内战,都可以被视为可能具有族群主导性的4 个主要代表案例。其中,车臣的少数族群仅占27%,卡拉巴赫的少数族群仅占24%。④Nicholas Sambanis and Ibrahim Elbadawi,“How Much War Will We See? 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Civil War in 161 Countries,1960-1999,”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6,No.3,2002,pp.307-334.因此,如果上述案例能够证明分离主义起源于少数族群,那么就可以解释族群主导性对于内战爆发的催化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的族群联邦制也为此提供了足够的组织资源和动员能力。也就是说,苏维埃的政治制度会滋生出对于族群动员路径的一种强大依赖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缓和的自治主义也会逐步发展为激进的分离主义。然而,季什科夫(Valery Tishkov)也指出,单一的族群冲突分析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致命缺陷。毕竟大部分的多族群社会依然稳定,而大部分的少数族群也没有发动叛乱。⑤Valery Tishkov,“Ethnic Conflict in the Former USSR: The Use and Misuse of Typologies and Dat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6,No.5,1999,pp.571-591.所以说,族群边界并不是造成国内冲突的唯一原因,反而可能会随着族群冲突的发展演化,逐渐地得到强化或者削弱。
(2)流程中含盐废水循环使用,根据其含盐浓度决定是否进行置换,不仅节约了除盐水的消耗,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污水的排放量。
在2018年12月15-16日,中华龙舟大赛总决赛将再次划向碧海蓝天,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继续书写龙舟归乡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期待!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如霍洛维茨(Donald L.Horowitz)曾提出,族群冲突或国家内战的发生并不一定是因为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也可能是由国内少数族群的相对剥夺感而产生。①Donald L.Horowitz,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9.但实际上,高加索地区中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不大,再加上苏联的平均化政策与分配体系,不同族群在经济上的相对剥夺感也会较弱。更为重要的是,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一向没有主动地把经济上的歧视作为反抗的合法性理由。即使是在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北高加索地区,也不是所有的国家内部都出现过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更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经济上相对富足的阿布哈兹地区会发生国家内战,而其他贫困的地区却没有类似的分离主义问题。因此,低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内战之间似乎缺乏一种明确的因果联系。
(二)国家治理论
在新兴国家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往往会面临政权交接上的动荡。费伦与莱廷强调,国家取得独立的前两年里发生内战的几率最高,而政治的不稳定也是内战爆发的重要原因。②James D.Fearon and David D.Laitin,“Ethnicity,Insurgency,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7,No.1,2003,pp.75-90.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急剧的政治变动都会带来内战的潜在风险。在这一方面,就算是民主政体也没有天然的豁免权。科利尔(Paul Collier)同样发现,与民主政体相比,威权政体在这方面的国家脆弱性并不显著。③Paul Collier,“Doing Well out of War: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Mats Berdal and David M.Malone (eds.),Greed and Grievance: Economic Agendas in Civil Wars,Boulder,Colo.: Lynne Rienner,2000a,pp.91-113.费伦(James D.Fearon)对此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混合政体要比单一的威权政体或者民主政体更加危险,因为有限度的民众自由会催生反叛情绪,进而带来无限度的军事镇压。④James D.Fearon,“Rationalist Explanation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Vol.49,No.3,1995,pp.379-414.
(三)历史冲突论
国家治理论认为,能否实现国家的善治,决定了战争是否会发生。一方面,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够保证高效的资源分配,进而缓解国家内战的爆发;另一方面,稳定的国家治理也能够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以及在对外政策上保持一定的连贯性,从而避免国家间战争的出现。换而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局势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有效的国家治理难以实现,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会极大地提高。
在高加索地区,几乎大部分的国家都经历过政治上的剧烈动荡,才逐渐步入了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过渡的转型时期。因此,这些国家也普遍具有这样的特性,即政治空间的拓展伴随着国家能力的下降。换言之,政治自由化与国家现代化为内战开启了一个爆发的机会窗口。随着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高加索地区的国家政治精英竞争陷入无序状态,原来的国家制度也不再内嵌于政治进程之中。因此,在车臣、阿塞拜疆以及卡拉巴赫等地区,分离主义者时常通过街头暴力与激进运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科雷的文化里,有一种崇尚创新、敢于冒险的精神。”在谈及科雷的企业精神时,项建龙不无自豪地说道,“科雷人喜欢钻研一些世界性印刷难题,不是说哪个产品赚钱就去生产哪个产品,而是愿意去探索、解决那些对全行业而言较为棘手的问题”。
历史冲突论代表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之间在历史上发生过较为激烈的冲突,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将会受到这一历史冲突的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冲突双方或多方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与恐惧感。之前的冲突给政治精英与国内民众留下的历史记忆,也会对其策略选择与行动偏好产生推动作用,进而加剧当前的危机情况。从高加索地区的四场战争来看,这一相互对峙的局面之所以会进一步恶化,大多是由于历史上发生的冲突给彼此带来的安全匮乏。
(四)叛乱支持论
随着主流冲突理论对经济因素的日益重视,叛乱组织的资金支持问题也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如石油、宝石等经济价值高的自然资源,成为了叛乱组织赖以依存的重要基础。不少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显示,石油的产量与内战的爆发、分离主义冲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甚至会引发来自外部的武装干预。可掠夺的自然资源变成了叛乱组织的首要控制目标,从而形成所谓的“资源诅咒”。①Michael L Ros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source Curse,” World politics,Vol.51,No.2,1999,pp.297-322.
综上所述,首先,苏联解体对高加索地区的诸多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除了合法性降低与治理能力下降以外,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甚至还失去了对国家暴力的合法垄断权。因而,不少的武装叛军能够汲取资源、筹措资金及缔结联盟,以此来对抗中央政府。其次,国家主义者与改革主义者控制了中央政权,国内的政治精英对于寻求脱离苏联达成了不稳定的共识,进而加剧了族群间的冲突现状。所谓的车臣革命清除了苏联官僚势力,但是,新的政治当权派却依旧陷入分裂与斗争的困境。在格鲁吉亚,国内情况也十分地相似。国家精英在赢得民主选举之后,不仅没有与旧的政治势力达成和解,反而引发了新的国内矛盾。对民粹主义的过度依赖,使得格鲁吉亚走向了激进的国家“去制度化”。
(五)族群分布论
不少跨国家的定量分析与案例比较都已经表明,多族群国家在爆发内战上的可能性并不比单一族群国家高。①Douglas 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27-43.在科利尔和霍夫勒(Anke Hoeffler)看来,与族群碎片化相比,族群同质化高的国家安全性更低。他们的理论假设是,族群碎片化增加了内战中作战人员的招募成本。②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Resource Rents,Governance,an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9,No.4,2004,pp.625-633.因此,族群的主导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催生内战爆发的重要因素。一旦国内社会变得不稳定,族群因素甚至会成为内战爆发的首要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约有超过一半数量的内战受到了族群因素的显著影响,超过三分之一数量的内战甚至可以被定义为族群战争。③David A.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Ethnic Conflic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8.
尽管如此,低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内战爆发两者之间,还是不能够简单地划上等号。在费伦与莱廷看来,战争的风险主要取决于国家面对叛乱的应对能力。⑤James D.Fearon and David D.Laitin,“Explaining Interethnic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0,No.4,1996,pp.715-735.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动员水平与行动方式。但在高加索地区,很难将所有发生内战的国家都归入欠发达国家的行列。20世纪90年代,格鲁吉亚的经济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低并不是高加索地区中国家内战频繁发生的真正原因。
(六)地理环境论
武装叛乱的地形环境之所以受到学界的重视,主要是因为不少的学者认为,多山地形能够为叛乱组织提供良好的避难所或隐藏地,并且极大地增加了政府军的镇压成本。这两个因素直接关系到武装叛乱的成功与否。在多山且地形复杂的高加索地区,频繁发生的内战冲突似乎也表明了其地形环境与武装叛乱的潜在联系。但事实上,内战冲突往往围绕权力斗争而展开,武装叛乱更多的是在国家首都或周边城市中发生。特别是在南奥塞梯战争中,地形因素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杨先生说:“不容易啊。从马占山将军算起,国人抗战,打了十四个年头。现在好容易要把东洋人赶跑了,你这时候去那狼窝,要有个三长两短,就太不值了!”
政府军借助冬季山区的物资匮乏,成功地封锁了叛乱组织的行动,并切断了他们与北奥塞梯之间的联系。在阿布哈兹与卡拉巴赫战争中,冲突双方的争夺要点在于具有战略性的大城市,而不是广袤的边远山区。至于车臣战争,武装叛军只是在失去城市的根据地后,才不得不退往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因此,多山的地形地势或许只是延长了内战的持续时间,而不是导致内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红色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中占比不足,红色教育活动开展较少,教育形式也局限于征文比赛、演讲比赛、合唱比赛、观影活动等。受时间、经费等因素的限制,去烈士陵园扫墓、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活动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导致学生接受红色教育途径少,校园红色教育实效性差。除了线下活动,据调查,各大高校少有建立专门的红色教育网站或在官网上有红色专题宣传板块,即便已建立的红色教育网站也存在内容陈旧、更新慢、吸引力不强等问题,点击量少,不能充分发挥网络红色教育作用,教育体系不够完善[4]。
三、国家转型、地区秩序与战争爆发
从1989年以来,高加索地区卷入战争的次数,约占全世界内战爆发总量的30%。①Suzanne Goldenberg,Pride of Small Nations: The Caucasus and Post-Soviet Disorder,London: Zed Books,1994,pp.24-37.然而,该地区所发生的国家内战并不支持冲突理论的两个普遍性假设,即国家内战的发生与多山地形地势、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与此同时,国家内战的发生与新兴政体的脆弱性之间反而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在后冷战时代,高加索地区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治理能力上的极大削弱,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国家却能够迅速作出调整,而不至于引发内战。这主要取决于不同国家中政治精英结构的庞大断层与内部分裂是否能够被弥合。更为重要的是,族群在地理分布上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国家内战的发生风险。叛乱组织通过族群动员获取民众的支持来维持内战的消耗,并借助资源汲取来凝聚反抗国家的力量。
冲突理论认为,族群杂居的复杂性会增加分离主义叛乱的发生风险。②Edwar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Democratic Transitions,Institutional Strength,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2,2002,pp.297-337.在高加索地区,国家内战之所以频繁爆发甚至升级,主要是因为主导性族群的“统治排斥”。在南奥塞梯、车臣以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因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国家分离主义叛乱,时常需要中央政府或外部国家的军事介入才得以终止。在上述的案例中,一旦叛乱与暴力蔓延开来,那么势必会导致大规模的族群清洗与国家内战。随着国内局势的恶化,族群冲突甚至可能演变为国家间的战争。正如科利尔和霍夫勒的观点,族群的碎片化分布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冲突的发生率,同质性低的多族群国家反而更加稳定。①Paul Collier,et al,“What Makes a Country Prone to Civil War?” Paul Collier,V.L.Elliot,Havard Hegre,Anke Hoeffler,Marta Reynal-Querol,and Nicholas Sambanis (eds.),Breaking the Conflict Trap: Civil War and Development Polic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53-92.这是因为,族群的碎片化极大地增加了组织暴力的成本。
与此同时,苏维埃联邦制所塑造的政治边界也进一步加剧了族群的对立。多数族群希望的是维持以往的优势地位,少数族群则迫切要求改变当前的不平等状态。在国家的内部问题上,自治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为了获取更多的特权,不惜脱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因此,在高加索地区国家分离主义日益兴起,而争取选举合法性也成为了武装叛乱的理由之一。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民众暴力都能够转化为行动有素的武装叛乱。在之前的案例中,无论是车臣战争、卡拉巴赫战争还是阿布哈兹战争,无一例外都属于人民战争,得到了大多数当地民众的积极支持,这也使得内战的持续性大为加强。在冲突理论看来,对自然资源的汲取是叛乱组织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而在高加索地区,自然资源的作用却显得微乎其微。只有车臣地区和阿塞拜疆拥有较为重要的石油资源。但是,对于这两者来说,石油资源与族群冲突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因为阿塞拜疆的政治精英更热衷于权力斗争,而不是对亚美尼亚发动战争。
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没能带来经济上的发展,反而造成了高度的政府腐败、贫乏的国家治理以及频发的地区冲突,这也证明了自然资源的可掠夺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国家内战的持续时间。例如,在阿富汗,宝石与鸦片交易一直是北方联盟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如此,但这并不是说自然资源会直接导致内战的爆发。在高加索地区,也只有阿塞拜疆与车臣满足“资源丰富”这一条件,因此理论的解释力存在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先前的战争无疑会滋生后续的战争。在五年内发生过内战的国家存在着内战重燃的高风险性。再加上长期内战的巨大消耗,一个国家在面对新的内战时应对叛乱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论商标戏仿的法律性质 ...........................................陈 虎 12.22
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塞拜疆似乎也步入了常见的“中亚式政治崩溃模式”。1992年,阿塞拜疆因为输掉了对亚美尼亚的战争而政权更迭。然而,新的执政者执政仅15 个月,又由于政治斗争失败而不得不黯然卸任。亚美尼亚同样面临着国内政治上的持续僵局,尽管夺回卡拉巴赫在短期内避免了新旧精英之间的进一步分裂,但在加入欧盟以及国家转型问题上双方仍然分歧重重,极有可能陷入内战循环的风险中。在这一方面,达吉斯坦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采取权力下放和实行地区自治等多种手段,达吉斯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内政治转型的平稳过渡。如此来看,国内转型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政治精英的和解能力。
她把行李打开铺好,又把房间简单那么一收拾,马上焕然一新,细心的姑娘在这一点上,就比小伙子强,房间立刻融满了说不清是香水还是香皂的馨香气味。
四、高加索地区的战争案例
(一)车臣战争
在车臣战争这一案例中,斯大林时代中央政府与车臣的冲突历史与俄罗斯军队的军事行动,无疑成为了车臣叛乱组织最好的动员工具。而长久以来俄罗斯对车臣人的不信任,更是加剧了彼此之间的仇恨与不安全感。车臣叛乱组织的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不像其他联邦共和国一样拥有温和的政治精英与中产阶层。而在苏联解体之后,车臣也正式宣布从俄罗斯联邦独立出来。对此,俄罗斯以其归属于自己的加盟共和国管辖为理由,发动了旨在维护俄罗斯统一的车臣战争。第一次车臣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最后俄罗斯在国内政治斗争的困扰下,不得不签订停火条约并撤出车臣。
直至1999年,俄罗斯国内的不同城市发生了多起严重的爆炸案。俄罗斯又以反恐为名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在俄罗斯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车臣叛乱组织产生了严重的内部分歧与派系分裂。再加上石油资源收益的进一步减少,更加削弱了车臣叛乱组织的武装战斗力。在两次车臣战争中,族群主导性因素所起的作用并没有特别的显著。俄罗斯军队在占领车臣地区后,也没有发起种族清洗或大屠杀。而且,尽管车臣人在反叛武装部队中占绝大多数,但其所针对的同样不是俄罗斯人。因为在车臣战争开始之前,大部分的俄罗斯人就已经从该地区撤离出来。与之类似,地形因素在车臣战争中的影响也非常有限。虽然车臣反叛武装部队在作战失败后选择退回山区坚持进行游击战,但这只是稍微延长了战争持续的时间。它既不是国家内战发生的主要条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内战的进程。
(二)格鲁吉亚战争
格鲁吉亚战争的基本结构主要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居于顶端的俄罗斯中央政府,然后是居于中间的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最后则是居于底层的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它再一次揭示了苏联的族群联邦主义对国家内战所起到的催化作用。这一自上而下的等级化结构在政治控制力上日渐减弱,而分离主义压力却在不断增强。这也直接表现为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正式宣布独立。格鲁吉亚的国家脆弱性主要体现为执政者的内部分裂。再加上激进的社会运动以及日益增多的武装叛乱,使得格鲁吉亚不得不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来维持国内稳定。而阿布哈兹内战与南奥塞梯内战的爆发也与之密切相关。它们与俄罗斯组成了一个策略性联盟,即俄罗斯支持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的独立,后两者也同意加入俄罗斯联邦。尽管格鲁吉亚采取了民粹主义式的国家动员,但依然无法与强大的分离主义势力对抗。
由于格鲁吉亚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只能通过别的方式来筹集战争的资金。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格鲁吉亚战争的持续时间一般都比较短。格鲁吉亚国内外的阿布哈兹人与南奥塞梯人积极地为自己的武装部队提供人力、武力与财力上的支持,因此可以说,族群主导性因素在这两场内战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苏联统治的时期内,作为多数族群的格鲁吉亚人享有政治经济特权以及苏联军队的保护。而在苏联解体之后,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地区内的族群主义与分离主义动员也日渐增多,最后演变为大规模的独立运动与暴力冲突。直至今日,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仍然处于冲突频发的状态中。无论是俄罗斯、格鲁吉亚还是其他的外部势力,都始终在争夺这两个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在“ABB电力与自动化世界”上,ABB集中发布了68款新品,并向中国市场推出20项ABB AbilityTM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及最新的数字化平台,支持电力、工业、交通与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用户加快数字化转型。这也是一年多来ABB最大规模向中国用户集中展示ABB在数字化领域取得的最新技术成就和重要突破。
一般人家都有一个小庭院,院前用篱笆围起来,院后有竹篁,院内的小路用的是青石板,用刨木板来架构房屋,松明照亮,一家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村田园生活,如图2所示。
(三)卡拉巴赫战争
卡拉巴赫战争是中央政府丧失执政合法性与强制性权力的一个典型代表。与车臣、格鲁吉亚相比,卡拉巴赫是唯一一个在外部威胁影响下执政者与反对派达成合作共识的案例。当然,这一合作共识并没有阻止国家内战的发生,反而起到了某种加速战争的催化作用。高加索地区中最早发生暴力冲突的正是卡拉巴赫。卡拉巴赫一方面缺乏成熟的制度机制来应对族群冲突,另一方面又在苏联的影响下丧失了自主决策权,最终导致了局势的失控。直至1989年12月,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依然尝试着通过苏联宪法来解决这一领土转移问题(question of territorial transfer),即要求脱离阿塞拜疆、回归亚美尼亚,但莫斯科方面否决了这一请求。①James Hughes and Gwendolyn Sasse,“Comparing Regional and Ethnic Conflicts in Post-Soviet Transition States,” 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Vol.11,No3,2001,pp.1-35.Ted R.Gurr and Barbara Harff,“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Ethno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Conflict,” Ted R.Gurr and Barbara Harff (eds.),Ethnic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Order,Boulder,Colo.: Westview,1995,pp.77-97.1991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分别获得独立之后,双方在卡拉巴赫的对峙也开始逐步升级。阿塞拜疆正式废除了卡拉巴赫的自治州地位,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将该地区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国家内战随即爆发。
卡拉巴赫案例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学界主流冲突理论的挑战。冲突理论认为,在自然资源丰富、多山地形的国家中更容易发生内战。但是,在山区众多且石油资源丰富的卡拉巴赫,这两点因素没有对内战的发生产生太多的推动作用。在本文高加索地区的诸多冲突案例中,国家的脆弱性一直占据着关键的地位。由于阿塞拜疆中央政府在卡拉巴赫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与强制性权力,再加上亚美尼亚的分离主义动员,由此导致了国家内战的不断升级。除此之外,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也有着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当不同的族群密集地定居于某一狭小地区,且彼此之间有着明确的分界线时,国家内战发生的风险最高。对于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将是族群冲突爆发的催化剂。在卡拉巴赫案例中,历史上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长期的冲突状态导致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尤其是1988年2月针对亚美尼亚人的苏姆盖特大屠杀,更加证明了如果没有可信的安全承诺保障,那么暴力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一再发生。
(四)反常案例:达吉斯坦问题与阿扎利亚问题
关于达吉斯坦这一案例,学界中一直存在着众多的理论解释。一般主流的观点是,它基本上验证了科利尔和霍夫勒的冲突理论,即低碎片化的国内社会要比高碎片化的国内社会更加脆弱。科利尔和霍夫勒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因果解释机制:首先,在高度碎片化的社会中,联盟机制会尽可能地排除政治上的极端思想。其次,碎片化的族群分布也会增加民众动员的难度与成本。②Paul Collier,et al,Breaking the Conflict Trap: CivilWar and Development Polic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a,p.53.这两点都极大地降低了国家内战的发生概率。因此,族群社会的碎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效应。正如达吉斯坦案例所揭示的那样,形成联盟与寻找共识是避免国家内战最好的方式。跨族群之间的紧密联系与1994年的达吉斯坦宪法是维持达吉斯坦稳定局势的两个互动性机制。前者有助于达吉斯坦形成较为稳定的政治同盟,而后者则通过族群比例代表制帮助不同族群找到了一致的共识。在这样的前提上,来自苏联的外部干预对于达吉斯坦不再是一个破坏性因素,反而有利于缓解达吉斯坦不同族群之间的紧张态势。即使到了苏联解体的后冷战时代,达吉斯坦的政治精英依然能够在国内权力的分配上保持着较高的认同,而不至于发动国家内战。
人民城市人民管。永济市把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精细化管理城市的一大法宝,将城市驿站作为联系群众和管理者的一个枢纽,对群众反映的市容环境、乱搭乱建、流动摊点、市政实施维修等问题做好记录,打包上报城建局,分解到城管队,通过销号的方式进行解决,问题处理在驿站进行公示,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形象。
尽管阿扎利亚也饱受分离主义冲突的困扰,但是,为什么它并没有像南奥塞梯或者卡拉巴赫一样升级为国家内战呢?从总体上看,阿扎利亚地区70%以上的人口都属于阿扎利亚人这一族群,也有着较为成熟的政治制度来进行民众动员。由于大部分阿扎利亚人都是穆斯林,因而与格鲁吉亚的“国教”身份——基督教存在着极大的隔阂,甚至要远远大于格鲁吉亚人与南奥塞梯人之间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阿扎利亚人有着充足的金钱、物力以及人力来实现自我武装,以阿扎利亚的自治主义来对抗格鲁吉亚的国家主义。在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看来,尽管阿扎利亚人与格鲁吉亚人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但阿扎利亚人依然将自己视为格鲁吉亚国内的重要一员,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从祖国中独立出去。①Monica Duffy Toft,“Multi-nationality,Regional Institutions,State-Building and the Failed Transition in Georgia,” 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Vol.11,No.3,2001,pp.123-142.德卢古安(Georgi M.Derluguian)认为,在苏联统治时期格鲁吉亚所采取的同化政策极大地削弱了阿扎利亚实行独立的政治合法性。②Georgi M.Derluguian,“The Tale of Two Resorts: Abkhazia and Ajaria before and since the Soviet Collapse,” Beverly Crawford and Ronnie D.Lipschutz (eds.),The Myth of “Ethnic Conflict”: Politics,Economics,and“Cultural” Violen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Digital Collection,No.98,1998,pp.261-292.也就是说,阿扎利亚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被过多地政治化。而且,苏联军队所提供的安全承诺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阿扎利亚变成第二个波斯尼亚。最后,格鲁吉亚与阿扎利亚政治精英之间的高度一致性确保双方能够建立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消除了潜在的国家内战风险。
结语
如前所述,单纯从族群政治的角度出发,很难解释高加索地区的动乱状态。车臣、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无一例外都面临着国家重建的问题。在国家重建的过程中,又因为政治承诺的可信性而催生出新的族群冲突。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既没有对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叛乱与国家内战问题作出详尽的说明,也没有充分解释地区间的紧张局势如何转化为有组织的暴力。①Christoph Zürcher,Pavel Baev and Jan Koehler,“Civil Wars in the Caucasus,” Paul Collier and Nicholas Sambanis (eds.),Understanding Civil War: Evidence and Analysis,Vol.2,Europe,Central Asia and Other Regions.Washington,D.C.: World Bank,2005,pp.259-299.换言之,叛乱组织的作战成员是以何种方式被招募,又是如何武装自己、如何汲取可利用资源这一些问题仍待解决。所以本文认为,在分析这一系列族群冲突的发展轨迹时,“制度”应该成为最为重要的影响变量。这是因为,“制度”决定了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方式,行为体也依赖于制度来选择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制度性框架能够塑造行为体的期望、恐惧以及偏好,并将其全部转化为战略行为。因此,在解释国家转型、地区秩序与战争爆发三者之间的潜在联系时,需要考虑到“制度”所带来的影响。而本文所提到的6 个风险性因素,同样能够纳入制度的解释体系之中。例如,通过评估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可以反映出其制度运作的基本情况。在上述的6 个风险性因素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无疑是促使内战爆发的直接原因,而历史上的冲突情况、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叛乱组织的资金支持充足以及有利于武装叛乱的地形环境都是导致内战发生的间接原因。特别是在特定的背景条件下,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非常有可能成为催化国家内战的主导性因素。因此,不仅是国际制度能够影响到地区秩序,有时国家制度反而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了将“行为体中心(actor-centered)”这一视角引入理论分析之外,制度还能够纠正冲突分析中的多元偏差,简化冲突过程里的中介变量。②Christoph Zürcher and Jan Koehler,“Institutions and Organizing Violence in Post-Socialist Societies,” Berliner Osteuropa Info,Vol.17,2001,pp.48-52.Fritz W.Scharpf,Games Real Actors Play: Actor-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cy Research,Boulder,Colo Westview.1997,p.36.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解决跨学科的多种问题。例如,经济学家通过制度主义来解释经济绩效、欧洲各国福利政策的差异、大规模的历史变迁以及官僚阶层的行为惯性。政治学家利用制度比较来分析国内政治的不同情况,国际关系学家则关注的是制度因素在国际合作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在冲突研究中,制度无疑也具有着强大的解释力。然而,制度的影响同样有着一定的两面性,它不仅能够减少冲突,同时在特定情况下也能够滋生冲突。因为任何冲突的发生与消解,都是国家与社会中制度性框架的输出结果。从总体上看,“制度”主要通过两个机制来避免冲突的发生:一是借助特定程序来弥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竞争;二是利用强制性手段(如监管与惩罚)来防止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升级。即使冲突依然无法完全避免,但也可以说制度内置于冲突之中,并能够对其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制度拥有着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民主程序能够保证不同群体尽可能地参与政治与塑造政体。保护弱者的制度设计可以缓和少数族群中的不满情绪,而权力下放与地区自治更是对各方利益的兼顾与平衡。
在苏联国内不同族群之间的权力划分,大部分都通过自治州或领土内部自决的方式加以实现。在多族群地区与共和国中如卡巴尔达—巴尔卡里亚与达吉斯坦,多数族群有可能会对少数族群形成某种政治上的高压。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强制性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它通常表现为国家的治理以及对暴力的垄断。大多数的国家稳定往往建立于强大的制度能力之上,但是,也有不少形成了制度化的恩庇关系网络。①恩庇关系网络指的是一个具有强制性,能够持续运作的政治组织,其行政人员能够成功地持续主张他们是正当地以垄断武力作为执行命令的后盾,所以是包含有命令、行政人员、合法武力后盾等特性的组织。这一恩庇关系内嵌于国家制度之中,并随着官僚阶层的发展而演化为复杂的关系网络,直接影响着政体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一般来说,制度变迁并不容易发生。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算政治制度依旧保持稳定,这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体都会满足于当前的权力均衡。一旦发生急剧的制度变迁,将很可能导致国家内战的爆发。在高加索地区,国家转型造成了制度衰落,进而引发战争冲突,最终影响到地区秩序的平稳化过渡。这一因果解释机制也说明了制度的分配性结果以及其内嵌于冲突之中的调节或强制能力,对于解释族群冲突与国家内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上述的案例中,国家转型与制度衰落为战争爆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窗口,而战争的扩大化与外部力量的介入,又使得高加索的地区秩序陷入一种“冲突循环”的状态中。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关键问题,即多族群国家如何能够避免内战的发生,并采取何种方式的制度强化来实现自身政治的巩固。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稳定也能够进一步形塑其外部周边的安全环境,并且有利于保证良好的地区秩序以及去冲突化。
作者简介:张敦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与安全战略。(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2096-4536(2019)05-0098-18
(责任编辑:史泽华)
标签:族群论文; 国家论文; 内战论文; 高加索论文; 冲突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战争与和平问题理论论文; 《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年第5期论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