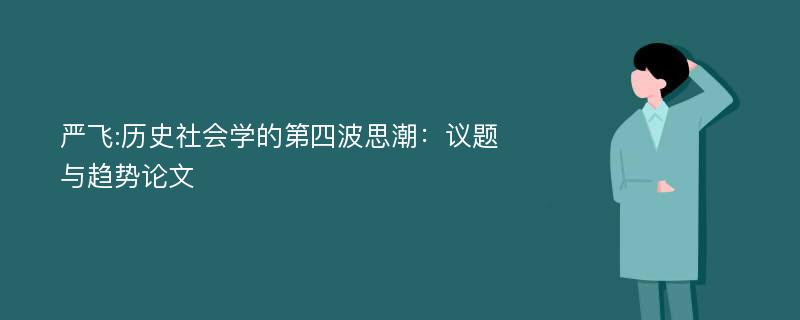
[摘 要]历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已经历过三波发展思潮,实现了研究焦点从社会结构到主体行动的转变,行动者的能动性和情感被赋予新的解释。在最近十多年里,历史社会学在第三波思潮的基础上,进行了崭新的探索。本文从研究方法、理论建构、宏观研究议题和微观研究议题四个维度梳理了历史社会学大致的发展趋向和框架式脉络,展望历史社会学的第四波思潮。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 研究方法 思潮 社会结构 行动者
1959年,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明确指出,“历史想像力”对社会学的研究十分必要。①事实上,社会学的出现,正是为了回应和解释时代性的社会变迁——诸如资本主义的诞生、现代国家的起源、工业化与商品化的发展、社会制度的演进与更迭这样宏大的命题,无不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②历史社会学也因此成为社会学学科领域里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分支,吸引了众多研究者投身其间。正如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鼓舞人心的宣言所昭示的,“历史社会学已经从涓涓细流汇聚成了滔滔江河,流遍社会学领域的各个角落。”③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自1960年代迄今一共经历了三波发展的思潮。④然而1990年代到今天,历史社会学领域内又延展出崭新的趋向和议题。本文将就这些趋向和议题,结合新一代历史社会学者的研究,进行分类和总结,并就历史社会学第四波思潮的发展路径进行剖析和展望。
一、历史社会学的三波思潮
历史社会学的三波发展思潮深深嵌套在社会学学科本身的演化中。第一波思潮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对政治转型与变迁背后的制度性动因表达出深刻的历史关切,提出要返回历史的大视野,去剖析现代性的形成。但这种关切,还是帕森斯式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一种递进,试图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社会运行演化体系,将复杂的历史过程化约为无关时间的结构性变化,但忽视了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历史的动态变化和关键节点上的历史偶变性,在历史社会学理论层面,也缺少突破和创新。这一阶段代表人物和作品有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odernization:ProtestandChange)、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inIndustrialSociety),以及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早期作品《旺代》(TheVendée)。
第二波思潮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更加关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差异性,或者说是历史变量的差异性。研究命题依旧集中在宏观层面上,注重结构性分析,特别是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共力之下如何产生叠加的聚集效应,从而导致出诸如革命爆发、国家建构、资本主义形态的不同历史演化轨迹。这一阶段的学者,普遍忽略个体情感、文化制度这些重要因素,同时不再关注意识形态、思潮、观念或者是社会心理层面的变量如何影响国家、阶级的形成。
那些出土的木锹、竹筐、藤篓、绳索、木钩、木槽、桶、勺等器具,直观地告诉我们古代矿工采掘每一块矿石的艰难。采矿是地下的营生,矿工们用木头撑起长宽约六十厘米左右的方形框架,形成一个个地下洞穴。矿工们在这狭小的井洞里,像老鼠般蜷缩着,展不开臂,伸不直腰。在木头支架吱吱作响、时时有塌方冒顶可能的“猫耳洞”里,用铜斧、凿、锄、钻、石头、木头,一点一点地从坚硬的岩石上,撬下一块块矿块。然后,用绳索系着藤蒌,一筐一筐地把矿块矿屑吊上地面,送去冶炼。
在方法论上,此一时期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就是历史社会学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它把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纳入到历史社会学的范畴中,达成了研究方法上的提升。⑤譬如说斯考切波在其代表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中,不仅论述了“国家自主性”这一核心观点,试图统筹结构和能动这一矛盾,而且结合大量史实加以论证,确立了比较历史研究法的研究范式。
第二波思潮也在学科范式的探索中陷入困境——虽然学者们努力在寻找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点,但在实践中却受到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批评,被指为制造出“社会学的四不像”(sociological unicorns)。⑥一方面,社会学家批评宏观比较的历史社会学家未能遵循标准的实证路线,必然导致事先选择有限的因变量,使得其解释的适用范围缩小,认为他们应当更加注重一般性、抽象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则批评历史社会学未充分关注个案的特定属性,未深入掌握相关的原始素材和第一手文献资料,放任自己做出缺乏根据的、叠加的抽象研究。与此同时,由于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中的求同法和求异法在案例选择的时候,多是在横向时间维度上进行比较,而缺乏纵向时间维度的因果机制提炼,导致出现所谓的“有历史无时间”的问题。⑦
第三波思潮则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一大特点,即研究维度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和对于行动者能动性(agency of actors)的强调。此一时期的学者们站在重塑现代性(reshape modernity)的立场上,将第二波所忽视的诸多文化维度放在了研究前端。他们透过对微观情境中行动者主观行为和动机的分析,试图实现从社会结构到主体行动的转变。
John Goldthorpe, “The Uses of History in Sociology: Reflections on Some Recent Tendencies,”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 vol. 42, no. 2 (June1991), pp. 211-230.
⑥Lawrence Stone, “The Revolution Over the Revolution,”NewYorkReviewofBooks, 11 June 1992.
在这三大框架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罗杰·古尔德(Roger Could)抛弃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理论,揭示出阶级行动者的行动并不是来自共有的阶级意识,而是基于社区中的非正式网络,在相邻的社区中通过彼此的文化纽带而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动员的力量,从而凸现出各种网络、资源和文化建构的过程性关系。凯伦·巴基(Karen Barkey)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时间维度出发,考察了决定帝国延续的多重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国家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结构洞。菲利普·戈尔斯基(Philip Gorski)舍中心取毛细,追溯各种主题概念形成的制度化谱系。赵鼎新则强调在社会运动研究中互动双方的情感预期,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去查看这样的情感预期如何影响运动参与者的情绪变动,进而影响运动的发展。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以情感的模式重新检视中国革命,发现情感治理是中国式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历史时间上得到延续和继承。
历史社会学的第一波思潮重点解构现代性发展的政治过程,关注宏大的命题,缺少理论精炼。第二波思潮则撇去情感、心理、意识形态这些变量,主要看结构性的动因,并明确提出学科研究方法为“比较历史分析”。第三波思潮重新进行文化的转向,通过对微观情境的分析探讨第二波所忽视的诸多文化维度,并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试图揭示出因果性的机制和逻辑。第三波的学者实现了从社会结构到主体行动的转变,行动者的能动性以新的方式成为了思考的焦点。
二、第四波思潮的潜在趋向
迄今为止,我们依旧处在历史社会学第三波思潮之中。会不会有第四波思潮?什么时候会出现第四波思潮?对于这样的疑问,我们目前尚难以给出非常明确的回答,但至少有四点历史社会学发展的新趋向,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新一波历史社会学研究更加倾向于使用包括档案、口述史、信函、内部文件在内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在以巴林顿·摩尔和斯考切波为代表的早期学者研究中,囿于研究设计和数据质量,基本上都是基于已经公开发表的二手资料。这一时期有高达84%的学者仅仅依靠二手资料就完成了比较历史研究。尽管第三波思潮的学者已经愈发重视一手经验材料的使用,但根据一项针对1993年至2013年32部在美国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分会(AS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Section)获奖作品的分析来看,尽管学者们在专著中更多地引用一手文献资料,但经验性证据的比例整体在下降,同时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研究性论文更多的使用了一手文献资料。虽然使用二手文献资料是可以被接受的,但过多的倚重二手资料而缺乏一手经验材料的支撑,就会陷入“对于解释进行再解释”的双重建构之中,难免不会出现断章取义、囫囵吞枣式的歧义和选择性书写。因此,越来越多新一代的比较历史研究学者,深入田野、档案馆和案例所在地区,通过不断挖掘原始档案资料和口述史访谈,再现历史的情境。
第二,在理论建构上,新一波历史社会学研究更加强调对于因果机制的探寻。对于历史图景背后的机制挖掘,其目的,一是运用通则性的机制解释更大的变异。研究者的旨趣,不仅仅停留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机械还原或者把社会学的理论嵌套在史料之上,而是更进一步从复杂的历史叙事中理出非故事性的逻辑,掌握其内在的因果律。二是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在比较的视域里扩展出对单一社会与政治现象的联动性解读,强调解释变量在不同时空脉络背后所发挥的预测性效应(predictive power)。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强调因果律的可预测性与可重复观测性。研究者们通过一个具体的实证案例研究,挖掘出事件发生背后的社会机制,并将这一机制放置在另一个社会情境、国别体系之下检测是否依旧有其效度和解释力。只有经过这样的反复检验和比较,才可以形成一个更优越的“经过社会科学认证过的故事”。
第三,在宏观议题上,新一波历史社会学研究更加重视量化技术分析。针对大跨度、长时段的历史纵贯变迁,学者们依托结构化的历史数据,或对已有的理论和模型进行检验,或通过定量研究发现新问题并建立新理论。早在1970年代,蒂利就已经认识到数据收集的重要性,不再进行人工的手动编码,而是借助电子计算机的帮助,对国家缔造和资本主义诞生等宏大命题进行探索。最近十年里,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们通过报纸杂志、简报文件、档案县志等资料开始系统收集历史维度的数据,为数据进行编码并建立数据库,用计量统计探讨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的诞生和蔓延,政治暴力的崛起和衰落,以及在空间维度上社会运动的扩散模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在历史社会学领域里的应用和发展。传统定量研究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手段,是采用经典的线性或非线性计量模型进行变量关联的参数估算,但是这一方法却常常基于以年为单位的截面数据,忽视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难以解答时空跨度极大的宏观社会学问题。大数据的出现和发展,为历史社会学者对宏观社会结构进行大历史、大时空的时间序列解读和预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前景。譬如,在“文化组学”(culturomics)的框架之下,学者们利用谷歌八百万册电子化图书语料库进行大数据文本分析,并运用主成分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探讨了社会公众的阶层话语和宏观经济指标在20世纪的因果关系。此外,又用同一方法,提取计算了中国294座城市在英语书籍中出现的热度,在300年的时间跨度上分析了都市治理体制变迁的内生性原因,以动态地测量城市文化的历史演变路径和形成机制。还有学者收集并构建了800余位唐代诗人的年龄、籍贯、科举、官秩等指标,及《全唐诗》、《唐诗别裁集》、《唐诗三百首》所录诗作数量,对“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传统观点进行定量分析,展现了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进行量化历史社会学的研究。
第四,在微观议题上,新一波历史社会学研究更加侧重历史情境的模糊性(ambiguity)与偶变性(contingency)对于行动者的选择与行为的影响。延续第三波学者对于个体能动性的微观探讨,最近的研究则更进一步地追问,在什么样的历史场域中,在什么样的历史转捩点上,行动主体会做出回应性选择(无论是理性的亦或者是非理性的),改变行动,从而深度影响历史的进程。一般而言,当行为者处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必然会面临选择。在这一关键时刻,行为者被置于某一特定位置,并且运用其个体判断力做出决定。当被置于不确定性的政治环境中,就会迫使个体面临随之的选择,选择又反过来产生新的分化、利益和身份认同。
首先,“模糊”是相对于“确定”的一个概念,“模糊”意味着无法预测和不确定。在传统的结构性分析当中,个体的结构性地位是一个相对静态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选择推断是基于内在身份和地位利益,以及人们在正式组织中的社会关系,因此具有稳定性,更能适应对较长历史阶段的分析。但在历史图景风起云涌、政治情势变化迅速的情况下,行动者不再能够明确区分什么是对与错的意义,社会结构模型的解释力度就会减弱。语境的转变要求行动者迅速采取行动,并对外部的变动做出即时反应。对潜在机会和政治威胁的不同的“感知概况”就会使得行动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行动者的决定性决策是深深嵌入在不断变化的地方语境(local context)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语境都处于模糊的状态。那么,模糊不清的地方语境什么时候会出现?有学者就发现,反复无常的外部信号会导致当地政治环境产生混乱,因为它“可能构成一个障碍,阻止[有偏见的]人按照他们的偏见行事,或者相反,当地的互动可以把人们拉进他们以前可能没有计划的活动中,”从而阻碍置身于当地环境中的行动者做出可靠的判断以及一致、冷静的决定。一旦这个过程开始,它便可生成自身的动态性且无法停止。
其次,在模糊且持续变化的情境下,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是一种应对外部冲击的回应性选择。回应性选择是一种认知机制,在此机制下,行动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政治现实进行策略上的重新解释,并做出决策。在新选择之下,新的政治身份以及新的政治利益就会产生,并促使行动者在接踵而至的政治事件中策略性地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些身份不再是静态的,也不再根植于既存的结构属性中。相反,它们是流动的、有弹性的、可塑的,并且可以进行重塑和转化。
再次,还原历史的偶变性,就需要采用序列研究法(sequential method)去追逐事件发展的“过程”(process)。所谓过程,指的是“一系列特定的事件如何随时间进行变化”,是具有显著社会结果和效应的历史过程。历史景观之所以存在,正是存在于相互作用或相互关联的情境中。新一代学者更加看重构建并分析在时间序列上身处历史情境中的行动者不同的策略操纵、变革套路、互动参与(包括跨界互动、组间互动、组内互动)等关键过程和衔接行为。
三、总结与展望
以上从研究方法、理论建构、宏观和微观研究命题四个维度梳理了历史社会学最近十多年大致的发展趋向。实际上,在很多精妙细微的层面,历史社会学也展现出了一些有趣的分支演进。譬如说,历史社会学是否可以引入实验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发展到今日,当下最为流行的研究方法,是基于设计的实验法。在政治学领域,实验法因为可以通过严谨的实验与控制的对照组设计,为研究者提供更为准确的因果效应估值,因此被广泛地应用在测量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政治传播等研究领域。历史社会学因为其学科本身的特殊性,没有办法专门设计出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对照,所以可以尝试借助“历史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 of history)进行研究。所谓“历史自然实验”,是挑选一些受到历史关键事件影响的个体和一些未受影响的个体组成对照样本,再通过测量比较他们受此历史事件所造成的长期冲击——譬如教育水平、政治态度、社会信任等,来进行长时段历史遗产的因果识别。例如有学者就通过自然实验,发现在同一地域范围内,接受过殖民统治的地区相较于未被殖民的地区,其殖民遗产对当地的福利提供和民众收入提高都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历史自然实验面临代表性问题,同时因为涉及到选取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测试,要求研究者同时拥有计量分析技术和辨别历史史料的敏锐感。
素养考查分析:该题考查了频数分布表与频率分布直方图之间的对应关系、平均数、概率等知识,以及纸笔作图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做好这题,要求学生能够根据题目中提供的频数分布表进行数据分析与数学计算.如第三问中,为了求出一年能节省多少水,可先求该家庭使用节水龙头前后50天日用水量的平均数:
总而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新时代中国强国必先强教,高等教育已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地位,对于西藏自治区的发展而言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样重要。同时,高等教育的效用分割性和正的外部效益决定了西藏自治区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拨款和支持。
再譬如说,历史社会学是否可以和艺术、文学相结合?一方面,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嬗变,本身就是源自于社会变迁与都会文化的发展。以19世纪中期的巴黎大改造为例。城市空间改造之前,巴黎在文学领域有浪漫主义诗人与小说家,之后则是严谨、精简而洗练的散文与诗歌。改造之前,整个社会盛行的是乌托邦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后则是现实的管理主义与社会主义。从文化转移与知识生产的角度出发,文学艺术无疑是历史分析的最好载体。另一方面,从文学的文本出发,彼得·盖伊(Peter Gay)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中展现出如何从小说的叙事切入,分析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小说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政治之中如何形成,以及小说作者如何赋之以生命形式。”社会学领域里的最新研究,则利用社会网分析法,剖析了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其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 )中如何通过叙事构造出历史社会学的时间性问题。小说家和历史学家都是在追寻一种“真实性”。
此外,历史社会学如何进行本土化的探索,实现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也值得深思。譬如前文提到的情感治理术,就具有非常鲜明的本土特色。在文化的维度,中国人更加强调情感上的共情共生。这样的共情应用到国家治理上,就将“国家”这样的抽象概念拟人化。诸如“忆苦思甜”、“两忆三查”、“送温暖”等情感性技术应运而生,被策略性地用于唤起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值得我们结合本土经验,进行深入研究。
历史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充分获得了学科内的制度性认受,越来越多的学者回归到历史的视野,透过历史的脉络去洞察社会运行背后不断重复的机制性动因,寻找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与此同时,新一代历史社会学学者也在不断成长,将跨学科视野和复合分析方法带入传统的比较历史分析中。米尔斯在阐释“社会学的想像力”时,曾以属于个人的生命经历(biography)与整个社会的历史过程(history)相对照,强调社会学的课题即在于取两者并观,互相阐发,因为“无论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或者一个社会的历史,若未得一并了解,则两者皆不可解。”于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历史社会学的第四波思潮,将会以更加兼容并包的姿态,去审视历史的存续、绵延、自新和变革,并由此扣问现代性处境下的人心、文化与制度流变。
①C. Wright Mills,TheSociological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45.
②严飞:《历史、社会与历史社会学》,北京:《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8辑。
③Theda Skocpol,VisionandMethodinHistoricalSoci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56.
④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Introduction: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and the Three Wave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eds.,RemakingModernity:Politics,History,andSoci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72.
⑤Craig Calhoun, “The Rise and Domestication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errence J. McDonald, ed.,TheHistoricTurnintheHuman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p. 305-337
2.2 BMI对肝癌术后累计复发率(cumulative recurrence rate, CRR)的影响 388例HCC患者中,消瘦组、体质量正常组与超重肥胖组的中位TTR分别为14、42.5、48个月;208例ICC患者中,消瘦组、体质量正常组与超重肥胖组的中位TTR分别为7、11、12个月。
⑦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北京:《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
⑧Richard Lachmann,WhatisHistoricalSociology, New York: Polity Press, 2013, p. 10.
Chen, Yunsong, Fei Yan and Yi Zhang, “Local Name, Global Fame: The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of Chinese Cites in Modern Times,”UrbanStudies, vol. 54, no. 11 (August 2017), pp. 2652-2668; Chen, Yunsong and Fei Yan,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as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Provinces,”SocialScienceResearch, vol. 76 (August 2018), pp. 23-39.
⑩Charles Tilly,PopularContentioninGreatBritain, 1758-183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95;P.3838.
譬如Mark R. Beissinger,NationalistMobilizationandtheCollapseoftheSoviet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rew Walder and Qinglian Lu, “The Dynamics of Collapse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China in 1967.”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 122, no. 4 (January 2017), pp. 1144-1182; Joel Andreas, “The Structure of Charismatic Mob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Rebellion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vol. 72, no. 3 (June 2007), pp. 434-458.
严飞:《历史、社会与历史社会学》,北京:《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8辑。
Wolfgang Knöbl, “Soci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HistorickáSociologie, vol. 2013, no. 1 (January 2018), p. 9-32.
Ann Swidler,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vol. 51, no. 2 (April 1986), pp. 273-286.
Roger Could,InsurgentIdentities:Class,Community,andProtestinParisFrom1848totheCommun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Karen Barkey,EmpireofDifference:TheOttomansinComparative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Philip Gorski,TheDisciplinaryRevolution:CalvinismandtheRiseoftheStateinEarlyModernEurop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Zhao, Dingxin, “Theorizing the Role of Culture in Social Movements: Illustrated by Protests and Contentions in Modern China,”SocialMovementStudies, vol. 9, no. 1 (January 2010), pp. 33-50.
Elizabeth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TheChinaJournal, vol. 57 (January 2007), pp. 1-22.
Kenneth A Bollen, Barbara Entwisle, and Arthur S. Alderson, “Macro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AnnualReviewofSociology, vol. 19 (August 1993), pp. 321-351.
Damon Mayrl and Nicholas Hoover Wilson, “What Do Historical Sociologists Do All Day? Methodological Architectur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Working Paper, December 2013.
首先,第三波学者试图用社会行动主体的能动性来对抗第二波的结构主义路径,以及组织、社群、群体的理性选择对内在社会结构的冲击。理查德·莱赫曼(Richard Lachmann)就指出,“历史社会学解释应该要区分出人们日常的不重要的行动和改变社会结构的稀有的行动”。⑧当分析单位从宏观体系迈向个体的行动和社会互动时,学者重点关注社会关系如何反映在历史过程中,并生产出边界、身份、社会联系这些期然或非期然的社会结果。特别是身份认同,作为一个明确的文化指标,如何被强化、转换和越界,进而点燃所有历史在场者(包括参与者、表演者、旁观者)的情绪,激发出譬如暴力、革命、社会运动等历史事件的规模性递进和扩展。⑨诚如这一时期的蒂利所言,“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心理或社会整体) 是最基本的现实。”⑩其次,第三波学者对权力的分析不再从一个系统复杂的、宏观的视野出发,而是强调微观分析,深入到细节和进程中去。权力被拆解为不同官僚层级之间的协商、共谋与冲突,以及自下而上视角中基层民众的动员和回应。同时,重新认识社会史的重要价值,并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基础上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演变进行解剖。再次,第三波学者除了聚焦政治、经济结构之外,重新关注情感、性别、身体、话语,乃至符号与剧目式表演这些要素,重点查看文化向度、情感变量是如何影响社会转型、城市发展、历史迭变、组织演化,以及现代性下的家庭与社会公共生活之间的互动。这其中,文化作为一个工具包(tool kit),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按照蒂利的说法,“我将文化……视为社会行动发生的外在框架,将话语视为行动的主要手段。”
这一方面值得推荐的代表性作品,可以参见Wenkai He,PathsTowardtheModernFiscalState:England,Japan,and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Xiaohong Xu, “Belonging Before Believing: Group Ethos and Bloc Recruitment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Communism,”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vol. 78, no. 5 (October 2013), pp. 773-796;Yanfei Sun, “The Rise of Protestantism in Post-Mao China: State and Relig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 122, no. 6 (May 2017), pp. 1664-1725.
从图8仿真结果可以看出:随着信噪比的降低,各种成像方法的成像质量都呈下降趋势,但是前三种方法成像质量下降的尤为明显.总的来看,在不同的信噪比条件下,前三种方法的成像质量均差于方法4以及本文方法,这是由于方法4以及本文方法在重构过程中存在积累过程,提高了低信噪比条件下的重构能力,因而本文方法更有利于低信噪比条件下的信号重构,这也验证了前文的分析结论.图9的图像熵值以及对比度值也验证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在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如何稳健地实施货币政策,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行为反应。正因如此,货币政策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研究成为近年来的热点。
Duncan J. Watts, “Common Sense and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 120, no. 2 (September 2014), pp. 313-351.
在老油田周围深入勘探。这不仅包括已知油田的扩边和发现新的含油气区块,而且包括在老产层上下发现的新产层新产油层系。
Charles Tilly,Stories,Identities,andPoliticalChange,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p. 40.
Edward Shorter and Charles Tilly, “The Shape of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0,”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 vol. 13, no. 1 (January 1971), pp. 60-86.
Andreas Wimmer and Yuval Feinstein,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 to 2001,”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vol. 75, no. 5 (October 2010), pp. 764-790; Xue Li and Alexander Hicks. “World Polity Matters: Another Look at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 to 2001,”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vol. 81, no. 3 (June 2016), pp. 596-607.
Similarly,the results of the in-phase correlation of the early branches can be,respectively,expressed as:
Andrew G. Walder,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SocialScienceHistory, vol. 38, no. 3&4 (January2014), pp. 513-539; Yang Su,CollectiveKillingsinRuralChinaDuringtheCultural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Michael Biggs, “Strikes as Forest Fires: Chicago and Pari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 110, no. 6 (May 2005), pp. 1684-1714.
陈云松、贺光烨、吴塞尔:《因果、时间与空间:走出定量研究的双重危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3期。
对于第一种情况,当功率因数为零的时候,则无功功率Q不存在为空的,因此负载只有吸收有源功率P,图9给出了完整模型的极点图。
Jean-Baptiste Michel, Yuan Kui Shen, Aviva Presser-Aiden, and et 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ulture Using Millions of Digitized Books,”Science, no. 331 (January 2011), pp. 176-182.
Chen, Yunsong and Fei Ya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ublic Concerns about Social Class in Twentieth-century Books,”SocialScienceResearch, vol. 59 (September 2016), pp. 37-51.
⑨Charles Tilly,Identities,Boundaries,andSocialTies,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05.
陈云松、句国栋:《国家不幸诗家幸?唐人诗作与时代际遇关系的量化研究》,北京:《清华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10辑。
因为,就只有这样,广大教师才能真正成为课程改革的主人,而不是始终处于“被运动”的地位,也不会因为“理论优位”这一传统认识而永远处于“受教育或被指导”的位置.这事实上也是国际上的普遍趋势:“就研究工作而言,仅仅在一些年前仍然充满着居高临下这样一种基调,但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已转变成了对于教师的平等性立场这样一种自觉的定位.当前研究者常常强调他们的研究是与教师一起做出的,而不是关于教师的研究,强调走进教室倾听教师并与教师一起思考,而不是告诉教师去做什么,强调支持教师与学习者发展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力图去改变他们.”[23]
Ivan Ermakoff, “The Structure of Contingenc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 121, no. 1 (July 2015), pp. 64-125.
Mohammad Ali Kadivar, “Alliances and Perception Profiles in the Iranian Reform Movement, 1997 to 2005,”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vol. 78, no. 6 (November 2013), pp. 1063-1086.
Diego Gambetta, “Signaling,” in Peter Bearman and Peter Hedström, eds.,TheOxfordHandbookofAnalytical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Stefan Klusemann, “Micro-situational Antecedents of Violent Atrocity,”SociologicalForum, vol. 25, no. 2 (June 2010), pp. 272-295.
Rogers Brubaker and Frederick Cooper, “Beyond Identity,”TheoryandSociety, vol. 29, no. 1 (February 2000), pp. 1-47.
Tulia G. Falleti and James Mahoney, “The Comparative Sequential Method,”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AdvancesinComparative-Historical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pp. 211-239.
“人人成功”是未来素质教育恪守的誓言,而一切素质教育都是从学生学习语言文字开始的,学生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语文教师的熏陶。作为进行素质教育的语文教师,其自身的素质和教育行为对学生的素质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下面笔者仅从教学习惯、教学方式、教学观念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Andrew Bennett and Jeffrey T. Checkel, “Process Tracing: From Philosophical Roots to Best Practices,” in Andrew Bennett and Jeffrey T. Checkel, eds.,ProcessTracing:FromMetaphortoAnalyticToo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38.
Delia Baldassarri and Maria Abascal, “Field Experiments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AnnualReviewofSociology, vol. 43 (July 2017), pp. 41-73.
Benjamin Smith, “Analyzing Natural Experiments: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pproach,” Working Paper, July 2015.
良渚反山遗址12号墓玉钺一套3件,其中钺通长70厘米,上端宽14.4厘米,刃部宽16.8厘米,最厚0.9厘米,孔径0.53厘米。此钺南瓜黄色,有透明感。上部有孔,但很小,显然,不是用来悬挂和捆扎用的,那么,它到底作何用?是装饰,还是别的?不得而知。
马啸:《基于历史的因果识别设计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北京:《公共管理评论》,2018年第2期。
Daniel C. Mattingly, “Colonial Legacies and State Institution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 vol. 50, no. 4 (March 2017), pp. 434-463.
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公路高敦施工工艺逐渐受到业内人士的关注。高敦施工直接影响着公路桥梁建设的安全性,目前我国公路桥梁间中仍多以高敦施工环节为主。我国高速公路工程建设起步较晚,施工单位缺乏专业的施工技术,对先进的施工技术不能有效应用到施工建设中[1]。我国地理环境条件复杂,施工经验不足,使得高敦施工质量难以保障,导致高敦施工技术不能满足高速公路建设需求。
陈映芳、伊沙白等:《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融合》,北京:《读书》,2019年第2期。
[美]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刘森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John F. Padgett, “Faulkner’s Assembly of Memories into History: Narrative Networks in Multiple Time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 124, no. 2 (September 2018), pp. 406-478.
严飞、曾丰又:《历史社会学的本土自觉:革命、国家治理与教育再生产》,南京:《学海》,2018年第3期。
有关“送温暖”的情感治理研究,可参考Yang Jie, “Song Wennuan, ‘Sending Warmth’: Unemployment, New Urban Poverty, and the Affective State in China,”Ethnography, vol. 14, no. 1 (March 2013), pp. 104-125.
参看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上海:《社会》,2015年第1期;应星:《略述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南京:《学海》,2018年第3期;周雪光:《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C. Wright Mills,TheSociological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6.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3-0174-08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与创新研究”(项目号19YJA840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严 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
[责任编辑 陈泽涛]
标签:历史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论文; 思潮论文; 学者论文; 《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与创新研究”(项目号19YJA840019)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