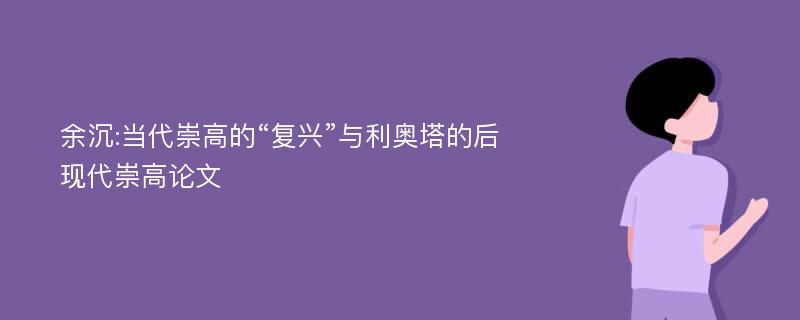
[摘 要]20世纪70年代开始,崇高概念迎来了它在当代的一次“复兴”。当代崇高的复兴也被视为一场后现代崇高的“复兴”,后现代再度激活了崇高概念的理论生命力并重塑了它的思想内核,同样,后现代也借助崇高来实现自我建构、自我表达。利奥塔是这场复兴思潮中最积极的引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他以一种对绝对差异敏感的感性学的形式来重新界定崇高,这种重新界定构成其确立后现代范式的方式之一。通过探讨利奥塔的崇高理论,可以为理解这场复兴思潮中崇高与后现代之间的互动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崇高;“复兴”;后现代;利奥塔
一、当代崇高的“复兴”
崇高作为一个经典的美学范畴,早在公元1世纪就由古希腊演说家郎吉努斯确立,然而直到17、18世纪才获得广泛的关注并由此在浪漫主义中兴极一时。到了19世纪中期,崇高概念在理论界又归于黯哑。待崇高再度活跃于西方思想舞台上,已是一个世纪之后。
20世纪40年代左右崇高概念逐渐在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和色域画派等小范围领域内涌动,诸如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man)、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杰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美国现代绘画的代表性艺术家追求以极其抽象的形式来展现一些宗教意象和情感,企图摆脱传统欧洲艺术那些老旧过时的美学理念与表现形式。他们本身与浪漫派传统和美国绘画传统——美国西部原始、粗犷而又浩瀚的自然景观所激发的崇高风景画有密切关联并从中汲取养分[1],崇高也就成为他们所推崇的绘画理念。然而这在当时形式主义仍占主流的艺术领域内并未即刻产生重要影响。
直到20世纪70年代,崇高概念开始登录欧陆思想理论界,并逐渐从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等领域蔓延开来,渗透于诸多学科或话语实践之中。于是不仅哲学、美学和艺术,还有文学、历史、伦理、宗教神学、语言学和修辞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建筑学,包括诸如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社会批判等领域都开始谈论崇高或借助崇高来进行言说。20世纪晚期的这股崇高“思潮”为当代思想理论与文化生活呈上一场热闹又精彩的盛宴,无论名家大师还是普通学者都被裹挟而入,难以置身于事外。由此西方学界普遍将这股潮流称为一场崇高的“复兴”。在克里斯汀·普利斯(Christine Pries)看来,崇高概念“在20世纪的进程中被遗忘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今天人们很难真正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这却使得崇高的这场复兴格外“令人震惊”[2]。西方理论界对崇高的热情,至今仍有延续。
如今,“崇高”和“美”一样成为一种相当普泛的概念或范畴。也因为如此,当代对崇高的使用和界定呈现出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人们可以给予这一名词以无数的前缀:“美国的”“反(的)”“建筑的”“资本的”“堕落的”“数字化的”“女性主义的”“哥特的”“历史的”“军事的”“否定的”“核能的”“东方的”“技术的”“后现代的”“人种的”[3]等。在英国艺术家和艺术史学家西蒙·莫利(Simon Morley)看来,崇高一词就仿佛一个空洞的容器,可以任人填加任何内容。不过莫利也对当代崇高的多样性用途作出一番整理,在他编纂的《崇高:当代艺术文集》(The Sublime: Documents of Contemporary Art)一书中莫利大致总结出崇高的五种最为广泛的用法,分别与不可呈现之物(主要在艺术领域)、超越的体验、恐怖、怪诞(uncanny)以及意识中的他性状态相关,此外他还指出自然与技术构成这些相关讨论的主要语境。
崇高何以在20世纪中晚期再度赢得理论的好感?实际上,崇高概念的复兴从艺术评论与实践领域开始,自然源于崇高首先是一个美学范畴,它的无形式的特征通过康德的诠释构成对形式美学的一种背离。当现代艺术企图叛出形式美学而在无形式的抽象方式上开辟新的道路,崇高无疑能够为它们提供一种有力支持。某种意义上当代崇高从一开始就承担起“美学终结”以及“美学终结之后”艺术的可能性的使命。
《岭外代答》①本文所引用的《岭外代答》内容为杨武泉先生校注的中华书局2000年版,以下不再赘述。是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1134-1189年)所撰的历史地理文献集成。周去非为永嘉人(今浙江温州),宋孝宗隆兴元年进士,曾经历试桂林尉、钦州州学教授,且在淳熙五年任静江府通判[1]。由于他的任职主要是为了对广西各地方官进行监察管控,而他本人对区域历史地理又颇感兴趣,所以将自己当官的过程同时也变成学术研究的过程。他借助自己在广西搜集资料、调查研究的便利,编撰合计10卷的《岭外代答》。虽然该书存在大段直抄《桂海虞衡志》等问题,但文献价值颇高。甚至有学者认为该书是“广西地方古文献中的压卷之作”[2]。
采集数据的准确和清晰是探测效果良好的关键,其中采集参数的设置尤其重要,主要有时窗设置、采样频率选择、叠加次数确定、道间距确定、采样点设置以及零点搜索等[10],时窗要按照计算测深大于推测深度的原则进行设置,防止遗漏深部反射信号。本次探测具体采集参数设置如表1所示。
无疑,无论是要考察当代崇高话语,还是要考察后现代思想理论,抑或是考察崇高与后现代之间的化合反应,都不可能逃开利奥塔。在20世纪这场崇高的后现代“复兴”中,利奥塔的贡献最引人注目。他不仅是当代欧陆学界最早带动起对崇高的兴趣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为坚定而明确地给予后现代崇高以理论奠基和理论地位的思想家之一。利奥塔对崇高的界定与阐释,不仅为当代先锋艺术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更在思想界(诸如詹姆逊、拉库·拉巴特、朗西埃)以及艺术评论领域中引发了广泛而持续的讨论和影响。因而利奥塔不仅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旗手,他也被人称为20世纪崇高复兴之父[10]。以利奥塔的崇高话语为切入口,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20世纪这场特殊的“复兴”思潮中崇高与后现代之间的互动关联。
除此之外,对于这场崇高的复兴而言,最为关键性的缘由是后现代思想的崛起与风靡。如美国学者恩斯特龙(Timothy H. Engstrom)所指出的,当代对崇高的热情是一个在普遍意义上的从18世纪德国先验主义向20世纪法国后现代主义转变的标记[5]。正是出于后现代对崇高的格外青睐,才再度激活了这一概念的理论生命力。不难看到,后现代领域正构成展演当代崇高最主要的舞台之一,最有影响力的当代崇高话语也大多出自此处。也因为如此,学界称这场崇高话语的热潮为后现代崇高的“复兴”。
二、后现代境遇中的崇高理论
电视记者向全媒体记者的转型,必不可少的是对新技术的及时“刷新”,例如在采编过程中引入“机器人记者”“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为电视新闻记者的创新发展敞开了一扇门。“机器人记者”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支持下,能够对经济、体育、灾害等报道题材中的数据、图表进行量化分析,为电视记者及时发声提供了有效依据。“无人机”的应用则实现了电视新闻素材采集的重大突破,航拍辽阔的视野、快速移动的镜头,使新闻素材的质量获得大幅跃升。
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芭芭拉·弗雷曼(Barbara C. Freeman)则关注现代性进程中崇高在性别认同的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她通过对传统的崇高文本的解读,指出其中主要的崇高理论是依靠性别差异的隐喻才得以描述崇高,同时崇高的结构也是基于并且来源于预先存在的“女性”(feminine)结构。弗雷曼从而对寻求掌控、侵占和殖民的父权式的崇高理论进行批判,并探索一种新的构想与书写崇高的(女性气质的)方式,以及探索这一方式在政治层面的应用[8]。
总体而言,相比于古典崇高,后现代崇高的特质在于:其不拘泥于孤立的美学领域,而是参与到各种思想流派和话语实践的建构之中,经历了一个世俗化、内在化、“物”化① 菲利普·肖(Philip Shaw)指出当代崇高思想有一种共同之处,即将崇高的超越的维度还原为某种(拉康式的)“物”(Thing)的结果,因此这些崇高思想都有某种“唯物主义”的倾向。CF. Philip Shaw. The Sublime[M].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131.的过程,并且转向了生存论维度与张力内涵。生存论维度上的崇高更多的与感官、感受、感性而非理性、道德、精神相关。而崇高的张力内涵,指的是它所寓示的矛盾、分裂或差异。在当代崇高中,分裂性、从超越无限的失败而来的对有限性的痛苦体验或者一种永不停滞的对立的紧张关系取代了古典崇高中超越性和总体化的旨趣。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当代崇高的“后现代性”所在。
后现代与崇高之间的亲切性使得后现代选择了崇高概念,并重塑它的思想内涵,以便借助它进行自我表达。后现代的崇高话语因而呈现出种种不同以往也互不相同的面貌和诉求。诸如,在精神分析领域,根据克雷顿·克劳克特(Clayton Crockett)的介绍,从弗洛伊德和拉康开始,崇高便在创伤、压抑、意识、无意识或意识的他者等机制下获得阐释,它成为对主体与自我的内在障碍或失序的一种诊断。尤其是在拉康的影响下,结构主义符号学也被引入精神分析的崇高之中。一般而言,精神分析的崇高是指基于意识反思的不一致而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和混乱的情感,这一不可思议的情感在意识的意向性之前、之后或之外,使得所有确定的意识反思颤栗不安[7]。克里斯托娃、齐泽克以及托马斯·韦斯凯尔(Thomas Weiskel)等都是这一领域中的代表。
此次问卷主要是在微信平台借助问卷星软件进行发放,以某大学大学学生为采集对象,涵盖各年级和各专业,共收回150份答卷,均为有效答卷。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他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则将后现代崇高与无所不包的、极权主义的社会秩序,即“晚期资本主义”关联起来,其被定性为“歇斯底里的”(hysterical)既恐怖又兴奋的激情。歇斯底里的崇高意味着在后现代文化中,当代社会的“他者”、不可把握的整体不再是硕大无朋的粗野自然,而是技术,“第二自然”、新技术构成了后现代文化的特征之一。可以说,詹明信的后现代崇高呈现出的是一种资本经济与技术的崇高。
此外,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美学、艺术上的后现代(包括后结构主义)对崇高的关注,与它们同样抵制现代性或传统的表象文化、再现思想或视觉至上论有关。在这种抵制上,犹太人的宗教文化展示了它的影响力。或多或少得益于现代犹太人思想家(列维纳斯、弗洛伊德、德里达等)或艺术家(纽曼、罗斯科等)的推动,后现代偏爱从犹太文化中获取资源来重新塑造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在后现代语境中,犹太文明实际上被树立为希腊—西方文明的他者、对抗者和救赎者。犹太文化中对听觉的辩护以及它禁止偶像的这一崇高诫令在后现代对表象主义与视觉中心论的批判和瓦解中,以及在它发展一种听觉文化的过程中得以复现。而无论是犹太人的还是希腊—罗马的崇高,无论是朗吉努斯、伯克、康德还是浪漫主义的崇高,它们在当代理论境遇中的重新激活使吕克·南希如此评论道:崇高是一种时尚,但这种时尚是旧的。不过南希同样指出,即便今日的崇高是“旧”的,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在回到当初我们从之而来的那个崇高[6]。
何以后现代会青睐崇高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后现代与崇高概念之间具有一种亲切性。根据西蒙·莫利的介绍,1970年代开始,法国激进哲学家开始总结60年代政治运动的失败,寻求回应资本主义危机的适切方式,并且追求根本的社会变革。他们希望通过理解人类经验不可控的方面,来谋求某种可能的解放[3]。其结果是其中一些哲学家转向后现代领域。“后现代”集中表达了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状况的剧烈变革,一方面是信心危机或信任危机: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种种恐怖和创伤性经验的侵袭、虚无主义文化和心态的席卷、确定性的丧失、大叙事的解体以及合法性的没落,使人们开始反思启蒙理性的遗产;另一方面,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带给人们一种与过去全然不同的生存体验,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巨大(诸如全球化、摩天大楼、大都市)、快(诸如对速度的追求)、复杂性(诸如精密机器的结构、人体的结构)等冲击着人们既有的感官经验与理解能力。人们的生存状况已被非理性、模糊性、不确定性、不可呈现性、他性、暴力及冲突占据而充斥着震惊、恐怖、焦虑或者兴奋,其已经超出了美的凝神静观,而崇高恰以它所包含的动荡激烈的情绪体验构成对这一生存状况的适切回应。
当后现代重新激活崇高之后,崇高对后现代也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反哺。后现代为崇高提供了一个最为美妙的机遇和舞台,同样,崇高也成为后现代自我建构、自我表达的独特手段,其为后现代作出了一种极富洞察力的注解。威尔·斯诺康柏(Will Slocombe)甚至在他的《虚无主义与崇高的后现代》一书中声称,没有崇高,就没有后现代。一切后现代的产物——无论是后现代艺术,还是后现代理论——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崇高的,否则它们就不成其为后现代的。崇高并非后现代的一个部分、一种成分,而是相反[9]。崇高与后现代的这一同构性在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另外,根据内斯比特(Kate Nesbitt)的分析,20世纪的现象学与美学为崇高在当代的兴起与扩张铺设了理论环境。现象学使人们重新回到一个前概念的生活世界,突显了人对现象的感官的和精神的把握,带来了“身体的革命”,开发了视觉、触觉、嗅觉和听觉等感性接受的方式[4]。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及其后期的美学思想,为现代文化带来一个生存论的向度,其推崇人与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取代自启蒙现代性以来确立的认知与攫夺的关系。因而审美成为对人的生存境况的一种呈现和展示,美学从传统的对形而上及理性秩序的隶属转向对生存体验的感性维度的张开① Neal Oxenhandler还指出语言和文学领域中对情感问题研究兴趣的复兴也推动了崇高话语的回归。CF. Neal Oxenhandler.The Changing Concept of Literary Emotion: A Selective History. New Literary History[J]. 1988: 20(1).。
三、利奥塔的后现代崇高感性学
具体来说,利奥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一种新的崇高美学的积极投身是他对艺术一贯的兴趣延续。不能忘记利奥塔说过他年轻时就梦想成为一个画家,只苦于天份不足而放弃。虽然没有成为艺术家,但从社会政治实践活动退回到书斋之后,利奥塔却开始致力于成为一个美学家和艺术评论家。从古典艺术革新蜕变而来的种种现代艺术形式无疑最为吸引利奥塔的注意,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流派,诸如抽象表现主义、极简主义等,它们对传统的美与再现艺术的反叛,引起了利奥塔的共鸣。对利奥塔而言,这种先锋艺术实践代表着文艺领域中的“后现代”状况。作为对这一状况的回应,利奥塔推出崇高美学来为先锋艺术提供理论基础。在当代美学史的领域内,利奥塔无疑能够凭借他的崇高美学思想赢得一席之地。
1979年利奥塔出版了著名的《后现代状况》一书,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发了理论界有关后现代问题的热议,同时它还被学界视为利奥塔思想的“后现代转折”①比如Bennington等人就提出了这一说法。的标志。在此书之后利奥塔也开始不断地澄清他对“后现代”概念的界定,丰富其内涵。崇高概念正是在利奥塔为后现代辩护和立论的过程中被引入,成为其后现代理论的关键“论据”之一。也正是出于崇高概念的关键性地位,利奥塔在“后现代转折”之后便极力发展和推崇崇高理论,使他的思想很快进入一个“崇高的转折”中。而这一转折,或者如恩斯特龙所言,利奥塔“对崇高的重新定位——从启蒙转向后现代”,就是他将那一普遍而重大的转变——从18世纪德国先验主义向20世纪法国后现代主义的转变概念化的方式之一[5]。换句话说,利奥塔对崇高的重新定位,正是他确立后现代范式的方式之一:他在“美学”一词原初的意义“感性”(aisthesis)之上谈论崇高,将这种感性呈现为一种对绝对差异敏感的感觉力,从而将其树立为在后现代状况下,在没有元叙事、元规则的时代中一切思考、判断和行动的依据与准则,展现了后现代性如何可能在感性层面上获得奠基的问题。
但是,利奥塔提出崇高概念的动因不仅仅来自他的审美兴趣。正如鲁道夫·加谢(Rodolphe Gasché)所指出的那样,利奥塔对崇高的关注来自他对一个哲学问题的回应,这个问题是利奥塔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差异。
实际上,从前期的漂流状态中稳定下来之后,利奥塔思想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向总体性开战,为差异与多元正名。利奥塔是当代法国差异哲学思潮的中坚分子之一,在其思想发生了“后现代转折”之后,“纷争”(differend)就成为利奥塔异质性哲思最为明确且独特的概念表达。正是在建构纷争哲学的过程中,崇高概念被利奥塔引入。也就是说,崇高概念首先在纷争哲学语境中获得重新界定,利奥塔的崇高美学与艺术思想正是以此为起点和基点。当考察崇高介入纷争哲学的环节与利奥塔对崇高美学的表述时,可以看到这二者之间的高度一致性和连续性,即无论在哲学问题还是在美学问题上,崇高都是在面临呈现不可呈现之物的困境时被利奥塔提供出来,构成呈现不可呈现之物的方式。在根本上,崇高是为着利奥塔所提出的拯救思想的荣誉,也即为着为纷争作证的问题而进入他的理论视线,也正是通过纷争哲学的重新铸造,古典的崇高概念才得以成为后现代的时尚。
“人家苹果论斤卖,我论个卖,去年5元一个卖了近万个,今年还没摘就按4元一个全被包了,用诺贝丰的水溶肥种苹果就是不一样!”走进白水县林皋镇吴家尧村诺贝丰水肥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的示范田,果农孙江斌正兴奋地和前来观摩的人们说着自己的感受。
在利奥塔这里,崇高的证明或呈现的方式是一种否定性呈现的方式,其实质就是一种极简的感觉、情感的方式,也就是一种与超出了理性、意识或语言能力的绝对他性相遭遇的方式。借助于崇高理论,利奥塔的最终意图在于培育一种感性形式来应对后现代状况下的感觉经验,这种感性是一种源始的纯粹的接受性的感性,一种易感性(passibility),对纷争或事件敏感,具有被影响而不是去影响的能力,如此才能触及、抵达深埋在各种同一性机制之下的绝对异质性与独一无二性,而又尽可能地避免对差异与特殊产生新的压制。就如斯蒂芬·怀特所指出的,利奥塔试图“把崇高作为能够抵抗社会合理化过程所带来的均质化和常规化的力量的后现代感觉方式的核心”[11]101。
要而言之,经过后现代的纷争哲学的重新刻画之后,利奥塔后现代崇高的基本内涵就在于激活与见证(感觉)差异,向总体性开战。由此,与古典崇高相比,利奥塔的后现代崇高体现出两个特征:第一,崇高不再刻画一种精神的超越性、无限性或统一性,它的矛盾情感刻画的是纷争的不可公度性,是发生的独一无二性,是人的有限性和被动性;第二,崇高并不一定是由诸如康德崇高所表明的那些偶尔遇到的巨大或无形式之物引发,它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细微处,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崇高”[11]107。虽然利奥塔将一些特殊的、不易经常复现的历史(重大)事件,诸如奥斯威辛、法国“五月风暴”等作为后现代崇高的范例,但当利奥塔通过语用学而将不可调和的冲突普遍化、微观化之后,作为对这种冲突的唯一伴随物的崇高情感也就获得了一种普遍化的可能,它能摆脱只有在特定状况下才能与其相遭遇的条件限制。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非物质社会,崇高情感就可能成为对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资本与技术的话语权威的抵抗方式,成为在现代性之内来重写现代性的方式。如此,“对崇高的经验能够而且应该在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层面上被唤起”[11]104。这一唤起的意图在于:“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见证分歧”[11]107。
如前所述,利奥塔建构崇高理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仅仅建构一种后现代的美学理论,他对崇高的重新界定,实质上就是对一种后现代的感性学范式的建构尝试,他的后现代计划①如果将利奥塔中后期思想的基本立场或特征以“后现代”命名,那么这一后现代思想大体上是由三个基本的理论域构成:崇高美学理论(包括文学与艺术等相关方面),后现代知识与社会—政治理论,以及纷争(differend)或事件哲学理论(包括短语语用学方法论)。下文也即是以这三个领域为问题域。也正是立基于这种感性学而获得建构:第一,崇高感性学树立了后现代美学与艺术的原则,其表明现代艺术所力图唤醒的不是美而是崇高情感,它要求的是一种通向纯粹质料的感性能力(passibility)。这种能力成为利奥塔对资本和技术的总体化控制所带来的非人性的批判与抵抗方式,帮助利奥塔建构起另一种非人、一种不可调和的纷争的“证人”。第二,崇高感性学为后现代政治理论提供支持。利奥塔的政治呈现为一种受公正理念约束的政治判断,其要求尊重特殊,采取逐例判断的形式。对此,崇高感性学则以审美反思判断力来提供一种无规则的判断模式,以对理念的呈现能力来为判断提供多元异质的公正理念,对判断加以调节。第三,崇高感性学为事件、发生或纷争哲学奠基。事件或发生(occurrence)哲学是利奥塔以多元、差异为核心的整个后现代思想的哲学基础。围绕着事件或发生概念,利奥塔意图承继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之思的批判,并希望推进海德格尔的追忆被遗忘之物的思想路径,使思想回到一个不同于希腊的全新的“开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崇高情感的本质就是被遗忘的“存在”的基础情绪[12],它是对位于“开端”处的“发生/不发生”之调音的揭示,并使思想走向对“开端”的见证。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美学、政治—伦理领域还是哲学中,见证差异的任务最终将依托于崇高的情感或感性来进行。
利奥塔以后现代的差异哲学重塑了崇高的精神内核,使其得以印证无法被理性、语言或意识捕捉、调和、同化的不可公度性或他性,从而激活了它在后现代状况下的理论生命力。借助于崇高概念,利奥塔也实现了对其后现代理论的一种即使是碎片式的,但也仍具有内在线索性的建构。利奥塔的崇高尤其能够表征一种对后现代精神的皈依,它为后现代的雄心壮志背书。而利奥塔的后现代,体现出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后现代。
四、余论
实际上,利奥塔所描述的后现代性仍然在刻画着时代的特征,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地区冲突、难民问题等持续考验着人们对自由、民主、解放、博爱等现代性大叙事的信心,分裂与矛盾威胁着人们构筑种种共同体的努力。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崇高不仅仅是因为人们经历过奥斯维辛、911或汶川地震这样的“巨大”的灾难,也是因为在被权威、技术与资本控制下看似平静而普通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需要警惕和反思,是否对差异与他性失去了敏感和尊重。而后现代崇高,特别是利奥塔的崇高理论所提供的以感性的方式对差异与他性的证明或呈现模式,就构成我们思考的一个可能角度。
坐标转换矩阵在运动学中是用4×4矩阵来描述两个刚体的空间几何关系。基于几何变动在装配体中的传递方式,本文用坐标转换矩阵来表达零件间特征或要素间的几何关系。两个不同坐标系之间的平移和旋转关系可用转换矩阵T表示[5]:
他在诗中多次表达对隐逸生活的羡慕,但这只是诗人在科举不第的失意之感,漂泊无定的悲苦之情的发泄,并非真的想归隐遁世,马戴是一个积极用世之人,他的主要思想倾向还是入世的。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罗森布卢姆. 现代绘画与北方浪漫主义传统[M]. 刘云卿,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03-228.
[2] Christine Pries. Das Erhabene: Zwischen Grenzerfahrung und Grossenwahn[M]. 转引自Bonnie Mann. Women's Liberation and the Sublime: Feminism, Postmodernism,Enviro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29.
[3] Simon Morley. Starting into the Contemporary Abyss: The Contemporary Sublime[J]. Tate Etc, 2010:20.
[4] Kate Nesbitt. The Sublime and Modern Architecture:Unmasking (An Aesthetic of) Abstraction[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5:26(1).
[5] Timothy H. Engstrom. The Postmodern Sublime?:Philosophical Rehabilitations and Pragmatic Evasions[J].Boundary 2, 1993:20(2).
[6] Jean-François Courtine [et al.]. Of the Sublime: Presence in Question[M]. trans. Jeffrey S. Libret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1.
[7] Clayton Crockett. Interstices of the Sublime: Theology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M]. USA: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Barbara Claire Freeman. The Feminine Sublime: Gender and Excess in Women's Fic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9] Will Slocombe. Nihilism and the Sublime Postmodern: The(Hi)Story of a Difficult Relationship from Romanticism to Postmodernism[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2006:xi-xii.
[10] Kenneth Holmqvist, Jaroslaw Pluciennik. A Short Guide to the Theory of the Sublime[J]. Style, 2002:36(4).
[11] 斯蒂芬·怀特. 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M]. 孙曙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12] 如鲁道夫·加谢(Rodolphe Gasché)认为,利奥塔的崇高是对海德格尔称为西方思想开端处的基本情绪(Grundstimmung)的 重塑。CF. Rodolphe Gasché.The Honor of Thinking: Critique, Theory, Philosophy[M].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7, p. 321.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9)04-0055-06
[收稿日期]2019-02-13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金(J01001985)
[作者简介] 余 沉(1983-),女,安徽铜陵人,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博士。研究方向:后现代理论。
(责任编辑:邓文斌)
标签:崇高论文; 后现代论文; 利奥论文; 美学论文; 理论论文;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金(J01001985)论文; 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