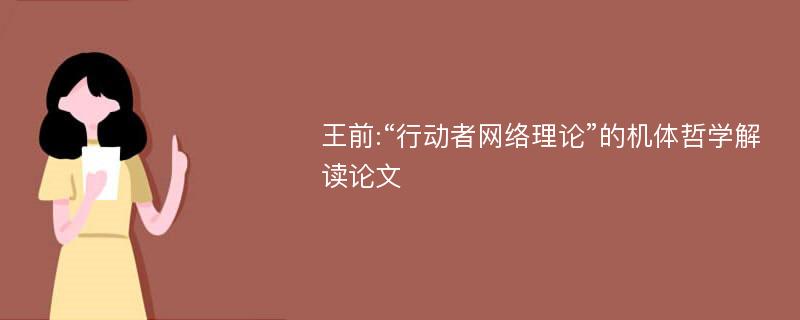
摘要:“行动者”是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其特点在于将人和“非人”的事物都视为具有能动作用的行动者,通过结成网络而相互作用。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非人”的行动者的能动性来自各种类型机体相互作用时“生机”的转移,而“行动者网络”体现了机体的存在方式和相互作用路径。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机体哲学解读,有助于发现“行动者网络”演化的目的性、意向性和“转译”的动力机制,使科学技术的社会建构活动得到更深入的阐释。
关键词: 机体哲学; 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 社会建构
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近些年来在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一理论在消除主客二元对立、身体与心灵对立、语言与事实对立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行动者网络理论总体上看仍然是对人类社会活动某一方面特征的现状及其运行机制的概括,而对于“行动者网络”的存在和运行“何以可能”的问题,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入探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提到的“非人”的行动者的行动能力是从哪里来的?行动者为什么要结成网络来行动?“行动者网络”演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应该如何识别和培育“行动者网络”?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采用机体哲学的视角。这里所说的机体哲学,并非指西方哲学史上莱布尼茨、柏格森、怀特海和汉斯·尤纳斯等人的机体哲学,而是指我们基于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对机体本质特征和规律性的哲学思考。这种机体哲学思考有着与西方机体哲学流派不同的逻辑起点,可以展现出西方机体哲学流派尚未涉及的一些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从这种机体哲学视角出发解读行动者的特性,有助于揭示“行动者网络”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推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为什么“行动者”会有行动能力?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行动者并非不产生任何差异的仅处于被动地位的中介者。行动者由于具有行动能力,会造成网络中各种条件和信息发生转化,这种转化被称之为“转译”(translation)。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行动的人(actor)还是物(object),都是行动者(actant)。换言之,行动者包括在相互结成的网络之中具有能动性的所有的人和“非人”。作为行动者,人本身就有行动能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说“非人”行动者具有和人一样的某种行动能力,这是不寻常的。拉图尔对“非人”行动者的行动能力的阐释,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在拉图尔的早期著作《实验室生活》和《科学在行动》中,他认为行动者的行动能力的实现主要借助了人或科学家的代言。拉图尔借用政治学的“代言”一词,认为在实践中代表“人”发言和代表“物”发言,其实质是一样的。这种代言的正确性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通过“力量的考验”(trial of strength)[1]130。这种力量的考验一方面来自外部,即一些外行人的质疑。为了对付外行人的质疑,科学家必须与“非人”行动者结成紧密联盟,同时还要运用一系列防御手段,包括图标、文本、仪器等,让外行人的质疑失败。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内部——同行的检验。拉图尔甚至认为每个实验室实际上都是“反实验室”,要对付如此多的同行,科学家也可能采取其他策略,如借助更多的“黑箱”、使参与者背叛其代表、塑造新盟友等[1]132-157。
随着研究的深入,拉图尔有了新的提法,他认为“非人”行动者的行动能力的来源,是人将其目的“铭刻”(describe)进了“非人”行动者之中。他在论文《何处去寻暗物质?》(WhereAretheMissingMasses?)和专著《重组社会》(ReassemblingtheSocial)中进一步探讨了这种行动能力的来源问题。拉图尔曾引用司机减速的案例加以说明。有两个司机同时都减速。一个司机是因为看到了限速的黄色标识而减速,而另一个司机是为了保护他的汽车悬架不被“限速带”破坏也减速。第一个司机减速是基于道德、信号、黄色标识的原因,而第二个司机所产生的服从来自被精心设计好的混凝土带。他们都服从了某种需要:第一个驾驶员服从于利他主义——保护他人的安全,而第二个驾驶员则是服从于自私的心理——为了保护车的悬架。在这里,不能说第一种方式是社会的、道德的,而第二种方式就是物质的、客观的。“道德和悬架这两者并不都是社会的,但是一定都是通过道路设计师的特定工作使它们联合在了一起。”[2]77也就是说人通过实践活动,将“脚本”写入了黄色的减速标识和限速带之中,它们“转译”了司机的行为。
拉图尔对“非人”行动者的行动能力的探讨是深刻的,但是在揭示这种行动能力的来源方面存在不足之处。人类将目的“铭刻”或将“脚本”写入“非人”行动者之中,这种做法可能只是改变了“非人”行动者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但是从逻辑上推导不出这样做一定会使“非人”行动者由此具备行动能力,因为行动能力需要源于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动力。而且“非人”行动者必须首先具备行动能力,这样将目的“铭刻”或将“脚本”写入才会有意义、有效果。换言之,“非人”行动者应该和行动的人一样,具有某种能动性或者说“活性”,才能够实施行动,体现人的目的和意向。借用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术语,“非人”行动者应该具有某种“前结构”或者“前功能”,一旦人们将目的“铭刻”或将“脚本”写入“非人”行动者,它们就会行动起来。行动者网络理论并没有明确揭示“非人”行动者这种本身的内在机制,没有指明行动者为什么会有“行动能力”。而基于中国文化思想资源的机体哲学,为解读这方面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新思路。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重要价值之一,是指出“行动者网络”由人和“非人”行动者共同构成。从基于中国文化思想资源的机体哲学角度看,“行动者网络”是人的生命机体和人工机体、社会机体、精神机体这四种类型机体相互连接的复杂系统。很多时候,“非人”行动者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特定关系的必要中介。比如,学校宿舍管理人员和住宿学生之间除了直接的互动产生关系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联系渠道,那就是作为“非人”行动者的钥匙或者门卡,它们建立了宿舍管理网络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某种特殊的稳定关系。从四种类型机体相互连接的角度理解“行动者网络”的内在结构,可以使人和“非人”行动者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得以进一步细化,展现出彼此更为复杂的作用方式。
具体说来,当人们建构各种人工机体、社会机体、精神机体这些非生命体的机体时,已经将“生机”赋予这些机体,使之在各类机体相互作用时能够呈现行动能力。这种行动能力不同于一般的功能,因为其具有“能够通过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收益”的机制,一旦运行起来就会体现出这种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非人”的事物才可以称之为行动者,它们才会体现“转译”的功能。在拉图尔提出的“限速”案例中,黄色标识和“限速带”能够迫使司机减速,这只是它的功能,而通过限速来保障行人的安全,具有“道德物化”的特点,则体现了黄色标识和“限速带”的行动能力,这种行动能力正是其“生机”的体现,具有“能够通过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收益”的机制。人们感到黄色标识和“限速带”似乎具有某种“活性”,这显然是人类专门赋予的。将目的“铭刻”或将“脚本”写入的过程,必须考虑到这种“生机”如何发挥作用,才能够将人的目的、功能和意向转移到“非人”的行动者之中。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唐·伊德提出人与技术人工物之间意向关系的四种形式,分别是“具身关系”“诠释关系”“他异关系”和“背景关系”[3]。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拉图尔和伊德的思想,提出了“技术中介论”,认为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着“中介调节”(mediation)的作用。他们提到的技术人工物的“意向关系”和“中介调节”作用,实际上都要以技术人工物具有“生机”为前提,因为已经失去“生机”的报废的人工物不可能再具备“意向关系”和“中介调节”作用。比如,透镜可以放大物象,这是它的功能;通过放大物象可以提高人类的视觉能力和认知功能,这是它的“行动能力”,即它作为技术中介物介入了人类的感知活动。这种“行动能力”在设计、制作和使用透镜的时候就已经“嵌入”其中了,这就是透镜具有“生机”的体现。这种理解也可以阐释透镜演化的动力。从最初的眼镜、放大镜、显微镜到后来的电子显微镜、遥感装置,等等,都体现了不断追求通过较小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收益的努力,因而结构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强大,“生机”也越来越旺盛,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未能充分予以考虑的。
基于中国文化思想资源的机体哲学思考以“生机”范畴作为其逻辑起点,将是否具有“生机”作为区分机体与非机体的根本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对“生机”的深刻理解。“生机”是“生”与“机”的结合。“生”意味着自然呈现的新陈代谢态势,而“机”表示以较小投入取得显著收益的活动过程,如机遇、机关、商机等等。所谓“生机”,指的是一种能够通过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收益的生长机制,如动植物的生长、机器的生产、社会生活的效益、精神成果的生命力,等等。以“生机”作为机体的本质特征,意味着只要在事物的相互作用中体现了“生机”的这种机制,无论这些事物是生命体还是非生命体,都可以认为这些事物是“机体”,它们之间的联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有机联系”。如果某种机体逐渐失去“生机”,入不敷出,每况愈下,就会向非机体转化,走向消亡。死去的动植物、报废的机器、已经解体的社会组织和完全失去存在价值的精神成果就不再是“机体”了,因为它们失去了通过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收益的生长机制。这样来理解机体的本质特征,不仅符合人们使用“机体”这一范畴的语境,而且可以避免莱布尼茨、柏格森、怀特海等人将一切事物都看做机体,实际上取消机体与非机体区别的“泛机体”倾向(怀特海等人用“关系”“过程”“生成”等范畴来定义“机体”,而这些特征其实是机体与非机体事物共有的),也有助于发现技术人工物、社会组织、观念体系等非生命体所具有的与生命体共同的机体特征(避免将“机体”仅仅局限于生命体)。因为技术人工物、社会组织、观念体系等非生命体的机体特征,正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将自身的生命机体特征赋予这些事物的结果。技术人工物、社会组织、观念体系等非生命体相应地可称之为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它们有不同形态的“生机”,而它们的“生机”其实就是拉图尔所说的“非人”行动者的行动能力。
概言之,行动者(特别是“非人”行动者)之所以会有行动能力,是因为行动者都有各自的“生机”,而“非人”行动者的“生机”是人类赋予的,它驱动着非人行动者的“行动”。当然,这种“行动能力”需要在网络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涉及下一个问题:行动者为什么要结成网络来行动?
二、行动者为什么要结成网络来行动?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拉图尔是在工具意义上使用“网络”一词的,但这并非是指实际意义上的实体性网络。“网络是一个概念,而并非外在的一种事物。它是有助于描述某种事物的一种工具,而非正在被描述的东西。”[2]131我国学者李雪垠和刘鹏指出拉图尔的“网络”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层含义,在本体论上完成了从“空间之网”到“时间之网”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他实现了“从混合本体论到行动中的关系本体论”的转变[4]。拉图尔所说的网络是行动者的行动所形成的动态网络,所有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变化成为一切变化的根源,这是一种关系实在论的观点。所谓关系实在论,“是主张关系即实在,实在即关系,关系先于关系者,关系者和关系可随透视方式而相互转化的一种哲学观点和理论”[5]。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拉图尔是一个关系主义者[6]。那么,为什么行动者必须要结成网络来行动呢?拉图尔虽然没有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按照刘鹏的观点,拉图尔之所以强调行动者要依靠网络是因为人和物都是对彼此开放的,他们的属性并不是被隔离地分为“主体性”或“客体性”,而是两者在共同的集体(collective)中流通地分享着彼此的属性,从而都具有“集体属性”[7]。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拉图尔要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中阐述具有集体属性的“拟客体/拟主体”的概念,提倡从中间王国出发来解释两极,进而提出他的“反哥白尼革命”[8] 89-90。拉图尔对“为什么行动者必须结成网络来行动”的回答,强调行动者“属性”的形成需要网络,这种回答虽有积极意义,但缺乏从“关系”角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近年来,人行昆明中支持续运用政策工具积极支持小微企业破解“融资难”问题。截至6月末,云南省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达5034.39亿元,比年初新增135.27亿元,同比增长14.27%,快于同期大中型企业贷款增速8.84个百分点,超过同期各项贷款增速5.58个百分点,困扰小微企业最关键、最核心问题的“融资难”问题得到缓解。
从基于中国文化思想资源的机体哲学角度看, 行动者之所以要结成网络, 是因为行动者只有在网络关系中才能够保持其特定属性, 具备其行动能力,发挥其应有作用。 网络不仅将行动者联系在一起, 而且提供了行动者相互作用的途径和方式, 使行动者的“生机”得以彰显。 在这个意义上, 行动者的网络具有类似人的生理系统的功能。
新媒体和地方传统媒体分别代表了不同视角的文化,两者之间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与人们想象的恰恰相反,它们两者之间往往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才能真正显示出它们的重要作用,发挥其最大的价值。虽然中国地方传统媒体展现出衰败的迹象,新媒体展现出一片光明的前途,但是社会在某些领域的话语权处于真空状态,为了填补这个真空需要地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共同努力。
“行动者网络”中的各种关系是行动者得以存在的前提。某一个行动者的存在,不仅要体现其能够将“生机”传递给其他行动者,还要依赖于其他的行动者给他(或它)提供“生机”,保证其能够持续存在下去。“行动者网络”中的各种关系就是传递“生机”的联系通道,而各种联系通道交织在一起必然构成网络。这里面有些联系通道是显性的,容易进入人们的视域;有些则是隐蔽的,往往被人们忽视。如进入巴斯德实验室,人们往往容易注意直接从事实验的研究人员与作为“新客体”的疫苗存在紧密联系,但是为整个实验室筹集经费的人员却容易被忽略。拉图尔注意到了这种隐性联系,提出了“谁在从事科学”的问题,展示了他们共同结成了一个网络。现象学的突出贡献之一便是揭示这种“不在场”的隐性联系,让不在场的事物“出场”,进而展示决定事物存在的相关网络。中国传统思维强调“位”决定了个别事物的存在方式、性质、状态和发展趋势,如《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是强调“行动者网络”中的各种关系对于行动者得以存在和传递“生机”的意义。
然而拉图尔对“行动者网络”的动力机制解释是有缺陷的。 第一,“转译”忽视了人对“非人”行动者在意向和责任上的转移。这一点维贝克在他的“道德物化”思想体系中已经作出了说明[11]。他将拉图尔和唐·伊德进行比较,认为前者重视对人行动上的影响,后者重视对人意向性上的影响。 第二,容易遭受被视为“万物有灵论”(hylozoism)的批评。“转译”虽然成功地将“非人”也纳入“行动者网络”之中,并对其发挥的作用作出了说明,但是有学者认为它取消了人与物之间的差别,“非人”行动者不可能具有能动性[12]。西蒙·沙弗尔(Schaffer Simon)就认为根据广义对称性原则, 该理论并没有成功地解释人如何有效地利用“非人”行动者取得成功, 除非退回到“万物有灵论”。 在他看来,在拉图尔解释巴斯德的成功案例中, 要说明作为“非人”的微生物“热心”地服务于巴斯德的原因,只能是“万物有灵论”, 因为拉图尔在很多论证中并没有回答好这一问题, 忽略了很多巴斯德的竞争对手失败的论证[13]。在沙弗尔的理解中, 能动性是一种主动做事情的能力, 拉图尔的“非人”行动者要“主动”帮助巴斯德或其他人做事情,除非具备“万物有灵”这个前提。
“非人”行动者的“生机”演化有积蓄和展开两个阶段。在积蓄阶段,人将自身的机体特性开始赋予“非人”的机体,主要体现为功能的转移。“非人”行动者与人之间的结构还比较松散,相互制约、相互规定的关系还没有明确体现出来。“非人”行动者对人的影响更多的是功能上的依赖,尚未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精神或者身体的一部分。以手机发展史为例,在手机最初处于模拟信号阶段即1G时代,“大哥大”是这个时代的标志。这个阶段手机依赖于人的操作、控制和设计,而人主要依赖手机的通话功能来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个阶段人的功能部分转移到手机中比较多,而意向性和责任的转移比较少。此时手机功能相当于卡普和马克思所说的“器官投影”和“器官延长”阶段,只是作为人的功能的延长工具而非必不可少的部分。用伊德的话语来说,这时候人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他异关系”和“具身关系”。在“生机”展开阶段,人不仅将功能赋予“非人”行动者,也将意向、责任等都赋予了“非人”行动者。这个阶段“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在人和“非人”行动者共同组成的网络中开始显现出来,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即人工机体开始渗透到生命机体中,或者成为精神上必不可少的物件,或者植入体内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这时伊德所说的“诠释关系”和“背景关系”也开始出现,尤其是智能技术广泛地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层面,并力图用智能机器的优势来取代人的部分智能活动。智能手机不仅实现了彩屏、易携带等外在功能,人的意向和责任也被更多地“嵌入”其中,有效地实现了人机互动。由此可见,“行动者网络”演化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将功能、意向和责任不断转移到“非人”行动者之中,使之具有在层次上不断提升的“生机”,由此带来各种“非人”行动者的行动能力的不断增强。
2007年,医院将建于1892年的巴洛克式建筑旧址改造为医院历史纪念馆,成为医院文化的汇聚地,后被定为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文化交流基地。
三、“行动者网络”演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拉图尔认为“行动者网络”中的内在动力机制就是“转译”。转译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塞尔(Michel Serres)提出,后来法国哲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建立了初步的动态模型,再被拉图尔进一步拓展[9]。拉图尔认为转译是将利益与研究纲领的观念融合为一,它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转译”意味偏移、背叛、模棱两可。人们从各种利益(interest)或语言游戏间的不对等关系出发进行表达,最终目的是使两个主张对等起来。贺建芹提出“转译”可以被理解为“行动者不断地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利益通过自己的语言翻译和转换出来的过程”,就是基于对这个层次的理解[10]。第二,“转译”这字眼也带有策略意味。它说明了每个行动者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建立据点等,都必须透过对手的立场,帮助他巩固其自身的利益。这个层次上的转译被拉图尔称为“英雄的历史”——虽然每个加盟的行动者都帮助过最初理论或者“黑箱”的创始人,但人们往往将功劳只归功于创始人。第三,可以在语言学上理解这个字眼,就是说,所有的语言游戏都可以被翻译成同一版本,都可以被代之为“不论你愿望如何,这就是你真正想说的话”。这个层次即是一种被代言人代言的过程,如科学家代表“新客体”阐述其原理。
白雪终于将衣鞋摊放在石屏上,缓和过来的柳含烟起身又摇起一桶水从头到脚淋下。她用浴巾将身上的水渍拭干把赤裸的身体放进宽大的宝蓝色真丝罩袍里,系上腰带。她微微点了一下头,仿佛满意真丝罩袍恰到好处掩住她一双莲足,也似乎是从罩袍的样式和颜色意识到是在涤尘居门前沉思的萧飞羽赠予。
浙江省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孤儿和困境儿童福利事业的意见》中规定:孤儿们长大后,可优先安排到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就业。若自谋职业,能享受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免费职业介绍、职业介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对有劳动能力且处于失业状态的,要将其列入城镇“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和农村低保家庭劳动力就业扶持范围。
价值的含义从哲学的角度讲,一般认为是指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和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效益关系。“青年价值观就是青年对其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能否满足自身需要进行认识、评价、决定取舍时所持的基本观点。”[2]青年价值观的内容由价值目标、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构成。
“转译”概念之所以会出现意向性方面的缺失,是因为这一概念是从行动者之间利益的角度开始阐发的,无论是一方行动者用自己的话阐释另一方行动者的话,还是“黑箱”创始人对加盟者的控制,其核心点都着眼在具体利益上。巴斯德派学者的利益在于推广其科研成果获得社会认可,卫生专家的利益在于解决公众难题维护他们集体的利益,军医的兴趣则是维护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等。当“转译”在描述人与“非人”行动者互动时,注重“非人”行动者被早已“嵌入”的脚本对人利益的影响,其关注点必然落在行动上而非意向性上。伊德虽然注意到了技术对人的意向性影响作用,但对“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来源问题并没有明确回答。前面提到,从基于中国文化思想资源的机体哲学角度看,“非人”行动者之所以会有行动能力,是因为它具有人类赋予的“生机”,而这种“生机”驱动着非人行动者的“行动”。
沙沟左岸区域存在两处滑坡:沙坡滑坡和马桑弯滑坡,是区内主要泥石流物源。在2016年6月特大暴雨期间,出现多处局部滑塌。两处滑坡坡方量较大,占总储量的40%,如失稳下滑,将对淤积前缘沙沟,对沟口众多居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威胁极大。
“行动者网络”中的某些关系具有动态稳定性。即使行动者自身发生某种改变,他(或它)们之间的联系通道却可以保持不变,这是“行动者网络”能够抵御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干扰保持稳定属性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这种性质也是需要通过网络得以保持的。比如实验室中领军人物提出的重大研究方向改变会影响这个实验室前途和命运,但是实验室中行动者的某些关系(人员结构、仪器设备、规章制度等)却有着相对稳定性,并不会随着行动者研究方向的改变而改变。被拉图尔称为“黑箱”的机器或理论在不同地方都会呈现出相同的效果,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来,这是因为尽管使用“黑箱”的行动者会有所不同,但是只要“凝固”在“黑箱”中的操作程序、实验室环境依然按照原有的关系进行复制,那么依旧可能出现普适性。“现代人仅仅是通过招募(enlist)某一特定类型的非人类而创造了长网络(longer network)。网络的延展过程在其早期阶段就已经被打破,因为它可能会威胁到领地(territory)的维持。但是通过增加半客半主的综合体——我们称之为机器和事实——的数量,集体改变了其地形学。”[8]133换言之,最初在实验室形成的局部网络,通过在其他地方复制“黑箱”及维持“黑箱”的关系环境,使得这种局部网络变成了扩展到了实验室之外的“长网络”。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长网络依然是网络,因为它依然具有和原先的局部网络同样的关系特征,在关系网络覆盖的范围之外这种适应性是没有的,例如火车能够快捷地到达铁轨铺设的领域,但面对铁轨之外的领域则无能为力。
拉图尔认为:“能动性总是体现在对做某事的描述中,即对某事态制造差异,通过C的考验将A变成B。”[2]52-53从基于中国文化思想资源的机体哲学角度看,“非人”行动者之所以能够迫使人按照其被嵌入的“脚本”行动,正是因为“非人”行动者蕴含“生机”,而这种“生机”一定要体现为对行动者关系的定向改变,使之实现人的目的和愿望。“转译”概念强调了人与“非人”行动者在能动性上的平等,却并未强调“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来自人的赋予。这种赋予不是“万物有灵论”,而是各类机体之间“生机”转移机制的体现。
四、 应该如何识别“行动者网络”?
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中,没有社会与自然的对立,也没有行动者之间的对立,有的只是他(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要识别这种网络,必须跟随行动者,尤其要重点考察正在形成的网络,而非已经形成的网络,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行动中的科学,而不是已经形成的科学或技术”[1]418。为了叙述这种网络的形成和相互关系,拉图尔还强调必须用次语言(infra-language))即行动者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行动,而非用社会科学的元语言(meta-language)去还原行动者的语言[2]49。但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角度看,仅仅做到这些还是不够的。在识别“行动者网络”上,还应当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注重对“行动者网络”内部各种关系的考察;另一方面,要注重对“行动者网络”蕴含的“生机”考察,揭示“行动者网络”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动态的关系网络。运用逻辑分析来认识这一带有关系特征的网络,相当于给动态的关系过程拍出一幅幅静止而清晰的“定格”照片。逻辑分析的优点在于便于精细分析,但缺点在于忽略动态的关系特征。在《科学在行动》中,拉图尔讨论了质疑“黑箱”的困难[1]105-132。质疑“黑箱”如科学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黑箱”并非简单的知识形成的网络,它是由各种行动者加入的网络,要质疑“黑箱”实际上要质疑一个庞大的行动者构成的联盟。首先,质疑“黑箱”的人遇到的是文本,它在外行人看来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引用了很多其他文献——从简单的语句到更复杂的图标、记录等,这会使得一般的外行人望而生畏。其次,即使质疑者对文本也具有一定基础,那么他还要面对说明这些数据的科学家。最后,即使质疑者能够直接驳倒科学家,马上迎接他的则是实验室。在实验室中,质疑的人将要面对一堆复杂的科学仪器以及仪器产生出来的数据和新客体,这大大加深了质疑的难度。所以拉图尔得出的结论是:之所以质疑文本如此困难,并非仅仅是科学素养的问题,还在于编写的论文中运用了修辞的方法,在科学事实建构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这完全不同于普通人的认识。因此,识别“行动者网络”必须考虑“黑箱”中各类“机体”的动态关系,分析在实验室里面科研人员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各种实验仪器的功能和承载的意向性、科研组织的社会特性、科学知识形态和研究范式的作用途径,以及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将实验室中的各种人和“非人”行动者的动态关系呈现出来。人们比较关注各种人之间显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将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的隐性关系揭示出来,才能完成识别“行动者网络”的任务。
“行动者网络”都有其“生机”,整个网络也是一个传递“生机”的网络,这是识别“行动者网络”的更高层次的要求。这就需要了解“行动者网络”中每个行动者的“生机”状态,行动者之间传递“生机”的状态,以及整个“行动者网络”的“生机”状态。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如果“行动者网络”中加盟的新的行动者越来越少,那就意味着该网络的扩展已经接近于它的顶点,发展空间日益缩小,其“生机”也就趋向衰落了。如闻名一时的日本柯达胶卷公司,虽然在早期垄断了世界胶卷的大部分市场份额,但是它后期在数码技术出现时,却反其道行之,依然延续旧有的胶卷技术追求短期的利益,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结果导致其投入产出比越来越少,丧失了“生机”,最后整个柯达企业走向了破产。从基于中国文化思想资源的机体哲学角度看,柯达公司阻止了数码技术这一“新客体”的加入,导致柯达公司的网络扩展已经达到了它的临界值,其“生机”趋于衰落。其他公司虽然刚开始“行动者网络”规模较小,但是由于数码技术的加入,使得更多围绕着这一新客体的盟友不断加入,“生机”趋于旺盛。在这些行动者的共同努力下,其网络最终扩展的规模超过了柯达公司。
识别“行动者网络”的“生机”状态,要考虑机能要素、时效要素、自调节要素和创新要素[14]。机能要素指的是机体的“功能”或“效能”,即“投入产出比”;时效要素指的是机体演化从萌芽出现到后果完全显现之间的时间距离;自调节要素指的是机体演化过程中应对内部和外部各种变化自动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创新要素指的是机体在演化过程中产生新事物的能力。不同的“行动者网络”中每个行动者的这些要素都不尽相同,然而正是这些差异和由此产生的互动促进了整个“行动者网络”的演化。
从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视角考察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展现了这一理论的更深刻的价值和不足之处,这对于进一步发展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十分必要的,由此提出的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布鲁诺·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刘文旋,郑开,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5.
[2]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唐·伊德. 技术与生活世界: 从伊甸园到尘世[M].韩连庆,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72-117.
[4] 李雪垠,刘鹏. 从空间之网到时间之网——拉图尔本体论思想的内在转变[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25(7):52.
[5] 罗嘉昌. 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体[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3.
[6] 刘世风. 相对主义与实在论之间:拉图尔的关系主义分析[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2,34(1):21.
[7] 刘鹏. 现代性的本体论审视——拉图尔“非现代性”哲学的理论架构[J]. 南京社会科学, 2014(6):47-48.
[8] 布鲁诺·拉图尔. 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M]. 刘鹏,安涅思,译.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9] Callon M. Struggles and Negotiations to Define What Is Problematic and What Is Not: The Socio-logics of Translation[M]∥Knorr K D, Krohn R, Whitley R. The Social Proces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Dordrecht: Springer, 1980:197-220.
[10] 布鲁诺·拉图尔. 巴斯德的实验室——细菌的战争与和平[M]. 伍启鸿,陈荣泰,译. 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16:42.
[11] 张卫,王前. 道德可以被物化吗?——维贝克“道德物化”思想评介[J]. 哲学动态, 2013(3):72.
[12] 安德鲁·皮克林. 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M]. 邢冬梅,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222.
[13] Schaffer S,Latour B.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Bruno Latour[J]. Studies in History &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1,22(1):175-192.
[14] 王前. 生机的意蕴——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219-223.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Organism
WANGQian,CHENJia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Actor” is the core concept of Bruno Latour’s actor-network theory(AN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regarding both human and non-human things as active actors that can interact by forming a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organism, the agency of non-human actors comes from the transfer of vitality in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organism, whereas the actor-network embodies the way of existence and the path of interaction of the organism. 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helps to find the purpose and intention of actor-network evolution, and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ranslation, so tha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be further explained.
Keywords: philosophy of organism; actor-network theory; actor; social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N 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9)01-0001-07
doi: 10.15936/ j.cnki.1008-3758.2019.01.001
收稿日期:2018-09-20
作者简介:
王 前(1950- ),男,辽宁沈阳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研究;
陈 佳(1984- ),男,湖南常德人,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李新根)
标签:机体论文; 网络论文; 生机论文; 关系论文; 拉图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流派及其研究论文;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