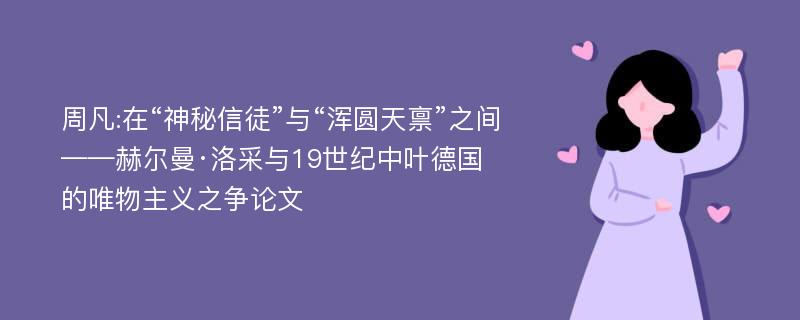
哲学研究
·洛采哲学研究专题·
编者按:
鲁道夫·赫尔曼·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1817—1881) 最早被中国学人所知是通过郭大力先生译早期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朗格的《唯物论史》,在论述19世纪中叶德国唯物主义争论及德国心理学中的赫尔巴特派这两个地方,洛采均被提及。只不过在这本出版于1936年的译著中,洛采被译为陆宰。后来,唐钺先生在1963年出版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选译本中仍沿用了陆宰这一译名。19年后,唐钺先生在其专著《心理学史大纲》(1982)第十章写陆宰的一节中,第一次在陆宰这一译名后的括号里附加了“洛采”这一新译名,但在行文中,仍然使用陆宰之名。尽管“洛采”这一新名在唐钺先生的这本专著中仅仅在括号里出现了一次,但它却深深铭刻在中国翻译史和学术史之中。20世纪90年代,赵修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中、周凡在硕士论文《价值与人的生存》、梁宝珊在硕士论文《久被遗忘的洛采:对洛采哲学思想及其与现象学之关系初探》中正式使用洛采这一译名并把洛采作为19世纪中后期重要哲学家来看待。进入21世纪后,洛采受关注的程度有所提高,对他的思想的研究也渐次展开,然而,由于洛采著作的中文翻译的缺失,长期以来国内对洛采的研究并没有大的突破。在2017 年 5 月洛采诞辰 200 周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周凡教授组织了“洛采与价值哲学”研讨会。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洛采思想专题研讨会,以这次会议为契机,第一次形成了洛采译介和研究团队。我们从相关研究成果中选出一篇考察洛采介入19世纪中叶德国唯物主义争论的论文和一篇论述洛采对詹姆士影响的译文,以回应并纪念洛采一开始传入中国学术界时的两个原初语境:唯物论史与詹姆士的心理学。也希望通过这个栏目,进一步激发人们对洛采思想的关注与兴趣。
[摘 要]从1854年9月18日正式开始,德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唯物主义的争论。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卷入其中,围绕争论的问题纷纷发表演讲、论文和著作。洛采虽然不愿意介入争论,但是最终还是被争论双方的主辩手拖入了这场持续几年的争论中。为了回应科学唯物主义者的指责,洛采发表了四篇评论文章,并出版了著名的《论辨集》。在这些文本中,洛采对科学唯物主义基于感觉论的狭隘经验主义提出了批评,借助于这种批评,洛采表达了自己对唯物主义的独特理解。在争论中,洛采自始至终站在中间立场上而不彻底倒向任何一方,他既不主张用观念论取代唯物主义,也不同意用唯物主义吞并观念论。作为一位机敏的科学家,同时又作为一位观念论哲学家,洛采最大的希望是科学与形而上学能够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科学和形而上学就如肉体与灵魂一样,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
[关键词]洛采;科学唯物主义;观念论;争论;形而上学
19世纪50年代,德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唯物主义的大争论,朗格在《唯物论史》中称“这一争论的情形堪比宗教改革时代的宗教大辩论”[1]264-265。许多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新闻记者以及众多学者纷纷亮相发声,或主动挑起或愤然应对或被卷挟其中,论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愈演愈烈。丹皮尔在《科学史》中说,发生在德国的这场唯物主义争论甚至“普及到广大的阶层中去,这在其它国家是办不到的”[2]410。 由于论战持续时间长、争鸣范围大、涉及问题多、影响程度深,它被称为“那个时代最大的思想辩论之一”[3]237。 在这个著名的争论中,唯物主义一方的主辩手是被马克思戏称为“浑圆天禀”的博物学家卡尔·福格特先生(Karl Vogt,1817—1895),唯心主义一方的主辩手是被卡尔·福格特戏称为“神秘信徒”的哥廷根大学比较生理学和动物学教授、生理学研究所所长鲁道夫·瓦格纳(Rudolph Wagner,1805—1864)。而站在“神秘信徒”与“浑圆天禀”之间的是一位生性腼腆、低调谦逊且向来不愿与人争论的哲学教授,但是争论双方的主辩手都紧紧抓住这个老实人不放,都拿他来说事儿,便把这个人拖入了争论的漩涡。这个被拉下水的无辜者就是当时已颇有声望、后来更是成为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的赫尔曼·洛采(Hermann Lotze,1817—1881)。弗里德里克·拜塞尔在《德国晚期观念论》一书说:“这场辩论,无论是好是坏,都使洛采在德国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3]237被卷入到这场争论中的洛采不得不针对争论双方对自己的误解而澄清自己的真实观点和态度,正是在这种自我辩护中,洛采清晰地展示出他对自然科学的机械论观点和对形而上学的观念论观点的一种折中与调和,而这种折中与调和在很大程度上映照出洛采哲学的总体取向和基本特征:它不完全拒绝唯物论,同时又为观念论留下一片宽阔的高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说他要做的就是限制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而洛采要做的无非限制自然科学以便为形而上学预留一席之地,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试图把实在论与观念论接合起来从而造就一种类似于沿垂直方向带状分布的“多元一带”式的独特思想格局。
天上高名世上身,垂纶何不驾蒲轮。一朝卿相俱前席,千古篇章冠后人。稽岭不归空挂梦,吴宫相值欲沾巾。吾王若致升平化,可独成周只渭滨。(《全唐诗》[8],后文所列诗歌均引自此书)
一、科学主义的兴起
洛采生活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自然科学获得空前的繁荣与发展。洛采的学生约翰·梅尔茨在其名著《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中说:“人们公认,与其他时代相比,科学精神是本世纪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相当多的人可能确实倾向于把科学看作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因此,19世纪可以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世纪,就像上个世纪称为哲学的世纪、16世纪称为宗教改革的世纪、15世纪称为文艺复兴的世纪一样。”[4]89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科学精神在法国得到哺育,“长大成熟并充满活力”[4]156,很快,它就开始向欧洲其他国家转移、拓展。到19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在许多原来未曾涉足的崭新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研成果——比如被恩格斯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科学本身的含义、功能、结构、组织形态以及应用方式等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与实际社会生活进程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科学研究本身就产生了当下社会的实际需要并开创了新的产业,就像丹皮尔在《科学史》中所说的那样,“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与发明。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2]283-284。科学变成了生产力,成为工业化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和决定性要素,它对社会生活的塑造、影响越来越大,人们的心智也越来越热衷于科学。对此,洛采在《小宇宙》的导论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每一步都无法避免利用科学的便利,那么,他就会心照不宣地承认科学真理。”[5]
毫无疑问,鲁道夫·瓦格纳在哥廷根会议上的致辞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他反对唯物主义的神圣战争的第一枪”[3]239,而且,他的枪口对准的人物也昭然若揭。如上文所述,1852年初鲁道夫·瓦格纳出版了自己的《生理学通讯》,这个书名当时德国人太熟悉了,因为,有一个学者在1845年代因为发表通俗而生动的《生理学通讯》而出了名,接着他在1846年和1847年又连续出了两册《生理学通讯》,它们都成为雅俗共赏的畅销书。这个人就是声名远扬的博物学家卡尔·福格特先生。两年前,当福格特看到鲁道夫·瓦格纳也出版一本《生理学通讯》并且在书里引用自己的一大段话加以批评,他当时就已经非常生气了,正是在对鲁道夫·瓦格纳的愤慨中,他撰写了《动物生活图景》这本充满趣味的书,当然,在这本研究动物的专著里,他已经向鲁道夫·瓦格纳表示了严正的抗议。“如今,这个鲁道夫·瓦格纳竟然变本加厉,居然在一个公共学术平台上、在全德自然科学家协会的机构性会议上大肆攻击自己,而且自己当时并不在场。背后向人开枪,这算什么?福格特勃然大怒,立即向鲁道夫·瓦格纳提出公开辩论的挑战。一开始鲁道夫·瓦格纳答应下来,可是,他很快又改了口,说自己患了突发性感冒,不能参加原定的辩论。在福格特看来,这分明是骗人的借口!向别人发动突然袭击,一旦对方还手,却想逃之夭夭、溜之大吉,哼!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老东西,你也不想想,我福格特是谁?”
与科学繁荣相伴随的是科学主义的兴起。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原则作为根本的世界观,认为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学科、一切领域里的所有问题。丹皮尔在《科学史》中在谈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哲学的影响时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大致说来,达尔文的成功的第一个主要结果就是机械论哲学浪潮的再起。我们不妨说:进化论的确大大加强了自然界可以了解的感觉,并且增强了那些把他们的生命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们的信心,我们这样说是完全正当的,而且毫无夸大之处。可以说,进化论的确立,加上生理学与心理学,从生物学方面补充了当代物理中出现的一些趋势。这些趋势使人觉得很快就可以用永恒不变的质量及有限的数量和绝对常住不变的能量,来对无机世界给予完满的说明了。”[2]422-42319世纪的科学主义有一种强劲的僭越逻辑:既然物理学的规律可以运用于生物现象,那么,它也可以进一步运用于心理现象,并且,它还可以运用于精神生活领域。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分子运动的方式,及机械的或化学的能量表现”[2]423。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自然主义的绝对支配——把自然界的规则运用于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精神领域。狄尔泰在论述自然科学的原则时指出,“一个客观的、可以理解的、有关既定东西的条件体系所具有的理想,是通过发现热的机械当量、确立力的守恒法则,而沿着这些思路得到的。这并不是一种先天的法则;毋宁说,各种经验发现已经使自然科学更加接近了人们以前所陈述过的某种理想”[6]。人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纷纷在人文社会领域内建立各种“科学”的声势浩大的风潮:孔德创建社会物理学,斯宾塞创建社会静力学,穆勒创建人性科学,狄尔泰创建精神科学,勒南创建宗教科学,如此等等,似乎一切都要打着科学的旗号才能名正言顺,一切只有借助科学东风才能起帆远航。
自然主义的强势扩张给哲学造成了空前的挤压甚至消蚀。把一切学科包容在自身之内的宏大的元哲学叙事已随黑格尔主义的解体烟消云散。19世纪下半叶,不仅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消亡了,就连与科学平起平坐的哲学也难觅踪影,哲学似乎要永远屈居于科学之下,或者彻底变成科学的附庸,或者完全被科学所取代。即使哲学还存在,它也早已被自然主义的盐碱所浸透,变得僵硬不堪:哲学的实证化趋势在19世纪后半叶迅猛发展、不可阻挡。正是在科学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的蔓延中,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物化概念浮现了出来。海德格尔在《哲学的规定》一书论述洛采的那一节,以一种令人压抑的语气描述了洛采在进行哲学探索时面临的困难形势以及承载的思想负担:“自然主义导致了对精神的绝对事物化,将一切存在都还原为有形的、物质性的、事物性的事件,还原为物质和力,拒斥一切根本的思索”[7]。这显然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的一种物化机制,它是由自然主义方法论导致的精神物化,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自然主义方法论导致的思维方式上的物化正是洛采哲学的一个深层背景,实际上,也只有探明了这个深层背景,我们才能真正深刻地领会洛采何以要从事物的存在中区分出一个有效的价值空间。
回到十年后血海肉林的灵宝谷,如果届时我们毫不犹豫地出手杀了哥舒翰,去掉将要轻出潼关的主帅,大军就会由混乱里镇定如常,反攻叛军,稳住阵脚,回师潼关,天下的大势就会发生转换,大唐的元气会重新凝聚起来。
二、洛采与德国生理学
第一,地区间存在差异。这主要表现为时间长度和实施水平两方面:一方面,从目前出台的规定来看,各省市地区的产假时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西藏、吉林、重庆等地的产假时长均可延长至1年,其他地区产假时长则由98到158天不等。这种时间长度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女性人才多向产假时间较长的地区流动,进而造成人才分布的不平均,不利于地区之间的公平与发展,而且从实质上说也不利于女性的平等。另一方面,由于各省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和劳动者整体素质、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等具体情况和水平的不同,产假制度在各地的实施情况和监管水平也存在着差异,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等性。
作为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洛采当然属于韦伯学派。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Ernst Heinrich,1795—1878)是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解剖学家,是洛采在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的指导老师。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在约翰内斯·弥勒之前就已经开始独立进行一系列心理物理学研究。他引入物理学的方法对主观感觉现象进行了精密研究,获得了著名的韦伯心理物理学定律。属于韦伯圈子的莱比锡大学哲学院古斯塔夫·特奥多尔·费希纳教授(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以其闻名遐迩的《心理物理学原理》(1860年)四卷巨著进一步阐释和应用韦伯感觉定律,从而把心理物理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费希纳第一次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心理量的测量方法,从而为科学心理学奠定的基础。正是由于费希纳的杰出工作,才有了“心理物理学”这一名称以及由这一名称所标示的新学科。梅尔茨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中称自学成才、多才多艺的费希纳“是德国文学、科学和哲学上独一无二的人物”[4]509。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在论及费希纳时怀着无比景仰的心情说道:“他逝世时,莱比锡大学的师生无不哀悼,因为他是理想的德国学者之楷模,生活简朴,思想新颖,虚怀若谷,和蔼可亲,孜孜为学,唯真理是服膺,而且文采翩翩,纯系日尔曼口语体裁。……他具有最为耐心的观察力,最为准确的数学,最为敏锐的辨别力,又最富于人情味。这些特点丛集于身,相得益彰,而无互相削弱的痕迹。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虽然他不像多数哲学家那样热衷于单薄的抽象观念。”[8]
综上所述,我国的社保工作已经步入一个大信息时代。国有企业社会保险经济业务集约化管控系统建设越来越显得十分必要。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的工作开始向集约化发展。相信通过不同部门人员的共同努力,社保的信息化建设一定可以步入一个新的高度。
鲁道夫·瓦格纳本人把这种解决信仰与科学的矛盾的方式称为“复式簿记”(dopelte Buchhaltung),即科学问题记在科学的帐目上,信仰问题记在信仰的帐目上,两者不可交叉混淆。在这个阐述他对理性和信念的基本立场的文本中,他再一次提到了洛采。在他看来,洛采不仅是基督教价值的守护者,而且一直主张灵魂的存在及其独立性,因此洛采当然是自己的同道。鲁道夫·瓦格纳是洛采的提携者和恩人,当初正是在他的大力宣传、反复举荐和机智的运作下,洛采才为作优秀学者被引入到哥廷根大学并一步到位直接聘为教授。就像他在1844年把洛采成功引进哥廷根大学一样,如今,他又成功地把洛采引入到关于唯物主义的争论中,并且把洛采牢牢在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这个素来不爱争论、逃避争论的人,在自己恩主的召唤与引领下,这次看来是逃无可逃了。
唯物主义争论正式开始于1854年在哥廷根举行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31届大会。哥廷根大学生理学研究所所长鲁道夫·瓦格纳在开幕式上致辞,题目是“人类的起源与灵魂实体”——这是他在会议召开的几天前仓促写成的一篇发言稿。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他认为,自然科学仍然不能推翻《圣经》创世篇关于上帝造人的神圣教义。至于人死之后的命运问题,他坚决维护灵魂不朽的信念。正是在关于灵魂实体这一问题上,他对于灵魂之学(即心理学)越来越沦落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失去神学和哲学的庇护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弗里德里克·拜塞尔在《德国晚期观念论》中这样叙述鲁道夫·瓦格纳发言的核心内容:“在此,他认为他必须对最近的科学研究方向发出警告。一些生理学家倾向于唯物主义学说,他们不仅怀疑而且否认灵魂和自由意志的存在。瓦格纳缓慢而庄重地说,这种新的唯物主义的问题在于,它逐渐破坏了一种对道德和政治秩序至关重要的信念:即对灵魂不朽的信念。基督教关于道德世界秩序的教义——奖赏有德之人、惩罚邪恶之人的神圣天意——就基于这种信念。任何想要在‘去基督教化的大众’中维护道德和宗教的人,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坚守这种信念。随后在致辞结束时,瓦格纳呼吁:自然科学家应该考虑他们的研究方向;他们应该避免传播损害道德、宗教和国家的学说。”[3]238
三、“神秘信徒”与争论的发起
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由于自然科学的高歌猛进,科学登上了最高峰,它第一次成为凌驾于哲学之上的王中之王。一切东西似乎只有在科学中并通过科学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就连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也改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更不用说那些科学家在阐明他们的科学研究的原理和方法时有意无意地确立起来对物质及其关系的优先性的信念了,这种由科学家基于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而提出的唯物主义被当之无愧地称为“科学唯物主义”,它体现了科学精神与哲学理想的有机结合。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唯物主义,那么,思想史上的很多脉络与线索也就接不上了,就连历史唯物主义的背景和内容也难以真正看得清楚。就本文探讨的主题而言,如果不提这个“科学唯物主义”,我们也就无法讲述洛采对“唯物主义争论”的介入。丹皮尔在《科学史》第八章“十九世纪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专门花费笔墨对“科学唯物主义”进行了一番勾勒,他说,一度在18世纪的法国勃兴的唯物主义哲学在19世纪的德国再度崛起,这一唯物主义哲学的早期领袖——如福格特(Karl Vogt,1817—1895),摩莱肖特(Jacob Moleschott,1822—1893),毕希纳(Ludwig Büchner,1824—1899)——“都把他们的哲学建立在科学成果上,特别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成果上。毕希纳的书名《力与物质》(Kraft und Stoff,1855)就说明把力与物质看作最终的实在的观念构成这个唯物主义运动的一个必要部分。在有些玄妙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盛行半世纪以后,这样的唯物主义学派,促使人们注意自然科学的明晰成果,其影响究属良好”[2]400。在当时的德国,生理学(或更一般地称为生物学)走在自然科学的最前列,最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者都接受过正规的生物科学训练,上面提及的早期领袖摩莱肖特、毕希纳和福格特,以及科学唯物主义另外一员健将乔尔贝(Heinrich Czolbe,1819—1873),他们都拥有医学学位。所以,他们的唯物主义也被称为“生物学唯物主义”。
福格特确实是一个卓越不凡的人物。19世纪30年代,他在吉森跟随著名化学家李比希学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却成为一名新闻记者。40年代,福格特出版了当时属于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的旅游学、地质学、动物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畅销书,赢得了广泛的名声。更为传奇的是,他追随蒲鲁东和巴枯宁从事革命活动,1848年被选为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成为议会中极端左翼的引领者。革命失败后,被流放到意大利。不久后,又受聘担任瑞士日内瓦大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教授。作为左翼革命者,福格特大力宣扬一种基于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理学最新研究成果之上的唯物主义学说,他认为,人的思想不过是大脑的生理活动的产物,在1846年的《生理学通讯》中发布的唯物主义类比在当时的欧洲思想界几乎人人皆知——思想之于大脑的关系就如同胆汁之于肝脏、尿液之于肾脏的关系。[11]在持续流传与反复转述中,这句话后来演变成臭名昭著的思想泌尿学公式:就像肾脏分泌尿液一样,大脑分泌出人的思想。与他的科学唯物主义相匹配,他在政治上一直尖锐地批判德国现行体制,当然也包括德国大学的教育制度。他在《动物生活图景》的最后一章“动物的灵魂”中激愤地指出,鲁道夫·瓦格纳就是糟糕的德国大学体制中最糟糕的代表:迷信、保守、冥顽不化。作为记者、政治活动家和革命斗士,福格特向来能言善辩,由于他身体肥胖,威猛无比,所以他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头野蛮而狂怒的公牛。鲁道夫·瓦格纳之所以回避与福格特的当面对决,想必也知道这头体格健壮的公牛不那么好对付。
也正是因为它是发生在生物学界的哲学争论,洛采被卷入其中的可能性才非常大,因为不论是在求学时期还是在教书时期洛采都具有双重身份——他同时取得医学和哲学双博士学位,他既在哲学院教书也在医学院授课,他既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哲学教授。作为韦伯学派的正宗成员,他不仅是生理学名家的弟子,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的开端,他连续出版了两部弥漫着浓厚哲学气息的生理学专著——即1851年的《肉体生命的普通生理学》和1852年的《医学心理学或灵魂生理学》。洛采作为医生和哲学家的两重身份正好契合这场争论的性质与主题。不过,洛采在出版这两部著作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德国生物学界正在悄悄酝酿个一场论辩风暴,他更不知道,正是他出版的这两部著作,会把他牵连到这场始料未及的口诛笔伐的尖锐对垒战之中。
当前,理论界正在进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和凝练,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邓小平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但从文献检索情况看,在《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中,邓小平使用“价值”一词达15次,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使用“教育”一词就达149次,其中蕴含了一些关于价值观教育的思考。特别是他关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论断,成为我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在新形势下,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对深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不过,洛采在延续韦伯—费希纳的基本思想的同时,也从约翰内斯·弥勒那里借鉴、吸收了很多东西。约翰内斯·弥勒(Johannes Müller,1801—1858),是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生理学教授,现代医学柏林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以其对生理学的杰出贡献而被誉为德国的居维叶、19世纪的哈勒。他以研究感觉神经而著称,1831年,他以青蛙为对象的实验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苏格兰解剖学家贝尔(Charles Bell,1774—1842)首先提出的关于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功能不同的理论的正确性。当然,他还有更独创性的发现——这个发现在感官知觉生理学中被称为“神经特殊能量论”。这一理论意味着我们感觉的性质并不取决于刺激的经验类型,而是取决于神经器的作用。他的著名例证是,压力或其他机械刺激作用于视神经和视网膜也照样能够引起与光刺激相同的视觉经验。这个由约翰内斯·弥勒最先提出、后来经过赫尔姆霍兹进一步发展完善的“神经特殊能量论”给洛采带来很多灵感与启发:一方面是洛采提出一种关于灵魂具有不同质量的理论,这显然与约翰内斯·弥勒对感觉过程中神经元的独特质量的分析有某种类似性;另一方面,洛采在《医学心理学或灵魂生理学》(1852年)中阐述的“部位记号”理论,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约翰内斯·弥勒对于神经元的定位作用的分析,就像《劳特利奇哲学史》精辟分析的那样:“洛采认为,灵魂不可能被神经系统的空间分布所影响,而只会被神经系统在任意给定点的活动强度所影响,作为弥勒早期定位论的追随者,洛采主张,确实如弥勒所提出的那样,不同部位的大脑活动产生不同的心理状态。但是,灵魂对这个活动所能知道的只是它的强度、强度的位置以及那个位置上强度的变化,灵魂不能直接直觉到神经系统中各个强度的分布。”[9]尽管洛采对约翰内斯·弥勒的活力概念以及把运动皮层比喻为钢琴键盘的说法都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是约翰内斯·弥勒的感官生理学对洛采思想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梅尔茨才说自己的老师“知道如何在约翰内斯·弥勒学派和韦伯学派那里耕耘身体现象和心理现象的边缘地带”[4]500。“边缘地带”在这里尤为确切并且具有多重含义:它既指身体与灵魂的边际地带,也指约翰内斯·弥勒学派和韦伯学派的思想交界面,同时它又切合19世纪中后期的思想处境。那时,物理学的机械主义方法已经深入到了生理学内部和心理学的深处,处于强势地位的自然科学已经把哲学从中心挤压到边缘。在论及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时,丹皮尔说,科学家那时普遍“讨厌黑格尔派,最后干脆不理会他们。就连赫尔姆霍兹在对这种态度表示感叹时,也认为哲学的功能只限于它的批判功能——阐明认识论,它没有权利去解决其他更富于思辨性的问题,如实在的本性和宇宙的意义等更深奥的问题”[2]393。而伴随着青年黑格尔学派对黑格尔主义的四面围攻,曾经强盛无比的观念论哲学此时风雨飘零。在黑格尔主义的分崩离析中,只有唯物主义异军突起,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自然科学的大棚里培育出来“科学唯物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乘势而上、竞相涌动。在这样的情势下,观念论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形而上学好像在边缘地带发出若有若无的呻吟。
1941年4月4日,熊式辉向蒋介石进言:“领袖只宜以思想领导干部,功名利禄,只能奔走一般中下之士,凡为革命奋斗冒险犯难而不辞者,皆思想上信仰力之驱使,故把握正确的思想路线是第一要务。”㊾实则亦是针对蒋以功名利禄笼络干部的做法提出的改进意见。
19世纪德国在科学上最伟大的进步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丹皮尔在《科学史》中就说:“在十九世纪的飞跃进步中,最有效地扩大了人们的心理视野,促成思想方式上的另一场革命的既不是物理知识的大发展,更不是在这些知识基础上建筑起来的上层工业大厦。真正的兴趣,从天文学转移到了地质学,从物理学转移到了生物学和生命的现象。”[2]344就连“生物学”这个词也由德国的一位学者型医生G.R.特雷维拉努斯(G.R.Treviranus,1776—1837)最早使用。梅尔茨明确指出:“生理学,或者用其更一般的名字即生物学,可以说是一门德国的科学,就像化学可称为一门法国科学一样。”[4]193-19419世纪早期,主导德国生理学研究的有两大学派:莱比锡大学韦伯学派与柏林大学弥勒学派,而后一学派影响更大。洛采从莱比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那一年(1838),耶拿大学植物学教授马蒂亚斯·施莱登(Mathias Schleiden,1804—1881)提出了关于植物结构和生长的细胞理论。几乎在同时,卢汶大学教授特奥多尔·施旺(Theodor Schwann,1810—1882)把这一理论推广到动物机体,这就是被誉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的细胞学说,这一学说开辟了科学思想史和一般思想史的一个新时代。细胞学说的这两位创始人就属于弥勒学派。梅尔茨在评论细胞学说时充满赞誉地说道:“这一学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成为整个系列的重要发现的出发点。它为德国赢得了生理科学长期的权威地位。这种权威地位是由汇聚于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和约翰内斯·弥勒的名下的诸多学派的大量细致研究来维持的。约翰内斯·弥勒学派的特殊功绩在于把精密研究方法引入整个生理现象领域,在全德国建立起类似吉森-李比希化学实验室的生理学实验室,真正驱除了旧形而上学派的模糊概念,传播了真正的科学精神。它以一长串杰出教师的名单占据德国各大学的医学、生理学和解剖学教席而自豪,他们把这种真正的科学精神传遍医学科学的每个分支。这个学派由此把医学科学引进精密科学即力学科学的范围之中。”[4]196-198
蒋光篯(1866—?),字介眉,号芥湄,浙江诸暨人。丁酉科(1897)举人。[3]1910年2月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
鲁道夫·瓦格纳在发言中,为了使自己的演说更具有现场效果、更具有说服力,他引用了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位年轻教授的著作中的一段话。他没有直接说出这位教授的名字,只是说这位教授是“坐在我们中间最机敏的科学家”。据说,当时这位教授坐在台下因为害羞而涨红了脸。这个极易害羞的人就是哥廷根大学哲学院的洛采教授。鲁道夫·瓦格纳引用的是洛采1852年的《医学心理学或灵魂生理学》第一卷第一章第3节“唯物主义的反驳”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这些唯物主义推理已经在通识教育的逐步衰退中获得了巨大的扩展(Die grosse Verbreitung),而且无疑会继续获得进一步的扩展,这就需要我们在对有意义的成功不抱希望的情况下,去验证他们的主要论点。”[10]30鲁道夫·瓦格纳在哥廷根会议上的致辞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许多参会者对他发言中把学术与政治扯在一起的粗暴方式感到震惊。在会议结束后的几周,为了回应他的致辞引起的争议,他又发表了《关于知识与信仰》,提出了一种关于新教教义的双重真理学说。弗里德里克·拜塞尔对这一双重真理学说有精准的把握:“根据这一学说,信念和理性在各自的领域中运作,只要它们都在各自的范围内,就不会互相矛盾。信念不应该对科学问题作出断言,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感觉经验和理性来了解科学;但是科学不应该以信念为前提,因为我们通过《圣经》,即神的启示的记录,来了解信念。对于瓦格纳来说,信念不仅仅是信仰的问题,而是路德和加尔文所指导的那样,是一种直接的经验和确定性。信念给予我们超自然事物的知识,正如理性给予我们自然事物的知识;正如盲人不应该擅自判断他所看不到的东西,不相信自然科学的人也不应该怀疑基督徒通过信念之眼所相信的东西。”[3]239
洛采正是在老韦伯和非凡人物费希纳这两位科学名师的熏陶、指导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洛采对感觉的分析、对心理现象的探索很多方面都直接受惠于这两位杰出人物。由于洛采与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的动物解剖学副教授艾尔弗雷德·威廉·福尔克曼(Alfred Wilhelm Volkmann,1800—1877)保持着亲密的友谊,而福尔克曼是费希纳的姐夫,因此,洛采在大学时期与费希纳的精神契合度与私人情谊看上去远远超过了与其学业导师韦伯的关系。青年洛采的思想无疑是处在韦伯—费希纳所确立的心理物理学的路线的延长线上。诚如梅尔茨所言:“洛采自己表述了心理物理机制概念,利用了韦伯的那些精构思而又还有根本重要性的实验和观察作为概念内涵的范型。”[4]504
四、“浑圆天禀”的愤怒
由于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关联以及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日益增强,并且它支配和推动产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科学的实际应用效益愈发突显。这时,科学本身也开始职业化和专门化。梅尔茨指出,与之前不同,在19世纪后半叶,“化学、电学和热学上的伟大发明都是在实验室里作出的”[4]92,而且,实验室不再是科学家设在家中的私人房间,而是由大学、研究机构或企业来开设并且成为向很多人才开放的公共研究平台,如此一来,科学就不再是被少数天才人物独占的地盘,而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科学的职业化为许多社会成员提供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也为他们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提供了一条现实的路径。而科学的职业化必然带来科学的专门化。科学研究者为了赢得社会的认可、获得社会荣誉,便不断向未知的领域拓展,不断创设新的学科,不断进入新的主题,于是,科学的范围日新月异地扩大。不过,这里所说的科学范围仅仅是在经验科学的意义上说的,因为,19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以追求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为目标,不再致力于阐释普遍的本质与永恒的真理。科学变得经验化、工具化、实用化了。伴随着科学的经验化,科学越来越倾向于根据现实的需要而迅速调整自身的结构与功能,科学变成了一个开放、可变、服从于当下“时态”、非确定性的“机会主义”系统。
德国科学唯物主义的领军人物都是生物学领域有造诣的科学家,他们在生物学领域著书立说,还积极参与当时生物学界的学术争论。当时生物界争论最激烈的三个主题是:活力问题、自然发生问题以及物种转化问题。特别是关于活力的问题,牵涉甚广,很多科学家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洛采在早年的《普通病理学和作为机械自然科学的治疗学》(1842年)就从纯粹物理学的意义探讨过活力概念。在1842年下半年发表在《生理学手册》上的文章《生命、活力》则围绕约翰内斯·弥勒的活力论展开讨论,洛采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对活力论的批判。据说,洛采这篇文章极大鼓舞了科学唯物主义的干将乔尔贝,成为科学唯物主义的重要灵感。不过,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唯物主义争论并不是由上述三个问题引发的出来的,它另有其独特的起源。作为这场论战的亲历者,朗格在他的《唯物论史》中,这样述说它的前奏:“1852年初,鲁道夫·瓦格纳出版了《生理学通讯》,4月,摩莱肖特写成《生命的循环》的序言,9月,福格特在《动物生活图景》中宣告,现在务必要抵制那势焰嚣张的权威。”[1]264争论双方最主要的人物在论战正式打响之前纷纷在锻造批判的武器,似乎已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如果单从他们著作的名称看,似乎是生物学之争,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些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是在捍卫各自的哲学立场,确切地说,他们是借生物学的地盘贩卖自家的哲学干货。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在生物学研究中应该以唯物主义作为基本原则吗?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双方都要对唯物主义表明自己的态度,所以这场发生在生物学领域的哲学争论才被称为唯物主义之争。
然而,被激怒的公牛已经狂奔起来并发出角斗的吼叫。弗里德里克·拜塞尔在《德国晚期观念论》一书中有点煽情地写道:“在1854年秋天,几个火热而又激动人心的星期里,福格特撰写了一篇猛烈而精彩的反对瓦格纳的檄文,这就是他的《盲目信仰与科学》(Köhlerglaube und Wissenschaft)。”[3]241《盲目信仰与科学》发表于1855年1月,它把这场争论带入1855年并引向高潮。正是在这篇引人注目的檄文中,福格特给鲁道夫·瓦格纳起了一个浑名——“神秘信徒”,同时也顺带赠给洛采一个富有文色彩的雅号——“一位思辨的蓬头彼得(Spekulierender Struwwelpeter)”。“蓬头彼得”是德国儿童文学中的著名人物形象,他是一个淘气的男孩,留着长指甲、蓄着长长的红头发,通常被家长用来恐吓德国小孩,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言而喻,这是在暗示洛采是鲁道夫·瓦格纳的追随者,那稀奇古怪的长指甲和蓬松的红色长发宛如洛采的观念论哲学。这个缺乏自信的鲁道夫·瓦格纳搬出了一个卡通式的淘气鬼来吓人,而问题在于,福格特可不是能够轻易被吓住的小孩,即便你长着长长的指甲、即便你披着长长的红头发,又有什么用呢?
《盲目信仰与科学》的第一部分是对鲁道夫·瓦格纳的思想低能的公开而恶意的人身攻击。福格特说,鲁道夫·瓦格纳是懒惰的人,但是由于当上了一个科学刊物的编辑,从而获得了大部分应归于他人的声望。当他作为解剖学家的无能终于无所遁形时,另外一位学者被召来哥廷根接替他的工作。福格特最不能容忍的一点是,作为科学家,鲁道夫·瓦格纳粗心大意,竟允许个人信仰干扰他的科学研究。第二部分转入正题,讨论鲁道夫·瓦格纳提出的两个主要观点——人类同源说与灵魂不朽。关于第一个观点,福格特充分调动自己的广博学识进行了批驳,他指出,“所有来自地理学和解剖学的证据都表明了不同人种之间的差异,每一人种都必须有其自己最初的一对。从地质学上也可以明显看出,地球的年龄比《圣经》上的任何说法都要早得多,而且人类的起源远远早于四千年前。因此,《圣经》的教义并为凌驾于经验性的确证或伪证之上,而是断然与事实相反”[12]81-82。关于第二个观点,福格特坚称,关于非物质性灵魂的存在,最新的生理学研究并没有提供可以证明灵魂与大脑相分离的任何证据,恰恰相反,它却表明了精神活动与大脑功能的不可脱离的紧密结合,因为,一旦大脑受伤,精神活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完全停止。生理学和医学的手段已经可以探测并确定大脑中用于特定精神功能的特定部分。福格特自然就引出一个坚实推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意识完全依赖于大脑过程”[12]109,承认了这个推论,所谓肉体死亡之后灵魂存在的观念也就不攻自破了。福格特通过自然科学的成果确立了自己的无神论,在他看来,宗教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迷信。虽然福格特与鲁道夫·瓦格纳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太明显了: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诚如弗里德里克·拜塞尔所言:“在福格特和瓦格纳的争论之下隐藏着他们的政治冲突。福格特是一位激进分子,他曾经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为民主而战,而瓦格纳是一位反动分子,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回到旧秩序的君主政体统治。……他们的政治立场又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哲学立场。瓦格纳想要维护天意和不朽的信仰,使君主制合法化,并控制“去基督教化的大众”。福格特想要破坏这些信仰,之所以要破坏它们,是由于它们是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武器,是组织他们在新的民主秩序中掌控自己生活的一层欺骗性的面纱。”[3]242
当然,即便是同处左翼政治的革命战线上,也会有不同的别派,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福格特在1850年代末就与唯物主义的另一个领袖人物展开了更加复杂、更加剧烈、更让人纠结的论辩。这个唯物主义的领袖人物就是卡尔·马克思。1860年底,马克思在伦敦出版了著名的《福格特先生》,在这部论战性著作中,马克思沿用了福格特的律师对其主顾的昵称——“浑圆天禀”(Abgerundete Natur)——来戏称自己的对手福格特。福格特的律师之所以用“浑圆天禀”,主要夸赞其主顾性情温厚而又禀赋超常,而马克思借用“浑圆天禀”之名则是嘲笑福格特笨重肥胖,是一个“一塌糊涂地狂吃”的蠢才呆瓜。[13]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披露了福格特职业生涯中的大量细节,却唯独没有提及福格特在50代中期介入的唯物主义争论。我们推测,马克思应该知道这场大辩论,并且也应该清楚“浑圆天禀”在这场论战中的表现。只不过,由于这个“浑圆天禀”很快就开始向马克思怒吼了,对于这头好斗的公牛的昔日战绩,马克思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五、洛采的折中主义立场
先是被称为“神秘信徒”的鲁道夫·瓦格纳把洛采引为同道,接着是被称为“浑圆天禀”的福格特把洛采视为鲁道夫·瓦格纳的追随者,认为他们共同创造了哥廷根经院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混合物——灵魂实体。如此一来,被称为“思辨的蓬头彼得”的洛采无论自己是如何不愿意争论,终究还是被双方拖了进来。赖因哈特·佩斯特在1997年出版的《洛采的思想和研究之路》一书专论唯物主义争论一节中指出,由于历史文献缺乏相关记载,“所以我们对洛采参加哥廷根会议的情况也就知之甚少”[14]。但是,通过洛采写给朋友的一些信件可以得知,洛采为参加1854年9月在哥廷根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31届大会作了一些准备,他还邀请一些师友在会议期间来家中作客,并且,还亲自参与了会议的一些组织和监督工作。对于鲁道夫·瓦格纳与福格特之间愈演愈烈的哲学争论,这位“思辨的蓬头彼得”实际上并没有象福格特暗示的那样做出什么吓唬人的举动。正如弗里德里克·拜塞尔描述的那样:“尽管有福格特的挑衅和瓦格纳的花言巧语,洛采还是极力漠然处之。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而且理由很充分。没有理由攻击福格特,因为洛采已经在他的《医学心理学》中阐明了他对唯物论的观点,也没有理由为瓦格纳辩护,因为说到底,他们实际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3]242-243
说他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显然也不是事实。洛采与鲁道夫·瓦格纳一样不愿意放弃灵魂概念以及灵魂存在的学说,正是在这一点上,鲁道夫·瓦格纳把洛采视为“自己人”。不过,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间在哲学思想上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如夏洛特·莫雷尔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瓦格纳和洛采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来谈论唯物主义。尤其是洛采,他很清楚,他自己需要与瓦格纳所采用的‘复式簿记’保持距离,以便在讨论像人类的起源或是灵魂存在这样有争议问题时,可以把科学知识与宗教信仰的有关的话题和答案合法地区分开来。同时,他也反对瓦格纳提出的‘灵魂是可分的’这一命题。”[15]91尽管洛采确实不同于鲁道夫·瓦格纳,并且他有意表明他并不是后者的思想保镖,但是,科学唯物主义者仍然没有轻易放过洛采,他们在痛击鲁道夫·瓦格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要对洛采说上几句。所以,洛采虽然很想游离其外,但是,他终究不能明哲保身。
(4)结合本区域综合地质调查成果,初步划分了3个找矿靶区,即拉窝西金找矿靶区、希望沟找矿靶区及哈日扎北多金属矿找矿靶区,为区内开展下一步工作寻找金银多金属矿提供有意义的帮助。
1855年,唯物主义争论渐入高潮。福格特在年初发表的《盲目信仰与科学》似乎只是抛砖引玉之作,接下来,两部伟大的唯物主义巨著相继问世,这就是海因里希·乔尔贝的《感觉论新述》和路德维希·毕希纳的《力与物质》。毕希纳在《力与物质》中采取了一个高超的论证策略,他一边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洛采具有唯心主义倾向,一边又援引洛采说过的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话,从而表明,就连处在唯心主义阵营中的有名的哲学家也无法完全否认唯物主义,也不得不承认人的精神活动与大脑不可分割的联系。在随后发表的《论物理学的和哲学的原子论》一文中,毕希纳又从物理学的最新成果出发坚决捍卫了原子论,认为物质性的原子才是终极性的实在,在这篇文章中,毕希纳再次点名批评洛采的灵魂实体论。乔尔贝在《感觉论新述》的序言中,更加老练地运用辩证分析法来剖析洛采思想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对洛采在《生命、活力》(1842)与《医学心理学》(1852)中对活力论的批判表示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与兴奋,他甚至毫不隐讳地坦言,洛采对活力论的批判成为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的灵感来源。乔尔贝几乎要把洛采当作自己走向唯物主义道路的引导者了,他不断向人们暗示,如果洛采更坚定一些、更始终如一一些,那么,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很出色的唯物主义者。然而另一方面,乔尔贝对洛采脱离唯物主义的倾向表示了不满,对洛采迷恋并维护超感觉的东西展开了毫不容情的批驳。
1855年,在唯物主义争论达到高潮之际,洛采并没有直接与福格特对阵,而是选择了毕希纳和乔尔贝作为回应对象。他在《哥廷根学者通告》(Göttingen gelehrte Anzeigen)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评论,一篇是《评毕希纳的〈论物理学的和哲学的原子论〉》,另一篇是《评乔尔贝的〈感觉论新述〉》。1856年,乔尔贝发表了《自我意识的产生:对洛采教授的答复》,1857年,洛采在《哥廷根学者通告》上又发表了《评乔尔贝的〈自我意识的产生:对洛采教授的答复〉》,对乔尔贝的回应作出再回应。1857年,洛采出版了著名的《论辩集》,在《论辩集》中,洛采针对这场争论集中谈了四个问题:原子论、生命与机械论、身心相互作用、灵魂的处所。1859年,洛采又在《哥廷根学者通告》发表《评卡尔·斯内尔的〈唯物主义争论问题〉》。总之,1855—1859年,洛采就唯物主义争论写了四篇回应性评论,出版了一部《论辩集》,这在洛采学术生涯中是唯一一次就同一个主题来回反复与别人针锋相对地展开较量的一场理论争鸣。由此可见,“神秘信徒”和“浑圆天禀”挑起了关于唯物主义的争论最终把“思辨的蓬头彼得”深度地卷了进来,“蓬头彼得”被逼无奈只得在辩论中进行思考、在思考中进行辩论。对于不喜欢与人争吵辩论的“蓬头彼得”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劳累痛苦的差事。洛采本人在评价这场争论时,甚至说它只会带来“毫无意义的痛苦”[15]90。
不过,洛采的痛苦并不像他本人说的那样是无意义的。在这场争论过去一个半世纪之后,再回头认真审视一番,我们惊奇地发现,洛采对“科学唯物主义”的批评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包括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批评、尤其是对所谓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批评存着很多相通的地方。当代研究唯物主义发展史的专家夏洛特·莫雷尔非常正确地指出,洛采所批判的唯物主义只是“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15]92,这种唯物主义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拒绝全面了解心理学的最新成果;二是对科学抱有一种虚假的热情。这两点实际上涉及的是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本质就是经验主义和直观主义。把科学知识仅仅建立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并且这种经验论是一种只承认感性认识的狭隘的粗陋的感觉主义。关于洛采对乔贝尔的感觉主义的批评,弗里德里克·拜塞尔有很精彩的总结:“洛采在他的评论一开始就指出,他发现乔尔贝实际上把唯物论等同于经验论是很奇怪的;毕竟,对于一个唯物论者,也就是一个相信物质的唯一实在性的人来说,维持内在原则和观念的存在是可能的。他也忽略了乔尔贝的任何证据,即任何无法预知和超感觉的事物都是模糊的;毕竟,最明白易懂的思想互动是无法用感官感知的。但是,撇开这些观点不谈,洛采主要关注的是乔尔贝的经验论,尤其是他试图将超感觉从一切思想活动中剔除出去。洛采认为,乔尔贝的一切努力都最终要彻底失败,因为所有的思维都是在直觉材料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超感觉的东西。感官显示给我们的,只是性质规定的连续和共存,它们并不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这些联系只能通过思维提供。”[3]245
确实,洛采对“科学唯物主义”的这种批评就像夏洛特·莫雷尔所说的只能恰当地理解为是对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而不是对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批判”。在1852年出版的《医学心理学》第一章“论灵魂的存在”的最后一节“唯灵论的观点”的一开头,洛采非常率直地讲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赋予物质以实在性;能把灵魂看作一种完全独立而又与物质不同的合法的实在与物质同列地一起,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尽管在此我们将为个人的心理研究保留清晰而适宜的直觉方式,但是,我们必须暂时返回到这里,即返回到物质原则中,以便证明对物理-心理机制的可行而清晰的描述是对真正发生的事情的节略性的表达”[11]55-56。显而易见,在物理层面或者说在机械层面,洛采从来不否认物质的实在性,并且一直认为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对物理-心理机制的“节略性的表达方式”是完全可行的。不仅如此,在洛采看来,唯物主义完全可以容纳更多的超感官的理性思维,甚至可以兼容观念论的某些优点。唯物主义其实应该表现得更好。唯物主义难道只有停留在直观经验的层次上才叫唯物主义吗?唯物主义难道只有拒绝灵魂学(即心理学)才能保持自己的合法性吗?洛采之所以始终站在“神秘信徒”与“浑圆天禀”的中间而不彻底倒向任何一方,原因就在于,他既不主张用观念论取代唯物主义,也不同意用唯物主义吞并观念论。说得更形象一点,“蓬头彼得”就是“蓬头彼得”,他既不是“神秘信徒”,更不是“浑圆天禀”!
洛采始终是一位谦谦君子,即便在最得意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提醒自己只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至于像世界统一于精神、万有归结于物质这样的狂想妄见,他连想都不去想,更不用说去付诸哲学实践了。J.T.比克斯比曾说:“在那些他处理的问题前,洛采总是显得博文多识。与之有关的每一条信息、值得关注的任何一种观点,对他而言都不是陌生的;他以最广博的心灵处理了这些问题。他判决式的语调异常沉稳,他论述严谨、考虑周全,不妄下定论。他是如此谨慎,以至于在高明地讨论了那些重大问题之后,他常常不给出正面的结论。”[16]不过,谨慎绝非没有主见。在事关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这样重大的问题面前,作为19世纪中后叶最伟大的观念论哲学家,洛采无疑拥有最清晰无比的观念:科学再强大,它也不能代替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再弱小,它也总能发出自己美妙的声音。
在这场唯物主义争论中,“思辨的蓬头彼得”站在“神秘信徒”与“浑圆天禀”之间,保持着一种高贵而独立的姿态,他在严肃地思考科学迅猛发展之下的形而上学的命运问题。作为一位机敏的科学家,同时又作为一位观念论哲学家,他最大的希望是科学与形而上学能够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科学和形而上学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或者就如诗人舒婷所描绘的那样,仿佛是并排长在一起的两棵树:橡树与木棉——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哲学家洛采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这位在毕德麦雅时期成长起来的诗人,在喧哗的争吵中,仍然在静谧而热烈地构思着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恋人般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1] Frederick Albert Lange.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M].Kegan Paul,Trench,Trubner&Co.Ltd.1925.
[2] 丹皮尔·W C.科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3] Frederick C Beiser.Late German Idealism[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 John Theodore Merz.A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Nineteenth Century[M].William Blackwood & Son, 1923,(1).
[5] Hermann Lotze.Mikrokosmus. Ideen zur Naturgeschichte und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M].Leipzig: Hirzel,1856:BandI,ix.
[6] 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246.
[7] 海德格尔.哲学的规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52.
[8] 威廉·詹姆士.多元的宇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81-82.
[9] Ten C L.Routle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II[M]. Routledge,1994:326.
[10] Rudolf Hermann Lotze.Medicinische Psychologie oder Physiologie der Seele[M]. Leipzig,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852.
[11] Karl Vogt.Physiologische Briefe für ge- bildete aller Stände[M].Stuttgart/ Tübingen, Cotta, 1846.
[12] Karl Vogt.Köhlerglaube und Wissenschaft: Eine Streitschrift gegen Hofrath Wagner in Göttingen[M].Gießen: Ricker, 1856.
[13]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93.
[14] Reinhardt Pester.Hermann Lotze:Wege seines Denkens und Forschens[M].Würzburg: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1997:213.
[15] Charlotte Morel:Lotze’s Conception of Metaphysics and Science. A Middle Position in the Materialism Controversy[M].Philosophical Readings, 2018,X(2).
[16] Bixby J T. Hermann Lotze on The Soul and Its Organism[M].The Unitarian Review and Religious Magazine (1874—1886)Mar 1877,7(2):10.
[收稿日期]2019-07-15
[作者简介]周凡(1966-),男,河南息县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政治哲学和价值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9-0031-14
〔责任编辑:杜 娟〕
标签:瓦格纳论文; 唯物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论文; 德国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学术交流》2019年第9期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