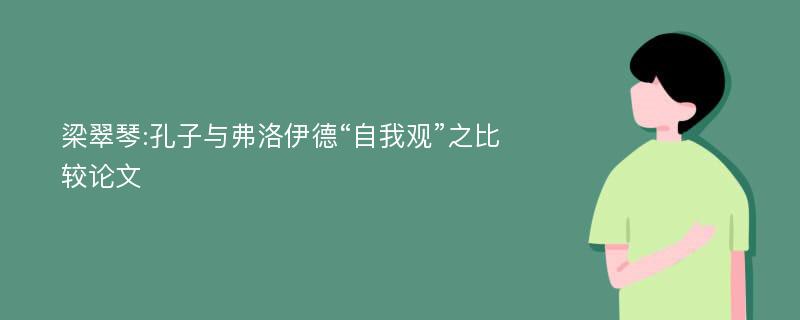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是柏拉图提出的人生哲学“三问”,充分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好奇与反思。2500多年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我”的追问,“自我”成为了历久弥新的话题。其中,“自我观”的建构更是“自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孔子和弗洛伊德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代表,在“自我观”上显然是异中有同的。
首先从“自我”的定义来看,西方语境中的“自我”主要有三层含义:“在一个人中真实地、内在地是“他”的东西(与偶然的相对);我(通常与灵魂或心灵相等同而与身体相对立);一个处于连续变化的意识状态的永恒主体。”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自我”是由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感情、知识、记忆、意志等组成的集合体,是由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构建而成的人格系统。相比之下,中国传统语境很少谈及“自我”,绝大多数情况下由“我”及它的近义字,如“吾”“己”“身”“私”等替代。关于“我”,《说文解字》载:“施身自谓也。或说我,顷顿也……凡我之属皆从我。”段玉裁注云:“施身自谓也。不但云自谓而云施身自谓者、取施与我古为韵。施读施舍之施。谓用己厕于众中,而自称则为我也。”“我”作为当事人的自称,主要指向了承担活动或行为的主体自我,相当于英文中的“I”。而弗洛伊德所关注的“自我”则更多的指向了“客体自我”,因为它是被当作认识、研究的对象来看待的,相当于英文中的“Me”。
中西双方对“自我”涵义的不同注脚反映了双方对不同“自我”的侧重。概括来讲,由于西方把“自我”看成被研究的客体,于是更注重从形而上的角度对“自我”的本体进行追问。从刻写在希腊德尔斐神殿上的“认识你自己”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再到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的盛行,实际上都反映了西方人对“我是谁”这一本质问题的思考。而中国传统语境则习惯把“自我”视为行动的主体,更注重从形而下的实践中谈“自我”的建构,从“克己复礼”到“格物致知”回答的都是“我该怎么做”这一问题,借助具体的行动表达抽象的“自我观”。而孔子和弗洛伊德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代表,两人的自我观自然也呈现出一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面貌。下面先来探讨两人“自我观”的相似或相近之处。
一、同:“自我”的三重面相
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是弗洛伊德所划分的三层人格结构。他认为,本我是最原初的、潜意识的、非理性的心理结构,它充溢着源于天性、本能的欲望冲动,且受快乐原则的支配,一味希望得到满足。自我则是一部分本我经知觉系统影响而修改形成的人格组成部分,它代表理智和常识,按照现实原则行事。超我是与本我相对立的人格结构,它代表了高级的、道德的、超越本能与现实的心理结构,以良心、自我理想等至善原则来约束自我。
在线考试系统运用.NET+AJAX技术,采用B/S三层体系结构设计与实现,该系统具备传统考试中的出卷、考试、阅卷、试卷管理、成绩管理等功能。该系统的使用可降低教育成本,使考试更加客观、公平、合理,有效提升考试质量。
本文运用的治疗方法是国际公认的液氮冷冻治疗。具体的治疗步骤是结合患者的临床情况,有针对性的使用棉签或冷冻枪治疗,当疣体四周出现2 mm左右的白晕后停止冷冻。一次治疗给患者进行2~4个冻融,每20~30天之内只能对患者进行一次治疗,对每个患者最多进行四次治疗。
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探讨“自我”观念,但观其话语系统,不难发现“自我”作为一种构造性的存在,同样呈现了三重面相,分别为源于天性的本我、现实存在的自我以及作为理想人格的超我。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作为生物性存在的“自然之我”、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应然之我”和作为道义性存在的“超然之我”。虽然表述不同,但明显也是参照弗洛伊德的人格说进行阐述的。为了更好地论述孔子与弗洛伊德“自我观”的相同点,本文继续沿用了“本我”“自我”“超我”的说法。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处于人格结构的最底端,它蕴含了强大的原始冲动力量——力比多(Libido)。本我是由天性、本能、欲望等力量所构成心理结构,所以它是最本初、最神隐、最混沌而难以把握的部分。它遵循的是唯乐原则,意在求得个体的生物性欲望的实现,满足“食色性也”的本性欲求,追寻快感。
除了言语上对源于天性的本我的承认之外,孔子在实际生活中也给予了本我适当的表现空间。如弗洛伊德所言,本我蕴藏了强大的力比多作为能量,而力比多作为“本能”的代名词,又代表了潜伏在生命内的一种渴望生存、谋求发展、充盈爱欲的力量。因此,即使孔子也不可能完全压抑住本我。与心怀长寿希冀的普通人一样,孔子也有很浓厚的惜命求生的意识。“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齐”即斋戒,表现了孔子对礼一如既往的虔诚和重视;“战”指战争,凸显了孔子“仁者爱人”的人文意识;“疾”即疾病,反映了孔子对生命的珍重和爱惜。人们总习惯于把圣人的诸多优点附到孔子身上,所以不习惯谈论孔子身上所展现“凡人”的一面,而正是被人所忽略的“凡人面”折射出了孔子对源于天性的“本我”的认知和尊重。
孔子对超我人格的塑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仁”“义”的推崇和践行,二是对于“道”的坚守和弘扬。孔子认为,“仁”与“义”是君子必须拥有和践行的品性,只有心怀仁义,才能升华道德品格,丰富内心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成为“仁人”。同时还要践行仁义,只有将之付诸实践,才能将“内圣”之德延伸至邦国,达到“外王”的目的。因此,他强调对于仁义的坚持要超脱于本我的欲望之外,故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在义与利的对立中以义为上,舍利求义。甚至在特殊情况下,纵然惜生如孔子,也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要求自己能够超脱于个体生命之外,用实际行动维护、践行仁义。对于“道”的坚守和弘扬亦如此,不仅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摆脱对物质欲望的留恋而坚守“道”,还要把弘道视为己任,即使“知其不可”而仍要“为之”。
长久以来,由于对孔子“克己复礼”的刻板印象以及后世儒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变奏,人们形成了孔子乃至先秦儒学并不认可人的天性、欲望的认识。其实不然,孔子在强调克己复礼,追求内圣外王的同时并没有否定人的欲望、本能的合理性。相反,对于人们逐利求富的自然欲望,他是予以尊重和肯定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在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并没有否定“富与贵”等人欲,相反,他肯定人们对于富贵的追求和贫贱的厌恶乃是人之常情,是天性使然之举。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在“邦有道”的情势之下,“贫与贱,耻也”,应当把贫贱视为耻辱,继而发出了“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的慨叹。可见,孔子不但没有反对利、欲等人之天性,而且还鼓励有原则、正当地追求富贵荣华,反映了其对人的欲望、本能的尊重。
这些自然力介入的活动雕塑装置,让人感受到空气、风、地球引力所带来的微妙的作用力的存在,在一种循环往复又似乎无序的动态变换中,造型本体的形式美感应运而生。动态雕塑不是为动而动,而是用“最合适”的形态来转译空气与动力的形态,借以唤醒那些常常被遮蔽的——人们对自然的力量和自然界的循环规律的感知。
(2)P既不是循环群也不是广义四元数2群.若q∈π(o(g1))π(o(g2)),由(1)可知d(g1,g2)≤2.若g1是p元素且q∈π(o(g2)),存在m4∈N∗使得1<o()<qm,则g1~≃ g2,即d(g1,g2)≤ 3.若g1,g2均为p元素,g1~ g1µ ~ µ(∈ Q1)~ g2µ ~ g2.综合上述3种情况可知d(g1,g2)≤4.
基于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中西对“自我”涵义的理解也各有侧重。Traindis(1989)认为存在两种自我,即个人自我与公共自我(或群体自我)。他认为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自我(Private Self),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公共(Public Self)和群体自我(Collectivist Self)。中国更看重群体中的“自我”,从集体的角度去观照个人的存在;而西方则更突出个人自我,立足于独立个体对“自我”展开追问。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提到的,“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跟‘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它是互以对方为重,互相以对方为重。”
此外,孔子对“自我”的规范不仅体现在利欲的满足上,还渗透到了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孔子提倡在常见的君臣、父子、朋友关系中也应当遵循相应的社会规范。对于君,臣应“事君以忠”,忠于自己本分与职责,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还应“勿欺也,而犯之”,宁愿犯颜直谏,也不可欺瞒君上;对于父母长辈,子女则要“入则孝,出则弟”,不仅在温饱上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还要有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对于朋友,则要“谨而信”,诚信是立身之本,应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为人所践行。其实通观《论语》全书,不难发现言忠信、行笃敬等品质,孔子大多是针对君子阐发的。“君子”作为儒家行为规范的代表,其建构过程正映照了孔子对于现实存在的“自我”的理解和认知,它提供了在自然欲望和社会规范之间取得平衡,并能为人所仿效、学习的现实样本。因为“君子”的格局小可小至个人的修身、齐家,大则可延伸至治国、平天下,比起需要仰望的“圣人”,“君子”在现实中更容易实现。
在孔子看来,“君子”是现实存在的“自我”的依归,“内圣外王”的境界则是“超我”的外化表现。超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是道德化的自我,主要由行为规范、伦理道德观及价值取向等社会意识形态内化而来,它是社会文明规训的结果之一。弗洛伊德指出:“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为的主体。”超我,作为一味追寻快乐的“本我”的对立面,它遵循的是至善原则,一方面既时刻抑制着力比多驱动,另一方面又追求完善、完美的境界。正是因为孔子对理想人格“超我”的不懈追求,才能从争鸣的百家学者中脱颖而出,被后世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
2.语言表达应简洁且富有节奏。低年级学生在口语交际能力上的表现并不成熟,若绘本中存在结构比较复杂句子,学生很有可能难以理解,而这一问题也会导致后续阅读过程和写话训练的开展难以达到预期。针对这样的问题,教师应在对绘本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尽量选择语言具备一定重复性且结构简单的绘本。
因此,儒家文化在谈论“自我”的时候,其实指向的是“群体自我”,并习惯于把个人放置到由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而成的网络中去考察“自我”的存在。所以,不同于西方学者注重从形而上的角度对“自我”本体进行追问和思考,孔子习惯于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去考量“自我”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关系的坐标系中明确个人的定位。正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通过正名,“自我”才能明确自己在群体秩序中的位置,担当起个人的职责和践行义务。不单是普通人,连“士”也只有在宗族、乡党等群体中才能建构起对自我身份的认知,进一步发挥志士仁人的作用。《论语·子路》载有:“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自我”总是隐匿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导致了儒家的“自我”概念具有较大的兼容性和伸缩性。海外学者杨中芳把中国人的自我分为“个己”和“自己”,前者以个人身体为标志,树立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边界,乃成“个己”,等同于现代语境下的“个人自我”;后者则指把与个己联系紧密的他人都囊括进来,继而形成“自己人”集体,类似于“群体自我”。在“自己人”的集体中,孔子认为,应当遵循“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准则,不仅要形成对“仁”“义”“礼”等社会规范的统一追求,还要“毋我”,即“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包括不凭空臆测,不固执成见,不自以为是,不以自己的得失和利益为原则。除此之外,孔子还倡导追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见,孔子对“自我”的关注往往落脚于“群体自我”,侧重于论述“自我”在集体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鼓励弘扬“群我”意识时也不忘追寻“大我”境界。
二、异:对“群我”或“个我”的强调
余英时在《现代儒学论》中表示,于众多方面都存有明显分歧的中西文化,在文化模式上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本偏于群体论——今天西方人称之为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与西方近代主流文化之偏于个体论——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恰成鲜明的对照。”一般来说,集体主义文化突出强调集体和国家的第一性,认为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更多的从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在集体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考察个人的作用和地位。而个人主义文化则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单独的个体身上,强调个体的特殊性、独立性和自主性,认为集体虽由个体所组成,但在社会事务中,集体应以个人的幸福和需要为先。
然而作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个人,如果任由快乐原则的支配,让本我随意发泄,那么社会将会变得混乱无序。人心欲望的膨胀及其不可实现之间的矛盾将加剧,最终非但快乐得不到满足,还会招致焦躁和痛苦。因此,在本我和现实生活之间就需要“自我”作为协调而存在。“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过程的连贯组织;我们称之为自我。这个自我与意识相联系,它控制着能动性的通路——也就是把兴奋排放到外部世界中去的道路;正是心理上的这个机构调节着它自身的一切形成过程……自我还由此起着压抑作用,用压抑的方法不仅把某些心理倾向排除在意识之外,而且禁止它们采取其他表现形式的活动。”也就是说,自我虽然是从本我的基础上分化而来的(汲取原始的心理动力),但它通过压抑、投射、升华等方式调节了本我与实际、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并遵循现实原则,以合理的方式响应本我的需求。因此,孔子一方面认识到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承认了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要求人们通过正当的途径,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去获得利欲的满足。
孔子对“内圣外王”境界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了其建构理想人格“超我”的重视和努力。“内圣外王”的超我人格、肯定人欲的合理性的本我与以“君子”为现实依归的自我一起构造了孔子“自我观”的三重面相。这反映了孔子和弗洛伊德一样将“自我”视为一个可被不断建构、处于连续变化中的有机体,它不是一个稳定不居的实体,而是在生理上、心理上和道德上由多种力量角逐、联合而形成的动态平衡。并且由于受人类向善习性的影响,在变化生长的过程中,呈现出一股向上升华的趋势。
与孔子相异,弗洛伊德对“自我”的关注落脚于对单独个体的分析,他以“个人自我”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探讨了人们普遍拥有的三层人格结构。其实,无论是对梦的解析还是对潜意识的挖掘,他都是以个人为单位展开论述的。正是因为弗洛伊德对“个人自我”的侧重,所以他更关注源于天性、本能的“本我”,强调要给予“本我”合理的发泄空间,认为若过分突出良心、道德等至善原则对自我的规范,而忽略本我的释放,将会激起心理的焦虑信号,继而引发众多神经癔症。并且他还认为,蕴藏于本我之中的力比多,是人类生存、发展及建构文明所必需的内驱动力,人类所有高级精神文明活动本质上都是力比多的替代或升华。因此要正视和肯定欲望、本能在人格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即使是在弗洛伊德为数不多论及群体心理学的著作中,他也是立足于个体心理的变化来对群体心理进行解读、剖析,认为“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的联系”,依旧是从“个人自我”的角度开展相关论述。
可知,分别处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文化模式中的孔子和弗洛伊德虽然都谈论“自我”,但两人是各有侧重的。孔子习惯于把“自我”置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去谈论“群体自我”的应尽之责,而弗洛伊德则聚焦于对“个人自我”的分析,常以个体为单位探索人类所共有的心理系统和人格结构。
3.设定催款时间并及时催款,安排专员负责催款,到期未还款可以从负责人工资中扣除,直到还完为止;避免占用其他科研项目经费,保证科研项目资金得到合理的使用。
三、异:对“理想自我”的态度
弗洛伊德指出,“超我”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代表了社会道德,是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被长期约束、文明规训的结果之一。“超我”起源于“本我”,致力于把文明社会的种种规范内化为个体内在的道德标准,压制各种不被现实所接受的欲念冲动。所以,伴随着“超我”的形成,“个体如果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就会产生愉快的情感体验,即自我奖励;如果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就会产生良心谴责、内疚感和羞耻感,即道德焦虑。”引起道德焦虑不仅是“超我”的体现,还是加强对“本我”的约束和压制的重要途径。它把道德系统与是非判断连为一体,一旦人们做出有违道德的事情,于内,大脑会生成内疚、羞耻等负面情绪进行自我惩罚;于外,则会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道德谴责。长此以往,由于人们怀有对内疚、羞耻等负面情感的担忧和恐惧,为了避免惩罚的到来,大脑会释放出焦虑信号,形成道德焦虑。因此,通过焦虑机制,道德等文明社会的规范就达成了对本能的自然压抑,逐步从外在的行为标准内化为个体的人格力量,同时成功把个人纳入到现代文明的社会体系中。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发展限制了本能”,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背后所隐含的对生之本能的长久压抑是文明的“缺憾”,文明影响了人类对于原始幸福的追求,这是“超我”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弗洛伊德不同,孔子始终以肯定的态度仰望“超我”,他认为以“仁”“义”“德”建构起来的“超我”是高级的善。故“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一心向仁总是没有坏处的。正是因为“超我”代表了高级的善,所以孔子要求人们要积极主动地去实现“理想自我”,用实际行动来践行高级的善。这里它主要借用了道德心理的倡导功能,通过“促成人们将道德认知转化成实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机制”,让人们从价值取向和情感倾向上自愿选择或追求某一道德行为,并保有付诸实践的持久毅力。正如孔子所云:“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即使到了相对落后的地方也不能放弃对仁德的践行。除此之外,孔子还倡导要把对“超我”的仰望和追求内化为实际的行为规范或准则,个体应依靠自己的力量,主动去维护、施行仁德。唯有做到了“为仁由己”,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尚境界。
由此可知,弗洛伊德认为“超我”主要履行了道德力量的压抑功能,外在的道德规范通过生成道德焦虑而对内在的天性本能进行压制,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我”损害了个人对原始的快乐、幸福的追求。而孔子则凸显了“超我”所具有的道德德性的倡导功能,突出了道德规范在塑造儒家理想人格方面的重要地位和强大作用,通过彰显理想人格的至善至美来形成内在激励机制,感召人们践行和完善“理想自我”。
结语
孔子和弗洛伊德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代表,两人的“自我观”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虽然两者均观照了自我的三重面相,都对源于天性的“本我”、现实存在的“自我”以及作为理想人格的“超我”予以了一定的关注。但集体观念更强的孔子显然侧重于谈论“群体自我”,突显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而深受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熏陶的弗洛伊德则始终把目光聚焦于“个人自我”,看重在群体、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个人的本能、天性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两人对“群我”和“个我”的侧重影响了他们对待“理想自我”也即“超我”的态度。孔子把“超我”视为高级的善,于是倡导人们积极主动去践行仁义道德;而弗洛伊德则认为,“超我”对人性本能的压抑损害了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是文明社会的“缺憾”。通过孔子与弗洛伊德的“自我观”的对比观照,可窥见中西方语境中“自我”观念的异与同。
[作者简介]梁翠琴,暨南大学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
[责任编辑:张 玙]
标签:孔子论文; 自我论文; 弗洛伊德论文; 道德论文; 人格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伦理学(道德哲学)论文; 人生观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人文天下》2019年第9期论文; 暨南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