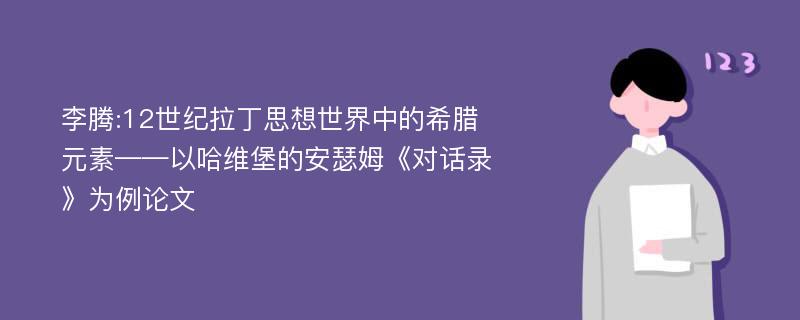
【拜占庭与欧洲中世纪】
提 要:12世纪中期的拉丁西方积极寻求古希腊哲学和神学,并将之融汇于自身的神学思想建构之中。作为12世纪为数不多的亲自出使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会神学家,哈维堡的安瑟姆的作品《对话录》中包含有大量希腊哲学与神学元素。这一方面来自于拉丁文献中既有的希腊智慧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源于当时最新的翻译成果。本文试图对安瑟姆作品中希腊元素的来源进行探讨,尤其侧重于分析纳西昂的格里高利对其思想的影响以及安瑟姆匿名征引的原因和可能来源,以这一个案分析12世纪中期拉丁西方与希腊东方的深层思想汇通。
关键词:哈维堡的安瑟姆;12世纪文艺复兴;希腊神学;纳西昂的格里高利
一、问题的提出与哈维堡的安瑟姆
在“12世纪文艺复兴”鼎盛时期,拉丁西方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在十字军运动和经院哲学初兴的背景下,大量希腊—拜占庭和阿拉伯翻译作品从12世纪中期开始涌入西欧,为拉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从两个重要的源泉获得生命力:部分地根植于已在拉丁西方显现的知识和思想,部分地依赖新学问和文献从东方的流入”。1[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夏继果译:《12世纪文艺复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关于大翻译运动,参见徐善伟:《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154页。哈斯金斯所指的主要是在哲学、科学和医学等领域,然而,在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神学思想往往是各种思潮碰撞的焦点,因此希腊教父等神学思想在拉丁思想世界的呈现似乎尚未受到哈斯金斯及其后学的相应重视。
在12世纪东西方神学思想交互中,哈维堡的安瑟姆(Anselm von Havelberg,约1095—1158年)值得特别注意。安瑟姆约出生于1095年,早年求学于列日(Liège)和拉昂(Laon)等地的主教座堂学校,1129年由马格德堡大主教诺伯特(Norbert von Xanten,约1080-1134年)祝圣为哈维堡主教后活跃于教廷和皇宫,成为12世纪普遍存在的廷臣—主教(courtier-bishop)。2 关于廷臣主教,参见C. Stephen Jaeger, “The Courtier Bishop inVitae from the Te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Speculum: A Journal of Medieval Studies, vol.58, no.2 (1983), pp. 291-325。113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洛泰尔三世(Lothar III,1075—1137年)与拜占庭皇帝约翰·科穆宁二世(John II Comnenus,1087—1143年)商讨结盟,派遣安瑟姆率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1 当时的历史背景见F. Chalandon, Les Comnène Études sur l’empire byzantin au XIe et au XIIe siècles, Tom. 2, Paris: 1912, pp. 166-169。安瑟姆一行人是从威尼斯经水路抵达君士坦丁堡的,见Translatio Godehardi episcopi Hildesheimensis, MGH SS, 12, p. 649; Jay Terry Lees, Anselm of Havelberg: Deeds into Words in the Twelfth Century,Leiden, New York and Köln: Brill, 1998, pp. 43-47。在去往君士坦丁堡途中,安瑟姆对希腊的宗教生活多有见闻,并同当地神学家交流,更于1136年4月在君士坦丁堡同尼科米底亚大主教尼基塔斯(Nicetas of Nicomedia)进行了两次关于东西方教会神学分歧的公开辩论。1149年,拜占庭使团在图斯库卢姆(Tusculum)拜访教宗尤金三世(Eugene III,1145-1153年在位)时提出了东西方教会合一的障碍,教宗特邀安瑟姆撰写《对话录》(Dialogi,希腊文转写作Anticimenon/Antikeimenon),详叙他在东方的见闻及其对东西方神学差异的意见与辩论,以作为教宗处理这一问题的参考。2本文中使用的《对话录》原文来自米涅版《教父文献大全》(Patrologia Latina)第188卷。另外,本文还参考了电子化的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藏15世纪抄本(Munich, BSB, Lat. 6488[anno 1437])、17世纪印刷本(J. L. D’Archery ed., Spicilegium sive collectio veterum aliquot scriptorum, Paris, 1677, 13: 88-252)征引仅注明米涅版的章节和栏数。
多数学者认为《对话录》并非真实辩论的精确复现。《对话录》与辩论发生间隔了十三年,没有证据表明安瑟姆保留有相关记录,且安瑟姆本人在前言中明确表示,他会“添加一些对信仰而言并不需要的东西,以能更适应此类作品”。3Dialogi, Pro.: 1141 A: “addens quaedam non minus fidei necessaria,quam huic operi congrua.”笔者所见唯一例外是埃文斯,她认为安瑟姆“尽其所能地回忆了与尼塞塔斯的辩论过程”,但未进一步解释,见G. R. Evans, “Unity and Diversity: Anselm of Havelberg as Ecumenist,” Acta Praemonstratensia, vol. 67 (1991), p. 43。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话录》大量引用、转抄甚至改写了拉丁和希腊教父的作品,更表明他在撰写期间参阅了大量文献,并按自己的意图“重构”了辩论过程。因此,《对话录》中对希腊—拜占庭思想的借鉴与创造性解读,为了解12世纪中期拉丁西方与希腊东方的思想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安瑟姆本人思想中的多元化倾向也促使他最终以希腊神学思想为根基构建了整部《对话录》。
既有研究从不同方面对《对话录》中的希腊—拜占庭思想进行过探讨。罗素(T. N.Russell)详细梳理了《对话录》二、三卷中的拉丁—希腊教父引文来源,但存在着“过度诠释”的倾向。4 T. N. Russell, “Anselm of Havelberg and the Union of the Churches. 1.The Question of the Filioque,”Sobornost, vol. 1 (1979), pp. 19-41; “2.The Question of Authority,” Sobornost, vol. 2 (1980), pp. 29-41.杰伊·里斯(Jay T. Lees)在对安瑟姆生平思想进行了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指出,安瑟姆根据当时的需要补充、改写了辩论过程,并探讨了部分希腊教父文献的来源。5Lees,Deeds into Words, pp. 226-230.布莱恩·邓克尔(Brain Dunkle)则详细探讨了《对话录》第二卷关于“和子句”辩论中对拉丁和希腊教父文献的运用,但因割裂了文本统一性,进而严重低估了希腊教父对安瑟姆的影响。6 Brain Dunkle, S.J., “Anselm of Havelberg’s Use of Authorities in His Account of the Filioque,”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vol.5, no.2 (2012),pp. 695-722.阿历克斯·诺维科夫(Alex J. Novikoff)的最新研究聚焦于中世纪的“对话”写作形式,认为安瑟姆的写作模式可能受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并将《对话录》视为经院神学初期发展的产物。7 Alex J. Novikoff, “Anselm of Havelberg’s Controversies with the Greeks: A Moment in the Scholastic Culture of Disputation,” in Averil Cameron and Niels Gaul eds., Dialogues and Debates from Late Antiquity to Late Byzantiu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gde, 2017,pp. 105-122.
然而,上述研究都相对割裂了《对话录》各卷之间的联系与内在统一性,且未能将《对话录》中对希腊—拜占庭思想的运用置于12世纪中期两种文化交融的广阔视野中审视。有鉴于此,本文以《对话录》整体文本为考察对象,探讨12世纪上半叶拉丁教士对于希腊—拜占庭思想的追索、理解与运用,在全面梳理《对话录》中基于拉丁文本的希腊知识后,将着重探讨希腊教父纳西昂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约329—390年)对安瑟姆思想的影响,并对安瑟姆匿名引用这位希腊教父的原因及其文献来源提出新的解释,为理解“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拉丁西方同希腊东方的交融碰撞与思想流动提供一个可能的新视角。
二、基于拉丁文本的认识
在中世纪时期,希腊语在拉丁西方并不流行,除意大利南部、西班牙等与拜占庭有密切交往的地区外,掌握希腊语的学者并不多见。如雷诺兹所说,“在整个中世纪,懂希腊语成了一种极为罕见的造诣,甚至外交联络有时也会因为缺乏合格的翻译而有所延宕”。1 [英]L. D. 雷诺兹、N. G. 威尔逊著,苏杰译:《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8页。关于中世纪拉丁西方的希腊语学习,参见Bernhard Bischoff,“The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vol. 36, no. 2 (1961), pp. 209-224。希腊文化对拉丁西方的影响却从11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而再度勃兴。到12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兰斯、沙特尔、拉昂的主教座堂学校,还是贝克、列日的修道院中,都产生了对希腊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浓厚兴趣。
这段话呈现了典型的拜占庭式神学思考模式。从弗提乌斯以来,哲学概念进一步渗透到拜占庭神学中,11—12世纪希腊教会探讨神学问题往往从逻辑入手,以理性原则讨论“圣灵发出”(the Processionof the Holy Spirit)更是弗提乌斯以来的传统。1Photios,On the Mystagogy of the Holy Spirit, translated by Transfiguration Monastery, Astoria, New York: Studion, 1983, pp.70-123; Kallistos Ware, “Tradition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in Later Byzantine Theology,” in Eastern Church Review, vol. 3, no.2 (1971),pp. 131-141.这既体现安瑟姆对关键哲学概念的把握,更表明了他熟悉当时东方教会的神学讨论模式。
在《对话录》中,安瑟姆刻意在对话结束时使用了希腊文,以强化记叙的真实性和戏剧化效果,两场对话分别以“Doxa si, ō Theos”(感谢主)、“kalos dialogos”(一场很棒的对话)以及“holographi”(都写下来)等作结束语。3Dialogi, II. 27; III. 22: 1210B, 1248B.当谈到希腊文在拉丁教会中的运用时,安瑟姆借“对话者尼塞塔斯”之口说:“我们必须不能轻易忘记——希腊人的权威曾经在拉丁教会中如此之高,以至于教会职位名称本身,或者庆典都是以希腊文奠定的。”4Dialogi, III. 14: 1231D. 之后列举了数十个教会职务、建筑、制度和节庆名词,这些都源于希腊文,但在米涅版、15世纪抄本与17世纪印刷本中都直接写为拉丁文。希腊文对中世纪拉丁词汇的影响,可参见Walter Berschin, Greek Letters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From Jerome to Nicholas of Cusa, translated by Jerold C. Frakes,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8,pp. 30-34。这都表明安瑟姆掌握了一些希腊语的日常对话和教会用语。
式中:x0,y0为平移参数;α为旋转参数;m为尺度参数;x2,y2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下的平面直角坐标;x1,y1为原坐标系下平面直角坐标[7];坐标单位为m。
在所有的学问当中,但特别是在高尚的神学中,我们必须防备polyarchia,也就是根源的多元性。事实上,最智慧的希腊人已经避免了这项(错误)。事实上,他们也避免了anarchia,也就是缺乏根源。另一方面,这些圣人也谨慎地界定了monarchia,亦即根源的单一性,并教导我们敬重地接受。因此,他们否认了上帝可以是双重根源的,这也就是polyarchos,如同他们所说的,这将只会引起(上帝之神性)内在的混乱。5这里的“principium”既可以译为“原则”,也可以译为“根源”或“本质”。Dialogi, II.1: 1165B: “In omni philosophia, et maxime in summa theologia cavendum est, et sapientissimi Graecorum hactenus vitaverunt dicere πολυαρχίαν, id est multa principia; vitaverunt etiamναρχίαν quae est sine principio; elegerunt autem et venerati sunt, et nobis venerandam docuerunt μοναρχίαν, hoc est unum principium.Idcirco autem noluerunt suscipere in Deo πολύαρχον, id est multa habens principia, quia quod habet multa principia, dixerunt esse litigiosum. Noluerunt etiam suscipere in Deo ναρχον, id est sine principio, quia hoc quod est sine principio, dixerunt esse inordinatum.”需要注意的是,在米涅版《拉丁教父大全》中将这些名词还原成了希腊文,而在15世纪抄本和17世纪印刷本中则都是以拉丁文拼写的,因此安瑟姆自己书写的版本中,这些名词应该都是以拉丁字母转写的。
根据《对话录》中的记载,安瑟姆本人并不懂希腊文,但对希腊哲学并不陌生。安瑟姆少年时曾在拉昂求学,亲炙经院哲学早期大师拉昂的安瑟姆(Anselm de Laon)、拉尔夫(Ralphde Laon)等人,拉昂的主教座堂学校在当时也是辩证法研究的重镇,其主要教学内容就是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方法,综合教父著述对《圣经》进行阐释。2 关于当时列日和拉昂主教座堂学校的教育,参见C. Stephen Jaeger, The Envy of Angels: Cathedral Schools and Social Ideals in Medieval Europe, 950-120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pp. 54-56; Cédric Giraud, Per verba magistri: Anselme de Laon et son école au XIIe siècle, Turnhout: Brepols Publishers, 2010,pp. 186-193。
安瑟伦在《对话录》建构中所使用的论辩技巧可能直接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启发。2 Novikoff, “Anselm of Havelberg’s Controversies with the Greeks,”pp. 116-117.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Topics, VIII. 159a)中谈到,公开场合的竞赛式辩论与教学中的辩论不同。对于前者而言,双方探究询问和相互理解后,获胜的捷径是为对方设置一个逻辑陷阱,使其自相矛盾从而驳倒对方。3《论题篇》的拉丁文本传承,见L.Minio-Paluello, “The Text of Aristotle’s Topics and Elenchi: the Latin Tradition,”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5, no. 1-2 (1955), pp. 108-118。关于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世纪西方的传播与影响,参见徐善伟:《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世纪拉丁世界的复兴及其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对话录》文本发展也符合亚里士多德在《论辩篇》中辩论技巧的运用。安瑟姆为尼塞塔斯设计的陷阱是,如果将“原则”(principium)理解为“根源”,则圣灵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就会陷入“多元论”错误;然而将“原则”理解为“本质”,则必然地陷入到“无源论”当中。因此,安瑟姆就可以宣称在“理性的位置”(propositas rationes)中,尼塞塔斯别无选择,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所承诺的效果。4Dialogi, II.3: 1170C. Novikoff, “Anselm of Havelberg’s Controversies with the Greeks”, pp. 117-118.然而,尼塞塔斯按同样的逻辑也可以推出圣灵“从自己发出”,因为在三位一体中圣灵与圣父圣子也是“同质”的。5Dialogi, II.20: 1194D-1195D.由此可见,在玄奥的神学探讨中,一个逻辑陷阱往往会造成另一个逻辑陷阱,而12世纪解决这一问题的普遍方式是将之追溯回教父权威。
《数据结构》是计算机科学的一门专业基础主干课程,主要研究非数值计算的程序设计问题中计算机的操作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操作等。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学会分析计算机所处理数据的结构特性,以便能为应用选择适当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设计相应的算法,并初步掌握算法的时间分析和空间分析技术[2]。
因此,安瑟姆在卷二第二十四节中专门汇集了希腊教父对“圣灵发出”的论述,分别引用了奥利金(Origen,182-254年)、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塔纳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296-373年)、蒂提姆斯(Didymus,313-398年)、以弗所大公会议(Council of Ephesus,431年)、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378-444年)和约翰·克里索斯托姆(John Chrysostom,347-407年)等关于“圣灵发出”的论述,指出这些希腊教父和大公会议的论断都是支持拉丁教会对于圣灵发出的解释的。6Dialogi, II.24: 1202D-1203C.
将这一问题置于12世纪上半叶希腊与拉丁文化交融互动的大背景下,可以提供更宏阔的视角,也能在缺乏抄本文献对照的情况下为探究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12世纪的拉丁世界非常热切地渴望阅读希腊教父的文本,12世纪希腊文本的增加得益于若干希腊人或者通希腊语学者的巨大努力。2 Maria-Thérèse d’Alverny, “Translations and Translators”, in Robert L. Benson and Giles Constable eds., 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 427; Albert Siegmund O.S.B., Die Überlieferung der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Literatur in der lateinischen Kirche bis zum zwölften Jahrhundert, Munich: Filser-Verlag, 1949, pp. 3-5, 292-293.在西西里岛上,国王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Sicily,1131-1166年)曾委派卡拉布里亚的亨利·阿里斯提普斯(Henry Aristippus of Calabria,约1105-1162年)翻译纳西昂的格里高利的全文。可惜的是,现有信息无法确认这一工作是否完成,迄今也没有发现这一翻译的任何文本资料。而且,从安瑟姆撰写的时代以及西西里王国同神圣罗马帝国、教廷的关系来看,安瑟姆也不太可能阅读到这份文本。3 关于这一翻译计划的简介,见Charles Homer Haskin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pp. 142-143。
在《对话录》中,尼塞塔斯很欣悦于安瑟姆引用希腊教父,反问他说作为一个拉丁人是否也接受希腊教父的权威?安瑟姆的回答极具典型意义,说“我不排除、鄙视、拒绝或判断圣灵所给予任何忠信基督徒的恩典,无论他们是希腊人、拉丁人还是其他种族,只要这种训导符合使徒训导,我都乐于去接受”,鲜明地体现出了12世纪拉丁教会的开放精神。1Dialogi, II.24; PL 188, 1204A-B.事实上,安瑟姆和阿伯拉尔一样,都倾向于认为拉丁与希腊教会在神学上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种种差异性解读往往是因为两种语言不同的表现力所造成的。在这个方面,另一位同名的坎特伯雷的安瑟姆则体现了对希腊人更为强烈的敌意。2 G. R. Evans, “Anselm of Canterbury and Anselm of Havelberg: The Controversy with the Greeks,”Analecta Praemonstratensia, Vol. 53(1977), pp. 158-175; Matthew Knell, The Immanent Person of the Holy Spirit from Anselm to Lombard: Divine Communion in the Spirit,Eugene: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0, pp. 24-42.
此外,安瑟姆在这部分征引中有两处重要添加:一处是论及蒂提姆斯作品是“由在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上都非常博学的哲罗姆所翻译的”;另一处则提到蒂提姆斯“因为眼睛受伤而视力有损”。借由这一线索,我们发现安瑟姆的希腊教父知识来源中又多了一位拉丁作家,亦即卡西多奥鲁斯(Cassiodorus,约490-585年)。卡西奥多鲁斯的《神圣与世俗学问指南》(Institutiones divinarum et saecularum litterarum)在数个世纪中为拉丁教会提供了关于亚里士多德和希腊教父的知识,在11—12世纪更是流行教科书。3 R.W. Southern,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173-174.这里恰恰提供了阿伯拉尔未曾涉及的信息——卡西奥多鲁斯写道,“这位蒂提姆斯,虽然在肉体上是一个盲人,但(正如)隐修主义之父蒙福的安东尼以先知的眼光所言,他拥有超性之眼,能够看到肉体之眼的力量所无法把握的。”安瑟姆此处正是化用了这句话,说“蒂提姆斯虽然失去了外在的视力,却完美地照亮了内部(内心)”,修辞手法如出一辙。4 文本对照参见:Cassiodorus Vivariensis, De institutione divinarum litterarum, V; PL 70,1116B; Dialogi, II. 24: 1203A。卡西奥多鲁斯的作品是中世纪时期了解蒂提姆斯思想的主要来源,参见Muckle, “Greek Works Translated Directly into Latin Before 1350(Continuation),” p. 102。此外,《对话录》第三卷中关于阿里安派(Arianism)的记叙,也全部源于卡西奥多鲁斯的《教会史》。5文本对照参见:Dialogi, III.6: 1216A-1217A; Cassiodoru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tripartita, V.17, VII.19, edited by Walter Jacob and Rudolph Hanslik, Vienna: Hoelder-Pichler-Tempsky, 1952, pp. 237-241, 416。
由此可见,安瑟姆在撰写《对话录》时依托于拉丁西方的既有文献,尤其通过阿伯拉尔和卡西奥多鲁斯使自己对希腊教父的表述更为全面。然而,安瑟姆对于希腊教父的运用远远不止于此,其中最重要也最有趣的就是《对话录》中匿名征引了纳西昂的格里高利的言论。
三、匿名神学家:纳西昂的格里高利
纳西昂的格里高利(Γρηγόριος Ναζιανζηνός/Gregory of Nazianzus)、大巴希尔(Basil the Great)和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并称“卡帕多西亚教父”,是希腊教会中最权威的教父之一。以弗所大公会议将格里高利援引为权威,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Council of Chalcedon,451年)更授予他“神学家”(Theologus)的桂冠,其思想还深刻影响了叙利亚教会、亚美尼亚教会和操阿拉伯语的东方礼教会。6 相关抄本传承的介绍,参见Frederick W. Norris et al., Faith Gives Fullness to Reasoning: The Five Theological Orations of Gregory of Nazianzus, Leiden: E. J. Brill, 1991,pp. 73-82, esp. 75-77。
在三位一体的神学论述中,格里高利在希腊教会中享有与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在拉丁教会中类似的地位,而且格里高利率先采用了“发出”(processio)一词来描述圣灵在三位一体中状态,在整个圣灵论的神学解释传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7 M. Edmund Hussey, “The Theology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Writings of St. Gregory of Nazianzus,” Diakonia, vol.14, no.3 (1979), pp. 224-233; Christopher A. Beeley, “The Holy Spirit in Gregory Nazianzen:The Pneumatology of Oration 31,” in Andrew Brain McGowan, Brain Daley and Timothy J. Gaden eds., God in Early Christian Thought:Essays in Memory of Lloyd G. Patterson, Leiden: Brill, 2009, pp. 151-162.格里高利的第三十一篇神学讲演中集中讨论了“圣灵发出”的问题,是东方教会的权威著述,直到15世纪才由彼得·包布斯(Petrus Balbus,1399-1479年)翻译为拉丁文。8 Agnes Clare Way, “Gregorius Nazianzus,” in Paul Oskar Kristeller,Catalogus traslationum et commentariorum: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atin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ies, Annotated Lists and Guides 2,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72, pp.138-140, 192; J. T. Muckle, “Greek Works Translated Directly into Latin before 1350,” Medieval Studies, vol. 4 (1942), pp. 33-42 and vol.5 (1943), pp. 102-114.然而,安瑟姆《对话录》中竟然以拉丁文大量征引了这部讲演中的内容,且从未提及这位希腊教父的名字,这份文献的来源和将格里高利匿名的诡异现象一直困扰着后世学者。
当年,莒沂县群众推着400辆小车运送5.5万公斤白面上前线,他们从沂蒙家乡出发,路径江苏、安徽,长途跋涉千余公里,吃完了随身携带的干粮和咸菜,也绝不吃车上的白面。郯城县民工李荣祥,在运粮途中自己带的地瓜叶窝头吃光了,就吃咸菜喝白水充饥,他推着几百斤重的木轮车行至苏北草桥镇时,竟饿昏了过去,醒来后喝点白水继续赶路,也舍不得吃满车干粮。
《对话录》的整个文本中到处可见对于纳西昂的格里高利的化用。首先,《对话录》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来自于格里高利。在论述圣灵同发于圣父和圣子时,安瑟姆认为这并非是“双重原则”的错误,并说“按照您的术语,即非δίαρχον(diarchos)或τρίαρχον(triarchos)”。在关于根源的理性论证上,安瑟姆的文本也与格里高利如出一辙。1如“pantokratoun”、“homoousion”和“heterousion”以及“sumpnoia”和“sunneusis”,分别参见Anticemenon, II.3, 10, 12:1169A, 1178D, 1181A;Gregory of Nazianzus, Ora., 29.3。希腊原文见Arthur James Masoned., The Theological Orations of Gregory of Nazianz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9, pp. 76-77; 英译本见Norris et al., Faith Gives Fullness to Reasoning, pp. 246-247。值得注意的是,格里高利文本中的若干希腊神学和哲学名词似乎从未被拉丁神学家使用过,格里高利的这部分内容更没有被此前的拉丁教会神学家征引。2 此处论断基于笔者对布莱珀斯(Brepols)出版社的“拉丁文本图书馆”(Library of Latin Texts-Series A and B)数据库的检索。在《对话录》卷一第二节中,安瑟姆颂扬圣灵给教会带来了生命并统治、管辖着教会,而这个圣灵则是存在的、多样的、独一的、可动的、雄辩的、无玷的、确定的、甜美的等等,这些颂词在卷二第十三节中又出现了一次,且都源于格里高利的这篇讲演,形容词的顺序都是一样的。3文本对照参见:Dialogi, I.2, II.13: 1144B, 1182C-1183B. Ora.31.29: Mason, The Theological Orations, pp. 183-185; Norris et al.,Faith Gives Fullness to Reasoning, pp. 295-297。
其次,《对话录》中的一些辩论技巧乃至论述“桥段”也来自于格里高利。最为明显的是当尼塞塔斯要求安瑟姆解释“发出”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时,安瑟姆的回应与格里高利在381年面对类似质疑时如出一辙。安瑟姆说:
一方面节约了授课医师的课上时间,把可能需要大段时间讲解的内容省略掉,只讲解内容的重点难点。所需上课时间灵活机动,不需要挤出大段时间影响正常的医疗工作。而规培医师也可以通过提前的线上学习,在课堂授课学习时快速掌握更多的知识。
向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圣父的非被生(Unbegottenness),以及圣子是如何被(圣父)所生,然后我将告诉你圣神是如何发出的!但是,在探究这些神圣奥迹(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会变得很愚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都是难以言喻的,超越了任何理性受造物的理解。它们的崇高和深奥超越了所有人类,甚至天使的理解。4Dialogi, II.5: 1171D: “Dic mihi quae vel qualis sit Patris ingeneratio,et quae vel qualis sit Filii generatio; et ego narrabo tibi quae vel qualis sit Spiritus sancti processio, et ambo insaniemus divina mysteria perscrutantes, et de his rationem investigare volentes, quae tanquam ineffabilia supra omnem intellectum rationalis creaturae esse dignoscuntur, et sua profunditate vel altitudine omnem sensum humanum, necnon et angelicum supergrediuntur”.格里高利在那篇神学讲演中则说:
幸运的是,《对话录》中很详细地介绍了安瑟姆与尼塞塔斯辩论时的三位翻译:威尼斯的詹姆斯(James of Venice,生卒年不详)、比萨的勃艮第奥(Burgundio of Pisa,约1110-1193年)和贝加莫的摩西(Moses of Bergamo,约1157年后去世于拉文纳)。这三位译者的名字在12世纪大翻译运动中熠熠生辉,而且他们都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直接从希腊文将古典希腊文本及神学著作译为拉丁文,其中许多译本直到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仍被当时的人文主义者视为典范译本。早在1128年,圣米歇尔山(Mont-Saint-Michel)修道院院长托里格尼的罗伯特(Robert of Torigni)就曾记录说,威尼斯一位名为詹姆斯的教士从希腊文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翻译为拉丁文,并对之进行了评注,其中所提到的作品正是前文提及的《论辩篇》。1Haskin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Science, p. 227. 关于威尼斯的詹姆斯,参见L. Minio-Paluello, “Jacobus Veneticus Grecus,Cannonist and Translater of Aristotle,” Traditio, vol. 8 (1952), pp. 265-294。贝加莫的摩西更是当时拉丁世界收集希腊手稿的第一人,语言、学术素养俱佳。在安瑟姆的介绍中,摩西的声誉更胜过其他两位,因此被选定为辩论时双方可信的译者。2Dialogi, II. 1: 1163C. 关于贝加莫的摩西,参见Charles Homer Haskins, “Moses of Bergamo,”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vol. 23, no.1(1919), pp. 133-142; idem,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Science,pp. 194-222。
最后,《对话录》受格里高利思想影响最深的地方是在卷一的神意历史观构建中,这也是前文提及的现有研究中被相对忽略的方面。安瑟姆在卷一中建立了三位一体在人类历史逐渐展开启示的框架,这一模式被前辈学者视为中世纪“历史进步理念”的典范,在中世纪拉丁神学传统中极具独创性。6 关于安瑟姆的“历史进步理念”的研究甚多,最主要的参见Milo Van Lee, “Les idées d’ Anselme de Havelberg s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dogmes,” Analecta Praemonstratensia, vol. 14 (1938), pp. 5-35;John Joseph Heneghan, The Progress of Dogma according to Anselm of Havelberg,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1943; K. Fina, “Anselm von Havelberg: Untersuchungen zur Kirchen- und Geusresfeschichte des 12. Jahrhunderts,” Acta Praemonstratensia, vol. 32 (1956), pp.69-101, 193-227; vol. 33 (1957), pp. 5-39, 268-301; R. W. Southern,“Presidential Address: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 2. Hugh of St Victor and the Idea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Fifth Series, Vol. 21(1971), pp.159-179; Walter Edyvean, Anselm of Havelberg and the Theology of History, Rome: Catholic Book Agency, 1972。《对话录》中说:
综上所述,给予鼻腔鼻窦良性肿瘤患者采用鼻内镜下低温等离子射频手术进行治疗,其治疗效果显著,且出血也较少,患者受到的损伤也小,极大的缩短了手术时间,对患者的术后恢复等具有重要作用。
旧约清晰地表明了圣父,但是没有明白地、而是非常隐秘地预兆了圣子。然后,新约清楚地昭示了圣子,但是只以一瞥投与圣灵,即解释了其(圣灵)神性。在那之后,圣灵被彰显出来,给予了我们关于祂神性更为明显的证据。1Dialogi, I.7; PL 188, 1147D: “Vetus Testamentum praedicavit manifeste Deum Patrem, Filium autem non adeo manifeste, sed obscure. Novum Testamentum manifestavit Deum Filium, sed submonstravit et subinnuit Deitatem Spiritus sancti.”
而在格里高利的第三十一篇讲演中,也有着非常相似的表达:
我在这里能够对上帝教义的演进做一个对比……在前一个事例中,变化来源于减省;而在这里,趋向完美的增进源于添加……以这种方式,旧约对圣父做了清晰的宣讲,而圣子则较为不清晰。新的盟约使圣子彰显出来,而对圣灵的神性只是一瞥。在现在这个时间,圣灵居于我们中间,并将它自己比以前更为清晰地显现给我们。2Ora. 31. 26; Mason, The Theological Orations, p. 178; Norris et al.,Faith Gives Fullness to Reasoning, p. 293.
据笔者所见,只有美国学者邓克尔对此处安瑟姆借鉴格里高利的说法持有异议,认为安瑟姆可能是受《新约·(伯多禄)前书》影响而独创了此类表述。3 Dunkle, “Use of Authorities,” p. 711.《新约·彼得(伯多禄)前书》1:20中说:“他(基督)固然是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的,但在最末的时期为了你们才出现。”这里虽然有“隐秘-显现”的意味,却完全没有建构旧约和圣父、新约和圣子间的关系,更没有延伸到圣灵。按,注释中《圣经》文本取自思高本,以其本部分的翻译更符合拉丁圣经的含义。但从这两处引文在各自文本中的上下文内容来看,邓克尔的说法明显站不住脚,且更能确定安瑟姆对格里高利的征引与借鉴。在格里高利的此处引文之前主要讨论的是上帝的恩典如何首先赋予犹太人,再扩展到外邦人。他认为,犹太人先是以献祭为核心,后来割礼逐渐取代献祭成为救赎的标志。在《新约》中,保罗宣称割礼也将被洗礼所取代,人类已经借由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与复活从罪恶中被救赎出来。这个从犹太人到外邦人、从献祭经割礼到洗礼的转变,恰恰正是《对话录》卷一开篇五个章节讨论的中心。安瑟姆在《对话录》中明显融合了保罗和奥古斯丁的思想,将之呈现为“偶像—律法—恩典”的转变。4Dialogi, I.3-5: 1144C-1147D.安瑟姆和格里高利一样,都认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神性是递进式展现的,只有当前者被完全理解之后,后者才能被理解。5文本对照参见:Dialogi, I.6: 1148A. Ora. 31. 26; Mason, The Theological Orations, p. 178; Norris et al., Faith Gives Fullness to Reasoning, p. 293。于是,奥古斯丁的线性历史观和格里高利的“三位一体”演进说在安瑟姆的《对话录》中融合了,并在卷一后面的章节中以这一复合框架重述了以拉丁西方为核心的教会发展史。
因此,《对话录》中既有对格里高利文字、修辞上的借用,更有思想框架上的整体移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安瑟姆的《对话录》体现了东西方神学思想的深度融合,使其可以被视为拉丁西方接受希腊教父思想而建构的文本。可是,为什么安瑟姆在征引的时候完全隐匿了纳西昂的格里高利的名字?安瑟姆又是如何得到这份在12世纪从未被其他拉丁人所获知的文本的呢?
四、东西方神学的隐秘嫁接
(一)安瑟姆对格里高利匿名的原因分析
对于安瑟姆刻意隐匿格里高利姓名的做法,此前学界主要有两派意见。
第一派的观点以法国学者米罗·冯·李(Milo Van Lee)为代表,认为希腊教父在12世纪时不像拉丁教会那样有权威,而且安瑟姆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征引的材料源自于格里高利,因此《对话录》中没有提及格里高利的姓名。6 Milo Van Lee, “Les idées d’ Anselme de Havelberg s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dogmes,” pp. 33-34; Berschin, “Anselm von Havelberg ( †1158), die Griechen und die Anfänge einer Geschichtstheologie des hohen Mittelalters,” in F. Kolovou Hrsg., Byzanzrezeption in Europa.Spurensuche über die Renaissance bis in die Gegenwart, Berlin und Boston: De Gruyter, 2012, pp. 37-40.
然而,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早在公元400年,也就是格里高利去世十年左右的时候,阿奎利亚的茹费努斯(Rufinus Aquileiensis,约340—410年)便将其九篇关于基督论的讲演翻译为拉丁文,并称赞他是“大公信仰的仲裁者”、正统的三一论和基督论教义之柱石。1 茹费努斯的翻译包括格里高利讲演的第2、6、16、17、41、26、27、38和39篇,见Augustus Engelbrecht ed., Tyrannii Rufini Opera,Pars I: Orationum Gregorii Nazianzeni Novem Interpretatio,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46, Vindobonae: F. Tempsky,1910, pp. 3-5。这个译本是目前所知15世纪前传承下来的唯一一部格里高利作品的拉丁译本,不仅使其在拉丁教会中享有盛誉,从古代晚期的哲罗姆到中世纪早期的约翰内斯·司各特·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以及约克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都从茹费努斯的译本中引用过格里高利。2 Neil Adkin, “Gregory of Nazianzus and Jerome: Some Remarks,”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S. 58, no. 37 (1991), pp.13-24; Ioannes Scotus Erigena, De divisione naturae: PL 122, 481B,586A, 772A, 804D; Alcuinus, Adversus harresin Felicis: PL 101,113C-114A.这都足以表明纳西昂的格里高利在拉丁教会中享有足够的权威,绝非寂寂无闻。然而,《对话录》中最为吊诡之处在于,其所引用的格里高利文本并未包含在茹费努斯译本中,且完全没有征引过这部译本的内容。
探究城市建筑工程中地质岩土勘察及地基的处理措施……………………………………………………… 袁佑明(7-62)
因此,以杰伊·里斯为代表的第二派学者认为,安瑟姆因为自知刻意曲解了格里高利的思想,所以对文本来源加以隐瞒。3Lees,Deeds into Words, pp. 197-198, esp. note 109.但就上述分析来看,安瑟姆的阐释并未与格里高利的思想相互矛盾,如果说有不同之处的话,只是安瑟姆在文本中试图调和纳西昂的格里高利与希波的奥古斯丁对圣灵的解读。具体来说,安瑟姆继承了格里高利对三位一体渐进的模式,但是却以奥古斯丁关于“圣灵是圣父和圣子之间永恒的爱和联系”的观念,维系了三个位格的内在统一:
要注意圣灵是圣父和圣子之间的爱,它们之间的联系,他们之间的交流,他们之间的爱。我会说,圣子的圣灵,(它)是真理,是真理的圣灵教导了所有的真理,而它自己(圣灵)则由作为真理的圣子所发出,它(圣子)奠定了福音,而且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为使徒们建立了信仰。4Dialogi, II.23; PL 188, 1201A-1201B: “Ecce Spiritus sanctus amor Patris et Filii, connexio amborum,communicatio amborum, charitas amborum; Spiritus, inquam, Filii qui est veritas, Spiritusveritatis docens omnem veritatem, qui et ipse procedens a Filio, qui est veritas,Evangeliumcondidit, et fidem secundum tempussuf ficientem apostolis instituit.”
更重要的是,安瑟姆对希腊—拜占庭神学、哲学也有很清晰的认识。比如,在第一场关于“和子句”的辩论中,安瑟姆详细地“复述”了尼塞塔斯的论述:
旋风分离器是通过气固两相流体从而实现旋转运动,并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将固体颗粒从气流中进行有效分离的设备。可能会由于工作人员的安装和调试以及运行经验不足等问题,导致旋风分离器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堵塞的情况,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并进行疏通操作,就会出现床温急剧升高,气温快速下降的情况,这样的情况非常容易导致床层或分离器结焦等问题,导致机组被迫停运。通过对75t/hCFB锅炉运用情况的分析和调试,总结出了有效解决和增加旋风分离器效率的办法。
同格里高利一样,安瑟姆将圣子视为真理本身;同奥古斯丁一样,他又将圣灵视为真理的教导者,从而赋予其由“圣子所发出”的意涵。5Ora. 31.26: Mason, The Theological Orations, pp. 178-179; Norris et al., Faith Gives Fullness to Reasoning, pp. 293-294. Augustine, De Trinitate, XV. xix.有学者认为,奥古斯丁最早关于圣灵是圣父圣子之间“关系”的学说,就是受到了纳西昂的格里高利的启发,参见Irénée Chevalier, OP, S. Augustin et la pensée grecque, Fribough:1940, pp. 141-152。换句话说,圣灵本身所传达的真理,也曾经由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所宣扬,耶稣本身所教导的真理就是圣灵,由此推衍出圣子发出圣灵的神学观念。这种调和性的阐释事实上触及了位格论和三位一体内部统一的张力,也是后来拉丁西方和希腊东方的圣灵论分歧的一个催生因素。6 C. A. Beeley, Gregory of Nazianzus on the Trinity and the Knowledge of God: In Your Light We Shall See L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07-209.
而在笔者看来,要解决安瑟姆匿名征引格里高利这个问题需要回到文本本身的产生语境和预设对象。首先,《对话录》是在教宗尤金三世要求下撰写的,性质是为教宗处理与希腊教会争议时提供参考,所以其预设读者是教宗本人和教廷中的高层教士。如果在处理这一敏感问题上过度依赖于希腊教父,很容易使教宗及其他高层教士产生误解乃至不满,这或许是安瑟姆刻意隐匿文献来源的原因。其次,《对话录》的主体虽是安瑟姆与尼塞塔斯的两次辩论,但安瑟姆所添加的第一卷实际上起到了统摄全局的作用。通过建立一种统一信仰下多样性发展的神学历史观,安瑟姆不仅表明东西方教会应当而且能够合一,并且也指向了当时拉丁教会内部因新兴修会林立而引发的统一危机,故而安瑟姆思想的理论基础正是格里高利的“演进”理念。如果直陈这些思想源自于希腊教父格里高利的新文本,而且是拉丁教会在历史上从未细致阅读、征引和评注的作品,也会使安瑟姆陷入一种两难境地。最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对话录》本身处理的是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谁享有更高权威的问题,如果说衡量的标准并非奠基于拉丁教父而是希腊教父的教诲,那如何来说明拉丁教会应当享有更高的权威呢?此外,安瑟姆毕竟不懂希腊文,可能也会担心自己对于文本的掌握、翻译和阐释中存有漏洞,通过匿名征引的方式避免授人以柄。
为了尽可能降低在房屋建筑过程中发生冷桥现象,目前国内很多建筑商在进行房屋构建层面,一般会采取保温层建设的方式进行该现象的规避。常用的材料为聚苯板,这种材料不仅能够更好的满足房屋保温需求,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起成本相对较低,使用范畴非常广泛。
因此,笔者认为安瑟姆正是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核心思想框架奠基于纳西昂的格里高利相关论述的情况下,才刻意避免提及这位希腊教父的名字,以隐匿的方式大量借用了格里高利此前未曾翻译为拉丁文的第三十一篇讲演。在这部既要阐述东西方教会分歧,又要回应拉丁教会内部多样性的文本中,安瑟姆已经提出了许多异于同侪的见解,为了尽量保证《对话录》为教宗和教会高层采纳,故而隐匿了纳西昂的格里高利的名字。
(二)格里高利的文本来源分析
那么,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份文本是如何翻译成拉丁文并传到了安瑟姆手中的呢?根据《对话录》中精确的翻译与征引,可以确定安瑟姆在撰文时手边就有这部译稿。在格里高利文本来源的问题上,近年来也有学者尝试提出新的解释。邓克尔认为,安瑟姆可能参考了尼塞塔斯·塞德斯(Nicetas Seides)的作品,因米兰大主教彼得·格罗索拉努斯(Peter Grossolanus)曾于1112年在君士坦丁堡与希腊教会神学家进行了一场类似的神学辩论,主要参与者尼塞塔斯·塞德斯撰写了题为《十一场对话》(λόγος Καʹ)的小册子,其中也“匿名地”引述了格里高利。1 Brian Dunkle, “Use of Authorities,”pp. 714-717.然而,邓克尔自己也承认仅有的两处文字相似并无法建立《对话录》与塞德斯文本之间的确定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前述的三位一体演进论等重要内容都没有出现在《十一场对话》中,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本小册子被译为拉丁文。
安瑟姆此处关于希腊教父的内容几乎都来自阿伯拉尔的《神学导论》(Introductio ad theologiam)。埃文斯曾认为他们可能拥有一个共同的文献来源,但从文本对照来看,安瑟姆无疑直接摘引了阿伯拉尔的论述。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阿伯拉尔后来对《神学导论》进行了多次修订并更名为《基督教神学》(Theologia Christiana),安瑟姆在此处参考的应该是最初版本。7 G. R. Evans, “Anselm of Canterbury and Anselm of Havelberg,”pp. 164-166。详尽的文本对照,参见Dialogi, II.24; PL 188,1202D-1203D以及Introductio ad theologiam, XIV.15; PL 178 ,1077A-1077D。因安瑟姆所提到的以弗所会议只出现在《神学导论》的最早版本中,而后来修订的《基督教神学》则对此没有提及,文本比对参见Abelard, Theologia Christiana, IV, in Buytaert ed.,Opera Theologica 2, pp. 333-334 (PL 178, 1302C-1303C); Introductio ad theologiam, XIV.15, PL 178, 1077A-1077D。事实上,安瑟姆不仅在对希腊教父的理解上基于阿伯拉尔,两人在学缘上也有明确交集。阿伯拉尔的《神学导论》完成于1124年(一说1121年),而安瑟姆直到1126年才离开拉昂。8 Michael Clanchy and Lesley Smith, “Abelard’s Description of the School of Laon: What it might Tell Us about Early Scholastic Teaching,”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vol.54 (2010), pp. 1-34.因此,安瑟姆不仅有机会阅读阿伯拉尔的作品,且很可能同窗共读,甚至有学者认为安瑟姆的开放、多元的思想倾向也得益于阅读阿伯拉尔的著作。9 Winfried Eberhard, “Ansätze zur Bewältigung ideologischer Pluralität im 12. Jahrhundert: Pierre Abélard und Anselm von Havelberg,”Historisches Jahrbuch, vol. 105 (1985), pp.384-387; Petrus Abaelardus,Introductio ad theologiam, II.15; PL 178, 1079D-1080B.
笔者认为,安瑟姆最有可能从他的随行翻译那里获得了格里高利第三十一篇讲演。因为安瑟姆的旅程有数月之久,且圣灵发出问题是当时东西方教会神学争议的核心,因此他很可能在旅途中与希腊神学家对话时获悉格里高利的这篇讲演是东方教会理解圣灵论的核心论述,并因此请求随行翻译将之译为拉丁文供其参考。
什么是“发出”?你向我解释什么是圣父的自生(έκπόρυεσθαι),我将给你一个圣子的被生和圣神发出的(合乎)自然的解释。然后,就让我们因为探究上帝的秘密而走向疯狂吧!我们是谁,有什么能力呢?我们甚至无法看到我们脚下的是什么,无法数清楚海中的沙子,数不清这个世界的雨滴和时日,更不用说进入上帝的深度。对于这种奥秘本质的解释,实在超越于任何语言文字。5Ora. 31.8: Mason, The Theological Orations, p. 155; Norris et al.,Faith Gives Fullness to Reasoning, p. 283.
2)任务负荷(Task Load Index, TLX)会增加疲劳感受(Multidimensional Fatigue Instrument, MFI)。
积极幸福感被视为最佳心理健康过程,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它是指人们对生活或锻炼的满意度与愉悦感,是衡量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A组为慢跑组,B组为慢跑与音乐结合组。由图1得知,慢跑组运动前后积极幸福感有显著性差异,积极幸福感的量表问题有“我感到伟大”、“我感到积极”、“我感到强壮”和“我感到非常棒”。慢跑的运动量较小,慢跑可以解释为放松跑,众所周知,运动对不仅对人的身体有积极影响,对心理也有积极作用。慢跑结合音乐组运动前后积极幸福感有显著性差异,其原因是,慢跑本身是一种放松运动,在慢跑的时候听音乐,可以缓解心理压力。慢跑组和慢跑结合音乐组相比较,积极幸福感无显著性差异。
然而,笔者认为最可能为安瑟姆提供格里高利第三十一篇神学讲演之拉丁翻译是《对话录》中提到的第三位译者比萨的勃艮第奥,主要理由有如下三点。
首先,1136年安瑟姆在拜占庭举行辩论时,勃艮第奥正担任比萨驻拜占庭的使节。根据记载,他是1135年由威尼斯沿水路到拜占庭的。3 关于勃艮第奥出使君士坦丁堡,参见Peter Classen, Burgundio von Pisa, pp. 30-33。因此,他很有可能从一开始就与安瑟姆同路而行并担任翻译,在安瑟姆与沿途的希腊神学家讨论时提供了格里高利这篇讲演的拉丁文本。
其次,与其他几位译者相比,勃艮第奥最热衷于神学作品翻译,且与罗马教廷关系密切。《对话录》是在尤金三世教宗的要求下撰写的,而这位教宗本人对希腊教父思想也非常有兴趣,曾要求勃艮第奥翻译了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的《论正统信仰》(De fide orthodoxa),勃艮第奥翻译的约翰·克里索斯托姆(John Chrysostom)《马太福音注解》(Homilies on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也题献给尤金三世,翻译底本则是尤金三世从安提阿宗主教处获得后转赠的。4 该书大约完成于1153-1154年,当时尤金三世已经去世了。关于这一译本的特点及其影响,参见Peter Classen, Burgundio von Pisa: Richter, Gesandter, Übersetzer, Heidelberg: Carl Winters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 1974, pp. 16-18; Irena Backus, “John of Damascus, De fide orthodoxa: Translations by Burgundio (1153/54),Grosseteste (1235/40) and Lefèvre d’Etaples (1507),”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49 (1986), pp. 211-217。此外,他还翻译过当时被认为是尼撒的格里高利所著之《论人的本性》(De natura hominis),这部文献直到15世纪末才被乔治奥·瓦拉(Giorgio Valla, 1447-1500年)鉴定为埃米撒的内梅西乌斯(Nemesius of Emesa,约390年去世)的作品。虽然在文献作者的考证上有所疏失,但这些神学翻译对彼得·伦巴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关于勃艮第奥在若干领域的翻译总结,参见Haskin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Science, pp. 206-209。
最后的一个重要证据是,13世纪神学家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e,1221-1274年)在其作品中同时征引了大马士革的约翰和格里高利的这篇讲演,并说“依靠的是勃艮第奥的权威翻译”。波纳文图拉研究的权威学者雨果·道森德(Hugo Dausend)指出,波纳文图拉此处提出了一个难题,亦即现在并未发现格里高利第三十一篇讲演在12-13世纪的拉丁译本。6 Hugo Dausend, “Die St. Gregor von Nazianz-Stellen in den Werken des hl. Bonaventura,” Franziskanische Studien, vol.3 (1916), pp. 151-160.虽然道森德没有意识到哈维堡的安瑟姆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引用过这篇讲演,但他的发现给出了一个旁证:很可能存在着一部勃艮第奥在12世纪完成、但现在已经失传了的格里高利第三十一篇神学讲演的拉丁译本。
虽然现有的拉丁抄本和史料还无法确定勃艮第奥翻译了格里高利的这篇讲演,但鉴于他浓厚的神学兴趣、扎实的希腊文功底以及同安瑟姆本人和教廷的密切关系,都使他成为了安瑟姆手中那份格里高利文本最有可能的来源。
结 语
依据前文所论,可以构划出如下图景:安瑟姆早年求学时期,就在拉昂的主教座堂学校中开始接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并从波爱修斯、卡西奥多鲁斯以及阿伯拉尔的作品中读到了希腊教父对圣灵论的阐述。在1135年从威尼斯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他通过与希腊神学家的对话获悉了格里高利的第三十一篇讲演是希腊圣灵论的权威文献,便在勃艮第奥的帮助下获得了该文献的拉丁译本。于是,他不仅在与尼塞塔斯的辩论时大量引用了这一译本,同时也将之带回西方,并在1149年撰写《对话录》时与其他著作一起,再次加以参考。最为重要的是,这份译本不仅为安瑟姆提供了希腊教会关于圣灵论的权威论证,更启发了他对三位一体演进观念的思考,但基于现实考量,他在《对话录》刻意隐匿了格里高利的名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话录》成为了12世纪拉丁西方隐秘接受希腊神学思想的范本。
进县团委工作不久,我作为三十岁以下的后备干部被选拔到另外一个县级城市进入市委常委班子,一晃数年,我已是这个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再也没有机会回过那个小镇了,只是时不时有些小镇的零星记忆从我脑海的角落里探出头来,静静地打量着我,尤其是桃花绽放的时候。但城里难得一见桃花。
在大翻译运动全面展开之前,拉丁西方已经重燃了对古典希腊思想的热情。在发掘传统拉丁资源方面,波爱修斯和卡西奥多鲁斯等传统拉丁文本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阿伯拉尔更从早期拉丁教父作品中辑录了大量希腊教父的论述,这些都体现出12世纪上半叶拉丁西方对希腊哲学、神学思想的积极探求。而在新翻译的希腊文献方面,并不局限于古希腊的哲学、科学作品,还包括了纳西昂的格里高利、大马士革的约翰、约翰·克里索斯托姆等人的神学著作。这些哲学和神学作品翻译,不仅填补了拉丁西方“缺失的传统”,更激发、催生了新的思想。
就拉丁西方的思想世界而言,12世纪上半叶最大的变动便是经院神学的发展。在其方兴未艾之际,就特别强调“异中求同”(concordantia discordantia)的理念,从而实现“多样而不冲突”(diversi sed non adversi)。这一路径随着大翻译运动的发展、大学等教育机构的确立以及拉丁西方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也逐渐走向了深化。甚至到12世纪中后期,当拉丁教会内部出现神学争议时,一些人甚至会主动寻求希腊神学思想资源以调和矛盾。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179年,一位来自德意志地区的匿名神学家访问君士坦丁堡时,希望从希腊神学传统中找到支持他们学派关于三位一体思想的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神学家专门提到了大巴希尔和纳西昂的格里高利,希望能获得这两位教父的译本,可见当时的拉丁人对于希腊教父相当熟悉。1 这封信的原本现存于剑桥大学(MS. Ii. Iv. 27, ff. 129-130v),抄录于Haskin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Science, pp. 210-212。
12世纪的拉丁西方并非静待文本的翻译,而是以一种自觉的意识积极寻求新思想的引入,以期碰撞出新的火花。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发展视角下来看,如果说阿伯拉尔的《是与否》(Sic et Non)主要是罗列历代教父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那么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则成为了对不同看法的综合性阐释,并依据理性逻辑、圣经文本和教父传承,形成系统性的解释,并最终建造起了经院神学的大厦。最为有趣的是,阿奎那在书中以“哲学家”来称呼亚里士多德,而以“神学家”来称呼纳西昂的格里高利,体现了对希腊文化的高度尊重。2对于阿奎那文本中纳西昂的格里高利思想之来源,学术界仍然缺乏探讨,有待于后续研究的深入开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泛包含着希腊哲学和神学资源的《对话录》,成为了拉丁—希腊文化在中世纪盛期交汇融合过程中的重要见证。
生育期过量灌溉会引起棉花过快,中度水分胁迫会导致棉花株高过矮(图1 a)。不同灌溉量棉花各生育期株高表现均为M3W4>M3W2>M3W3>M3W1,苗期各处理株高增长较缓慢,进入蕾期后棉花生长速度明显加快,株高在6月6日至6月26日增速较大,7月6日之后株高不再增长(M3W2处理除外)。
在上述分析条件下,根据RCS11样品色谱信息,以信噪比S/N=3计,得野黑樱苷检测限为0.1 μg/mL;以信噪比S/N=10计,得野黑樱苷定量限为0.2 μg/mL。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2.004
[作者李腾(1986年—),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34]
[收稿日期:2018年10月19日]
(责任编辑:王晋新)
标签:格里论文; 希腊论文; 神学论文; 教父论文; 教会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基督教论文; 教义论文; 《古代文明》2019年第2期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