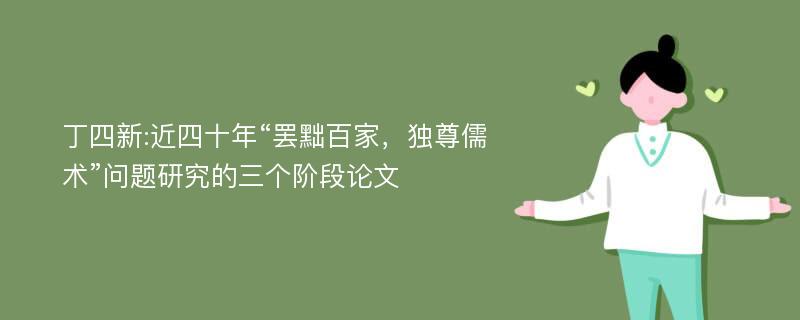
摘 要:以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10年代初为界,近四十年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初步反省期,学者论证了《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五月的观点,否定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而实行这一政策的说法;不过,对于这两句话究竟是由谁提出来的问题,学者普遍缺乏探索的兴趣。第二阶段属于深入辩论期,这两句话产生了两种用法,贬义用法认为它们在思想上属于专制性质,褒义用法则认为它们是对汉代学术思想政策的恰当描述。对于武帝或汉代是否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问题,学者提出了多种意见;同时一般不否认班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概括。第三阶段属于学术总结期,有多篇综述发表,有多位学者认为易白沙是这两句话的真正提出者。目前,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有待于形成新的学术共识。
关键词: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三策》;专制;汉武帝;易白沙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两句众所周知的口号。近四十年来,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其相关问题,学者发表了大量论文,展开了持久的学术反思和争论。这场争论和反思不属于政见之争,而属于时过境迁的学术“较真”,既解决了一些老问题,又提出了一些新问题。笔者在阅读了其中六七十篇论文后,仍感到有一些关键材料和关键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叙述,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解决,及我们对于汉代学术思想政策的评判。
一、引言
在近四十年里,学者发表了大量探讨和研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论文和文章,估计在100~200 篇之间①在2013年,郝建平统计发表的相关论文约为180 篇。在2015年,郭炳洁说:“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有上百篇之多。”参见郝建平《近30年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4 期,第103页);郭炳洁《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15年第8 期,第105页)。。另外,有大量书刊文章或论文在不知不觉中采用了这两句经典口号,“读秀学术搜索”(www.duxiu.com)显示,有近五万条之多。近十年来,有三篇文章专门综述了研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学术成果,它们分别是刘伟杰的《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1]、郝建平的《近30年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综述》[2]和郭炳洁的《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3]。这三篇文章都采用分类法,综述了1993-2005、1983-2012、1979-2014年间的研究成果,其中郝、郭二文的综述较为清晰和细致,在质量上明显胜过了刘文。郝氏的综述包括如下五个方面:汉武帝是否实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一政策何时实行,谁是这一政策的首倡者,以及独尊儒术的原因和历史作用是什么这五个问题[2]。郭氏的综述也包括五个方面: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信性的质疑和反驳,对这一政策的原因分析,历史过程考察,与董仲舒的关系,及其内涵和性质的重新诠释[3]。很容易看出,这两篇综述在子题上颇为相近,对讨论的问题都做了很好的概括。依此,郝、郭二氏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做了较为细致的综述。
由于学生的每天的课余时间、每天的课程不同,笔者估计每天能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大约总共有2h左右。笔者设置每天的时间为1到3h,且为了更精确地分析体验的差别,将问卷以四个时间段进行分组,分别是:1h以下、1~2h、2~3h、3h以上。再以五个流畅特征为变量,以这四个时间组别为标准,进行方差分析。
分类综述有一大好处,即能够很清晰地显示各子问题及学者对于这些子问题的回答。郝、郭二氏的分类综述正是如此。不过,他们的综述难以避免分类综述本身所固有的缺点或不足,即它容易忽视某一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主要问题,容易犯主次不分的毛病,容易不辨是非而杂陈各家意见。在笔者看来,学术综述的目的应当:一在于告诉人们研究的历程和不同层面;二在于告诉人们已取得的积极成果和正确结论;三在于告诉人们既往研究之不足,并进而指明问题之所在。在这三点上,郝、郭二氏的综述又是颇为不足的,甚至存在严重的缺欠。就当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郝、郭二氏忽视了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的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忽视了对人们研究此问题之动力的揭示,以及忽视了对主导意见的强调和对于不同意见之是非的评判。因此郝、郭二氏的综述实际上仅罗列了一堆看似“不偏不倚”的意见,但其是非然否则仍有待读者的甄别和评判。
笔者认为,当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1993年至21世纪1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21世纪10年代初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为初步反省期,第二阶段为深入辩论期,第三阶段为总结期。每一阶段各有其问题、内容和特点。
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对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计算得到锅炉各处烟气温度以及各换热器出口温度进而应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 分析。
二、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研究为初步反省期,主要围绕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于何时和汉武帝是否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两个问题展开。
曹爽和他的同党们,很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清除得一干二净。何晏也没能逃过一劫,史书上以最为简单暴力的三个字,记录了他的下场:
此一阶段的研究以学术争论为其基本特征,各方观点蜂出,纠缠不清,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某些错误的看法反而大获流行。不过,可以肯定,对于谁首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及其思想性质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学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和理解。同时,学者开始意识到,“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和“谁实行”这一政策,其实是两个问题。
需要指出,尽管于、施、岳三氏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正确的观点,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此后仍有许多人在“《天人三策》作于何时”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或者顽固地坚持司马光旧说③例如张大可维护建元元年说,见氏著《董仲舒天人三策应作于建元元年》(《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 期,第39-45页)。,或者别出心裁、提出新说,例如刘国民提出了元光五年说[11],孙景坛提出了班固伪作说④孙景坛说:“《天人三策》无疑是班固作的伪。班固为什么要作伪呢?……前两策非董仲舒所作是肯定的。……由于第三策是董仲舒与汉武帝晚年的书信,所以司马迁当时不可能见到,后来班固虽见到了,但却将它误成了董仲舒的儒学考试对策。这也许就是班固伪造《天人三策》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始动机和唯一根据。”见氏著《董仲舒非儒家论》(《江海学刊》1995年第4 期,第113-114页)。;而王葆玹为了论证“汉成帝建始二年开始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的观点,竟然轻率地同意了苏诚鉴的元朔五年说[12]。
就第二个问题,即就“汉武帝是否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问题,学者一般不否定这一政策的存在①例如张岱年先生即是如此。参见张岱年《汉代独尊儒术的得失》(《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 期,第1-4页)。,但在“何时实行”及“由谁实行”的问题上,王宾如、苏诚鉴、王葆玹和黄开国等人的意见不同。王宾如、王心恒认为“罢黜”和“独尊”都发生在“王莽当权之时”,而“不是武帝在位之际”[13];王葆玹认为发生在汉成帝建始二年[14];苏诚鉴、黄开国则重新肯定所谓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政策的流行意见[15-16]。王葆玹还认为:“汉武帝不但没有‘罢黜百家’,反倒使官方学术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更为宽广了。”[12]
与以上诸氏不同,赵克尧主要从内容和思想实质上直接批评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说法本身,认为它是难以成立的。他说,“罢黜百家”的提法“不够科学”“不符合实际情况”,从枢臣的构成来看汉武帝是兼收并用的,从人才观来看汉武帝是宽容“百端之学”的。又说,汉武帝实行的是“崇儒”,而不是“独尊儒术”的政策,而且其“崇儒”有始无终、有名无实,其本身即是汉代思想学术统一之过程的一个结果[17]。1991年,柳丝在一则补白短文中说道:“人们长期以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或‘独尊儒术’,是误记了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臆说的。……所谓‘表章《六经》’,也只是设置‘《五经》博士’,把几个传授《五经》的迂儒养起来,还替他们招了五十几名官费学生,叫作‘博士弟子员’,把《五经》传颂下去,并无禁止百家流传的措施。”[18]柳氏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流行说法其实是对班固《武帝纪赞》“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臆说和歪曲。赵、柳二氏的观点颇具价值,后来在第二阶段的研究和学术争论中一再得到重复。
(3)对施工中可能影响到的各种公共设施制定可靠的防止损坏和移位的实施措施,加强实施中的监测、应对和验证。同时,将相关方案和要求向全体施工人员详细交底。
总之,在此一研究阶段,虽然绝大多数研究者依循惯性仍然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作对汉代学术思想政策的恰当定性,但是部分学者表示了怀疑,提出了颇具价值的新观点:其一,肯定《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五月,而不是作于建元元年,从而否定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云云的流行意见;其二,质疑甚至否定武帝实行了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者又表现为两个方面:王葆玹、王宾如二氏认为这一政策分别是由汉成帝和王莽实行的,而赵克尧则针对这一政策本身,认为汉武帝实行的是“崇儒”而非“独尊儒术”、是包容“百端之学”而非“罢黜百家”的政策。柳丝沿着赵克尧的意见,进一步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乃是对班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说的歪曲和臆说。可以看到,在此一阶段,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见解。不过,距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真相的揭明尚远。绝大多数学者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所谓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乃是由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易白沙正式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究竟是由谁提出来的问题,学者在那时一般缺乏探索的兴趣,而付之阙如。
很多人知道滥用抗生素会引起细菌耐药,但英国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给婴儿用抗生素还可能引起湿疹。研究人员发现,1岁内的婴儿使用抗生素,患湿疹风险将增大40%,广谱抗生素对此的影响最大。该研究提醒医生及父母,给孩子用抗生素时应当谨慎。
情绪劳动的考核应该包括情绪劳动的考核对象、情绪劳动的考核主体、情绪劳动的核方式、情绪劳动的考核措施建议等方面。
三、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1993年至21世纪10年代初)的研究为争论深入期,以孙景坛与其他学者的争论为主线,人们继续讨论了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何时和汉武帝是否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两个老问题,同时开始思考这一政策的思想性质及探索它最先是由谁正式提出来的问题。此一阶段具有明显的争论特征,孙景坛是这场争论的发起者和主角。孙氏自为一方,管怀伦、吴九成、杨生民、张进、刘伟杰、江新、邓红等为另一方。从1993年至2010年,孙景坛至少发表了12 篇相关论文[19-30],其观点基本上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和《董仲舒非儒家论》二文中表达了出来。概括起来,孙氏的观点大体如下:(1)孙氏认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第三策乃是对董仲舒晚年诏对的拼凑,武帝的尊儒与董仲舒的建议无关。(2)孙氏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他不反对汉代存在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它不是由汉武帝或由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实行的,而是由汉章帝开始作俑的。(3)孙氏将汉武帝的政策与董仲舒的建议在性质上二分,认为后者可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概括之,且属于所谓“思想专制”性质。(4)孙氏认为,董仲舒不属于“儒家”,而属于“术家”。所谓“术家”,指申子、韩非、李斯等人物。(5)孙氏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或“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问题,他认为,既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属于子虚乌有,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真正基点。(6)孙氏反驳了管怀伦、刘桂生、张进和刘伟杰等人对于他的批评。
总之,在此一阶段,《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五月的说法进一步得到明确,而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讨论在不断深化和两极化,并产生了两种用法:一种用法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性质上属于专制,为贬义用法;另一种用法则认为,这两句不过是对汉代之学术思想文化政策的客观描述,它们只不过表明了汉武帝对儒术的尊崇和重视,为褒义用法。前一种用法为流行意见,后一种用法见于周桂钿、刘桂生、刘伟杰等人的论文,其中刘桂生为这两句话专门作了辩诬。进一步,汉武帝本人是否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有两种意见:一种肯定之,但有贬义和褒义之别;一种否定之,且在此否定意见中,又有只否定汉武帝却不否认汉代曾实行过这一政策(如成帝或章帝说),及完全否定汉代实行过这一政策的分别。不过,二说一般不否认班固所谓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的说法。
在此阶段,杨生民与周桂钿,陈新业与李玲崧还展开了两场小争论。杨生民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的建议,但汉武帝没有采纳,武帝实际上实行的是“尊儒术”“悉延百端之学”和兼用诸子百家的政策[40-41]。后来,他回应周桂钿的批评时还说道:“汉武帝只是在学术上‘独尊’了儒术,并未把这一方针贯彻到用人和政治各方面去。”[42]周桂钿不同意杨生民所谓武帝“并非独尊儒术”的说法,他说:“从汉代产生经学这一事实来看,汉代是独尊儒术的,以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为标志。”又说:“经学是如何产生的?那就是独尊儒术的结果……不能因为汉武帝任用了一些其他学派的思想人物,就否定他独尊儒术;也不能因为他独尊儒术,就否定他任用儒家以外的人物。”又说:“如果没有汉武帝独尊儒术,怎么会有经学产生?”[43]周氏肯定和维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说法。不过,很显然,他对于“独尊儒术”之思想性质的理解与梁启超、易白沙的定义不同。陈业新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早是由卫绾提出的[44],而李玲崧认为它最早是由董仲舒提出的[45]①李玲崧将作者“陈业新”错写成了“陈新业”,又将该文的发表期数误成《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 期。。此外,庄春波[46]、朱翔非[47]等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首先是由司马光提出来的。
管怀伦、吴九成、张进、刘伟杰、江新、邓红等人批评了孙景坛的观点。管氏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又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过程,“不仅是由八个形态各异的重大事件构成,而且充满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和波谲云诡的政治权谋”[31-32]。吴九成专文批评了孙氏所谓董仲舒不属于儒家而属于术家的观点[33]。张进认为孙氏所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的主张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所谓《天人三策》乃班固作伪等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因此在张氏看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绝非谎言[34]。刘伟杰认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儒术恰恰是从汉武帝时代起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的,并且董仲舒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并没有错。”[35]江新再次肯定和论证了董仲舒对策之年为元光元年五月,批评了孙氏所谓《对策》为班固伪作的说法[36]。邓红将孙氏的论调概括为“董仲舒否定论”,即从怀疑《天人三策》的个别文本到怀疑其与董仲舒的关系,推断其为班固的伪作,进而否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历史事件。邓氏指出,在日本,平井正士、福井重雅二氏此前已持“董仲舒否定论”。邓教授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并从方法论上对“董仲舒否定论”做了深入的批评[37]。此外,刘桂生从近代学者之曲解的角度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作了有力的辩护,其要点如下:(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统一入学、入仕的学术思想标准,不是统一社会的政策。(2)“罢黜”是罢之令归、斥之令退,而不是禁绝之意,所谓“独尊儒术”乃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地位之意,与欧洲的宗教专制不同;同时,孔子也不等于罗马教皇。(3)将“罢黜百家”等同于“禁绝诸子”,“独尊儒术”等同于“儒学专制”,支持这种思想的理论渊源于欧洲,直接来自日本,且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由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共同评定的。梁、章等人认为,汉武帝的“罢黜”与“独尊”就是学术文化上的独裁,它们是扼杀学术与思想自由,造成中华民族在近代濒于危亡的重要缘由[38-39]。通过如此这般的辨析和考证,刘桂生剥离了“专制”“独裁”的价值含意,而继续维护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流行说法。换言之,刘氏在一本正经地矫枉这两句话的原意,而使之向积极意义的一端滑转。可惜,他的学术考察漏过了易白沙,同时在方法论上没有反省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在此时代背景下此二语所具有的特定的思想性质。
现在看来,孙氏好辩。他撰写了大量论文,是此一阶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之讨论和争论的动力源头。孙氏有些意见是正确的或恰当的,如他认为汉武帝没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属于思想专制性质,应当从“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来看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等,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见解。但是,他有更多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荒唐的。例如,他主张汉章帝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俑者,认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董仲舒非儒家,宋明理学非儒家,及主张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等,这些观点或论调要么过于大胆,要么根据严重不足,它们很难说是正确的。
就第一个问题,大部分学者赞成由范文澜、侯外庐和翦伯赞主导的意见,认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于建元元年(前140年)[4-6]。不过,于传波、施丁、岳庆平三位开始了批评,认为由司马光提出的这一说法是不对的①司马光将董仲舒对策一事系于汉武帝“建元元年”条下,并在《通鉴考异》中说明了其理由。参见(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第2 册第549-556页《汉纪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1 册第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他们认为《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于氏说:“上述大量事实确凿地证明了董仲舒对策是在元光元年。”[7]施丁的主张更为具体,认为《天人对策》作于元光元年五月,并大力批驳了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和元光元年二月说,且详细地列数了古今提出或支持这四种说法的学者。他认为,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8]。应该说,“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何时”的问题在施丁那里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岳庆平[9]继续了于、施二氏的观点,不过他的批评针对的主要是苏诚鉴[10]所谓元朔五年的新说②苏诚鉴的元朔五年说,还遭到了周桂钿、于传波的批驳。参见周桂钿《董学探微》第10-1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于传波《从董仲舒在胶西的年代看元朔五年对策说》(《学术研究》1990年第3 期,第102-103页)。此外,周桂钿较早地维护了元光元年五月说。,有较强的针对性;同时岳文在资料上有所扩充。
四、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研究自21世纪10年代初至今。这一阶段为总结期:其一,学者开始了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整理和综述,其中郝建平[2]、郭炳洁[3]的综述较好;其二,在掌握诸说的基础上,少数学者开始跳出历史的限宥,把握关键问题和环节,展开了深度的学术辨析和研究。在此方面,宋定国、邓红、郑济洲、秦进才和笔者的观点值得注意。
在当代学者中,朱维铮是最先言及易白沙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关的学者,但是从其论述来看,朱先生的反省意识不强,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由易白沙首先提出来的这一学术要点②朱维铮《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见氏著《中国经学史十讲》第6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该文原题《经学史: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载《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2年上海图书馆刊行,写于1982年4月)。。另外,朱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于三十多年前,至今几乎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引用,影响极小。
近十年来,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宋定国、郑济洲、秦进才和笔者相继指出,易白沙是解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关键。宋定国指出,易氏《孔子平议》有一段话是“最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字”[48],换一句话说,易白沙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者由宋氏重新揭明了出来。不过,从其引述来看,他似乎没有亲自查对原文,所引易白沙文很可能转引自他人。郑济洲不但肯定易白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者,而且认为易氏的思想“带有强烈的新文化运动的情结”[49-50]。最近,笔者和秦进才教授都再次肯定易白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语的最先提出者。秦氏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词源学的系统考察肯定了此说③秦进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词语探源》第46页(《2018 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笔者则试图做系统的学术梳理和总结性的研究,全面辨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及重新判断汉代是否实行了儒学学术思想专制的政策①丁四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驳论(提纲)》(《2018 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165-170页)。。
总之,虽然学界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总结开始了一段时间,但仍有待深入研究,得出更为扎实的结论和形成广泛的学术共识。
五、结语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流行于现代中国的两句口号和咒语。近四十年来,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大体说来,目前对于此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如下成绩: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写于汉武帝元光元年五月,这是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汉武帝或汉代是否实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怀疑和讨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性质是什么,引起了学者的广泛思考和反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历史形成问题,受到学者的重视;而否定汉武帝实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意见,在学界似乎占据了上风。此外,部分学者还区别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董仲舒《天人三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班固《武帝纪赞》“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不同。
从总体上来看,在现有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成果中,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看法纠杂在一起,长期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难以达成共识。在笔者看来,以往的研究缺陷或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绝大多数研究者不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正来源,不知道这两句话最先是由谁及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2)研究者一般缺乏追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思想性质的兴趣,要么顺从流行说法,肯定其为专制,要么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一个恰当的客观描述,认为它很好地肯定和描述了儒学在汉帝国中曾经享有的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3)绝大多数研究者似乎不明“独尊”一语的词源及其思想内涵,不知董子《天人三策》“邪辟之说灭息”的语源出处。由此,他们也就难以准确地理解“独尊”和“罢黜”两词的含义。(4)多数学者不能恰当地处理和辨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独尊儒术”与“悉延百端之学”“汉家本以霸王道杂之”的关系。(5)绝大多数学者没有分辨“《六经》”与“儒术”的关系,对《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及汉代的知识体系缺乏必要的理解。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如下问题是仍然值得研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句话最先是由谁提出来的?其本意或思想性质是什么?进一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是否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而汉武帝是否实行了这一政策,且二者孰先孰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否是对汉武帝或汉代所实行的学术思想文化政策的准确概括,它是否与那时的历史实际相符合?或者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否可以应用于对汉武帝、董仲舒,或对汉代之学术思想文化政策的概括?与此相关,汉代是否实行了所谓儒家学术思想专制的政策?进一步,从语义和思想上来看,董仲舒所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班固所云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是研究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所要关注和讨论的学术重点②本节文字及笔者对于相关问题的新研究,参见拙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驳论》(待刊稿)。。
参考文献:
[1]刘伟杰.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J].南京社会科学,2007(2):70-76.
[2]郝建平.近30年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综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4):103-107,42.
[3]郭炳洁.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J].史学月刊,2015(8):105-112.
[4]史念海.董仲舒天人三策不作于武帝元光元年辨[N].天津民国日报,1947-09-01(6).
[5]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1 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8.
[6]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2 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6.
[7]于传波.董仲舒对策年代考[J].学术研究,1979(6):30-31.
[8]施丁.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辨——兼谈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J].社会科学辑刊,1980(3):92-101.
[9]岳庆平.董仲舒对策年代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116-122.
[10]苏诚鉴.董仲舒对策在元朔五年议[J].中国史研究,1984(3):90-92.
[11]刘国民.董仲舒对策之年辨兼考公孙弘对策之年[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3):83-89.
[12]王葆玹.天人三策与西汉中叶的官方学术——再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问题[J].哲学研究,1990(6):98-108.
[13]王宾如,王心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G]//《中国古代史论丛》编委会.中国古代史论丛:第7 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295.
[14]王葆玹.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J].哲学研究,1990(1):108-115.
[15]苏诚鉴.汉武帝“独尊儒术”考实[J].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1):42.
[16]黄开国.独尊儒术与西汉学术大势——与王葆玹先生商榷[J].哲学研究,1990(4):61-70.
[17]赵克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J].社会科学,1987(12):70-73.
[18]柳丝.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92.
[19]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J].南京社会科学,1993(6):102-112.
[20]孙景坛.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二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J].南京社会科学,1995(4):33-44.
[21]孙景坛.董仲舒非儒家论[J].江海学刊,1995(4):109-115.
[22]孙景坛.宋明理学非儒家论[J].南京社会科学,1996(4):28-34.
[23]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J].南京社会科学,2000(10):29-35.
[24]孙景坛.《董仲舒》一书中几个重要问题之商榷[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3(5):86-89.
[25]孙景坛.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5(6):33-39.
[26]孙景坛.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兼论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7(1):92-96.
[27]孙景坛.元光元年儒学考试的第一名是公孙弘——再谈董仲舒没有参加汉武帝时的儒学对策兼答张进(晋文)教授[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1):104-109.
[28]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新探——兼答管怀伦和南师大秦汉史专家晋文(张进)教授[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2):103-109.
[29]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新探——兼答管怀伦和晋文(张进)教授[J].南京社会科学,2009(4):90-96.
[30]孙景坛.中国古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是汉章帝——驳“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同刘桂生、刘伟杰、管怀伦、张进等商榷[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3):92-97.
[31]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J].南京社会科学,1994(6):13-18.
[32]管怀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过程考论[J].江苏社会科学,2008(1):192-195.
[33]吴九成.略论董仲舒的儒家属性——兼与孙景坛同志商榷[J].江海学刊,1996(4):115-118.
[34]晋文(张进).也谈“汉武帝尊儒”问题——与孙景坛教授商榷[J].南京社会科学,2005(10):41-46.
[35]刘伟杰.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J].南京社会科学,2007(2):70-76.
[36]江新.董仲舒对策之年考辨兼答孙景坛教授[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27-32.
[37]邓红.日本的董仲舒否定论之批判[J].衡水学院学报,2014(2):7-18.
[38]刘桂生.论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解[G]//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大史学:第2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16-132.
[39]刘桂生.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其成因[G]//袁行霈.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史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5-527.
[40]杨生民.略谈汉武帝的文治[J].炎黄春秋,2002(1):78-80.
[41]杨生民.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探——兼论汉武帝“独尊儒术”与“悉延百端之学”[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11-16.
[42]杨生民.论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也谈思想方法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2):124-128.
[43]周桂钿.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兼论思想方法诸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2):33-38.
[44]陈业新.“罢黜百家”语出何人[J].中国史研究,1998(2):169-170.
[45]李玲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语主考辨——与陈新业先生商榷[J].学术研究,1999(7):69-70.
[46]庄春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辨[J].孔子研究,2000(4):59-71.
[47]朱翔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辨[J].江淮论坛,2006(5):144-149.
[48]宋定国.国学纵横[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21.
[49]郑济洲.“规约君权”还是“支持专制”——重论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J].衡水学院学报,2016(2):46-52.
[50]郑济洲.董仲舒的“规约君权”理念——“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新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7-21.
Three Stage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Respecting Confucianism While Abandoning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DING Six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early period of 1990s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2010s as the boundary, the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respecting Confucianism while abandoning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The first stage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initial reflective period, during which some scholars have demonstrated the viewpoint that was put forward in Tian Ren San Ce, written in May of the first year of Yuan Guang (134BC) and negated the view that Emperor Wudi of the Han Dynasty adopted the policy suggested by Dong Zhongshu, but they generally lacked the interest in exploring who actually raised the two sentences.The second stage can be considered a period of in-depth debate, during which some scholars have interpreted the two sentences into derogatory usage and ameliorative usage.The former is considered as an despotic thought and the latter an appropriate description of the academic thought and policy of the Han Dynasty.And they raised many opinions on whether Emperor Wudi or the Han Dynasty adopted the policy of“respecting Confucianism while abandoning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In addition,they have generally denied Ban Gu’s generalization of “commending the Six Classics while abandoning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The third stage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eriod of academic summary, during which scholars have published many review papers,holding that Yi Baisha was the real person who raised the two sentences.The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respecting Confucianism while abandoning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still needs to be deepened and a new academic consensus needs to be formed.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while abandoning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 Tian Ren San Ce;despotism;Emperor Wudi of the Han Dynasty;Yi Baisha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9.03.002
作者简介:丁四新(1969-),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06)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9)03-0010-08
收稿日期:2019-02-19
(责任编校:卫立冬英文校对:吴秀兰)
标签:儒术论文; 罢黜百家论文; 董仲舒论文; 汉武帝论文; 这一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汉代哲学(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论文; 《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06)论文; 清华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