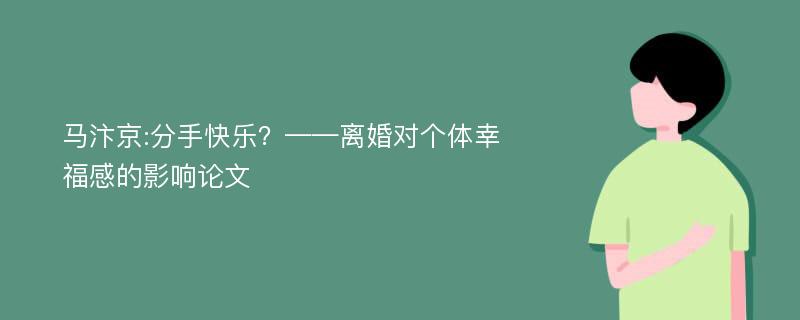
摘 要:中国离婚率连年快速攀升引发了广泛关注,但鲜有文献定量评估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文章首次采用追踪数据(CFPS)定量评估了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冲击及其动态演变,为理解中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提供了一个新观察视角。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离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短暂的负向冲击。按自评收入分为5个阶层,离婚当年人们遭受的幸福感损失,相当于从中等阶层下滑到最低阶层。离婚对幸福感不存在长期影响,离婚者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在离婚3年后即基本消失;是否再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男女、城乡、不同教育水平、有无子女等不同群组幸福感受离婚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但均呈现出共同动态演变趋势。考虑到离婚个体在离婚前夕的幸福感水平,应该已经低于其他已婚者,那么离婚应该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离异者幸福感恢复迅速表明在遭受巨大打击后,其心理上表现出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离婚主观成本相对较低,或是离婚率高企的重要原因。应该审慎地看待离婚对幸福感没有长期影响的结论,该结论不应被视为支持乃至鼓励中国居民离婚的经验证据。本研究仅显示:一个离过婚的人,也可以像常人一样幸福快乐。
关键词:离婚 幸福感 追踪数据
一、引言
中国离婚人数连年快速攀升引发了广泛社会热议和学界关注。大量文献对中国居民婚姻解体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陆益龙,2009;许琪等,2015;林莞娟、赵耀辉,2015;鲁建坤等,2015;郭婷等,2016)。然而,鲜有学者关注离婚对个体福祉产生的冲击。显然,离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升当事人幸福感。当人们被问及一生中遭遇到的重大变故时,丧偶和离婚始终高居榜首(Miller and Rahe, 1997)。在当今中国的社会评价中,离婚即使算不上“伤风败俗”,显然也不甚光彩。很多公众人物乃至普通民众,即使离婚多年也秘而不宣。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既然离婚意味着“劳民伤财”和负面社会评价,那么一向以“隐忍”著称的中国居民,其离婚规模为何屡创新高?
1.2.1 0 统计方法应用EpiData数据库管理软件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构成比(%)表示,采用X2检验,检验水准α定义为0.05(双侧)。
民政部《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大陆居民离婚人数从2002年117.6万对增长至2017年437.4万对。而2017年登记结婚人数则为1063.1万对。粗略算来,超过2/5的婚姻关系可能以离婚结束。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控制了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我们定量评估了离婚对人们幸福感水平的冲击及其动态演变。本文试图以离婚与个体主观福利关系切入,为当今中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成因提供一个崭新的观察视角。
离婚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识别有待深化。基于横截面数据关于婚姻状况与幸福感的研究,普遍发现了离异者幸福感水平明显低于已婚者的经验证据(Wade and Pevalin, 2004;Amato,2010;池丽萍,2016)。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认定离婚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毕竟,一段婚姻的延续还是解体,都是双方权衡利弊后的抉择。简单地进行横向比较,并不足以揭示婚姻解体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理性选择理论甚至认为,离婚理应增进了离异者幸福感水平(Becker,1992)。在婚恋自由前提下,两个理性人既然自愿结束一段婚姻,那么他们离婚潜在收益应该大于其潜在成本。
离婚对幸福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作为人生的重大变故,离婚对个体而言往往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艰难抉择。婚姻关系的解体通常是不可逆转的,其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在面临类似“百年不遇”抉择时往往进退失据,难以准确而全面地评估其可能导致的主观福利得失(Gilbert et al.,1998)。更何况,婚姻作为长期承诺普遍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容,其解体也往往掺杂了大量情绪因素。这可能导致人们在展望离婚后的幸福感水平时造成更为严重的误判。另一方面,即使在个体意识彰显的中国大城市,离婚与否也不纯粹是当事人的自主选择,而是掺杂了大量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Yan, 2015;范子英,2016)。
随着追踪数据的出现,有学者尝试探究离婚对欧美国家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使用德国面板数据Clark et al.(2004)研究发现,离婚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复杂的前导和滞后效应,且以女性观测值尤甚。基于美国面板数据的研究则更为丰富。使用1980,1983和1988三波追踪数据,Booth and Amato(1991)发现在离婚日期迫近时人们压力最大,但随着婚姻解体其精神压力最终缓解。Johnson and Wu(2002)将数据扩展至1992年新一波调查,发现精神压力得以缓解的现象仅限于离异后再婚样本。上述基于美国面板数据的研究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每次调查间隔较长而只能借助回溯式访谈获取的主观福利指标,难以准确地刻画婚姻解体时的个体幸福感水平。使用英国家庭追踪数据(BHPS),Pevalin and Ermisch(2004)考察了精神压力对离婚概率的影响。Gardner and Oswald(2006)使用BHPS数据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发现婚姻解体后第2年人们的幸福感水平就明显超过了离婚前1年。
然而,颇具特色的中国式离婚,其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异于西方发达国家。一是,中国式离婚很难说完全由夫妻双方自主决定。与发达国家践行婚姻个人主义的情形不同,即使《婚姻法》明确规定婚姻自主,中国式婚姻更多体现为两个原生家庭的互动。无论结婚还是离婚,都不能被视为纯粹的当事人个人选择。双方父母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往往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Yan, 2013)。二是,中国离婚成本相对较低。不少西方发达国家,都要求必须分居一段时间才能离婚。而在中国只要双方谈妥条件,即可以在工作日到民政部门登记解除婚姻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离婚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The Economist, 2016)。
本文首次采用追踪数据定量评估了离婚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动态影响,从而为解释中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即使有极少数文献聚焦于婚姻状况与中国个体幸福感的关系,也是基于横截面数据的观察。这显然难以准确地揭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甚至相关关系,也难以刻画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动态冲击。我们发现离婚对中国居民幸福感负面影响巨大但持续时间较短。其一,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负面冲击在婚姻解体初期非常明显。其二,中国居民离婚后幸福感水平恢复相当迅速。3年之后,有过离婚经历的人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在统计上已经不再显著。人们在婚姻解体后幸福感恢复迅速表明中国离婚的主观成本相对较低,这或是其离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⑦ 刘译: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one has heard the Way before the other and that one is more specialized in his craft and trade than the other-that is all.[4]38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本节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交代数据的来源与处理,然后是变量定义与设置,以及描述性统计;最后是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个体层面数据来自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CFPS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等在内的诸多研究主题,是一项具有广泛影响的多学科社会跟踪调查项目(谢宇等,2014)。CFPS调查覆盖的25个省、市、自治区,其人口占全中国总人口的94.5%,具有全国代表性。迄今已经发布了2010/2012/2014三期面板数据,其总观测值分别为33600,35720和37147个。本文主旨在于定量评估婚姻解体对个体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故将研究对象限定在至少结过一次婚的非丧偶观测值,共84271个。然后剔除掉幸福感缺失、拒绝回答或不适用的个体,最后用于分析的观测值共78485个。其中曾经离异样本2470个,已婚样本76015个,分别占比3.15%与96.85%。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有分析都限定在曾经结过婚且报告幸福感数据的78485个观测值中。
本文使用生活满意度表征被解释变量幸福感。在CFPS问卷中其题项是:“您对自己生活满意程度?”其答案选项共有5种,其中将“非常不满意”赋值为1,“非常满意”赋值为5。作为一个通用的度量主观福利水平问题,这与其他同类调查中相应问题“总的来说,您现在觉得自己幸福(快乐)吗?”类似。本文采用生活满意度而不是幸福感直接衡量个体主观福利,其理由有二。其一,幸福感更多反映了一个被调查者接受访问时相对瞬时的心理状态,而生活满意度是被调查者综合考虑生活多个维度之后做出的综合评估,反而是人们长期幸福感的稳定度量指标(Deaton and Stone, 2013)。其二,CFPS 2012年的追踪调查只剩下生活满意度指标。
表1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变量描述样本量年龄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均值(47.64),标准差(13.91),最大值(110),最小值(16)78481通货膨胀分别使用城乡CPI度量。均值(102.67),标准差(0.758),最大值(106.5),最小值(100.5)78080幸福感使用个体生活满意度度量;非常满意(20.88%);比较满意(29.75%);一般(35.67%);比较不满意(13.69%);非常不满意(4.42%)78485离 婚占比状况:曾经离婚(3.15%),其中离婚后再婚(1.45%),离婚后未再婚(1.70%);从未离婚(96.76%)78485离婚时间占比状况:对照组为从未离婚者(96.76%);离婚1年内(0.11%);1-2年(0.17%);2-3年(0.19%);3年或以上(2.37%);离婚时间数据缺失(0.40%)78485初 婚占比状况:初婚(93.64%);对照组:非初婚(2.73%);数据缺失(3.64%)78485育有小孩占比状况:育有小孩(93.16%);未育小孩(6.84%)78485户 籍基于国家统计局城乡分类标准;占比状况:乡村(54.07%);城镇(45.93%)78080工作状况状况占比:在岗(59.81%);对照组:未工作(39.17%);上学等不适用(1.02%)78485性 别状况占比:男性(48.76%);女性(51.24%)78485个体相对收 入占比状况:自高到低共5等,其中第3等为对照组(38.44%);第1等(2.17%);第2等(5.63%);第4等(25.64%);第5等(23.41%);不适用组(4.71%)78475教育水平状况占比:对照组为高中/中专/职高/技校(12.88%);文盲/半文盲(29.56%);小学(22.77%);初中(28.38%);大专(4.04%);大学本科(2.22%);硕士(0.14%);博士(0.01%)。76594
数据来源:宏观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3,2015),微观数据来自CFPS(2010,2012,2014)。
本文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为是否离婚以及接受问卷调查时距离最近一次离婚的时间。对个体而言,离婚的负面冲击究竟是一个可以适应的短期危机还是长期必须直面的灾难,至今仍未有定论(Amato, 2010),也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与法定离婚时间相比,个体感情破裂时间或分居时间是一个更理想的离婚时点变量。不过遗憾的是,CFPS问卷没有报告此类信息。于是,借鉴Gardner and Oswald(2006)我们采用了法定离婚时间作为婚姻解体的时点。然后,用个体接受调查的年份减去其上次婚姻解体的年份,得到距离上次离异的时间。为了更细致地考察离婚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本文根据个体接受调查时(最近一次)婚姻已经解体的时间,将其细分为4类:离婚第1年(d<=1;94个观测值)、离婚第2年(1<d<=2;145个观测值)、离婚第3年(2<d<=3;161个观测值),以及3年或以上(d>3;1967个观测值)。由于未知原因,少数离异者未报告婚姻解体的具体时间,本文为其设置了离婚日期缺失虚拟变量(d数据缺失为1,其他为0;523个观测值)。于是,以从未离婚者作为对照组,我们构造了5个虚拟变量。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样本中离异样本男性比例高出女性一截(56.45% vs 43.55%)。
图1比较了有过离婚经历的人与从未离婚者的幸福感状况。分别有30%和21.05%的从未离婚者认为自己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换言之,超过一半的从未离婚人士对自身生活状况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而那些有过离婚经历的人,报告幸福或非常幸福比例则分别为22.38%和15.97%。这意味着,其中经过婚姻解体的人仅有不到四成对自身生活状况比较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相应地,在曾经离婚群体中,报告非常不幸福者比例高达9.48%,同比是已婚群体的2倍。
图1离婚个体与已婚个体幸福感分布(%)
(二)变量设定
精准地评估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动态效应,对调查数据有着严格的要求。其一,必须是长期追踪数据。显然,婚姻的解体和幸福感感知,都可能受到性格等不可观测个体因素的影响。仅仅基于截面数据信息,难以对这些异质性因素进行有效的控制。其二,需要清晰地界定个体婚姻状况及其持续时间。CFPS追踪问卷详细询问了被调查者的离婚时间、是否初婚、是否有小孩等丰富的婚史信息。最后,我们对3次追踪调查进行交叉验证,最终获得了2470个曾经离婚的观测值,再婚与未再婚人数分别为1135和1335个,其中2121位报告了具体离婚时间。在3期调查期内即2010-2014年间,共有370个观测值经历了婚姻解体,折算为185对。这个数字与我国同期2‰-2.8‰离婚率有所出入,Gardner and Oswald(2006)基于英国追踪数据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现象。不过,本文无意在宏观层面探讨粗离婚率,而是在个体层面聚焦于婚姻解体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动态演变。
2.面板数据模型
图2 离婚时间与个体幸福感 (%)
主要控制变量包括是否初婚、工作状况、教育水平,以及相对经济地位。一是初婚变量。于是,本文以非初婚作为对照组,设置了初婚和信息缺失两个虚拟变量。二是教育水平变量。CFPS数据按照学历将调查对象细致地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直至硕士、博士等8类。本文以高中/中专/职高/技校作为对照物,设置了7个学历虚拟变量。最后是相对经济地位变量。CFPS迄今3次调查中共有15690个观测值没有报告个人收入数据。即使在报告个人收入的样本中,其收入中位值也是0。基于中国居民的研究显示,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能影响个体幸福感(Knight and Gunatilaka, 2011;Easterlin et al., 2013),于是本文设置了个人相对收入变量。具体地,问题为“您的收入在本地属于?”,共分为5档。我们将最高设置为第1档,最低设置为第5档。另外有在校学生等没有个人收入的观测值,为他们设置了“不适用”档。于是,以个人在本地相对收入为中等的第3等作为对照组,我们设置了包括“不适用”档在内的5个刻画个人相对收入的虚拟变量。综合考虑已有文献和数据可得性,本文没有控制绝对收入变量。
(三)模型与方法
本文使用了两种方法定量评估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动态效应。一是应用最小二乘方法的混合截面数据模型(Pooled OLS),二是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Fixed Effect Model)。
1.混合截面模型
借鉴Ferrer-i-Carbonell and Frijters(2004)研究思路,本文采用混合截面最小二乘方法考察离婚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Happinessit=α+βdivorit+θmacroit+rmicroit+u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Happinessit代表第i个体在t调查期自报的幸福感水平,本文用生活满意度衡量,其中最高为5,最低为1。i=1,2,. . .,n;t=2010,2012,2014。婚姻状况divor是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曾经离婚取1,从未离婚则取0。macro和micro都是向量,前者代表可能影响幸福感的通货膨胀、调查批次等宏观因素,后者则刻画了观测值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幸福感视为基数连续变量(cardinality variable)而不是定序变量(ordinality variable),其理由有二。其一,Ferrer-i-Carbonell and Frijters(2004)研究表明,对定量考察幸福感因素而言,使用上述两种变量衡量,其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都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其二,基数连续变量估计结果之间,在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上更具有可比性。事实上,不少探讨中国居民幸福的经济学文献,如 Knight and Gunatilaka(2011)都使用了类似准线性概率模型。
为了刻画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动态效应,如变量设定部分所述,本文按照距离(上一次)离婚的时间将曾经离婚的观测值细分为4类。加上未报告离婚时间者(k=6),以及作为对照组的从未离婚者(k=5),共6类。本文使用5个虚拟变量予以刻画。
(2)
在追踪调查中难免存在观测值流失现象。在CFPS数据3期调查中,相当比例的观测值至多出现了2次。我们尝试将分析对象限定在3期都出现的观测值,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报告在表4的Panel A部分。我国婚姻法规定最低结婚年龄为男性22岁,女性20岁,故离婚年龄不可能低于20岁。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男性的婚姻状况,而60岁是我国法定男性退休年龄。于是,我们尝试将分析对象限定在20岁与60岁之间的观测值,其回归结果报告在表4的Panel A部分。结果显示,无论离婚作为虚拟变量,还是其对个体幸福感的长期动态效应,Panel A和Panel B回归结果都与表3基准回归结果没有明显差别。
图2描绘了婚姻解体后个体幸福感发生的动态演变。在婚姻解体当年,有19.54%的个体觉得自己非常不幸福,同比高出从未离婚者3倍有余。到了婚姻解体的第2年,报告非常不幸福的比例已经降至11.03%,之后尽管有所反复但一直呈下降趋势。离婚当年将近1/5的人报告比较不幸福,比从未离婚者高出1倍,且在之后2年中变化不大。到了离婚第4年或更久之后,报告比较不幸福者比例下降至1/7。离婚当年仅有10.34%的人报告自己比较幸福,在第2年该比例即上升至18.38%,到了离婚第4年或更久,接近1/4的人报告比较幸福。
一是成立专业化测土配肥机构。针对土地流转加快,土地集中,大户出现,农资企业若能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专业化测土配肥机构,最好挂靠在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或协会框架之下,针对大户进行合同化服务,一对一定制式服务,是适应新形势的重大举措之一。现阶段,这样操作可能和传统渠道有一定冲突,但可以和经销商联手,合作共赢。配出的肥料一定是根据土壤肥力、作物需求和提高亩产而设计的精准配方,并且是散装掺混肥料,真正的BB肥,就像欧美发达国家的一样。当然,这样的机构成立,在中国最好是由专业市场营销策划公司进行策划和协助,企业组织运作,适当的商业广告投入是必须的,先打造一个样板市场,成熟后复制。
6种猕猴桃酒理化指标的测定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以红阳猕猴桃作为原料酿造的果酒酒精度最高(13.4%vol),维生素含量最高(244 mg/L),滴定酸结果最低(6.2 g/L);而以海沃德作为原料酿造的果酒酒精度最低(10.2%vol),总糖含量最低(5.7 g/L);以翠香作为原料酿造的果酒干浸出物最高(17.4 g/L),以徐香作为原料酿造的果酒干浸出物最低(15.6 g/L);以秦美作为原料酿造的果酒维生素含量最低(168 mg/L)。
首先,变压器的使用方面。减少变压器的无功损耗,合理选择变压器的负载率。变压器的节能体现在装设无功补偿、降低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几方面。提高变压器的系统功率。具体的实施方案为改进变压器的铁心制造工艺,选用低损耗的变压器;适当减少线圈数和绝缘面积,提高填充系数;当变压器使用量需求较大,需要的容量增大时,要设置静电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不能一味的追求变压器的容量,而忽视变压力的负载率。要根据实际需要对变压器的负载率进行合理的选择。
在另外一种定量识别策略中,本文使用了面板模型固定效应方法。该方法可以控制性格、偏好等不可观测且长期保持稳定的个体特征(λi)。显然,这些不可观测的异质性特征对个体婚姻状况和幸福感水平,都可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不过,仅使用横截面数据或混合截面数据,难以有效地控制上述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然而,本文所使用的CFPS追踪数据,可以有效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更精准地评估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净效应。相应地,具体回归模型设定为
Happinessit=α+βdivorit+θmacroit+γmicorit+λi+vit
(3)
应用固定效应方法处理面板数据时通常用到组内估计量(Within Estimator)和一阶差分估计量(First Differencing Estimator)两类模型。本文数据包含了3期追踪调查,若vit是独立同分布的,则组内估计量更有效率(Wooldridge, 2010)。故本文采用组内估计量进行估计。相应地,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动态影响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为:
(4)
三、主要发现
本节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给出了混合横截面估计结果;二是报告了控制个体不可观测特征后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平遥县汾河灌区片末级渠系配套工程青落村农渠混凝土防渗工程,原设计为底宽70 cm、高70 cm的梯形防渗渠6条(1-1农~1-6农),共计4 834 m。因占地等矛盾久调不决,致使青落村此6条农渠防渗工程无法实施,并且在项目村内其他区域也无法调整实施,项目村委同意将该部分渠道防渗任务调整到其他项目村实施。
(一)混合横截面估计结果
Panel C结果显示,剔除婚姻满意度最高的已婚观测值后,无论是否再婚,离过婚的人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水平差距都不大,且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统计检验。我们更关注离婚对该群体幸福感的动态效应。第(3)列结果显示不区分再婚状况时,剔除婚姻满意度最高的已婚观测值后,婚姻解体当年离婚个体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增加至-0.683(p=0.021);随着时间流逝其幸福感落差变小的速度也更快,到了婚姻解体第3年其幸福感落差已经基本消失。第(5)列和第(7)列结果显示,剔除婚姻幸福感最高的观测值后无论是否再婚,婚姻解体对个体幸福感都不存在的显著的长期负面冲击。人们在离婚3年后或更晚其幸福感甚至反超从未离婚者,不过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统计检验。
表2离婚与个体幸福感:PooledOLS
全样本离婚后再婚+从未离婚离婚未再婚+从未离婚(1)(2)(3)(4)(5)(6)(7)离婚-0.327∗∗∗(0.033)-0.235∗∗∗(0.033)0.00710(0.049)-0.435∗∗∗(0.038)距离婚的时间:共6组,调查时间-离婚时间(d年) 对照组为从未离婚者,最后一组代表离婚时间缺失第1年-0.658∗∗∗(0.14)-0.934(0.61)-0.638∗∗∗(0.13)第2年-0.426∗∗∗(0.089)-0.325(0.36)-0.440∗∗∗(0.096)第3年-0.347∗∗∗(0.088)-0.0979(0.21)-0.455∗∗∗(0.097)3年以上-0.200∗∗∗(0.038)-0.0126(0.051)-0.393∗∗∗(0.048)离婚时间缺失-0.0829(0.080)0.205∗∗(0.10)-0.508∗∗∗(0.11)相对收入 共5等,第1等最高,第5等最低;对照组为第3等;另有在校学生等没有收入者作为不合适组第5等-0.501∗∗∗(0.015)-0.501∗∗∗(0.015)-0.496∗∗∗(0.015)-0.495∗∗∗(0.015)-0.500∗∗∗(0.015)-0.500∗∗∗(0.015)第4等-0.302∗∗∗(0.010)-0.301∗∗∗(0.010)-0.299∗∗∗(0.010)-0.298∗∗∗(0.011)-0.299∗∗∗(0.011)-0.299∗∗∗(0.011)第2等0.287∗∗∗(0.019)0.287∗∗∗(0.019)0.285∗∗∗(0.019)0.285∗∗∗(0.019)0.290∗∗∗(0.019)0.290∗∗∗(0.019)第1等0.488∗∗∗(0.034)0.488∗∗∗(0.034)0.493∗∗∗(0.034)0.493∗∗∗(0.034)0.490∗∗∗(0.034)0.490∗∗∗(0.034)不适合-0.129∗∗∗(0.025)-0.129∗∗∗(0.025)-0.123∗∗∗(0.025)-0.123∗∗∗(0.025)-0.128∗∗∗(0.025)-0.128∗∗∗(0.025)年 龄-0.0131∗∗∗(0.0021)-0.0134∗∗∗(0.0021)-0.0129∗∗∗(0.0021)-0.0130∗∗∗(0.0021)-0.0120∗∗∗(0.0022)-0.0121∗∗∗(0.0022)年龄平方/1000.0226∗∗∗(0.0022)0.0228∗∗∗(0.0022)0.0224∗∗∗(0.0022)0.0224∗∗∗(0.0022)0.0216∗∗∗(0.0023)0.0217∗∗∗(0.0023)女 性0.123∗∗∗(0.0093)0.123∗∗∗(0.0093)0.122∗∗∗(0.0095)0.122∗∗∗(0.0095)0.127∗∗∗(0.0093)0.126∗∗∗(0.0093)城 镇0.0247(0.018)0.0245(0.018)0.0276(0.018)0.0274(0.018)0.0279(0.018)0.0278(0.018)育有小孩0.0418∗∗(0.019)0.0410∗∗(0.019)0.0458∗∗(0.020)0.0458∗∗(0.020)0.0404∗∗(0.020)0.0391∗∗(0.020)通货膨胀0.0406∗∗(0.017)0.0405∗∗(0.017)0.0409∗∗(0.017)0.0410∗∗(0.017)0.0414∗∗(0.017)0.0415∗∗(0.017)工作状况[0.42][0.43][0.42][0.46][0.80][0.80]健康状况[0.00][0.00][0.00][0.00][0.00][0.00]是否初婚[0.00][0.00][0.13][0.13][0.10][0.09]教育状况[0.00][0.00][0.00][0.00][0.00][0.00]省际固定效应无有有有有有有时间固定效应无有有有有有有样本量78,68876,07476,07474,79574,79574,97174,971R20.010.150.150.150.150.150.15
注:经过县区级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报告在括号内;中括号内是联合检验对应的p值,其中工作状况共3种:在岗、不在岗与不适用,对照组为在岗;健康状况为自评健康,共3组:健康、一般与不健康,对照组为一般;是否初婚共3种:初婚、非初婚与数据缺失,对照组为初婚;教育状况共8组: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对照组为高中;*,**,***分别代表在10%,5%与1%显著性水平;数据来源同表1。
是否再婚在离婚与个体幸福感关系中或许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政部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有340.44万人再婚,其中相当比例是离异后再婚。于是,本文以是否再婚为界,将曾经离婚者划分为两组并分别与从未离婚者进行比较,结果报告在第(4)列与第(6)列。第(4)列结果显示,对于已经再婚个体而言,曾经的离婚经历对其幸福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第(6)列所示,对于离婚后一直未再婚的个体而言,其幸福感要比从未离婚者低出0.441。这大致相当于个人在当地的相对收入,从中间的第3等滑落至最低的第5等所造成的幸福感损失。
离婚与个体幸福感之间关系有其动态演变过程。心理学主流文献认为,一次性冲击难以对个体幸福感造成长期影响(Frederick and Loewenstein,1999)。亦有研究表明,遭受严重伤残等重大冲击后个体幸福感会回升但很难恢复至初始水平(Oswald and Powdthavee,2008)。为了更全面地考察离婚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本文根据个体接受问卷调查时距离上次婚姻解体的时间,将所有离异样本和已婚样本划为6类,具体方法见数据与变量部分。于是,以从未离婚者作为对照组,我们构造了5个虚拟变量。第(3)列结果显示,与从未离婚者相比,人们在婚姻解体当年幸福感水平最低(-0.658),第2年已有较大程度恢复(-0.426),但一直到第4年甚至更久之后,其幸福感水平与从未离婚者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0.200);且这些幸福感水平落差全部在统计上高度显著(p< 0.001)。第(5)列结果显示,对已经再婚个体而言,在上次婚姻解体当年遭受了可观的幸福感损失但恢复非常迅速,到了离婚的第3年其与从未离婚者的幸福感差距就已经基本消失。第(7)列结果则意味着,对离婚后一直未再婚者而言,其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差距,虽然也随着时间流逝逐渐缩小但仍非常可观,且在统计上高度显著(p<0.001)。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基于混合截面的估计结果仅表明:与从未离婚者相比,(未再婚)离异个体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幸福感落差。显然,离过婚的个体与从未离婚者之间,除了婚姻状况,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相当一部分差异属于性格、人生观等不可观测的异质性特征。这些不可观测特征通常具有长期稳定性,且有可能在婚姻状况和幸福感感知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Wassmer et al., 2009)。仅使用横截面数据,往往难以有效地控制这些个体特征的影响。若采用面板方法固定效应模型,则就可以比较好地处理这一难题。
(二)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表3报告了离婚与个体幸福感关系面板数据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第(2)列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一系列影响幸福感的个体特征和宏观变量,以及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离过婚的个体幸福感水平明显较低(-0.220),且在统计上显著(p=0.011)。这里同样将伴随婚姻解体而呈现出的幸福感落差与相对收入变动进行比较。表3第(2)列回归结果中,个人相对收入从中间的第3等上升至第2等,其幸福感水平可望提高0.209,若下滑至第4等,幸福感水平则将下降0.208。我们也尝试按照是否再婚对曾经离婚者进行分组,结果分别报告在第(4)列与第(6)列。结果显示,与从未离婚者相比,离婚后再婚个体的幸福感落差很小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p=0.57),而离婚未再婚观测值则呈现出明显的幸福感落差(p=0.015)。这也许意味着,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负面冲击,主要由离婚后未再婚的观测值驱动。
ofo后又通过抵押动产(单车)的方式获得阿里17.7亿元贷款。“这是个折中方案,阿里给了一些现金救急,借款不需要滴滴签字。但这需要签对赌协议,ofo需要在一年内盈利1000万元。”Raven说,从目前的情况看,这几乎不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使用了CFPS三波追踪数据,但个体层面时间跨度至多也仅有4年。所以,户籍状况、教育程度、是否有小孩、是否初婚等等变量短期内变化极小且有可能是测量误差导致,故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中就不再予以控制。当然,为了保障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下文会进行相应的分组子样本回归。另外值得说明的是,表3回归结果与表2回归结果使用的是同一个数据集,但略有区别。由于应用面板方法控制个体固定效应要求观测值至少出现2次,所以在表3和后文表4回归结果中不再包含仅在1期调查出现的个体。还有就是,由于观测值在追踪调查期间出现了跨地区流动,故聚类稳健性标准误矫正在技术上无法实现,故使用一般性的稳健性估计。
第(3)列报告了离婚对个体幸福感动态影响的全样本估计结果。婚姻解体初期对个体幸福感冲击巨大,但3年后即基本消失。与从未离婚者相比,人们在婚姻解体当年(d<=1)幸福感落差相当明显(-0.448),且在统计上显著(p=0.014)。这里同样跟个体在当地相对收入变动进行比较。在该列回归结果中,一个人相对收入水平从中间的第3等,上升到最高的第1等,其幸福感可望提升0.373;若下滑至最低的第5等,其幸福感则下降0.347。这意味着,个体在离婚当年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比相对收入从中间位置下滑至最低水平还要大。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离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以精神压力视角看,在一段蕴含长期承诺的关系突然结束时,人们最初的反应往往是愤怒、纠结与不甘。这些负面情绪在短时期内的集中爆发,会在极大程度上恶化人们的身心健康(Perlin et al., 2005)。社会支持论者则强调,婚姻提供了包括陪伴、日出照顾以及情感支持等多种收益(Peters, 1986)。然而,婚姻关系的解体,意味着上述已经习以为常的婚内多种收益在短期内迅速归零。这种始料不及的外部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恶化人们的生活体验,与从未离婚者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幸福感落差。此外,婚姻结束时人们往往会失去将近一半的社交圈子。雪上加霜的是,并非所有与离婚人士亲近的人都会提供期待的情感支持,Stewart et al.(1997)显示将近一半的离异者报告称不少亲友并不赞成他们分手。与从未离婚者相比,到了婚姻解体的第2年人们幸福感的落差已经缩小至-0.286,不过仍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在离婚后的第3年,他们之间的幸福感落差再次大幅缩小,且在统计上已经不再显著(p=0.291)。离婚第4年或更久之后(d>3),离过婚的人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在数值上相差很小(-0.062),其在统计意义上更是没有差异(p=0.534)。
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动态效应与个体是否再婚有关。第(5)列展示了与从未离婚者相比,离婚后再婚个体幸福感水平的动态演变。由于离婚当年或第2年就再婚观测值非常稀少(分别为4人和14人),其代表性不够充分。此外,离婚后不久即再婚的观测值,出于某种考虑,更有激励不报告离婚时间。一个间接证据是,该列离婚时间缺失变量系数为0.518,且至少通过了显著性为1%的统计检验。通过比较他们离婚第3年或之后的幸福感变化,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婚姻解体对后来已再婚观测值的幸福感并没有长期的负面效应。
BIM技术应用主要分为前端信息处理及末端技术控制两个方面,前端信息处理即根据工程施工要求,对工程设计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并结合现有的工程建设设计资料,对可能发生的工程建设问题进行预估,将工程建设设计方案以立体化形式进行呈现,确保相关的工程建设问题能够更为直观的呈现在技术人员面前。末端技术控制的优势在于,对各个施工环节能够进行合理的管控,并及时的对相关工程质量及安全问题进行调整,主要应用于工程施工阶段的技术管理,使工程施工技术管理更为规范,为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有效的技术管理支持。
表3离婚对幸福感的影响:PanelFE
全样本离婚后再婚+从未离婚离婚未再婚+从未离婚(1)(2)(3)(4)(5)(6)(7)离 婚-0.262∗∗∗(0.089)-0.220∗∗(0.087)-0.0972(0.17)-0.231∗∗(0.095)距离婚的时间:共6组,调查时间-离婚时间(d年) 对照组为从未离婚者,最后一组代表离婚时间缺失第1年-0.448∗∗(0.18)-1.315(1.042)-0.266(0.17)第2年-0.286∗∗(0.13)-0.379(0.48)-0.237∗(0.14)第3年-0.136(0.13)-0.182(0.24)-0.0937(0.15)3年以上-0.0624(0.10)0.0394(0.18)-0.186(0.12)离婚时间缺失-0.402∗(0.24)0.518∗∗∗(0.15)-0.494∗∗(0.27)相对收入 共5等,第1等最高,第5等最低;对照组为第3等;另有在校学生等没有收入者作为不合适组第5等-0.347∗∗∗(0.014)-0.347∗∗∗(0.014)-0.343∗∗∗(0.014)-0.343∗∗∗(0.014)-0.346∗∗∗(0.014)-0.346∗∗∗(0.014)第4等-0.208∗∗∗(0.011)-0.208∗∗∗(0.011)-0.206∗∗∗(0.011)-0.206∗∗∗(0.011)-0.207∗∗∗(0.011)-0.207∗∗∗(0.011)第2等0.209∗∗∗(0.017)0.209∗∗∗(0.017)0.211∗∗∗(0.018)0.210∗∗∗(0.018)0.213∗∗∗(0.018)0.213∗∗∗(0.018)第1等0.373∗∗∗(0.032)0.373∗∗∗(0.032)0.373∗∗∗(0.032)0.373∗∗∗(0.032)0.379∗∗∗(0.032)0.379∗∗∗(0.032)不适合-0.0710∗∗∗(0.024)-0.0707∗∗∗(0.024)-0.0646∗∗∗(0.024)-0.0647∗∗∗(0.024)-0.0717∗∗∗(0.025)-0.0713∗∗∗(0.025)通货膨胀0.0267∗∗∗(0.0098)0.0268∗∗∗(0.0098)0.0267∗∗∗(0.0099)0.0267∗∗∗(0.0099)0.0274∗∗∗(0.0099)0.0276∗∗∗(0.0099)工作状况[0.23][0.24][0.22][0.22][0.27][0.28]健康状况[0.00][0.00][0.00][0.00][0.00][0.00]个体固定效应有有有有有有有时间固定效应有有有有有有有样本量72,26071,88971,88970,73870,73870,85570,855观测值数29,07329,04629,04628,67728,67728,71728,717R20.080.110.120.120.120.120.12
注:同表2注。
表4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样本敏感性分析
全样本离婚后再婚+从未离婚离婚未再婚+从未离婚(1)(2)(3)(4)(5)(6)(7)Panel A:3期调查都出现的观测值离 婚-0.290∗∗∗(0.11)-0.262∗∗(0.11)-0.117(0.28)-0.240∗∗(0.11)距离婚的时间:共6组,调查时间-离婚时间(d年) 对照组为从未离婚者,最后一组代表离婚时间缺失第1年-0.511∗∗(0.20)-1.323(1.24)-0.297(0.19)第2年-0.203(0.14)-0.127(0.68)-0.190(0.15)第3年-0.179(0.15)-0.0861(0.26)-0.113(0.17)3年以上-0.106(0.12)0.313(0.25)-0.237∗(0.14)离婚时间缺失-0.617∗(0.33)_-0.494∗∗∗(0.32)样本量5644656,01155,17655,12856,01156,011观测值数20,04420,01920,01919,80719,80719,74519,745R20.080.110.110.110.110.11Panel B:年龄介于20岁与60岁之间的且至少出现2期的观测值离 婚-0.300∗∗∗(0.092)-0.275∗∗∗(0.091)-0.163(0.21)-0.279∗∗∗(0.098)距离婚的时间:共6组,调查时间-离婚时间(d年) 对照组为从未离婚者,最后一组代表离婚时间缺失第1年-0.516∗∗∗(0.19)-1.336(1.041)-0.324∗(0.17)第2年-0.324∗∗(0.13)-0.400(0.48)-0.266∗(0.14)第3年-0.162(0.13)-0.201(0.24)-0.106(0.15)3年以上-0.103(0.11)0.00533(0.21)-0.212∗(0.12)离婚时间缺失-0.384(0.26)0.539∗∗∗(0.15)-0.494∗∗∗(0.30)样本量56,10555,78455,78454,79354,79354,91154,911观测值数23,80223,77523,77523,45223,45223,49123,491R20.080.120.120.120.120.120.12Panel C:剔除婚姻幸福感最高的观测值离 婚-0.256(0.16)-0.156(0.17)-0.118(0.19)-0.118(0.24)距离婚的时间:共6组,调查时间-离婚时间(d年) 对照组为从未离婚者,最后一组代表离婚时间缺失第1年-0.683∗∗(0.30)-2.042∗∗∗(0.76)-0.158(0.29)第2年-0.279(0.25)-0.113(0.60)-0.0117(0.32)第3年-0.192(0.23)-0.0480(0.31)0.0609(0.30)3年以上0.0579(0.12)0.197(0.22)0.178(0.29)离婚时间缺失-0.370(0.32)0.205∗∗(0.079)0.418(0.42)样本量23,62723,50423,50422,35322,35322,47022,470观测值数9,0369,0379,0378,5028,5028,6828,682R20.030.070.070.070.070.070.07
注:各列控制变量同表3。
对于离婚后未再婚的观测值而言,离婚对其幸福感的动态影响则相对复杂。第(7)列结果显示,对离婚后未再婚者而言,与从未离婚者相比其幸福感落差从离婚后呈缩小趋势,到了离婚第3年其幸福感落差已经基本消失。不过,即使离婚过了3年或更长的时间,与从未离婚者相比那些未再婚的人仍然呈现出较低的幸福感水平。大概相当于从当地相对收入水平的中间位置的第3等滑落至第4等(共5等)。其可能解释有三。一是,离婚后2-3年是重新步入婚姻的黄金期,之后再婚可能更为困难。二是,人们在决定离婚时可能过高估计了自己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离婚后多年难以再婚的遭遇使其感到不幸福。最后,离异多年未再婚的个体,可能更不愿意报告自己离婚的时间。与第(5)列结果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离婚时间数据缺失变量在第(7)列为-0.494,且至少通过显著性为5%的统计检验。
四、稳健性分析
本文在两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分析。一是将研究对象限制在更严格的范围,进行样本敏感性分析。二是根据性别、城乡,以及教育程度、是否有小孩等维度将研究对象细分,用于分组子样本稳健性分析。
(一)样本敏感性分析
其中dtime代表个体接受CFPS问卷调查时与(最近一次)离婚相隔的时间,由5个虚拟变量构成。当dtime=1即离婚第1年或当年,虚拟变量dtimeit1=1,否则等0。当dtime=2即离婚的第2年,则dtimeit2=1,否则等0。
Panel C报告了剔除婚姻幸福感最高的观测值后的估计结果。如前述及,CFPS数据中曾经离婚的观测值占比也不足3.5%,其与从未离婚者进行比较时可能存在样本平衡性问题。考虑到婚姻满意度较高的个体的离婚概率相应较低。为了增强可比性,本文尝试剔除婚姻满意度较高的观测值重新进行回归分析。遗憾的是, CFPS数据仅在2014问卷中包含了个体婚姻满意度指标“总的来说,您对您当前的“婚姻/同居”生活有多满意?”。其中1代表非常不满意(2.21%),5表示非常满意(64.72%)。于是,剔除2014年婚姻满意度最高的观测值并保留离异观测值,然后向前回溯在CFPS2010和2012中匹配出相应观测值,构成了一个平衡面板数据。虽然历次调查都有相当规模观测值流失或加入,但历次调查各类婚姻满意度占比非常稳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样本流失不至于对本文研究结论造成严重影响。
表5离婚对幸福感的影响:分性别与城乡
全样本男 性女 性农 村城 镇(1)(2)(3)(4)(5)距离婚的时间:共6组,调查时间-离婚时间(d年)对照组为从未离婚者,最后1组代表离婚时间缺失第1年-0.448∗∗(0.18)-0.392∗(0.21)-0.490(0.34)-0.357(0.23)-0.584∗∗(0.29)第2年-0.286∗∗(0.13)-0.296∗(0.16)-0.274(0.23)-0.364∗∗(0.15)-0.171(0.25)第3年-0.136(0.13)-0.167(0.16)-0.0751(0.21)-0.205(0.15)0.0105(0.24)3年以上-0.0624(0.10)0.00915(0.13)-0.161(0.16)-0.189(0.13)0.146(0.17)离婚时间缺失-0.402∗(0.24)-0.130(0.24)-1.052∗∗(0.53)-0.380(0.32)-0.386(0.24)个体固定效应有有有有有时间固定效应有有有有有样本量71,82634,98936,83732,12539,701观测值数29,04214,35514,74013,32016,567R20.120.130.100.120.12
注:各列控制变量同表3。
表2报告了离婚与个体幸福感关系的混合横截面OLS估计结果。第(1)列结果显示,与从未离婚者相比,离过婚的个体幸福感水平明显较低(-0.327),且在统计上高度显著(p<0.0001)。在第(2)列我们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同时影响婚姻状态和幸福感的控制变量。其中包括相对收入、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年龄及其平方项等个体特征,以及通货膨胀、调查批次等宏观因素。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差异,各地对离婚的态度与幸福感的定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苏理云等,2015)。于是,本文加入了省际固定效应,以控制由于历史、文化等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因素的影响。
NDVI在高植被盖度区易饱和、低植被区易受土壤背景影响的环境下,MODIS增强性植被指数(EVI)可较好地克服NDVI的弱点。EVI可用MODIS数据公式:
(二)分组回归稳健性检验
表6第(2)-(3)列报告了分教育程度子样本回归结果。大量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对婚姻稳定性有着重要影响,这也是教育作用于幸福感的核心渠道(Park and Raymo, 2013)。同时,不同学历群体之间对幸福感可能有着不同的感知(Chen,2012)。那么,离婚对幸福感的冲击及其动态演变,在不同学历群体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具体地,将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个体划分为高等学历群体,高中学历及其以下划分为非高等学历群体。第(2)列结果显示,对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群体而言,在离婚当年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即不存在明显的幸福感落差(p= 0.565),之后在数值上有较大反复。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本文分析对象中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者占比较低(6.39%),故对其结果解释需要格外小心。第(3)列结果展示了在高中或以下学历群体内部,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动态效应。与从未离婚者相比人们在婚姻解体当年呈现幸福感落差为-0.474且在统计上显著(p=0.018)。到了第2年,其幸福感落差大约缩小了50%,且仅在统计上勉强显著(p= 0.084)。在离婚的第3年,曾经离婚者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进一步缩小至-0.130,且在统计上不再显著(p=0.325)。婚姻解体3年后,二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已经基本消失。
离婚与个体幸福感关系的动态效应不受城乡差别驱动。第(4)-(5)列报告了分户籍子样本估计结果。对比两列回归结果,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动态影响,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呈现出共同的演变趋势。与从未离婚者相比,农村居民在婚姻解体当年的幸福感落差较大(-0.584),且在统计上显著(p=0.042)。到了第2年其幸福感落差缩小至-0.171,且在统计上不再显著(p= 0.489)。第(5)列结果显示,与从未离婚者相比城镇居民在离婚当年幸福感水平落差为-0.357,不过在统计上并不显著(p=0.117)。虽然在第2年其幸福感落差有所扩大且在统计上显著(p=0.017),但到了第3年已经减少至-0.075且在统计上不再显著(p =0.352)。在婚姻解体第3年或更晚些,其幸福感甚至反超从未离婚者,不过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统计检验。
表6报告了分学历和生育经历的估计结果。考虑到教育水平可能是个体婚姻状况和幸福感水平的共同原因(Chen, 2012),本文按接受教育的程度细分样本,回归结果分别报告在表6第(2)-(3)列。生育状况对个体婚姻稳定性和幸福感水平都有着重要影响(许琪等,2013)。那么,在已育有子女的群体与未育子女群体之间,离婚经历对个体幸福感水平的动态影响也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于是,本文根据生育状况将全样本细分为有子女样本与无子女样本,回归结果分别呈现在第(4)-(5)列。
离婚与个体幸福感关系的动态效应不受性别因素驱动。Becker(1993)认为,由于家庭分工男女在婚姻专用品方面的投资存在不小的差距。那么,婚姻解体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动态演变,男女间就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表5第(2)-(3)列分性别子样本估计结果显示,与全样本估计结果类似,无论男女都是在离婚当年报告的幸福感落差最大,分别为-0.392与-0.490。其中女性样本系数明显高于男性样本系数,不过二者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能由于抽样误差的缘故,后者系数未通过传统的显著性检验(p=0.154)。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随着时光流逝无论男女,婚姻解体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呈减小趋势,到了离婚3年后已经非常微弱。
第(4)-(5)列报告了分生育情况子样本估计结果。Becker(1992)提出,许多家庭内投资都具有婚姻专用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两人共同生育的孩子。那么,育有子女的离婚者,与离婚未育者,其幸福感演变模式是否存在差异?第(4)列结果显示,在未生育的情况下与从未离婚者相比,个体在婚姻解体当年幸福感落差为-0.239(p=0.437)。到了第2年其幸福感水平甚至反超从未离婚者,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p=0.845)。随着距离上次离婚时间越来越久,其幸福感落差虽有所反复,但仍呈现出递减趋势。育有子女的情况下婚姻解体对个体幸福感的动态影响,更值得关注(袁晓燕,2017)。第(5)列结果显示在育有子女的情况下,与从未离婚者相比,人们在婚姻解体当年报告的幸福感落差为-0.565,且在统计上显著(p=0.007)。同等情况下,一个人相对收入水平从中等的第3等滑落至最低的第5等,其幸福感水平变化为-0.347,仅有婚姻解体造成的幸福感损失的6成(0.347/0.594=0.614)。在婚姻解体的第2年,育有子女个体幸福感水平恢复了将近4成,不过在统计上仍然低于从未离婚者(p=0.037)。到了离婚后的第3年,该群体的幸福感水平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差距已经基本消失,且在统计上不再显著(p=0.589)。
在买卖关系之下,买卖双方的价款流向是从买方到卖方的单向流动,任何影响价款流动的第三方因素都会被双方所禁止。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行为人将自己的二维码覆盖在商家二维码之上这一预备行为就已经遭到商家的反对;第二,行为人利用顾客向错误的二维码扫描付款标志着实行行为开始,商家知悉后也是明确拒绝的。商家对于该笔价款的归属具有强烈的可期待性,可以说行为人整个取财的过程完全违反被害人的意愿。在盗窃罪所要求的行为手段中,行为人的偷换行为巧妙地避开了买卖双方的自由意志,没有对顾客以及商家的主观意志产生任何影响,成功实现秘密窃取。
表6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学历与生育情况
全样本高等学历非高等学历未育子女 育有子女(1)(2)(3)(4)(5)距离婚的时间:共6组,调查时间-离婚时间(d年)对照组为从未离婚者,最后1组代表离婚时间缺失第1年-0.448∗∗(0.18)-0.210(0.37)-0.474∗∗(0.20)-0.239(0.33)-0.565∗∗∗(0.21)第2年-0.286∗∗(0.13)-0.416∗(0.23)-0.251∗(0.14)0.0826(0.42)-0.295∗∗(0.14)第3年-0.136(0.13)-0.0353(0.44)-0.130(0.13)-0.540∗(0.30)-0.0740(0.14)3年以上-0.0624(0.10)-0.586∗(0.31)-0.00909(0.11)-0.106(0.38)-0.0423(0.11)离婚时间缺失-0.402∗(0.24)-0.571(0.58)-0.371(0.25)0.210(0.38)-0.446∗(0.25)个体固定效应有有有有有时间固定效应有有有有有样本量71,8264,44567,3814,19267,634观测值数29,0421,97327,1673,06127,615R2 0.120.130.110.120.11
(三)内生性讨论
本文结论可能面临多种内生性威胁。一是遗漏变量问题。有些变量,如性格特征、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等,可能是婚姻状况和个体幸福感的共同原因。对其若不能予以控制将会导致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的追踪数据,已经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控制了性格等不随时间流逝而发生改变的个体特征。在回归方程中也包含了个人相对收入、健康状况等一系列可能对婚姻状况和幸福感水平都产生影响的因素。
运动可以提高患者的身体素质,改善患者的身体机能状态[15]。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动机性访谈,干预后6个月,干预组舒张压、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的改善显著好于对照组(P<0.05),这表明动机性访谈能够促进患者坚持长期运动,从而改善其心血管的适应性和耐受性。此外,由于体力活动的增加,患者的食欲和蛋白质能量摄入得到改善,肌肉蛋白合成增加。干预后6个月,干预组血红蛋白及血清前白蛋白明显升高,表明患者的营养状况有所改善。
二是测量误差。若解释变量存在随机测量误差,将会导致估计结果发生向零偏倚(atttennus bias)。CFPS数据关于婚姻状况的问卷设计相当细致,且通过多种方式提问跨期交叉验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测量误差。值得说明的是,有部分个体没有报告具体离婚时间,若简单地将其剔除可能导致样本选择偏倚,本文为其设置了“离婚时间缺失”虚拟变量。
三是反向因果关系。显然,幸福感水平较低的夫妻更可能解除婚姻关系。那么,本文关于离婚对个体幸福感存在负面影响的结论,就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借助CFPS追踪数据信息优势,对于2010年之后解除婚姻关系的观测值,本文可以控制个体初始幸福感水平;对于2010年或之前解除婚姻关系的观测值,本文使用的组内估计量方法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双向因果关系造成的估计偏差。
最后是观测值流失问题。CFPS规定,在2010年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领养子女将作为CFPS的基因成员,成为永久追踪对象。另外,我们也比较了三次调查都出现的观测值的婚姻状况以及离婚时间信息,结果显示与2010年基期调查差别不大。CFPS各期离婚观测值中都出现了女性占比偏低现象。可能的解释是,女性尤其是再婚女性更不愿意报告婚史信息,从而被归类到从未离婚者样本。考虑到女性幸福感普遍高于男性,若曾经离婚观测值中女性流失比例更高的话,那么将会低估曾经离婚观测值的幸福感。这意味着我们高估了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即使存在高估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没有发现离婚对人们幸福感存在长期显著负面影响的证据。这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展望
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后,离婚在短期对个体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冲击但不存在长期效应,其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在离婚3年后即基本消失。分性别、城乡、教育水平、生育状况以及再婚状况的子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无论将分析对象限制在3期追踪调查都出现的观测值、年龄介于20岁与60岁的观测值,亦或是婚姻满意度不太高的群体,都不影响本文基本结论。值得一提的是育有子女个体受到离婚的影响。与未育离婚个体相比,他们在离婚第1-2年受到的幸福感负面冲击更为严重,不过其恢复也更为迅速,到了3年后与从未离婚者的幸福已经不存在显著差异。
2.1两组患儿的护理有效率对比 实验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96.67%,对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76.67%,实验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表示统计学有意义。见表1。
婚姻解体可能提升了离婚个体幸福感。基于常识推断离婚个体在离婚前夕的幸福感水平,应该已经低于其他已婚者,这也许是他们婚姻走向解体的重要原因。那么,本文关于离婚个体幸福感水平在3年后基本与从未离婚者持平的发现,可以看作婚姻解体最终提升了离婚个体幸福感的证据。基于国外的数据也有类似发现。Gardner and Oswald(2006)基于英国追踪数据的研究发现婚姻解体后第2年人们的幸福感水平就明显超过了离婚前1年。而Hetherington(2003)则显示离婚6年后就有超过3/4的人自认其当年离异不是坏事。
我国离婚的主观成本和客观成本都比较低。由于不需要分居、手续简化等原因,中国已经跻身世界离婚(客观)成本最低国家之列。当然其时代底色是,中国连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和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加上妇女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提升催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使人们尤其是女性不再单纯出于物质考虑而迁就婚姻。而本文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居民离婚后也不必承担长期的精神痛楚。于是,将离婚的主观成本和客观成本结合起来考虑,或许有助于理解中国当前离婚率的不断攀升。
应该审慎地看待离婚对幸福感没有长期影响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以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初步定量考察了离婚对人们幸福感影响。本文关于离婚对人们幸福感不存在长期负面效应的结论,不应被视为支持乃至鼓励中国居民离婚的经验证据。至于随着时间流逝离异者幸福感恢复至与从未离婚者无甚差别的现象,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在遭受巨大打击后,离异者心理上表现出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一个离过婚的人,也可以像常人一样幸福快乐。一个佐证是,中国居民离婚后再婚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民政部数据显示,中国再婚登记人数从2006年的184.4万人上升至2015年的340.44万人。或许,他们不是不相信爱情,仅是不再爱对方而已。另外,和平分手已经成为离婚的主流方式。在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修订时,超过50%的夫妻需要通过法院判决或调解才能解除婚姻关系,而到了201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不足1/6。
这是因为该建筑物附近处于地铁施工后期,这期间会因为深基坑和建筑物本身荷载的影响而出现明显的沉降,所以沉降速率明显加快。2013年4月15日后趋于平稳,监测点沉降速率明显减慢并趋于平缓。在整个监测过程中,最大沉降量为3.8 mm,对应监测点为JH-6。从沉降曲线图还可以看出该建筑物的沉降量与监测时间整体上呈明显的线性关系。
本文聚焦于离婚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动态效应的定量评估,对其作用渠道并未深入探索。毕竟,限于数据可得性,我们无从知晓在遭遇离婚这一人生重大变故后,离异者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福的家庭各不相同。我们有理由怀疑离异者群体内部存在更大程度异质性。Hetherington(2003)基于追踪数据的研究发现,离异者短期内都经历了不同程度身心折磨;多年后,绝大多数人都适应了新的生活,不过仍有一定比例的离异者挣扎在痛苦的深渊。即使对那些适应新生活的大多数而言,在遭遇离婚这样的人生重大变故之后,虽然时间可以缓解痛楚,但很难彻底治愈其伤口。我们的研究仅表明,经历了离婚这样的人生重大变故之后,人们仍然可以过着与常人一样幸福的生活。至于如何发掘婚姻解体对个体幸福感发挥作用的中介机制并深入探究其异质性,以及进行相应的情感干预或救济,则是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池丽萍,2016,“中国人婚姻与幸福感的关系:事实描述与理论检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45-156页。
郭婷、秦雪征,2016,“婚姻匹配,生活满意度和初婚离婚风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劳动经济研究》,第4卷,第6期,第42-68页。
林莞娟、赵耀辉,2014,“‘重男轻女’降低女性福利吗?离婚与抚养压力”,《经济学(季刊)》,第14卷,第1期,第135-158页。
鲁建坤、范良聪、罗卫东,2015,“大众传媒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人口研究》,第39卷,第2期,第67-77页。
陆益龙,2009,“‘门当户对’的婚姻会更稳吗?——匹配结构与离婚风险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第33卷,第2期,第 81-91页。
范子英,2016,“为买房而离婚——基于住房限购政策的研究”,《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第1-17页。
苏理云、柳洋、彭相武,2015,“中国各省离婚率的空间聚集及时空格局演变分析”,《人口研究》, 第39卷,第6期,第74-84页。
谢宇、胡婧炜、张春泥,2014,“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理念与实践”,《社会》,第2期,第1-32页。
袁晓燕,2017,“众里寻他!?——一个基于婚姻匹配理论的综述”,《南方经济》,第2期,第87-101页。
许琪、邱泽奇、李建新,2015,“真的有‘七年之痒’吗?——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及其变迁趋势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第216-241页。
Amato, P.R., 2010, “Research on Divorce: Continuing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 (3): 650-666.
Becker, G.S.,1993,“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85-409.
Becker, G.S. and Murphy, K.M., 1992,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4): 1137-1160.
Booth, A.and Amato, P., 1991, “Divorce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2(4):396-407.
Clark, A.E., Diener, E., Georgellis, Y. and Lucas, R.E., 2008, “Lags and Leads in Life Satisfaction: a Test of the Baseline Hypothesis”,Economic Journal, 118(529): F222-F243.
Deaton, A. and Stone, A.S., 2013, “Do Context Effects Limit the Usefulness of Self-reported Wellbeing Measures?”, Research Program in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288.
Easterlin, R.A., Morgan, R., Switek, M. and F.Wang, 2013,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 (25) : 9775-9780.
Ferrer-I-Carbonell, A., Frijters, P., 2004, “How Important is Metho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Economic Journal, 114(497): 641-659.
Frederick, S. and Loewenstein, G., 1999, “Hedonic adaptation.in E. Diener”, N. Schwarz and D. Kahneman (Eds.) Hedonic Psychology: 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Enjoyment, Suffering, and Well-being.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302-329.
Gardner, J. and Oswald, A.J., 2006,“Do Divorcing Couples Become Happier by Breaking Up?”,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169(2): 319-336.
Gilbert, Daniel, Pinel, T., Elizabeth, C., Wilson, Timothy, D., Blumberg, Stephen, J., Wheatley, and Thalia, P., 1998, “Immune Neglect: A Source of Durability Bias in Affective Forecast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3): 617-638.
Hetherington, E.M., 2003, “Intimate Pathways: Changing Patterns in Clos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cross Time”,Family Relations, 52 (4): 318-331.
Huang, F., Jin, G.Z. and Xu, L.C., 2016, “Love, Money, and Parental Goods: Does Parental Match Making Matte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hnson, D.R. and Wu, J., 2002, “An Empirical Test of Crisis, Social Selection, and Role Explan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Disrup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Pooled Time-Series Analysis of Four-Wave Panel Data”,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1): 211-224.
Knight, J. and Gunatilaka, R., 2011, “Does Economic Growth Raise Happiness in China?”,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9(1): 1-24.
Miller, M.A. and Rahe, R.H., 1997, “Life Changes Scaling for the 1990s”,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43 (3): 279-292.
Oswald, A.J. and Powdthavee, N., 2008, “Does Happiness Adap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isability with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sts and Judg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5-6): 1061-1077.
Park, H. and Raymo, J.M., 2013, “Divorce in Korea: Trends and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1): 110-126.
Peters, H.E., 1986, “Marriage and Divorce: Informational Constraints and Private Contracting”,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3):437-454.
Pevalin, D.J. and Ermisch, J., 2004, “Cohabiting Unions, Repartnering and Mental Health”,Psychological Medicine, 34(8): 1553-155.
The Economist, Divorce: A Love Story, 23/01/2016.
Williams, K. and Dunne-Bryant, A., 2006, “Divorce and Adul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larifying the Role of Gender and Child 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8(5): 1178-1196.
Wade, T.J. and Pevalin, D.J., 2004, “Marital Transitions and Mental Health”,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5 (2): 155-170.
Wassmer, R., Lascher, E. and Kroll, S. 2009, “Sub-National Fiscal Activity as a Determinant of Individual Happiness: Ideology Matter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0(5): 563-582.
Yan, Y., 2015, “Parent-driven Divorce and Individualiza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Youth”,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64(213-214): 317-330.
HappyBreakingup?TheEffectofDivorceonPersonalHappiness
Ma Bianjing
Abstract: The roaring in divorce rates has been widespread concern in China, but few literatures have quantitatively assessed the impact of divorce on individual subjective well-being. Using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 this article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impact of divorce on individual subjective welfare and its dynamic evolution,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high divorce rate. After controlling individual fixed effects and time fixed effects, divor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individual well-being. According to the self-assessment income, it is divided into five levels. The loss of happiness suffered by individuals in the year of divorce is equivalent to the decline from the middle class to the lowest class. Divorce does not have long-term effects on personal happiness. The happiness gap between divorcees and those who have never divorced disappears after 3 years of divorce; whether remarri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t.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happiness affecting divor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with or without children, there is a common dynamic evolution trend.Considering that the happiness of divorcing individuals should be lower on the eve of divorce than that of other married people, divorce should enhance their happiness. The rapid recovery of the happiness of the divorced person indicates that one’s psychological performance shows an amazing self-repair ability after suffering a huge blow. The subjective cost of divorce is relatively low in China, or contributes to the high roaring divorce rate.The conclusion that divorce has no long-term impact on happiness should be considered cautiously. The conclusion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or even encourage Chinese residents to divorce. This study only shows that a divorced person can be as happy as other people.
Keywords: Divorce; Happiness; Panel Data.
DOI:10.19592/j.cnki.scje.360812
分类号: I31, J12, J17
中图分类号:F0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9)07-113-20
马汴京,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E-mail:bianjingma@163.com,通讯地址:杭州市学源街18号,邮编:310018。作者感谢韩军、罗楚亮、吴一平、何晓波、詹鹏、郭峰、孙聪等学者,以及鲁建坤、苏卫良、姜磊、李佳慧等同事的修改建议;本文曾在香樟经济学论坛(上海)和第二届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报告过,感谢与会者的有益评论,作者文责自负。
基金信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703144;7186302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15XJC790014)。
(责任编辑:谢淑娟)
标签:幸福感论文; 离婚者论文; 个体论文; 婚姻论文; 时间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南方经济》2019年第7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703144; 7186302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15XJC790014)论文;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