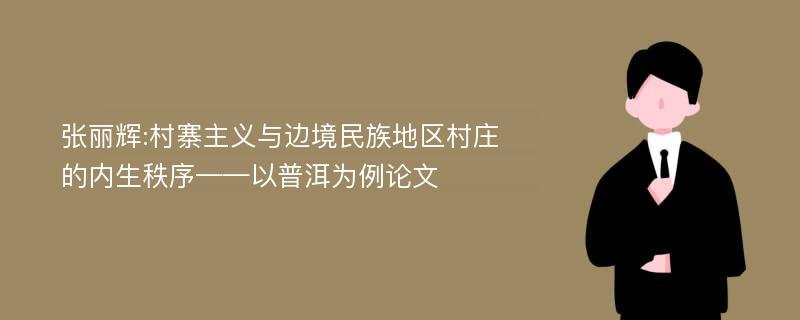
【社会学研究】
摘 要:村寨主义是以村寨利益为最高原则来组成和维系村寨社会文化关系并运行村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制度。观察普洱边境民族地区的村庄可以发现,村寨主义具备或满足“有明确的村寨物理空间标识”“用系统的村寨性宗教祭祀活动来建构和强化村寨空间神圣性”以及“村民的集体行动总是遵循以村寨为边界的文化逻辑”等三个特征,是这类地区村庄内生秩序得以保留的根本原因。在村寨主义影响下,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在现代发展中秩序建构面临怎样的困境与出路,需要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村寨主义;内生秩序;村寨空间;边境民族地区
一、样本特征与问题缘由
边境地区在政治学和地理学意义上是指邻近边界、国界的区域范围,有别于边界;边境民族地区是指邻近边界、国界区域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此区域的驻民有别于边民。
中国边境线绵延2万多公里,与15个国家接壤,要对边境民族地区村庄内生秩序做一一了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课题组以云南省普洱市为例进行研究,源于普洱特殊的区位:全国唯一一个“一市连三国”“一江通五邻”的地区,陆路与老挝、越南、缅甸三国接壤,水路可通往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全市下设9县1区,9个县均为少数民族自治县,居住着汉、哈尼、彝、拉祜、佤、傣等14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61%,属于典型的边境民族地区。我国社会文化多元并存、差异性大,通透解读普洱这个典型区域,虽然无法代表对我国边境民族地区的一般认知,但却可以提供一种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视角,这既为准确解析这一区域的农村社会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也为边境民族地区的农村治理提供依据或思路。
Spark作为整个系统最上层部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主要包括了对数据预处理、特征转换与特征提取、行为分类模型训练和最终的结果预测。其中数据预处理会通过相似度判别过滤失真数据,接着根据行为表示的定义方法对关节点数据进行特征转换与特征提取并写入到RDD中。在以上基础上,利用行为分类器对数据进行训练。当需要对未知行为进行预测时,从HDFS中提取已有持久化的分类器模型完成行为数据的最终分类并将结果持久化到HDFS中。
“农民合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少,合作的成本越来越高,在这种条件下试图建立内生性的村庄秩序,实在大成问题”[1]。这是贺雪峰在考察我国东中部地区农村时得出的一个结论。董磊明、吴理财、张良、申端锋和王玲等学者从公共空间与乡村秩序关联的角度出发,认为随着农村传统公共空间的萎缩和凋零,乡村社会的秩序走向瓦解,众多学者认为,乡村社会内生秩序正在被市场经济和急剧流动的人口所解构。然而,课题组在考察普洱农村时看到的景象是:传统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淳朴诚实、勤劳勇敢、鄙视偷盗、重视家庭伦理、乐天安命等传统认知观念,仍然鲜活地存在于各民族的观念、情感、习惯和行为中,人们对村庄认同感强,行事有底线,村庄平静祥和。这独有的魅力不断招引笔者去找寻现象背后的原因,课题组曾给出了很多假设性答案,如:公共空间、村庄共识、民间组织与精英、自我约束机制等等,在反复调查与体验中意识到:这些假设是答案又非答案。是答案,因为村庄秩序的形成都与这些因素关联;非答案,因为这些因素没能从最本质的层面给予解释或回答,直到阅读了马翀炜教授《村寨主义的实证及意义——哈尼族的个案研究》一文,终于豁然开朗,颇有同感之余是找到答案的欣喜:村寨主义的存在正是普洱村庄内生秩序得以存在的最根本解释。
2.例文不够多。64篇习作中老教材才出现4篇例文,主要为读后感例文、写信例文、缩写例文、我的小伙伴(开头)例文。在这4篇中有3篇是应用文。而细节描写、修改的形式、应用文的格式等重点都没在例文中体现,更没有以正楷字的形式、标准的格式写进方格中。
二、秩序存在之源
村寨主义为边境民族地区村庄内生秩序的存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然而,随着“全球化”、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市场经济的浸润和人口的急剧流动,村寨主义遭遇冲击、衰退和变异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只有进行积极合理的调适、吐纳和蜕变,其在村庄治理中的秩序建构功能才能得以继承和发扬。
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观测可以看出,村寨主义在普洱边境民族地区广泛存在。在此,笔者无意去评判或褒贬,只是想通过深入观察和细致描述,为人们研究村庄内生秩序提供一种崭新的认识视角,以期拓宽村庄治理的研究思路。
马翀炜认为,“村寨主义在一些哈尼族村寨是存在的,把维护村寨利益作为最高原则的村寨主义的大量存在是可以肯定的”[2]。普洱作为典型的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各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对村寨的强烈认同,村寨为村民提供水、田和地,使人们谷物满仓,衣食无忧;由于地处边缘,历史上无论完成较大作业,还是抵抗灾难与风险都只能依靠所属村寨,使得边境村民把最基本的信任关系建立在本村本寨,村寨成为他们社会关系得以延展的可靠舞台,村寨主义在此基础上被模塑。借用马翀炜教授度量村寨主义的三个维度,可对普洱村寨作一个大致检视。
重视和发掘节日庆典仪式的社会功能,是村寨主义“用系统的村寨性祭祀活动来建构和强化村寨空间神圣性”[2]的现代转换和适应。
第二,“用系统的村寨性宗教祭祀活动来建构和强化村寨空间神圣性”[2],普洱13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年节庆典都与宗教祭祀活动相联,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这里列举其中9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宗教祭祀与节日,见表1。
在全面的组织框架及完善制度的基础上,以总务处为代表的医院后勤团队发挥着能源管理组织和实施的功能。总务处下设办公室、维修中心、动力科、电力科等科室,同时搭建能源管理平台(运行机制见下页图示),针对能源管理专题开展工作和研究。能源管理平台的建立,促使能源管理工作与医院各部门的联动更加密切,充分发挥了医院能源管理这支队伍的能力和作用。该平台负责人袁星向记者介绍,平台自运行以来,以不同能源主题的项目为切入点,推动医院节能工作更加持续有效地开展。
表1 普洱部分世居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地、祭祀和传统节日
注:竜林即指寨神林
民族 主要分布地 主要祭祀 传统节日佤族 西盟、澜沧、孟连 鬼神、祖先、自然、动植物,如:祭火塘、神树(榕树)、水鬼“翁木”、水牛崇拜等木鼓节、新米节、新水节、新火节、播种节布朗族 澜沧、墨江、景谷 鬼神、祖先、自然、动植物,如:祭寨神(恰克里)、供奉白石或黑石作为“寨心神” 祭竜节、火把节、收棉花节傣族 景谷、孟连、江城、澜沧 鬼神、祖先、自然、动植物,如:祭祖先勐神、祭寨心、谷魂、水神、竜林等泼水节、新米节、开门节、关门节拉祜族 澜沧、西盟、孟连 鬼神、祖先、自然、动植物,如:祭天神(“厄莎”)、祭猎神、竜林、寨神等扩塔节、葫芦节、新米节、火把节、祭祖节哈尼族 墨江、宁洱、镇沅 鬼神、祖先、自然、动植物,如:祭寨神(“艾玛突”)、祭竜神等 火把节、十月节彝族 景东、景谷、镇沅、宁洱 天神、地神、加神(祖先)和竜神 火把节傈僳族 思茅、孟连的勐马、芒信 鬼神、祖先、自然、动植物,如:祭竜、祭火等 阔时节、新米节、火把节景颇族 孟连景信、澜沧勐朗 鬼神、祖先、自然、动植物,如:祭寨神、家神和谷神等 新米节、播种节、尝新节瑶族 景东、墨江、江城 鬼神、祖先、自然、动植物,如:祭寨神、家神、谷神、猎神和祖宗等 苗年、四月八、鼓社节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一是普洱各少数民族信仰原始宗教,相应的各种祭祀活动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为各民族的传统节日,节日庆典与宗教祭祀活动紧密相联。二是宗教祭祀活动中,无论祭祀鬼、神或祖先,都以庇护村寨为共同特征。普洱是倚山地而居的民族,都崇拜山,祭“山神”成为一项重要的祭祀内容。靠水而居的民族,普遍崇拜水,最典型的就是傣族。此外,哈尼族、彝族等祭龙或龙潭,也包含着对水的崇拜,并形成许多与水有关的禁忌等等[4]。上述种种可以看出,普洱各民族的宗教祭祀活动,无论祭寨神、竜神、水神,还是谷神、火神,都是为了保证村寨内人畜平安、无灾无难、五谷丰登,无形中捍卫和强化着“村寨空间神圣性”,村寨成为村民们的认同和行动单位。
样式是指用有意义的名称保存的字符格式和段落格式的集合,也就是说将要设置的多个格式命令加以组合、命名,应用一次样式,就可相当于设定这些格式,每个样式都有唯一确定的名称,用户可以将一种样式应用于一个段落或选定的字符上。例如使用系统自带的“标题1”样式,即可将所选文字设置为2号字体、加粗、多倍行距等效果。当鼠标指向“标题1”时,就可以看到应用样式的效果,就是应用了一组格式的集合,这一组格式设置按常规要分几步才能完成,现在只需要应用样式就可一步完成,从而简化了字符、段落的格式排版,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接收机的时延由接收链路上的功能电路如放大器、混频器件及滤波器等引起,下面分别对各部份电路的时延进行分析和仿真。
三、秩序建构之策
“村寨是一定的人群按照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组成的一种生产生活空间”[2]。马翀炜教授认为,“维持群体存在的纽带也可能是多样性的”[2],“村寨普遍存在,但组成村寨及维系村寨社会的原则是不同的。如华南汉族地区的村寨就有以宗族利益为最高原则和理想来组织和维系民众的宗族主义”[2],“村寨主义则是指以村寨利益为最高原则来组成和维系村寨社会文化关系并运行村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制度”[2]。村寨主义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有明确的村寨物理空间标识”[2],二是“用系统的村寨性宗教祭祀活动来建构和强化村寨空间神圣性”[2],三是“村民的集体行动总是遵循以村寨为边界的文化逻辑”[2],这些特征都指向一个关键词——村寨社会空间。笔者在《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村庄内生秩序生成》一文中曾论述到:“乡村公共空间的分享是内生秩序形成的前提和基础”[3],“公共空间的分享类型越丰富,村民的‘共’‘通’性越强,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越大,社会关联度因此增强,内生秩序的形成获得了牢固的社会基础”[3]。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公共空间是构成村庄内生秩序的重要因素。马翀炜教授所讲的村寨社会空间,其实就是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村寨主义的提出依然照应了已有的研究结论,即公共空间是中轴和核心;所不同的是村寨主义强调在既定的物理空间范围内,用宗教祭祀活动对空间神圣性进行强化,人们的行为带有明显的边界文化逻辑,即寨内与寨外。对寨内空间的维护是自然而然也是不假思索的,无需追问,不用理由,村民的言行映射出村寨利益至上的原则,这是内生秩序产生并得以延续的“源”与“本”。
第三,“村民的集体行动总是遵循以村寨为边界的文化逻辑”[2],村寨有物理空间边界,也有社会文化边界,前者是有形的,后者却是无形的,作为无形的社会文化边界需要通过相关的仪式、习俗禁忌来凸显和强调。普洱民间的各种习俗禁忌,对人们进入或走出村寨有一定的规范,例如:普洱各少数民在大年初一,一般都禁止外人进入寨子,本寨人也不许到外寨去,意在避免邪恶出入,造成灾难;拉祜族祭送火神的当天,禁止外人进入寨子,各家各户也不准留宿外人,以免把灾星带入寨子;布朗族主祭日这天,禁忌外寨人入寨,以免招致不测;澜沧茨竹河一带的拉祜族认为红色不吉利,因而忌穿纯红色的衣裤,也禁止外人带入红毯子、红毛巾等物,等等。这些禁忌是以村寨边界为限来保平安、避灾难[4]。此外,各民族中盛行的招魂,也有相同的意蕴,拉祜族认为人得病,是鬼怪作祟的结果,得请“魔巴”来做法事,吟唱叫魂,将灵魂召回附体。这些仪式,在赋予村寨社会丰富文化内容的同时,又如显影剂一般对村寨的社会文化边界进行着呈现与复制。
(一)文化架构中的村寨主义
马翀炜教授在分析哈尼族村寨主义的文化结构时指出:“传统的民间宗教组织及传统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元阳一带的哈尼族社会中,咪咕、魔批以及尼玛以各自的作用形成的三元一体的文化架构的影响依然很大。”[2]综观普洱的情形,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民俗活动不同程度地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宗教组织中的各类精英,如祭司(巫师)、魔巴等的地位、职能和作用都发生了流变,地位逐渐边缘化、社会职能减弱,由原来精神活动的主宰者变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民众心灵的慰藉者,村委会组织、村党组织和村民小组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节日文化源于宗教祭祀活动,节日是一种具有强烈人为因素和浓厚文化色彩的岁时民俗,是民俗事象超越时空的汇聚和展示,具有全民性、集体性和传统性[5]。将普洱各民族的节日归类大致可分为岁首年节、祭祀节日、宗教节日和农事节日四大类。岁首年节最具代表性的有傣族的泼水节、拉祜族的扩塔节、哈尼族的十月年节;祭祀节日有佤族的拉木鼓节、接新水节和取新火节,拉祜族的祭祖节,哈尼族的祭母节,瑶族的盘王节,以及在傣、拉祜、哈尼和彝族中流行的祭竜节等;宗教节日有傣族的开门节、关门节、赕佛节、赕白象和赕白牛,回族的开斋节等;农事节日有在拉祜、佤、哈尼和景颇等民族中普遍流行的火把节、新米节,哈尼族的苦扎扎节,佤族的播种节等[4]。这些年节凝聚着各族人民的生命意识、伦理情感、审美情趣和宗教情怀,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表现,是对既有文化价值观的认定和维护,通过共同神灵、共同祖先和共同记忆的唤醒,彰显文化上的一致性,强化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团结内部成员,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有效地维护着村寨社会秩序[4]。
传统符号作为传统文化的彰显和标识,承载着村庄共同的价值伦理,因强化村民内在认同心理而起到维系村庄秩序的功能。边境民族地区村庄的传统符号包括房屋建筑、服饰、语言以及民族传统节日等等,从文化内涵的角度看,服饰、建筑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本民族的社会特征、伦理秩序,起着规范社会秩序的功能。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地把汉语当做族际交流的共同语,砖木结构的平房和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逐渐代替了传统民居,室内布局陈设趋向新潮和现代;各民族多姿多彩的传统服饰逐渐被现代服装替代,很多村寨民族服饰只在妇女中传承,男子只有在重大节庆或商业表演中才穿戴民族服饰,民族服饰规范社会秩序的功能逐渐弱化[4]。相反,与宗教祭祀紧密相连的节日庆典因具有较强文化象征意义,在文化保护传承与经济开放并举的双重需求下,得到恢复、开发而发扬光大,文化架构视角下的村寨主义,要以此为重要内容和载体。
第一,“村寨主义的村寨有明确的村寨物理空间标识”[2]。纵观普洱各村寨,物理空间标识非常清晰,一般以山、水、田、树林或石碑为界,界标附近修筑寨门,寨门以内即属于自己的空间范围。以拉祜族为例,带领大家修寨门是拉祜族头人的一项重要职责,寨门又叫“龙巴门”,澜沧革新寨拉祜族在东南西北4个方向分别设置了4道“龙巴门”;傣族也非常重视筑寨门,他们建寨从寨心开始,向四周发展,四周分别留东南西北4个门,管理寨门、寨心的人一般被称为“召色”。其他各民族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也保存着修筑寨门的传统,独具特色的寨门铸造,在彰显民族自识性的同时更强化了村寨认同。没有修筑寨门的村寨,村民们也会沿着界标的延长线,心照不宣地恪守,少有纷争,若有边界模糊地段,大家会遵循尽量避开或不触碰的原则。
(二)自我约束机制下的村寨主义
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指出:“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否则的话,正式的法律制度就会被规避、无效,而且可能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6]这里提及的习惯或惯例,在乡村社会中起到自制、自控和自律的作用,实质就是自我约束机制,它一般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来呈现。池建华在《从村规民约看乡土社会规范的多元性》一文中把村规民约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包含“遵循和重述国家法的内容”,另一部分蕴含“传承和弘扬公序良俗”[7]。对国家法的遵循与重述,带有明显的共通性;公序良俗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个部分,是本村村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个性特征明显。将普洱多个村庄现有的村规民约文本内容进行对比,发现除村庄名称不同外,其余内容大同小异,甚至可以替换。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村庄放置村规民约的这些条款似乎都通行,说明“公序良俗”这一本该体现村规民约个性化的内容还很单薄。
公序即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秩序”,“是指村民参与乡村公共生活而形成的惯常规则,……包括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公共财产等内容”,公序强调对公共空间和财产的维护;良俗即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道德”,包括“物权习惯、债权习惯、互助习惯、婚姻赡养习惯、丧葬及祭祀习惯等”[7]。在边境民族地区村寨,公序良俗的很多内容是从原始宗教信仰中的习俗禁忌转化而来,习俗禁忌因此成为公序良俗的主要来源,如对山、水、树、猎等诸神的敬畏,有了保护山林、树木、水源和动植物的意识和行为,在保护公共空间与财产、维护公共秩序的同时,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畏惧于天、畏惧于祖、不亵渎传说中的英雄,村民注重自我教化,不贪不偷、劳动致富、行善尽孝、邻里和睦、体恤相助、扶危济贫,以此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公序良俗还包括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习惯,乡村社会的纠纷,涉及违法犯罪的,必然要由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理;对于不触及法律底线的,公序良俗中有相应的规约,一般走双方协商、村中调解为主,司法为辅的路子,其解决程序由下而上依次为“双方协商—村民小组—村调解委员会—村委会—乡镇”,核心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宽容,以和解的方式化解矛盾,避免矛盾扩大化,此番内容彰显的是人与社会的和谐。
概而言之,村规民约作为乡村社会最重要的自我约束机制,其内容要善于挖掘和吸纳村寨主义中蕴含的各种资源,在调适和吐纳中凝练、提升,促使其向公序良俗转化,既发挥新的社会控制功能,又赋予村寨主义新的时代内涵。
四、结论
以马翀炜教授考察哈尼族村寨时提炼出的“村寨主义”概念为核心,向外进行辐射和扩散,看此概念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适用,结果发现,村寨主义在普洱农村大量存在。如前所述,中国乡村社会多元复杂,即便是边境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结构关系也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不能简单认为边境民族地区良好的村落秩序都是村寨主义的影响使然。但文章提供的个案至少说明,村寨主义的存在是一些边境民族地区内生秩序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与普洱毗邻的西双版纳、临沧等地,有寨门、寨神和寨心的村落不在少数,村寨主义的特征或表现也是有的,课题组未对此类地区做深入调研,不能轻易下结论,但因村寨主义的影响使村庄内生秩序得以较好保留的情况,普洱绝非个例。
通过中铁六院隧道院在多个城市的CPⅢ实际应用研究,地铁轨道控制网约束平差后的精度评价指标大小,与高铁CPⅢ平面网的指标大小大部分相同,只有方向观测中误差2″、距离观测中误差1.2 mm和点位中误差5 mm或3 mm不同。坐标增量较差的限差定为2 mm,当地铁轨道控制网的平面上级控制点的间距约为600 m时,坐标较差的限差可以定为3 mm。
研究内生秩序的现实动力在于思考如何实现边境民族地区村庄的有效治理,村寨主义无疑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认识和研究视角,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村寨主义影响下的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在现代发展中秩序建构面临怎样的困境,出路在何方。
参考文献:
[1]贺雪峰.乡村秩序与县乡村体制——兼论农民的合作能力问题[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4):95.
[2]马翀炜.村寨主义的实证及意义——哈尼族的个案研究[J].开放时代,2016(1):206-221.
[3]张丽辉.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村庄内生秩序生成[J].安徽农业科学,2017,45(16):238-240.
[4]李娅玲.普洱文化通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5]黄 泽.西南民族节日文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6]苏 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
[7]池建华.从村规民约看乡土社会规范的多元性[J].学术交流,2017,278(5):118-225.
Villagism and the Internal Order of Villages in Frontier Ethnic Areas——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Pu’er
Zhang Lihui
(Teacher and Education College,Pu’er University,Puer,Yunnan 665000,China)
Abstract:Villagism is a socio-cultural system which takes the village’s interest as the highest principle in forming and maintaining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hip and managing its daily life.The observation of villages in ethnic areas along the border of Pu’er shows three features as following:firstly,villagism“has clear physical space marking of villages”;secondly,“the spatial sacredness of the village is established and reinforced by systematic sacrificial ceremony”;thirdly,“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villagers always follows the cultural logic which draw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of the village”.This is reason why the internal order of village has been remained.Under the influence of villagism,peopl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light and solution for constructing the order in the rural areas of frontier ethnic areas in modern development.
Key words:villagism;internal order;village’s space;the rural areas of frontier ethnic areas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9)04-0008-06
DOI:10.13747/j.cnki.bdxyxb.2019.04.002
收稿日期:2018-11-09
基金项目:2016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边境民族地区村庄的内生秩序研究”(16YJA840016)
作者简介:张丽辉(1971-),女,云南宁洱人,教授,主要从事边疆农村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 石丽娟)
标签:村寨论文; 普洱论文; 秩序论文; 主义论文; 村庄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保定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2016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 边境民族地区村庄的内生秩序研究"; (16YJA840016)论文; 普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