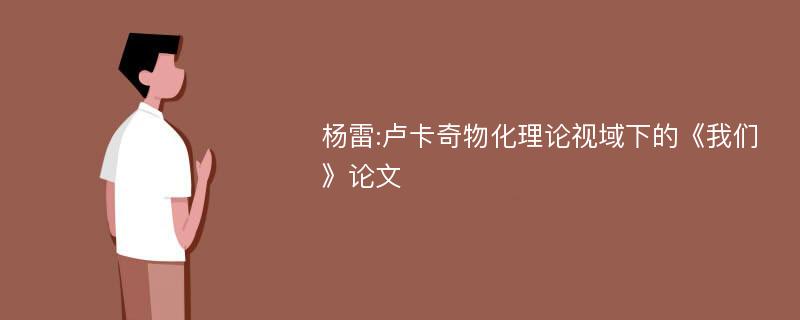
摘 要:异化现象是反乌托邦文学的天然属性。对异化现象的批判是马克思幸福社会图景构建的一个重要方式。因此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开山之作《我们》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物化理论所批判的对象。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继承和深化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揭示了《我们》 “幸福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以及 “幸福社会图景”破灭的必然性。
关键词:卢卡奇;《我们》;伦理; 物化
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是匈牙利著名的思想家,也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和奠基人。他以《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为理论基点,通过《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以及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著作,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物化理论和物化思想。他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具有惊人的相识之处,但在存在范围上却有质的区别。马克思是在对私有制的分析和批判中引申出异化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创新。他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了异化概念,认为异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主客体关系的颠倒。主客体颠倒使人的产物(客体)反过来与人(主体)相对立或敌对,并成为控制人的力量(主体)。这一逻辑颠倒构成了异化的内在逻辑。[1]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中,着重了对恢复“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的关注。强调了只有恢复了“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摆脱异化的命运,才有可能构建幸福社会的未来图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重点关注的是人的生存方式,体现了其对人向人的本质复归的强烈渴望。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侧重于从阶级的视角阐释无产阶级的劳动异化。他认为异化是在商品交换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异化的核心是人与人的本质的相互疏离。在他看来,人的幸福问题与人的价值、人的意义等问题一样都是对人的本质追求和探索。受时代的局限,马克思的异化观点主要关注劳动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所带来的非人化的后果。[2]卢卡奇与马克思不同,他认为异化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异化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是资本主义社会机械化大生产、技术理性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技术理性时代各种社会文化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这种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的控制和消解,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所取代。使物化的普遍化衍生为物化的内化,变成一种统治和支配人的精神活动和心理活动的物化意识。可以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站在马克思异化的基础上,对其理论的“微进化”,使异化理论更加完善和发展。虽然我们不知道卢卡奇是否与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扎米亚京相识相知,是否研读过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文学开山之作《我们》,①但其理论确实与《我们》的构想不约而同,成为物化在文学创作上的呈现。《我们》中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生产领域还是意识思想领域,无一不是对其“物化”现象和表现形式的生动展现。虽然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属于哲学范畴,《我们》也没有列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中。但是,作为同时代的人,二者对社会的发展脉络从不同的层面走向相同的认知。如果说反乌托邦文学自带“异化”的特征的话,那么作为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的《我们》则更青睐于卢卡奇的“物化”属性。
包装箱瘦身、循环使用中转袋(箱)、送货使用纯电动车……今年“双11”,云南快递业刮起“绿色环保风”,为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增添一份力。
成书于1920年的《我们》是扎米亚京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奠基作品。扎米亚京虽然是俄罗斯作家,但他的亲身经历和背景确是处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虽然《我们》一直被视作反对社会主义、映射极权统治而被当时的苏联社会所不容,但是就其产生的年代和背景来说,《我们》构建的社会图景首先定位在机械化大生产的背景下,更多的是对未来技术理性超越式发展所造成的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危险的预测和警示。更加注重的是社会发展中人的异化问题,重点关注的是社会以及存在其中的人。
基于C型环结构的环偶极子超材料设计与仿 真 …………… 赵崤利,王 爽,朱剑宇,王 松,李 泉(11)
《我们》故事背景是在一千年之后的大一统王国,用主人公的生活,向人呈现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完美”世界。故事中大恩主为大一统王国的灵魂人物,王国的成员作为人却没有属于人的名字,只有代号,生活在暴露的毫无隐私可言的玻璃房里,生活不受自身控制,《守时戒律表》是人们生活的准则,几百万人的作息比机器还要准时,在同一分、同一秒起床、工作、结束工作,“性活动日”人们才可能找回一点点自尊,放下玻璃房的窗帘,即便如此,也是有票才有资格进行,获得票的程序亦很复杂,“性管理局对每一个号码进行血液检查,根据号码血液中的激素水平来决定性活动日的具体时间,在这个流程走完之后,号码才可以申请票”意味着统一大王国中,没有感觉亦没有爱情,人性伦理灰飞烟灭,自由、个性、人权通通沦丧。主人公举出了个体对群体的例子,“天平的一端是一克,另一端是一吨,显然一克为我,一吨为王国;这就可以得出,属于王国的一吨,应该享有足够权力,而属于我的一克,则只配拥有义务,否则,就会出现一吨等于一克的情况。王国中想要使我变得伟大,就可以把我想象成为一吨的百万分之一。”《我们》中有乌托邦文学“去私为公”观念,但“乌托邦”精神在现代工业社会下没有实际意义,反倒成为主客体颠倒的借口和手段,为大恩主的极权统治创造条件。在这个“乌托邦”的王国里,物化已浸染到各个领域,政治领域、生活领域、思想意识领域物化随处可见。政治统治、生产生活、思想心灵都经过合理化的计算固定下来,一切都尽在掌控之中,号码们只需充当“快乐的数字”按照既定的程序幸福生活即可。情感、个性等无法合理化计算的都成为病态的、应消除的不稳定因素。人在社会里完全沦为客体和附庸,行尸走肉般活着,完全印证了卢卡奇提出的物化的人和社会。可以说,《我们》是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小说版。
首先,主人公D-503以第一人称“我”记录下“我们”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这一数字记录的写作方式开启了小说数字化的表现方式。记事本里记载了号码们高度统一的生活、工作和作息,在有神一般权威的统治者的管辖下,大一统王国就似一双眼睛监督人们在透明的玻璃房中完成各种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成为机器,不如机器,作为机器的一部分,获得“数字般精确、绝对的幸福”。整齐划一的社会化生产使人抽象为一个符号,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台大机器,国民仿若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全部以号码数字标识,男性为阳性号码(奇数),女性为阴性号码(偶数);小至衣食住行,大至社会各项决策都有条条框框的束缚,社会生活的“和谐统一”都如数字般精准确定。小说不仅在人物称谓设置上用数学符号表示,更是把数学运用到人的精神层面,使人的思想都达到了数字般的抽象化。为了对感情进行数字化处理,大一统王国制定了性活动日期表。一切情感都通过数字化的处理变成可衡量可计算的数字确定下来。大一统王国的生活准则《守时戒律表》把号码们训练成没有人格的机器和数字。人的活动演变成专门的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号码们脱去了情感的外衣,如数字般刻板机械,也如机器般冰冷僵化。身为大一统王国公民,只要按照设定好的程序就会得到想象中的机械化的幸福生活。“我”既是个体也是“我们”这个整体。在“我”和“我们”之间只存在数量上的差异,没有个性的区别。 “我们”是数字,是符号,是没有人类情感和精神需求的代码。 “我们”这个题目也在突出强调数量,弱化个体,突出整体性和统一性。这里人的主体性已经失落,人变得抽象化和数字化。扎米亚京根据机械化大生产的社会现实,创作出数字化的号码们,大胆预测未来人类社会必将走向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批判了人的数字化导致的过分依赖使用机器,最终会变得像机器一样,丧失人性特征。
作为科学学科教师,无论是刚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的,还是中途转岗教学的教师,都需要有一个不断学习和自我完善的过程。课前,都必须要熟悉《课标》,都要仔细研读教材课标的要求,对要涉及的实验进行预做,对实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才会了如指掌,教学时才能有所防范。课中,师生的实验操作必须规范、严谨,认真客观地对待实验进程,仔细分析实验现象,探究实验结论。课后,作为教师更要要及时反思和总结实验中出现的问题,以待下一次实验中有所改进。
暴雨灾害又被称为洪涝灾害,这一灾害对农业生产也能产生较大影响,影响比例为20%。特大暴雨、持续性暴雨一旦发生,将形成严重的暴雨灾害,此时易发生河岸决提、洪水泛滥等,而一旦洪水偏离了河道,则直接造成农作物被淹没或冲毁,影响作物产量甚至导致颗粒无收。在我国暴雨灾害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东南部地区易出现,集中分布在黄淮海流域。
卢卡奇物化理论第二种表现形式就是主体的客体化。人由在生产过程和社会发展中的自觉自动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或追随者。人的属性和特征日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我们被整合到大一统的整个机械系统中,成为这个自给自足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个人必须绝对地服从这个系统。因此,在大一统王国中,个人的意志完全丧失,变成客体和追随者。 “我们”的世界类似于监狱,所有人都必须遵守《守时戒律表》,同时作息、散步、吃饭、工作,包括性生活也要遵守统一的安排。人是被抽取了人的特征的抽象物,没有名,没有姓,是被奴役的奴隶和没有意志的行尸走肉。[7]在《我们》中,时间成为限制人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家在每个号码身上都装有一台看不见的、轻轻滴答作响的计时机,所以号码们不用看表,也能准确地知道时间。戒律表和计时器统一规定着号码们何时该做什么动作,人的个性在时间的界定下消解。虽然暂时号码们每天还有两个小时的个人时间,可以获得短暂的有限的自由。但是D-503也预言说总有一天这段时间也会被统摄到守时戒律表中去,这也就意味着人终将失去个人时间,也就是失去自我。
卢卡奇物化理论中主要有三种物化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数字化。数字化是工业社会理性化进程的产物。在工业化社会中,由于生产过程中机械化和合理化的加强,劳动逐渐演变成可计算的工作额定,人变成了抽象的数字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失去了主体性和能动性。人的活动(劳动)在机器化大生产中变成了一个专门的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活动失去了其活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我们》对这一表现形式使用得尤为突出。整篇作品都与数学密不可分。作品中随处可见数学号码、数字符号、数学公式。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与数学息息相关,缺了精准计算的数学应用,“大一统王国”将不复存在。
卢卡奇物化理论第三种表现形式是人的原子化,即人与人的隔膜、疏离、冷漠,丧失了统一性和有机的联系,变成了各自孤立的、被动的原子。也就是说,社会生活中人的关系已经完全被物的关系和物的原则所取代。在人类社会关系中,最小的社会结构应该是家庭,个体的人网结于其中。家庭繁衍出后代,作为夫妻情感的纽带和桥梁,延续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而《我们》的社会中取消了家庭的维系,情感是不被需要的、病态的东西,后代也不再是维系情感的手段而变成了可生产制造的物品。一切都是可量化,可计算的。不能计算和衡量的东西是不被社会所需要的。也就是说,异化的社会中个体的人就像原子一样成为了最小的、不可再分割的单位。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疏离、孤独、独立的存在,人被彻底孤立化,原子化。没有家庭,人与人之间没有情感纽带的维系,人变成了冰冷的符号,就像孤独而被动的原子,整齐划一地生活。国家预先设置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行动。“我们”构成一个“完美”的原子化社会。人与人之间不需要情感和人际交流。“我们”丧失了人的特征,也丧失了对社会正常的理解能力,展示了异化的特性和命运。“我们”生活在玻璃房中,一切活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中,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们都是平等的,同一时间做出相同的动作,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经过合理化、可计算的。也意味着我们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情感。我们融合成具有百万之手的统一身躯。从肉体到精神都没有“我”的位置。因此,当主人公“D-503”看到绿墙外正常的人类社会图景时,才会震惊茫然,并困惑为何当时的国家政权能够允许没有大一统王国这样的时间戒律表?怎么能不对用餐时间、起床、睡觉、劳动等事项做出精确安排,而任人随意安排自己的活动?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当时的国家对人的性生活也放任不管,不管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及进行多少次性交,都由自己决定,完全不像大一统王国这样按科学规律行事。这里折射出一旦正常的人类情感纽带断裂,那么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就会自动屏蔽人类的情感,反觉得正常的情感非常荒诞怪异。也就是说一旦人进入原子状态,那么人类正常的情感需求和行为习惯就会呈现一种陌生化的模式,亲情、爱情、友情等正常的情感都变成了一种多余的、妨碍幸福的病态的情感。因此,当“D-503”恢复了人类的情感,品尝爱情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矛盾的、纠结的,他觉得自己是病态的,喜忧参半的:既陶醉于爱情的甘甜,又恐惧此情感的诱惑力。只有消除这种不安全的情感,恢复原子的孤立状态,消除这种“病态、不确定的情感”,才是通向“幸福之路”的必然选择。所以,大一统王国的号码们可以笑看大一统王国对于产生情感的“病态”号码的极端处理方式。这种正常情感的缺失和消解使大一统王国的“一切完美制度”表现出怪诞和荒谬的效果,致使大一统王国进入幸福的疏离状态。
为了对比主客体的异同,“我们”中用较少篇幅描绘了一个与大一统王国不同的绿墙外的世界,虽然只描绘了一点事物,但却是《我们》中最具特色的一个部分。从字面上看,绿墙内外的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绿墙外的世界物质不够丰富,但是在那里有“我”复苏的情感,有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的感受,有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体现了人对人的本质回归的强烈渴望,以及作为“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恢复的迫切需求。那是与丧失主体地位的号码人不可同日而语的。不允许个性和自由,大一统王国本质上已是扼杀人权拥有绝对物质的极权统治,这种世界会让人们恐惧乌托邦世界,丧失对理想世界的信心。完美世界如不考虑人性,主客体颠倒,那么即便物质上再丰富,人也不过是满足口福之欲的躯壳。
在“我们的世界”里所有人的情感诸如爱情、亲情、友情等等都是病态,是获得幸福的阻碍,需要手术治疗。这里不需要也不允许号码们有个体的思想,个体的自由。每个号码都应该是“大恩主”的追随者,是“我们”这个整体。人的属性和特征在“我们”的压制下不断的消解,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爱和劳动本来是避免客体化的主要途径,但是在大一统王国里这两条途径也是行不通的。王国里不需要也不允许爱情的存在,《刑法典》里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国家在解决了生存的第一要务饥饿之后,就要开始向另一个主宰爱情宣战。要把这种不受国家控制的个人情感进行数字化处理,变成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控制的物质。人从主体地位变成性的客体,每个号码作为性的产物对其他号码享受权利。在大一统王国里,不会再有爱情悲剧、占有嫉妒等情感的困扰,因为爱情已成为荒唐的过去,号码们不再有任何嫉妒的理由,现在的号码们已经不需要知道什么是爱情,爱情已沦为像做梦、体力劳动、吃饭、排泄等其他生理功能一样。而劳动同样如此,在大一统王国中,只有大恩主一个人是劳动的主体,其他号码们都沦为劳动的工具。号码们日复一日重复的劳动,被训练成一架劳动机器,却仅能得到必需的生活用品。从大一统王国一直宣扬的《三个获释的农奴》的故事可以看出人的物化达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故事讲的是大一统王国进行了一项关于劳动的实验,有三个号码被解除了一个月的劳动,任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三个可怜虫已经习惯了统一的劳动,因此不能劳动的他们只好在过去劳动惯了的地方逛来逛去,眼馋地朝里面张望,在规定的时间里,站在场院里不断地重复着劳动动作。因为这些动作早已变成了他们机体的需要。虽然手中没有工具,但是他们依然做出拉锯子,推刨子,握锤子锤打铁块的动作。不能劳动的痛苦最终催毁了他们,“不劳动毋宁死”,他们手拉手,伴着《进行曲》节奏走入河里, 让河水解除了他们的痛苦。从这里可以看出,不劳动毋宁死的号码们机器化程度之高达到令人恐怖的地步。劳动已不仅仅是人的需要,而是变成了“劳动需要人”。[3]
社会发展最根本、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谈到人的解放和幸福,必然会涉及到现实社会中的人的主客体关系问题。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人的异化问题在近现代哲学发展演变过程中一直得到重点关注。费尔巴哈把对异化问题关注的重点投入到宗教方面,而黑格尔则一直探索精神异化问题。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关注劳动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所带来的非人化的结果。他的著名的劳动异化理论关注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人的解放。他将目光主要投注到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困境主题,较少关注文化层面上普遍的文化力量对人的异己统治问题。而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技术统治、理性至上时代的到来,卢卡奇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创新性地进行了解读,提出了物化理论。这一理论从根本上完成了技术理性统治时代的文化批判的主题转换。物化理论虽然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相同,即同样致力于批判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但他的理论不仅仅分析人的劳动,而是与近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大生产、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着重对技术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批判,重点阐释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以及社会文化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而这种以社会文化力量消解人的主体性的观点恰恰契合了俄罗斯反乌托邦代表作《我们》构建的“幸福社会图景”,也打破了《我们》所营造的幸福社会的虚幻和荒唐。
人类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探索完美社会制度构建,期望建立一个物质丰富,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完美社会。从思想家到文学家,从柏拉图到《乌托邦》,从思想建构到文学想象生成,完美国度不断建构不断消解。直至20世纪发达工业社会带来了虚假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让人觉得人类无所不能,误以为借助科技力量一统天下缔造完美国度指日可待。刻意地忽视人性的复杂性、多变性,期望用政治上的铁腕和科技力量强行地把人类推向“幸福”。可事实确是20世纪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和谐完美,相反人类失去了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危机严重,道德沦丧带来精神危机,共产主义的火车头并没有向我们驶来。扎米亚京的《我们》虽然没有探讨生态危机的问题,但是其营造的政治危机、心灵危机也足够振聋发聩。《我们》的世界如一道闪电劈向盲目乐观的人们,借助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深刻地揭示出“物化的我们”是多么的可怜、可叹,构建的“幸福社会图景”是多么千疮百孔、不堪一击。反乌托邦文学具有异化的天然属性,作为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我们》更是物化现象呈现的加强版。物化的人是不幸的,也是不可能幸福的。物化的世界也不会、也不可能是幸福完美的社会。《我们》中刻画的“幸福社会图景”处处可见人的异化和幸福的疏离。幸福和自由的悖论在《我们》中依然没有解决,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更进一步揭示了“我们”的末日:“我们”已经处在地狱的边缘,无论如何精心粉饰,终究逃脱不了“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命运。
注释:
本文对《我们》引文皆出自叶·扎米亚京著:顾亚玲、邓蜀平、刁绍华译,《我们》,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本。
参考文献:
[1]颜军.马克思幸福社会图景的异化批判逻辑及其价值意蕴[J].东岳论丛,2017,(11):48.
[2]衣俊卿.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一种演进思路[J].哲学研究,1997,(08):11.
[3]余自游.悖论与悲剧—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5:20-21.
AnalysisonWefromthePerspectiveofLukacs’MaterializationTheory
YANG L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Qiqihar University, Qiqihar Heilongjiang 161006, China)
Abstract:Disassimilation?is the natural attribute of anti-Utopian literature. Criticism of disassimilation?phenomen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onstruct Marx's happy society. The social picture construction of We - the first work of anti-utopia in the 20th century coincides with the materialization theory of Lukacs, the founder of Western Marxism in the 20th century. Lukacs' materialization theory inherits and deepens Marx's theory of disassimilation, revealing the?materialization phenomenon in a "happy society"?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destruction of such a “happy social scene”?in?We.
Keywords:lukacs’;We; ethics; materialization
收稿日期:2019-05-24
作者简介:杨雷(1970-),女,教授,文学硕士。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WY2018069-B);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业务专项人文面上项目(135109501)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9)09-0128-04
(责任编辑 吴明东)
标签:王国论文; 乌托邦论文; 社会论文; 理论论文; 号码论文;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论文; 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WY2018069-B) 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业务专项人文面上项目(135109501)论文; 齐齐哈尔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