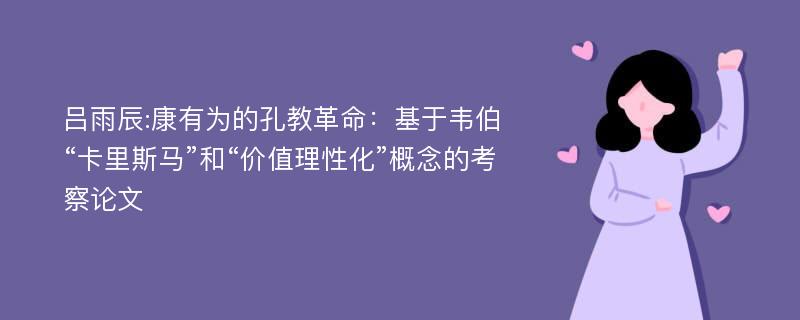
摘 要: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关键词:康有为 孔教 韦伯 卡里斯马 价值理性化
一、引言
李猛(2010)的《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是将韦伯学说和中国问题相结合的一篇重要论文。该文不仅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梳理了韦伯的中国观察,而且重估了中国在与理性化的西方碰撞以后的命运,可以说,它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语境中对韦伯学说做了再阐释。相比于韦伯笔下中国传统社会的静态性,近代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总体性变迁,要将韦伯学说延伸到这一时期绝非易事。
韦伯(1999)的《儒教与道教》一书考察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各个面向,却将重心放在对儒教及其担纲阶层的剖析上。在题为“儒教与清教”的结论中,他指出了儒士阶层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及对巫术的容忍,把这看作阻碍理性化资本主义发展的症结。借着后见之明,笔者看到了晚清一批革新派儒士的反传统言行及其变教和创教激情。可以说,恰恰是从儒学1.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本文只在转引韦伯文本等必要场合使用“儒教”一词,在其他时候一律使用“儒学”的措辞。但是需要明了,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教”和“学”并不构成分化的领域。传统的担纲者当中,走出了一批理性化转轨的“扳道工”。这是否意味着韦伯的中国观察失去了效力?
作业过程中难以实现雨污分流,异味问题更是十分严重。挖掘机作业时每一斗的接力摆渡,以及无意间的垃圾翻动就是一次异味释放,该工艺的环境控制是通过喷洒生物除臭剂得以实现的。
在对李猛文章的研读中,笔者格外关注了“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移置于近代中国的意义。李猛(2010)强调,韦伯的这两个概念看似很不同,却都具有冲击传统的革命性。同时,二者在冲破传统和塑造实践伦理上的力量都局限在初始时期。李猛(2010)指出,中国的理性化始终具有移植性的特征,并且凭借了官僚体制的支配性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暗示了这样的观点:即便看起来是把西方现成的理性化成果拿来的过程,但在其初始阶段,仍然离不开卡里斯马推动的“个性”塑造与价值理性化推动的“非人格性”的社会秩序之理性化。这两点不仅是西方理性化的奥秘,也可以用来对中国的近代转型做发生学的考察。
甲午战争以降直至清亡的近二十年,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在中国近现代的第一个激越期。在这个激越期中,分水岭式的关键事件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作为这次变法的深度参与者,也作为这一时期最激进的意识形态革新(即孔教)的首倡者,康有为被笔者选定为首要的研究对象。本文可以看作是把韦伯的比较宗教学理论和本土的现代性经验相结合的一次初步尝试,它不是在韦伯的西方研究史的脉络中追踪线索或者辨析概念,而是用这些概念来观照近代中国的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
康有为(1858-1927年)和韦伯(1864-1920年)是同时代人,尽管彼时中德两国的国运高下悬殊,且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进入现代性,但是两人之间却颇有可以会通之处。在国族和文化的危亡境遇中,康有为在以“保国”为目标的诸项纲领中,一方面富于远见地提出“物质救国论”和一系列体制性的改革日程,另一方面却特重“保教”,可以说是以孔教为终极的依归。这种思想取向,让人想到韦伯在审视西方的理性化进程时是如何遍历各个领域而最后聚焦于宗教(韦伯,2007:[前言]12-13)。下文的内容将揭示更多的可比性,譬如,康氏在反思孔学2.在本文中,“孔学”与“孔子之教”同义,意指围绕孔子的生平、门徒、撰述的教—学传统,其含义较“儒学”为窄。“孔教”则是康有为缔造的儒学革新形态的名号。不振的症结时,把矛头指向“巫觋”、“淫祀”、“神怪”这些民间宗教的具体形式,这和韦伯批评儒学在祛魅上不力恰好形成了某种应和。再如,康氏对于世界诸宗教的演进史、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未能跳脱传教士所提供的知识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讲,戊戌变法前后的康有为,相当程度上也默认了“基督教中心主义”的预设,而这恰是当代学者对于韦伯的突出批评。
本文分为六节:第二节对韦伯的若干概念及其中国观察做简要介绍,并引出他的“中国转型之问”;第三节解析康有为的卡里斯马自觉的产生以及他对孔子和孔学的神秘化再阐释;第四节论述康氏如何筹划对孔学作普适化的重建,却又迫于现实的情势转而附议“庙产兴学”;第五节较系统地呈现孔教革命在理性化进程中的努力和困境、张力和背反;第六节引入太平天国和“主义”政党作为对照物,明确化孔教革命的历史定位。
二、韦伯学说及其中国观察
本节将参照李猛(2010)一文的内容,在儒学传统的背景下,对价值理性化和卡里斯马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做一个最低限度的介绍,一些引述留待后面的章节。
在开始之前,先有必要对“理性化”这一术语做一澄清。与检视孔教思想时所用的价值合理化的术语不同,理性化更多地被用来指称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世界的转型进程的核心特征。理性化的理论视野十分宏阔,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通俗意义上的“现代化”。在理性化的进程中,一方面目标理性以不可逆转的趋势不断自我复制与强化,但另一方面,目标理性又和诸种价值理性以及其他社会行动类型生成着非常微妙复杂的关系,充满了紧张、危机、冲突乃至裂变。
教师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告知学生,较多的生物学家认为,人类正处于生命史上速度最快、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灭绝中。在未来50年,如果人类不断地砍伐森林,栖息繁衍于其中、占地球半数的物种都可能会灭绝,呼吁学生要树立起保护地球环境的意识。
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何以仅诞生于西方文明?正是基于这个提问的“视角”,韦伯认为清教推动了狭义的价值理性化。对此有必要结合目标理性的概念来看。一方面,近代西方的独特道路、其社会行动的特征主要是以目标理性的逻辑来设定的,因而带有“态度和行动上的相似性、规律性与持续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全新的生活秩序的出现,其关键却在于自觉的价值理性化的推动——在经济伦理这个韦伯最为关切的面向上,扮演扳道工角色的是新教改革后的加尔文教派(李猛,2010:4-5)。
回过头来看孔教。康有为的这一宗教改革尝试将儒学转化为一个价值合理化程度更高的救世性普适宗教,然而这一改革工作面临两个基本的困境:其一是,孔教在知识论上的一元调和主义进路及其试图重塑政教关系的努力与价值理性化的分化趋势相背反;其二是,作为泛宗教领域的价值合理化努力,孔教却置身在一个科学理性主义正当强势的世俗化时代。这两个基本困境各自对应了上文所论的价值理性化的两点内在张力,即分化之作为价值理性化的内在要求和分化的价值理性之间的此消彼长。
韦伯(1997:495、500)在宗教高人类型学的视野下,对“先知”的特征做了如下描画:纯粹个人魅力的体现者,根据自己的使命宣告一种宗教教义;履行“个人的”使命而不是根据他人的委托,从而有别于神职人员;为了自己的宗教目的而篡夺权力。深度介入戊戌变法之前的康有为,无论是厌弃文典学习,经由修炼自证其宗教禀赋与救世使命,还是自许教主、藐视儒士阶层的传统权威,都十分符合广义的“先知”的范畴。梁启超和谭嗣同都把他们的老师看作孔教之马丁·路德(梁启超,1998:424;谭嗣同,1998:173),也就是说,一个有先知色彩的“宗教革新家”。这是专指戊戌前后这一时段而言的。12.塞巴斯蒂安·古兹曼(Guzman,2015:73、81、85)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质理性支配”(substantive-rational authority)的概念,以对应于四种社会行动类型中的“价值理性行动”。路德被古兹曼看作是这种支配形式的典型。这个新提法对于把握康有为也颇有价值。下文中我们将一再看到,对于康氏的心智世界来说,神秘主义的宗教体验和外来的世俗西学并不互相排斥。“实质理性支配”的提法对于把握这种兼容状态很有帮助,它还进一步说明了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之间的相通性。
在抽象意涵上,就最一般化的界定而言,卡里斯马意指“一个人的被视为非凡的品质……因此,他被视为天份过人,具有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的……力量或素质,或者被视为神灵差遣的,或者被视为楷模,因此也被视为‘领袖’”。在这个定义中,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其一是支配正当性来源于领袖个人,从而区别于传统型和法理性支配者来自外部的正当性;其二是领袖禀赋相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性”,尤其是对于经济生活的陌生感;其三则是决定性的——卡里斯马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关键在于“追随者们”对于领袖的品质做出何种评判(韦伯,1997:269、272;Ji,2008:49)。
实际上,马铃薯种植密度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管是土地环境还是马铃薯品种都会影响马铃薯的产量,因此在种植马铃薯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当地的土壤情况,选择适合当地的马铃薯品种,随后根据土壤条件控制马铃薯种植密度。
这里面最重要的特征三,意味着韦伯的卡里斯马概念并不追究领袖是否真有超凡脱俗的内在禀赋,它具有很强的“建构主义”特征而绝非“本质主义”的。这一方法论取向有助于处理两方面的操作性问题:其一,记载卡里斯马领袖言行的文献常有诚伪难断的问题。康有为的《我史》就是典型。其二,卡里斯马式的宗教领袖多是“先时之人物”,相比于身后持久而巨大的影响力,他们生前作为真实个人或许建立过的支配关系,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意义反而较小。许多情况下,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四部《福音书》中的耶稣基督或是《坛经》中的六祖慧能,如果以严格的“信史”为标准,那么对这些典籍的运用实在是无从措手。但是,如果从“建构/象征的卡里斯马”的角度去看,那么文献不足征的困难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事实上,历史上围绕这些宗教领袖形成的卡里斯马支配,无论是它的起源阶段还是转折更生阶段,都是和杰出的布道家或是宗教改革家的建构工作相伴随的。6.胡适把弘扬慧能南宗禅的神会比作“禅宗的保罗”。神会和保罗,是布道者式的卡里斯马的理想类型。康有为对于孔子形象的重塑,无疑是基于对上述情形的高度自觉。
价值理性化和卡里斯马之间有同有异,先看异的方面。首先,卡里斯马是一种个体性、人身性的内在力量,而价值理性化则和观念领域关联更密。其次,前者始终是激越的颠覆性的力量,而后者只在特定时期才如此。最后,价值理性化不仅“在否定的方向上牺牲习俗,也牺牲情感性的行动”(李猛,2010:6),因而这一过程常常包含着对卡里斯马的抑制。
再看两者相通的方面。除了反传统的革命性以外,上文还指出了价值理性化在其根基处的“非理性”,而这也是它和卡里斯马共有的特征。当我们把这两点共性放到清教革命的语境之中,就能够初步把握“祛魅”的含义:在价值理性化、卡里斯马和传统之间,就如在价值理性化和目标理性化之间,充满了冲突和深刻的张力。清教背景下的理性先知预言,确立了一种理性化的、生活一体性的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与植根于巫术之中的经验现实高度紧张,并导向对于生活和世界的彻底重估。这个重估剥夺了巫术式的世界图景的魔力和意义,从而为理性取向的入世支配的实践伦理铺平了道路(李猛,2010:2、21)。7.如王斯福(Feuchtwang,2008:91)所指出的,卡里斯马可以被应用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普遍历史情境当中,但韦伯当初发明这一概念的用意却是指向现代性、世俗性和祛魅的。
何师傅,明天就不要来了,晚上老钳工在这里,白天,我还能动,你能来看我,就感激不尽,你每天来护理我,我心里不安呀。
回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中来,在韦伯的观察中,无论是价值理性化还是卡里斯马,都未能冲破“传统主义”的普遍支配地位。这突出反映在儒士这个主导阶层的“精神”特质上。就价值理性化来说,尽管某种意义上的理性化乃是中国家产官僚制和儒家伦理的固有特征,但在儒学理性主义的内核中却早已嵌入了对“永远如此的传统本身”的“恭敬”,使其无法克服传统的束缚而陷入停滞;而儒士阶层作为儒学政教事业的担纲者,集中体现了这种外在形式化的“实用理性主义”。就卡里斯马来说,酒神精神对于崇尚克己复礼的儒学传统乃是全然陌生的,“麻醉与放纵的‘着魔’剥掉了一切卡里斯马式的神圣评价,只能被视为受恶魔控制的征候”(韦伯,1999:284-285)。与儒士阶层注重礼仪外表的形式主义相映衬的,是一种“警醒的克己、自省和矜持”的心态。李猛虽然批评韦伯只知“礼之文”,不知“礼之质”,但是也承认儒学的伦理气质是情感和礼仪取向的,无法达成清教伦理的那种意志和伦理取向的理性化(李猛,2010:8、10、16-18)。
传统主义赖以维系的另一要义在于“巫术”的恒久影响力,儒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对其无从摒弃。事实上,由于巫术性的信仰和心态在“孝敬”和限制专断皇权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使它得以渗入儒学伦理的隐秘之处(李猛,2010:10、18、25)。其结果就是,儒士阶层虽以施行教化为己任,也成功地使儒学礼教沉淀在了一般民众的生活日用当中,但是和清教相比,它并未能充分地将巫术从民众乃至自身的信仰生活中祛除出去。8.可参见杨庆堃(Yang,1961:250-265)论述儒士阶层用以“知天命”的种种巫术性手段,特别是占卜、风水、面相术等,此外还需注意围绕科举及第的天命和报应观。由此可见,儒士阶层的理性主义和巫术之间的紧张性并不如清教传统中那么强烈。佛教的情况亦然。9.韦伯(1996:437)指出,大乘佛教在中国,就像它在印度一样,不得不对俗人信仰做出各式各样的让步,接纳祖先崇拜、风水、驱邪等传统的宗教形式。如此这般的结果是,佛教无力对“巫术的大花园”做实质性的改变,它对于中国人生活态度的影响主要在于强化了人们的恭顺戒律和同情体谅之心。
一方面是儒学传统与皇权—官僚体制的主宰地位,另一方面则是渗透在民间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巫术性力量,共同拱卫了中国人在生活之道和社会秩序上的传统主义。那么,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打破这些障碍,为理性化进程开辟道路?——或许可以这样概括韦伯的中国转型之问。这个发问也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
三、作为改制教主的康有为
康有为是晚清政坛和知识界的一大改革家,本文聚焦于他作为宗教改革家的一面。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思路,早先多将康氏的宗教改革作为服务于维新变法的思想工具来看,近年来则主要将其放在康氏民国后的生涯中,从文化—政治保守主义的角度来加以把握。本文拟跳出思想学术史的交叠脉络,先从卡里斯马的概念视角出发,揭示康氏的孔教思想在其原初状态的革命性及其驱动机制。
康有为早年的圣人情结广为人知,但是尚须加以更严肃的对待。据康氏自订年谱《我史》,1878年21岁时,从学于大儒朱次琦的康有为剧烈地偏离了经院修学的正轨,有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开悟体验:
……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茅海建,2009:14-15)
澳大利亚不同年龄段消费者对于酒种的偏好具有较大差异:14~17岁年龄段消费者更偏爱喝预调烈酒,但随着年龄增长,喜爱瓶装葡萄酒的消费者占比逐渐增加,而预调烈酒的占比逐渐减少。对于烈酒,14~17岁年龄段消费者消费烈酒比例占该群体总消费酒精饮料的60%,为各年龄阶段群体中最高。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消费者饮用烈酒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8~24岁年龄段消费者消费烈酒的比例占该人群总消费酒精饮料的22%,为各年龄阶段群体中最高。25~29岁及30~39岁消费者消费普通烈度啤酒占该人群总消费酒精饮料的27%,为各年龄层最高。具体情况见图2。
弃学静坐,反映出康有为厌弃汉学、喜好宋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基本倾向。10.这个倾向虽然在朱门是异端,但是在更大的文化地理背景中却是渊源有自。参见杨念群(1997:216-268)对于“岭南神秘主义”的研究。若从卡里斯马的视角去看,此时的康氏已经有了跳脱经典考释这种传统型的行动,从自身内部寻找力量和启示的冲动了。根据茅海建(2009:15)的研究,这段文字的最初版本要惊世骇俗得多,如开悟后的“自以为圣人”,原版为“自以为孔子”。如果说以圣人自许还是一种得到儒学正统首肯的传统主义取向的激越,那么“自以为孔子”的体验就是一种革命性的僭越了。11.不仅如此,发展到后来,康门弟子各以“超回”、“轶赐”等为号,自视优于孔子诸门徒。在这个语境下,康有为自号“长素”,无论其最初的含义为何,都确已含有了“长于素王”之意(黄彰健,2007:47)。
一年后的1879年,康有为在西樵山白云洞专习道、佛之书并进行修炼。如果说前一年的静坐实践及其体验仍可以看作是宋明理学家静坐传统的延续,那么此时的康氏就已经进入了异端外道的神秘世界:
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者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茅海建,2009:15)
在日后的回忆中,康有为对自己的这两次宗教经验做了较为否定的评判,认为前一次是“《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后一次的“狂喜大乐”只是“以为证圣矣”(唐文明,2012:38)。但是,这并不影响以下推断:当日的康氏因为有了此种证悟的体验而大起济苦救世之使命感,乃至有日后的孔教之议。原始手稿中尚有“复以民生多艰,□□我才力聪明,当往拯之”等语,亦是证据(茅海建,2009:15)。
(4) 在下横担以下部位,4类场地下钢管塔的位移都很小且大小几乎相同,在下横担以上部位钢管塔的位移随着塔身的增高而明显增大.
固然,康有为早年的宗教体验,即便不是日后的自我神化,也无从考证其真伪。但是,康门弟子心悦诚服追随左右的事实,已经让这种宗教卡里斯马具有了现实性的支配力量。章太炎(2003:3)在1897年的一封信中说:“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固然,章氏对康氏怀有很深的敌意,但是他所描述的这种激昂而躁动的氛围确是当时康门的实情。梁启超自己在民国后的回忆中也写道:“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书》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黄彰健,2007:53)。这种初次接触隐微义理所产生的强烈感受,恍若听闻“第一义谛”的大乘佛教信徒的“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此外,梁启超(1998:427)还曾有将康氏拔高到救世菩萨行之高度的描述,虽然不乏宣传的意味,但也反映了在当时佛教洋溢的氛围中,他们对于导师乃至自己的期许:“不歆净土,不畏地狱;非惟不畏也,又常住地狱;非惟常住也,又常乐地狱……以故日以救国救民为事”。
从卡里斯马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如实理解康有为“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的超人自信的源泉所在,也才能理解康门义理授受、锐意变法的精神枢纽为何,乃至谭嗣同甘为变法事业流血的信念所立之基。如果只从今文经学演进的理路,或是西学、佛学的思想刺激出发,则可能导致问题视野的窄化,把思想观念层面的消长和裂变等同于人与群的行动本身。康有为之所以能够创设孔教,首要的即在于他个人的宗教卡里斯马成为凝聚一个革新派小团体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从困境和激情出发,由内而外重塑了康氏及其弟子的信念和行为方向。作为宗教革新家的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重新宣告一种(真正或者据说是)旧的默示”(韦伯,1997:495),通过向传统的神圣起源的回溯,揭示并宣布要解除它在特定历史时期受到的遮蔽,让它的精义在今日重光并扩充其逻辑,抵达更彻底的境界。
在此有一个分期界定的工作要做。本文所聚焦的是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和此前此后的一贯观念——即以孔教为“人道教”而区别于西方等国的“神道教”——相对照,此一时期康氏的孔教运动激活了儒学传统中宗教性的一面,而他也以改制教主的使命自许而卓立于世。虽然仅有短短的几年,但这却是孔教唯一富有反传统意蕴的时期,此时恰逢理性化转型关键的“初生阶段”。下文将以“孔教革命”称呼这个时期的孔教,以便与康有为流亡以后、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孔教运动相区别。
7套试卷知识点来源于高等数学专业知识与高中数学知识,包括极限,一元函数微积分,级数收敛,矩阵及其变换,概率与统计,空间直线方程,平面方程,曲线方程,简易逻辑,算法框图,数列,函数等等.重视大学本科数学专业知识,考察最基本、常用知识点、性质及其相关定理的应用,仅考查中学数学知识点的题目少;若仅考查中学知识点,一般为概率与统计模块,利用分类加法与分步乘法原理确定随机事件的概率,且题目载体相似.
戊戌变法被学界广泛地看作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分水岭。即便有日后的大量作伪,康有为在这一变法运动中所发挥的扳道工的作用也是不可抹杀的。孔教思想在戊戌变法的政改蓝图中不占重要位置,现实意义似乎很淡。但事实上,它不仅关乎康门投身变法维新的驱动力问题,而且为现实变革扩展了意识形态的纵深。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日后中国的转型进程有着深远的开启意义和征兆意义。
带着改制教主抱负的康有为,力图宣告一个据说是旧的、被扭曲的神圣传统的重光。而孔子之所以被塑造成托古改制的教主形象,虽然有学理上的推演论证,但更主要的是,康氏基于“自以为孔子”的超越性体验而获得的一种对历史人物“身临其境”的主观把握。康氏的卡里斯马自证是他日后建构卡里斯马化的孔子的先决条件,而具有了“建构的卡里斯马”的孔子形象,则为康氏的变法改制活动提供了支配的象征资本。上述的建构工作,主要是以彰扬“圣人以神道设教”展开的。
在康有为一贯的理念中,孔子因为“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而使儒教成为最先进的宗教。其实即便在孔教革命时期,他的这个理念也并未真正改变。康氏在此时强调神道设教的关键考量是树立在其三世说基础上的宗教进化观,即从多神教先演进到一神教,再至无神的人道教。康氏进而指出,“中国尚为多神之俗,未知专奉教主,以发德心”,因而有独尊孔子的必要性;而恢复孔学的神道面向,则是尊孔的主要途径。康有为说:“孔子六经、六纬之言鬼神者晦,而孔子之道微……魂灵故孔子之道,而大地诸教乃独专之,此亦宋贤不穷理而误割地哉!”(唐文明,2012:124-128)为此,他着手对儒学进行系统化的改造,以便将孔子从儒学的注解常轨中摆脱出来,以“大地教主”的形象再现于世,从而为将孔教确立为国教提供合法性。
然而,这一神圣化孔子、救世化孔教的工作之所以可能,却是靠了长期被儒学视为异端的诸子学、佛教、基督教等的助力。这其中,来自基督教的影响尤为重要。
在康有为看来,相对于孔、佛二教,基督教的优势在于直捷、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梁启超,1998:427)。正是基于对基督教诸多方面的观察,康氏才有了认为孔学散漫无纪、无力祛除多神崇拜之俗的结论,从而锐意推动孔教的神道化。作为一神教的成熟形态和西方式“宗教”概念的范型,基督教为康有为的神道设教提供了世界观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他很可能还吸收了中国宗教大传统中的救世主义潜流,从而“围绕孔子”建立了“一个皈依和教化性的宗教王国”(渠敬东,2015:10)。最密集地呈现了孔教的救世化与普适化特征的,或许是康氏写于1898年年初的《?孔子改制考?叙》,其中说道: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息,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世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乃立元以统天,以天为仁,以神气流形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为仁政。(康有为,2003:1)
在此,孔子不仅是万世师,更是神明、圣王和大地教主。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康氏援引了汉代谶纬书目《演孔图》中黑帝降精而生孔子的说法,很可能是对《圣经》福音书中玛利亚感孕而生耶稣的仿照(唐文明,2012:95-96)。在这个孔教的“创世记”里,“天/黑帝”、“孔子”、“神气”构成了高仿的“三位一体”的世界图景。作为救世主的孔子,其所立“三世之法”,虽然依据的是他所身处的春秋乱世,却已经注意到了晚清世代所处的“中国仅为大地上的列国之一”的新处境。三世演进而“见太平大同之治也,犹孔子之生也”(康有为,2003:2)。在此,孔学不仅获得了一个高迈的目的论境界,而且因其弥赛亚主义之色彩而逆转了儒学三代理想中“未来感”的缺乏(Goossaert and Palmer,2011:171-172;张灏,2006:68)。此外,拥戴孔子为圣王、为教主,还有一层更隐晦的意图,即把儒学道统改造成“一种绝对王权,一种普遍君主,一种大一统意义上的君统”(汪晖,2008:812)。
可见,在康有为的孔教革命时期,他个人的教主抱负和推举孔子为大地教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并可通过卡里斯马的概念视角贯穿起来。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讳言康氏本人的教主野心,而这往往又引发另一问题,即未能充分检视康氏以孔子为圣王—教主的反传统意蕴。康有为暴得大名之后,朝野各界多有抨击其孔教思想的异端性的,不过这些抨击背后,确实往往带了不单纯的动机和心态。相较而言,富有政治洞察力的局外人王国维的观点更让人信服。他在早年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氏(笔者注:指康有为)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其以预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德之野心者也。”(王国维,2009:122)13.王氏早年曾供职于时务报馆,对于章太炎描述的馆内康门弟子的情状想必有亲身的观察。抛开这一观点所包含的贬意,更重要的是,王国维在此明确指出,康有为之孔教设想绝非一种单纯的学术或是世界观的创新,也不仅仅是为狭义的政治议程服务,而是有一执持国政、变革儒教的宏远蓝图。
四、孔教的普遍主义及其变教尝试
前一节论述了开悟体验带来的卡里斯马自觉如何把康有为推向变革孔学的宗教使命。通过对传统的神圣起源的回溯,康氏宣布要让被遮蔽的儒学精义重光并得到扩充。梁启超的《南海康先生传》中指出,其师的思想富于“个人的精神”和“世界的理想”,而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国家主义”(彭春凌,2011:174)。孔教革命的激越的普遍主义,就体现在个人的精神和世界的理想上,而国家主义的暂时性缺乏则和民国后与国族重建相结合的保守主义化的孔教形成了反差。普遍主义和价值合理化、卡里斯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救世主义的宗教/革命运动中。14.托克维尔(1994:21-22)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把法国大革命定性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而与早期基督教相提并论。托氏的相关论述被汪晖(2008:827)引入《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作为对康有为研究的总结。很显然,在康有为的孔教革命中,存在着颇为类似的普遍主义精神,它为托克维尔的以下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明:“为了改变具体的习俗而援用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绝非一种新颖的做法。就本文的案例而言,借着神圣化、超越化的孔子的言行,康有为揭示了一个抽离春秋时代背景的、普适性的“三世之法”,通向九界破除后的大同境界。这一重塑宗教—知识体系的工作既是价值合理化的内在要求,同时也由康氏个人的卡里斯马自证开出并提供担保。
孔教革命的普遍主义,可以看作是儒学传统固有的天下精神在外在刺激下的复苏和自我扩展,它努力在全球新情境的冲击中,将异质的外部经验—知识纳入自身固有的认知结构(汪晖,2008:752)。对于有普适效力的世界图景的巨大需求,是转型时期的突出特征。谭嗣同早于孙中山而倡言“贵知不贵行”,又以“教”为“求知之方”,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谭嗣同,1998:238)。谭氏所说的“教”即是孔教。作为“公理”话语的早期倡导者,康有为意识到孔子之道作为“教”的一面的散漫不彰,若不加以系统性的改造不足以应对列国竞逐的新时代(张翔,2015a:13-14)。在康有为及其门徒眼里,孔教激活并扩充的儒学精义表现为多个层次上的普遍主义,它们或者立足于政治上的民权主义,或者强调教化上的全球视野,再或者注重信仰生活的一体化,贯穿其中的平等主义取向无疑对固有的政教结构形成挑战。
和弟子们相比,康有为更有城府,对于政治利害更为敏感,他的行动策略也更具机会主义的成分。在戊戌年得到光绪帝赏识之后,康氏由推动自立民权一转而为依靠君权变法,孔教思想中伸张民权的一面被搁置了下来(黄彰健,2007)。即便是扩张孔教于全球的理想,其意义仍指向中国自身的困局。结果,有机会在戊戌年间对具体的政治议程乃至政策产生影响的,是打破信仰生活的区隔、把孔教推广为一般中国人的宗教的理念。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旧有的宗教大传统开始被卷入巨变的历史车轮。
前述引言中提到,康有为及其弟子的宗教史图景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传教士提供的。基于这一有争议的图景,康氏反思了儒士阶层在影响大众信仰生活上的局限性。康氏的一个主要关切是狭义的孔学仅由建制化的精英担纲,与民众间缺乏亲和。虽然孔学居于儒学正统意识形态的核心,得到官方的尊崇、科举制的加持,并通过伦常、礼制对一般民众产生着持续的影响,但是把持民众信仰世界的却是佛道和民间宗教中的神灵、观念。民众熟悉业报、轮回、菩萨、阎王,却往往不知颜渊、子路这些孔门弟子的名字(黄进兴,2015:230)。在宗教生活的实践方面,孔学与民众的距离甚至更远。谭嗣同(1998:207-208)曾有这样的观察:“府厅州县,虽立孔子庙,惟官中、学中人,乃得祀之……农夫野老,徘徊观望于门墙之外,既不睹礼乐之声容,复不识何为而祭之”。结果,普通人把孔庙看作与科举功名相连的“名利场”,许多人皈依到了“在理教”这类民间宗教门下,甚而落入“无教”可依的境地。
黄进兴(2015)称孔庙为“儒教的圣域”,他对于康有为的孔教改革的研究,就是放在打破孔学和民众间的信仰隔阂的背景中展开的。从他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的影响是首要的。正是在与基督教主导的“宗教”概念对照之后,康有为看到了孔学的封闭性,看到它未能脱离儒士阶层和国家祀典的范围,成为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普适宗教。他指出,“欧美之民,祈祷必于天神,庙祀必于教主,七日斋戒,膜拜诵其教经,称于神名”;而中国的情况却是“惟童幼入学,读经拜圣,自稍长出学,至于老死,何尝一日有尊祀教主之事”。为此,康氏提出了一系列变教的政治议程。起初,他提议在国内广立“善堂”、学堂,以弥补官方孔庙建制的不足。随后,在给朝廷上书言事的几份奏折中,他又提出了更系统性的激进设想: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配天,听全国国民皆祀谒之;废除淫祠,改充孔庙,自京师城野县乡,皆独立孔子庙;所在乡市,皆立孔子教会,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以七日休息,宣讲圣经,男女皆听;孔子教会其上以衍圣公为会长,等等(黄进兴,2015:240-247;唐文明,2012:133)。
1.3.3 防治要点发病一般的田,掌握在拔节于孕穗期当病丛率达20%时施药防治,发病早而重的田,掌握在分蘖末期当病丛率达10~15%时即施药防治。常用药剂为井冈霉素50单位溶液,即5万单位的商品加水1000倍液喷雾;也可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20%望佳多可湿性粉剂,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作为孔教运动之破斥对象的淫祀、淫祠,是指未经官方认可的民间信仰、民间崇拜及其所在寺庙。这些民间宗教活动不为知识精英所重视,但却是中国宗教生活的一大潜势力,佛道两教的制度化部分也立足于其上(Goossaert and Palmer,2011:91)。对于儒学何以占据了正统的地位却无法转化为民间宗教,康有为有过很多的思考。比如,从“教”的角度出发,康氏认为,孔子“敷教在宽,不尚迷信,故听人自由,压制最少。此乃孔子至公处,而教之弱亦因之”(唐文明,2012:127);从“政”的角度去看,历代朝廷对孔学的尊崇流于具文,“未令天下人民专祀先圣”,而人民的信仰需求不可阻遏,正信既然不彰,异端之教就会取而代之(彭春凌,2011:92-93)。另外,康氏还就民众的信仰习惯评论道:“夫小民智者少而愚者多,势必巫觋为政,妄立淫祠,崇拜神怪,乃自然之数矣;积势既久,方将敬奉之不暇,孰敢与争。”(黄进兴,2015:244)
显然,康有为在面对孔学改革破局之困时,他的个人立场和所处的历史—文化脉络都与作为外部观察家的“西方文明之子”韦伯极不相同。虽然康氏在面对民众信仰时毫不掩饰其心智优越感,而且他绝不会像韦伯那样把儒学的缺陷视作内在的、本质性的,但是相比于前代的儒士精英,他对问题的症结却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即,巫术势力根深蒂固而又顺应“民情”,儒学与帝制的当前形态无力扭转这一长期现实。可以说,康有为的变教努力在客观上和韦伯的中国转型之问有很大程度的呼应性。
在彰扬孔学的路径上,康有为不认同宋明理学中以乡约推动教化的做法(唐文明,2014:18),他转而致力于“恢复”孔学原有的重魂主义。15.在儒学史中,和康有为所谓的重魂主义最接近的实例之一是阳明学泰州学派下的颜钧(山农)。根据余英时(2004:216-225)的研究,颜氏的救世精神不像一般儒士那样以俗世性为主,而是有很强的宗教的经验在其中。他自命教主,认为孔子的圣学发展到最高阶段即是以“神道设教”;他对自己的门人构成了卡里斯马型的支配,并以“自立宇宙,不袭古今”的气魄解经讲道——以上这些都和康有为相近,尽管康氏没有在神秘主义的路上走很远。余氏还采用了韦伯对于宗教领袖的类型学划分,将颜山农判为“先知”和“伦理教师”的混合型。然而,尽管孔教革命和民间宗教都有某种形式的神道设教,但是前者对儒学传统的宗教性一面的彰扬却并不意味着对后者的宽容乃至吸收。恰恰相反,虽然儒士群体一直在推动以儒学正信祛除淫祀,但是康氏征毁淫祠、广立孔教的主张却达到了不同寻常的激烈的高点,而且尝试挟持国家机器来达成这一主张。然而,随后的历史进程却滑向了以庙产兴办新式教育的方向,以康有为无法预料的方式步步向前。康氏的孔教理想始终无从着落,而中国宗教在民间社会自成一体的格局也开始了它的终结之旅(汲喆,2009:41-42)。
在进行当前人力资源管理中,企业需要制定长远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规划,衔接好不同的管理环节,结合实际工作情况,选聘更多优秀的人才,进一步优化人才管理机制,做好调整工作,激发人才对单位的认同感。因此,企业需要建立透明化的管理机制,分析潜在的影响因素,重点加强对存在问题的管控,满足实际工作的基本要求,对企业的未来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相比于早在1895年就提出的“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庙”的动议(康有为,1981:132),将淫祠改为小学堂的奏折则要迟至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这个从改为孔庙到改为学堂的转变,对康有为来说多半是因势利导,不得不如此。因为此时真正有力量、也有现实利益动机来推动“庙产兴学”的乃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而他们对于孔教的动议是拒斥的。为了从建制上落实孔教,康氏除了主张孔学应当成为各类学堂的必修内容之外,还转而在士绅阶层中筹设圣学会,而政治性更强的强学会和保国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孔教会的预备组织形态(唐文明,2012:113-121)。16.此时的孔教会被构想为国教形态的教会机构,而等到它在1912年正式成立时,其性质仅为一社团组织。戊戌变法失败三年而有新政,庙产兴学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开展,成为地方政治精英汲取社会资源、推动新式教育的重要手段,而康有为用以辅翼改制乃至作为改制之归宿的孔教设想却再无着手的现实凭借。与此同时,康氏对于毁庙做法的态度渐趋负面。他先是在流亡期间辩解自己毁淫祀的主张不触及佛道两教,到了民初更是为被打压的民间信仰和节庆发声。时势如高山滚石,彼时康有为曾有挟持国家机器推动变教的机会,不出十几年,儒学的正统地位都已岌岌可危,而佛道两教乃至民间宗教也都成了必须串联的难友(彭春凌,2011:94-97,141-142)。在这种新形势下,孔教虽然在民初正式立会,仍有影响上层政治、形成自组织的机遇,但是和当初那个革命性的孔教相比,已经置身迥然不同的语境之中。
危亡的时势曾给予康氏从边缘到中心的不世之遇,但是与他的改制变教的理想相比,现实能够提供的机会窗口是残缺的、稍纵即逝的。即便在拥有政策影响力的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也未能让孔教动议得到落实。日后世殊事异,孔教再未能向后人展开其革命形态所含藏的全部历史意蕴。在此至少可以指出这样一点:孔教与民间宗教间亦敌亦友的微妙关系提示我们,若要在近代中国反传统变革的问题视野中审视孔教革命,则不仅要看到它冲击宗教大传统的旧有格局、开启祛魅进程的重要影响,也要看到它试图维系儒学—儒士的支配地位,使其在理性化时代获得新生的用心。
五、理性化视野中的康有为与孔教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虽然强调的是儒学传统中宗教性的一面,但同时它又是在理性化时代应运而生的,这其间的张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孔教的特征和命运。
互联网期刊出版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传统期刊的数字化并在互联网上出版;另一类是期刊在线数据库出版。顺应时代与市场的需求,传统期刊正在经历数字化,而随着网络的发展,光盘、磁盘等形式出版的数字期刊已逐渐被网络出版所替代,大多数期刊在线数据库已转变为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发挥平台集成性优势向消费者提供海量内容与定制化服务,因此大多数期刊选择在互联网期刊数据库进行网络出版,由中国知网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就是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官方平台。据了解目前国内传统期刊选择的互联网出版平台主要有《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
首先介绍价值理性化,这需要从广义和狭义两种意涵加以把握。广义的价值理性化3.德文中与价值理性化对应的概念兼有“价值合理化”的意涵,后者更适合用来指称它的广义意涵。下文中将酌情使用价值合理化的措辞来与狭义的意涵相区别。乃是对特定价值体系、世界图景的合理化过程,使其更具有普适性、自洽性和彻底性。这个广义的价值理性化的涵盖面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它和我们通常理解的理性主义不可一概而论。4.举较为极端的例子来说,巫术虽然是价值理性化的主要障碍,但是巫术在其自身的发展史中也存在“价值合理化”的过程,可以道教为例(苏国勋,1988:181)。韦伯的理性概念在其根基处是“视角主义”的,即“从这一观点看去是‘理性的’,从另一观点看来却可能是‘非理性的’”(韦伯,2007:[前言]12)。在对比儒教和清教时,韦伯指出:“这两种伦理都有它们非理性的本源,一个是在巫术,另一个则在一个超俗世上帝的绝对不可臆测的决定”。“从巫术那儿推衍出来的是传统的不可动摇性……然而从超俗世上帝与现世……的关系上,却造成传统之绝对非神圣性的结果,以及要将既有的世界从伦理与理性上加以驯服和支配的无尽的任务,此即‘进步’的合理客观性”(韦伯,2004:324-325)。可见,韦伯并非是在本质主义的意义上将清教视作“理性”的。
综上所述,不同工作时间N2层级护理人员在微量泵技术操作考核中常见错误各有不同。因此,在以后培训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工作时间的护理人员,根据出错率较高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和培训措施,对培训过程中针对主要存在问题进行重点培训,确保临床护理人员通过操作技术培训能够真正掌握该项操作并正确熟练应用于临床护理工作中,确保患者安全,避免发生护理不良事件。
不光是在不同的行动类型之间,单是在不同的价值理性之间,就已蕴含了深刻的内在张力。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是价值理性化与分化的关系,其二是分化的价值理性之间的交互、消长关系。
就价值理性化与分化的关系来说,不同的价值理性化为不同的文化领域提供了各自的终极视角,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有各种社会秩序的“分化”并彰显出其内在固有的法则性。若无价值理性化的充分发展和“升华”,一个社会的不同文化领域、社会行动的界限便是模糊不清的(李猛,2010:2-4)。就分化的价值理性之间的交互、消长关系来说,不同的价值理性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会建立或者良性互动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第二节中曾提过清教伦理的例子。这一宗教领域中价值理性化的较彻底形态,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初生时期曾与其建立过“选择性亲和”的关系,但是等到经济和科学理性主义取得支配性地位之后,清教伦理无论在经济伦理领域还是在世界图景领域,都转而被视为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力量。
在近代西方的理性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化和目标理性化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背反关系。价值理性化具有打破传统的革命性,是理性化激越的初生阶段;而目标理性化则是常态化的,专注于“功利目标”。后者在自身的纯粹形态中丧失了“价值”乃至“精神”,因而,目标理性化的达成也就意味着价值理性的行动的牺牲(李猛,2010:3、6、28)。理性化进程的背反还表现在,清教伦理在发生学上的关键意义并非由于它自身的目的论设定,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其他因素间的“选择性亲和”。日后不论是在功利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伦理领域,还是在科学理性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图景领域,清教伦理都转而被看作了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力量(施路赫特,1987:28、32)。5.从这个角度看,价值理性化无论广义还是狭义,从其根基上看就是视角主义的。即便是科学理性主义,也奠基于非理性的前提,涉及对知识积累的自身价值的信仰(施路赫特,1987:32)。
下面谨从三个面向介绍康有为的努力所向,再以更大篇幅追踪其预料外的后果。
面向一,孔教在知识论上的一元调和主义。康有为追随董仲舒,重新确认了“气”的本体论首要性。这个气既是物质的,又是活力论意义上的“神气”;进而,“天”也成为了人格性的有机存在体,一切生命的创生之源,乃至“人人皆为天之子”(张灏,2006:37,42-43)。更进一步的申发则是,天化育万物而为仁,人类则是“取仁于天而仁”。但是在此,“仁”已经与气相通而兼具了物质与伦理的双重维度,故而康氏才可以说:“不忍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张灏,2006:43-44,54)仁的意涵是如此博大超绝,而让康氏自觉站在一个至高的视点,可以将孔、耶、佛三教合一,因其“立教之条目不同,而其以仁为主则一也”(梁启超,1998:428)。可见,康有为的“仁学”将哲学、伦理学、物理学、宗教等维度调和到了一个一元论的视野中。更准确地说则是,这些后来彻底分化的知识—观念领域,在康氏那儿维持乃至加强了它们的混融性。17.这种混融性或许和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影响有关,康有为和谭嗣同很可能接受了他们以实证科学印证自然神学信仰的基本预设。可参见艾尔曼(2016:388-393,501-506)的研究。
面向二,孔教在重塑政教关系上的努力。康有为虽然承认“君、师合一”只是“人民之先”的普遍情形,但是他在谈及“离于帝王之以为教”的基督教时,所留意的还是它最终“于罗马立教”,政教一体而行其政教(唐文明,2012:77)。维新变法的大力赞助者陈宝箴有过一段对康氏孔教主张的剖析,常为研究者所引用。18.“康有为当海禁大开之时,见欧洲各国尊崇教皇,执持国政,以为外国强盛之效,实由于此。而中国自周秦以来,政教分途。虽以贤于尧舜、生民未有之孔子,而道不行于当时,泽不被于后世,君相尊而师儒贱,威力盛而道教衰……是以愤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元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稣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曾亦,2013:64)康有为绝非不了解“欧洲各国尊崇教皇,执持国政”的情形已为陈迹,政教一体主要是他个人执念的反映,即想要改变“君相尊而师儒贱,威力盛而道教衰”这一中国的固有国情。维新变法时期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其实是试图在官方化儒学的固有建制之外,以孔教会为新的机构依托来普及孔学(唐文明,2014:18-19)。看起来,这颇有政教分离的色彩,但事实上,它意味着“系统性政治组织和新的政治中心的形成”(张翔,2015b:79),康氏之实际意图仍然是由讲学而立教、由立教而摄政。
面向三,孔教的宗教转向及其价值合理化努力。这一点在第三、第四节中已经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包括宗教演进之“三世说”,神圣化、救世化孔子而建立的世界图景,孔教在原则与建制上的普遍主义等,故此处从略。
可以说,康有为为改造中国宗教的大传统而注入的新思维,导向了宗教与迷信的新范畴的通行,从而奠定了1901年开始的“反迷信运动”的观念基础(Goossaert and Palmer,2011:46-47)。19.事实上,康有为所参与推动的“宗教”概念,起初几乎是基督教的同义词,连佛、道二教也不包括(Goossaert,2003:434)。由此可见,“反迷信运动”发展到后来把一切宗教都等同于迷信,并不是无因的激进化。若结合韦伯的中国观察可以发现,“迷信”这个出现在19、20世纪之交的新词汇和韦伯的巫术概念重叠度很高。由此来看,康氏的孔教革命还参与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祛魅进程。
大数据时代下在数据开放共享的同时,也面临数据安全的威胁,我国目前信息安全制度还不健全,对数据资源采集、存储、利用等方面的管理不规范,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随着数据应用越来越频繁以及解读技术的提高,网络数据安全风险不断加大,使得公民个人隐私、国家机密的保护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事与愿违,孔教并未得到儒士阶层的广泛支持,随后的历史进程似乎处处与之相违。更为吊诡的是,孔教正是因其最初的革命性而对日后弃它而去的历史进程起了多方面的催化性影响。
面向一,孔教在知识论上的一元调和主义的影响。这种一元调和主义的取向,意在让孔教站上普遍主义的思想高地,但是其对于普适性的追求却是以牺牲自洽性为代价的。早在康氏引领的“新学”大行其道的1897年,章太炎就已经因其“杂糅”、“辄以算术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谈”而颇加讥弹(汤志钧,2013:22)。而当时被章氏批评的梁启超,也在民国后批评其师“好依傍”世俗西学以伸张孔教而造成“名实混淆”(彭春凌,2016:64)。然而,换个角度去看,康氏之一元调和主义恰因其对儒学传统的破坏性改造,而为随后的知识—观念诸领域乃至制度的分化清扫了道路。
这种破坏性的改造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仁”从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体系中超拔出来,成为一种近乎超验性的主导性价值。康有为把仁诠释为“平等”,并和耶、佛两教乃至墨家互通;而“义”却沦为专制等级主义的象征,和仁的博爱、开放精神构成对立(张灏,2006:35-36)。由此,儒学正统的纲常礼制与等差之爱都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一破坏性改造的触媒作用,反映在梁启超20世纪初的政教思想上。他先是倾向于激进的共和革命,不久后又退守立宪改良的道路;相对应的,他也曾一度倾心佛教,之后虽然回归孔教,但却是要将其与“新民说”结合起来,对于孔教在建制、祀典方面的议程则虚与委蛇(彭春凌,2011:174)。正是由于康氏将孔子从儒学道统和纲常礼制中超拔出来,并一度造成了孔佛二教在精神原则上的趋同,他的弟子才获得了将孔教分解为“公民伦理”的思想条件。
面向二,孔教重塑政教关系的努力所造成的影响。和上一点一样,这种努力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政”的方面,前文已述,国教化孔教含有将其打造成新的政治组织中心的意图,这是对帝制—皇权体制之固有逻辑的破坏。在“教”的方面,孔子祀典在1906年被提升为了最高一级的国家祭祀,但另一方面,孔教普遍主义却在1904年帮助促成了帝国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即放弃了通过册封(canonization)将民间信仰整合进国家祭祀的传统。可以说,孔教的神道化取向是和削弱帝国旧有的神道设教体系相关联的(Goossaert and Palmer,2011:55-56)。
再进一步地看孔教和官僚制的关系。就其触发意义来说,不论是止于设想的庙产兴教还是付诸实施的庙产兴学,都可以被看作是接下去的大半个世纪中官僚制扩张、下沉、集权的先声。新政开始特别是1908年以后,庙产和寺庙不仅被用于兴学,而且也因为自治局、兵营、警察局、邮局等新式政府机构的需要而被征用。到了这时,毁庙运动已经成为官僚制自我扩张和理性化的汲取对象,日后不论康有为还是别的什么人出面反对都为时已晚。更富有戏剧性的是,自1901年开始的大规模的庙产兴学,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进而加速了科举制于1905年被彻底废止。从此,儒士阶层和帝国体制之间的关键纽带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孔教的建制基础却依然没有着落。进入民初,学堂内的祭孔仪式被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以政教分离的理由废除(Goossaert and Palmer,2011:47、57),而在孔教会基础上组织政党的计划也始终踯躅难行。如果说孔教在教育领域的失势主要是由于价值理性化的分化趋势的话,那么它在政党政治中的无力,则反映出儒士阶层在失去帝国官僚体制的俸禄之后,缺乏独立的经济、社会资源(艾森斯塔德,2012:78)。
面向三,孔教的宗教转向及其价值合理化努力的影响。尽管康有为对于孔教的神道化发展富于价值合理化的意义,但是从儒学内部的视角出发,则是对其理性主义传统的大削弱。在西方挟理性化力量大举侵袭之时,儒士阶层内的精英分子从陈宝箴到严复、黄遵宪,普遍对康氏高举“保教”大旗不以为然(张翔,2015b:88-89)。王国维(2009:122)对于孔教的批评也类似,他说:“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然而有趣的是,王氏指陈基督教是“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大致不假,但他说孔教有“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的威势,却也同样真实。
在中国近代宗教史上,“正统”与“异端”的二元对立范畴被“宗教”与“迷信”取代,是一个分水岭式的转变(Goossaert and Palmer,2011:51)。康有为立孔教、毁淫祀的主张,其基调仍然由树正信、破邪信的传统认知所设定。然而,上述两组二元对立范畴之间并不缺少转变的坡道。比如说,前述康氏认为“巫觋为政,妄立淫祠”之所以普遍,是因为“小民智者少而愚者多”。他的这个解释和梁启超将“智信”与“迷信”对立起来,都隐隐可见新范畴的轮廓。另一个例证是,康有为的宗教进化之三世观中,以多神论为最低下的阶段而有待于向一神论转变,而他同时又有意识地把自己神道化孔教以取代淫祀的做法和这个宗教的进化历程相对接。再考虑到此时的康氏对于西方宗教学界对巫术与宗教、多神教与一神教等的区分已经颇有了解(唐文明,2012:124-125),那么只需要把淫祀等同于西方语境中的“巫术”,将其贬为“迷乱的信仰”,然后宗教与迷信的新范畴就呼之欲出了。
随着高校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和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学生管理与教育任务越来越繁重;而学生工作人员的相对紧缺,使学生问题表现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兼职班主任这一角色应运而生。有研究表明,由专业教师兼任班主任的班级,学生在学习、社会活动和科研方面明显优于非专业教师任班主任的班级,提示专业教师兼任班主任对学生的生活、学习有明显帮助[1]。目前,专职辅导员与兼职班主任并用方式已得到了众多高校的认可。
六、余论
上文结合韦伯的理论概念,论述了康有为孔教革命的缘起、内涵、被抛入其中的时势与事件、意图与预料外的后果等。在这一系列考察的基础上,本节旨在重估孔教革命的历史意义,更明确地揭示康有为所扮演的扳道工角色的性质、局限和原因,为此有必要回到引言所展示的问题意识,从韦伯的中国转型之问再次出发。
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打破皇权与儒士阶层的结盟,祛除民间的巫术性力量,为理性化进程开辟道路?对于这个问题,韦伯本人并不是没有观察、没有态度的,事实上,他曾据此给予了太平天国运动极高的评价。韦伯(1999:269)认为洪秀全破除偶像、反巫术的先知预言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还说:“让一种土生土长的但又从精神上接近基督教的宗教产生出来。对于在中国产生这样一种宗教来说,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从今天回看,韦伯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的厚望颇有一些诡诞。同为基督教影响近代中国的突出事例,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分别代表了精英的和大众的救世主义运动。结合日后的历史进程,本文认为,相比于后者在破除偶像和反巫术上的作为,前者所触发的“庙产兴学”和“反迷信运动”在祛除巫术势力上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实际历史中,破除巫术的理性化进程的真正发轫处是在儒学与儒士阶层内部,而非来自某种民间性的势力。
对照孔教革命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它们各自的缔造者,从两位教主的个人气质、禀赋,到它们对基督教的吸收程度,再到各自乌托邦的特征,乃至教权制的发展情况,都可以看到显著的区别。就康有为而言,早年的宗教修炼虽然带给他六经注我的自信,但是他阐发微言大义的方法论却是理性主义而非神秘主义的。康氏早年的《郑康成笃信谶纬辨》中便说:“盖时主不信儒,儒生欲行其道,故缘饰其怪异之说……后世儒术尊明,诚觉前人之迂怪,而未识创教之难也。”(康有为,2007:311)固然,基督教对康氏的影响远不只是提供了“缘饰其怪异之说”的素材,但必须指出,基督教虽然鼓舞了康氏的先知—教主使命,却并没有转换他的儒士气质。虽然“天”的概念在康氏那儿具有超自然的乃至人格性的力量,但是天启式的奇迹却是他的心灵气质所全然陌生的。无论是“以孔配天”,还是模仿基督教会的建制和礼俗,都是外观化的、有选择的移植,远未深入基督教精神的内核。在韦伯看来,这正体现了儒士气质的一条突出特征,即“绝对缺乏任何的‘救赎要求’,特别是出离此世来为伦理寻找根基的做法”(李猛,2010:23)。
此外,康氏虽然在十几岁时就已接触西学,但是他真正严肃而富有热情地阅读西学,却是在开悟体验之后(张灏,2006:28)。上述种种均表明,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对于巫术力量的祛除,并非像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那样是受到基督教弥赛亚主义影响的结果。它的核心动机,可以用《理性化及其传统》中的一句话来点出:“儒家的伦理可以不受先知革命和救赎要求的困扰,但却无法回避西方理性化进程带来的挑战”(李猛,2010:23)。正是理性化的西方的挑战,才激活并强化了理性主义面向的儒学基要主义(Confucian fundamentalism)和对职业僧侣与教权组织的固有敌意(anticlericalism),从而有“庙产兴学”运动的展开。20.参见汲喆(2009:42)所引的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的观点。
在同时代人中,康有为对于“保教”和“变教”的认识是非常早熟而深刻的,但是他的孔教思想从未得到儒士阶层的广泛认可,并且很快就转而以文化—政治保守主义的面目示人,而它原初的激越的普遍主义精神,连同康氏并不隐秘的教主雄心,一并被流亡后的康有为本人亲手掩埋。可以说,孔教革命参与召唤的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是极为短暂的,它未能孕育自己事业的直系继承人,因而它对于日后历史进程的影响仅是触发性的乃至征兆性的。
孔教革命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局限,一方面是因为它自身的缺憾,另一方面则与康有为的变教意图有关。对于前一方面,下面谨从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的角度各做一概述。
先从卡里斯马去看。和大多数创教教主的禁欲气质不同,康有为富于拥抱现世的欢乐气质。禁欲气质的意义在于和现世的距离感,进而产生伦理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在康氏那儿是找不到的。他的《大同书》对人性所做的是一种坦率的享乐主义的解释,只不过,大同社会中世俗幸福的极大化和道德之至善不再构成矛盾,而是相辅相成(萧公权,2007:21;张灏,2006:69)。也因此,大同境界虽然为孔教引入了未来感,但是这一乌托邦和现实之间缺乏宗教性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的缺乏,让康氏可以为了回避政与教的斗争而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并对小康之义和大同之义做看似并行不悖但事实上内在分裂的处置(张翔,2015b:92、96),在此受到损害的是孔教作为“求知之方”而重塑行动取向的潜能。
再从价值理性化去看。康有为试图以“公理”话语的建构在世俗西学的强势涌入下为孔教奠定普遍主义的新基础。作为一种策略,他把“科学”从“西夷”的技术性力量提升为了“一种客观知识、一种看待世界的框架、一种重新规划世界关系的原理、一种‘自然法’……从而总是与本体论或宇宙论的视野结合在一起”(汪晖,2008:768)。这也是为什么“以太”可以作为宇宙本源的表征物而与“仁”互通,从而被吸纳进康氏的一元调和主义的知识论混融体当中。然而如上一节所指出的,这种知识论与价值理性化的分化趋势相逆而行,因而在自洽性上存在先天缺陷。科学理性主义的强势地位意味着它将很快获得独立的话语空间,然后迅速从康氏粗拙的体系中抽身而去,让后者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
事实上,康有为的大同说虽然以孔子三世说作为理论框架,但是这一普遍主义乌托邦所设置的议题——国家、种族、性别等九种需要破除的界限——表明世俗西学已取得支配性地位(汪晖,2008:773),而得到接纳和重用的西学,在其内在逻辑不断延伸之后,终将危及孔教自身的合法性。这在康氏论及大同世的纪元形式时可以看出。他先是认为君主纪元不如教主纪元能够维系长久,但随后又指出教主纪元也和大同之世不相洽。康氏的理由是:“新理日出,旧教日灭,诸教主既难统一全地,终当有见废之一日。此大劫难挽,亦与国主略同,但少有久暂大小之殊耳”(唐文明,2012:138-139)。也就是说,即便是先进如孔教者,由于“新理日出”的大势,也无法在大同世占有立足之地,会大行其道的反倒是仙学和佛学(郭鹏等,1989:242)。
然而,孔教革命的局限性也必须结合它的反传统面目之下的保守性意图来看。这里所说的保守性,指的是儒士阶层在理性化大变局中对于自身整全性的维持。众所周知,儒士阶层身兼文人和官僚两种角色,对家庭、教育、文化—学术、行政—法治乃至天人之际等诸领域施加主导性的影响。儒士阶层所承载的儒学传统,既是一种综合性的观念体系,又意味着相应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秩序。这两点既是“意识形态”一词的基本定义,也是“教”之所以为“教”的所在。儒教的无所不包性与儒士阶层不同角色间的功能混融性互为表里,并以此支配了中华帝国的政治(阎步克,2015:10-11)。
与帝国体制相结合的儒学与儒士,本是“周秦之变”后的新发展。在这一从宗法—封建时代向帝制—郡县时代过渡的过程中,曾经的“士大夫”阶层成功地在文明的推进中升华了它所带有的功能混融性和角色弥散性,从而在分化程度更高的社会环境中维系了它原有的精致、丰厚而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阎步克,2015:414)。在19、20世纪之交的新一轮的大变局中,虽然自我维持的努力是普遍的,但是对儒学传统进行系统的创造性转化,以图立足于新社会、参与再造新社会的尝试,或许康氏之孔教革命是仅有的一次。孔教之变教,不管是其一元调和主义的知识论和以教摄政,还是宗教转向下的价值合理化,大抵都有一个无需言明的意图在,即重塑原先由儒教所统摄的“信仰、知识与权力三位一体的传统秩序”(汲喆,2017:38),从而维持儒士阶层的功能混融性和角色弥散性。
这一保守政教传统的意图,在康有为那一代的革新派儒士当中是有普遍性的,并且指引了他们日后的保守主义化(另一个典型的代表是章太炎)。进入民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趋新的知识分子脑海中的关键词从“教”变成了“主义”,然而其中有着接续性。新一代当中流行的“有主义总比没主义好”的看法(王汎森,2013:4),差不多就是清末的“有教胜于无教”的世俗化翻版。孔教,作为清末变教—创教运动的主峰,预兆了以“主义化”为特征的大革命时代的到来。激荡着救世主义精神的大同说,“几乎塑造了后世中国人的一种绵延百余年的抽象理想,在后来的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诸种意识形态中,我们皆可见其中最基本的精神气质”(渠敬东,2015:10-11)。
不过,“主义”较之“教”的优胜之处,却不仅限于思想—精神的层面,也在于它落实为了革命政党这一全新的建制。尽管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在大革命时代继续发挥着冲破传统和塑造实践伦理的作用,但是破旧立新将越来越依赖理性化的官僚制。相比于帝制时代官僚体制根深蒂固的“传统”性,“主义”政党在推进官僚制理性化上的成果令人瞩目,并和康党乃至同盟会所依靠的“党羽”“会党”的组织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理性化官僚制相辅相成的是革命动员的自转之轮,这是“主义”政党得以成功的另一大奥秘,即“建立了一种能够持久对抗传统的力量,将处于‘初生状态’的卡里斯马的革命性瞬间改造为一种持续不断的革命进程”。这种“不断革命”的动能还使它得以完成一个孔教仅仅只能够提出的任务,即将“少数大德高人”和“仍旧生活在传统和习惯中的大众”的伦理生活的二元格局打破,“通过‘教派’建立一种受统一的伦理要求和纪律支配的理性化世界”(李猛,2010:15、22;韦伯,2004:486、489)。
参考文献(References)
艾尔曼,本杰明·A.2016.科学在中国(1550-1900)[M].原祖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艾森施塔德,什穆埃尔·N.2012.大革命与现代文明[M].刘圣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郭鹏、廖自力、张新鹰.1989.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M].成都:巴蜀书社.
黄进兴.2015.儒教的圣域[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黄彰健.2007.戊戌变法史研究[M].上海书店出版社.
汲喆.2009.居士佛教与现代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7(3):41-64.
汲喆.2017.世俗主义的中国之路:“教”的分化与重构[J].原道23(2):20-38.
康有为.1981.康有为政论集[M].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
康有为.2007.康有为全集(第一集)[M].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康有为,等.2003.儒家宗教思想研究[M].李建,主编.北京:中华书局.
李猛.2010.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J].社会学研究(5):1-30.
梁启超.1998.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M].陈引驰,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茅海建.2009.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彭春凌.2011.儒教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D].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论文.
渠敬东.2015.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J].社会35(1):1-25.
施路赫特,沃尔夫冈.1987.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M].顾忠华,译.台北:联经出版社.
苏国勋.1988.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谭嗣同.1998.仁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唐文明.2012.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唐文明,等.2014.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J].开放时代(9):12-41.
汤志钧.2013.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
托克维尔.1994.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王汎森.2013.“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J].东亚观念史集刊(4):3-88.
王国维.2009.王国维全集(第一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汪晖.2008.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韦伯,马克斯.1996.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M].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社.
韦伯,马克斯.1997.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韦伯,马克斯.1999.儒教与道教[M].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韦伯,马克斯.2004.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伯,马克斯.2007.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萧公权.2007.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阎步克.2015.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念群.1997.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余英时.2004.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曾亦.2013.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4(4):63-71.
张灏.2006.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M].北京:新星出版社.
章太炎.2003.章太炎书信集[M].马勇,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张翔.2015a.从立公理之学到以大同为教——康有为奉孔子为“大地教主”的过程与方法[J].哲学动态(3):13-22.
张翔.2015b.大同立教的双重困局与不同应对——康有为政教观初论[J].开放时代(3):79-98.
Feuchtwang,Stephan.2008.“Suggestions for a Redefinition of Charisma.”Nova Religio: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Emergent Religions 12(2):90-105.
Goossaert,Vincent.2003.“Le Destin de la Religion Chinoise au 20eSiècle.”Social Compass 50(4):429-440.
Goossaert,Vincent,and David A.Palmer.2011.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i,Zhe.2008.“Expectation,Affection and Responsibility:The Charismatic Journey of a New Buddhist.”Nova Religio: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Emergent Religions 12(2):48-68.
Guzman,Sebastian G.2015.“Substantive-Rational Authority:The Missing Fourth Pure Type in Weber’s Typology of Legitimate Domination.”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5(1):73-95.
Yang,C.K.1961.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ang Youwei’s Revolution of the Confucian Religion: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Weberian Concepts of Charisma and Value-Rationalization
Lu chen
Abstract:What kind of forces can break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imperial monarchy and Confucian elites,and disenchant the popular belief in magic,and thereby clear paths for the process of rationalization?This is the essential question in Max Weber’s inquiry of the eventu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Inspired by Li Meng’s writing,this paper undertakes a case study on the initial stage of rationalization in modern China by examining Kang Youwei’s revolutionary endeavor of refashioning Confucianism around the Hundred Days’Reform. Applying Weberian concepts of “charisma” and “valuerationalization”,the paper explains how Kang,with a conviction of his own charismatic potential to be a religious reformer,reinterpreted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religiously and mythically,and thus played a role of breaking the tradition and reshaping ethics in pre-modern China.The Confucian Religion(Kongjiao )in its revolutionary period articulated universalism rather than nationalism.Drawn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hristianity,Kang attempted to lift Confucian teachings beyond the limits of literati and national ceremonies to a universal religion not only for China but the whole world.Although Kang’s vision failed,his call of reinventing Confucianism heralded the later social campaigns such as the“Building Schools with Temple Property”and“Anti-Superstition”.The spiritual dimension in Kang’s ideas and the need to fend off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modern West made his“value-rationalizing”effort almost impossible to succeed.Despite of its radical appearance and rejection from Confucian traditionalists,in the end the goal of Kang’s Kongjiao movement is still about preserving the social integrity of Confucian literati.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r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eventually fell upon the revolutionary parties in the Republican era.
Keywords:Kang Youwei,Confucianism, Max Weber,charisma,valuerationalization
*作者:吕雨辰 巴黎文理研究大学,高等研究实践学院(Author:L Yuchen, cole pratique des hautesétudes,PSL Research University)E-mail:simondeqin@gmail.com
责任编辑:田 青
标签:理性化论文; 韦伯论文; 卡里论文; 康有为论文; 孔子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近代哲学(1840~1918年)论文; 康有为(1858~1927年)论文; 《社会》2019年第6期论文; 巴黎文理研究大学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