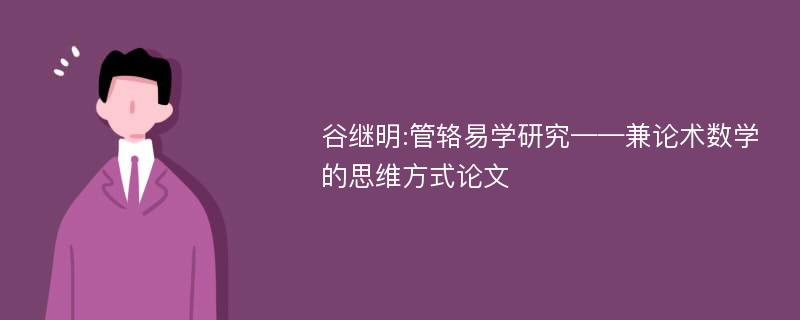
摘要:易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论的层面和术数的层面。学界以往对易学的术数层面关注较少,一是缘于学者对“术数”的偏见,二是术数学自身缺少系统性反思的理论大师。三国时的管辂便是试图对术数学进行理论说明的人。牟宗三曾经藉由管辂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一类知识系统,但尚有许多内容待发掘。管辂说“善易者不论《易》”,这是对术数易地位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经学易和玄学易的回应。这种反对,不能从象数和义理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而应从文本和实践的区别来认识。管辂认为,术数的根本在于“神”,这个神不是玄学或思辨意义上的“玄之又玄”,而是实践意义中的通感和知几能力,它奠基于人自身的命限和气质中。但对于神的体悟又不能仅仅等同于“直觉”和“神秘主义”,因为它对于表现的通孔——象,以及工夫论基础,都有明确的要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隶属于理性、直觉或神秘主义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
关键词:管辂;六朝易学;术数;周易;玄学
而今学界的易学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易学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易学哲学家通过注释《周易》所涉及的哲学问题,如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等;一是作为经学的易学,研究《周易》的训诂、文本构成、注《易》的义理结构等。两类皆侧重于《周易》“学”的层面。这与历来知识界强调《周易》的“学”,认为谈术数会导致渎乱不经有关。但术数方面的易学,在历史上占有实实在在的重要地位,不会因为人们在公共讨论中的缺席而消失;相反地,不屑于谈术数,完全将之让给民间的术士来研究,将失去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一把钥匙。术数易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或知识类型,却又与传统思想紧密相连。
除了学界不屑于讨论此类问题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术数往往在民间传授,多传闻和事迹例证,少理论总结,故缺乏集中性、系统性探讨的资料。所幸毕竟还有一些人既精于术数,又有理论层面的反思。曹魏的管辂就是这样一个人。魏晋之际,从经学层面看,由郑玄学向王弼学转变。学界关注最多的易学家,便是荀爽、虞翻、郑玄、王弼,管辂受到了很大的忽视。因他被视作术士,而非易学家。但他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术士,对《周易》的定位和运用,是当时术士型易学理论的集中代表。牟宗三先生在《才性与玄理》中就曾专辟一节,研究其思想,这是牟先生高明和敏锐的地方。今更在牟宗三的基础上,探讨若干问题,以推进此类学问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使用的“知识类型”一词,指的是术数作为一种广义上的知识技术门类,其思考的结构和获得体认的方法。这既与福柯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知识型”(Episteme)有别,也与狭义地定义为认知理性的“知识”有别,而近于“思维方式”的意义。
一、管辂对《易》的定位:善易者不论《易》
管辂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周易通灵决》二卷(原注:魏少府丞管辂撰)。《周易通灵要决》一卷(原注:管辂撰)。”《隋志》又有“《鸟情逆占》一卷”,不著撰人,姚振宗引《管辂传》及两《唐书》著录《鸟情逆占》一卷为管辂撰。[1](P1451)我们比合各类史志,排定管辂遗著如下:
《周易通灵决》二卷,魏少府丞管辂撰。(《隋志》)
中南6省/区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中标效果评价…………………………………………………… 袁 姣等(15):2017
《周易通灵要决》一卷,管辂撰。(《隋志》)
《鸟情逆占》一卷,管辂撰。(《隋志》、《唐志》)
《周易林》四卷,管辂撰。(《唐志》)
《风角占》若干卷。(见下文说明)
以上书加起来,统共八卷。又《隋志》中有许多种不著撰人的《风角占》《风角要集》等,这其中或有管辂的《风角占》。至于《唐志》中出现的管辂《周易林》,或许是旧本,但也有可能是后人从《管辂别传》中辑出来的,现在因已亡佚,也难以断定。
(一)客观方面不是基于抽象之量概念,如物质、质量、密度等,而是基于具体的感应之机。在对象方面,并不是经由一“抽象的分解”而为机械的推知。
我们了解管辂其人,主要依靠其弟管辰所作《管辂别传》。需要提及的是,魏晋术数家史传的一个特点,便是其传记往往采自其自己的术数活动记录。术数家最可传者,不是他的德行或者哲学思想、仕宦沉浮,而是其术数实践。同时,术数家也有意识地保存自己的实践记录,每一个易占的术数家皆有自己的“易林”,这也正是“易林”类著作如此纷繁的原因。所谓“易林”其实就是将自己的记录汇集起来,林林总总。[注]需要指出的是,《焦氏易林》取义于将占筮的断辞系于每卦之下,井井有条,如树林。与此有别。这一个个涉及具体人事的占筮记录,就是术数家鲜活生命的展现,就是他们在场的明徵,也是他们参与历史的发展、参与学术之流行的标识。《管辂别传》主要取自管氏的《周易林》,而《晋书》的《郭璞传》也主要取自郭氏的《洞林》。
《管辂别传》记载了管辂与何晏、邓飏的交往:
辂为何晏所请,果共论《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时邓飏与晏共坐,飏言:“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故也?”辂寻声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晏含笑而赞之:“可谓要言不烦也。”[2](P821)
在城市发展中,活化更新已有较为详尽的定义,即拆除或改建破烂、陈旧的建筑物,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在广袤的农村地界,应在保证文脉延续的前提下,使传统村落恢复活力,以全新的面貌适应当前新农村建设。传统村落不能套用城市更新的规律,其人口膨胀、土地扩展的问题对于传统村落并不适用,那么如何进行传统村落的活化更新,需注重以下几点。
对于管辂的“神”,目前只有牟宗三先生做过深刻的分析。他在《才性与玄理》中专辟一节,据管辂而论及术数学的特点:
这句话的意义正在于,它扭转了以往对“善易”判断的标准。《荀子·大略》说:“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此后,“善为易者不占”几乎成为易学的标准。在汉代的官学系统中,尽管不少易学博士都“长于卦筮”,皇帝或公卿也常找他们求卦,但这都是副业。管辂则以占筮蜚声显名,可见他不认可“善易者不占”这句话。不仅不认同这句话,还要藉此语以转变方向,提出“善易者不论《易》”。这是对术数易地位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经学易和玄学易的回应。朱伯崑先生在分析此段的时候指出,不论《易》就是不讲卦爻辞中的义理。[3](P356)实则管辂的重点不止于此,因为他不仅不讲卦爻辞中的义理,也不会像荀爽、虞翻那样讲卦爻辞的象数——他不仅反对玄学,而且不从事文本注释,不管这种注释是义理的还是象数的。
当孔子说“不占而已矣”、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之后,易学的内容,便成为对文本和卦爻象的研读、思考。汉代的经学兴起后,易学主要表现为对《易经》的注释,如今《汉书·艺文志》经部《易》类所载的那些书便是。玄学兴起后,《易》又成为清谈辩难的重要资源。经学家的《易》,与玄学家的《易》,都是管辂所谓“论《易》”的内容。管辂的不满,第一个原因是认为他们都忘了《易》最初的功用和目的——通天人之道以预料福祸。经学家注释《周易》,拘泥于卦爻象和《周易》的文本;玄学家论《易》,似乎是将《易》作为一种谈资。即便是解释通了《周易》的经文,或者辩论过了别人,对于实际占卜技术的提升,又有何意义呢?
以上仅仅是管辂在易学范式方面的不满,而“不论《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易》不可论。因为易术的根本在于“神”,这是不可论说的。刘邠曾经注释《周易》,管辂认为其注解《周易》无神,故没必要注:
管辂说“不论《易》”,隐含了对何晏、邓飏的轻视。他评价何晏说:“何若巧妙,以攻难之才,游形之表,未入于神。夫入神者,当步天元,推阴阳,探玄虚,极幽明,然后览道无穷,未暇细言。”[2](P816)他认为,何晏沾染的名士习气,使他不能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周易》的道理,而只是肤浅地拿《周易》作为谈资。由此,何晏没有、也不可能“入于神”。可见,“入神”是管辂的最高标准。
管辂认为,注《易》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所以,他也不是完全反对《周易》文本的注解。只是此事太过重大,稍有偏差,遗害万代,若非真正有见,是注不了《易》的。刘邠正是因为没有“神”,故不适合注《易》。那么,他说的“神”究竟为何?这是我们下面要分析的问题。
乙组采用DHS内固定术治疗,在股骨粗隆外侧作一长度为12 cm的切口,以便充分暴露近端股骨外侧面。然后,在大粗隆的顶端5 cm位置,经颈干角定位器协助导针前倾15°,置入股骨颈中下方,并将头钉置于股骨颈的中心位置。如果骨折粉碎,则需要通过钢丝/拉力螺钉对骨折块进行固定处理。这时,应在钢板外侧置入螺钉,并将切口缝合,实行负压引流操作。
二、术数易的根本:“入神”
故郡将刘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与辂相见,意甚喜欢,自说注《易》向讫也。辂言:“今明府欲劳不世之神,经纬大道,诚富美之秋。然辂以为注《易》之急,急于水火。水火之难,登时之验;《易》之清浊,延于万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后垂明思也。自旦至今,听采圣论,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辂不解……”邠依《易系词》诸为之理以为注,不得其要。辂寻声下难,事皆穷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变化之根源。今明府论清浊者有疑,疑则无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辂于此为论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论开廓,众化相连。邠所解者,皆以为妙,所不解者,皆以为神。自说:“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历载靡宁,定相得至论,此才不及《易》,不爱久劳,喜承雅言,如此相为高枕偃息矣。”[2](P823)
花生种子在燃烧时,会向不同方向射出火苗,也会有小小的脂肪颗粒燃烧着向周围喷射。显然,这样的火苗释放的热量很难被测量记录。将使用解剖针扎入的花生用打火机引燃时,若转动着使花生全部开始燃烧,燃烧速度很快,其热量损耗的也就较多。若只是集中外焰点燃花生的一端,使其燃烧的较小火焰加热试管底部,待燃烧一半左右时,再转动解剖针,让另一端花生开始慢慢燃烧。这样处理的结果是花生燃烧时间较长,其热量损耗就会相应的减少。
按《周易·系辞传》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又说“阴阳不测之谓神”。这当是管辂在文本上的依据。不过,韩康伯注释说:“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也”,明显属于玄学化、形上化的解释。管辂则无取于此,而是有十分明确、具体的指向。入神而能致用,当是预测福祸之类的“用”;阴阳不测之神,则是能够在事物发展之前,洞彻其先机。基于此,他认为入神能够“步天元,推阴阳,探玄虚,极幽明,然后览道无穷”。步天元是精通天文历算之学,推阴阳是可以推算阴阳四时变化,探玄虚是能窥探凡人所难见的东西,极幽明则直接指向沟通人间与鬼神。每一句话都指向一门具体的术数,但又不拘泥于术数之中,最后总括以“览道无穷”。
由此可见,“入神”也不局限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术数中。故他又说:
夫物不精不为神,数不妙不为术,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几微,可以性通,难以言论。是故鲁班不能说其手,离朱不能说其目。非言之难,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之细也;“言不尽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谓也。[2](P822)
按“言不尽意”,经过王弼的发展,成为魏晋玄学的基础命题。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说:“王弼依此(得意忘象)方法,乃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其基础由此而奠定矣。”[4](P26)管辂则不然,他不关心玄学家们的抽象思考,而是藉由“言不尽意”为术数易学奠基。这里的不可言说性,不是指向沉思的范式,而是术数实践中的不可言说。他举鲁班和离朱的例子,就是凸出实践的方式。
不过艺术家本人表示,其作品与当代诸多问题之间的相似点,可以说只是出于偶然。她试图阻止作品意义变得狭隘,争辩道:“如果政治是开放而非封闭的,艺术家的作品则会适应这种环境。”
管辂的“神”之所以要在实践中呈现,乃是因为“神”与“几”有密切的关联。《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这句话可以有哲学和术数的两重解读。对于管辂来说,“几”就是能对福祸洞烛先机,把握到最微妙的动起状态。一般人是无法把握的,只有达到“神”的人才可以。
这种讲法似乎很玄妙,其实道理并不绕。更具体来说,神与占筮时的“不可为典要”相关。《周易》的占筮和断卦,会涉及一定的规则。比如说起卦的时候,大衍筮法就很严密;而断卦的时候,学《易》的一般都知道六爻不动看卦辞、一爻动看动爻爻辞之类的规则。朱子甚至通过考订,建立了更细密的规则,以穷尽所有动爻的情况。然而问题在于,实际的占筮是没有定准的,这种规则仅仅具有参考的意义。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北史》卷八十九所载赵辅和占筮:
有人父为刺史,得书云疾。是人诣馆,别托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后,辅和谓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则父入土矣,岂得言吉。”果凶问至。有人父疾,托辅和筮,遇乾之晋,慰谕令去。后告人云:“乾之游魂。乾为天,为父,父变为魂,而升于天,能无死乎?”亦如其言。[5](P2937)
IEEE14节点配电网因为有3条馈线,所以又称为三馈线配电系统[9],系统基准容量为100 MVA,基准电压23 kV,整个网络总负荷为28.7+j7.75 MVA[10],其结构如图3所示。
泰卦是天地交通之卦,此处应该是占得泰卦六爻皆静,一般说来,就根据卦辞“小往大来吉亨”而占,是比较吉利的。赵辅和的同事便据此为断。然赵辅和分析卦象,认为泰卦是父入于土,凶之大者。事实证明赵辅和的判断是正确的。下面一个例子,乾之晋,似乎也是从纯阳之卦变为明出地上之卦,看样子不太差;而赵辅和却据京氏易体系,指出晋为乾之游魂这样一个事实。赵辅和与同事的分歧,不是具体路数的分歧,而是普遍规则与当机而断的分歧。在古代的例子中,也有直接根据卦爻辞进行占断且毫发不爽的。所以,问题不在于依据卦爻辞判断还是据卦象,或者据纳甲筮法哪个更准;而在于根据机缘选择某一种方式。这意味着占筮的每一次情境,都是具体的,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到底选择哪种占法;甚至选择用象进行判断的时候,为何选这个象而不选那个象,都是没有固定规则的。这也就是“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在占筮中的体现。
这一段最有意义的,是管辂的回答:“夫善易者不论《易》也。”邓飏发难说:“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故也?”是因为管辂在为何晏解说九事的时候,没有引用《周易》卦爻辞的文本进行解说。那么可以想见,管辂运用了术数的话语体系。
课后拓展效果V3(82.1)中引导反思V31(81.3)、拓展实践V32(82.5)得分较高,说明课程教学较好地实现了课后知识迁移,较好地实现了教、学、思、做的统一。
(二)具体的预测,其心灵活动完全是直觉的。其机械性甚弱,全无定准。[6](P81-82)
牟先生将知识的形态分为四种:(1)常识的闻见形态,此囿于耳目之官;(2)科学的抽象形态,此囿于概念;(3)术数的具体形态,此超越概念而归于具体形态;(4)道心的境界形态,此超越知识而为“即寂即照”。[6](P83)正是因为术数的非抽象性,其判断要靠“象征性的直感”,也就是术数家的“知几其神”。[6](P82)
从跑步运动消费形塑跑者身份,彰显自我阳光健康、乐观向上、坚定勇敢的身体形象和内在品质,到跑步运动分享展演跑者身份,在他者的印象评价这面“镜子”中确认自我观念,进而实现了客我身份的重建。而这种“跑者”身份,在面对现代困境以及未来冲击时,不仅可以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世界的纷繁变化,以勇敢的精神迎接不可预测的挑战,同时也可以坚定的品质避免多样选择中的迷失。
王基向管辂学习术数,才开始还能推算明白,推着推着便乱掉。这不是说越到后面越复杂。因为术数学到后面,不仅仅是像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那样是一个理论逐渐深化和复杂化的问题,而是需要一个飞跃。飞跃需要“入神”,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王基由是才感叹“此自天授,非人力也”。即便是管辂的弟弟,也无法习得:
科学知识的特点,一是理论的普遍性和可确证性,[7](P226)二是“客观”性。如果一个人说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也做了实验,但其他人做不出来,它就不可以称作是科学知识。这实际上预设了科学真理的普遍性,并将世界看作一架机器。同时,在科学实验中,人一定要将自己同研究的对象分离开来,进行最基本的“观察”。术数的实践完全与此不同:它每一次都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要与对象分离开来。因为“感应”恰恰是一种与物相互交融的状态。同时,所谓的乘承比应,以及卦象的选取,根本不是数学中的公理;而占筮时貌似根据某种道理进行的判断,也就不同于普遍的公理在某一个具体范围中的应用。其实不仅仅在对结果的判断、解读上,科学与术数有根本不同;即便是在某一次实践产生的源头上,它们也是不同的。科学实验是有目的的行为,为了验证某一原理或得到公式,科学家在控制各种变量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实验,这是有预期的行为。术数家则必须要放空自我,未来是完全开放的;而未来展示到现在的通孔,则放任给蓍龟。稍有意必固我,占筮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以至于差以毫厘、谬以千里。
但是,术数中的这种“象征性的直感”,是否就是任意的判断呢?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术数不追求一种精确的判断规则,甚至说没有规则,那么,你们又定出乘承比应的爻位规则、定出“乾为马、坤为牛”这些取象规则干什么呢?更进一步,何不把蓍龟都摒弃,直接凭内心的照彻呢?
首先,在我们看来,牟宗三先生直接用“直感”这个词可能会带来一种混淆,即术数中的判断好像不需要经过深沉的思考和分析,不需要相应的工夫以及曲折回还。尽管牟先生此处的“直感”未必是世俗所可能误会的那个意思。用“感应”一词,或许会更清楚。也就是说,术数要做出判断,一定是基于“动”,即发生了什么事情,显现了什么兆象。这个“动”来感术数者的心灵,术数家据此做出反应,此即“感应”。感应的最终结果,来感者的状态,以及术数者本人的心灵状态,都是关键因素。感不是虚的,心中的应也是实在的,而且确实有不同的类型,同时还有客观的卦象立在那里。这里的判断尽管不容易描述,不可重复,此种“对机”反对固化规则,但绝对不是随便。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王船山解释得最好。他根据《系辞传》的“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将占筮定位为人自己的理智判断与不可知力量、未知知识的一种交互感应。为什么要有蓍龟和卦象?因为事情发生的关键,以及不可知的深意,一定要通过象透出来。所以管辂说:“夫风以时动,爻以象应,时者神之驱使,象者时之形表。”[2](P817)人不是神。只有一神论中的上帝,可以站在全知全能的立场上,对于人类命运,就是知道而已,毫不需要通过什么占筮才得知,甚至还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但中国传统上并非这种宗教观,人也不可能即在此世成神,故需要象数、语言的体系来表达和理解,进行天人或人神的沟通。既然在人神之间,其中就有人谋与鬼谋的张力。就如我们上面举到的赵辅和的例子,面对占得的泰卦,筮者固然有多种选择,比如根据卦辞,或者根据卦象,或根据纳甲,甚至根据《易林》,这看上去没有规则;但你只能就着泰卦来说,因为在此刻,只有这个泰卦才是事情的先机,而不是其他卦象。象的出现,及其一系列称不上规则的规则,给“入神”提供了跳板,或者是通道。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如果你的判断或“感应”不是随意的,却又无法以规则和语言来表明,那么,凭什么保证其正确性呢?术数当然不能给予科学规范的准确性保证。这并非意味着它没有好坏优劣。难以言说的背后,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纷繁的随机性,却恰恰是最为真实的存在。但因其难以言说,所以入神的水平如何,只有另一个入神的人能加以判断。入神者之间的交流,也是通过超越于言说的感应来实现的。正如《庄子·大宗师》里面所提及的“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对持行为主义立场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接受的。不过,行为主义者对于我对他人“痛”的领会都保有质疑,因而与整个中国传统,不仅是术数传统,包括理学等都是相悖的,我们也就不专门在此展开讨论了。要言之,只有入神者能真正地理解入神者,未入神的,却也可以凭借自己的福缘找到比较可靠的入神者。
为了真正地能“入神”,术数也讲求许多修养工夫。最基本的,《系辞传》讲到占筮的时候,就说“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朱伯崑先生说,《易传》里有两套语言:一是关于占筮的语言,一是哲学语言。[3](P61)其实还应有第三重,即术数的话语。就此句来说,既可以解读为圣人一般性的工夫修养,但更基层的是占筮时的精神状态。如《卜筮正宗》说:“凡有所占,当必诚必敬,斋心盥沐,焚香祈祷,则能感格神明,洞垂玄鉴。苟或不然,难望响应。”[8](凡例第1页)这当然是针对一般的占筮者而言,其中的斋戒工夫尚未脱离他律,但仍足以说明,“入神”是需要工夫的。甚至最高的入神,与道家的坐忘相通。只有至虚至寂,才能至公而神,发生最精的感应。牟先生将术数知识看作直觉,将道家看作境界形态,认为二者不同。然而在实践中,二者恰恰是相通的。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完美融合能够推进两者的发展,激发二者之间的本质关系。要逐步改变教育教学形式,慢慢地实现数据智能化的共享。实现教育教学模式终身化,努力打造能够终身学习的环境,构建优良的教育氛围。
三、术数是可学习的吗:气质与命运
在管辂为术数所做的理论说明中,“神”既然不可说,那么也暗含着它是不可学的。正因如此,我们前面提到,刘邠放弃了注《易》。因为他被管辂批评为没有“神”,而且这种神不容易习得。王基弃学《易》,也是如此:
基曰:“吾少好读《易》,玩之以久,不谓神明之数,其妙如此。”便从辂学《易》,推论天文。辂每开变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尝不纤微委曲,尽其精神。基曰:“始闻君言,如何可得,终以皆乱,此自天授,非人力也。”于是藏《周易》,绝思虑,不复学卜筮之事。[2](P814)
牟宗三的学问底子是理学与康德哲学,却能对术数家的管辂如此关注,不仅做出了有力度的分析,还给予术数系统的知识形态以相当的肯定。可见其作为当代哲学家的卓识。今借牟先生的分析,更广而论之。
弟辰尝欲从辂学卜及仰观事,辂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见其数,非至妙不能睹其道,《孝经》、《诗》、《论》,足为三公,无用知之也。”于是遂止。子弟无能传其术者。[2](P827)
对于具体教学方法的设计而言,上述第二条基本原则是首要的,也就是说,首先要分析清楚所要教学的度量和度量单位是通过什么形式得到的,进而可以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在确定了教学策略以后,再合适地融入第一条和第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基本原则是为了明确教学过程的核心思想和基本框架,在教学过程中突出数学的本质.第三条基本原则强调注重学生认知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还要关注学生数学素养的形成.下面,简单描述这样的教学设计过程.
之所以不可教,并非说术数本身不可以传授,否则术数早就断绝失传了。管辂只是认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系辞传》),亦即没有相应材质的人,学不得这些。如果强硬要学,亦只是学成半瓶子醋,害人害己。在六经中,《诗》《书》《礼》《乐》是显教,《易》与《春秋》是隐教;从另一角度来说,其他五经是人道,而《易》为天道。管辂重视显教的意义,且认为不必人人皆掌握易术。一般人只需要把其他经典学好就行了,比如《孝经》和《论语》。毕竟我们主要生活在一个“明”的世俗间,不需要那么多人、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去做沟通“幽—明”的事。
由此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管辂的术数,在哲学根基上,还是汉代以来的气质论。人的气质不同,感应的能力也不同,术数的进境也有差别。此类气质是否可以通过修习而提升呢?并非绝对不可能,特别是后来到了理学那里一直强调“变化气质”,但气质的变化在现实中非常困难。要言之,管辂在人性的看法上,仍秉持了一种古典的气质论。
这种气质论,也是命运预测术的基础,管辂在解释自己为何能通神却夭寿时说:
吾额上无生骨,眼中无守精,鼻无梁柱,脚无天根,背无三甲,腹无三壬,此皆不寿之验。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得讳,但人不知耳。[2](P826)
动物实验的采用和发展是生命科学及医学发展的推进剂,解决了许多以往不能解决的医学实际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在动物实验中,不能仅将实验动物看做是一次试验的对象,要引导学生把实验动物看成是需要实施医学抢救的鲜活的个体,把每一次动物实验课看做是现实生活中的一次医学救援。因此,在动物实验教学中强化学生医学救援理念,对培养学生医学救援素质起到促进作用[1]。在实验内容方面,动物实验不仅包括传统教学实验,还要涉及一些与临床应用和科学研究相关的内容,充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增强学生独立运用和综合运用各种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气质决定了人的通神能力,以及性格、健康状况和寿命,乃至穷通。追求气质之来源,则是天之赋予。所谓“天之赋予”,未必有一个人格神的天,也可以是自然造化之所赋,但不管如何,赋予的过程中便有一定的机,而人的气质由此确定。管辂此处说“天有常数”正是指的这个。管辂尽管不会认同王充的无鬼说,但在气质和骨相方面,二人却有相通之处。最后,管辂预测自己的命运说:“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与我才明,不与我年寿,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儿娶妇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阳令,可使路不拾遗,枹鼓不鸣。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2](P826)“有分直”,是说命运不可移。
不过,人并非一次受气质之赋之后便脱离了天地的环境。人一直在天地中生存,便与大化时时发生气的交流。是故能否学术数,以及何时通悟,除了先天的根骨,还须后天的机缘。比如虞翻之所以能注《易》,是据说他的徒弟梦到虞翻行路时遇到一个道士,在地上布了六爻后,将其中三爻给虞翻喝了。虞翻固然不是因此才获得的易术(因为是他徒弟的梦,不是老人在虞翻自己的梦里来传授),但却将此作为他受天命注《易》的符征。就像孔子尽管一直有圣人的智慧,却要等到西狩获麟,才作《春秋》一样。
综上分析,在管辂那里,术数是可学的,但不是教科书式的教授;所以学到最关键处,还是要学生自己领悟。因此,学成与否,还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自己的气质,二是后天的机缘。管辂是自学而通,郭璞是得郭公秘授而通,不管学的途径有何区别,最终都是要自悟。
四、管辂的定位和意义
我们从管辂与何晏、裴徽等名士的交往,可以看到的是即便放达或风流如何晏等,他们对于福祸、寿禄也仍十分关心。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周易》的“学”之层面与“术”之层面,不能仅仅把前者看作是精英文化,把后者看作是民间文化。因为对于术数的讲求、信奉,世族、庶人是共通的。在敦煌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比如吐鲁番洋海张祖墓出土的《易杂占》,以京氏易学为背景,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9](P112-114)其占卜的内容可施用于各个阶层。职是之故,此方面的研究,今后亟须开展和加强。管辰在评价管辂的时候,以京房作比较:
昔京房虽善卜及风律之占,卒不免祸,而辂自知四十八当亡,可谓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见遘谗之党,耳听青蝇之声,面谏不从,而犹道路纷纭。辂处魏、晋之际,藏智以朴,卷舒有时,妙不见求,愚不见遗,可谓知几相邈也。京房上不量万乘之主,下不避佞谄之徒,欲以天文、洪范,利国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谓枯龟之余智,膏烛之末景,岂不哀哉!世人多以辂畴之京房,辰不敢许也。[2](P827)
管辰虽然一再攻击京房,辩解管辂比京房要高明;但这种辩解,正说明京房在当时的强大影响。实际上,管辂以及后来的郭璞,其占筮理论都是基于京房的。同时我们推测,以“京房”为名的大量《易》占著作,也是在六朝时期增加起来的。敦煌的《易杂占》也以京房法为主,比如说“诸鬼爻持世,法不宜兄弟”等。[10](P24)而《晋书·郭璞传》称郭璞“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11](P1899)可见管辂在京房到郭璞中承先启后的地位。我们可以说,京房奠定了整个象数体系,郭璞将之运用在占断个体人事上,在实践中达到了最高水平;管辂则是留下了最深理论说明的人。同时,京房时代的术数主要指向国家政治生活;而六朝的易占,虽然运用京房的理论,却指向了个体生活层面,管辂可视为这个转变期的关键人物。六朝时期的个体性易占,在敦煌文献中能偶尔发现一些零碎的片段,而集中的代表是《火珠林》。今本《火珠林》虽非唐朝之旧,但也保存了一些基本的形态,后来衍伸出《易林补遗》及《卜筮全书》,但其最基本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根底,已包含在管辂的说明中了。
2018年8月20日,由人像摄影杂志社主办、新疆摄影行业协会协办的第九届中国摄影化妆造型十佳大赛复赛新疆站在乌鲁木齐隆重举办。
易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论的层面和术数的层面。学界以往对易学的术数层面关注较少,一是缘于学者对“术数”的偏见,二是术数学自身缺少系统性反思的理论大师。三国时的管辂便是试图对术数学进行理论说明的人。牟宗三曾经藉由管辂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一类知识系统,但尚有许多内容待发掘。管辂说“善易者不论《易》”,这是对术数易地位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经学易和玄学易的回应。这种反对,不能从象数和义理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从文本和实践的区别来认识。管辂认为,术数的根本在于“神”,这个神不是玄学或思辨意义上的“玄之又玄”,而是实践意义中的通感和知几能力,它奠基于人自身的命限和气质中。神的表现有其通孔或路径,这就是象,象的选取不是随意的;同时入神还需要相应的工夫论保障,也是有具体规范的。也就是说,入神并非忽然得到的宗教天启,也不是完全不可捉摸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隶属于理性、直觉或神秘主义的一种独特思考方式。
无论是怎样的分组方式,小组成员都不宜过多,小组规模越大,小组中某个学生被隐藏和忽略的机会也就越大,最终小组的学习任务也只是少部分同学在完成,使合作学习的效率低下。小组的成员也不宜过少,过少的成员的分组可能会造成学习小组众多,教师没有充足精力照顾到每一个小组,课堂时间也不够每个小组展示发言。在提倡小班化教学的今天,小班额的班级为合作学习的科学分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本次研究的固定分组方法是把学生划分成4人小组,一个班级大约8—10个小组,这种分组方式可以使小组合理的开展分工合作,每个学生也有机会发言,学生参与度高,学习效率提高。
参考文献:
[1]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朱伯崑.易学哲学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
[4]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5]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牟宗三.才性与玄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英]卡尔纳普.科学哲学导论[M].张华夏,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
[8]姚际隆删补.卜筮全书[M].崇祯刻本.
[9]余欣.中古异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0]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11]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AstudyofGuanLu’sIChing-learningandtheepistemeofnumerology
GU Ji-m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IChing-learning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was the theory and the other was divination or numerology. The numerology of IChing was not very popular with the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one hand, many scholars had a prejudice against numerology; on the other, numerology lacked a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by great scholars. Fortunately, Guan Lu, a master of IChing in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s a scholar who gave it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from whom Professor Mu Zongsan benefited in his research on Chinese classics. Guan Lu once said: “A real IChing master rarely discusses IChing,” which was a defense for numerology-based IChing and against other approaches. We should not comprehend this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umberology and philosopy, but a distinction between textualism and practice orientation. Guan Lu considered Shen(magic) as the key point of divination. However, this Shen was not a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 but an ability of perceiving slight changes and predicting the future. Significantly, this Shen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intuition or mysticism, because Xiang(image) and the Attainment Theory were distinctly required in this procedure, which made it a unique mode of thinking different from rationalism or intuitionalism.
Keywords: Guan Lu; IChing-learning in the Six Dynasties; numerology; IChing; metaphysics
中图分类号:B23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9)01-0040-07
收稿日期:2018-08-10
作者简介:谷继明,男,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陆继萍
标签:术数论文; 周易论文; 易学论文; 入神论文; 玄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诸子前哲学论文;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同济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