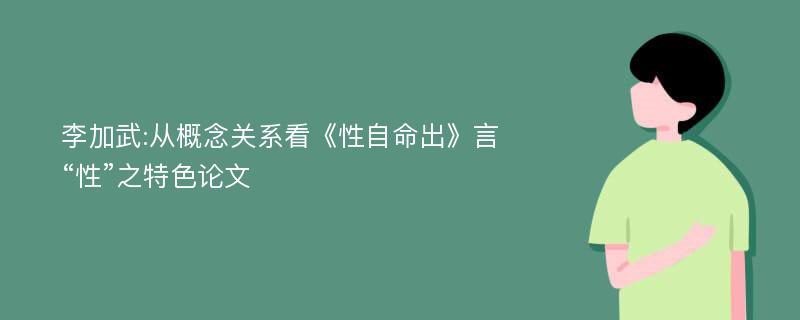
摘 要:在《性自命出》中,“性”是一个核心概念,它与“天”“命”“气”“情”“心”“物”“学”“教”等外缘性概念共同构成一个层次鲜明、内容丰富的立体架构。其中,“天”以“命”为中介而为“性”的根据,“情”是“性”的外在显现,“气”和“物”分别是使“性”转化为“情”的内在依据和外在条件,“学”和“教”是塑造和培养“性”的两条主要途径。这一立体架构的逻辑展开,不但构成简文内容进展的内在依据,而且使得“性”字的丰富内涵得以澄清。
关键词:《性自命出》;性;气;情;物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是孟子以前儒家讨论人性问题最为集中的一篇文献。该篇“性”字凡26见,多写作“眚”,“眚”字通“生”,“生”即为“性”的古字[1],“溯中国文字中性之一字之原始,乃原为生字”[2]6。丁原植先生认为:“简文的‘性’,不但应当读作‘生’,而且也需要从‘生’字来领会。”[3]230“生”属象形字,在甲古文中从从一,象草木出于地,有生长之意,初指草木之生,继指万物之生。《说文·生部》云:“生,进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可见,“性”字的本义当与生命的发生和成长有关,这从简文中也可得到印证,如《语丛三》有“生为贵”“有性有生”“有性有生乎名”的说法、《性自命出》有“性或生之”的说法。对于“性或生之”一句,蒙培元先生认为,这里的“或”字疑是“者”字之误,那么此句即为“性者,生之”,意即“性”就是生命或生命创造本身。这虽然“还不是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题,但是已经正式提出‘性’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生命本身”[4]。
在“以生言性”的理论视域下,“性”的内涵及外延无疑是非常广阔的,举凡人先天具有的客观材质或本然质素、人的主观倾向性和能力、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都属于“性”的范畴。如《性自命出》简7说:“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这里的“性”就是指万物(也包括人)先天具有的客观材质或本然质素;简4及简8说:“好恶,性也”“人而学或使之”,则是指人生而具有的倾向性和能力;简43-44说:“用身之弁者,悦为甚。用力之尽者,利为甚。目之好色,耳之乐声,郁陶之气也”,是指人的生理及心理需求。
当前,高职院校护理专业的信息化教学资源与医院实际护理信息系统存在脱节的情况,即护理专业学生在院校学习过程中很难接触到实际工作中需要用到的信息系统,这也就使得护理专业学生在进入医院进行护理实习时,需要进行二次培训,无形中增加了培训成本。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增强护理专业学生的护理专业能力,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要求护理专业教学加强与医院的合作,积极开设第二课堂,改变以往护理专业校内教学与医院护理岗位实习相脱离的教学现状。
在明确了“性”的内涵及外延以后,简文又从多个角度展开对“性”的内容及特点的分析,分别阐明了它的来源、本质、显现和趋向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是“性”与“天”“命”“气”“情”“心”“物”“习”“教”诸概念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以此为逻辑线索来考察简文言“性”的特色。
一、“性”与“天”“命”
《性自命出》简2-3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简文出土伊始,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句话与《中庸》“天命之谓性”说的关联,甚至还有学者据此断定简文与《中庸》属于同一思想流派。我们觉得,虽然这两篇文献在论述的对象上有相同之处,即都是在讨论“性”与“天”“命”的关系问题,在论证的逻辑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两者在具体的观点上却有着明显不同,即简文只是将“天”“命”作为“性”的来源看待,至于“天”“命”与“性”在外延和内涵上是否一致则未加详述。当然,从简文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推断,“性”的外延要小于“天”“命”,“性自命出”意味着“性”只是“天”“命”显发出来的一部分内容而已,它与“天”“命”并不是等值的。而《中庸》的“性”与“天”“命”在本质上却是等值的,只不过“命”是由天而言、“性”是由人而言罢了[5]。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天命之谓性”是一种定义性的陈述,表明了“性”的内涵就是“天”“命”,即“A是B”。而“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则仅仅是一种关系性的陈述,表明了“性”的源头是“天”“命”,但在“性”与“天”“命”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即“B从A中来,并不完全是A”[6]。
简文以“喜怒哀悲之气”论“性”,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以情论性”的范畴。虽然在理论上“性”是“情”的本质,但是由于“性”处于隐而不显的地位,所以在现实中我们只能通过外显之“情”的特点来了解内在之“性”的特点。因此,“情”反倒成为“性”的本质。在《性自命出》中,“情”主要是指人的自然情感,它和人的自然生命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关联,“自然情感就是自然生命的最直接体现,离开自然情感去谈论人的生命问题,是根本不可思议的。”[16]所以,简文“以情论性”仍然是在孔子乃至更早时代的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说“性”。“性”并不具有纯粹抽象与超越的特点,也不具有价值内涵。
分别在固定周期传输和变周期数据传输网络中发送3000个数据包,并重复20次试验。统计两种数据传输模式下监测软件接收数据情况。网络稳定性测试结果如图12所示。
相较而言,《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则直接指出: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简文中的“喜怒哀悲之气”也同时包含物质性和精神性因素的存在。这是因为每一个人内在情感的产生,既与他的生理性(物质性)因素有关,也与他的心理性(精神性)因素有关。因此,《性自命出》中的“气”乃是指一种与人的心理及生理因素都有关系的生命存在,是个体生命实存的整体。同时,简文不是强调“气”作为概念的特质,而是强调它“诚于中、发于外”的能力以及它作为主体生命力量的展现这一点。这与帛书《五行》说文“仁气”“义气”“礼气”的说法颇有相通之处,即两者都是强调“气”的能动性特点。所不同的是,在帛书《五行》中“气”是主体道德实践的发动力量,而在《性自命出》中,“气”则是主体自然情感的发动力量。
二、“性”与“气”
《性自命出》简2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作为人情内在依据的人性,在人体内部又以何种状态存在呢?对习惯于作象思维的古人而言,人性既能存在于人体内部,又了无形迹,那么它的唯一存在形态只能是“气”[12]。这是因为“气”虽然是一种实存,但却无形无状、不著形迹,正应了人性的这一存在特点。这种以“气”论“性”,以“气”为内、“情”为外的观点也见于简文的如下表述中,简36-37说:“目之好色、耳之乐声,郁陶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目之好色、耳之乐声”就是指人的好乐情感,简文认为这种好乐情感产生于人体内部的“郁陶之气”。“郁陶之气”作为好乐情感的产生根据,也就是好乐之“性”。“郁陶之气”为内,显发于外则表现为“目之好色、耳之乐声”的好乐之情。当然这种以“气”论“性”,将“情”“气”相连的做法并非简文首创,它也见于先秦时期的其他文献中。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之语:“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其中,“六气”就是指“阴、阳、风、雨、晦、明”,它们作为天地之间的存在聚集于人体内部,并产生出“好、恶、喜、怒、哀、乐”这六种自然情感。这样就把人的自然情感与“天地之气”联系了起来,从而为人情找到了内在根据。然而是篇还没有直接将人体之气(即“天地之气”)称为人性。
以“天”为自然之天、“命”为自然生命、“性”为自然人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三者间的内在联系,也见于先秦时期的其他文献。如郭店楚简《语丛三》说:“有天、有命、有生”,就是对三者之间衍生关系的简明表达。《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这里的“命”就是指“生命”,此“命”生于天、地,在人则为“性”(生)。《管子·业内》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生”,在这里也是指“自然生命”,如果我们将其读作“性”,以之为“自然人性”也未尝不可,它是禀于天而在于人者。《大戴礼记·本命》云:“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王聘珍在《大戴礼记解诂》中说:“道者,天地自然之理。”可见,“天”与“道”实为同一对象的不同名称而已:“天”重在其实体义,“道”重在其规律义。“天”之为“天”,即在于其生生不息、创化不已,这也是“天道”的核心要义[7]。此处所说的“命”实际上是指得之于自然之天的自然生命,“性”是指体现于个体的自然人性。《庄子·天地》:“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未形之“一”(即“天”或“天道”)分散于各个事物,使得每个事物自然分定如此,这就是“命”。“命”则生物,物则有形有神、有条有理,这就是“性”[10]。综上所论,我们不难发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一命题并不是一个有关善恶的价值判断,而仅仅只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客观陈述。它是对古初以“生”言“性”这一理论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并且将“生之谓性”所包含的“性由天赋”思想明确表达了出来。
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喜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喜必见。怒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怒必见。欲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欲必见。惧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惧必见。忧悲之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忧必见。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隐也。
它认为人有“五性”,所谓“五性”就是指喜、怒、欲、惧、忧“五气”,它们隐藏于人体内部,然而这“五气”本身又具有外发的倾向性和动力,它们“诚于中”必然要发现于外,当其发现于外时就成为喜、怒、欲、惧、忧五种自然情感。实际上《礼记·乐记》“(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的说法就与此处“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的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其中,“四”是指阴、阳、刚、柔“四气”,亦即指人性,“发作于外”则是指人情,这实际上还是在说情气、性情之间的关系问题[13]。另外,郭店楚简《语从一》说:“凡有血气者,皆有喜有怒,有慎有庄。其体有容,有色有声,有嗅有味,有气有志。”其中,“志”当为情志,“有气有志”即“有气有情”,联系“凡有血气者,皆有喜有怒”的说法,那么简文也是在说人体内部的“血气”是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的产生根据。
海明威在其创作中一直遵循年轻时形成的“电报体风格”,在其作品《午后之死》中也正式提出了他在创作上的“冰山原则”。海明威以冰山为喻,表达了作者只应描写冰山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而隐藏于水下的则应该通过文字的延伸由读者去想象补充这一主张。本文通过解读《老人与海》,分析小说的文体风格及人物塑造来探究“冰山原则”的独特之处。
有学者将先秦文献中的“气”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指物质性的质料,一是指精神性的存在。例如《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孔颖达疏谓:“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这里的“气”就是指物质性的质料;而《礼记·祭义》“气也者,神之盛也”中的“气”,则是指精神性的存在。那么,简文所说的“喜怒哀悲之气”又是属于何种性质的气呢?其实,当我们这样来提问时,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这种简单二分法是否适用于先贤有关气的思考?难道在“气”的物质性因素和精神性因素之间存在着绝对对立、无法逾越的鸿沟?难道在主要是作为物质性(或精神性)存在的“气”中就丝毫没有精神性(或物质性)的因素存在吗?当然,答案是否定的。例如荀子在《修身》“治气养心”一章中就明确将“治气”与“养心”放在一起讨论,指出在“气”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因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张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同时入手,以期达到“治气”与“养心”的双重目的,而他寻找到的有效途径就是“礼”。
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说:
里藏泰实则气不通,泰虚则气不足,热胜则气寒,寒胜则气热,泰劳则气不入,泰佚则气宛至,怒则气高,喜则气散,忧则气狂,惧则气慑,凡此十者,气之害也,而皆生于不中和。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舒之以意;惧则反中,而实之以精。
长期以来,我国铁路建设项目大都是中央政府投资占主导地位,包括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在内的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额虽略有增加,但所占比重仍然很小。
这段话的主旨是在谈“养气”,它指出影响“气”的存在状态的既有身体性的因素,如“里藏泰实”“泰虚”“热”“寒”“泰劳”“泰佚”等;又有精神性的因素,如“喜”“怒”“忧”“惧”等。因此要想达到“养气”这一最终目的,就要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同时着手。
《摘编》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三农和贫困群体,亲力亲为,践行庄严承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亲民爱民惜民之情怀。读罢,一位站高望远、总揽全局,决胜脱贫攻坚、共享全面小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大国领袖形象跃然纸上。“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既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为民情怀,也是一个执政党为民造福的应为之事。
“越中山水之奇丽者,剡为之最。剡中山水之奇丽者,金庭洞天为之最。其洞在县之东南。循山趾而右去,凡七十里,得小香炉峰,其峰即洞天之北门也……真天下之绝境也……是以琅琊王羲之领右军将军,而家于此山。其书楼墨池,旧制犹在……其金庭洞天,即道门所谓赤城丹霞第六洞天者也……过此峰东南三十余里,有石窦牙为洞门,即洞天之便门也。人或入之者,必赢粮秉烛……莫臻其极也……登书楼,临墨池,但见其山水之异也,其险如崩,其耸如腾,其引如肱,其多如朋。不三四层,而谓天可升。”[3]7520
需要指出的是,《性自命出》以“气”论“性”,还处在“即生言性”的阶段。这是因为在简文中,“气”还是指自然生命之气,它是产生喜、怒、哀、悲等自然情感的内在根据,在这样的“气”中并不包含善恶等道德价值,正如庞朴先生所说:“这样的气,无所谓善不善的问题,顶多是一些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素材,一些待发的力。”[14]而由这样的“气”所决定的“性”,就是自然人性,也就是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当然,简文的观点是对“生之谓性”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因为它已明确指出“性”的实际内容就是“喜怒哀悲之气”。
三、“性”与“情”
《性自命出》简2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简文认为,“诚于中”或“藏于内”的人性在外物的刺激下,由内而外地表现出来,展现为“喜怒哀悲”等不同类型的自然情感,这与《礼记·乐记》篇“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的说法明显一致。而好、恶、喜、怒、哀、悲等自然情感之所以能表现于外,除了需要借助于外物的感召和刺激外,还需要有来自于主体内部的根据。这就是相对于已发之“情”的未发之“气”,也就是“性”,故简5说:“凡性为主,物取之也”。“性”是产生“情”的材质、倾向和能力,是产生“情”的内在生理及心理基础。从“性”“情”关系的角度看,“性”是“情”的未发状态,“情”是“性”的已发状态。从未发处言,“性”、“情”实为一体;从已发处言,“性”、“情”已显分野[10]。这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说法颇有相通之处,对此朱熹《注》云:“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性也。”可见,两者都将“性”理解为内在的未发状态、“情”理解为外在的已发状态。而《性自命出》对《中庸》的深化及发展处在于,它明确指出由未发之“性”到已发之“情”的过渡与中介是“物”。“性”“情”的“未发”“已发”关系也表明,“性”的存在是不可直接体验和证知的,对它的认识只能通过“情”来进行。这也体现出“性”“情”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即“性”虽然是“情”的本质,却不可见,具有抽象隐含的特征,它必须藉情而显[15]。此即唐李翱所说:“性不自性,由情以明。”
《性自命出》“情生于性”的命题又见于郭店楚简《语丛二》,《语丛二》说:
爱生于性,亲生于爱。欲生于性,虑生于欲。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宜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
恶生于性,怒生于恶。喜生于性,乐生于喜。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人均谷类产量很低,豆类和薯类作为当时人们摄取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来源,也被列入了粮食范畴。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其中构成豆类主体的大豆作为植物油原料的比例越来越大②,大豆与其他植物油籽(如油菜籽、花生等)已经没有根本差别,延续既有的统计方式,仍将大豆统计到粮食中不仅不合时宜,还容易造成粮食和油料统计分析的系统误差。此外,除西南、西北等少数贫困山区外,薯类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作为蔬菜食用,也不宜继续列为粮食进行统计。③
愠生于性,忧生于愠。惧生于性,监生于惧。
本届展会以“科学发展·低碳节能”为主题,以科技创新、清洁高效、节能减排为主要内容,来自中国及其他近10个国家的煤炭企业、煤炭洗选设备制造企业、煤矿节能及环保设备企业、煤化工及石化企业和相关科研院所的200多家单位参加了展览,展览面积超过1.3万m2,集中展示了煤炭洗选加工、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煤化工及石油化工等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和新成果,充分体现了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人民日报等20多家新闻媒体对展览会进行了采访报道。
强生于性,立生于强。弱生于性,疑生于弱。
简文只是笼统地提出“情生于性”“情出于性”的命题,而《语丛二》则将其详细展开,分别指出爱、恶、愠、亲、怒、忧、欲、喜、惧、乐、疑、虑等不同类型的自然情感都产生于人性,并且它还进一步指出以上各类情感间的内在衍生关系及其强烈程度之别。例如,亲、怒、忧生于喜、恶、愠,两者虽然都属于自然情感的范畴,但是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强烈[13]。当然,有关自然情感之间的内在衍生关系及其强烈程度之别也见于《性自命出》的相关表述中。例如,简34-35说:“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作。作,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通。通,愠之终也。”作为同一类型的自然情感,喜、陶、奋、咏、犹、作各自所体现出的喜悦程度是不同的,同样,愠、忧、戚、叹、辟、通各自所体现出的悲伤程度也是不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情感程度递次加深的关系。
在明确了两者间的区别以后,我们就要详细考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一命题包含有哪些具体内容:首先,简文将“天”作为“命”的来源、“命”作为“性”的来源,“天”以“命”为中介而为“性”的根源,这就意味着“天”“命”并不是高高在上、与人无关的绝对力量,而是授人以“性”、与人相通的最高存在。对人而言,“天”“命”是亲切的,“天”“命”与人性之间存在着授受关系。这一授受关系绝不是外在的因果关系,而是内在的本质联系[4]。当“天”“命”授人以“性”时,“天”“命”并不是从外部作用于人,使人相应地具有某种“性”。如果是这样的话,“性”是“性”、“命”是“命”、“天”是“天”,“天”“命”与“性”之间仍然是两个东西,只是人性要听命于“天”“命”罢了。相反,它们是一种内在的转化关系,即“天”“命”的一部分转化为“性”、成为“性”的具体内容[4]。其次,从人性的角度看,既然人性源自“天”“命”,那么这就意味着人性具有超越的形上根据,“天”“命”保证了一切人性的绝对性、神圣性和平等性。正如郭店楚简《成之闻之》所说:“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别之”,即在天生的层面、天道神圣的层面,一切人性皆平等[7]。另外,这也意味着“天”“命”的性质决定了人性的性质。虽然在这句话之后,简文再也没有关于“天”“命”的论述,但“天”“命”决定下的人性的性质和内容却成为简文理论体系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并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了简文的理论特点。再次,在《中庸》那里,“天”“命”尚未明确区分,而在简文中,“天”“命”已经出现分野,“命”成为沟通“天”与“性”的中介:它一方面上显于“天”,另一方面下化成“性”;一方面将“天”之博厚高明贯注于现实人性当中,另一方面又将人性的体验显发给“天”、成就“天”的生机。如果没有“命”,“天”就无从体现它的博大深邃,“性”也就无从显现它的源远流长[8]54。通过“命”的衔接与过渡,“性”与“天”相契相合,因此“命”就成为一种流动的双向显发的存在[9]。而在“天”与“命”之间,“天”显然更加根本,“命”和“性”的性质和内容都是由“天”决定的。“天”处在“性”“命”概念系统中的最根本位置,是一切生化流行之源[8]54。当然,这与先秦儒家谈论人性问题的一般方式也相契合,即先秦儒家不是仅从人自身出发来说明人性问题,而是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既然“天”与“性”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有何种意义上的“天”也就有着何种意义上的“性”。
四、“性”与“物”
《性自命出》简4-5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凡性为主,物取之也。”关于“势”,简6说:“物之设者之谓势”,指“物所处的形势。”[17]95简文认为,在“性”“物”关系中,“性”虽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物”和“势”只是使“性”表现出来的外在条件,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外在条件,“性”就无从表现出来。换句话说,人性虽然可以外显为“情”,但却不会无端表现出来,促使“性”转化为“情”的中介和桥梁就是“物”。而何者为“物”呢?简文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给“物”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凡见者之谓物”,即任何看得见的东西都属于“物”的范畴。从主体的一面看,主体本身虽然具有好恶的倾向性和能力,但只有在外物的刺激和感召作用下,才能表现为:“当好时则好、当恶时则恶、当喜时则喜、当怒时则怒、当哀时则哀、当悲时则悲。”[12]如果没有“物”在外部取“性”的话,“性”是出不来的,这就像金石等乐器虽然内含声音,但如果没有槌子在外部敲击它,也不会发声一样,所以简5说:“动性者,物也”“出性者,势也”。从对象的一面看,当对象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时,主体则好之;否则,主体则恶之。可见,“那些同人的需要毫无关系的事物,是不能引起人们相应的感情的;只有那些与人的需要密切有关的事物,才能引起人们或肯定或否定的情感。”[18]换言之,好恶并不是没有针对性的情感或欲望,它总是针对特定对象而发的,故简3说:“所好所恶,物也”。只有当好恶之性落实到具体对象上时,它才会成为具有实际内容的现实存在。
五、“性”与“学”“教”
《性自命出》简7-9说:“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凡物无不异也者,刚之树也,刚取之也。柔之约也,柔取之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简文指出,人和动物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动物的实然之性就是它自然本性的原始呈现,而人的实然之性却可以呈现出与他的自然本性完全不同的面貌,这是因为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重新培养和塑造自己的自然本性。相对于动物被动地随其本性,人却能因积学而成其性[5]。有鉴于此,简文十分重视后天人为对人性的塑造和培养,它的大部分内容也都集中在讨论如何“动性”“逆性”“交性”“厉性”“绌性”“养性”“长性”上。简9-14说:
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凡见者之谓物,快于己者之谓悦,物之设者之谓势,有为也者之谓故。义也者,群善之蕝也。习也者,有以习其性也。
在先秦时期,“天”有多重意涵,它既可以指“神性之天”“主宰之天”,又可以指“自然之天”“运命之天”“义理之天”。而《性自命出》中的“天”是指何种意义上的“天”呢?由于简文没有详细说明,我们也无从知晓。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既然“天”“命”与“性”是内在统一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通过“性”的性质和内容来逆推“天”的性质和内容。如果我们从“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四海之内,其性一也”等一系列说法逆推“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意义,则可以确知简文的“天”当为“自然之天”[10],那么,由自然之天所降生的“命”即为自然生命。因此,简文中的“命”从形式上说是指“天命”,从内容上说是指“生命”。“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是说人性源自人的自然生命,人的自然生命来源于自然之天,这实际上说的就是一个自然生命的生发过程。诚如傅斯年先生所言:“古初以为万物之生皆由于天,凡人与万物生来之所赋,皆天生之也。故后人所谓性之一词,在昔仅表示一种具体动作所产之结果。”[11]
简文认为,对人的自然本性来说,触动它的是外在之物,迎合它的是欢悦之事,教育和改造它的是有目的的人为,磨砺和锤炼它的是行为之义,使它表现出来的是客观情势,培养和塑造它的是后天积习,增长和统率它的是人道[19]。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动性”“逆性”“交性”“厉性”“出性”“养性”“长性”七者不是任意的罗列,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逻辑递进关系,共同反映了由一般地叙述“性”、“物”关系到有意识、有目的地用人伦规范来塑造和培养人性的整个过程[12]。而简文之所以一开始要讨论“性”“物”关系问题,也是要为重新塑造和培养人性的后天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在此基础上,简文进一步指出塑造和培养人性的两条主要途径,即“学”和“教”。首先,它十分重视学习对于人性的塑造和培养作用,简8、11、14说:“人而学或使之也”“养性者,习也”“习也者,有以习其性也。”“学”和“习”原本是中性的,是指所有可以使人性受到影响的外部因素:它既包括使人性日趋于善的因素,也包括使人性日趋于恶的因素,所以孔子说“习相远”。但在这里则是指对人性的正面影响因素[13]。其次,它也充分意识到教育对于人性的塑造和培养作用,简9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简文认为,虽然每个人的自然本性是相同的,并不存在善与不善的区别。但是在现实中,却表现出善与不善的差异,这些都是由不同的教育引起的,因此要想使人性日趋于善,就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简18说:“教也者,所以生德于中者也。”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生德于中”,即将美好的道德品质在人性中固定下来[15]。而教育的具体手段是“诗”“书”“礼”“乐”,“诗”“书”“礼”“乐”是由圣人创作出来的,圣人根据一定的目的和意图创造它们,然后以之为手段来教育百姓,使百姓日趋于善,简15-18说:
智生于性,卯生于智。子生于性,易生于子。
“诗”“书”“礼”“乐”的核心内容是“道”,即“人道”。简14-15说:“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它的具体内容就是先秦儒家所提倡的仁、义、忠、信等人伦规范。圣人通过“诗”“书”“礼”“乐”对人心施加影响,并通过影响人心来作用于人性。在诸种教育方式中,简文尤其重视“乐”的作用,这是因为在“诗”“书”“礼”“乐”四者当中,最容易打动人心的莫过于“乐”,“乐”能与人的内在情感产生共鸣,通过“乐”的作用可以使人性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善道的感化[12]。故简22-26说:
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叹,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咏思而动心,喟如也,其居次也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始其德也。
在简文中,“礼”有广狭两层含义:狭义上的“礼”是与“乐”对举的“礼”;广义上的“礼”是包含了“乐”的“礼”。此处所说的“礼”则是广义上的“礼”,“乐”在这里不但是“礼”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礼”的深层表现。简文认为,一般的声音,只要它是出于人的内在真情实感,就能真切地打动人心。例如,人们听到爽朗的笑声就会鲜明而喜,听到动听的歌谣就会快乐振奋,更何况是听到美妙的音乐呢?所以人们听到琴瑟之声就会激动而赞叹,观看“赉”“武”就会庄重而恭敬,观看“韶”“夏”则会惭愧而收敛[17]97。由于“乐”在培养和增进主体内在德性的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性自命出》给予其特别的重视,简28说:
郑卫之乐,则非其听而从之也。凡古乐动心,益乐动嗜,皆教其人者也。
鉴于国外对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管理较国内起步早,其对设备开放共享问题的研究、实践、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均值得探讨和思考。
简文指出,“乐”分“古乐”和“益乐”两种,“古乐”是指合于礼义的音乐,“益乐”即“淫乐”,是指非分乱礼、毫无节制的音乐。虽然它们都能拨动听众的内在心弦,对人心产生深刻影响,但真正能增进主体内在德性的只有“古乐”,“益乐”只能挑起人的内在嗜欲。所以简文主张通过“赉”“武”“韶”“夏”之类的“古乐”来教育普通民众,而不是以“郑卫之音”使百姓受到负面的诱导。至于“乐”为何能深入并打动人心,简29-31说:
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哭之动心也,浸杀,其央恋恋如也,戚然以终。乐之动心也,浚深郁陶,其央则流如也以悲,悠然以思。
自古以来,柳在中国都备受人们喜爱,人们不仅将其本义传承下来,还为其注入新鲜意蕴。从历时的角度看,“柳”历经千百年的岁月变迁,不断吸收各种文化,逐步形成了多种文化内涵。
简文认为,这是由于“乐”本来就来源于人情,它发自于人的情感深处和生命根源处,是人的内在真情自发、自然、自觉、自由地流露而不带有丝毫强制性,同时,它通过对自然情感的感染催生起道德情感,使听众本有的意志之心得以感发而兴起[10]。所以,用“乐”来塑造和培养人性就比“礼”来得更加直接和深入。
综上可见,《性自命出》提出“性或生之”,还属于孟子以前“以生言性”的老传统。“天”“命”分别作为“性”的终极根据和直接来源,决定了人性的性质、内容、特点,并成为简文理论体系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与“天”“命”作为人性的超越、形上根据不同,“气”则是“性”的现实依据、是使“性”显发出来的内在动力。“性”之显发即为“情”,“情”是“性”的外在表现,没有已发之“情”就无从认识未发之“性”。而由“性”及“情”的过渡与中介是“物”,“物”是使“性”显发出来的外在条件。自然人性需要通过后天的塑造和培养才能合乎“道”“义”,这就离不开“学”“教”。“学”“教”的根本目的是“生德于中”,具体手段是“诗”“书”“礼”“乐”。在这四种工具中,“乐”由于其自身特点而最受重视。
㉒王浦劬、赖先进:《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廖名春.伟大传统——荀子二十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83-206.
[2]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 谢维扬,朱渊清.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4] 蒙培元.《性自命出》的思想特征及其与思孟学派的关系[J].甘肃社会科学,2008(2):36-43.
[5] 郭振香.《性自命出》性情论辨析——兼论其学派归属问题[J].孔子研究,2005(2):25-32,126-127.
[6] 范赟.《性自命出》的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心性学说的推进[J].社会科学论坛,2010(17):150-156,171.
[7] 赵广明.神圣与世俗的先验根基——试论先秦性情思想[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8-33,111.
[8] 欧阳祯人.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9] 刘文朝.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中庸》的性情哲学[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2.
[10] 余开亮.《性自命出》的心性论和乐教美学[J].孔子研究,2010(1):18-25.
[11] 梁涛.竹简《性自命出》的人性论问题[J].管子学刊,2002(1):65-69.
[12] 陈代波.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简析[J].东疆学刊,2000(4):58-65.
[13] 陈来.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J].孔子研究,1998(3):52-60.
[14] 李锐.孔孟之间“性”论研究——以郭店、上博简为基础[D].北京:清华大学,2005.
[15] 黄意明.“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J].中州学刊,2010(1):136-141.
[16]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6.
[17]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18] 赵馥洁.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价值意识[J].西安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58-61.
[19] 梁涛.《性自命出》与早期儒家心性论[R]//潘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学术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62-371.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Xing” in XingZiMingCh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Relation
LI Jiawu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Xing”(human nature) is a core concept in XingZiMingChu, which makes a stratified coexistence structure with Tian, Ming, Qi, Qing, Xin, Wu, Xue and Jiao. Tian is the source of Xing with Ming as an intermediary. Qing is the outward expression of Xing. Qi and Wu a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Xing to Qing respectively. Xue and Jiao are the main ways to shape Xing. This structural logic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the bamboo slips and clarifies the abundant meanings of Xing.
Keywords:XingZiMingChu; Xing; Qi; Qing; Wu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634(2019)05-0026-07
收稿日期:2018-1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ZX036)
作者简介:李加武 (1985-),男,安徽舒城人,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 蒋涛涌)
标签:自然论文; 人性论文; 情感论文; 之气论文; 是指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ZX036)论文;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