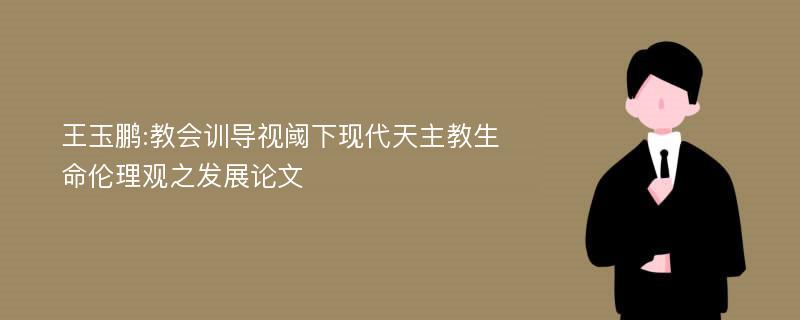
人类已进入一个新纪元,科技将人带到十字路口。现代生物科技突飞猛进,尤其自上世纪80年代“人类基因体研究计划”(HGP)启动以来,基因治疗、基因筛查、基因转殖、基因编码技术等在当代分子生物领域如火如荼展开。这在伦理、法律、社会、经济诸多领域引发广泛而尖锐讨论。在所有围绕现代生物科技伦理的讨论中,罗马天主教会的立场颇引人注目,其表达以清晰明确、一以贯之为显著特征。天主教生命伦理学内容丰富,流派纷呈,成果丰厚,对之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并非易事。本文仅以天主教会训导和教宗神学思想为视阈,力图简要勾勒现代天主教生命伦理观之发展图景,以发现其为“保护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之努力。
一、奠基:《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与《人类生命》通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医学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一个崭新时代,由此导致西方社会人们的两性关系、婚姻家庭和生命伦理等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人们逐渐接受抗孕(contraception)、代孕、安乐死、器官移植等技术。
综上所述,高频超声频率和低频振动频率均会对试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在合理选取超声频率、振动模态且低频激励电压较大时,损伤试样的调制系数远大于参考试样,非线性振动声调制方法能够较易分辨试样是否存在缺陷。
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对天主教基本伦理价值观带来严重冲击,对此,罗马天主教会也做出了回应。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重要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有专门部分对“人与人的爱与尊重生命之间的和谐”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宪章》指出,“在天主就传送生命与真正的婚姻之爱两者所钦定的法律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矛盾存在”,“每一个婚姻行为本身必须向传送生命开放”,其根本归旨在于以天主教伦理捍卫“人格”以及“婚姻与家庭”的尊严。或许可以说,梵二《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为现代天主教生命伦理发展放下了第一块基石。
如果说《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为天主教会应对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提供了一个牧民性的纲要,那么,1968年教宗保禄六世颁布《人类生命》通谕则为教会这些教导提供了具体内容。通谕重申教会对人类两性关系方面“恒久且一致的训导”,即两性行为中包含结合和生育的双重意义,通谕反对“人工的办法”抗孕,主张采取合乎道德的调节生育,即“自然调节生育”或“周期性节制”。通谕发布后,引起世界舆论大哗,教会内外对这份文件都有所批评和保留,它甚至被称为是天主教史上“最愚蠢”的通谕。面对强劲的科学至上论和现代哲学的高扬的主体价值论,天主教伦理神学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亟需从神学上对之进行有说服力的辩护。尽管《人类生命》通谕备受争议,但凡涉及生命伦理问题,后来历任教宗都以之作为讨论的起点和准绳。可以说,它是为现代天主教生命伦理发展放下的另一块基石。
二、走向成熟:《身体神学》与《生命的福音》通谕
(一)若望保禄二世的《身体神学》
教宗保禄六世《人类生命》通谕成为其继任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宣讲和写作《身体神学》最直接的目的,最初动机,而他身体神学的最终也是要落实到《人类生命》所倡导的“全面的人观”那里去。简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身体神学》就是要阐发《人类生命》之神学意义,从理论上回应教会内外对这份通谕的争议。为此,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既立足传统天主教启示神学、伦理学和人类学,同时运用圣经诠释学、现象学、后现代理论等,在捍卫梵二会议和《人类生命》通谕所表达出的传统天主教伦理价值观同时,通过对现代哲学和科学至上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结合圣经和天主教伦理神学做出了新的神学诠释与建构。
如果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身体神学》主要侧重于两性伦理学的话,那么,他在1995年发布的《生命的福音》通谕则在两性伦理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到生命伦理学领域。
(二)《生命的福音》通谕
若望保禄二世在其《身体神学》中,提出按真义重读“身体的语言”。教宗着重分析和揭示了圣经先知书,雅歌和多俾亚传中所表达的身体的“真义”,即超越情爱进入纯爱(agape),以忠诚和贞洁活出婚姻生活的本质。在具体牧灵指导中,若望保禄二世同样主张“自然调节生育”或“周期性节制”。其理由是,这样一种两性道德规范,首先它是自然律的一部分,另外它更合乎天主启示的道德秩序,与圣经原始资料所包含的整个启示教导相一致,植根于圣传和圣经传统之中,且具有完整的人学和伦理学基础。只有采用这样的调节生育方法,才能显示“夫妇的洁德”以及他们对生命和家庭价值的尊重,才能表明其对“造物主的计划”的忠诚。为此,婚姻中的男女应该学会“自我克制”,行艰苦的克修之功,对那“来自天主的”都怀有敬意,向圣神的恩赐开放,藉着恒切祈祷和常领圣事,在婚姻与家庭生活灵修中,读出“身体的语言”之真义。
小学数学学科作为教育中的三大主科之一,与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应该创新小学数学的教学方式,促进小学数学的教学效率,以促进学生的发展。在教学当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
在《身体神学》中,关于人类生殖,教宗集中讨论的问题是生育中各种人工调节技术和抗孕措施的做法,如堕胎、直接绝育等。在《生命的福音》中,教宗在第3,11-13,58-63条又进一步对上述行为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认为堕胎是“本质上的恶”,属于“罪”的范畴。这种推论,究其根源,在于如何界定人,即仍然要回归到一个古老的基本问题,人是什么?按照天主教会的观点,人从受孕的那一刻起,就应受到尊重,并应该得到如同一个“位格”应有的待遇,换言之,人之为人,从受精卵就开始了。以此而论,胚胎、胎儿都应该享有人类生命的尊严,而不可以作为“生物材料”使用,随意进行试验、销毁,或供作移植的器官或组织,以治疗某种疾病。教会对胚胎、胎儿的作为人之本体及其道德地位的肯定,很难为现代医学技术所认可,且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国家中,反对的意见也很大。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人们普遍接受“人始于生”(《荀子》、《韩非子》)的观念,认为只有出生后的人才可称为真正的人,比较难认同作为受精卵和胎儿形态的人。当这种传统观念与现代各种医学的误导以及经济利益纠结在一起时,就会赋予上述行为以更大的道德上、法律上的正当性。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9年发布《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该通谕属于教会社会训导,旨在依据“在真理中的爱德”这个原则促进“全人发展”。在通谕中,教宗认为《人类生命》以及《生命的福音》通谕所论述的并不是一种纯粹个人的伦理,它更指出了生命伦理与社会伦理间的密切关系,开创了一项训导主题的先河。在通谕中,教宗也提到科技本身“利害相参”,肯定妥当运用新发明可以促进世界进步,但却不能将科技进步绝对化,将科技进步和它的伦理价值及人类的责任分割开来。
在若望保禄二世时代,对天主教伦理神学构成重大威胁的另一项医学技术就是安乐死和生命维持技术。教宗在《生命的福音》中第15,64-67条,对此作出了回应,明确了教会的基本立场。病痛、死亡是人类的恶,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对之都进行过各种的神学论证、道德训诫和超脱之路,但在惨痛的事实面前这一切似乎都显得很无助。生命维持技术的出现好像为减轻人的病痛,能够更有“尊严”地无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大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教宗在《生命的福音》中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类“自比创造者”的态度和举动,人们认为可以自己操纵个人的生死大权。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击败死亡,反倒是为死亡所征服、击碎,没有发现生命的真正意义与价值。这种技术反映的深刻的社会的“罪的结构”,即认为那些不再创造社会财富的残障者、老弱病残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是可以采取像盖世太保在奥斯维辛那样的处理方式的。而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有权利去超越天主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对此,教宗指出,“当人类篡夺这权力,受到愚蠢自私思想的束缚时,就不免会将这权力用于不义和死亡。于是弱者的生命就掌握在强者手中;社会的正义感丧失,各种真正人际关系的基础,即彼此的信赖,也从根本受到了损害。”
综合来看,教宗在阐述自己关于身体和生命的意见时,使用了两种语言。一种是神学的或宗教式的语言,另一种则是哲学的语言。天主教会要想让世界听懂自己的语言,需要先熟悉和熟练运用世界的语言,其中最重要的语言就是哲学语言。熟练运用现代哲学语言,以“理”服人,避免自说自话,互相指责,促进教会与包括医学界在内的整个科学世界实现有效的沟通。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通过运用哲学语言表达天主教生命伦理价值观,既坚持了教会传统立场,又能够进入到公共话语系统中,展开与现代科学伦理的对谈。他的这种对谈的策略与艺术,表明现代天主教在构建其生命伦理学时寻到了适切的工具,是其走向成熟的标志。
《愿祢受赞颂》是现教宗方济各针对当代世界环境和生态问题于2015年发布的一道通谕,但其中也包括对现代新的生物科技的教会训导。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教宗方济各大致采取与教宗保禄二世类似的“持平”或折中立场。一方面强调科学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益处,“人负责任地参与天主创造工程,乃是崇高的召唤”。另一方面则提出要对其目标、效果、整体情况和伦理限制做出风险评估,因为任何对自然与生命合理的干预,只应为了“有利于受造物依据天主的计划,发展各自本性”。关于基因改造(GM),教宗指出,因为基因改造种类繁多,所以难以下一个总体判断,故需要做个别的考虑,具体的分析。教宗进一步提到,即使尚未有确实证明基因改造谷物对人类有害,但在某些地区,基因改造谷物在带来经济增长同时,会引发新的贫困以及更为棘手的伦理问题。
自然语言中的单独词项都不是真值表达式,那么弗雷格所说的真值表达式到底是什么呢?真值表达式是弗雷格对自然语句进行改造后得到的表达式,改造的方法是剥夺自然语句的判断力,使之变成一个纯粹只有指称功能的表达式。弗雷格规定,如果某个自然语句是真(假)的,那么与之相对应的真值表达式就指称真(假)。例如,在自然语言中,“2+2=4”是一个具有判断力的语句,但在弗雷格那里,“2+2=4”被剥夺判断力而退化为一个真值表达式,因为作为自然语句的“2+2=4”是真的,所以弗雷格通过去判断力得到的真值表达式“2+2=4”指称真。
社会公平感知不仅包含整体社会公平感知,也包含个体层面的公平感知。个人公平感知中收入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用个人收入公平感知可以较为准确、简洁且全面地衡量个体层面公平感知。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本研究所选各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
三、深入发展:《在真理中实践爱德》与《愿祢受赞颂》通谕
生殖技术既包括生育的人工调节技术,另外还包括辅助生殖技术,主要有人工受精、体外受精、代孕母的出现。辅助生殖技术一方面对许多不孕者而言,可能是一种福音,但另一方面,它也引发深刻的生殖伦理问题。借助这项技术,父母可以拥有不必是完整拥有双方遗传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后代。如果说人工抗孕是将生育从两性关系中抽离出来的话,那么,辅助生殖技术则是将两性结合从两性关系中分割开来。无论哪种技术,实际上都是将人类两性关系中的结合与生育进行了切割。对此,教宗在《生命的福音》第23条指出,“人类的‘性’原有的含意也因此遭到扭曲和篡改,夫妻行为中固有的‘性’的两种意义:结合和生育,也被人为的方式分开,如此,人们背叛了结合的真义,而其繁殖性也由夫妇任意决定”。
在此,教宗并非是要否认人求生的意志,漠视人对高质量生命存在的追求,他实以超性的眼光来看待包括安乐死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现代医学技术。在他看来,现代医学技术并未把人的身体视为真正的生命体,仅仅把身体狭义地理解为肉体,将身体贬低为物质,只不过是一堆器官、功能能量的组合。但实际上,身体应被看做一个具有位格的实体,一个与他人、与天主及与这世界关系的标记和场所。由前者出发,产生的是教宗在《生命的福音》中所讲的现代的“死亡的文化”,而由后者出发,则是“生命的文化”。
《在真理中实践爱德》与《愿祢受赞颂》两道通谕对于天主教生命伦理理解的深化在于,由对生命伦理进入到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伦理讨论,注意从社会结构层面去分析生命伦理危机的根源,同时以天主教生命伦理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进路。诚如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中所言,尊重生命“无论如何不能与民族发展相关的问题分开”,“向生命开放是真正发展的所在”。养成了对生命开放的态度,甚至可以有助于消除全球性的不公正现象。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通谕中也指出,现代生态危机以及生物科学技术的不当运用皆有其人性根源。基于“万物相联”的整体生态观,他认为保护胚胎,尊重人类生命有助于去关心比人类更为脆弱的其他存在物。这样,他就将天主教生命伦理由人及物,扩展至生态伦理领域,发展出一种“整合的崭新论点”。
集中器作为无线通信的局端设备与无线采集器或者无线通信电表组成本地无线通信网络,形成以空间为传输介质的数据传输通道。无线集中器负责主动与每个无线采集器(无线通信电表)进行数据通信(采集),并通过远程通信网络将数据回传给主站系统。无线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结构如图所示。
四、结语
综上,面对势不可挡的现代医学技术对生命伦理的冲击,天主教会始终持相对保守的立场。这容易给人以落后于时代的印象,如同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从而成为新技术推行者和各种自由派神学家攻击的目标。天主教会所表达的道德良知,很容易被大众的喧哗所淹没。教宗本笃十六世曾在其著作《基督教导论》开篇讲了一个“小丑”的故事,来说明基督信仰在今天社会中的地位。或许,这个例子亦可以用来说明天主教的生命伦理在现代医学和生命技术中的地位:“小丑”在到处呼唤去“救火”,但人们却置若罔闻,嬉笑小丑的的作为,小丑伤心地“哭了”。最后,大火吞并了整个乡村,乡村被夷为平地……这虽则只是一个比喻,但对于人们综合反思现代科技发展之利弊、边界,则不失为一味清醒剂。
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面对现代医学与生命科学的巨大挑战,罗马天主教会并非持极端消极抵制态度,而是努力保持其“先知性”与对话沟通之间的平衡性。事实上,天主教支持并参与现代科学的合理性运用,教廷设有宗座生命科学院,重视科技研究,如“分子生物学,以及与其它学科的配合,如基因学等,应用在农业和工业技术上”所作的贡献,只是要反对“任意的基因操纵”。现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中指出,“不同领域的科学之间同样需要交谈,因为每一种科学都可能趋于局限于自己的语言之内,而科学的专门化导致某种程度的孤立,并绝对化自己范畴内的知识”,故需要有宗教与科学之间开放和彼此尊重的交谈。他进一步指出,伦理原则即使是以宗教语言来表述,这也无损其在公开讨论中的价值。基于此,积极开展宗教与现代生命科学之间对谈必要且可能,通过寻求宗教伦理与科学伦理最大公约数,就可以最终使现代科学趋利避害,造福人类。
最后,天主教生命伦理观也需要进入到不同的文化传统中,积极展开与不同文化传统之生命价值观、伦理观对谈。中国文化对生命有其区别于西方的独特认知与表达,在诸如“人始于生”、“人定胜天”等生死观、天人观上与天主教生命伦理有所抵牾。同时,国情有殊,天主教生命伦理观亦应对各国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进行充分考量。鉴此,天主教生命伦理欲在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处境下真正发挥作用,自然需要倾听、分辨和自我调适,走本地化和中国化的路子。
标签:天主教论文; 生命论文; 教宗论文; 伦理论文; 神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基督教论文; 对基督教的分析与研究论文; 《中国天主教》2019年第1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