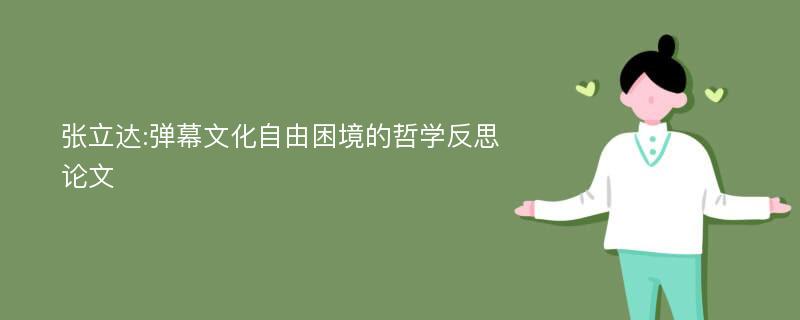
[摘 要]弹幕文化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是它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对自由的渴求;但它在进一步丰富人的生活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弹幕所具有的信息碎片化特点,使得人在以弹幕视频为对象的活动中迷失自身,无法得到客观的自我意义的确证;人们纷纷进入虚拟世界中反抗来自现实生活的规训,沉溺于主观任意自由的个人无法摆脱自身的“再沉沦”。克服这一困境,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反思与批判人本身的行为活动,以此来获得现实人的生存意义。
[关键词]弹幕文化;自由;困境;反思;生存意义
1993年,弹幕最初出现在日本的游戏视频中,后经日本公司改良运用于NICONICO动画,从此开始流行。近年来,弹幕在网络生活中的火热流行,已然使它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对此,学界已经开始了研究,但是研究角度主要集中于社会学、文化学方面。在笔者看来,若要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现象,我们的反思还应该深入到文化哲学层面。
一、弹幕狂欢背后是自由的扩大
弹幕在中国几年时间就拥有了庞大的受众群体,并掀起席卷全网的弹幕狂潮。面对这一文化现象,我们不禁会思考:人们迷上弹幕和弹幕视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现实中沉默寡言的人,在弹幕视频这一场所中,却变得积极活跃?通过具体考察弹幕活动的切身感受和弹幕内容,可对上述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弹幕视频中受众能够相对不受约束地从事网络活动,运用富有个性的语言评论吐槽内容,宣泄情感;对视频内容进行意义再创造,新的内容解读不受阻碍地传播与扩大,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人在发送弹幕的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弹幕活动给人带来的自由体验,不仅激发了人潜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但值得思考的是,弹幕活动带给人的自由体验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个人来说是否自由程度越大越有价值?对以上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从探讨人的本质出发,对弹幕文化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
自由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53在这里,马克思赋予类本质三个规定性: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正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53,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指出,人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是自由的是因为人有意识。人将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意识的内容和对象,就表明人不仅拥有对象意识,最重要的是还具有自我意识。“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归根结底是人对自己的生命活动具有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是自我二重化,即主体我(I)—客体我(ME)。”[2]52客体我为主体我进行意识区分提供了物质载体,主体我又为自我被对象化的过程提供认识基础,因此这样的关系形式确保了人能够超越自然给定性(客体我向外延伸),进而在实践活动中与外部对象建立多样化的关系。我和外部对象的关系,则使人的自由和创造有实在的内容支撑。“因此对象化活动的具体结构就可以展开为‘主体我—客体我—外部对象’,在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中将对象人化、我化就是对我的主体性、自由的确证。”[3]59-60这也就是马克思说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53。
就弹幕而言,这一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线上自由”,就是人打破强制性的对象形式,获得超越现实生活中的必然性、必要性的新自由。因弹幕的产生,受众与视频的对象性关系由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能动的关系,观众不仅能够在视频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也能够对内容本身间接地产生影响。然而,在弹幕活动中所进行的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又是有条件的,这一活动过程只能够在特定网络环境中进行,所以弹幕活动又可被称为“虚拟实践”或“虚拟活动”。“虚拟实践是人们以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为媒介,在虚拟空间有目的地探索与改造虚拟客体的一切客观活动。”[4]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和发展是虚拟实践存在的基础,虚拟实践的产生打破了人类只存在于物质生产活动中并且只能以现实存在为对象的传统哲学认识。“使人的实践对象第一次突破了纯粹形式的外部物质世界的界限,在虚拟空间中,实践的桥梁和中介则变为数字化符号,计算机系统将人类现实的社会活动的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就将主体置于一个新的关系实在的虚拟实境中。”[5]90在这一虚拟实境中,时间虚拟化为脱离具体空间参照的全球性统一的时间,空间虚拟化为不限制在地理环境中的抽象存在。实践中介将人类活动信息“数字化”,使得现实存在的局限性被打破,实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人以数字化符号为中介手段,使自身存在于一个新的对象性关系实在的虚拟情景中,进而打破传统现实中人与对象活动的约束与规范,扩大了人与对象交流、互动的自由空间。这本质上是以信息流扬弃了物质实体世界的僵硬性,使人掌握对象的方式超越了对象本身的限制,进而使得人获得自由的空间扩大了。
在弹幕视频这一虚拟空间中,受众打破时空限制所构造出的虚拟共同在场,是“新”自由超越现实生活必然性的客观条件。虚拟构造的共同在场,即群体存在于同一个虚拟空间中,以语言符号作为沟通工具,这是弹幕活动的主要交往模式。这种虚拟的共同在场感,因其特定的环境与群体,赋予了参与者更大的意义感和自由感。群体行为可以为个体行为实现更大的意义确证,乃至找到情感归属。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对群体心理作解释时就清楚地说明:“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6]16-19。可以说,自觉融入群体中的个人已经放弃了自身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以此取得自身和群体在感情和思想上的一致性,而在这无意识的行为过程中,个体获得了更大的满足感和情感寄托。但是,在弹幕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群体行为又不同于传统的群体行为,同一视频中密集的弹幕激发了个人自由表达的欲望,这种被动驱使下的弹幕语言缺乏缜密思考,在这种非理性的状态下受众体验到了自身融入集体和集体意义的分享;另一方面,弹幕发言群体处于较为抽象的层次,不仅表现在这一群体中的个体无法面对面地活动,而且仅在针对同一对象的评论中具有同一性,因此使得评论具体内容的弹幕发言极具差异性和个体性。可以说,这种虚拟在场以自身特殊方式将集体性和个体自由这看似对立的两方面统一起来。
内爆一个重要的具体表现就是信息的碎片化,因为只有碎片化才能超越客观事物的现实规定性,以超常规的方式快速增殖,实现对真实世界的遮蔽。弹幕所具有的碎片化特性成为了个体在超真实状态下非理性狂欢和宣泄的基本方式。弹幕活动将受众与视频的对象性关系由被动接受转变为积极建构,弹幕语言由于自身的即时性消解了视频内容的整体意义,不可避免地使弹幕内容相对于视频内容本身具有了碎片化的特点。碎片化意味着对整体模式的把握是从许多随机现象中获得的,把握这种随机性又是通过审视既有模式的局限性而得以实现;它所具有的反语境特点,使得信息脱离所产生的具体情境,打破原有解释,而被赋予新的意义,所以碎片化又具有解构与建构双重属性。个人难以用具体方式把握住整体现实,而在这个符号取代人的超真实世界中,人克服了自身所具有的原始缺陷,通过解构与建构的双向活动,构造出自身在场的虚拟空间。这个由碎片裁剪拼接而成的世界,人更容易把握,并在解构与建构的自由活动中获得更大的自我认同感。但是过分沉溺于这样的碎片世界也就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把握,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容易陷入盲目,个人也就更容易在碎片化所带来的非理性狂欢中迷失自身。
BP神经网络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理论上已证明含有一个隐含层的BP神经网络,通过设置足够多的隐含层节点,就能对有界区域上的任意连续函数以任意精度逼近,因此,合理选取隐含层节点是至关重要的[7]。为了避免神经网络的陷入局部最小值,将输入、输出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以缩小结果的搜索范围,提高计算效率。另外,训练函数也是影响神经网络可靠性的重要因素,合理有效的训练函数既可以提高计算效率,还可降低陷入局部极小值的可能性。
在弹幕视频中,发送弹幕这一活动所具有的新的功能特点,将特定客体主体化、共同在场感虚拟化,让集体狂欢与个人自由共存,进一步使得弹幕语言具有形式多样、结构非线性、内容口语化的特点。不同文化层次与多元的文化体系相互融合,受众在自我隐身的环境下,能充分凸显自身特色,互相交流,并且不受制于特定话语情境,对视频内容和人物环境作更具特色的意义解读,使得任何一个弹幕视频都具有强烈个性。如今弹幕文化的大众化使得它在人们的观影生活中越来越普及,在弹幕视频中,受众就像蒙面者参与集体性狂欢,表达的自由可以得到集体性的确证,而“自我”却不会被他者客体化,削减了他者的干扰与侵犯,充分满足了现代人的情感宣泄与个性表达。
基于鲍德里亚对当代现实的解读,我们可以把弹幕空间也看作一个由符号系统建构起来的超真实世界。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鲍德里亚对“超真实”作了明确的解释:“拟真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开始……真实化为乌有……变成一种为真实而真实……它不再是再现的对象……即超真实。”[7]105原本作为真实事物之“代理者”的符号体系,反而因此成为了“代替者”,掩盖并僭越了真实世界,自我建构为一个仿佛更真实、更不可摆脱的世界了。在弹幕空间中主体通过弹幕活动得到自我确证。虚拟空间中的一堆话语符号成为了比现实主体更加真实的存在。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人类长期建构的生存方式和周遭世界被符号化,同时,这些符号话语又将现实的逻辑和原则遮蔽,人类也潜移默化地被它们的运作方式所塑造,进入到了“超真实”的生存状态。在弹幕空间中,从人的实际存在形式来看,人的真实存在被吸收进了符号系统中,导致人的存在脱离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使符号化的个体在弹幕空间中获得了绝对自由。由于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缺乏理性思考的条件,语言符号又在超真实的状态下按自身的逻辑增殖扩张,自身的内在意义和自我指涉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语言符号的存在就离开了真实生活,仅同纯粹的信息生活相连接。当语言符号从主体的身份“代理者”转变为存在“代替者”时,它就脱离了人的主体性而从属于符号体系,语言表达也就成了自身自足的目的。现实世界太过复杂,无法把握,作为代替者的语言符号在使用过程中克服了人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弹幕视频作为真实世界的拟像似乎也就成为了个人能够真正把握的现实本身。
上述状态也可描述为信息符号的“内爆”现象,即信息的自我复制、自我增殖。符号本身具有自足性,没有现实原型和标准,在自己的符号系统内增殖繁衍,当符号的数量和意义不断膨胀,便出现了“内爆”现象。在内爆过程中生成的符号并没有具体意义,而自身的生成价值也只有在与其他符号的差别中才得以体现。对于弹幕本身而言,它具有非常明显的自生性。弹幕空间对人表达的欲望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它给人充分自由的表达空间,却不给人思考的时间,这就使得“表达”本身成了目的,而表达的“内容”反倒不那么重要了。弹幕语言符号在自己的符号系统中没有止境的自我繁殖与传播,这个过程完全与现实世界无关,因为语言符号内爆后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已与现实无关,其现实的指向性被消解。而弹幕语言的内爆过程也模糊了真实与拟像之间的明确界限,信息技术的拟真性取代了人的真实性,主体与世界共同消融于符号游戏中。这一消融过程将主体从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主体利用数字媒介获取信息时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使主体的意志选择处于一种非确定性的状态。这种内爆出来的拟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取消了人理性存在的可能性,消解了人与对象世界的辩证张力,进而让个体丧失了反思的空间。
二、弹幕空间:一种超真实和非对象化的世界
弹幕文化根植于社会现代化这个更大的背景下,因此对这一文化现象作进一步的认识与批判,就必须对现代社会的本质进行整体反思。
3.由主题开始,用粗线条表示主分支,将每一个主要的观点或内容与主题相连,并在线条上写下可表示该观点或内容的一个关键词。
二是建立系统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事业单位在选取指标体系时,应该根据自己的行业和职能特点,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技术创新等方面,使绩效评价更好地反映单位责任和实际情况。比如,科研事业单位可以将科技成果转化的质量和效益、科技成果申报产生的知识产权数量、科研成果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等纳入考核指标。
在虚拟空间中,活动主体的隐匿性特征是集体性和个体自由统一起来的重要因素。现实的“自身”与“他者”被隐匿在网络ID之下,而所呈现出来的交往互动也就缺乏现实性。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实际交往活动中,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确证,进而约束与规范自身行为。正如萨特的他者理论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自我意识”的产生是因为“他人”的存在,我感觉到了“他人”,然后才反思到“我自己”,通过他者来反观自身行为和语言并加以约束与规范,实际上是对自身自由的一种否定行为。在与现实主体共同在场不同的虚拟主体共同在场中,主体所具有自我隐身的特性则使彼此的对象化活动变成了一堆话语,虚拟实践的现实主体隐藏在这一堆话语之下无法得到他者的关注,不会因被他者对象化活动而感到不自在,也就不会反观他者行为来自我约束。因此,个人在弹幕空间中就会表现出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的行为和语言自由。
汤翠有时候也很自责,何必去吃一个失踪十几年的人的醋呢?更何况,这个人还是她的亲姐姐。女儿长到六岁,越来越像她大姨汤莲,那眉眼,走路的姿势,甚至说话时嘴角稍稍向上斜的样子,几乎就是汤莲的翻版。开始只是汤翠的父母偷偷地说,后来,连那些老邻居也这样说。汤翠相信,侯大同肯定也注意到了,侯大同却佯装不知。要不然,侯大同怎么这么喜欢这个女儿?给她洗澡,搂着她睡觉……女儿都六岁了啊,是大人了。汤翠当然不敢说出来,一说就等于挑明了。侯大同即使心里有汤莲,那也是过去的事了,何必自讨苦吃呢?汤翠却从此心存芥蒂,跟女儿说话就没有个好脸。
三、从弹幕文化透视现代人的生存矛盾
弹幕视频的兴起使大众获得了超越现实生活范围的自由体验。在虚拟空间中,受众参与集体狂欢,获得了更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然而,当弹幕视频因污秽言语而充满消极与负面情绪时,又打破了受众从中获得更大幸福感的美好愿望。在这种集体狂欢的自由中,受众宣泄自身情感,同时也受到许多负面影响和精神压抑。在面对狂欢自由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就需要追问:这种自由是否就是“过有意义的生活”所需要的自由?如果这种自由本身存在缺陷的话,那有助于人实质性的全面发展的自由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虚拟空间中的弹幕活动很大程度上可被定义为非对象化的活动。就马克思解释的异化是人丧失对象而言,异化也是一种非对象化,但是马克思又指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104,因为非对象性的东西无法确定任何规定性,也就只能是虚无。所以非对象化只能在相对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只能是某种特定的对象关系的丧失。弹幕空间归根结底仍是人创造的对象世界,但是这个对象世界太过灵活地进行自我增殖和游戏,这种状态直接与人活动的表面自由一体化,因此在直接的意义体验中很大程度上就成了非对象化的,从而人在弹幕空间中不再能够自我反思,也就无法实现对自身内在规定性的认识和超越。所以,这里所说的非对象化不是对对象化的完全否定,而是对象太过灵活,缺乏与实际生活的客观化、系统化联系,因此才显得非对象化了。人与弹幕关系的这种非对象化形式将对象化从整个生存层面、理性层面降格到日常游戏层面、感性层面,虽然表面上弹幕空间扩大了受众的自由,但是这种被扩大的自由却无法转化到现实的实际活动中去,如果过于沉迷在虚幻的自由中,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证也就失去了现实的根据。当然,非对象化也并非毫无意义,只是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审美活动中,而在必须进行理性思考的实践领域,非对象化也就意味着主体性的丧失。
综上所述,高校的人才培养要站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上,要牢记我国的教育方针和指导思想,要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要思考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这样,应用型的本科院校才能找准人才培养的方向,才能树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的目标,为中国梦贡献一份高校的强有力的力量!
鲍德里亚的理论本质上是对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和批判。“从社会结构转型角度阐释现代性本质,就是:从人的依赖(或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市场或资本力量相对独立出来;使个人相对独立成为主体。”[8]因此,可以将现代性看作“是一种注重能力、理性、自由的主体精神、批判精神”[8]。然而,人所依赖的工具体系的膨胀又导致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中充满着“物主导”与“人主导”的矛盾斗争,进而使得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消极效应。具体表现在:人类使用工具体系增强了自身实践能力,同时,却越发依赖整个工具系统对个人主体性的宰制,而又无法自主驾驭这个工具体系及其所带来的后果;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扩大,产生出区别于现实人类社会的虚拟空间,在这一场所中,人类的感性存在被符号体系所代替,克服了人类身体原始缺陷的符号游戏表面上导致了人自由空间的膨胀。但是,人为建构的符号世界又不像客观世界那样容易确定因果关系,有明确的行为规范,所以在感性自由膨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现实意义的迷失。
在现实生活中,对象化活动作为人根本的存在方式使得人自身陷入诸多生存矛盾中,例如: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个人与自然的矛盾、精神与肉体的矛盾等。个体在这些生存矛盾中经历着自身主体性被否定和自由超越性无法实现的痛苦,也迫切地想将自身从种种矛盾中解放出来。弹幕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虚拟空间,因其独特的功能为大众提供了宣泄情感的自由平台,个人的主体性在这里得到了张扬。弹幕将人的原始身体符号化,成为人逃离现实矛盾的具体方式,这种逃避行为可被视为人对现实生活中所受压抑和规训的反抗,但是由于这种活动空间和活动方式的开辟与发展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发性,所以就可能导致受众不加反思地沉溺于其中,进而陷入异化状态。这种状态可被看作人在虚拟世界中的“沉沦”。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指出“沉沦”属于此在的非本真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常人自以为培育而且过着完满真实的生活;这种自以为是把一种安定带入此在;……一切都在最好的安排中……沉沦在世对它自己起到引诱作用同时也起到安定作用”,“起引诱作用的安定加深了沉沦”[9]206。就弹幕本身而言,它显然直接张扬了个体自由,但正因此个体就容易满足于有限的努力所带来片面的成果,于是就不自觉地放弃了对自身现实的生存矛盾的反思和批判,必然导致“二次沉沦”,即“再沉沦化”。在对沉沦的反抗中人获得了片面的满足,才能够更坚定地二次沉沦。社会越现代,再沉沦就会更加成为沉沦实现自身的具体方式。[10]这样的现实悖论愈发显示出人的生存矛盾的深刻性与复杂性。
鲍德里亚的相关理论虽然深刻,却脱离人的实践整体来讲符号的自我体系化、游戏化,取消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过分夸大媒体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导致他只能描述异化的单行道,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中。本文则探讨了非对象化和对象化的辩证关系,把非对象化看作对象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就从理论根基上承认了人的主体性,揭示了人走出符号迷宫、扬弃非对象化、回归真实主体的可能性。当然,人的对象化存在方式只是给出了扬弃异化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具体实现只能建立在真正掌握、改造对象的实践能力发展基础上。
具体到发弹幕这种高度个人化且对后果不用负实际责任的行为,具体规章制度的效果不过是剔除极端言论,难以发挥更具体、更广泛的作用。因此,在面对实际矛盾处境时更需要每一个人反思自我的精神,反思自己在该活动中的得与失,而不至于在工具系统中迷失自我。不可否认,弹幕文化的兴起在社会生活中为大众营造了一个新的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自由在实际意义上实现了扩大,但是弹幕需要改进的地方正是要让这种主观任意的自由成为负责任的自由。这有赖于个人成熟主体能力的培养,这一过程只能在现实社会实践中完成。其中,民主法治建设对培养公民成熟的理性思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公民自觉拥有成熟的主体性和理性思维提供制度保障。人类拥有更加成熟的线上自由,即在自由的范围内更加理性地从事实践活动,未来将很可能不再采取弹幕这种不给人充分思考时间的活动方式。弹幕文化作为人类自由空间拓展的一个辩证的否定性环节,将呈现自身所具有的阶段性、历史性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 萧诗美.哲学如何把握人的类特性[J].江汉论坛,2007(4).
[3] 张立达.对象化和人的生存矛盾[M].上海:三联书店,2013.
[4] 杨福斌.信息化认识系统导论[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5] 张明仓.走向虚拟实践:人类存在方式的重要变革[J].东岳论丛, 2003(1).
[6]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8] 韩庆祥.现代性的本质、矛盾及其时空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6(2).
[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0] 张立达.电视相亲节目流行的哲学解释与反思[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4).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Boundary of Barrage Culture
ZHANGLi-Da,TANGShi-Ru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Barrage culture has been flourishing for it, to a greater extent, satisfies people’s desire for freedom. It, while further enriching people’s life experience, has brought many negative influences as the information fragments make people lose themselves in the activities with the barrage video as the subjects, which results in their denying objective self-meaning; people in the virtual world resist the discipline from real life, and indulge in subjective and arbitrary freedom which make their own “re-emergence” a haunt. One, if he/she wants to walk out of this dilemma, must reflect on and criticize their behavioral activities so as to obtain the meaning of the survival of the real person.
Keywords: barrage culture; boundary; reflection; meaning of existence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9)05-0053-06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9.05.006
[收稿日期]2019-03-18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哲学研究”(18ZXZ002)
[作者简介]张立达(1978-),男,江西万安人,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李长成]
标签:弹幕论文; 对象论文; 自由论文; 符号论文; 现实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世界哲学论文; 现代哲学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哲学研究”(18ZXZ002)论文;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