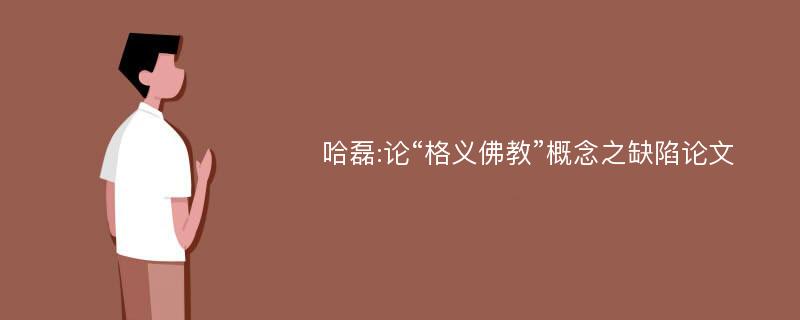
[摘 要]格义作为中国佛教早期的一种解经方式,采用儒道概念来解释佛教,对于佛教在中国本土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但在流传中也出现了违背佛教根本思想的倾向。随着佛教经论的翻译逐渐完备和佛教本有的理解路径的通畅,格义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在陈寅恪、汤用彤先生对格义重新阐发的基础上,从用语、习俗、思维方式等角度来探讨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差异,得出了中国两汉魏晋以来的佛教是格义的佛教,格义佛教是中国化佛教的本质特征等诸多结论。但这些结论显然不能成立,根据主要是:早期汉译佛经虽然使用了儒道术语,但这些术语的使用受到了佛教思想体系和解经原则的严格制约;汉魏两晋以来流行的毗昙学和般若学奠定了中国佛教的思想基础,并对中国佛教思想具有修正和净化的作用;中国佛教对内、对外采用不同的话语系统,日本等国学者偏据对外性的话语系统来观察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悖离史实的。
[关键词]格义;格义佛教;毗昙学;佛教概念系统;双重话语系统
格义作为中国佛教早期的一种讲经、解经的方式,通过将佛教概念与本土的儒家、道家乃至玄学的术语相比配、对照的方式,来消解听众对佛教观念的陌生感,拉近印度文化与本土信众的心理距离,以促成对佛教重要概念的初步理解和接受,对于佛教在中国本土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正面影响。但随着人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日渐深入,佛教与本土儒道等思想的固有差异日渐清晰地呈现出来,格义这种解经方法的缺陷也就日益触目。经过道安法师等一批佛教高僧的批评和反对,加上佛教经论大部分渐次译出,鸠摩罗什等人新译诸经经义大明,格义作为一种解经方法,遂渐归于消歇。
格义重新受到关注,当归因于陈寅恪及汤用彤二位先生。陈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1]185和《逍遥遊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2]96中,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3]166~168和《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4]282~283中,都从中印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格义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格义是“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承认格义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以梵、巴、藏与汉译佛经文本的比较研究为背景,从用语、习俗、思维方式、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差异等多个层面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由此得出中国两汉魏晋以来的佛教是格义的佛教,格义佛教是中国化佛教的本质特征等诸多结论,并以此质疑中国佛教作为佛教在核心观念、思想体系等方面的如实性与纯净性。加上国内佛学界关于佛教中国化相关论述氛围的助成,格义佛教的观念在国内渐有流行之趋势。考虑到“格义佛教”这一概念本身的缺陷,以及用“格义佛教”指称中国佛教会造成甚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对“格义”和“格义佛教”等相关概念实有加以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格义的兴起与消歇
关于格义的诸多讨论,主要立足于下面这段文字——这也是现存佛典中对“格义”加以明确阐释的主要文献:
(竺)法雅,河间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咸附咨禀。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乃毘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后立寺于高邑,僧众百余,训诱无懈。雅弟子昙习,祖述先师,善于言论,为伪赵太子石宣所敬云。[5]152~153
电动汽车行驶每小时耗电2kWh,充电站充电功率为10kW,效率为1。充电站A、C、D、E的预期电价以及目标函数α/β如表1中所示。分时电价制度按峰时每kWh为2.00元,谷时每度1.00元计算。
这段文字中,没有异议的大概是以下几点:第一,竺法雅是最早将佛经与儒道经典的重要概念加以对照的解经方法称为格义的人。第二,竺法雅在为弟子讲经时,常常是兼讲儒道经典的。第三,竺法雅的格义主要针对儒道等传统学问较好而佛教基础较弱的学生。第四,同时运用格义方法来训练门徒(比丘、优婆塞)的还有毗浮、昙相等人。第五,法汰以及后来反对格义的道安法师最初也是认同格义这种理解佛经的方法的。第六,竺法雅的弟子如昙习等,也用格义的方法来教授弟子。
当然,首章中也出现了诸如“魂灵”、阿罗汉能“飞行、变化”、“住寿命”、“动天地”等近于神仙家的表述,常为格义佛教论者所非议。可是这些表述也完全可以转换为印度佛教习用之术语,如神识、神足通、住寿一劫等等。当使用了“飞行”、“变化”这些术语时,难道真的歪曲了印度佛教的思想吗?
(释僧)先,受戒已后,励行精苦,学通经论。值石氏之乱,隐于飞龙山。游想岩壑,得志禅慧。道安后复从之,相会欣喜,谓昔誓始从。因共披文属思,新悟尤多。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先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5]195
通过老庄理解的佛教,是为格义佛教。[6]46
至于早期译经中常用的术语,如以守一译禅定、本无译真如、无为译涅槃等等,这些深为格义佛教论者指责的术语,是否严重背离了印度佛教的思想而将儒道的思想混入佛教呢?
选取2015年3月至2017年3月间在本院进行调强放疗的胸椎转移患者120例,其中男性患者78例,女性患者42例,平均年龄(53.7±10.1)岁,原发肿瘤中肾上腺癌9例,肺癌51例,甲状腺癌8例,乳腺癌28例,肝癌12例,前列腺癌12例;病灶椎体中合并椎体附件转移有18例,单椎体转移有21例,合并腰椎转移有47例,多发转移有97例,合并颈椎转移有33例,连续节段转移有31例,大体肿瘤靶区(GTV)的平均体积为(521.52±47.01)cm3。
二、“格义佛教”概念所蕴含的对中国佛教的曲解与误读意味
格义之学经陈寅恪先生重新揭示之后,汤用彤、吕澂、任继愈、冯友兰诸先生皆有所述及,但都将格义视为讲经之学问,而没有称为“格义佛教”的。日本学者则一方面以“格义佛教”这个概念来指称格义之学,如田茂雄、常盘大定等,另一方面,又将格义的含意扩充至译经、注疏及佛教流派等层面,并渐次形成了以此为基础来讨论、判定魏晋佛教乃至中国佛教性质的风气:
按照一般的理解,格义开始于东晋时代。可是利用外典用语和观念表现佛教思想的尝试,在东晋以前的汉译经典,已经实行起来了,譬如古译涅槃作“无为”、真如作“本无”,都使用了老庄语言来配对、迻译梵语。……从这点看来,汉译经典业已实行了格义的方法,并沾上了浓厚的老庄色彩。[6]45~46从儒道思想与佛教思想相对照的形式和方法开始,日本学者进一步追寻儒道思想在中国佛教中存在的范围和程度,而作为中国佛教立教根本的汉译佛经,就往往成为了考察的重点。如果仅从译语中的老庄之语和儒家之语的使用来看,不仅东晋之前的译经在广泛使用,甚至整个汉译佛经的全过程都无不在使用。如果我们不对这种使用儒道之词汇、吸纳儒道之思想、适应儒道之态度与坚持佛教之根本精神相区别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会承认和接受日本学者的以下论点:
实施主要通过无人机获取高精度DOM(数字正摄影像图)和DEM(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结合构建精密潮汐模型获取的平均高潮线、低潮线的85高值(85国家高程基准面),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进行海洋岸线类型识别;结合高精度DEM、水下地形数据,通过“等值法”和“二值法”对自然岸线的平均高潮线、低潮线、0m线进行提取。主要技术流程包括:资料收集,DOM、DEM获取,潮汐模型构建,坐标统一,岸线识别,岸线提取。
如上面所述的,格义是“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换言之,即借用老庄等学说来敷衍解释佛经道理。这是格义一词的最基本的意义。可是,这系约狭义说的。若约广义说,则不但解释佛经借用老庄等学说叫做格义,就是翻译佛经时,借用老庄等学说的名词术语,也是属于格义。不但这样,推而广之,佛教人士著书立说:消极的、被动的,以世学拟配佛义,可称之为格义,反之,积极的、主动的,以佛义融合世学,自亦可以算是格义。欲明了初期中国佛教的基本型态的格义佛教,必须从广义去理解,才能正确的把捉到其真相。[7]
怎样将读写训练深入细致开展下去,既有丰富的形式,又有实实在在的语言训练呢?这就需要老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读写训练时给学生一些具体可行的抓手,让学生真正读懂文本的语言精华,并运用到自己的语言训练中去。
僧先是热诚的佛弟子,精通法义,对于佛法也有非常深入的体验,与道安法师在法义上有很多的交流和切磋。但对于道安反对格义的深意,僧先似乎尚缺乏足够的敏感和理解,认为与从分析佛经中所获得的快乐、自在(“分析逍遥”①陈寅恪先生在《逍遥遊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引道安《道行经序》“要斯法也,与进度齐轸,逍遥俱遊”之语,认为道安“既取道行经与逍遥遊并论,明是道安心目中有此格义也。依僧先‘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之语,则知先旧格义中实有以佛说解逍遥遊者矣”。细读道安序,可知此句意为:般若波罗蜜极为重要,与精进波罗蜜并行,(当下及成就时)可得从色、心诸法及邪见、烦恼中而得解脱、自在。此句与序中“八地无染,谓之智也,故曰远离”之语同义,即从修行进程来讲,到第八地时,菩萨之心才得以从一切色、心诸法的执著、分别、追求中得以远离,不再被染污,得到真正的般若之智。第八地也译为不动地,自此以上,称为大乘无学道,无往而不自由,故称为逍遥。此即道安序“逍遥俱遊”之本意,与《逍遥遊》本无任何关联。因此,由“分析逍遥”而引申出的“先旧格义中实有以佛说解逍遥遊者”的结论自然也无法成立。细绎陈先生之失,实由《道行经序》中无处不在的老庄之语,往往误读亦势所难免。只是细读全文,序中实无只字论及《逍遥遊》,亦与老庄之学没有任何关系。从佛学眼光来看,道安序也非常纯粹,只关注《道行经》的主旨与读法,且可以与罗什所译的《大品》相参,甚少误读之处。若说道安序与玄佛合流之论有所相应之处,则仅在其完全以玄学语来讨论纯粹的佛教问题,其表现形式虽然给后来的读书人造成众多理解的困难,却在当时为佛教吸引了广泛的知识精英,这是研究魏晋佛学时所不得不深为留意之处。僧先之语,本来就是表达当下心境的,不宜作过深的阐释。陈先生之文,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6页。另外,陈寅恪先生还把六家七宗之说、合本子注及慧远以庄子之义解释实相的“连类”也作为格义的表现形式。实际上,这种归类还是存在诸多值得斟酌之处的。六家七宗之说,严格来说,是中国佛教般若学派初步建立的标志,尽管各家对般若的理解多少都有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其与作为训诱门徒、普及佛教知识的格义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着眼于对《般若经》的精深研究,以经典的深入阐释为目的,以合于经旨为最高追求。后者则以普及佛教知识,求得对佛教初步的理解和认同为主要目的。合本子注,也是以理解佛经为主要旨趣,参合诸译本以求同,以“子注”方式显示异文,以求得对梵本本义的契合为目的,与儒道之学距离甚远,自然与格义无多少瓜葛。连类出于慧远法师教学的机智,以化精通庄学者,庐山远公之外,他人的使用皆受到道安法师的禁止,其影响也不应作过多的发挥。)相比,格义在理解佛经上有欠妥当的问题,并非意义重大的事情,并且认为批评竺法雅等前辈也是很不应该的。道安法师则认为竺法雅等前辈所用的格义方法——“先旧格义,于理多违”——以儒道思想为途径所理解的佛经之意,与佛经的本义,在很多地方是相矛盾的。这是道安法师质疑格义的关键所在。
儒家和道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其影响通过经典、词汇、思想和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及生活态度,深入地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任何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承认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中国佛教只能建立在儒家或老庄思想的基础上的依据;也不能成为佛教必须被儒家的、老庄的思想所改造,而不能、不应该在依托印度佛教的梵巴文经典及中亚语佛教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取向、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有别于儒家、道家的新的思想流派和宗教形式的依据。退一步来讲,即使中国佛教看起来受到了儒道思想很深的影响,我们也没有理由和依据说儒道思想通过格义全面改造、彻底瓦解了印度传来的佛教,使中国佛教成为儒道思想的附庸。因为这与中国的思想史、生活史是严重悖离的。如果我们不能深入佛教思想内部来理解中国佛教,可能我们关于格义佛教、关于佛教的中国化、中国佛教的本质等等的论断,都属于臆测和妄想,比如下述文字,通过夸大“格义”负面影响的方式,来达到论证中国佛教是“变型”佛教的结论,几乎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
众所周知,中国人在接受和理解印度佛教之际,启动了中国固有的思想作为其媒介,这种做法叫做“格义”,而依“格义”建立的佛教就叫做“格义佛教”。[6]45
小乘三藏中的经、论二藏,是佛教概念最为集中的部分,《阿含经》作为佛陀言教的合集,体现了佛教法数(概念体系)的源头,《阿毗昙》则用种种不同的形式,对这些法数进行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分析和阐发。对佛教来说,无论《阿含经》也好,《阿毗昙》、《般若经》也好,一切思想和智慧的展开,都是建立在“法数”的基础上的。所谓“法数”、“事数”都是指佛教的这个概念体系。佛教传入中国后,无论安世高所传阿毗昙学还是支谦所传般若学,都沿用了印度佛教的概念体系,并通过汉语的对译,最终建立了汉语系的佛教概念体系。此中安世高所译《阿毗昙》,更是成为汉魏两晋中国佛教的显学,“硕儒通人”都把《阿毗昙》的学习,当作通向佛教真理和解脱的桥梁和舟楫,成为大小乘佛教学习的最为重要也最为用功的部分。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毗昙的学习和流传,都比般若更加兴盛:
三、格义佛教不能指代汉魏两晋佛教的理由
上述论点涉及了汉译佛经的翻译问题、中国佛教的思想基础和理解途径问题、文化背景导致的适应方式问题等诸多关乎中国佛教精神内核的问题,这些也是国内学者讨论、分析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非常关切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纳为一个问题,就是佛教如何适应中国文化的问题。与传统认为佛教成功地适应了中国文化的观点不同,格义佛教论者往往认为中国佛教相较于印度佛教或巴利语系、藏语系佛教,是“变形”的,甚至是“畸形”的佛教。尽管纯正与变形、成功与失败,往往是见仁见智的,但中国佛教在适应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对思想根本、价值取向、生活态度等本质特征的坚持与因风俗、文化差异、吸引信众所采用的语言、生活方式、宗教形态的适应性改变,还是有清晰的界限可寻的。即使单从所谓格义佛教的角度来看,这一特征也能够得到明晰的说明。下面分别从佛经的汉译、中国佛教的思想基础和理解途径、中国佛教的自度和化他的双重话语系统等几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在农资主业上,率先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和经营模式变革。持续推广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农资产品和新技术,并率先建成了渝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农资配送中心。规模更大、更现代化,总投资2500万元的新渝东北农资配送中心已在建设之中;在拓展发展上,顺丰农资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积极投身长江航运事业,并与专业船务公司结成合作关系,目前正建造6000吨级新型长江运输船舶两艘,很快总运力将达到5万吨。除此之外,顺丰农资还在农资电商、土地流转、乡村旅游等领域积极谋划探索,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新格局。
(一)汉译佛经的翻译用语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地理的困难,如雪山、大漠、万里风涛之类,暂且不说,语言的沟通首先就成为问题:
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8]723
由于到货验收单、投运单、质保单等物资合同结算单据中的数据均可以通过ERP主数据库进行提取,可以通过系统中结构化的数据自动生成付款单据,并结合移动应用、电子签章、生物识别等技术,实现合同管理过程的单据结构化。
当梵语与汉语相遇时,交流的巨大障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以精密深奥著称的佛教思想时,除了现成可以利用的儒道语汇、思想外,难道还有更好的途径吗?当然,如拉丁语之于基督教,中国僧众也可以学习梵、巴语。可是,历史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对于汉译佛经,学会了梵、巴语的日本学者,往往以挑剔的、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它。但即使以日本学者批评甚多、充满儒道语汇的最早的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为例,我们仍然能看到极为鲜明的佛教特征:
佛言:“辞亲出家为道,名曰沙门,常行二百五十戒,为四真道行,进志清净,成阿罗汉。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住寿命,动天地;次为阿那含,阿那含者,寿终魂灵上十九天,于彼得阿罗汉;次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还,即得阿罗汉;次为须陀洹,须陀洹者,七死七生,便得阿罗汉。爱欲断者,譬如四支断,不复用之。”
佛言:“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持五戒者一人;饭持五戒者万人,不如饭一须陀洹;饭须陀洹百万,不如饭一斯陀含;饭斯陀含千万,不如饭一阿那含;饭阿那含一亿,不如饭一阿罗汉;饭阿罗汉十亿,不如饭辟支佛一人;饭辟支佛百亿,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亲;教亲千亿,不如饭一佛——学愿求佛,欲济众生也。饭善人福最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二亲最神也。”[9]722
首章130字,出家、戒律、小乘佛教核心思想四谛和四沙门果的获得与渐次升进,都得到了精要的阐释,佛教独有的特征已明白无疑地显现了。次章150余字,表达了佛教的贤圣差别的观念,同时也表达了佛教的当报父母之恩的观念,虽合于本土“孝”的观念,但与“天地君亲师”的差异,亦不啻天地之别。
在竺法雅及其弟子推行格义的方法不久,格义方法的正当性即受到质疑。质疑者即是曾与竺法雅一同“披释凑疑,共尽经要”的道安法师:
格义作为佛教讲经方法被认可的主要依据,是基于佛经与儒道经典中的相似性。这种教学方法以“求同”为主要价值取向,“外典佛经递互讲说”的目的即在于具体分析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尽管作为宗师的竺法雅可能对佛教与儒道思想的差别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格义流行后,佛教思想的独特性,佛教超越于儒道经典的独特价值,则往往被后学、听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至少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从佛教的立场来看,这显然背离了格义是为了帮助理解佛法的初衷,而有将佛法混同为世间学问的危险倾向,因而会导致中国佛教的变形和异化。“弘赞理教,宜令允惬”,追求讲法的内容与佛经的一致性(允)以及传法方式的适当性(惬),成为反对格义最重要的动机。由于道安法师对佛教义理有深入钻研和精深理解,在苻秦、两晋之际他又在中国佛教界享有崇高地位②《高僧传》道安法师本传中有“其多闻博识如此,(苻)坚勅学士内外有疑皆师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之语。,因此,在遭到道安法师等人的强力反对之后,加上鸠摩罗什新译诸经妙合梵本经义畅达,依佛教思想的本有理路来理解佛经的道路从此通畅,格义也就逐渐归于消歇了。
守一,确属道家、道教所习用的术语,佛教借来指代禅定,更准确地说是指“心一境性”这一心所法,即心念持续地专注于同一禅修对象的状态。尽管守一的用语相同,但佛教的守一不同于道教的守一,佛教的安那般那、数息观不同于道教的调息、胎息,也是不言而喻的。
无为,是《道德经》中的习用语,佛教用来对译。a表示否定,相当于无、不,sam·skr·ta通常译作“有为”。是词根,表示作、为之意是过去完成分词,表示动作已完成。sam表共同、同时之意,引申为因缘、共生之意。无为对译,单从字面来讲,无为正好对应“非造作的”、“非所生的”之类的含义。当然,还有无生无灭、无因无果之引申义,而无为若视为道之属性的话,应当也包含有无生灭、无生因之义。至于小乘所讲三种无为法中的择灭无为即涅槃,如转换为《阿含经》的术语,即为“诸漏已尽,所作已作,不受后有”。其中“诸漏已尽,所作已作”即与“已无所作”、达于“无为”之义极为相近,“无为而无不为”则与“贪欲永尽、瞋恚、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而达于身心清净,离于染污的精神超越、自由自在的状态相似。由于无为与诸多的相近之义,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等诸多大师皆习用不移,可见其译义对于佛教信众来说,并不会造成重大的误会。当然,无为作为道之属性所具有的实体性、第一因性、能生性等与的差异,佛教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此处不作展开①佛教与道家的异同,道安、智者、吉藏、玄奘、宗密、宗杲、智旭等诸多佛教宗师皆有清晰、深入的分析或表述,并通过他们的著作或言行而内化为多数佛教信众的正见。此见与作为包容性的、适应性的、自我保护性的措施所倡导的“儒佛一致”、“三教合一”的观念并行,但并不意味着佛教丧失了自己思想的独立性和纯正性。佛道差异,参见吉藏《三论玄义》卷一。。
本无,是玄学语,有时对译真如,有时对译性空。当对译性空时,“本”指事物的基础或主体,略近于印度佛学的自体、主体、本性,“无”则对译空。从语义上来说,本无可译为主体是不存在的,性空是指事物的不变自性是不存在的。二者在语义上大体对等。当然深究的话,本与末相对,不完全等同于性空意指诸法依因缘而存有、非真实的存在等等含义,难免会有一点误解。但即使完全依梵文译为性空,就不会产生误解吗?宋明理学家理解空,多指什么都没有,即是例证。
可见是否会产生误解,不仅取决于翻译时的术语,很多时候也与读者对整个思想体系的认识、理解以及读者的立场、心态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采用儒道术语并不是中国佛教变形、畸形的充分条件。因为儒道术语的使用是受整个汉译佛教概念体系制约的,对这些术语的解释,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没有边界的。更何况这些术语在汉译佛经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并且大部分术语并不占有核心地位。而道安法师的“五失本三不易”①参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八。之论,则几乎成为历代译经者的共识,其中所体现的苦心与远识,实有待于格义佛教论者深思。
(二)毗昙学对中国佛教概念体系的奠基作用
自佛说法之初,佛教的思想就有非常严密的特点,与此相应地,一系列的概念也建立了起来。阿毗达磨(阿毗昙)兴起后,概念的分析更加严密而深入,以核心概念为基础,不仅确定每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同时还对数百种概念两两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一进行了穷尽式的分析和探究,几乎涵盖了世间、出世间的各个方面,由此建立了佛教思想的概念体系。般若学兴起后,一方面以大乘“一切法空”的立场重新观照以有部为代表的法体实有的观念,尽力破除其执于实有所产生的“法执”;另一方面则批判性地继承了以有部为代表的毗昙学概念体系。后起的唯识学也充分吸收了有部概念体系而另立新说。而印度佛教十八部派内部,对法义的研究及宗义的论辩,也都是在这一套概念体系上展开的。正如道安法师在《十法句义经序》中所说:
正侧位X线平片以及薄层CT扫描判断,分别观察椎间隙、椎体前缘、椎体侧方、椎管内的渗漏情况。测量手术椎体前缘和中部的椎体高度及后凸畸形Cobb角度的变化情况。椎体前缘和中部高度的变化用对照的邻近椎体高度的百分比表达,即骨折椎体高度/邻近对照椎体高度的平均值×100%。椎体前缘高度即骨折椎体上终板最前端与下终板最前端的距离,椎体中缘高度即骨折椎体上终板中点与下终板中点的距离,骨折椎体的正常高度由测量最近头侧、尾侧未骨折椎体所得的平均数估计。后凸角是患椎上位椎体的上终板垂线与下位椎体的下终板垂线的交角。
自佛即幽,阿难所传,分为三藏。纂乎前绪,部别诸经,小乘则为《阿含》。四行中,《阿含》者,数之藏府也。《阿毗昙》者,数之苑薮也。其在赤泽,硕儒通人,不学《阿毗昙》者,盖阙如也。夫造舟而济者,其体也安。粹数而立者,其业也美。是故《般若》启卷,必数了诸法,卒数以成经。斯乃众经之喉衿,为道之枢极也。可不务乎?可不务乎?[10]369~370
我们应先知道的是,格义佛教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触以后所生的变型的佛教,但它不但影响了以后的中国佛教,而且影响到中国文化,直接的促使了佛教的中国化。所以历史上的格义佛教时代,是一段很重要的时期,说后世的中国佛教是格义佛教的延长,亦非过言。[7]
苻坚之末,(僧伽跋澄)来入关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广,禅数之学甚盛。既至长安,咸称法匠焉。[10]522
汉魏两晋的禅数之学,实指禅定之学与毗昙学,有部以毗昙学指导一切禅修活动,因此禅数之学实兼摄义学及禅修等佛教义理及宗教实践方面。苻坚之末,即是罗什法师将至中原之前,此时虽为格义流行之时,但中原佛教的学习必定是以毗昙学为主的,对般若的理解可能也是透过毗昙来进行的。
在实际应用中,核方法的实施存在以下问题:只有选取合适的核函数才能提高原始数据的线性可分性。其次,找到合适的核函数将原始数据映射到高维空间时容易陷入“维数灾难”。为解决上面问题,本文将核空间中的内积函数转化为非线性映射核函数。本文采用表达式为K(x,y)=(1+xTy)d的多项式核函数。当多项式空间H的维数nH=nd,如果在H中进行内积运算,当n和d都很大时,空间H的维数会相当大,在H中进行内积运算将会引起“维数灾难”,因此具体实验时参数d取1。具体算法如下:
当然,我们在面对汉译佛经时,也往往会有自己的理解,尤其是当相关的注解和论典缺乏,甚至连经典文本都不完整时,这种主动的、以个人理解和发挥为主的解经方法就成为必要的、现实的途径。就像我们面对各种汽车零件而试图将它们装配成一辆汽车,手中又没有完整的资料和图纸时,想象和尝试就会是最合理的装配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装配必然是随意的和创造性的,因为汽车配件各自不同的功能和规格限定了装配的选择范围和途径。汉译经论的解说也是如此,“共披文属思”、“披释凑疑、共尽经要”,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形。尽管初期汉译的毗昙、般若只有零章断片,但印度毗昙、般若本身的结构在此局部也得以体现,不同的理解者以不同的方式在解说它时,差异和谬误就随之呈现,可能这就是道安发觉格义学过失的原因之一。
随着毗昙和经律的不断传译,对佛经和毗昙的理解不断得到修正,从而保证了中国佛教不断地消解格义可能带来的儒道影响而更趋近于纯净的佛教发展方向。毗昙学的流行则为汉译佛经的理解提供了最初的规范和方法,而格义之学受到毗昙学的指导和约束也是不言而喻的。当佛经文本和理解途径越来越充分、越来越多样时,儒道之学作为辅助理解佛经的途径日渐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
当格义从讲经、解经的方法中消退,以汉译佛经语汇建立的佛教概念体系即告小成,随着大小乘经论的广泛译传,这一思想体系日渐严密,并最终形成了体现中国佛教关怀和风格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不背离印度佛教的本质,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信众对佛教思想的独特理解、阐释以及实践途径,尽管它有别于印度,但它确实与儒道思想的渗透无关。
此次研究中,为患者进行护理,共有30例患者,采取积极的救治和护理后,有24例显效,5例有效,1例无效,临床护理的有效率是96.67%。在住院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肺部感染的病例,患者接受有效的翻身和按摩护理,没有出现压疮并发症病例,全部患者没有死亡病例,均顺利出院。
(三)中国佛教的双重话语系统
当我们较为完整而准确地了解了经藏和论藏中关于世间生活和佛教的出世间的精神解脱的相关部分时,我们往往会清晰地认识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是有非常明显的、根本的差异的,与道家的思想也有着本质性的不同,更不用说与道教神仙思想了。但在汉魏两晋之际,要明了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再加上当时佛教还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需要随时面对来自儒家知识分子缘于文化差异方面的排斥和来自道教的宗教竞争方面的排斥,以及来自政治的、王权的对于精神自由的威权的压制,等等。这几乎是佛教在中国需要始终面对的一种生存局面。
在拉斐尔前派的年轻人(当然也包括罗塞蒂)看来,这一自雷诺兹时代就已确立的延续已近百年的风格路线早已等同于僵化保守、矫揉造作以致毫无生机,为改变这种与时代脱节的“虚伪”艺术,“真先于美”的口号便被提出。
面对这样的严峻局面,佛教入华之初,即充分发扬了“通权而达变”、“方便有多途”的灵活策略,通过强调与黄老之学、道教神仙的相似性而被民众社会所接纳;通过强调周孔与释迦一致而成功地避免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排斥;通过强调近于道家的清净无为之精神追求,而被魏晋崇尚“高蹈嘉遁”文化趣味所接纳,从而成功融入传统文化体系,并成为文化主流之一。在此期间,“本佛”、“宗经”、追求解脱的本质则贯穿始终,成为中国佛教的根柢。因此中国佛教在很久以来或者说自始至终都存在和使用着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佛教内部用来理解经论、讨论法义、撰写注疏、建立宗义的自度的话语系统;一套是面对民众的、对佛教有兴趣与好感乃至偏见者的化他的话语系统。若以魏晋译经为例,佛经正文属第一套话语系统,经序属第二套话语系统。道安所作《道地经序》和《道行经序》等皆以玄学语写就,“以斯邦人,《庄》《老》教行,与方等(大乘)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11]851,表达的就是借第二套话语系统,帮助、实现第一套话语系统流通的例证。两套系统中,第一套系统是建立言教的根本,第二套是“方便”教化的形式,二者的交汇点即在“应机说法”,以更恰当的方式达到广泛流通佛法的目的。
第一套话语系统中,经、律、论三藏及印度贤圣著述为话语系统建立的根本,中国本土著述依此建立和发挥各自的理解和创见,因为叙述中连篇累牍使用佛教专门语汇,有些甚至还大量使用宗派专用语汇,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积累,“茫然不解”、“不知所云”往往是读者共同的感受。因此自唐末义学衰落之后,佛门之外的学者能够深入其中的甚为少见,他们往往偏据第二话语体系来观察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其结论失之偏颇、悖离史实也就毫不奇怪了。
关于中国佛教的自度、化他的双重话语系统,佛教经论史传中的相关论述为数甚多,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展开了。但由此双重话语系统的特征追溯佛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种种途径和历程,则中国佛教的本质、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的关系、魏晋时期的玄佛合流、佛教的中国化乃至今日流行的“人间佛教”思想等等,皆可有一全新的视角和全然不同的观感。
每次老K吃炖豆腐都很自私,他盛到碗里的豆腐总是最多的。他有点霸道。如果别人稍微多吃了一点儿,他就会很尖苛地骂起来。吃豆腐的时候,我们都让他先盛。这样,他就高兴了。
[参 考 文 献]
[1]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M]//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陈寅恪.逍遥遊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M]//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汤用彤.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M]//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 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唐秀连.僧肇的佛学理解与格义佛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7]林传芳.格义佛教思想之史的开展[J].华冈佛学学报,1972,(2).
[8]赞宁.宋高僧传[M]//大正藏:第50册.台北:白云精舍印经会,1988.
[9]迦叶摩腾共法兰.四十二章经[M]//大正藏:第17册.台北:白云精舍印经会,1988.
[10]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1]竺佛念.鼻奈耶[M]//大正藏:第24册.台北:白云精舍印经会,1988.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1-0119-06
[收稿日期]2018-05-28
[作者简介]哈磊(1968-),男,宁夏吴忠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佛教思想史、佛教文献研究。
[责任编辑:黄文红]
标签:佛教论文; 儒道论文; 佛经论文; 思想论文; 中国佛教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