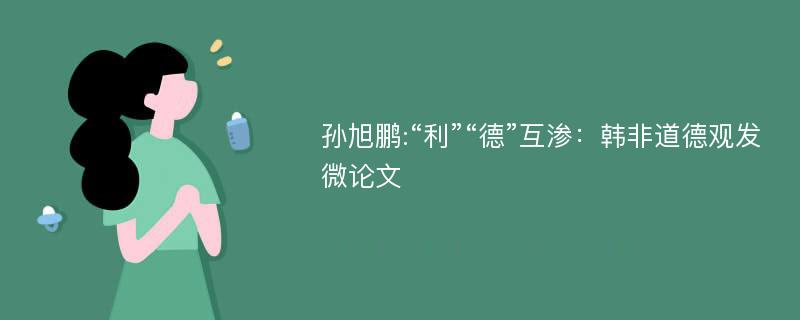
□中华德文化研究□
摘要:韩非的道德观较之于儒家的道德观,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向,它肯定了“利”对生成“德”的积极作用。韩非首先肯定了人性求利的不可改变性,与“道”所体现的客观规律性相契合而将“利”与“道”关联起来;进而,韩非又通过继承发展老子的道德体系,认为“道”是“德”的依据,“德”是“道”的显现,通过“道”将“利”与“德”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利”“德”互渗。韩非道德观给我们的当代启示是:道德不能脱离现实的个体利益而单独存在,个体利益也必须受到道德的规范;只有实现“利”与“德”互渗,才能切实保障个人正当利益,促进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韩非;道德观;“利”;“道”;“德”
韩非作为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人性理论及其政治思想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然而他的道德哲学却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究其原因在于,很多学者普遍认为韩非是反对道德的,他们的重要依据便是韩非对世事所下的论断:“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韩非子·五蠹》)从而认为,既然韩非否定了道德在现实中的作用,他怎么可能还有精深的道德哲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韩非所否定的只是儒家式的道德而不是一般的道德,并由此构建起了与儒家迥异的道德体系。韩非独特的道德观,较之儒家的道德观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向。首先,韩非肯定了人性是求利的,追求个体之利是人的共同特征,此即为人性之“道”,显然这就与儒家肯定的人性本具善端迥异;其次,韩非吸收借鉴了道家的道德体系,认为“道”为“德”之依据,“德”为“道”之显现,既然求利的人性是不易之“道”,那么“德”的建立也就必须顺应个体的求利之心,实现“利”“德”之互渗。应该说,韩非“利”“德”互渗的道德观能够有效克服儒家道德观中“义”“利”之间的紧张状态,具有丰富的现代意蕴。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如何协调个体利益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成为需要迫切解答的难题,而韩非的道德观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借鉴:社会道德的建设不能脱离现实的个体利益而孤立存在,同时道德也应该对不当的逐利行为进行规范,做到以“利”促“德”,以“德”规范“利”;一方面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促进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
一、“道”在“利”中
韩非的道德观与儒家的道德观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在儒家思想中,“利”往往被视为与道德相冲突的因素,因而陷入了“义”“利”之辨的纠缠中,而韩非的道德观则肯定“利”在促进道德中的积极作用。韩非认为人性天然地倾向于“趋利避害”,此为不易之“道”。也就是说,求利的人性是不可改变的,是人的天性,而这与“道”所体现的客观规律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可以说韩非在某种意义上将“利”与“道”关联起来,认为“道”在“利”中。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借鉴了道家的思想。
在“利”与人性关系的看法上,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韩非并未先入为主地将人性视为“善”或者“恶”,而是用一种写实的手法来描绘现实中的人性,认为人性的本质是“趋利避害”。韩非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韩非子·备内》)也就是说,人们行为的所有依据就在于逐利,考量是否有利可图,这是人的天然本性使然。周炽成认为:“在先秦时期,没有哪个哲学家像韩非子那样如此深刻地看到利益对社会关系的作用。”[1]这显然与儒家将“义”与“利”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同的。韩非肯定了利益对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作用。韩非认为不仅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为利益所驱使,即便是父母子女之间也充满着利益算计,这更加证明了人性是趋利的。韩非说:“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儒家肯定了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亲情关系的不可替代性,而韩非则认为利益可以冲淡血缘亲情。正如德国汉学家鲍吾刚指出:“韩非子的某些论述就像一阵遥远的回声,回荡着荀子对孟子所鼓吹的自然美德的批判,而这些所谓自然美德之最重要的温床就是家庭。”[2]在韩非看来,“自然美德”只是一种无用的摆设,而利益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韩非不仅认为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充斥着利益算计,而且在国家政治层面的君臣之间也充满着利益的博弈。韩非说:“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即君臣关系的本质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总之,韩非最终想要阐明的就是,“趋利避害”是人性使然,是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利”与人性天然地合二为一,人性本质上并不是天然纯善的,人类一切行为产生的动机都根源于现实的利益。由此可见,韩非是用一种非常冷峻的现实的眼光来审视人性的。
既然求利在人性中是无法回避的,那么,人们的求利行为从根本上就具有了合理性,因为这是人们自身无法超越的客观现实。人性“趋利避害”的客观实在性,与“道”的品格无疑有着天然的一致性。尽管韩非没有明确地讲“利”与“道”的关联,然而他通过对“道”的阐发,在客观上肯定了“利”是一种不易之“道”。综观韩非的思想可知,他对“道”的阐发是建立在老子的思想基础上的,同时也进行了自己的创新与发展。首先,他将老子形而上的“道”赋予了一种客观实在性。他指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韩非子·主道》)韩非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是非的准则”[3]。很显然,他将老子的“非常道”之“道”看成一种“常道”,把它从不可言说的形而上层面落实为可以言说的形而下的规律性,因而逐利的人性无疑就呈现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本质上即为“道”,即为结成社会关系的准则。其次,韩非论述了人性求利的规律性。遵循规律就可以有效地处理社会关系,例如君主可以通过赏罚等措施对大臣进行控制。“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由此可见,“利”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中枢,具备“道”的特性,亦即事物的客观规律性。韩非曰:“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韩非子·解老》)从本质上讲,“利”就是处理社会关系之“道理”。韩非认为只有顺应“趋利避害”的人性,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处理好各种关系,正如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所指出:“法家不是从遗传学而是从社会学方面来思考人类行为的。”[4]遗传学考虑的是人性善恶问题,这是儒家的致思路向,而社会学所关注的是人类结成社会关系的动机,这是韩非关注的重点。韩非所肯定的是,求利的人性是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的中枢,韩非将“利”融入“道”中,这一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处在战争状态不无关系,整个社会充满着事功的氛围,因此相对忽视了内在德性的养成。
总之,韩非将“利”与“道”关联起来的逻辑是:求利是不可改变的人性,而天然的人性就是天理,也就是“道”,因而“利”从本质上讲即为“道”。在具体表述中,韩非也将“天理”与“性情”连结在了一起,韩非说:“不逆天理,不伤性情。”(《韩非子·大体》)这从根本上承认了“性情”即为“天理”的观点,与后来儒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是相对立的;韩非肯定了“人欲”的客观性,并从逻辑上认同“人欲”即为“天理”。在韩非看来,“性情”或“人欲”最为根本的特征是求利,而且这种求利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具备“道”的特性,由此,韩非将“利”与“道”连结起来。“利”从本质上即为“道”,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利”之上的。这一认识被西汉的司马迁所继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利”便是结成社会关系的不易之“道”。
由于韩非明确地承认“利”的存在,并将其纳入到“德”的范畴,从而形成了一种“利”“德”互渗的道德形态,这与儒家的道德形态有很大不同。学者魏义霞曾将孔孟与韩非的道德学说分别归结为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9],这种区分大致是不错的。然而究其实质,韩非的“功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观,只不过相对于儒家更注重现实的利益问题,并且这种“功利主义”与“道德主义”并不是互相对立的。对此问题,胡适早有论断:“韩非的学说最重实验,他以为一切言行都该用实际的‘功用’作试验。”[10]韩非之所以重视“利”,并将其纳入“德”的范畴,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重视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客观效果,而非将道德聚焦在内在人格的完善;韩非反对儒家式道德也是从现实功用出发的,认为儒家提倡的道德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儒家的道德观具有一种先验品格,是用一种理想的模式去规范现实,而韩非则直接从现实出发,肯定“利”的客观实在性,体现为一种经验品格。在韩非看来,“德”永远只是对现实的反应,“德”的生成不仅不能脱离“利”,而且必须包含“利”,这确实是一种带有“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是对占主流地位的儒家道德观的拓展。以往我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韩非“利”“德”互渗道德观的研究不够,在谈到“道德”时往往将它不加思索地等同为儒家式道德,将“利”与“德”对立起来。韩非的道德观,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不同道德形态的新视角,那便是“利”“德”互渗。
二、“德”得于“道”
韩非既然打通了“利”与“道”之间的关系,认为求利是不可改变的人性,是“道”,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韩非对“道”与“德”关系的认识。如前所述,韩非所构建的道德体系是在借鉴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韩非反对儒家对“德”的判断,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很多学者认为韩非是反道德或者是非道德的。其实不然,韩非构建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体系,在这种道德体系中他沟通了“道”与“德”间的联系,为现实的道德寻找到了牢固的客观根基,而不是像儒家那样从人的主观先验情感中找寻“德”之依托。韩非对“道”与“德”关系的判断是:“道”是“德”的依据,“德”为“道”的显现;“道”体现为一种现实的客观规律性,“德”得于“道”而与“道”同在。
那么,韩非是如何构建自己的道德体系呢?韩非在借鉴老子“道”与“德”关系的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诠释。他认为“德”得于“道”:“道”是“德”的依据,“德”是“道”的显现。韩非指出:“道有积而积有功;德者,道之功。”(《韩非子·解老》)如此一来,韩非就将老子那里带有形而上色彩的“道”落实到了现实层面,认为“道”是可以被认知和描述的,“德”就是“道之功”。韩非特别强调“道”的功用性一面,认为只有通过对“道”的认知,“德”在现实中才成为可能。由此可见,韩非对老子“道”的创新与发展,集中体现在“道”是否可以被认知这一层面上。在老子那里,“道”是不可以被认知与描述的,是一种“非常道”;而韩非则从某种意义上将这种“非常道”落实到了“常道”的范畴里,即认为它是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把握和利用的规律,于是“德”便有了最终的依据。正如学者王威威指出,韩非努力尝试将道家高高在上的“道”拉向物的世界[6],削弱老子“道”的形而上色彩,强调了对事物客观规律性的把握与利用。既然韩非已经将“道”落实为一种现实层面的客观规律,那么“德”的显现也必然要遵循这种规律性。正是在这一关节点上,韩非所理解的“德”与儒家所阐发的“德”便有了天壤之别。儒家的“德”是一种内发式的个体的体悟与修养,认为人性本具善端,而韩非的“德”更强调现实功用,重视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与利用,认为遵循规律取得良好效果便是“德”。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儒家之“德”重个体人格之完善,韩非之“德”重社会现实之功用。韩非曰:“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禄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韩非子·解老》)在这里,韩非将“德”与“禄”相对应,而“建生”与“持生”强调的都是一种现实功用性,这种功用性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道之功”,只有遵循“道”的客观规律性,才能发挥出“德”的现实功用。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韩非十分重视“利”的作用,但他也不是对所有的逐利行为都持肯定态度,这又体现了他关于“德”对“利”进行规范涵养的一面。在韩非看来,个体追求正当利益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以破坏社会整体秩序为代价的逐利行为是必须予以禁止的,韩非称这种逐利行为是“私”,他指出:“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韩非子·奸劫弑臣》)很显然,这种“服私”的逐利行为危害了国家的稳定,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并且,韩非认为,制止这种行为的方式就是刑赏:“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韩非子·奸劫弑臣》)这与前面提到的“庆赏之谓德”不谋而合,保持了其思想的一致性。在韩非那里,“德”并不排斥赏罚,并认为赏罚恰恰是对“利”进行规范与涵养的有效方式。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韩非的“德”是建立在对现实利益进行协调的基础之上的,一旦达成了一致性协议便具备了对“利”进行规范的条件,这便是韩非道德观中“德”对“利”进行的规范,从本质上来看“利”只是作为实现“德”的依据,而不是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才是韩非哲学经世品格的必然追求。
重点是:一则保障牧草植株总量而不少苗;二则保障牧草进入正常生长状态;三则能顺利越冬而持续生产。盐碱和干旱是人工草地牧草生产中最大障碍。当出苗过程中受到土壤墒情影响时,进行小水漫灌提高墒情。出苗后,适时灌溉,保持田间持水量,同时配合土壤改良,压碱防害。柴达木地区土壤质地较轻,蓄肥保水能力相对差,豆科牧草部分品种虽具有固氮作用,但是仍旧不能满足生长需要。香日德地区紫花苜蓿人工草地在追肥尿素年225kg/hm2状况下产量(青干草)≥18 000kg[2]。
才仅仅是第三天的早上,就连脖颈处那两道最深的伤口,业已合在了一起,照这样的速度,用不了十天,伤口便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利”“德”互渗
★一万小时定律:你把一万个小时花在做同一件事情上,你就会在这件事上成为专家。我从小到大睡了几万个小时,怎么在入睡这件事上越做越差呢?
综上所述,学前教育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幼儿的健康成长。首先,由高校牵头,吸纳政府及相关幼儿服务单位以成立幼教协会,并由专人负责与政府、高校、用人单位的协同合作事宜。其次,严把学生质量,应招收有艺术加试合格证的学生入学,这是保障人才质量的基石。最后,对入学后的学生要进行职业认同感及社会责任感的思政培训,让学生牢记社会使命,肩负起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任。
由此可见,韩非所构建的道德体系具有经世致用的品格,他主张在社会关系中遵循和利用客观规律成就“道之功”、实现“德”之用。正如吕思勉所总结的:“法家贵综核名实,故其所欲考察者,恒为实际之情形。”[7]韩非正是从“实际”出发,将老子的“道”进一步具体化,主张遵循“道”的客观规律性来实现“德”,从而构建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体系。
首先,韩非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和取消道德,他只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儒家式的道德,认为儒家式的道德在当时“争于气力”的时代对国家在诸侯争霸中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韩非的道德观具备很强的经验品格,强调现实之事功。“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韩非这里所讲的“道德”是指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面对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试图恢复的正是上古时代的礼仪:“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侑》)韩非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处理世事必然采取不同的方式:“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事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韩非敏锐地察觉到,在战乱频仍的时代,人性趋利的一面更加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所以说“当今争于气力”;而所谓“争于气力”本质上即为追逐利益的行为。因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道德的内涵与标准也应随之改变,因此,韩非将“德”归结为一种奖励措施:“杀戮之为刑,庆赏之为德。”(《韩非子·二柄》)通过“刑德”来顺应趋利避害的人性。学者许建良认为:“在法家思想中,法度实践里的‘刑德’,就与天地之理紧密相连。”[5]由此可见,韩非所否定的只是儒家式的道德,而不是从根本上取消道德;恰恰相反,韩非试图探寻道德的“天地之理”,为其道德观的确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如前所述,韩非正是通过“道”,将“利”与“德”联系起来,也即现实生活中“德”的生成不能脱离“利”的客观需求,从而使其道德观呈现出一种“利”“德”互渗的样态,“利”是形成“德”的基础,“德”是涵养“利”的手段,“道德经过韩非思想的过滤之后变得更为复杂与精妙”[8]。一句话,韩非道德观改变了以往儒家道德的生成模式。虽然儒家没有否认“利”的存在,但却将“利”视为败坏道德的最危险因素,以致形成了义利对峙的思维模式,而韩非则肯定了“利”对道德生成的积极作用,认为“德”包含“利”,“利”与“德”之间不存在本质冲突。
韩非肯定了个体追逐正当利益的合法性,具备了产生类似西方近代“个体主义”的思想因子。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韩非的思想无法摆脱君主专制思维模式的影响,以致他最终肯定的“利”是君主之“利”,其道德观也是为君主实现统治服务的,诚如郭沫若所言,韩非的思想是专为帝王[11]。其实也不尽然,“韩非的‘圣人’观已经蕴含着对君主绝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思考”[12]。尽管韩非道德观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窥见其丰富的现代意蕴。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如何协调个体利益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无数的事例说明,道德不能脱离现实利益而孤立存在,否则就是无源之水;利益也不能脱离道德的轨道,否则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在一段时间里社会热议的话题: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被看成是一个棘手的道德问题,其棘手之处在于其中包含有“利”的成分,“人的自利心超过一定的限度会损害到社会利益”[13],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利”与“德”的关系。老人摔倒应该扶,但是同时也应健全法制,让想扶的人敢扶,让假摔的人付出相应代价。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利益的杠杆来调节道德,通过健全惩罚措施让想假摔的人不敢假摔,假摔的人少了,社会秩序就和谐了。如此一来,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就能形成,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利益而空谈道德。此外,韩非还深入思考了个人小利与社会大利之间的关系,认为个人小利与社会大利之间并不必然发生矛盾,个人趋利避害的倾向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治理,韩非“利”“德”互渗的道德观化解了儒家道德观中义利对峙的紧张局面,拓展了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内涵。在韩非的道德观中,“利”与“德”的双向互动告诉我们:道德不能脱离个体利益而孤立存在,只有在保障个体正当利益的基础之上,社会道德才能形成;同时,个体利益也必须接受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否则追逐不当之利的行为就会蔓延,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由此可见,个体利益与社会道德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道德建设不能否定人们对个体利益的现实追求,同时也应该对不当的逐利行为进行规范,一方面保障个体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促进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
总之,“利”与“德”之间存在着协调互动关系,我们只有处理好“利”与“德”间的关系,才能有效解决现实中的道德难题,这便是韩非“利”“德”互渗的道德观带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周炽成.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90.
[2]鲍吾刚.中国人的幸福观[M].严蓓雯,韩雪临,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68.
[3]《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周勋初,修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9.
[4]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M].张海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14.
[5]许建良.法家“理”的实践透视[J].武陵学刊,2014(5):1-8.
[6]王威威.韩非思想研究:以黄老为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64.
[7]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67.
[8]张昭.“道”与“德”、道德与非道德——韩非道德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考查[J].哲学研究,2016(4):114-119.
[9]魏义霞.七子视界:先秦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27.
[10]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59.
[11]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0.
[12]孙旭鹏,赵文丹.韩非的“圣人”观及其现代意蕴[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2):95-100.
[13]郭春莲.韩非法律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01.
中图分类号:B2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9)04-0012-05
DOI:10.16514/j.cnki.cn43-1506/c.2019.04.002
收稿日期:2019-04-12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学研究项目“荀子政治哲学的‘和合’思想及其现代价值”(18JK0599);西安石油大学“立德树人”研究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德树人功能研究”(LD201815)。
作者简介:
孙旭鹏,男,山东海阳人,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道德哲学;
为构造“反事实情形”从而使实施过境免签政策的分组与对照组具有共同趋势,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匹配。采用马氏距离方法进行一对一的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如表3,即模型(2)所示。比较匹配前后结果可以发现,相比匹配前的数据,匹配后的数据的均值偏差、中位数偏差均显著降低,匹配效果较好(表4)。进而采用匹配后的数据再次进行共同趋势检验,表2模型(3)表明依据匹配后的数据,政策虚拟变量并不显著影响入境旅游人次,即匹配后的数据满足共同趋势假定。
赵文丹,女,山西运城人,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伦理。
(责任编辑:张群喜)
标签:道德论文; 儒家论文; 韩非子论文; 道德观论文; 利益论文; 《武陵学刊》2019年第4期论文;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学研究项目“荀子政治哲学的‘和合’思想及其现代价值”(18JK0599)西安石油大学“立德树人”研究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德树人功能研究”(LD201815)论文; 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