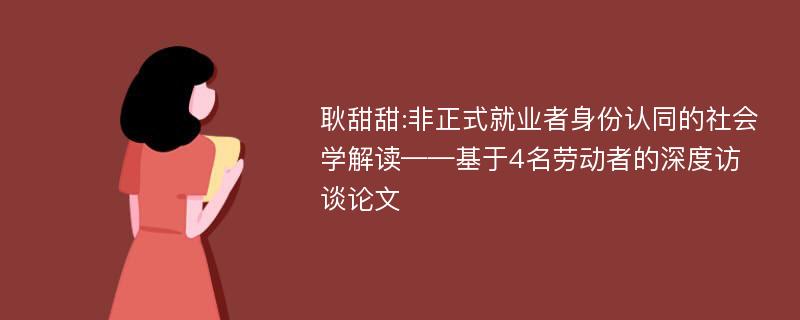
摘 要:在非正式就业模式急剧扩张的背景下,探究非正式就业者个体的身份认同有助于了解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文章通过对4名劳动者的深度访谈,发现在户籍、雇佣方式以及就职经济部门存在差异的非正式就业者们,将自身身份认同定义为“不种地的农民”和“没有保障的打工仔”,以社会学理论来解读非正式就业者的身份认同,发现劳动者面对的是市场转型与制度不完善的双重挤压。在这样的生存障碍背后,非正式就业是劳动主体在劳动参与中采取能动实践策略的结果,更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同时还被赋予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意义。
关键词:非正式就业者;劳动主体;身份认同;社会学解读;理性选择
在经济结构加速调整时期,“非正规就业被认为是解决我国严重失业问题的必由之路,也符合未来人们选择就业模式的发展趋势”,[1]与此趋势相对应的是,四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使中国劳动力市场部门的分割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有集体经济部门劳动人口急剧减少,而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比重突出增大”。[2]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统计年鉴》,非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为2.35亿余人,约占总城镇就业人员57%,可见“非正式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①已经成为主要的就业形式。
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进程以及非正式就业模式的急剧扩张,探究非正式就业者的身份认同有助于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非正式就业强调劳动者个人的经济活动或职业方式的“非正式性”,其要点包括就职部门的非正规性、就业方式和雇佣关系的非正式性。然而非正式就业是一个普遍的、包含的概念,户籍因素、是否就职于正规经济部门以及雇佣方式的不同造成了非正式就业者内部个体间身份认同的差异。本文通过对4位非正式就业者的深度访谈,借“主体—实践”的社会学理论框架,以劳动主体视角揭示非正式就业者的身份认同,探讨以下问题:在户籍、雇佣方式以及就职经济部门存在差异的非正式就业者当中,劳动参与经历有何不同?他们的劳动实践如何塑造其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非正式就业者赋予其身份认同的意义又如何?通过比较不同类型非正式就业者的身份认同,突出针对劳动主体的社会学解读意义,区别于传统的劳工研究,并为改善当前劳动力市场中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提供理论依据。
刘丽芳披着睡衣坐在床头,怀抱着一个毛茸茸的靠垫,眼神里写满了无辜与无助。彭伟民昨晚没与她同床,睡在另一个房间,一大清早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家。刘丽芳不敢过问。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酿就了一个非常时期,非常时期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导致战争。刘丽芳不敢冒这个险。如果昨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也许这个时候的她正在某家超市里逛着,说不定已经选购好了一大堆生活用品。
一、非正式就业与身份认同
非正式就业被认为“在外延上除了‘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也应当包含‘正规部门’的临时工 、兼职等”,[3]非正式就业者的主体主要由流动人口、农民工等群体构成。因此,无论是在就业效果、就业性质以及政府监管方面,“非正式就业”都属于较低层次的就业形式,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体系中处于“非技能劳动市场”,特点是工资水平较低、工作条件差、工作不稳定。身份具有社会属性,身份认同就是对身份的认定,可以定义为“个体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标识、社会属性以及社会位置”。[4]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身份认同的建构展现了将客观的社会现象与主观体验融为一体的脉络。
非正式就业群体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扩展而不断壮大,越来越多从事农业的人转向城市谋生,就业形式的改变影响着劳动者身份认同的改变,但他们无法完全参照户籍制度中“市民”与“农民”的划分方式构建其身份认同。大量因城市征地成为“农转非”②的人在失去土地这种生产资料后转为剩余劳动力,或自主创业,或进入城市打工,其中很多属于非正式就业者。就业效果、就业保障的非正式性致使他们无法形成围绕该就业形式的身份认同,同时非正式就业者还面临着此时户籍上的“市民”与彼时的“农民”交错的身份认同选项。对于户籍上还属于农业户口的非正式就业者而言,脱离土地,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劳动,仍旧会以“农民”作为自己的身份认同要素吗?还是认为城市会接纳自己作为 “新市民”的身份?
非正式就业者常处于被排斥的社会情景下,自雇者B本是农民却无地可种,拥有城市户籍却无法享受应有的“市民”待遇,甚至很有可能会遭受城市人在行为举止、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歧视。面对制度不完善与市场转型带来的生存条件障碍,自雇者们仍旧选择依靠自己现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生产,如自雇者B提道:“年纪是大了,但是我还能动啊,但一家人都要吃啊,好歹也得往家里拿俩钱。”在自雇者的认知里,他们不是在正式的劳动力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劳动主体,而从事“非正式就业”的方式能获取相对合理的收益,因此非正式就业是目标明晰且经济效益最大的行动策略,是在生存环境下的理性行为选择。
在某事业单位就职的受雇者D对保障不公的问题也深有体会:“这样确实不对,如果真的去劳动仲裁的话,是可以成功的,但是没有听过有人这么做,我也不会这么做,现在通知说(2019年)6月份会开始给我们交保险,未来这个制度应该会施行。”受雇者D并不会选择“劳动仲裁”解决问题,“没有人这么做过”说明该单位的临时工在行动上认同了“保障不公”的合理性。笔者推测有两个原因,一是稳定的工作难求,劳动者预估自己的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具备竞争力;二是从众效应,劳动者个体受临时工群体对“保障不公”知而不行选择沉默,以和他人保持一致。另外,D所在单位为行政单位,权威性效应以及未来劳动保障将覆盖于“临时工”的承诺都促进了临时工们对当下“保障不公”的容忍。
本次调查地点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地级市J,该市2018年常住人口约为234.31万人,生产总值约为1 351.9亿元,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23 855元③,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本次调查挑选了城镇地区中的四位非正式就业者,包括自雇者与受雇者各两位,户籍也涉及了农户与非农户,就职单位既涉及正规经济部门,也包含了非正规经济部门(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4名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基本就业信息
年龄户籍状态职业是否就职于正规经济部门自雇者A53农业户口小工、三轮车司机否自雇者B61城市户口(农转非)三轮车司机否受雇者C25城市户口个体兼职出纳是受雇者D24农业户口X事业单位行政内勤是
二、非正式就业者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
非正式就业在劳工研究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劳动主体没有得到过足够的关照,因此,针对其身份认同机制的研究当以劳动者主体体验出发,从劳动者的话语与行动中寻找表象背后的社会关系运作,发掘身份认同在初步建立时的社会资本情况以及进入职业场域后的行动策略运用,最终在静态的社会经济文化要素与主体动态实践的共同作用下确立其身份认同。
(一)初步建立:“自谋生路”和“靠关系”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融入行业英语(EOP)后的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生态再平衡,是指行业英语融入高职公共英语教学后,原教学生态势必失衡,出现诸多失调现象,引发不良影响,故运用生态语言学的原理探求融入EOP后的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生态再平衡策略,消除失调现象及不良影响,使重构的教学生态系统中的教者、学者、内容、方法、评价各生态因子关系重新达到良性平衡,提升教学质量,实现职场环境下学生英语运用能力培养的最大化。[2]
户籍制度曾经是划分农与非农的唯一标准,户口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先赋因素之一,潘毅将打工女性模糊的阶级认同归于户籍制度⑤,但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带来城乡隔绝界限的松弛,各种社会经济要素以及劳动主体的能动实践在身份认同机制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四位访谈对象中,除自雇者B是“农转非”后的城镇户口外,其余三位非正式就业者都属于农村户口。自雇者B提道:“我们村本来是农村,因为离城里近,离客运东站也近,所以现在归开发区了,(我们村的人)就都成了城市户口,但咱肯定还是农村人啊,这一辈子就都是农民……现在也没地种了,要不绿化了,要不修路了,反正都没地了。”为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征用大量城郊农业耕地,将“农民”在户籍上转化为“市民”,但在其认知结构中“农民”仍旧是自雇者B身份归属的关键印迹,自雇者A也提道:“现在种地的少了,自己的粮食也都是买着吃,虽然不种地了,但咱还是农民没错。”比较两位自雇者提到自己是“农民”的部分,自雇者B所提到的“农民”不是户籍所规定的合法性身份,而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记忆。既然“我”是农村人,一辈子以农业为生,即使户籍转变为城市户口,失去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农民的身份是既定不变的。在自雇者A这里,市场需求让他舍弃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劳动实践,选择进城务工成为非正式就业者,“农民”作为户籍制度安排的合法性身份仍被归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总之,无论是否接受户籍制度安排的合法性身份,依托非正式就业的劳动实践,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的自雇者A和B都将自己定位为“不种地的农民”。
王国维于1908~1909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最初发表于《国粹学报》,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
作为“农转非”的自雇者B,即使因失去土地而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还是将自己的非正式就业归因为年纪太大,劳动力市场不接受,A更是直接否定了农业作为就业方式对自己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转向非正式就业的契机。然而无论是A还是B,表面上的户籍差异不能作为结构性的阻碍因素而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属性,二者都身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非正规经济部门,在社会资本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无奈选择了自谋生路。
受雇者C和D都是大学毕业不久刚入职场的新人,都是农村户口,但从小到大都在城市生活。C经家里人介绍跟着一位从业多年的会计学习并担任其助理,日常兼任两家餐馆的出纳。D经亲戚介绍到市里某交警大队做行政内勤的工作,二人都是在正规部门就职的“临时工”,无法享有任何职工保障。D讲到:“我大学学的国贸,毕业后没考上公务员,父母就托人找了这份工作,实际上亲戚一介绍就能来”,“父母托人介绍”是受雇者获得这份职业的原因,是D家庭社会资本运用的结果,但是“没考上公务员”才是最主要的原因,D没能通过正式招考渠道进入体制内成为非正式就业者,故求其次成为体制内的“临时工”。受雇者C也说:“我妈因为觉得我是学会计的,才介绍我跟着这个老会计学,现在同时干着两个餐馆出纳的工作。”两位受雇者身处正规经济部门却成为非正式就业者的直接原因都是因“父母介绍”,餐馆作为个体工商户,也许是考虑成本或者C的经验水平不足,没有与其建立正式雇佣关系,而D是因为受该单位编制所限无法成为正式就业者,显然,C、D二人是被动接受家庭中的社会资本支持的。
上述四位劳动者作为非正式就业中自雇者与受雇者的代表,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获得方式凸显了劳动主体背后的社会资本差异。对于自雇者来说,农业生产活动带来的收益与风险不匹配,且年龄过大、技能缺乏等因素使他们根本不容易找到工作才加入非正式就业的行列中,而对于受雇者来说,依赖社会资本得到的工作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轻易地获取伴随的是劳动的无保障,受雇者也自动接受了这样的交换。自雇者对非正式就业的主动选择与受雇者的被动接受,实际上是社会资本差异的表现,初步奠定了非正式就业者在不同雇佣方式下身份认同的基础。
(二)巩固渗透:“自发的抱团”与“管理者权威压制后的抱团”
简金斯指出,认同(Identity)概念的现代功能事实上包含人际关系中的两个基本因素,即基于人们同一性的关系和基于差异性的关系。[5]因此,非正式就业者的身份认同包含差异性与同一性两方面,进一步可以区分为两个问题:我是谁?我和哪些人一样?寻找身份边界的过程,就是非正式就业者们巩固并渗透其身份认同的过程,两类非正式就业者为了尽快找到身份归属,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策略。受雇者D说:“我刚进去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临时工的话,单位也没有培训,只是领导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作为新人必须听话,对领导的任何安排都遵从。” 受雇者D作为刚入职的行政内勤,完全没有接受业务与技能操作的培训,仅仅是“领导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对领导的任何安排都遵从”,管理者基于职位等级的权威压制,与受雇者D“临时工”之上的“新人”的身份,共同加深了作为非正式受雇者“差异性”的认知。与此同时,受雇者D也在积极采取“同一性”策略, D提道:“开始我是觉得自己融不进去这个氛围的,后来发现也有和我一样的临时工,而且在这里干了好多年了,所以有事没事我就找他们问问题,聊天,他们也有拉拢我的意思,也会替我签到啊什么的,通常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吐槽领导总是要求加班、与正式工不一样的福利待遇等等,时间长了,我就加入了临时工的小团体”,在寻求“同一性”的过程中,受雇者D先是瞄准和自己职业身份一样的“临时工”,并主动与其交流,将讨论方向引至在劳动场所中共同需要面对的“管理者的权威压制”,所有非正式就业的临时工们在此方向上达成目标一致,产生“抱团现象”。由此,在群体组织当中,为了应付职业场域中的排斥,“他们会自觉地组成有利于自己的群体交往网络”,[6]这与赵晔琴对农民工的身份建构的分析不谋而合,即“围绕着‘我们’和‘他们’的话语模式所建构的起来的集体身份是一种在自我身份认同与被类别化之间的妥协,将我们和他们人为分割为两个不同的类别群体”,[7]同“农民工”与市民一样,在被分类以及个体主动强化分类的过程中,非正式就业受雇者深化并渗透了在正规经济部门中边缘化的身份认同。
与非正式就业受雇者不同的是,自雇者无须面对同一劳动场域中的“管理者权威压制”,自雇者既是管理者也是劳动者,主要特点是“分散地、 直接地、 主动灵活地面对不稳定的甚至是相互竞争的市场”,[8]即自雇者就职的场域有特定的价值观与规则,充满了竞争与冲突,然而在面对外来场域的入侵时,场域内部又会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对外的抵制机制,直至达到新的场域平衡。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三轮车司机都会在固定区域内拉客(比如,在某市中心广场周边和某居民聚居区周边),当问及停车地点时自雇者B说:“……我平时都在广场这块停着”,关于停车的位置自雇者B又补充道:“停在路上是有规矩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占了别人的路,影响交通,交警和商户都会赶你走……因为一直在这块聚集,自然而然就熟悉这片儿了,中午有时候会一起吃个饭,有时候互相提醒一下。”可见自雇者相互竞争不意味着完全对立,他们在某一聚集地的相遇是自发选择的结果,其“同一性”的基础在于“都是为了挣钱出来的”,面对交警的道路管制和商家驱赶,自雇者又建立起作为他者的“差异性”认知,即在面对生存机会受到阻碍、劳动场域遭到入侵之后会采取相应的抵抗机制,受雇者们会“互相提醒”彼此不要占商家的路,防止遭到驱赶。这类自发“抱团”的方式建立了一种规避法定规范之外的行业认同,并渗透在非正式就业自雇者的身份认同中。
在进入职业场域后,非正式就业者们都遵循着寻求“同一性”的行动策略,表现为“自发的抱团”与“管理者权威压制后的抱团”两种抱团方式,应对自己作为他者而遭受的“差异性”排斥。在正规经济部门中,受雇者相较于具有正式身份的领导和同事而处于边缘地位,就职于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自雇者,相较于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商户与交警又是被动的,于是在“抱团”的行动策略中非正式就业者深化了他们身份认同中“非正式性”的部分。
在四位非正式就业者中,A和B都是三轮车司机,三轮车作为劳动生产工具为自己出资购买,不存在雇佣关系,因此他们属于自雇就业。自雇者B今年61岁,因城市征地而 “农转非”获得了城镇户口,是一位全职三轮车司机,谈到自己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原因,他说:“我出三轮车有两三年了,因为(城市)征地没有地种了,主要还是年龄大了,打工都没人要,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行,才想着出来拉个三轮车。”迫于生计自雇者B自发选择了该职业,在自雇者B的讲述中,驱使他成为非正式就业者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失去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二是年龄太大,没有用人单位会接受60岁的劳动力。在自雇者B的认知中,60岁的年龄是他进入劳动力市场最大的阻碍,所以只能依靠自雇就业进行劳动生产实践。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涵义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125号)规定: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指国家法律规定的正常退休年龄,即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而目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在进行着“延龄退休”④的改革,据此可以推测,有大量像自雇者B一样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以非正式就业的形式进行劳动生产实践。与B不一样的是,自雇者A属于农村户口,是一名兼职三轮车司机,他说:“现在种地不挣钱,不种了,天暖和的时候我去打工,做一些木匠、装修小工,冬天装修就停了,没地方挣钱,所以才出来跑三轮,也是天天出来跑。” 自雇者A虽是一名兼职三轮车司机,但也是一位全职的非正式就业者,在自雇者A 的认知中,“种地不挣钱”是促使他转向非正式就业的主要原因,农业劳动的收益低于非正式就业收益,具体的劳动方式受外在的天气影响且不稳定,可见非正式就业是自雇者A为寻求更高经济回报的选择。
(三)最终确立:“不种地的农民” 和“没有保障的打工仔”
“身份认同的最终确认是社会记忆与社会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5]劳动者的家庭背景、社会资本等因素作为身份认同的静态机制发挥作用,而非正式就业者的主体实践在时间、空间中的沉淀依靠个体的“能动性反思”不断分化、重构,最终确立起对非正式就业的身份认同。
将仿真模型中电感值分别取为1 mH和20 mH,其余参数固定,根据仿真结果可知增大电感L取值,直流电压的振荡幅值变大,电池电流和直流电压振荡的周期减小,系统稳定性变差;当电感L取值较小时直流电压振荡幅值变小,电池电流的振荡更加剧烈。
皖河流域上游山区河床比降大,长河上游河床比降约1/2000,山坡坡度一般为30°~40°,最陡达70°,汇流快,洪水传播速度很快。各支流出山口以上河道洪水过程一般以单峰为主,洪水历时一般1~3天。
受雇者C和D属于正规经济部门的临时就业者,他们与正式就业者间也存在一道制度性壁垒。根据“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里的说法,“体制内外两种劳动力市场的区分并不是纯技术性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更多地受到制度性的保护,如工会力量、劳动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法等。”[9]当问及待遇、劳动保障问题时,受雇者D谈道:“我每个月固定工资1800,无险无金,除非考试才能转正,临时工就是个打工的,涨工资也遥遥无期,单位规定是一年涨20块。”没有保障的问题也在受雇于个体商户的出纳C身上体现出来:“每个店1600,兼职两个店就是3200,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基于编制产生的差别待遇是非正式就业受雇者所受歧视的主要因素,受雇者被贴上“临时工”的标签,没有得到应有的劳动保障。而 “我国《宪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都赋予劳动者以同工同酬的权利”,所谓的“同酬”指员工因雇佣关系从自身以外所得到的各种形式的回报都应当平等。受雇者C表示:“我知道他(个体工商户老板)是不对的,但是我如果找老板闹,我妈肯定不同意,因为本来就是跟着人家会计学的”,可见,受雇者C对保障不公问题诉诸政府部门解决是知晓的,然而又说:“我妈肯定不同意”,据前文可知C的工作是托父母的关系找到的,说明C的父母和该老板有社会资本(网络)的关联,所以C的母亲尽力维持当前社会网络的稳定与平衡,将“跟会计学”作为受雇者C非正式就业的主要目的,在社会关系网络主导的用工背景下,对劳动保障的公平追求反而退居其次了。
立足于我国特殊国情,许多学者对非正式就业者的身份认同展开了研究,主要的研究对象为流动人口、农民工群体,研究取向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基于制度认同、社会认同的背景,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比较特定区域中劳动群体的身份认同特征;另一类从劳动者主体出发,以定性的研究方法为主,建构农民工身份认同维度,探究其影响因素并提供解决非正式就业者认同感过低的对策,弱化甚至消除劳动者的边缘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非正式就业者身份认同的研究对象主要围绕着“农民工”群体展开,并强调该群体的身份认同在制度背景与社会经济文化中的建构机制,忽略了对非正式就业者日常劳动实践的解释理解。如今在市场经济新常态影响下,城乡二元体制对经济部门的影响在劳动群体中体现出的城乡隔离性渐渐隐蔽化,在非正式就业群体内部,户籍制度、雇佣方式以及是否就职于正规经济部门交织影响着劳动主体的身份认同。
两位非正式就业的受雇者在认知中都肯定了劳动保障制度的必要,但在行动上却认同了“保障不公”的事实,并不是非正式就业者对自己的劳动权益认知不够,追根究底还是劳动保障制度的“嵌入”不够牢固,受雇者即使当下承担着这份非正式职业的责任,其身份认同仍然是“没有保障的打工仔”。
三、非正式就业者身份认同的社会学解读
关于非正式就业者对身份认同的社会学解读,可以从多角度切入,如郑松泰以“信息主导”为背景,分析劳动者生存状态的被制约与身份重构,潘毅以劳资对立视角解构打工妹所受到的来自国家资本主义、资本家以及父权制三方面的压迫控制,但“由职业化决定的主体位置不仅影响着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更加决定着特定的主体经验和表达”,[10]非正式就业者的身份认同是职业化后的主体表达,是制度构建、社会文化介入与主体感受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借助市场化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以及社会流动理论,从非正式就业者劳动经历中解读其自我认同的意义。
(一)市场转型与制度不完善的双重挤压
非正式就业者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定义,凸显了非正式就业者“边缘化”地位在就业制度、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意义。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使内部的二元分割更为隐蔽且更加深入,受雇者C和D进入了正规经济部门就职,这些经济部门提供稳定、有保障、劳动者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晋升机会的工作岗位,当考虑到降低成本、扩大就业等因素时引入了“临时工”,并将其排除在编制制度之外。而临时工的标签意味着工作不稳定、工资低,无法被劳动保障制度所覆盖,制度性壁垒的存在使这一部分非正式就业者失去了晋升的空间。在用工双轨制下,对临时工的歧视成为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歧视的结果使得这一群体更为弱势化和边缘化⑤。
“在有限的国家控制条件下,大多数经济活动是自我调节的”,[11]随着官方规则的扩张,经济活动规避规则的机会也随之增加。非正式就业者身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不乏在国家管控“灰色地带”中就业的劳动者,在国家控制条件还未深入管辖的范围内,非正式就业倾向于遵循着市场化需要而产生。自雇者A和B所从事的三轮车司机职业本属于“非法营运”,政府曾多次对非法营运的电动三轮车进行集中查处,以规范道路交通运营秩序,目前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大城市里,非法营运的三轮车几乎销声匿迹,但在公共交通尚不发达的小城市里,人们偶尔只能依靠停留在街道上的非法营运车辆出行。由此,政府部门的交通管制与“非法营运”车辆的应市场需求而生的现象形成了悖论,即市场化催生了从事“非法营运”的非正式就业者,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为规避对交通秩序的不良影响,主动采取应对策略,如自雇者B都提道:“交警看你没有占路,也不会怎么难为你的,所以都停到不占路的地方,但是这也说不定,哪天政府出台什么文件了,要赶你也没法。”显然自雇者对“非法营运”的负面影响仅仅停留在国家管控的制度层面上,认为“不占路”就能规避这一公共危害,所以当不占路的时候,交警“也就不怎么难为你了。”据此可推测,对两位自雇者而言,对公共交通危害的影响不足以抵消掉市场化需求为他们带来的利益,然而言语中的“不一定”又透露出对未来国家管控的忧虑,当整治“非法营运”的规定全面深入到小城市后,这两位非正式就业的自雇者又将何去何从?
红松的生长习性是由其原有的生态环境决定的。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红松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具有较强的耐受性,对气候和土壤条件也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苗期生长发育初期生长缓慢,年龄相对较小。但随着树龄的增长,逐渐增强。成年红松具有较强的抗寒性、耐低温性和适应性。但即使是红松作为针叶树种,其主要根仍发育不全,侧根广泛扩展。因此,对土壤环境的渗透性和排水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合于山坡生长,不适合在多年冻土或排水沟不好的地方生长。此外,红松林的防守能力一般,应注意混合生态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培育人工林。
市场转型与就业制度间存在一种张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多元化需要催生了非正式就业队伍的壮大,对劳动力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就业制度不完善让“劳动保障制度”无法完全覆盖到非正式就业的受雇者身上,城市化的征地需求让“农转非”后的“市民”无地可种,被吸引到城市中就业,也只能在国家管控的“灰色地带”中艰难生存,至此,非正式就业者们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便显示出市场转型与制度不完善双重挤压的痕迹。
(二)生存环境下的理性选择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按照一种投入—产出的精于计算的方式选择他们的行动”,[12]作为系统的一部分,个人在目的性、合理性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三个方面选择行动,不断达到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平衡⑥。劳动者无论是出于谋生还是过渡而选择非正式就业,都是在权衡个体如何能在竞争场域中实现最大效能后产生的结果。
临时工是就职于城市正规经济部门的非正式就业者的代表,作为非正式就业中的受雇者,他们无法享有与正式职工一样的待遇,甚至无法得到基本的劳动保障。在同样甚至更高的工作强度下,非正式就业者在劳动保障和工资收入、声望等方面都远低于正式工。非正式就业者作为劳动主体,在衡量自己的劳动实践与身份认同时,要面对临时工身份与正式单位之间不匹配的矛盾,因此探究非正式就业者的身份认同就是探究市场化中劳动者适应的问题,更进一步是对就业与社会稳定问题的深入分析。
对于非正式就业的受雇者来说,横跨在“临时工”与“正式工”之间的不仅仅是劳动主体在经济上的待遇差距,更关乎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地位,这种差距让受雇者D戏称自己是“没有保障的打工仔”,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弃之可惜”,原因在于“临时工”的身份具有一定的性价比优势。首先,这是一份属于政府正规公共部门的职业,劳动主体对该单位具有名义上的“认同感”,除了不受劳动保障外,还算是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托人找来的工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劳动者社会资本的体现,而社会关系网络的约束会提高关系者的违约成本;最后,劳动者的个人能力也并未达到能够独自应对市场风险的程度,非正式就业的“过渡性”有利于劳动者积攒经验。如此衡量下来,作为一名正规部门的非正式受雇者确实是劳动主体理性衡量的结果。
(三)对未来社会流动的期待
陆学艺将 “社会流动 ”定义为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 ,包括“垂直”与“水平”两个方向的社会流动。劳动者在劳动中付出劳力而收获经济报酬,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日常基本生活物质需求,非正式就业的受雇者和自雇者对自身劳动所赋予的意义都在未来的社会流动层面上有所体现。
一是个税应该进一步降低。今年10月1日起,个税减税政策已经率先实施,工资薪金起征点提至5000元,并适用新的税率,而明年1月1日起个税改革将全面实施,老百姓还能享受专项附加扣除。个税起征点提高到每月5000元以后,从总体上来讲,税收一年大致要减3200亿。
垂直流动是指“一个人从下层地位和职业向上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 ,或者是由上向下的反向流动”,[13]文中的两位受雇者都着眼于“垂直的”向上的社会流动。在X交警大队担任行政内勤的D表示:“我可能会干个1、2年左右,现在每天都在学习,遇到招公考试就参加,毕竟这份工作真的不能长久。”受雇D抓紧时间抽空学习,未来目标是获得正式工作,完成“非正式”到“正式”的转换,进一步完成社会身份的转变。在个体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受雇者寄希望于凭借个人能力从政府等正规部门的选拔机制中脱颖而出,借此作为社会流动的渠道。受雇者C也同样如此,“我希望能考进银行之类的最好了,目前在准备农信社的考试……或者等我爸从银行退休,可以把我置换进去。”受雇者C所说的“置换”是一种职工子女置换就业政策,相关单位规定当职工达到退休年龄时,可在安排退休后将职位置换给其子女。可见除了考试之外,还可以借自己的社会资本达成正式就业,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
3.5 学习记忆 良好的睡眠可对记忆进行有效的巩固,而失眠患者通常存在不同程度的记忆力减退,其也是影响患者生活及社会活动的重要因素。陈莉弘和黄俊山[24]研究指出,睡眠与学习记忆关系密切。鲁珊珊等[25]研究指出慢性失眠对瞬时记忆、延时记忆等均具有显著影响。刘艳和吴卫平[26]对24只1月龄雄性小鼠进行研究,将其分为慢性睡眠限制组、睡眠剥夺组及对照组,结果发现,连续5 d,每天6 h的睡眠限制及睡眠剥夺均可减弱幼鼠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且睡眠剥夺的影响程度更大。
本次调查中的两位非正式就业的自雇者更希望实现子代的社会流动,倾向于 “水平流动”,即只是变换活动场所, 并不改变社会地位的社会流动。他们希望为自己的子女在城市中安家而提供经济支持,两位自雇者都表现出为子女在城市买房的急切心理,如自雇者A提道:“我有两个孩子,大儿子30多了还没结婚,小女儿读大学还没毕业,现在就是想赶紧给儿子在城里买房。”“给儿子在城里买房”说明自雇者对社会流动的期待是寄托在子女身上的,非正式就业能够生产出为下一代构建社会资本的经济价值,供子代拥有实现社会流动的际遇,并将城市作为主要社会活动场所。在城市定居并非社会流动的终点,非正式就业者们内心对“正式性”的追求更是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为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是非正式就业者身份认同的意义所在。
四、结 语
在劳动力市场中,非正式就业者身份认同的构建在实践中回应了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顺应了市场转型的步伐。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隔绝虽然渐趋弱化,但劳动主体的非正式就业选择在身份认同机制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了户籍在城市内部的二元差异。“农转非”后的市民失去了“农民”的制度性身份,依旧保留了先前社会资本较低的状态,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着户籍为“农民”的劳动者放弃农业在城市定居,并建立起高于农村的社会资本,如此看来“城乡隔绝”在城市内部是以隐蔽的方式蕴含着的。根据雇佣方式以及就职经济部门的不同,非正式就业自雇者与就职于正规经济部门的受雇者们分别以“自谋生路”和“靠关系”谋得职业并初建了身份认同,而后分别通过“自发的抱团”和“管理者权威压制后的抱团”的求同策略寻找其身份边界,巩固并渗透劳动主体的身份认同,在各种制度因素以及非正式就业者的能动实践条件下,确立起“不种地的农民” 和“没有保障的打工仔”的身份认同。在对非正式就业者身份认同的社会学解读中,无论是自雇者还是受雇者,都要面对市场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和制度安排不完善的双重挤压,无论是否就职于正规经济部门,制度壁垒只会越来越强力,在这样的生存障碍下,非正式就业既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完成未来代内或代际间“社会流动”的最佳路径。
市场化改革与经济转型是一个逐步蔓延的过程,大致是以从东部向西部的路径深入,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域转移到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调整。本文的调查地点在山西省,位于中国大陆的中西部地区,针对中西部地区的非正式就业研究,有助于了解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地域性分布。与将焦点放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其他非正式就业研究区别开来,并有助于就业制度的完善,优化对非正式就业劳动主体的保障安排。劳工研究于社会,于国家,于个人而言,都是关乎未来人类发展的重要议题,无论从哪方面论述劳动者,都不应当忽视在劳动实践中主体的“能动性反思”针对劳动本身做出的回应,但劳动主体的身份认同是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一环,本文仅是初步探讨,相信随着非正式就业模式的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会在该研究视角上有所突破。
(3)急性坏疽穿孔性阑尾炎:本组7例,表现为:阑尾肿大明显,性状不规则、位置较固定、轮廓模糊,边界不清;阑尾壁可见连续性中断回声,壁增厚,各层次不清;阑尾腔扩张无回声或呈低回声。超声可见阑尾区混合性包块,且存在实性低回声,强弱不等、回声杂乱,如可见强回声光斑于阑尾腔内,有结石,后方有声影,有明显腹腔肠间积液,且肠蠕动减弱。
注 释:
①“informal employment” 被译为非正规就业,是针对非正规部门内的就业形式,本文遵从社会学专业名词的翻译习惯,译为非正式就业.
②农转非:农转非指一种户籍制度。农,指农业;非,指非农业生产。农业户籍人口一般来说只能通过有限的几个途径包括升学、招工和参军转换为城镇户籍,本文中的自雇者B本是当地农民,后通过征地等方式转化为城镇户籍.
③数据来源于晋城市统计局.晋城市统计信息网,http://www.jctj.gov.cn/news/tjgb/131450134.html.
④2015年,人社部部长尹蔚民称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
⑤参见杨云霞,黄亚利.公共部门临时工的身份冲突——对88份文本的实证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12).
⑥这种平衡是动态的平衡,即个体的社会行动受社会系统的影响而调整,反过来社会系统也会受个体行动的影响而调整,以达到彼此适应.
股骨颈骨折患者多为老年人,会伴随者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系列其他疾病[4],使得该病的治疗的难度加大,在治疗时采取舒适护理,从患者的心理问题出发,安抚患者的不良情绪,并用专业的健康知识加以教育[5],使得其治疗的信心不断增强,最后在恢复期予以辅助护理,加快患者的恢复,因此,舒适护理对股骨颈骨折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鞍钢,杨韵新.就业模式转变:从正规化到非正规化——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状况分析[J].管理世界,2001,(2):69-78.
[2]刘精明.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收益[J].社会学研究,2006,(6):89-119.
[3]葛莹玉,张新岭,李春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建构基于人力资本形成与开发的耦合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4]陈红玉.消费与身份 20世纪后期英国的设计产业及理论[M].北京: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5]周明宝.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J].社会,2004,(5):4-11.
[6]隋春波.社会排斥与个体自我认同的重构[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7]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J].社会,2007,(6):175-188.
[8]万向东.非正式自雇就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特征与差异——兼对波斯特“市场化悖论”的回应[J].学术研究,2012,(12):62-69.
[9]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吴海红.“过更好的生活”:新生代流动女性的职业经历和自我建构——以皖中陶镇为个案[J].中国青年研究,2018,(1):64-73.
[11]Portes,Alejandro.The Informal Economy and Its Paradoxes[A]. N.J.Smelser & Swedberg,R.The Hand 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C].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12]刘少杰.理性选择研究在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与方法错位[J].社会学研究,2003,(6):24-32.
[13]许德友.社会流动与流动渠道:农民城市打工现状的理论解释[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3(3):25-29.
中图分类号:D6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19)04-0031-11
收稿日期:2019-05-20
作者简介:耿甜甜,女,山西晋城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宗教社会学、应用社会学。
DOI:10.19327/j.cnki.zuaxb.1009-1750.2019.04.004
责任编校:罗 红,张 静
标签:业者论文; 身份论文; 社会论文; 劳动者论文; 临时工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