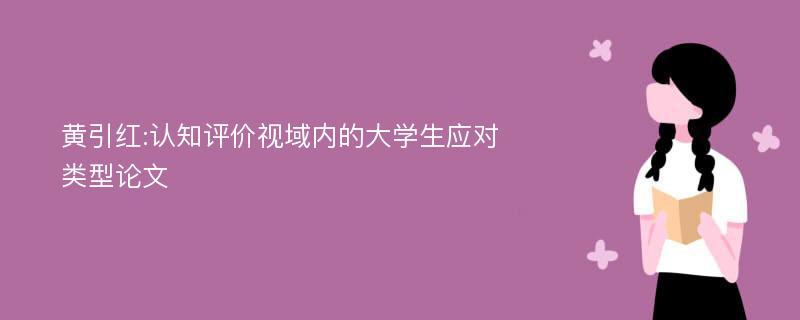
摘要:结合认知评价理论,划分大学生应对类型,探讨应对类型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使用应对方式问卷(CSQ)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西南地区1372名大学生施测。潜在类别模型显示大学生应对类型可划分为被动应对类型和主动应对类型,分别占比37.3%和62.7%;被动应对类型在CSQ各维度的组内相关比主动应对类型要大,且两者在各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结论:被动应对类型在选择应对策略时更盲目,不排除使用不成熟应对方式;主动应对类型能积极地选择应对策略,偏好问题解决应对方式。主动应对类型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关键词:认知评价;应对类型;潜在类别模型;心理健康
引言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指处在压力和困境下的个体用以调节自身生理、认知、情绪和行为的策略[1],主要包含两个功能,一是调节或消除与压力有关的不良情绪,这种调节被称为情绪取向应对方式(emotion focused coping);二是聚焦于现实并改变能引起应激反应的人为因素和环境因素,这种方式被称为问题取向应对方式(problem focused coping)。早期理论研究从自我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将应对方式视为人格的一部分,认为应对方式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方式,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和稳定性[2]。通过对人格特质的测量可以预测个体习惯采用的应对方式。应对方式与情境无关,与人格特质有关。人格特质是影响应对方式的最主要因素。在特质论的理论背景下,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比如有研究表明,在大五人格特质(the Big Five Personality)中,外向性与问题取向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宜人性与寻求社会支持正相关;开放性和责任感与积极应对方式正相关;而神经质与情绪取向应对方式正相关,与问题取向应对方式负相关[3]。王海明认为,神经质和内外向对不成熟应对方式有显著影响[4,5]。由于应对方式与人格特质存在显著相关,并受人格特质的影响,因而有学者提出,应对方式具备和人格特质一样的特点,即跨情境性。这种跨情境性是指同种特质的个体在任何情境下都存在相同的应对方式,应对方式在不同情境下是稳定的。然而由于特质论者忽略了个体认知评价对应对方式的影响,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同种特质的个体在不同情境下选择的不同应对方式,因而受到过程论者的质疑。
有研究发现,面对与自尊有关的应激源时,个体倾向于采用逃避-回避(escape-avoidance)等应对方式,并很少寻求社会支持[6];而面对与工作压力有关的应激源时,个体更多地选择直面问题[7]。应对方式因情境的改变而改变。情境因素在个体选择何种应对方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过程论认为应对过程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个体与应激情境的相互作用导致个体不断对应激源进行重新评价,并调整应对策略[2]。在情境因素的影响下,应对方式是变化的而不是稳定的。
没容辛娜回答,王树林就走向沙发,他听到手机振动的声响,以为是自己的。不是,是辛娜的手机在茶几上亮了一下。辛娜忘记拿手机了,辛娜洗澡都要带着手机,这一次居然忘了。王树林思虑一闪,手指滑键,是信封闪烁,一个下拉,短信赫然:亲亲奶茶,我想拎鞋。署名可乐。
2.1 临床情况 4例胎儿MRAA-LDA-DAO中,2例为本院建卡患者,行胎儿心脏筛查时检出,2例为外院转诊病例,外院超声提示“3VT见O形血管环形成,考虑多系DAA”,经过本科医师全面系统的检查,最后均确诊为MRAA-LDA-DAO。所有病例均不伴其他心内外畸形。
从个体与应激情境的相互作用来看,过程论与特质论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前者强调应对方式的情境不稳定性,即应对方式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不受人格特质的影响,而后者强调应对方式的情境稳定性,即同种特质的个体总会选取相同应对方式,不受应激环境的影响。由于过程论与特质论都能解释现实生活中关于应对方式的某些现象,因而两者存在新的整合的视角,即以过程-特质为研究取向的应对交互模式。该模式认为应对方式随着人格、时间、情景等因素动态变化,它是人格特质、时间和应激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格特质,时间,环境等因素通过认知评价(cognition appraisal)影响应对方式。
由于自我效能高的个体在选择应对方式时表现得更为主动,而自我效能低的个体在选择应对方式时更被动,因而应对者类型可分为主动应对和被动应对两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一为:由应对方式的选择模式而衍生出来的应对类型存在主动和被动两种。
认知评价理论从自我效能感的“高-低”维度对应对方式进行了分类。而这种分类是基于各种应对方式的选择模式形成的,包涵了各种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对关系。例如,直面问题的应对者A很少会使用逃避等应对方式,而直面问题的应对者B会经常使用逃避等应对方式,与传统理论不同,认知评价理论认为这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应对者。传统应对方式理论将主要应对方式与应对类型一一对应起来,认为只要应对者经常选择某一应对方式就属于某种应对类型;而认知评价理论认为,个体各种应对方式选择频次的高低模式决定着其应对类型,每一种具体的、可选择的应对方式并不能逐个对应自我效能感的某一类别维度(如表1)。按照自我效能感进行分类时需要考虑到各种应对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即选择模式。
Folkman认为认知评价在应激情境和应对方式中起着中介作用,分为初评价(primary appraisal)和再评价(secondary appraisal)。初评价是指对情境的危险程度的感知;再评价是指对自身应对资源的评价以及对情境能否被改变的一种判断[6]。当个体预感或直觉到自身应对能力足够改变情境时,就会倾向于使用直面问题等积极应对方式;反之,当个体认为情境不能被改变时,就会倾向于采取回避和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坚信情境能被改变的个体,会更加主动地面对和处理应激源,应对策略的选择更具积极性;而坚信情境不能被改变或者应激程度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个体,应对方式更加被动,应对策略的选择更加盲目。因而个体应对方式的选择取决于个体内在的认知评价。
表1 认知评价视域内不同应对类型示例
应对方式选择频次排序应对者A类型应对者B类型主要应对方式直面问题应对直面问题应对次要应对方式求助应对逃避-回避应对其他应对方式合理化应对自责应对
将应对类型与性别,城乡户籍,民族等人口学变量进行独立性检验,发现除了城乡户籍与是否为独生子女显著相关之外,其余变量之间并无相关(见表4)。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潜在类别模型(LCM)对1372名大学生划分应对类型。模型如果有更高的Entropy,更低的AIC和BIC,且LMRT达到显著性,则说明这个模型的拟合程度高[11]。综合来看,由于划分两类既符合上述标准,又是指标变缓的转折点,因而可将大学生划分为1型和2型两种应对类型(见表2),两种应对类型分别占总样本量的37.3%和62.7%。
(二)研究工具
1. 应对方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CSQ)
与对照组比较,各组乳腺癌患者临床组织标本中miR-200c mRNA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5),且淋巴结受累及远处转移严重程度越高,miR-200c水平升高越显著(P<0.05);各组乳腺癌患者临床组织标本中EZH2 mRNA表达显著降低(P<0.05),出现远处转移的D组EZH2 mRNA表达水平显著低于淋巴结受累的B组和C组(P<0.05)。见表1。
本书是阿里巴巴集团前总参谋长曾鸣对互联网时代的重要趋势做出革命性解读的作品,披露了其对于未来商业模式的思考和判断。作者基于在阿里巴巴集团十几年的实践经验,以及对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深入思考,在书中提出了未来30年新的商业模式——智能商业。“网络协同”和“数据智能”是新商业生态系统的D N A,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只有智能商业的新物种才能生存和发展。作者曾鸣,现任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湖畔大学教育长,阿里巴巴商学院院长。2006~2017年担任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
采用肖计划编写的应对方式问卷(CSQ)分析大学生应对类型。该问卷共62个条目,每个条目以“是”或“否”作答,分为六个维度。其中问题解决和求助是成熟应对方式,幻想,退避和自责是不成熟应对方式,合理化是混合应对方式[9]。研究表明,该问卷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在0.62~0.72[10]。基于本次测量数据,应对方式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6。
2.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将被试在应对方式问卷上的各维度得分进行标准化,并进行组内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显示,1型应对在问题解决、自责、幻想等应对方式上的组内相关(ICC=0.177,95%CI:0.140~0.217)比2型应对的组内相关(ICC=0.160,95%CI:0.132~0.190)要大,且1型应对在应对方式问卷上的各维度得分与2型应对存在显著差异(见表3),说明1型应对在选择应对策略时更盲目被动,不排除使用自责、幻想等不成熟应对方式;而2型应对在选择应对策略时更积极主动,偏好问题解决应对方式。2型应对在自责、幻想等不成熟应对方式上的得分低于1型应对(见图1),说明1型应对以不成熟应对方式为主。实验结果支持了假设一,即应对类型可分为主动应对和被动应对两种。
二、结果
(一) 应对类型的划分
在西南地区多所院校整群抽取1372名大学生,年龄段为17至23岁,其中男生550人(40.09%),女生822人(59.91%);城镇户籍266人(19.39%),农村户籍1106人(80.61%);汉族942人(68.66%),少数民族430人(31.34%),都为大学以上受教育程度。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量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该量表共90道题,包含十个因子,分别是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因子。各因子分和总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基于本次测量数据,该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6。
表2 潜在类别分析拟合指标(n=1372)
类型AICBICABICEntropyLMRT1类94212.8694583.77 94358.23--2类88625.75 89372.78 88918.53 0.890.00 3类87431.89 88555.0587872.08 0.860.00 4类86574.8688074.1687162.470.850.16
表3 两种应对类型在各应对方式上的比较
应对方式大学生应对类型(M±SD)被动应对类型(1型)主动应对类型(2型)Fη2问题解决6.98±2.398.67±1.68232.12∗∗∗0.15求助5.95±1.925.65±1.698.87∗∗∗0.01幻想5.43±1.783.08±1.56644.89∗∗∗0.32自责4.88±2.161.56±1.211322.39∗∗∗0.49退避5.77±1.963.09±1.59756.59∗∗∗0.36合理化4.82±1.973.18±1.27352.01∗∗∗0.20
注:***P<0.001,下同。
(二) 应对类型与各人口学变量的相关情况
研究表明,应对方式能显著预测心理健康水平。其中问题解决应对方式能正向预测心理健康水平,而幻想、自责等应对方式能负向预测心理健康水平[8]。由于主动应对类型的个体多采用问题解决应对方式(直面问题应对),而问题解决应对方式已被研究证实与高水平心理健康有关,因而主动应对类型的心理健康水平应更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二为:主动应对类型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针对污染情况比较严重的城市水环境,仅依靠水流自身的净化功能显然无法彻底改善污染问题,在此情况下,需要应用人工生态处理技术。人工生态技术处理即借助于各种人工生态技术对城市河流中的微生态加以改善,对河流中的污染物与其他污染源等物体进行处理,并且不会对河流造成二次污染,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河流处理方法[2]。但是,该处理技术应用成本较高,并非所有城市河流都适用,为此,应选择已经污染或问题比较严重的河流进行治理,促使其快速恢复到原有生态结构。
我们用东北地震的数据集说明,这个方法对于单个地震事件也是有效的。相应的质点分布快照图和估计参数的时间序列见图8和图9。由于这次地震为近海地震,因此在参数的初步估计中,有相当大的定位误差。但是在初至P波到达后40s,平均误差开始下降。随着地震破裂扩展,震级估计值由6.0增大到了8.4,这与地震破裂的机制相吻合。而估计的5个参数值均与日本气象厅地震目录中的值接近。
(三) 主动应对类型与心理健康水平
主动应对类型与被动应对类型在SCL-90量表上的心理健康总分存在显著差异,F(1,1370)=458.81,p<0.001,η2=0.25。被动应对类型的心理健康总分要高于主动应对类型(图1)。实验结果支持了假设二,即主动应对类型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图1 两种应对类型在各应对方式上的比较图
表4 应对类型与各人口学变量的相关情况(x2值)
12341应对类型12性别0.1413城乡户籍0.170.0214民族0.010.070.0115独生子女0.040.290.52∗∗∗0.19
三 讨论
(一)主动应对的研究现状
Aspinwall和Taylor将主动应对(proactive coping)定义为人们预期或发现潜在的压力和预先采取行动阻止它的发生或抑制它的影响过程[12]。主动应对是一种带有个性特征的面向未来的应对类型,是人格特质与认知评价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国内关于主动应对的研究多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开展,探讨主动应对的内涵与功能,而国外则积极开展对主动应对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国外对主动应对的测量通常使用Greenglass等人编制的主动应对问卷(Proactive Coping Inventory,PCI)[13],然而该问卷尚未经过国内标准化修订,因而鲜少被国内研究者引用。
(二)潜在类别模型划分应对类型的结果
主动应对是一种应对意识,并非一种可操作的、具体的、策略性的应对方式,其本质是根据当前情境积极地、适时地选择某种应对策略或应对方式,是应对方式的选择模式,而这种选择模式对未来有着积极的影响。主动应对主要表现在应对方式的选择倾向上,这种选择倾向受到个体特质和认知的双重影响。因此,在理论构念上,以选择倾向为基础的主动应对类型的识别不能建立在基于变量中心法(variables centered-approaches)的因子分析上,而应该建立在以个体中心法(person centered-approaches)为基础的潜在类型变量上。
潜在类别模型以被试对应对方式的选择模式为基础,通过最小二乘法估计经贝叶斯方法转化后的模型参数,从而得出模型拟合结果。根据以往的研究,这种划分结果较传统分数划界方法更为敏感和可靠[13]。本文通过潜在类别模型,证实了存在于应对方式选择模式之上的应对类型,即主动应对和被动应对两种类型,也验证了认知评价理论中的再评价划分的合理性。
(三)主动应对的特征及功能
主动应对类型的个体以问题解决应对方式为主,敢于直面问题,对环境有一定的控制力,自我效能感高,因而心理健康水平较高;而被动应对类型的个体在选择应对策略时更盲目,各种应对方式对其并无区别,不排除使用自责,幻想等不成熟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低,因而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研究表明,主动应对不仅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存在相关[14],而且对人的身体康复也会有间接的影响[15]。主动应对类型的个体对环境有一定的控制感和负责任的态度,其应对方式有利于将来避免压力和最小化压力,而最小化压力的能力与人的复原力(resilience)相关[16]。
(四)如何培养大学生主动应对意识
当前大学生面临大量的生活、学习和就业方面的压力,如何最小化这些压力和提升大学生复原力成为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一大难题。主动应对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大学生最小化压力,增强其复原力,提高其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培养大学生主动应对意识对于提高其环境适应力有着重要的意义。为培养大学生主动应对意识,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发挥大学生心理活动中心在大学生压力应对方面的科普宣传作用;其次,学校和社会应加强责任意识教育,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直面问题;最后,发挥积极归因训练在团体辅导或心理课堂等活动中的作用,重视归因训练对大学生主动应对意识的增强作用。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内归因与积极应对显著正相关[17]。正确的归因训练有利于促使大学生对困难进行内在的、可控的归因。基于认知评价理论,当困难被归因成内在的、可控的,个体应对方式的选择模式将得以优化,其心理健康水平也会得到相应提升。
参考文献:
[1] Skinner E A, Edge K, Altman J, et. al. Searching for the structure of coping: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category systems for classifying ways of cop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3,129(2): 216-269.
[2] 叶一舵,申艳娥.应对及应对方式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2,25(6):755-756.
[3] Le X, Ru-De L, Yi D, et. al.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oping style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 (8):1-11.
[4] 王海民.师范大学生应付方式的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3,12(4):447.
[5] 丁凤琴.国内大学生应对方式研究进展[J].中国学校卫生,2007,28(11):1046-1049.
[6] Folkman S. Dynamics of a stressful encounter: cognitive appraisal,coping,and encounter outcom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0(5): 992-1003.
[7] Folkman S, Lazarus R S. An analysis of coping in a middle-aged community sample[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80, 21(3): 219-239.
[8] 吕薇,英玉生.高职生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中国特殊教育,2006,(8):87-90.
[9] 廖友国.中国人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5):897-900.
[10] 肖计划,徐秀峰.“应对方式问卷”效度与信度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6,10(4):164-168.
[11] 张洁婷,焦璨,张敏强.潜在类别分析技术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12):1991-1998.
[12] Aspinwall L G, Taylor S E. A stitch in time: self-regulation and proactive cop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7, 121(3): 417-436.
[13] 苏斌原,张洁婷,俞承甫,张卫.大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的识别:基于潜在剖面分析[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31(3):350-359.
[14] Greenglass E R, Fiksenbaum L. Proactive coping, positive affect and well-being: testing for mediation using path analysis[J]. European Psychologist, 2009, 14(1): 29-39.
[15] Greenglass E R, Marques S, Deridder M, et. al. Positive coping and mastery in a rehabilitation sett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2005, 28(4): 331-339.
[16] 邵华.应对的研究设计,测量,类别及未来研究方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2,20(7):1121-1127.
[17] 张晓茹,杨宗莉.四川高职贫困大学生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1):130-132.
中图分类号:B8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80(2019)02-0047-05
doi:10.3969/j.issn.1009-2080.2019.02.010
收稿日期:2019-02-25
作者简介:黄引红(1991-),女,湖南郴州人,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小林)
标签:方式论文; 类型论文; 主动论文; 情境论文; 个体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