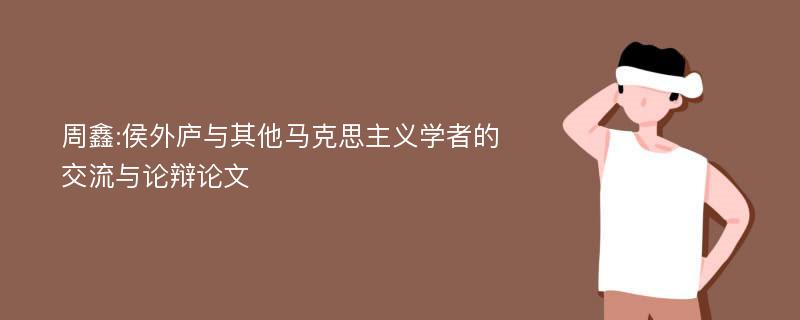
摘要: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所在地重庆,以周恩来为领导核心的中共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抗战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学者,为他们创造了学术风气正派、务求实干创新的研究环境。侯外庐作为当时的左派文化领导人之一,在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流与论辩中,思想觉悟与理论水平进一步提升。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习及其形成的诸多论断至今深有启发,特别是侯外庐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行研究的治史方法和“实事求是”“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成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关键词: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独立自得;马克思主义史学
重庆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读书、学术活动比较频繁,侯外庐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流增进了学术友情。值得一提的是,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圈有自由讨论和相互辩论的风尚,学术气氛比较活跃,有一定的思想自由,学术探索性强。这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潮能够发展壮大并征服人心的一个重要内因,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内在思想活力的表现。“对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的分歧意见动辄被上纲为‘阶级斗争’”[1],这也是侯外庐回忆这一段时特别强调的。侯外庐、杜国庠、翦伯赞、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风格,各自研究路径也不尽相同。比如他们关于古代社会分期的讨论,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但应该看到,这一讨论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促进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发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科学化意义重大。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还带有不少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那么,40年代这些缺点就明显地减少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大为提高。[2]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阵营中,由于思想深度不一,师承授受不一,个人才情与天赋千差万别,应该说有一个学术研究的风格问题。被史学界公认为“五老”的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的学术风格就不是一个模型铸就的。郭沫若的通家大气、范文澜的严谨贯通、侯外庐的理论艰深、翦伯赞的哲理思辨、吕振羽的不蔓不枝,给同时代及后辈学人以深刻的印象。“五老”走向史学的路径也不尽相同:郭沫若是由医学而文学而史学,范文澜是由文学、经学而史学,吕振羽是由工程技术科学而史学,翦伯赞是由商学、经济学而史学,侯外庐则是由法律、经济学而史学。他们个性、经历、学术传承和理论素养等的不同,使他们的史学研究各具特色和风格,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显得绚丽多彩。与翦伯赞、吕振羽相似,侯外庐也有短暂的留洋经历,起初学的也是经济学。与翦、吕不同,侯的经济学素养似乎深厚而且纯正得多,因为他与人合译并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他后来所以能主编著名的《中国思想通史》,绝非偶然。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侯外庐曾幸运地直接接受过李大钊的指点和影响。从《韧的追求》这部自传来看,侯外庐是一个颇为自信、颇为自负的单纯的学术中人,与郭、范、翦、吕四人相比,他的书生气最重,这大概是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中国思想通史》较少时代、时势痕迹而能传世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郭沫若最早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古史研究,侯外庐、范文澜则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的建立做出极大努力,成就斐然,翦伯赞、吕振羽在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方面建树颇多。
一、侯外庐与杜国庠
早在1931年,侯外庐开始与杜国庠通信。“那时我们都在搞翻译工作。我看到他用林伯修、关念兹笔名译的书,托某书店转寄他一封请教的信,内容主要是我翻译经典著作因了水平幼稚搞不下去了,冲不破难关。杜国庠同志的回信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他讲了一套有关边干边学的道理,结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都在学习的萌芽阶段,谁也不敢说译品成为定本,试做总比不做好,应准备做后来者的桥梁。”[3]
但侯外庐正式结识杜国庠,是在“文工会”。1940年12月,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成立,“文工会”团结的面比其前身第三厅更为广泛。它虽然是一个“研究机构”,但它的成员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或著书立说,或讲学论争,或从事文艺创作。他们广交朋友,联系群众,以学术文化活动的方式,造成健康的社会舆论,启发民众的政治意识,推动民主运动发展。“做学术讲演的人很多,有内部的,如郭沫若、杜守素等;也有兼职委员,如王昆仑、侯外庐、老舍等。王昆仑曾讲《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等,侯外庐讲过先秦诸子,老舍讲过北京的方言。”[4]在赖家桥,杜国庠和侯外庐交换过从先秦到近代一系列问题的见解,彼此发现是知音,越谈越深入,越讨论越细致。“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国封建社会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的问题。杜老问我,分界线应该划在何时。我说,不好用一个年代或一个事件来划分,应该存在一个过渡期,那就是唐中期,肃宗、德宗时代。杜老对此是同意的。又谈到唐代思想史,我说,柳宗元是有唐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最典型代表,他也极表赞成。”[1]“文工会”开展了许多学术交流活动,杜国庠做过《关于墨子》《公孙龙子》《明末清初顾、黄诸大师的学术思想》等学术演讲。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他为后来写作《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和与侯外庐等合著《中国思想通史》做了准备。
此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其他学者的论辩此起彼伏。抗战时期,冯友兰建立了由“贞元六书”构成的“新理学”体系,引起了社会关注。杜国庠发表文章批判冯友兰的“新理学”,侯外庐后来在《杜国庠文集·序》中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杜国庠同志还对冯友兰先生的著作《新理学》《新原道》《新原人》等宣传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辩论。”[5]
炎性细胞因子IL-8对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术后复发的预测价值初步探讨(吕立辉 康洪涛 王春河)2∶93
二、侯外庐与郭沫若
侯外庐在自己关于屈原评价的文章中也提出了与郭沫若不同的观点。论战是由郭沫若创作完成的关于诗人屈原的历史剧而触发的,历史剧《屈原》的主要内容是楚怀王与诗人政治家屈原之间围绕着反抗秦国还是与秦国合作问题而展开的斗争。那位没有能力统治国家的国王准备妥协,而屈原则怀有“高贵的统治者”的幻想,公开而且无畏地主张抵抗,不过他没有采取积极行动来反对国王,以至于最终失败,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个历史剧不光号召抗击外国侵略者,在当时也特别号召抗日,而且也以楚怀王其人映射蒋介石没有能力也不愿抗日。郭沫若作《屈原思想》连载于《新华日报》1942年3月9日第4版及3月10日第3版和第4版。该文系与侯外庐商榷屈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周恩来读后致信郭沫若:“……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质之你以为何如?”[14]4月,侯外庐的文章《屈原思想的秘密》在《中苏文化》上发表。在论战中,首先涉及对屈原的世界观和方法的评价。郭沫若认为屈原的世界观是进步的,而他的方法,即消极反抗是反动的。与之相反,侯外庐认为,屈原的世界观,即他对于“高贵的统治者”的信赖是反动的,而他探求真理的方法却是进步的。
侯外庐在与郭沫若交往中的友谊与学术分歧,从以下的几次讲话中可见一斑。1945年4月,重庆各党派领袖和文化界人士设宴慰问郭沫若和文化工作委员会诸工作人员,侯外庐与沈钧儒、左舜生等相继发言。侯外庐认为:“郭先生在文化学术方面的伟大贡献,使他不但是中国的权威,也是世界的权威之一,他几十年来奋斗所得的文化成果,给了我们许多不朽的著作,我们相信郭先生今后还要更多创造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作品。在欧美各国,最有成绩的学术研究机关,差不多都不是官办的,就是苏联,有名的学者也独立发展其研究,如瓦尔加的经济研究所。”[6]又,阳翰笙记载:“侯外庐先生主张在郭先生的领导下,创立一民间性的文化研究所。”[7]6月8日下午,中苏文协、全国文协、全国剧协举行欢送郭沫若等赴苏联访问的大会,侯外庐与邵力子、茅盾等致辞。侯外庐在发言中提出:“郭先生是中苏文协的领导者之一,郭先生在中国学术上的成就是没有能出于其右的。相信郭先生必能有很好的成就,且必能把苏联学术上的成就和他们的精神带回中国。”[8]8月,郭沫若在莫斯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历史哲学组演讲,郭沫若谈道:“在研究这一时期的哲学问题及其他思想形态问题的中国历史学家当中,侯外庐占据了最显要的地位。不久以前,他发表过《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二书。他认为周代是奴隶社会,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解和我是相符的,但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的许多问题,我们之间就有了本质的分歧。”[9]
综上所述,现金的控制和其流动的监控作为关乎公司经营、发展重点因素及战略决策实施的重点保障,其管理发展要格外注意。只有降低其存在的风险,企业才能平稳的在激烈的战争中保留一定的生存力、甚至获得扩大发展的动力。企业要实时关注市场动态,同时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在最短的时间内拟定一套详细的、合法的管理法规,从而实现企业资金的价值最大化,并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培养体育核心素养,可以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健康调节能力,现代的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很大,若不具备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会产生各种心理疾病,这就要求每一个个体都要具备健康的心理调节能力,增强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4)会意字的教学。在教授会意字时,应注意让学生在理解汉字各部分所代表的意义后记忆生字,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葬”字,本义是人死后盖上草席,用棺木埋入土中,教师在在教授“葬”字时可以将“葬”字的上中下部分联系起来帮助学生记忆。
(一)侯外庐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之比较
第三,关于“封国”非封建制度。侯外庐指出:“东方的王公诸侯,没有封建的影子。封建一词,日文袭中国文而译西文的费地阿里斯模,复由日文之译语,贩入中国,于是两合,封建便出于西周。”而实际上,“‘封’在殷周之际,是以树木分略疆界之谓,没有‘爵诸侯之土’的一点痕迹”,“不论从周金的文字,或从《周书》《诗经》的文字,赐、命、令、锡等文,殊为习见,而爵封则未一见。”“周代同姓诸侯之‘封建’相似罗马的殖民制度无疑,而异姓诸侯之‘封建’则不过自居于盟主地位罢了。”[12]因此,周之“封建”同作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封建制度”是截然不同的。
侯外庐称赞屈原是“中国历史中最可模范的人格”,这一点上,与郭沫若评论屈原有相同的认识。侯外庐在《屈原思想渊源的先决问题》一文中说:“关于中国周秦社会史的论断,我和郭先生虽然各有重点的注意,大体上是站在一道的,没有这个相接近的观点而研究屈原思想的渊源,好像如韩非子之评儒墨,‘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15]侯外庐又道:“关于屈原问题,四十年代我和郭老在认识上有三个共同的基点:其一,由于当时我们都认为封建社会始于秦、汉之交,所以一直地把春秋战国看作大转变的时代,封建制在难产中的时代。……其二,我们都确认屈原是儒者。其三,我们都肯定屈原人格伟大,屈原诗篇不朽。”“我们的分歧的核心在于:对于作为儒者的屈原,他‘问天’‘招魂’所寓之理想,究竟是‘以德政实现中国一统’,还是前王之制的魂魄,说得再简单些,究竟是社会进步的理想,还是倒退的奴隶制残余的梦想。”[1]
一碗拉面只吃了少半,吕凌子埋了单,重新返回物业公司。物业办公室那位名叫小雪的年轻女孩正在擦拭玻璃门。吕凌子问她陈主任来了没,女孩说还没来,招呼吕凌子办公室里坐。吕凌子没进办公室,她决定在门外候着,守株待兔。小区内环境优雅,秋日的阳光异常干净,洒在沾满露水的花草树木上,熠熠生辉。
第二,关于西周的土地所有制。侯外庐认为,“周代,已从殷代牲畜为主的社会,发展至土地农业生产的时代”,“土地国有制是周代的特点”[11]。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下,“因氏族贵族独占,生产力难以发达,未能产生典型的生产手段私有的显族。生产手段既为氏族贵族所有,则其所得形态,便是‘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故赋税与地租未能分开”。侯外庐还认为,《诗经》所言甫田、大田,“是鄙野之公田”,地块较好,在当时形成很大的规模,但“南亩、十亩,则可能为小生产市民如百姓、国人、士人之使用田,后者当然是土地制度的从属意义,支配者还是前者。西洋古典社会,也不是清一色的,自由民亦有其一分的”。“因此,‘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私亦不是自由买卖的私有土地,至多是在鄙野大量土地以外的自由民使用之小块田。”[12]
她对敬老院的老人和他们的儿女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家人该说的话,做家人该做的事。”因为化解了不少家庭矛盾,她获赞颇多,每次都不忘把这些赞扬美滋滋地和我分享。
在20世纪30-40年代,郭沫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首先站出来对儒学表示同情,大胆肯定儒学的现代价值,对于扭转一味批孔的偏激心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郭沫若关于儒学的看法,感情色彩比较重,这限制了他研究的深度。侯外庐、杜国庠等人弥补了这一不足,运用唯物史观对儒家思想做了比较客观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在历史断限上,侯外庐认为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起始于周初,终于秦汉之际。即是说,侯外庐也是个西周奴隶社会论者。不过,他的一些见解与郭沫若颇不相同,他有着自己的特色。他的主要看法是:
侯外庐充分注意到西周社会生活中氏族制的存在和土地私有制的不存在,是比较尊重中国史实际的,但他简单地认为靠“征服”整族整族地制造“集体族奴”,是有违西周史的。
西周封建社会论者与西周奴隶社会论者有过激烈的论辩,西周封建社会论者在反驳郭沫若以可以赏赐、买卖为由把“众”和“庶人”视作奴隶这一点上,是颇为成功的,因为,按斯大林的说法,农奴也是可以赏赐、买卖的;但他们把西周广大农业生产工作者视作农奴,特别是像翦伯赞那样,居然可以简单地、不加分析地说周灭商后,“首先便宣布土地王有,和奴隶制的废除”,诸侯们“一到封区,便把封区以内的人民,不问其为殷族,或为‘夏族’,不问其为自由民抑或奴隶,便把他们整族整族地转化为农奴”,同样是没有多少依据、缺乏说服力的。
郭沫若之失主要有二:其一,上面讲过,他把“众”“庶人”说成奴隶的主要依据不外乎这些人可以被赏赐、买卖,而仅凭这一点,是划不清奴隶同农奴之间的界限的。其二,把广大劳动者普遍化为奴隶。在郭沫若看来,西周社会除了奴隶主外,就是尽人皆是的奴隶。如果真是这样,西周岂不成了比希腊、罗马还要希腊、罗马的典型纯粹的奴隶社会了吗?因为,在希腊、罗马,除了奴隶主、奴隶外,也还有自由民的存在。当然,郭沫若这样说的时候,他自己也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不得不承认西周的奴隶与雅典颇不相同,承认后者“是无身体自由的”,而前者却和斯巴达的黑劳士一样,“有充分的身体自由”,“显得那么自由”。可到头还是借什么土地的“缧绁髡钳”作用,把这些“有充分的身体自由”的农业生产者一个不剩地全部划为奴隶。这种做法,实际是抱着奴隶社会的先入之见,硬在古代中国社会寻找奴隶,放大奴隶,制造奴隶。
第四,关于西周劳动者的身份。侯外庐认为,周人对殷人及其他族的不断征服,把大量的“俘族”“大抵全族转为生产者”,转为“族奴”,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井人等等;康王时期《麦尊》锡臣可多达“二百家”,足见他们是用于生产的,“因为家内奴隶是用不着这样大的数目,尤其在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之下”。金文中“锡田常与锡人并提,这种叙法正是土地与生产者的结合样式,并非偶然的事件”[12]。通过以上的对比与描述不难发现,周代生产者其实为集体族奴。
(二)侯外庐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之比较
侯外庐相继完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的撰著,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奠定了他在思想史领域的地位。为了尊重合作者的意见,《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一些独到的见解未能在《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中充分显露。如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侯外庐对孔子的看法同郭沫若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郭沫若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孔子倡导的日常生活中言行的指南。这里的“仁”是一种“牺牲自己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13]。对于孔子思想体系内核的探索,持不同观点的侯外庐则认为“立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孔子信奉的言行守则。孔子的仁政,从一般道德律的角度看,具有国民的属性,但是,每当触及具体的制度和传统观念时,“仁”的道德律又是“君子”所专有的了。
郭沫若和侯外庐的性格迥然有别,郭豪放外向,侯则矜持内向,他们的生活情趣也不尽相同,但是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他们却是同路人,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郭沫若比侯外庐年长11岁,当1921年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时,侯外庐还是一个中学生。1923年,东渡日本后,郭沫若潜心研究并广交朋友,利用自己的日语优势,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侯外庐当时虽然也已经读过一些陈独秀、李大钊等撰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由于书读得太杂而又无人具体指点,竟至于误入“孙文主义学会”,并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解放。1924年郭沫若回到上海,次年目睹“五卅惨案”,结识了瞿秋白,并与恽代英、张闻天、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从此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在他的带领下,创造社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1926年2月,郭沫若应聘去革命的中心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后参加北伐。这期间,侯外庐在同乡的引荐下认识了李大钊等革命人士,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他在参加学生运动的同时,开始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化名旅居日本千叶县市川市。此后两年间,他开始从事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史研究,并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其后,陆续出版《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书。侯外庐1927年赴法国求学,1928年开始试译《资本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郭沫若和侯外庐早年经历的对照,不难看出,在他们结交之前,郭沫若无论在政治上、理论上和学术上,其起步和成熟都比侯外庐要早。侯外庐在回忆录中说:“郭老对我,一向若师若兄。”[1]这既是他的肺腑之言,也的确反映了他们之间诚挚的友谊。20世纪30年代以后,郭沫若和侯外庐等新哲学接受者的理论水平有更大提升,他们既接受唯物史观,也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他们沿着李大钊开辟的研究方向,更为深入、更为具体地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取得了更大的成绩。
第一,关于周代的氏族组织。侯外庐注意到:“不论在希腊或罗马……氏族的血缘政治,后来都被土地私有制所冲破,财产贵族与国家机关代替了经济政治混合于血族的制度,……中国的古代制度颇有些特殊性。”“周代社会,……国家成立是没有疑问的,而其组织则是有它的特色。”这特色便是“土地制度的所谓‘国有’形态”和“周代政治成了绝对的家族长大氏小宗的贵族政治”。侯外庐强调:“民与氏是国家的两个基本条件”,“周代是以姬姓氏族为中心,而联合了其他氏族如曹姓、子姓、姜姓、己姓、姒姓、任姓诸氏族,而形成氏族联盟”,“周代的奴隶制则主要是氏族奴隶”。与希腊社会的“打破了氏族组织”不同,“周代则始终维持着氏族宗法制度”。正是由于“过时的氏族枷锁之于中国古代社会之束缚,……由于氏族古制的保存,使社会的变革,难以明朗化,走了长期转变的道路”[10]。
总体上来说,“以马释中”作为20世纪诠释中国哲学的主要范式之一,与郭沫若、侯外庐的成就与影响密切相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二人主要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解读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虽然他们都没有通史性的哲学史论著,但他们将哲学问题一般地内置于思想史之中,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对中国哲学史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侯外庐和郭沫若研究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历程,是当时史家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缩影。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侯外庐与郭沫若学术观点的异同较有代表性,以下简要分析。
总之,侯外庐与郭沫若在对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领域的研究中用力颇深,学术观点各有不同。郭沫若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对侯外庐的影响非常深刻,不但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逻辑架构等方面给予侯外庐以启示,而且他在古文献、古文字和考古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地上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相互印证的创新理念,以及对古史研究中疑难问题的大胆论断,也都开阔了侯外庐的眼界。此外,侯外庐与郭沫若不同的治学特点、不同的研究旨趣、产生的不同影响和贡献、二人之间的互相借鉴与促进,以及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丰富与促进,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今后做进一步研究。
三、侯外庐与翦伯赞
侯外庐与翦伯赞相遇在重庆《中苏文化》杂志。侯外庐是由西安经汉口到达重庆,然后通过孙科的代表王昆仑,进入《中苏文化》杂志。这时,翦伯赞则是“中苏文协”湖南分会的实际主持人兼湖南分会机关刊物《中苏》半月刊的主编。翦伯赞赴重庆前夕,在侯外庐主编的《中苏文化》上发表论文两篇。翦伯赞来到重庆后,以湖南中苏文协分会负责人的身份补为总会理事兼杂志副主编,身份和职守与侯外庐完全相同,住处也相邻,由此开始了他们的交往。侯外庐在晚年的回忆录《韧的追求》一书中,特辟一节“翦伯赞的风格”,追忆翦伯赞。对于这段追忆,与翦伯赞甚熟的刘大年说:“翦老这位挚友出于肺腑的对他的评价,公允精当,不可移易。”[16]侯外庐和翦伯赞是同辈、战友、同志,但《翦伯赞的风格》一节,侯外庐却是带着十分推崇的感情写出的,不但写活了翦伯赞,而且感人至深。这是迄今为止对翦伯赞最传神而又最洗练的概括评价。这一概括评价不但在刘大年看来“公允精当,不可移易”,与侯、翦都过从甚密的胡绳也“感到外庐同志对他们二人间的关系的描写是非常恰切的”[17]。
侯、翦之间彼此推崇,但并未成为至交,他们的“彼此推崇”,是建立在理性——“我们确乎是真正认识对方价值的”基础上的。[18]看来影响他们深交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们学术观点上的对立。所以,侯、翦之间有“隔阂”,完全可以理解。侯、翦之间的学术分歧主要表现在:在重庆时期,侯主“秦汉封建论”,翦主“西周封建论”,而且,侯外庐在论战时,主要以翦伯赞为目标。[19]侯外庐说:“我和伯赞在中国古代史分期、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很大,这是众所周知的。”[20]
经翦伯赞介绍,覃振的部分家眷亦住到白鹤林,侯外庐从此与覃振相交。距翦伯赞居所只有二三华里的山清水秀的白鹤林,就是王昆仑、曹孟君夫妇和侯外庐全家的居处,王昆仑、侯外庐两位是翦家的常客。住在赖家桥的郭沫若、于立群夫妇,还有郑伯奇、杜守素、白薇,住在北碚的吕振羽、张志让、周谷城以及陶行知、邓初民、章伯钧等也经常前来,周恩来、冯玉祥、鹿钟麟、覃振等也来过。至于追踪而来的记者,慕名而来的大中学生,几乎络绎不绝。对于翦伯赞来说,送往迎来都是革命工作。除此之外,翦伯赞的主要任务是讲理论、写文章、著书、立说。
另外,侯外庐与周恩来以及周恩来对活跃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圈所起的作用,值得一提。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领导核心的中共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抗战和学术研究而困难重重的进步学者,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实在难能可贵。身居重庆的侯外庐、郭沫若、杜国庠、翦伯赞、吴泽等人或创办进步刊物,或撰著、编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其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或发起成立“新史学会”,以特殊的方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新发展。这一阶段,侯外庐的交游非常广泛,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与社交活动,接触的人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为了保存干部,为将来新的战斗做好准备,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在重庆亲自部署和指挥党内外人士撤离。同时要求在大后方的党员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就是要“闭门”读书,开展业务活动,深入学术研究,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实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侯外庐想去延安,周恩来觉得去延安太冒险,建议他留下来抓紧时间研究学术。
1941年,中共和周恩来组织“读书会”,约两周一次,侯外庐和许涤新、胡绳等人为经常出席者。据《韧的追求》载:“当时我们这些同志,个个都把唯心主义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来了,……他平静而中肯地对大家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1]针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学界斗争的严峻性。翌年,侯外庐、杜国庠等成立“新史学会”,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队伍壮大了,新史学具有新的特点。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等著名学者都来参加活动,互相砥砺切磋,气氛很活跃。有一段时间,重庆、香港一些文化工作者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写真实”有不同意见,发表一些批评文章。[21]周恩来明确表示这是内部问题,他强调要培养良好的学术作风,认为学术上的问题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绝不能强加于人。周恩来的观点对侯外庐等人的学术导向产生一定的影响,侯外庐言:“如果说,我一生还曾取得一些成绩的话,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便是,我受到过周恩来同志的教导,我在那个环境中得到过支持,得到过锻炼。”[1]
今年由梅多克士族名庄联盟主席带队、一个由 36 位庄主组成的代表团近期亲临上海、北京和深圳3个城市,他们向数百位专业人士和记者介绍了近年来最优秀的年份之一——2015年份,同时梅多克士族名庄联盟主席奥利维·库维利耶(Olivier Cuvelier)先生宣布正式启动梅多克士族名庄分级制度,并详谈了酒庄甄选的条件及其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周恩来身在重庆,他在国共合作方面所做的努力,得到了国共双方及民主各界人士的认可,证明了共产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襟怀和至诚,对于全民抗战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侯外庐回忆:“刘仲容晚年有一次和我谈起周总理个人人格与形象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他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1]这句话很能反映周恩来对于统一战线所起到的非凡作用。
参考文献:
[1]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1985.
[2]刘茂林.抗战时期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苦心经营[J].郭沫若学刊,1988,(1):28-35.
[3]侯外庐.忆悼杜国庠同志[N].光明日报,1961-02-08(3).
[4]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6.
[5]杜国庠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
[6]在不自由的狭小天地中——欢宴文化战士郭沫若[N].新华日报,1945-04-09(2).
[7]阳翰笙日记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369.
[8]中苏文协等三团体欢送文化使节郭沫若[N].新华日报,1945-06-09(2).
[9]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J].中国学术,1946,(1).
[10]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上海:新知书店,1948:160.
[11]林甘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30.
[12]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5.
[13]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77.
[14]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216.
[15]王锦厚.百家论郭沫若[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484.
[16]翦伯赞纪念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2.
[17]卢钟锋.侯外庐纪念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4.
[18]李侃史学随笔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8:504.
[19]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J].历史研究,1959,(4):45-59.
[20]胡绳全书: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20.
[21]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05.
ExchangeandDebateBetweenHouWai-luandOtherMarxistScholars
ZHOUXin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Southern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Zhou Enlai as the core of leadership, united a large number of progressive scholars who were interested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and created an academic atmosphere for them to work hard and innovate. As one of the leftist cultural leaders at the time, Hou Wai-lu enhanced his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oretical level in his exchanges and debates with other Marxist scholars. Hou Wai-lu's great contribution to Marxist historical science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 many of his inferences drawn from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ical science are still of practical values.Historical scholars today still follow his method of integrating 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with the study of ideological history, and his advocacy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and to"think independently".
Keywords:Hou Wai-lu;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independent thinking;Marxist historical science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19)01-0032-09
收稿日期:2018-09-3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第63批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8M633635XB);贵州省领导指示圈示课题(QSBSHYB2017030)
作者简介:周 鑫,男,江苏东海人,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经济思想史。
责任编校:王彩红,陈强
标签:郭沫若论文; 屈原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史学论文; 中国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博士后第63批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8M633635XB) 贵州省领导指示圈示课题(QSBSHYB2017030)论文;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论文; 北京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