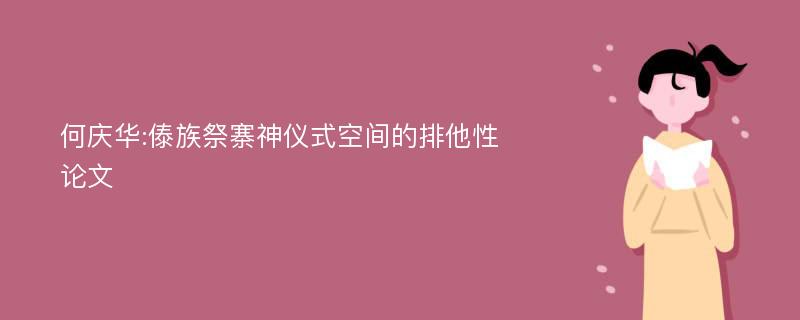
摘 要:傣族祭寨神仪式期间,傣族人物理的现实时空进入宗教的神圣时空,使村寨形成一个封闭的神圣空间。相对于村寨空间,寨神居住的寨神林空间在宗教体验上则更具神圣性。祭寨神仪式空间把佛和寨外排除在外,寨神林把寨内的女性排除在外。村寨内外、寨神林内外的空间安排,反映了傣族祭寨神仪式空间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充分体现了集体表象的功能。
关键词:傣族;祭寨神仪式;神圣空间
以空间关系来定义仪式是宗教人类学的新做法之一。①D.Parkin,“Ritual as Spatial Direction and Bodily Division”,in Daniel de Coppet,ed.,Understanding Rituals,Londan:Routledge,1992,pp.11-25.本文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腊镇曼旦村为田野点,运用该村祭寨神的田野材料,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探讨傣族祭寨神仪式空间排他的特性。文中涉及两类空间现象,第一类是指定点上的神圣空间——寨神林;第二类是仪式活动期间使得曼旦村转换成超时空的神圣空间。
一、曼旦村祭寨神的物理空间和物理时间
(一)物理空间
曼旦村世居民族为傣族,傣族村落的基本空间形态和布局思想,其一,受原始宗教的集体思想影响,使村寨空间呈现出封闭的形态,这一形态有利于民族凝心聚力;其二,“万物有灵”使傣族人认为,村寨与人一样是一个生命体,应有头、尾和心脏,呈现出人格化的特点。因此,设寨头、立寨心、定寨尾,成为傣族村寨的三个节点。这三个节点决定村寨的空间、控制村寨的走势。每个傣族村寨都有四道寨门,四道寨门围合的空间使村寨内与村寨外形成分界线,使傣族村寨空间呈现出稳固、内向、封闭的特点。寨头有茂密的树林,在树林中建一简易的凉亭,并设供台,这是寨神的居住地,也是祭祀寨神的地方。寨神是村寨的保护神,傣语称“丢瓦拉曼”(傣泐语音为teuvalamwan),寨内所有人与物都受寨神保护。祭祀寨神,傣语称“灵披曼”,直译为养寨鬼,是一项全村寨的集体活动。在村寨的中心处有石砌台,是村寨的心脏,傣族有一说法,叫“寨心不烂,寨子不散”。寨尾在寨头相对的位置,有一道寨门通往寨外,寨门外有一片坟山,这道寨门有通往黑暗的寓意。凡出殡,必经寨尾,不得过寨头,因为寨头象征光明。寨头、寨心、寨尾构成了一条控制傣族村寨空间序列和空间组织的依据,三者贯穿整个傣族村寨。
(二)物理时间
勐腊镇各村寨祭祀寨神的时间并不固定,大概在傣历的十二月或一月。曼旦村祭寨神活动隔一年举行一次,祭寨神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村寨的平安和洁净,将不洁净和危险因素从村寨中祛除,留下洁净的村寨内部空间,同时也有祈神赐福的含义。②参见艾菊红《西双版纳傣泐的居住空间结构及其认知逻辑》,《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此次祭祀订于傣历一三八零年十二月初八(公历2018年10月17日),祭祀期间封寨3天。曼旦村的寨神有两位,名为“达岭”和“达董”,他们是父子俩,在曼旦塔上有碑刻记载:建寨之初,森林里有大蟒蛇出没,见人吃人见马吃马,父子俩将蟒蛇制服后被封为寨神。寨神会附在“咪蒂嚢”①“咪蒂嚢”意为垫坐的女人,相传是寨神的座椅,鬼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身上,“咪蒂嚢”是女性,而且是村里的老人,只有“咪蒂嚢”才能与寨神沟通。寨神会通过“咪蒂嚢”指出谁是“波么”。②“波么”指傣泐村寨中主管原始宗教的祭司,与“波章”对应,两者的职责不同。“波么”会在自己的家里建一龛安置并保护寨神,形成村民与寨神的通道。如果谁家有事需要祭拜寨神,就要带上一两元钱和一对蜡条去请“波么”求神来保佑。
祭寨神仪式过程中,最重要的时段有:其一,封寨。封寨的时间定在仪式前一天傍晚,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上门的男性、出嫁的女性以及在村外干活的村民都要在封寨前进寨,否则不准进寨。其二,祭祀。“波么”带领寨内的男性村民到寨神林进行祭祀仪式。其三,请寨神。请寨神仪式举行并不意味着寨神会到来,据说曼旦的寨神于傣历一三七九年(2017年)泼水节来过,这是多年以来出现的一次。
祭寨神仪式过程将村民们从日常作息的时空中疏离出来,进入一个异常的时空隧道,亦制造一个全新的时空架构,使村民们产生错觉,而在心理状态上有所松动,准备进入非现实的氛围中。这是为要来的神圣体验作准备,再加上仪式的引导,使每个村民进入超越时空的神圣世界中。
二、祭寨神神圣空间的进入与离开
封寨、寨神林祭祀和请神三个仪式的举行均有一定的空间划分,且严格限制参加人员。从田野观察中我们看到,祭寨神仪式中,空间被有意分割。
分布在南部垣曲—绛县一带(即中条山成矿区)。均为小型矿区。有垣曲县宋家山矿区、马蹄凹矿区,绛县南华沟—回马岭等。
(一)关于时空方面
时间上:祭寨神之前,要派专人制作一种竹编神器,傣语称“达寮”。③“达寮”,即用竹篾编的网状六角形器物。这种器物具有驱鬼除邪的作用,在很多祭祀仪式上都有“达寮”。da是“眼睛”的意思,liao有“监视”的意思。参见朱德普《傣族神灵崇拜觅踪》,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29页。它是用竹子编成的“七眼星”,傣族人将其比作“带刺的眼睛”。“达寮”四周凸出呈尖状,尖状物有吓跑恶魔的意向,达到辟邪驱魔的作用。在傣族人遵循的观念中,它被列入显要的圣物之中。村长带领几个民兵封寨,在寨门处挂上用竹木制成的刀和“达寮”等物件,用障碍物围堵,由“细梢老曼”④“细梢老曼”指滇南南传佛教流行区域傣族村寨中处理村寨纠纷、传承伦理道德的民间组织,由4个老人担任。傣语直译为“村寨里的4 根柱子”,是傣族传统聚落空间观在社会组织结构上的转附。同时,也是这一非正式社会控制制度中传统权威执行者的称呼。拟订关寨门告示挂在寨门处,宣布:“祭寨神之日,任何人不得闯寨门入村寨。三天后撤‘达寮’,放人通行。”⑤阎 莉,莫国香:《傣族寨神勐神祭祀的集体表象》,《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每家用草绳和棉线编十几米长的线,再将其拼接起来,绑上木棍,形成象征性的寨墙,把整个寨子封起来,将寨内与寨外区分开,目的是使鬼和邪灵不敢入内。即刻起,村寨不仅是一个物理性质的居住空间,而且已由人们的居住空间转化为神圣空间。封寨期间限制外人闯入,不允许本寨人出境。若有人进出的话,不仅对寨子不利,对自身也不利,只有对进出人罚款后方可消除厄运。
粗锡或焊锡中的锡和所含杂质具有不同的沸点,控制温度在锡的沸点以下,在杂质的沸点以上,可使杂质挥发除去。各元素的沸点见表1。
这一声“姐”,道出学生对我教学的充分肯定,只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如同玫瑰花蕾绽放有早晚之别一样,孩子的成长也有快慢之分。我认为在学习中表现欠佳的所谓“差生”,只要善于引导,他们和优秀生一样都存在巨大的学习潜质。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学生,努力用爱心、耐心去关注每一个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在我的鼓励与陪伴中,我任教的每一届学生都能在学业上实现大幅度的自我提升。
仪式是时空的展示,但仪式自成体系和格局。就时间而言,时间制度在仪式当中的表现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有所不同,它经常是抗拒物理时间的一种表示。 在祭寨神仪式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被完全打破,仪式正好是物理时间的反叛。至于仪式中的空间概念同样复杂,我们所说的“时间/空间”概念与制度在具体的分类和分析中多少带有人为因素,以便于人们看待和认识上的清晰化。 仪式中的时空制度和关系更符合一种特殊的结构。日常时间的打破和日常空间的限定,使得村民进入祭寨神的仪式时空中。“神圣/世俗”之于仪式的实践而言,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①参见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14页、第317~318页。
(二)神圣与世俗的空间转换
祭祀寨神有严谨的仪规,在祭品、时间、人员、程序上均有体现。这次大祭,主要牺牲为一头长相健壮、没有伤疤的白猪,其他牺牲为黑鸡、白鸡各1只,鸭1只,还有日常生活用品,用于祭祀后便有了神圣性。祭寨神的地点为寨头的寨神林,只有男性村民能参加祭祀,他们每人背一白色布包,装有餐具、糯米饭、酒等吃食。约早上8点,“波么”带领大家到寨神林,老人们带着几个人杀猪和鸡鸭。朱德普在《傣族神灵崇拜觅踪》介绍了宰杀白猪的规定:头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前腿拴在一棵神树上,后脚拴在两个小木桩上。“波么”对猪进行祝祷,再用长刀杀之。古规曰,杀猪要杀三刀,但不能将脖子砍断,否则主凶;第一刀下去势必致死,前脚跪伏于地则大吉;若头朝寨子、四脚倒地则大凶;若猪未死,乱叫、乱跳,则认为不祥之兆,地方将乱。第二、三刀只是做个样子。然后,迅速将猪剥皮去内脏、肢解,又将猪血堆在祭台前,猪皮覆盖着猪头。“波么”主持祭礼,先向寨神敬酒,后祈求寨神佑护村民人畜兴旺、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诅咒邪魔被驱除扫尽。③参见朱德普《傣族神灵崇拜觅踪》,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44页。祭礼完成后,大家在寨神林里吃饭、喝酒、打牌,除鸡鸭、猪头、猪脚要带回村寨以外,其他的都在寨神林里吃了。女性村民则在家等候男性村民归来,约下午3点,所有参与祭祀的男性村民从寨神林返回村寨,寨子里开始娱乐。至此,祭祀从肃穆转向狂欢。有些男性村民把鸡鸭、猪头、猪脚带到“波么”家,准备晚饭。饭后,“咪蒂嚢”被邀请到“波么”家,“赞哈”唱起请神歌,请寨神来附“咪蒂嚢”的身,遗憾的是这次寨神未显灵。
信仰与仪式是涂尔干所认为的宗教现象的两个基本范畴,在其中,所有事物都被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神圣事物,另一类是凡俗事物。从表象上看,这些事物几乎都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东西,但某物只要被赋予神性,即变成神圣事物,其涵义异于凡俗事物。图腾就是这样一种事物,如澳洲某些部落崇拜的“储灵珈”。②在涂尔干看来,“储灵珈”原本只是普通的小块木头或磨光的石头,但是当被刻上表现该群体的图腾图案之后,它就由俗物变成了圣物,以至于人们要将它置于特殊的地方,被赋予神奇的性能,整个氏族的命运与这种圣物休戚相关,如果被丢失,将会是一场灾难,是氏族最大的不幸。作为一种普通的物件,“储灵珈”的功能和作用不是来自于它本身,而是图腾赋予的,作为图腾的载体发挥作用。参见[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梁敬东,汲 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45~159页。在西双版纳广泛流传一句俗语:“家长死后当家神,寨子首领死后当寨神,勐的首领死后当勐神。”这表明,寨神是曾在村寨里生活过的人,只是他们对村寨的建立有特殊贡献或重大影响。寨神指建寨的首领,或搬迁后立故土之主为寨神。尊为寨神之前,他们与凡俗之人无异,被奉为神灵后,就拥有至高无上的名望,人们将其编入神话传说中,并赋予其超自然力量,制服鬼怪、战胜恶魔。他的神圣性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由此他们从人升华为神,帮助人们生产和生活。所以,寨神的神圣性是被建构的结果,而不是自古有之。
空间上:祭寨神仪式期间,被围合的整个寨子成为神圣空间。祭期内不事生产,妇女纺线做针线也在禁止之列,牛马猪鸡要拴好关紧,不得骑车、放音乐,一切皆为表示对神的敬畏。祭神前要打扫屋内外,至祭期衣着整洁,不得挑扁担(“神役”不受此限),前往祭坛参加祭祀者穿戴不得违例(一般均身穿青色、蓝色,忌着红色,“波么”则多穿红衣红袍)。所有这些规范代代相传,成为傣族村民相互监督的制约力量和习惯强制力。
2.祭寨神仪式空间的神圣——世俗转换
(1)从寨外入寨内
村寨界限是区别神圣与世俗两个对应世界的分界线。寨门在这里既是通往神圣之地的空间象征,也是世俗世界得以过渡到神圣世界的通道。
(2)从寨内入寨神林,再由寨神林返回寨内
1.寨神是由世俗的转换为神圣的
(3)从寨内出寨外
“细梢老曼”定于傣历一三八零年十二月初十下午开寨门,“达寮”及障碍物被丢弃,寨子恢复日常。列维一斯特劳斯在其著作中提到,人类学认为空间因素是人类唯一的限制。①[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60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圣俗之间未产生足够的“间离空间”,崇高性便无法生成。②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18页。从寨外—寨内—寨神林—寨内—寨外的空间转变中,寨内和寨神林这两个空间与其他的空间“割离”开来,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意义。寨神的祭祀活动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感染力,寨神是村落共同体的象征,成为傣族人民的精神核心和联系社会关系的纽带,也是傣族地区长期保存村社组织的重要因素。③参见张公谨《傣族社会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第16页。
(三)寨神的显灵
封寨期间,寨子对村民来说不是一般世俗的体验空间,而是形塑出来的一个神圣空间。而昔日的宗教经验中包括有寨神的各种显灵事迹,所以村民脚踩在这个神圣空间的土地上,逐渐与寨神的神灵结合,这种结合到寨神林祭祀时到达最大限度。
健康与旅游(或度假)的关系首先得到了医疗领域学者的关注,有许多成果发表于国际刊物Journal of Travel Medicine上,但是研究的关注点是旅行中的疾病问题,例如旅游者容易感染的地方病,或者旅游中疾病的传播或扩散,其健康的概念主要集中在生理指标上。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健康成为了人们旅游的重要动机之一,健康旅游亦成为新的趋势,人们在旅游过程中寻求健康的主动性得以体现(Hall,2011),并出现细分的健康游客。这些健康游客对于健康的追求已经不局限于缓解压力,而是扩展到了寻求身体的舒适、积极的心态等方面。
当然,由于不是仪器的测量,这种推算公式不是百分之百的精准。一般来说,出生时的实际体重与预测体重会有正负10%~15%的误差。而越到怀孕的中后期,测出的指标越准确,对宝宝的生长指标也能有一个较好的了解。
寨神最近的一次显灵是傣历一三七九年的泼水节,寨神显灵时,女性不得靠近,“细梢老曼”请“咪蒂嚢”问寨神:“寨子里需要做些什么事情或是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现在曼旦水库被大修大建,这样好不好?对以后有什么影响?”若村民身体不适,也都请“咪蒂嚢”传话。据依香丙口述,在她上小学的时候,寨神显过灵,说是寨神告诉他们要建一个塔,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曼旦塔。曼旦塔是勐腊最灵验的塔,每年傣历四月都有很多人来赶塔。还有一次是奶奶患眼疾,到景洪住院治疗一个多月未愈。请寨神来,说:“在你们的桔子地里有一个洞,本可以供人避雨,但现在被填满了,因此奶奶的眼睛一直不好。只要把洞打扫干净,就会好的。”依香丙爷爷答应了寨神,第二天奶奶的眼睛就好了。有人说:“寨神附身‘咪蒂嚢’时,‘波么’给‘咪蒂嚢’倒酒喝,她喝完走了后,没有人再往杯子里加酒,杯子里又有满杯的酒,就是这么神奇。”似乎整个空间均笼罩在寨神的眷顾与法力下。
祭寨神仪式期间,村民们获得难得的放松和休闲的机会。 村民们在祭寨神的仪式空间里既“娱神”,也“自娱”。在此期间,寺庙则停止佛教仪式活动。村寨中的僧侣可以外出,不必参与祭寨神仪式。祭寨神仪式造成了村寨、村民与佛寺、僧侣的空间隔绝。
祭寨神空间承载着一群人的共同主观意愿,共同聚集回忆,共同一再咀嚼,共同期盼神圣的降临。曼旦村村民们借仪式的开始和结束,共同分享和创造这种神圣空间感。村民们在寨内、寨神林两个空间中共同体会寨神的神恩,共同沐浴在寨神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灵力下。寨神林就是Eliade认为的神圣空间,是神明显现的空间,是一个具象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神圣性是一直存在的,即使没人来祭拜时也不会减少。④参见M.Eliade,Cosmos and History,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1954,p.28.寨内则是Brereton所说的神圣空间,是举行仪式的地方。在举行仪式的时间内,一个普通空间变成神圣空间。⑤J.P.Brereton,“Sacred Space”,in Mircea Eliade,ed.,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vol.12,New York: Mac Millan Publishing Co,1987,pp.526~535.在傣族人的空间观念中,还有一个空间是无比神圣的,那就是寺庙。在祭寨神仪式中,形成了仪式内外两个空间,寨内和寨神林属于仪式内的空间,而寺庙则被排除在仪式空间外。
三、祭寨神仪式空间内的神与仪式空间外的佛
历史上,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来自社会外部,而原始宗教是本地原生的。对“神”的祭祀为土司和贵族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土司和贵族所要构建的社会是需要边界的,而土地就是有边界的,因而当地对“神”的信奉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本土性表达。而佛教对当地的渗透主要依赖于寺院系统,它不是任何一个社会独有的宗教,不属于任何族群。在进入任何地方社会的进程中,佛教从未失去过其作为普世的追求。所以,它超出了当地社会的边界,为各社会所同享。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西双版纳社会而言,南传上座部佛教仍保留了其作为他者的一面。20世纪50年代,西双版纳的土司制度彻底终结,但历经400余年沉淀下来的双重性观念结构并未被祛除。简言之,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社会的自我是在以原始宗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为核心的宗教关系结构中形成的。①杨清媚:《从“双重宗教”看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双重性——一项基于神话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在曼旦村,与宗教事宜有关的人有大佛爷、“波章”“细梢老曼”“波么”和“咪蒂嚢”。在这个体系中,他们与佛的关系依次疏远、与神的关系依次密切,他们的关系结构共同构成了曼旦村神与佛的空间观念世界。②参见杨清媚《从“双重宗教”看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双重性——一项基于神话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考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历史上,傣族人民认为,活着的人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原始宗教中寨神、勐神所规定和指明的道路;另一条是佛教所规定和指明的道路。③参见伍雄武《关于古代寨族的原始宗教》,《哲学研究》1983年第11期。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对原始宗教作了妥协和让步,并采取宽容、尊重和吸纳的态度。佛教非但不干涉人们对原始宗教的崇拜,在原始宗教祭祀场合,佛爷、和尚也常诵经祈福。另外,佛教又将原始宗教加入佛事中来,在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以及升佛爷、当和尚、祭佛塔、献经书等傣族重要仪式中,呼唤佛祖和原始宗教的四方神祇来同享供品。佛寺还有原始宗教的保护神,佛爷、和尚也有各自的保护神。西双版纳地区的献新米节原为原始宗教固有的祭神仪式,在每年稻谷收获后举行,现在却在佛寺举行,广场上还竖起佛幡,由佛爷诵经,请佛爷享用新米,并取了个佛教的名字叫“赕老轮瓦”,实际上已演变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活动了。④张公谨:《傣族社会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26页。
曼旦寺庙里有1个大佛爷、3个大和尚和5个小和尚。据小和尚岩宰香的奶奶介绍:“岩宰香当了小和尚后,只能睡在寺庙里,但可以在家吃饭。孩子入佛门后,就是佛祖的徒弟。”据“细梢老曼”波扁介绍:“寺庙是寨子之外的东西,不属于寨子。大佛爷、大和尚和小和尚入佛门,寺庙成为他们的家。过去,男孩子通常在8岁的时候便要入佛寺当和尚,他们在寺庙里接受教育,学习傣文化等。16岁升为二和尚,18岁能达到二和尚的标准,具备该社会成员应有的素质。此时他们面临继续升为大和尚,或者还俗回到村寨的选择。”⑤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53~254页。从二和尚开始是个分水岭,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越行越远。大多数人会选择回到寨神管辖下的生活空间——村寨,也有少数人会留在寺庙继续修行之旅。神与佛为二和尚准备的两个空间表明,双重宗教在傣族社会中共同起作用。⑥杨清媚:《从“双重宗教”看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双重性——一项基于神话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这些寨神显灵的事迹不断地在村民间传诵着,每一个场景均有特别的意义,都在与寨神进行心灵交汇。村民们期待自己能得到寨神的垂怜,希望寨神显灵。因此这一神圣空间是由神圣事迹和神话传说组成,是由人们的记忆和历史流程构成的。
四、被分割的祭寨神仪式空间
曼旦村如何经祭寨神仪式,由物理的现实时空进入宗教的神圣时空?这个宗教神圣时空的成立有三个因素:其一,在同一时空架构中,使村民们在村寨内有时空视错感;其二,神圣与世俗的空间转换;其三,寨神显灵使村民们处于一种与神灵同在的非现实时空中。
3)统一标准、科学评价。2016年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检查验收技术标准以普查时期为基础,2017年根据监测需要进行修改印发,全国执行统一标准,从国检中心到任务承担单位都积极开展质量培训,统一认识,明确要求,对成果质量依据标准进行客观、准确评价。
(一)村寨内外的空间分割
祭寨神仪式严格区分出寨内和寨外两个空间。寨内安全、封闭、洁净、有序,寨外危险、开放、不洁、无序。村寨是在最高灵力“丢瓦拉曼”荫庇之下的生命体。⑦艾菊红:《西双版纳傣泐的居住空间结构及其认知逻辑》,《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仪式的目的是强化信仰,使圣俗之物被区别出来。涂尔干将澳洲社会区分为日常谋食活动与集体宗教活动。“在集会中,人们将举行宗教仪典,在这种民族学称之为‘集体欢腾’的时间里,人们处在一种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状态,一切日常生活的准则都被抛开。人在这种迷狂的状态之中,往往会感到自己受到一种别的力量的支配,感到自己置身于另一个世界,或者感到自己已不再是自己。”①周树华:《神圣与凡俗: 二分法建构的宗教生活——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宗教起源研究》,《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神圣从凡俗中脱颖而出。
《谈寨神勐神的由来》认为,猎神、寨神、勐神是人们为了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而创造出来的,是由聪明、智慧的英雄人物沙罗、桑木底创造出来教化群众的;寨神勐神的作用就在于“把众人的意志和愿望统一在一起,杜绝人类愚蠢的分散……同心协力,去争取人类的生存权。”也就是说,傣族原始宗教的产生来源于加强社会团结、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②伍雄武:《关于古代傣族的原始宗教》,《哲学研究》1983年第11期。据曼旦村“细梢老曼”波扁介绍:每一片土地都有保护神,建寨之初都要供奉寨神,得到寨神允许后方可建寨,并每两年祭寨神一次,所以曼旦村的寨神只是本寨的神,与他寨的不同。长期以来,寨神由于一系列神秘而神圣的节庆祭祀活动,形成一种巨大的感染力,是一次只属于本寨凝聚力的聚会,把别寨的人排除在外。按照涂尔干的观点,任何宗教都是社会性的,宗教表现是表达集体实在的,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尤其是那些代表低级社会特征的宗教,在涂尔干看来更能够充分发挥群体在智识和道德上的一致性。“在低级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是共同的,活动是定型的。每个人都在同样的环境进行着同样的活动,而这种行为的一致性也只不过是思想一致性的体现。每个心灵都被卷进了同样的旋涡,几乎所有的个体类型都是按照种族类型的模式得以确立的。”③[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 东,汲 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傣族的祭寨神仪式具有涂尔干所描述的这种特征,是一项由全体村民参加的集体祭祀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山区群众对山洪灾害的认识,强化躲灾、避灾意识,各地应每年进行一次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发动。采取出动宣传车,出标语、横幅、宣传栏,设立警示牌,编印发送山洪灾害防御手册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措施,使有关法律、法规、山洪灾害防御常识和对策措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通过对山洪的防灾避灾宣传,牢固树立干部群众的灾患意识,达到自觉防灾避灾的目的。
图1:被分割的祭寨神仪式空间示意图
(二)祭祀寨神林空间的两性隔绝
傣族人把寨神林看成是祖先灵魂的居住地,认为:祖先已去,“灵魂”尚在,祖先来自森林,其“灵魂”必重返自然。傣族的男女老幼都对寨神林表现出敬畏之情,有的妇女甚至不敢提及,更不用说进入,无故进去会给整个村子带来噩运。“女性不得进入寨神林;妻子有孕的男性村民不得进入寨神林。在祭祀寨神前,要派专人调查非婚怀孕的情况,若有,应立即被处罚,令其祭寨神赎罪。在请神仪式空间内,男性把寨神与女性隔绝开,女性不能靠近寨神。”④李本书:《傣族“龙山林”文化禁忌与边疆生态环境的安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这些已经成为村民们的自觉行为。
Mary Douglas在《洁净与危险》一书的导论中,仔细考察了肮脏及其与人类的关联问题:“对肮脏的看法,包含着对有序与无序、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非形式、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肮脏的观念,它都是高度结构的,对它们的分析展示了这些深刻的主题。”⑤M.Douglas,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pp.5~6.女性的身体结构被看成“不洁”“污秽”,会危害他人、家庭以及社会,在人们的观念中女性成为了象征性的污染体系。⑥李金莲:《女性、污秽与象征:宗教人类学视野中的月经禁忌》,《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傣族村落空间同样表现出男洁女污、男尊女卑、男主女次的等级化特质,这一特质是通过对村落、家庭、寺庙的使用划分出来的,但这不是世俗化的习惯。傣族的宗教信仰使得这种性别禁忌表现出鲜明的宗教性,性别禁忌成为一种宗教禁忌。①参见章立明《傣族村落人聚空间的性别禁忌》,《民族艺术研究》2003年第4期。因此,祭寨神把女性排除在寨神林空间之外。
2014年,医院党委提出了建设无纸化医院的构想,责成有关科室对无纸化项目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工作,通过研究国家法律法规、相关政策要求,确立了法律依据。对实施厂家及实施医院进行多次参观考察,确立了技术可行性。
(三)神与佛的空间分割
寺庙在祭寨神期间停止了宗教的活动和仪式。傣族社会存在“摆”与“非摆”两套宗教活动及其行动逻辑。“摆”是当地佛事活动的总称,包括买佛、迎佛、赕佛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分别举行。“非摆”指的是当地“本土宗教”的信仰仪式,也即包括寨神祭祀、谷神祭祀等一系列属于“神”的仪式。②参见杨清媚《从“双重宗教”看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双重性——一项基于神话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根据田汝康的观察,这两套系统分别按不同的历法时间运行,他用中历(即农历)来记录“非摆”,用佛历和中历对比来记录“摆”,“摆”与“非摆”的交错运动构成了社区整体的时间系统。与这两套仪式相对应的仪式空间分别是冢房(佛寺)和社庙(祭祀寨神之处)。③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页。寨神只为本寨人所供奉,它与佛教的普遍性不同。村民们说:“佛是大家的,寨神就不同了。”
关于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原始宗教的激烈斗争,在佛经、传说、神话中都有记载。我们看到,在傣族社会中,佛殿与神坛自立门户,不相上下。④朱德普:《傣族佛教和原始宗教的关系试析——兼析两者长期共存的原因》,《思想战线》1992年第3期。祭寨神期间,不许外人留在寨内。期间,留在寨内的外人只能暂避佛寺,说明南传上座部佛教也是外来的,僧侣不得步入村寨。据西双版纳勐罕城子村还俗僧人康朗罕追忆:他初当小和尚时,听到祭寨神的炮声,便跑去看热闹,被大佛爷喝住,说谁去谁就不准再回佛寺,大佛爷让他们进佛殿跪向佛祖赎罪。祭勐神时,景洪召片领的文书官在宣读祭文时,勐神被称为佛祖的弟子,“波么”勐极力容忍,“波么”勐在祷辞中坚决不提佛祖。“波么勐”从祭坛返回召片领的宫府途中,对待僧侣和俗人一样处以神罚。⑤朱德普:《傣族佛教和原始宗教的关系试析——兼析两者长期共存的原因》,《思想战线》1992年第3期。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均表现佛神的对立,最终形成了南传佛教为表、民间信仰为里的宗教格局,⑥参见张振伟《身体与信仰:西双版纳傣族仪式治疗中的二元宗教互动》,《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更表现出祭寨神的排他性、封闭性。
五、结论:空间分割为祭寨神仪式排他性的反映
如涂尔干指出的,每一个社会都有集体共同形成的信仰,这些信仰以宗教的形式体现,并将其贯穿于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中,因此,“真正的宗教信仰总是某个特定集体的共同信仰,这个集体不仅宣称效忠于这些信仰,而且还要奉行与这些信仰有关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不仅为所有集体成员逐一接受;而且完全属于该群体本身,从而使这个集体成为一个统一体。每个集体成员都能够感到,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他们可以借助这个信念团结起来。”⑦[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 东,汲 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页。祭寨神呈现了傣族人对仪式和仪规的共同遵循,仪式还伴随着娱神活动,村民们狂歌欢舞,昭示敬奉神灵、禳灾驱魔。⑧杨民康:《贝叶礼赞》,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97页。傣族祭寨神体现了涂尔干所描述的宗教诞生的基础:集体欢腾与社会作用。仪式期间,村民们感觉到自己被神圣力量所支配,仿佛被送入神灵世界。不属于日常生活空间的祭寨神空间,既具有超越世俗、净化村寨的宗教功能,又具有凝聚村民的社会功能。封寨使村民进入一种类似时光隧道的状态,时间不再以某月某日来计算,而以封寨、入寨神林、从寨神林返回村寨、开寨来计算。空间亦不以往日的生活空间划分。这样一种超越日常作息及认知的时空体验,很容易使人忘却原有的存在经验,自生活作息中脱离出来。
由于人工窖泥制作过程中添加的酯化液会掩盖生泥味[8-9],并且与老窖泥自然形成的酯香类似,容易引起误判,如3年窖泥中的3号。
祭寨神时,村寨空间由世俗转变成神圣,神圣和世俗在这里既分离又融合,村寨在村民们心里充满了异于日常世俗的神圣。与村寨相比,寨神林的神圣性更加浓厚,似乎在宗教体验上,寨神林空间的神圣性强于村寨空间的神圣性。寨神林空间和村寨空间均是神圣的、同质的空间。村寨外的空间是日常世俗社会空间。祭寨神仪式过程为:世俗—神圣—神圣—神圣—世俗,即寨外—村寨—寨神林—村寨—寨外。
1.2.1 细胞培养 将购买的人前列腺癌细胞PC3解冻复苏,接种于含10%胎牛血清DMEM培养基中,置于37℃、5% CO2的潮湿培养箱中培养,待细胞长满瓶底85%左右时,弃去培养液,加入胰蛋白酶消化处理后,进行传代培养和细胞冻存。
事实上,人类的经验是复杂的,而且是交替式共存的。并非3天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个村民都沐浴在超脱经验中。例如村民们在家会打电话交代一些世俗琐事,也会谈论收成如何等。祭寨神仪式中神圣体验和世俗经验是交替并存的。在仪式空间中,表现出排他性的特征。傣族寨神祭祀的排他性在傣族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这种排他性体现的是傣族曾作为氏族的特征,寨神是傣族氏族社会的神,为氏族成员所共有。祭寨神成为凝聚、团结村寨成员的重要仪式。相反,非村寨成员禁止参与祭祀。寨神林内的祭祀仪式把村民们分为男女两性空间,女性不得参与祭祀。请神仪式空间中,女性则被男性隔绝在外围,不能靠近寨神,以免对寨神产生不敬。祭寨神仪式的排他性还反映了原始宗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差异性。虽然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其强大的力量渗透到傣族人的生活中,但傣族人体会到:“佛只管来生,而现实的衣食住行仍靠神的庇护。”①阎 莉,莫国香:《傣族寨神勐神祭祀的集体表象》,《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因此,空间分割成为祭寨神仪式排他性的反映。
Spatial Exclusiveness of God Worship Ceremony in Dai Villages
HE Qinghua
Abstract:During the Village-God Worship Ceremony, the Dai people enter the sacred space and time from the physical space and time, which turns the whole village into a closed sacred space for religious purpose.Compared with the village space, the God Woods where the Village God lives is more sacred.While the worship ceremony spatially excludes the Buddha and places outside the village,the God Woods keep out females in the village.The physical spatial arrangement inside and outside the village and the God Woods reflects the spatial exclusiveness of the worship ceremony in Dai villages.And the exclusiveness in turn display the functions of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Keywords:Dai people,Village-God Worship,sacred space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19)04-0078-08
作者简介:何庆华,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福建 厦门,361005)。
(责任编辑 廖国强)
标签:傣族论文; 村寨论文; 仪式论文; 空间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思想战线》2019年第4期论文;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论文; 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