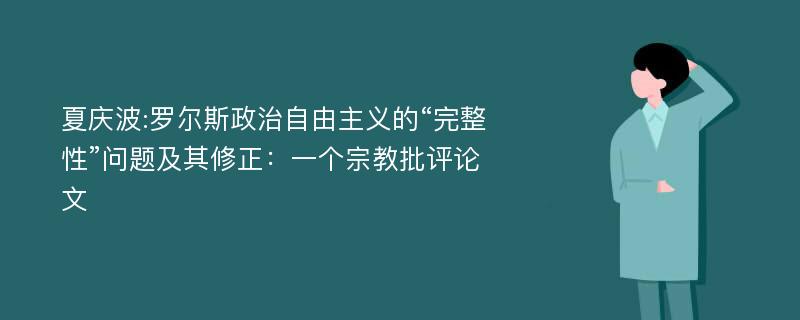
[摘 要]以“共识观念”为基础,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预设了一种“宗教约束观点”。在批评者看来,这种宗教约束观点必然导致“完整性”问题:由于宗教理由遭到“括置”,信教人士的宗教完整生活被“一分为二”。罗尔斯通过放宽对宗教理由的限制来回应批评,但是他的回应难以令批评者满意。批评者认为“聚合观念”更能包容宗教,尽管存在诸多困难。总的来说,我们应当尊重信教人士的宗教完整性,但是这不意味着“怎么都行”,另外,不宜夸大政治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之间关于“完整性”问题的冲突。
[关键词]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完整性;宗教批评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说法,在宗教与政治之间存在一个“神学-政治问题”,即:政治权威究竟应该植根于启示,还是植根于理性?[1]453-456在很大程度上,古今诸种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的出现、发展及证成皆或隐或显地包含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前现代社会,常见的假设是,人类的政治权威来自于某种神圣力量的授权。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借助理性宣布“上帝已死”,现代国家开始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全面转型。因此,现代政治的基本假设亦随之发生变迁:一方面,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来自于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的同意;另一方面,通过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宗教条款”而得到经典表述的“政教分离原则”力图在宗教与国家之间划出一道“隔离之墙”——通过这道墙,宗教被驱逐出公共政治空间,只能在私人领域承担“灵魂牧养”的角色。然而,随着人类理性遭遇“现代性”困境,我们看到,自20世纪后半期以降,各种宗教神学并没有像世俗化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逐渐“私人化”乃至于“消亡”,反而出现了全球范围的宗教“复魅”现象。[2]
这种强劲的宗教复兴势头加深了罗尔斯对“合情理多元论”的忧虑。他尝试以“政治自由主义”回应这一问题的挑战:“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情理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与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所组成的公正而稳定的社会如何可能保持长治久安?”[3]xxxvii罗尔斯试图以此重构一种面对“合情理多元论”的正当性理论。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正当性规划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在众多批评声中,“完整性问题”可能是从宗教视角出发的反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最流行的论证”[4]166。本文将首先阐明“完整性问题”的缘起,它滥觞于罗尔斯以“共识观念”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接着,在分析完整性批评的基础上,讨论罗尔斯的回应及修正;最后,笔者试图对罗尔斯的回应与修正、其他可能的回应路径以及完整性问题本身作进一步的反思。
一、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共识观念与宗教约束观点
在合情理多元论的现代条件下,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想的一个基本承诺是:政治权力的行使,只有这样才是完全适当的,即它所依据的宪法的根本内容,可以合乎情理地期待得到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按照他们共同的人类理性可以接受的原则和理想——的认可。这是罗尔斯所称的“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罗尔斯的正当性理念植根于一种“公民身份观念”:公民身份这一“根本政治关系”是处在社会基本结构之内的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关系,因此,政治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对于共享这种集体性权力的自由而平等的每个公民来说,它的行使必须是可证成的(justifiable)。[3]136-138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被当代政治理论家们进一步表述为“公共证成原则”:强制性法律L在公众P中得到证成——当且仅当P中每一个成员有充分的理由R去支持L的时候。[5]53根据这个原则,如果公众中的每个成员有确定的理由接受某项法律,那么政治权威对这项法律的实施是正当的,所有人都应该根据它去行动。
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家们认识到合情理多元论的挑战,他们都分享一种家族相似性,即他们大多同意,强制性法律的正当性在于它能够向所有人证成。每一个合乎情理的公众成员必须有充分的证成性理由——如果他们被自由而平等地对待的话——去认可该项法律。但是由于不同的理论家对如何阐释“证成性理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因而主要存在两种公共证成观念:一种观点认为,证成性理由R能够被公众P中的所有成员所共享。这是公共证成的共识观念。另一种观点认为,公众P中的不同成员通过各自的证成性理由(R1,R2,R3…… Rn)在法律L上形成聚合。这是公共证成的聚合观念。[6]262-264
旅游发展委员会(部分地区为旅游局)是主管旅游工作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服务质量、维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须规范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和服务行为;组织拟订旅游区、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旅游产品等方面的标准并组织实施;指导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和诚信体系建设;指导行业组织的业务工作○12。但是面对不合理低价产品时,旅游相关管理部门也存在着故意无视现象。
阻隔性较高的包装材料,能够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包装内气氛条件不变,从而使其对肉类的保鲜效果得到最大保持。本研究比较测试了新研发的2种高阻隔气调包装材料对羊肉的气调保鲜效果,为下一步对该材料的升级改造及推广应用提供必要的科学数据。
实际上,罗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将其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预设为一种“共识观念”——至少以“共识观念”为基础。[注]罗尔斯本人认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证成是一个两阶段证成观念的统一。第一阶段是“特定程度证成”:原初状态的各方在无知之幕之后根据严格的对知识和推理的限制产生了一个“自立的”政治性正义观念。这种证成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共识观念。第二阶段是“充分证成”:仅当良序社会的公民从其整全性学说出发接受政治性观念(特定程度证成)的时候(即形成重叠共识),充分证成才实现。这种证成实际上是一种聚合观念。因此许多理论家认为罗尔斯的公共证成采取的是一种共识观念与聚合观念的混合模式(如托马斯·内格尔、凯文·瓦利耶等);但是哈贝马斯认为,罗尔斯的第二阶段重叠共识证成(聚合观念)实际上仅仅表达了一种功能上的用途,并不能起到理论证成作用。综合起来,撇开哈贝马斯所激起的争论,我们至少可以说,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的基础是一种共识观念。参见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385-388.首先,罗尔斯为正当性原则设置了一个检验标准:相互性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公民们为自己的政治行动所提供的理由应该能够被其他公民合乎情理地接受。公民们对根本政治问题的公共推理应当由所有自由平等公民可以共享的理由决定。这样,整全性的宗教、道德及哲学学说由于不能通过相互性标准的检验而无法成为共享的证成性理由。罗尔斯相信,要想相互性标准不被僭越,证成性理由必须被表达为一类以基本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政治性正义观念”——尽管这类政治观念之间也是互竞的。[3]xlix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寻求这类“政治性正义观念”以作为能够得到公民们“公共承认”的“共享基础”[3]8-10。其次,罗尔斯认为,政治自由主义致力于一种作为“公民身份理想”的“公民性责任”:在公共证成活动中,公民们有为彼此提供共享理由的道德(非法律)责任,“他们要相互解释清楚,他们所拥护和投票支持的那些原则与政策怎样才能获得公共理性之政治价值的支持”[3]217。最后,罗尔斯宣称,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公平合作条款应该要满足“公共性”的要求。罗尔斯的公共性观念包括“共同接受的社会正义原则”、“共享的普遍信念”及“充分的证成”三个层次。在罗尔斯看来,仅当每个公民基于可公共运用的理由——政治性正义观念——去接受某项社会安排的时候,它才具有公共性。[3]66-69
这样,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假设公民们的总体观念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非共享的整全性的宗教、哲学或道德学说,另一个部分是共享的政治性的正义观念。当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处于攸关时刻,政治权力的行使只有基于人们可以合乎情理地期待所有公民都能按照他们共同的人类理性来认可的方式——即共享的政治性正义观念——才是正当的。[3]140进一步而言,罗尔斯以“共识”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正当性观念预示了一种“宗教约束观点”:当讨论宪法根本与基本结构问题时,我们不应当诉诸整全性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不应当诉诸我们认为是完整真理的东西,因为它们不能提供公共证成的基础。[3]224-225罗尔斯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如理查德·罗蒂就直截了当地宣称,宗教是公共对话的“阻断者”,现代政治无需哲学或宗教提供基础[7]168-174;而斯蒂芬·马赛多则认为,宗教理由是公共证成的“不恰当手段”[8] 22。
总之,对于批评者而言,对“完整性”的损害体现了处在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核心的一种“不平等”:信教人士在自由主义政治中被压制或者说被边缘化了。对于这一抱怨,马赛多以嘲讽的语气回击道:“如果有人因为这一事实——我们中的一些人相信,根据宗教或形而上学主张去塑造基本自由是错误的——而感到被压制或边缘化,那么,我只能说‘成熟一点吧’。”[8] 35尽管完整性批评可能不能驳倒罗尔斯,但是马赛多的这种回应却无疑是草率的,因为政治自由主义志在创造一个自由社会并守护公民(包括信教人士)的完整性,如果有人感觉被政治规范剥夺了完整性,那么,政治自由主义就必须认真回应这一批评。
然而,罗尔斯的宗教约束观点也招致了强烈批评。批评者抱怨,政治自由主义对宗教公民施加了过度的约束——它迫使他们在公共政治空间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完整性问题是批评者们基于宗教立场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所提出的最有力批评之一。
二、完整性批评
事实上,罗尔斯很早就提出了相对于“排斥性观点”的公共理性的“包容性观点”。根据“包容性”的公共理性,假如公民们“以强化公共理性理想的方式”,那么,“在某些境况中”,他们可以“提出他们认为是植根于他们整全性学说的政治价值基础的理由”。[注]罗尔斯承认,他最初坚持一种公共理性的“排斥性观点”。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247.罗尔斯解释了不同的情形。在一个“几乎是秩序良好的”(more or less well-ordered)社会中,因为公民们坚定地认可一种对“政治性正义观念”的重叠共识,所以他们不会为整全性学说的争论所动摇,从而可以遵循公共理性的“排斥性观点”。在一个“接近秩序良好的”(nearly well-ordered)社会中,由于不同信仰的人们对正义原则的应用存在激烈的争论而导致他们渐渐怀疑彼此之间对根本政治价值的忠诚。在罗尔斯看来,这时强化公共理性理想的最佳方式是各方“在公共论坛上解释人们的整全性学说是如何认可政治价值的”。再者,在一个“不是秩序良好的”(not well-ordered)的社会中,人们对宪法根本内容存在深刻的分歧。罗尔斯以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奴隶解放运动为例,认为废奴主义者基于宗教理由所作的论证“证实了明确的公共理性结论”并“强化了公共理性理想”。罗尔斯最后得出结论: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最好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公共理性的理想。在良好的时代(good times)条件下,可以遵循“排斥性观点”;在不够良好的时代(less good times)条件下,则最好采取“包容性观点”[3]166。
完整性因此与“认同”密切关联。根据认同观念,“完整性意味着对那些构成某人核心认同的规划与原则的忠诚”[9]155。在批评者看来,政治自由主义的二元论使得信教公民分裂为“公共的自我”与“非公共的自我”两个部分:在公共政治空间,他们应当将自己的宗教信仰深埋心底;只有在非公共空间,他们才能表达真实自我。以某个信教公民关于安乐死的观点为例:假设此人相信存在一个对安乐死的道德约束,如上帝的诫命,那么他可能认为安乐死是非法的,但是根据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他不应该基于这个宗教理由进行公共推理,相反,他应当通过共享的政治性正义观念从事对安乐死问题的证成活动。[10]882可以看出,政治自由主义的宗教约束观点使得信教公民不得不放弃对核心认同的忠诚,这进而产生了完整性问题。
在1996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平装版导论中,罗尔斯提出了“宽泛的公共理性观点”,更加放宽了对宗教理由的限制。这种观点允许公民们在讨论宪法根本与正义问题的“任何时候”诉诸整全性的宗教、哲学与道德理由,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在适当的时候”提出的公共理由应足以支持所引入的整全性理由所要支持的东西。罗尔斯将这个条件称为“限制性条款”。罗尔斯认为,他关于“包容性观点”的讨论中所提及的三种情形皆能满足这一“限制性条款”[3]xlix-l。可以看出,与“包容性观点”相比,“宽泛的公共理性观点”对宗教理由的限制更少:其一,公民们无需区分“良好的时代条件”与“不够良好的时代条件”,他们可在“任何时候”诉诸宗教理由;其二,公民们在诉诸宗教理由时不需要“同时”提供公共理由,只要“在适当的时候”提供即可。
不难看到,罗尔斯回应完整性批评的主要举措是放宽对宗教理由的限制:即政治自由主义不再坚持公民们在公共推理中只能诉诸公共理由,相反,只要满足一定条件,他们可以在公共论坛中诉诸宗教等非公共理由。罗尔斯的这种让步是逐步完成的。
一般来说,理论家们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完整性批评包含四层意思:第一,损害完整性是对信教人士宗教自由的侵犯。对信教人士来说,宗教信念是构成性的,是维持他们“完整生活”的源泉——他们是“出于”宗教信念而生活的,而政治自由主义否认了宗教信念在信教人士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它对他们宗教信念的“括置”等于“摧毁了他们本性中的精华”[12]181-182。因此,信教人士无法按照政治自由主义的要求把他们对政治立场的论证独立于自己的宗教信念之外,并且,这种要求无疑会侵犯他们的宗教自由实践。[11] 105第二,损害完整性表明政治自由主义对信教公民没有做到它所宣称的尊重。按照查尔斯·拉莫尔的观点,政治自由主义的根本前提是“我们在政治领域应该给予彼此某种尊重”[13]86。杰拉德·高斯与凯文·瓦利耶举了一个例子:假设阿尔夫支持一项法律,如果他尊重贝蒂的话,他就不能把这项法律强加给她;他必须要向她表明她有确定的理由接受它。[5]55如前文所述,政治自由主义认为这个理由应当是阿尔夫与贝蒂能够“共享的理由”,而不是他们各自的包括宗教理由在内的“私人理由”。克里斯托弗·埃伯利与特伦斯·库内奥批评道:“这一点并不清楚:诉诸公共理由就是尊重伙伴公民的最好方法。”接着,他们通过援引沃特斯多夫与杰夫瑞·斯塔特表明:“通过明确地向对方说出自己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无论这些理由是什么),并且对方也诉诸他们基于自己对这样或那样的整全性观点的承诺而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能够更好地提供尊重”[14]。第三,损害完整性的政治自由主义难以充分实现公共证成的目标。鉴于“合乎情理的多元论”,政治自由主义假设,只有“括置”整全性的宗教、哲学及道德学说,建立一种以共享的公民身份理想为基础的道德与政治规则,才能提供规范性的政治权威理论。但是,批评者反驳道,“括置”策略难以解释,如果一套规则仅仅以信教人士所接受的“次要价值”(即“共享的理由”)为基础,它怎么能够声称对他们来说得到了充分的证成?例如,如果我们把信徒阿尔伯特的宗教信念(他的天主教信仰、他对动物权利的承诺,等等)括置起来,仅仅关注于他对自由、平等及公平的共享政治理想的承诺,那么,说阿尔伯特有理由接受从括置装置中导出的原则。这可能只有较为有限的公共证成意义。[15]39-41沃特斯多夫进一步认为,我们把对人权的论证植根于世俗考量的尝试是失败的,相反,只有明确诉诸于有神论的假设,我们才能对这些权利的来源作一个充分的证成。[16]94-95第四,损害完整性会降低信教人士投身政治参与的热情。批评者认为,政治自由主义致力于把宗教驱逐出公共政治空间,然而,即使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宗教也可以是促进自由精神发展的巨大动力。与沃特斯多夫及佩里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完整性批评相比,保罗·威特曼对政治自由主义提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完整性批评。他论证了美国教会对促进民主自由及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在威特曼看来,教会提供“讨论的空间”,教育信教人士关于政治的常识,训练他们可以运用到政治生活中的“组织与议会技能”。威特曼宣称,正是通过参加宗教组织,许多文化及少数族群的成员——非裔美国人是其中之一——才获得了“实现的公民身份”(realized citizenship)与“自我价值感”。因此,政治自由主义拒绝信教人士依据宗教理由为其政治立场作论证实际上是对他们的公民身份与政治参与的限制。[17]22
“问题”是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发学生数学思考的有效载体。它可以优化教学方式,实现学生学和教师教的有效统一。如果能将“静态”的数学知识转化为“动态”的结构性问题,教学活动就可以成为围绕问题解决而展开的主动建构活动,即成为学生循序渐进、逻辑构建的认知途径。
其描述的具体要求如上,但固定用语(见下文)不同。“以下是体外获得的资料,但其临床意义尚不清楚。下列细菌至少90%显示,体外最小抑菌浓度低于或等于[药品通用名]敏感折点。然而,[药品通用名]在治疗这些细菌所致临床感染中的效果,尚未在充分的对照良好的临床试验中确定。”
三、罗尔斯的回应与修正
面对“完整性”批评,罗尔斯可能有如下三个选项:(一)放弃政治自由主义理想;(二)否认完整性批评;(三)坚持政治自由主义理想并对完整性批评作出回应。显然,选项(一)不会成为罗尔斯的选择;选项(二)正是马赛多所做的,但是如上文所述,这种对完整性批评的回应似乎失之草率;罗尔斯的选择是选项(三):发展一种能够守护公民(包括信教人士)完整性的政治自由主义。
尼古拉斯·沃特斯多夫提出了对政治自由主义最为典型的完整性批评:“我们社会中的信教人士理应把他们涉及根本问题的决定奠基于自己的宗教信念。他们不认为存在做或不做的选择,因为这样做也是他们的宗教信念之一。他们的信念是,他们应当终其一生地寻求整体性、完整性及统一性:他们应当让上帝之道、摩西五经的教义、耶稣的诫命与榜样,或诸如此类,来把他们的存在——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存在——塑造为一个整体。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宗教不是关于某种把他们的社会政治存在排除在外的东西(something other than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existence);它也涉及他们的社会政治存在。”[11] 105
针对罗尔斯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的宗教约束观点,“完整性”批评的要旨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所预设的二元论——一个人作为信徒,他拥有一套非共享的宗教理由,但是作为公民,他则应当拥有一套可共享的公共理由以支持或反对一种政治立场——意味着对宗教理由的括置(bracket);对于信教人士来说,宗教信念是如此重要,期待他们基于仅有次要价值的公共理由而不是构成他们身份认同的宗教理由为政治立场作论证无异于“以一种损害他们的宗教之完整性的方式将他们‘一分为二’”[4]166。
如果说公共证成的聚合观念仅仅要求公众成员按照他们自己的私人理由接受法律和政治议案的话,那么共识观念则要求公众成员所接受法律和政治议案的理由应该具有共同的认知属性。因此,政治自由主义需要回答的是,它的正当性原则是将证成性理由限制在公民们所共享的理由,还是可以接受公民们彼此之间完全不同的私人理由?
3.4 缺少必要的家庭和社会支持 老年人的家庭康复离不开家庭关怀和社会大环境的大力支持。社会支持可作为心理刺激的缓冲因素或中介因素,对健康产生间接的保护作用,从而有益于健康。研究显示,有家庭成员主动参与协助康复的患者,其康复效果、功能恢复程度比没有家庭支持的有明显进步[25]。然而国内老年患者的家庭关怀和社会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冯正仪等[22]调查脑卒中后家庭康复环境改造情况发现,只有7.7%去除了门槛等地面障碍物,11.5%为患者准备了专用坐便器;3.8%为卧床患者安装床档;无一户在卫生间安装扶手。
根据以上评估结果,D=F/E=11/7=1.57>1,故沙沟泥石流受灾体处于危险工作状态,成灾可能性大。
在1997年发表的《公共理性理念新探》一文中,罗尔斯把“宽泛的公共理性观点”进一步表述为“宽泛的公共政治文化观点”。首先,在这里,罗尔斯一方面对限制性条款作了更清晰的说明,另一方面也探讨了把整全性学说引入公共政治讨论的“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防御性的”根据。在罗尔斯看来,如果公民们相互了解彼此的整全性学说,他们就会认识到,他们忠诚于政治观念的根基在于其宗教或非宗教学说。正是这些整全性学说构成了政治观念的“关键性社会基础”,并能够“赋予政治观念以持久的力量与活力”。其次,罗尔斯还讨论了两种没有体现公共推理的言谈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宣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宣告自己的整全性学说——但是不期待其他人共享——以表明我们如何能够从自己的整全性学说出发去支持一种政治性正义观念。第二种形式是推测:我们从自己真诚地相信或推测属于其他人的宗教或非宗教学说出发,并试图表明,尽管他们持有这种整全性学说,他们仍然可以认可一种政治性正义观念。最后,罗尔斯清楚地表明,公共理性理念仅仅适用于公共政治论坛中对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的讨论;在“背景文化”与“非公共政治文化”,公民们可以基于宗教与非宗教理由展开充分而公开的讨论。罗尔斯相信,通过这些方式,公民友谊的纽带得到加强;公共理性的理想也得到强化。[18]136-138
这样,罗尔斯通过放宽公共理性的限制而寻求完整性批评与政治自由主义理想之间的一种平衡。一方面,罗尔斯明确表示,对宗教或非宗教学说自身应该如何表达,政治自由主义不存在任何限制或要求:这些学说不必符合某些逻辑标准,或接受理性的评估,或可以得到证据的支持。另一方面,罗尔斯也对政治自由主义理想念兹在兹。他强调,如果满足了“限制性条款”的话,把整全性学说引入公共政治文化就并没有改变公共证成的本质与内容,因为这一证成的基础仍然是族类性的“政治性的正义观念”[18]136。
四、进一步的反思
我们看到,对于现代多元社会的信教人士来说,政治自由主义提出了一个道德的两难:信教人士的信仰使他们倾向基于自己的宗教观点进行政治论证;但是根据政治自由主义的要求,如果他们是合乎情理的公民的话,他们就会承认,基于自己宗教观点的论证是对其他不共享该观点的人的不尊重。这样,信教人士感觉到,他们的宗教完整性似乎同民主的公民身份相冲突。
按照杰拉德·高斯的看法,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僵局:自由主义一直认真对待宗教自由,并强调信教人士依据其宗教信仰生活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具有强烈宗教承诺的人士却日益成为自由主义的尖锐批评者。[19]19-37那么,罗尔斯的措施能否成功回应“完整性”批评从而突破这一“僵局”?再者,有无其他回应这一批评的可能路径?最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所谓的“完整性”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从公共理性的“排斥性观点”到“包容性观点”,再从“宽泛的公共理性观点”到“宽泛的公共政治文化观点”,不难看出,虽然政治自由主义依然倡导政治性正义观念与整全性学说的二分,但是罗尔斯已经尽力把公共理性对宗教理由的排斥降到他所认为的最低程度:一方面,信教人士可以在“任何时候”基于宗教理据论证;另一方面,尽管存在一个“限制性条款”,即信教人士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提供公共理由,但是,按照罗尔斯的论证,这个以政治性正义观念为内容的“公共理由”也正是公民们(包括信教人士)的整全性宗教、哲学及道德学说的“重叠共识”的核心。换言之,信教人士对公共理由的提供是“出于”他们的宗教信念的。因此,罗尔斯似乎成功地回应了“完整性批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的回应并没有令完整性批评者满意。在批评者看来,政治自由主义依然是“不公平的”:它要求信教人士提供“公共理由”,这是一种不公平的义务,因为“自由主义整全性学说受到‘自我约束原则’的影响必定少于宗教学说及非宗教非自由主义学说”[20] 688,哈贝马斯解释了这种“不公平”:“许多从宗教的角度出发来对政治问题采取立场的公民,根本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想象力,来为此寻找世俗的、独立于他们本真的信念之外的论证。”[21]30所以,“宽泛的公共理性观点”中的“限制性条款”要求信教人士提供公共理由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注]但是,哈贝马斯并不因此赞同沃特斯多夫等人提议的仅仅基于宗教理由进行公共论证的主张。相反,哈贝马斯提出了类似于罗尔斯“限制性条款”的“制度性翻译条款”。与罗尔斯不同的是,哈贝马斯主张,“翻译工作”不仅仅是信教人士的任务,而且“应该被理解为一桩不信教的公民也参与进来的协作性任务”,这样,“翻译工作”的负担就能够得到一种“平衡”。哈贝马斯将这种“对理性的公共运用”称为“互补的学习过程”:公共空间允许宗教声音的自由释放;信教人士与世俗公民协同翻译,相互学习,共同实践公民德性。参见[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里的宗教:宗教公民与世俗公民的“公共理性运用”诸认知预设》,郁喆隽译, 载张庆熊、林子淳编:《哈贝马斯的宗教观及其反思》,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8-42页。这样,批评者坚持,“在公共讨论中,公民们可以仅仅提供宗教论证,并且,在在投票时,可以依赖于宗教理由”[17]3。
关于第二个问题。针对理论家们对导致“完整性”问题的“共识观念”的批评,近年来,高斯与凯文·瓦利耶等人逐渐发展了如前文所述的公共证成的“聚合观念”。在高斯与瓦利耶看来,“共识观念”之所以排斥宗教推理实际上是因为它对真正的多元推理存有“敌意”,甚至罗尔斯的“宽泛性观点”也太具有限制性了;“聚合观念”则更能表达对合情理多元论的深刻承诺。根据聚合观念,“即使宗教理由不为公民们所共享,它们也能够进入公共证成网络,使不同的合情理观点交错、重叠,以确保一个全面的公共证成”[5]61。与被称为“弱包容论”的罗尔斯“宽泛性观点”相对照,聚合观念被詹姆斯·贝彻称为“强包容论”:对于某个信教人士来说,证成一项法律的仅有理由来自于他的宗教学说,他无需像“弱包容论”所要求的那样再额外提供一份“公共理由”[22]498-500。由于聚合观念赋予宗教理由与世俗理由一样的证成作用,因此,对批评者来说,它比罗尔斯的宽泛性观点更有吸引力。埃伯利与库内奥曾经设想了一个场景:公民们在对医疗改革问题进行慎议。或者,这些公民采取的路径是罗尔斯式的:诉诸公共理由;或者,这些公民基于他们的整全性学说(犹太教、天主教、康德主义、佛教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医疗改革问题形成聚合。埃伯利与库内奥反问道:一个自主的合情理的公民会拒绝后一路径吗?[14]不过,聚合观念并未因此而免于批评。相反,批评同时来自于两个方向:宗教批评者抱怨聚合观念依然预设了类似于“限制性条款”的“最低程度条款”(minimalist proviso)[5]61;“共识观念”理论家们也批评聚合观念造成了诸多问题,比如它削弱了公共理性的真诚性,低估了共享价值的重要性,以及缺少充分的慎议等问题。[23]266
通过对南北山风景林造林示范栽培新疆忍冬苗木的成活率、保存率及枝条生长量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南北山风景林示范栽植平均成活率达到98.89%,平均保存率达到98.67%,平均枝条生长量达到20cm以上,苗木生长健壮,适宜西宁地区山地气候,造林效果非常好,适合今后大面积造林推广应用。
关于第三个问题。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信教人士的完整宗教生活理应得到尊重,这也是政治自由主义所珍视的宗教自由的要义。例如,哈贝马斯就宣称:“正是这种生存上的确定性的核心所获得的商谈上的治外法权,才能赋予宗教信念以某种整体特征。”因此,在自由主义国家,“必须使信教公民在感到他们的人格统一性受到攻击的时候,摆脱一种无理要求,即在政治的共同领域本身之中,在世俗理由与宗教理由之间进行某种严格的分离”[21]32-33。其次,尊重信教人士的宗教完整性并不意味着“怎么都行”,信教人士也需要表达对其他公民的尊重。完整性批评者埃伯利表示,“由于仅当某公民拥有一个以适当方式与他同胞的观点相契合的理据时,他对一项法律的支持才得到证成,所以,该公民的公共证成义务禁止他在决定是否支持某项给定的法律时仅仅诉诸自己的观点”[24]65。罗尔斯对此的解读是,“在支持一种宪政民主制度的时候,一种宗教学说可以说,这是上帝为我们的自由所设定的限制”[18]135。第三,不应过分夸大政治自由主义与其批评者之间关于“完整性”问题的冲突。我们发现,导致两者冲突的不是公民们据以行动的权威的实质内容,而仅仅是权威的来源形式。完整性批评者并不拒斥自由民主政体,相反,他们主张公民们应该只支持能够促进自由主义承诺的法律。在佩里看来,每个人真实完整的人性——即每个人的“不可侵犯性”——是自由民主政体的根本承诺,而“这一承诺是自由民主政体对某些基本的人类自由的进一步承诺的基础”[25]36。进而言之,完整性批评者所反对的只是这一观点,即政治权威来自政治自由主义的正当性规划;他们认为,政治权威只能来自信教人士对神的宗教义务。这样看来,关于“完整性”的“来源形式”而非“实质内容”的冲突似乎就不是不可调和的。
[参 考 文 献]
[1] Leo Strauss. Preface to Hobbes politische Wissenshaft[M]// In Kenneth Hart Green, ed.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lbany, NY: SUNY Press,1997.
[2] 夏庆波.罗尔斯宗教思想研究述评[C]//徐以骅. 宗教与美国社会(第12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211-212.
[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4] Patrick Neal. Is Political Liberalism hostile to Religion[M]// In Shaun P. Young, (eds), Reflections on Rawls: an Assessment of His Legacy, Burlington: Ashgate, 2009.
[5] Gerald Gaus, Kevin Vallier. The Roles of Religion in a Publicly Justified Polity: The Implications of Convergence, Asymmet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J].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09(35).
[6] Kevin Vallier. Convergence and Consensus in Public Reason[J].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 2011(25).
[7]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M]. New York: Penguin, 1999.
[8] Stephen Macedo. In Defense of Liberal Public Reason: Are Slavery and Abortion Hard Cases[M]// in Robert George and Christopher Wolfe(eds.), Natural Law and Public Reason,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0.
[9] Kevin Vallier. Liberalism, Religion and Integrit[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2(90).
[10] Melissa Yates. Rawls and Habermas on religion in the public sphere[J]. Philosp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07(33).
[11] Nicholas Wolterstorff.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Decision and Discussion of Political Issues[M]// in Robert Audi and Nicholas Wolterstorff, Religion in the Public Square: The Place of Religious Convictions in Political Debat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12] Michael Perry. Morality, Politics, and Law: A Bicentennial Essa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 Charles. Larmore. The Autonomy of Moralit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 Christopher Eberle, T.erence Cuneo. Religion and Political Theory[EB/OL].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5/entries/religion-politics/>.
[15] Gerald Gaus. The Order of Public Reaso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 Nicholas Wolterstorff. Justice: Rights and Wrongs, Princeton[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 Paul Weithman. Religion and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 [美]约翰·罗尔斯. 公共理性理念新探[M]//谭安奎.公共理性. 谭安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9] Gerald Gaus. The Place of Religious Belief in Public Reason Liberalism[M]// In MariaDimovia-Cookson and P.M.R. Stirk (eds), MulticulturalismandMoral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2009.
[20] Kent Greenawalt. On Public Reason[J]. Chicago-Kent Law Review, 1993(69).
[21] [德]尤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里的宗教:宗教公民与世俗公民的“公共理性运用”诸认知预设[M]//张庆熊,林子淳. 哈贝马斯的宗教观及其反思.郁喆隽,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
[22] James Boettcher. Strong inclusionist accounts of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J].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2005(36).
[23] Jonathan Quong. Liberalism without perfe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4] Christopher Eberle. Religious Conviction in Liberal Politic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 Michael Perry. Under God?[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e “Integrity” of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Its Amendment: A Religious Criticism
XIAQing-bo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2, China)
Abstract: Rawls’ “principle of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nsensus”, presupposes “a view of religious restraint”. To his critics, this view of religious restraint inevitably leads to the problem of “integrity”: religious integrity of believers, as religious reasons are “enclosed”,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Rawls responds to criticism by relaxing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reasons, but such response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to critics; the “convergent concept”, though with difficulties of all sorts, is more inclusive of religion. Generally speaking, we should respect the religious integrity of believers, but this does not mean “Non-boundary freedom”. In addition,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exaggerate the division between 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its critics.
Keywords: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integrity problem; religious criticism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9.04.007
[收稿日期]2019-01-28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重点建设项目(19JDSZK002);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宗教在公共理性中的作用问题研究”(SK2019A0080)
[作者简介]夏庆波(1972- ),男,安徽肥东人,安徽工业大学副教授,外国哲学专业博士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西方政治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9)04-0049-09
[责任编辑 李长成]
标签:宗教论文; 政治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公民论文; 罗尔斯论文; 哲学论文; 美洲哲学论文; 北美洲哲学论文; 美国哲学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重点建设项目(19JDSZK002)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宗教在公共理性中的作用问题研究"; (SK2019A0080)论文; 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