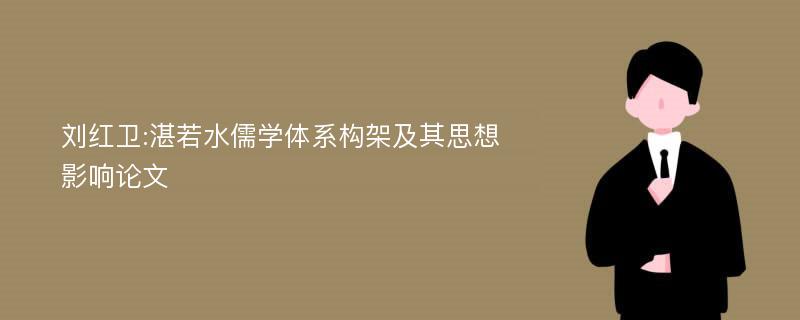
摘 要:本体论和工夫论构成了湛若水儒学的基本框架。湛若水在人与自然“一本”的基础上贯通了心体与道体,以道体的中正、自然特征诠释心体的中正、自然理念,形成了儒学本体论体系。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体认路径,以“勿忘勿助”为体证工夫,形成了儒学工夫论体系。道体作为客观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道体印证心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心无内外,是湛若水儒学区别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重要特征。湛若水及其后学的思想对明朝中后期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道体印证心体、兼顾心体与道体的儒学架构,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心体阐释的偏颇;“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儒学易简性的过度诠释。
关键词:湛若水;儒学体系构架;本体论;工夫论;阳明后学;影响
湛若水师从陈白沙,陈白沙的儒学架构、工夫论及求真、求实精神对湛若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白沙早年在践证心与理相凑泊时几乎导致了心疾,这充分说明陈白沙的儒学架构及工夫论是建立在笃实的体证基础上的。陈白沙在天道运行的体用关系中领悟了心体的体用关系,从而实现了心与理的凑泊。以道体印证心体,在人与自然“一本”[1](P43)的基础上实现心无内外,是陈白沙儒学的本体论框架。在体认路径上,陈白沙主张随处体认天理,强调真知对于成德的重要意义。在体证工夫上,陈白沙强调“勿忘”与“勿助”的均衡性,“勿忘勿助之间”是恰如其分的体证方式。湛若水继承了陈白沙的儒学架构与工夫论,在明朝中后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针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在儒学理论架构及工夫论上的偏颇,他特别强调道体对诠释、印证心体的重要意义。同时,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工夫论上的易简派对儒学易简性的过度诠释。
一 以道体印证心体,实现心无内外,是湛若水儒学本体论的核心内容
陈白沙在《偶得寄东所》一文中曰:“岂无见在心,何必拟诸古?异体骨肉亲,有生皆我与。”湛若水注云:“见在心者,人之本心,古今圣愚所同有,而何必拟古圣人之心哉?此二句指出心之本体也。又言民吾同胞,其实骨肉之亲。而天地间凡万物有生者,皆我之与,即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意。此二句指出道之本体也。然以此心会此道,一而已矣。”[2](P779-780)心体与道体既是陈白沙心学体系的两个支点,也是湛若水儒学体系的两个支点。道体是指天道运行的体系,或者指人所面对的大自然的运行体系,是一个充满了生机、井然有序的有机系统,其生命力充分体现在大自然的生化、运行之中。道体是客观存在的,有其客观的运行规律。湛若水认为,“实”与“有”是道体客观实在性的标志,他曰:“太虚中都是实理充塞流行,只是虚实同原。”[3](P176)又曰:“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来之宙,宇宙间只是一气充塞流行,与道为体,何非莫有?何空之云?虽天地弊坏,人物消尽,而此气此道亦未尝亡,则未尝空也。道也者,先天地而无始,后天地而无终者也。夫子川上之叹,子思鸢鱼之说,颜子卓尔之见,正见此尔。”[4](P811)春、夏、秋、冬更替的时序性、永恒性,万物各遂其性的自然规律,这些都是道体的显著特征。心体指具有生发功能的、生机勃勃的生命有机体,程子生动地将其比喻为“种子”,种子蕴涵了种子的现状及生根、发芽、成长乃至再次生成种子的一切生命特征。心体的本质是善,心体之善是通过亲情、恻隐之心所呈露的善端表现出来的,将亲情、恻隐之心所呈露的善端渐次扩充,便可以达致至仁、至善,到此境界,心体即仁体,亦即“纯亦不已”[1](P135)。在二程及陈白沙的儒学思想中,心体是一种客观的实存,相对于道体而言,具有独立的体系。作为江门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湛若水的心体理论遵循了二程及陈白沙的儒学体系。湛若水认为,个人的心理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但是,作为人的类性的心体却是客观的,有超越个人心理随意性的客观的本体存在。因此,湛若水曰:“天理二字,人人固有,非由外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可以为禹者,同有此耳。故途之人之心,即禹之心;禹之心,即尧、舜之心,总是一心,更无二心,盖天地一而已矣。《记》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古今宇宙内同此一心,岂有二乎?”[3](P156-157)“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可以为禹”就在于心体的本质是相同的,个人通过澄心见性的工夫,祛除个人的私欲、私见、偏见,就能达致圣人的境界。所以,湛若水曰:“尧舜之心,即禹、汤、文、武之心;禹、汤、文、武之心,即孔、孟之心;孔、孟之心,即周、程之心;周、程之心,即白沙先生之心。”[4](P781)心体与道体不是两个完全孤立的体系,人作为自然界中最灵秀者,最能体现道体的本质和特征;同样,只有将心体置于道体的背景之下,才能彰显心体的价值和意义。
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是宋明新儒学讨论的核心论题,在此背景下,二程提出了“道物无对”[1](P17)“物各付物”[1](P144)的观点。在二程“道物无对”的理论基础上,陈白沙将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解释为心体与道体的贯通。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讲,人与物的关系,实质上是心体与道体的关系。对道体的客观实在性的确认及在此基础上达致心体与道体的贯通,是江门学派的重要理论特征。外在的客观世界,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可触摸的,人的认识是从认识外在的客观世界开始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基础。因此,江门学派的认识论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江门学派之所以强调道体对于心体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道体与心体在本原上是统一的,二程称之为“一本”;二是道体的特征对于体认心体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是认识心体的重要因素。湛若水认为,人虽然是自然界中的最灵秀者,但在大自然的背景下,从物种的意义上讲,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物种而已,与别的物种一样,都是气化的产物,在大自然的规律面前,人与别的物种都是平等的。湛若水曰:“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来之宙,宇宙间只是一气充塞流行。”[4](P811)又曰:“天地之气,乃吾气也,是故喘息呼吸皆天也,性情形体皆天也,好恶用舍皆天也,食息起居皆天也。”[4](P481)人与万物“同一天地也,同一气也”[4](P781)。既然人与万物都是气化的产物,那么,人与万物在性、理上必然是相通的。湛若水在《心性图》中曰:“性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浑然宇宙,其气同也。”[3](P141)人与万物乃天地之气化生而成,在性上是相通的。他在《心性图》中又曰:“性也者,心之生理也。”[3](P141)既然人与物在性上相通,那么,在理上也是相通的,故湛若水论及“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时曰:“若非一理同体,何以云然?”[4](P808-809)人与万物在本原上贯通,是心体与道体贯通的宇宙论基础。
道体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与特征,对体认心体具有非常重要的参照意义。以道体印证心体,是江门学派基本的体证路径。陈白沙早年在践证心与理相湊泊时,在传统理学的路径下因用功过度而几致心疾。后来,他在江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放松身心时,看到大自然生机勃勃,万物各遂其性,由此受到启发,对道体的体用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并由道体联想到心体,由此茅塞顿开,心体与道体豁然贯通。此段体证工夫的艰涩性对陈白沙影响很深,决定了他在以后的教学中特别重视道体对心体的印证意义,所谓“随处体认天理”就是从道体对心体的印证角度而言的。对此,湛若水深有体会,在他的儒学体系中,“随处体认天理”是基本的体认路径。道体对心体的印证,有两个核心内涵:其一,天地生成万物之“仁”与人性善相对等,道体之“中正”与心体之中正相对等;其二,“天地以生物为心”[1](P366)而“无心”的承体起用、即体即用的体用观,与心体的承体起用、即体即用的体用观相对等,这是宋、明新儒学“勿助”工夫的核心内涵,是“勿助”工夫的至高境界,陈白沙最终将之发展为“自然之学”[2](P885)。当然,湛若水处于与王阳明、阳明后学辩学的特殊历史环境中,为了纠正现成良知派易简的工夫论对儒学易简性的过度诠释,没有充分发挥陈白沙的“自然之学”,而是强调笃实的体证工夫对于成就德性的重要意义。
二 “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之间”的体证工夫是湛若水儒学工夫论体系的核心内容
“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是湛若水儒学工夫论的核心内容。体认天理是湛若水儒学体系的门户,在体认天理的基础上,知行并进,以“勿忘勿助”的工夫进行切实的体证,达致心体与道体的贯通。湛若水在《南京上元县程明道先生书院记》中曰:“圣人之道之学,一而已矣。道乌一?仁也;学乌一?敬也。仁以言乎其体也,敬以言乎其学之功也。”[4](P775)“仁”即体证仁、善之为人的本质,并从生生不息的道体所表现出的特征以体证心体;“敬”即“勿忘勿助”的切实体证工夫。湛若水曰:“勿忘勿助,敬之谓也。”[3](P148)从体认路径的角度讲,湛若水将孔子的儒学概括为“孔门之教,求仁而已”[4](P775),此即仁;从切实的体证工夫的角度讲,湛若水将孔子的儒学概括为“孔门之学,敬而已矣”[4](P775),此即敬。体证天理为“致知”,敬以存之为“涵养”,致知与涵养如一车两轮,缺一不可。致知与涵养双管齐下,此即知行并进,湛若水曰:“夫仁以体之,敬以存之,仁、敬一致,体、存不忘乎心。”[4](P776)又曰:“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则知行并进矣。”[3](P146)强调知行并进,是江门学派的重要特征。
本文约定电机逆时针旋转方向为正方向,正的定位力矩对应着转子位置的正方向。当转子位于15°时,电机将逆时针旋转至下一个齿槽转矩的零点57°位置,当转子位于105°时,电机依然将顺时针旋转至57°位置的稳定点。因此,实际的稳定点是57°,180°,306°。
二程对孟子的“心勿忘,勿助长”的体证工夫进行了充分的诠释,提出了以“勿忘勿助之间”[1](P62)为体证工夫的恰到好处。二程之后,朱子学系注重阐发“勿忘”,以提撕、唤醒以固执于善作为主要的儒学修养工夫。陈白沙则全面继承了二程“勿忘勿助”的工夫论体系,“勿忘勿助之间”的体证工夫是江门学派工夫论体系的核心。“勿忘”的体证工夫对于成圣的意义自不待言,陈白沙在“勿忘”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以“勿助”为特征的儒学体证工夫的易简性。儒学的易简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儒学的成德之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容不得急于求成;其二,由亲亲之情、恻隐之心所呈露的善端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是将人的自然情感顺理推演而已,是“性其情”[1](P577)而已,其间容不得任何的助长;其三,“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无心”及万物各遂其性的道体承体起用的特征,印证了心体承体起用的易简性,由仁义行,自然易简,容不得任何助长。湛若水继承了陈白沙“勿忘勿助”的工夫论体系,并指明陈白沙的“自然”亦是指“勿忘勿助之间”而言。湛若水在《白沙书院记》中曰:“先生语水曰:‘千古惟有孟子勿忘勿助不犯手段,是谓无在而无不在,以自然为宗者也,天地中正之矩也。’……孔子之所谓敬也,即孟子所谓勿忘勿助也;孟子之勿忘勿助,即周程之所谓一,所谓勿忘勿助之间正当处而不假丝毫人力也。程子之所谓不假丝毫人力,即白沙先生之所谓自然也。皆所以体认乎天之理也。夫自然者,天之理也。故学至于自然焉,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之道,尽之矣。”[4](P782)湛若水将“勿忘勿助之间”视作进入儒学圣域之门的唯一路径,他曰:“所谓门者,勿忘勿助之间,便是中门也。得此中门,不患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责志去习心是矣,先须要求此中门。”[3](P157)同时,湛若水将“勿忘勿助之间”视作儒学体证工夫的把柄,有此把柄,则工夫有着力处;无此把柄,工夫则无处下手。他曰:“白沙先生所谓把柄在手者如此,此乃圣学千古要决。近乃闻不用勿忘勿助之说,将孰见之孰存之乎?是无把柄头脑,学者不可不知。”[3](P175)头脑即是真知,把柄即是“勿忘勿助之间”。在江门学派的工夫论体系中,“随处体认天理”与“勿忘勿助”都是建立在切实体证的基础上的,是对二程儒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 湛若水儒学体系架构及工夫论的影响
1) 根据表1的数值,批发价作为中间变量,只会影响到不同成员之间的收益分配,并不会影响供应链期望收益和最优订货决策.
对“勿忘勿助”有不同的理解,是湛若水与王阳明的工夫论的主要分歧。无论是江门学派的德性进路,还是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德性进路,都注重“真知”“易简”对儒学理论体系及工夫论体系的意义,但两个学派对“真知”与“易简”的理解有所不同。就“真知”而言,陈白沙强调获得“真知”的难度,要不断、反复从感性经验所呈露的仁、善的端倪去体悟、体证人性善的本质,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历反复的磨练,所以,陈白沙提出“随处体认天理”。只有琢磨透彻了,认知方能转化为“真知”,“真知”之后方能知行合一,因此,江门学派的体认路径是先知后行、知行并进,这与王阳明的体认路径是不相同的。王阳明晚年专提“致良知”,作为“真知”之良知的体认,王阳明认为并不困难,因为“良知”与“良能”一样,是人生本来具有的天赋,对此,王阳明认为上根之人点到良知即能醒悟。这一点与陈白沙对“真知”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一难一易,显示出两家在德性进路上的分歧。就“易简”而言,陈白沙和王阳明在早期的体证工夫中都经历了艰辛和遭受了挫折,两个人都几致心疾;在体证工夫豁然贯通后,两人对儒学体证工夫的易简性都有深刻的理解,而且都认为早期的体证工夫遭遇挫折主要是因为没有理解儒学体证工夫的易简性而过度专注于“勿忘”造成的。但是,两个人对“易简”的认识也存在分歧。王阳明不仅认为获得真知并不困难,这个过程本身是易简的。获得真知之后,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也是易简的。陈白沙则认为,儒学体证的易简性表现为先“难”而后“易”,在经过艰辛的体认之后,在实现心与理的凑泊之后,方能豁然开朗,方能易简。达致易简必然要经历“勿忘勿助”的体证过程。
“随处体认天理”在江门学派的儒学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进入江门学派儒学体系的门户。体证天理是通过亲亲之情及恻隐之心所呈露的仁、善的端倪体认仁、善之为人的本质,并由生生不息的道体所呈露的特征以体认心体,陈白沙称之为“立本”[2](P131),湛若水称之为“知本”。陈白沙在实现心与理凑泊的工夫历程中,曾经有一段艰辛的经历,他在传统理学的路径下摸索时,曾因用功过度而几致心疾;但是,一旦豁然醒悟,陈白沙便领悟到了“一日千里”[2](P132)的工夫境界。因此,陈白沙将体证天理看得很重。在体证天理的德性进路中,陈白沙强调“真知”,这一点也是湛若水儒学体系的重要特征。所谓“真知”即对仁、善之为人的本质及心体所呈露的承体起用、即体即用的体用关系有真切的体证,而非人云亦云。湛若水将“真知”称之为“知本”,他曰:“知之功,最先、最切、最大。”[4](P530)湛若水又曰:“夫学以立志为先,以知本为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志也。志立而知本者,其于圣学思过半矣。夫学问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则志立,志立则心不放,心不放则性可复,性复则分定,分定则于忧怒之来,无所累于心性。无累,斯无事矣。苟无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则情炽而益凿其性。性凿,则忧怒之累无穷矣。”[3](P146-147)“知本”是儒学的门户,立志不可不“知本”,“知本”方可立真志,在“知本”的基础上,通过儒学的体认、体证工夫,方可贞定德性,达致“动亦定,静亦定”的境界。湛若水将“真知”比作“真种子”,周孚先问:“戒惧不睹,恐惧不闻,敬也,所谓必有事焉者也。勿忘勿助,是调停平等之法,敬之方也。譬之内丹焉,不睹不闻其丹也,戒慎恐惧以火养丹也;勿忘勿助,所谓文武火候,然否?”先生曰:“此段看得极好,须要知所谓其所不睹,其所不闻者何物事?此即道家所谓真种子也。故其诗云‘鼎内若无真种子,如将水火煮空铛’。试看吾儒真种子安在?寻得见时,便好下文武火也。”[3](P157-158)又曰:“学者须识种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谓种子?即吾此心中这一点生理便是灵骨子也。今人动不动只说涵养,若不知此生理,徒涵养个甚物?释氏为不识此种子,故以理为障,要空要灭,又焉得变化?人若不信圣可为,请看无种子鸡卵,如何抱得成鸡子,皮毛骨血形体全具出壳来?”[3](P158)由以上分析可见,湛若水所谓的“真知”不仅知仁、善之为人的本质,还指知生生不息的心体。
北宋初期,周敦颐、二程在建构新儒学体系时,注重引用道体的内涵和特征来诠释心体,以道体来诠释、印证心体成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在原始儒学的基础上,二程赋予了“仁”三重含义:其一,仁即善;其二,仁之“生”意,即化生万物;其三,仁之“公”意。仁的三重含义均可以从道体的角度进行诠释和印证。大自然生物、成物即是仁之“善”意。大自然生生不息,即仁之“生”意。天降甘露,无所偏私,即仁之“公”意。特别是仁之“生”意、“公”意对新儒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儒学从仁之“公”意中阐发出“中正”理念,该理念后来被以陈白沙、湛若水为代表的江门学派所继承而成为该学派的核心理念。程子以种子类比心体,以种子之生发的自然特征类比心体承体起用的自然特征,江门学派由此阐发出“本体自然”[2](P776)的理论。江门学派对新儒学的阐发基本上遵循了周敦颐、二程的以道体诠释、印证心体的路径,中正、自然及由此阐发出的德性自由、人性自由理念成为江门学派的核心理念[5](P32-37)。在湛若水的儒学体系中,天理即仁,是一个贯穿了心体与道体的概念。对心体的体证不能脱离道体的参照,脱离道体来体证心体容易产生对心体理解的偏颇,最常见的是心体承体起用的“体用一原”的自然特征被误解为一种知觉,也就是儒家学者常讲的认知觉为性,将德性自由转化为随心所欲的情欲自由,从而演变为流禅或狂肆。王阳明认为,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是求之于外,有支离之病,正是因为王阳明忽略了道体对心体的印证作用。对王阳明而言,因其早期切实的体证工夫,对心体的理解自然不会有误,但对其后学而言,则在对心体的理解上难免出现偏差。此外,天理不仅仅表现在人性之善,还表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之中,人与物的关系恰到好处就是天理,这是宋、明新儒学“中正”范畴的重要内容。与王阳明解释“格物”不同,湛若水训“格”为“至”,即达致事物之理,摈弃主观臆见,方能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做到“物各付物”。湛若水曰:“仆之所以训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体认天理也。体认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内外言之也,天理无内外也。……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一耳。寂则廓然大公,感则物来顺应,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离于吾心中正之本体。”[3](P152-153)儒学的功能不仅仅在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而为黎民百姓谋取福祉是儒学的使命,湛若水的“格物”之“物”就包含了治国平天下的全部内容,不对客观的事物进行充分的理解,何以能发挥心体的最大效能?王阳明晚年专提“致良知”,有单提直指的特征,在工夫论上以正念头为主,客观地讲,有重内轻外的显著特征。王阳明的这种重内轻外的教学方法对阳明后学影响很大,最甚者流为空谈心性,流为空疏之学。清朝初年的一些学者认为,明朝的灭亡就是因为官僚阶层空谈心性造成的。因此,阳明后学虽然曾经盛极一时,会讲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如此大的规模,并非每个学生对心体都有切实的体证,阳明后学的晚期,周海门与陶望龄、陶奭龄兄弟均有流禅的明显特征。在明代心学史上,江门学派与阳明学、阳明后学之间一直处于交流与碰撞之中,两者之间曾有四次比较著名的分歧与争论,分别发生在湛若水与王阳明、黄佐与王阳明、许孚远与周海门、刘宗周与陶奭龄之间,江门学派以道体诠释、印证心体及“合内外”“无内外”的体证工夫对于纠正阳明后学对心体理解的简单化、片面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湛若水及其后学的思想对明朝中后期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道体印证心体、兼顾心体与道体的儒学架构,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对心体阐释的偏颇;“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对儒学易简性的过度阐释。
2.1.3 维生素缺乏 羊只在放牧过程中容易造成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的缺乏,引起羊只繁殖率低下和产弱羔、死胎等现象。所以,在补充饲喂时应注意胡萝卜素和多维素等的适量添加。
由于透水沥青混合料粗集料内部含有大量的沥青混合料,再加上高黏度改性沥青的拌和作业难度较大,因此,施工人员需保证混合料拌和的温度,即将混合料的出厂温度控制在既定的规范标准范围内。表2为透水沥青混合料的拌和施工温度控制要求。
受陈白沙的影响,湛若水认为,儒学的体证工夫主要是对“真知”的体证,其中包括对儒学易简性的体证。湛若水主张“致知”与“涵养”两者并行,“致知”即“随处体认天理”,涵养即“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湛若水主张知先行后或知行并进。他曰:“夫学不过知行,知行不可离,又不可混。《说命》曰:‘学于古训乃有获,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中庸》必先学问思辨而后笃行,《论语》先博文而后约礼,孟子知性而后养性。始条理者知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程子知所有养所有,先识仁后以诚敬存之。若仆之愚见,则于圣贤常格内寻下手,庶有自得处,故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则知行并进矣。”[3](P146)“知”即“致知”,“行”即涵养,“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如车两轮”[3](P145)。湛若水主张知行并进,目的在于强调在“知”之后必然有“勿忘于助”的涵养工夫,这点正是针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提出的。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他曰:“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6](P42)“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意思是说笃实之真知即是行,真知之后,自然无须时时提撕、唤醒而固执于善,真知之后自然易简。因此,王阳明对“勿忘勿助”抱有怀疑态度。湛若水则认为,“勿忘勿助”是体认真知及其后之涵养工夫的唯一途径,体认真知之后的涵养工夫,“勿忘勿助”自不必少;对于体认真知而言,学者求学之初即要明白“勿助”的含义,否则无法透彻理解心体的内涵。如果不理解由亲情及恻隐之心所呈露的善端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是一个自然推演的过程而无须助长,如果不理解心体承体起用、即体即用的“勿助”特征,以及儒学的成德、成圣之路容不得急于求成,则必然对心体的理解出现偏差。因此,湛若水曰:“勿忘勿助,只是说一个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体,此是心学最精密处,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师又发出自然之说,至矣。来喻忘助二字,乃分开看。区区会程子之意,只作一时段看。盖勿忘勿助之间,只是中正处也。学者下手,须要理会自然工夫,不须疑其为圣人熟后事,而姑为他求。盖圣学只此一个路头,更无别个路头,若寻别路,终枉了一生也。”[3](P150)湛若水论及王阳明时曰:“勿忘勿助,心之中正处,这时节天理自见,天地万物一体之意自见。若先要见,是想象也。王阳明遂每每欲矫勿忘勿助之说,惑甚矣。”[3](P178)唐君毅先生认为,湛若水质疑王阳明学说的核心就在“太易”二字,他曰:“甘泉之书之评及阳明者,如谓致良知之学,使人以此学本现成简易,不待学与虑。”[7](P374)又曰:“阳明之提出致良知之教,原视此为至简易真切之为学之道,亦愚夫愚妇五尺童子,皆行得之教,故甘泉尝以为太易。”[7](P375)王阳明忽略“勿忘勿助”工夫,对他自身而言,因其早期有切实的体证工夫而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对阳明后学则会产生不良影响。在没有“勿忘勿助”的切实的体证工夫的背景下过分谈论儒学的易简性,必然导致对心体理解的偏差而造成浮光掠影或玩弄光景。在阳明学及阳明后学的理论体系中,良知是“独体”,在“体”上体认、在事上磨练是阳明学及阳明后学体用关系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良知的理论,由此忽略了儒学体认、体征工夫的艰辛。阳明学及阳明后学对良知的理解与儒学传统观念中的良知是有差异的,例如,朱熹曰:“爱亲敬长,所谓良知良能也。”[8](P505)“爱亲敬长”有后天教育的成分。冯从吾曰:“性善,所谓良知也。”[9](P101)冯从吾是从性体,而非心体的角度解释良知。故湛若水曰:“良知二字,自孟子发之,岂不欲学者言之?但学者往往徒以为言,又言得别了,皆说心知是知非皆良知,知得是便行到底,知得非便去到底,如此是致。恐师心自用,还须学问思辨笃行,乃为善致。”[3](P168)“师心自用”刘宗周称之为:“堕体黜听,直信本心。”[10](P400)湛若水曰:“学者须先察识此体,而戒慎恐惧以养之,所谓养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若谓自然而中,则惟圣可能也。”[3](P160)由此可见,“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要诀,是进入儒学圣域的必由之路。
以陈白沙、湛若水为代表的江门学派,继承了二程新儒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其儒学体系构架及工夫论体系对明代心学及中国儒学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江门学派笃实的体认、体证工夫使其与阳明学、阳明后学始终保持了严格的界限,两个学派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促进了明代心学的繁荣,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两朵奇葩。江门学派对朱子理学及性体观念的继承、阐发,又克制了心学“认知觉为性”的弊端,对于矫正、规范儒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程颐,程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陈献章.陈献章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8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4]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M]//儒藏:第23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刘红卫.江门学派的中正自然、德性自由理念及其思想影响[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
[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3.
[9]冯从吾.冯从吾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10]刘宗周.刘宗周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ZhanRuoshui’sConfucianismSystemFrameworkandItsIdeologicalImpact
LIU Hong-wei
(School of Marxism,Wuyi University,Jiangmen,Guangdong 529020,China)
Abstract:Both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noumenon of heart and the noumenon of the nature,by knowing the justice everywhere as the route,by “No Helpping” and “No Forgetting” as the knowing skill,this i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confucianism of Zhan Ruoshui and the skill theory system.The noumenon of the nature possess the development law of itself.Confirming the noumenon of heart by the noumenon of the nature,and achieving no dividing inside and outside on the ground of the former,which is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to distinguish the confucianism of Zhan Ruoshui and the confucianism of Wang Yangming and his scholar of younger age.The confucianism of Zhan Ruoshui and his scholar of younger age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importantly.The confucianism framework of confirming the noumenon of heart by the noumenon of the nature and giveing consideration to the noumenon of heart and the noumenon of the nature balancedly corrected the deflection about the noumenon of heart by the scholar of younger age of Wang Yangming.The road by kowing the justice everywhere and the kowing skill by “No Helpping” and “No Forgetting” corrected the excessive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simple of Confucianism.
Keywords:Zhan Ruoshui; Confucianism system framework;ontology;theory of akill;scholar of younger age of Wang Yangming; influence
收稿日期:2018-1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门学派研究”(15BZX045);江门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门学派的道统体系研究”(JM2018B07)。
作者简介:刘红卫(1971-),男,陕西蓝田人,副教授,中国哲学博士,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4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9)04-0057-07
(责任编辑王能昌)
标签:儒学论文; 工夫论文; 体认论文; 江门论文; 勿忘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明代哲学(1368~1644年)论文;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江门学派研究"; (15BZX045)江门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江门学派的道统体系研究"; (JM2018B07)论文; 五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