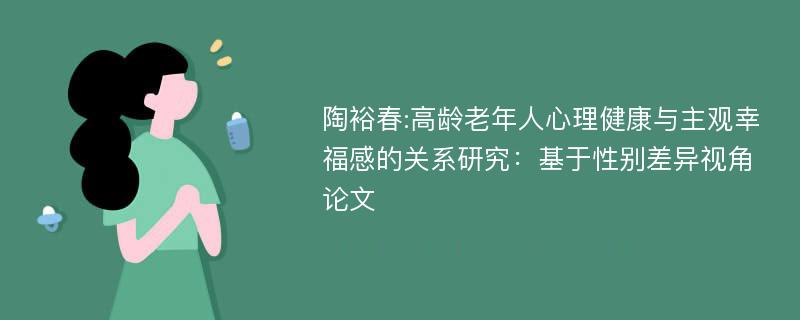
·老龄健康·
摘要: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年数据,选取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基于性别区分的心理健康状况对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我国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均值接近11分,报告高主观幸福感的人数占比达到80%,并且高龄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高龄女性老年人。二元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心理健康对高龄男性老年人和高龄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且对后者的影响效果更明显;年龄对不同性别高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完全不同的预测作用;居住安排仅对高龄男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Logistic回归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世界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2.40亿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1.58亿人,占总人口的11.4%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D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被学者们称之为“银发浪潮”或“人口海啸”。在“未富先老”的同时,我国老年人口出现高龄化、失能失智化、少子化和空巢化等趋势。在此情形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
纵观3个学段,6个版本教材中都出现了“平行四边形的概念”知识点.在第二和第三学段,除北师版外,其它5个版本均出现了“性质1(对边相等)”知识点;冀教版和青岛版都出现了“性质2(对角相等)”知识点.“高”“底”和“性质5(是中心对称图形)”等知识点与相关知识点组合情况在不同版本有较大差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幸福感是衡量老年人晚年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高主观幸福感源于老年群体现实生活需求的不断满足,幸福感高的老年人生活质量也较好(张秀敏等,2017)。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和感受也会出现不同的变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理想老龄社会不仅要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还要实现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年数据,比较不同性别及其他特征变量下高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并基于性别差异视角,分析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影响因素即心理健康变化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果,以期为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评价,提高其生活质量,有效实现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主观幸福感
作为个体主观感知的一部分,主观幸福感不仅包括身体无疾病,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对个体心理功能和经历的评估(Ryan et al.,2001)。主观幸福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评估幸福感,即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其整体生活和认知的评价及判断;二是情绪幸福感,即个体短时间内的心理感受,包括开心、悲伤、紧张等各种积极和消极情感;三是自我实现幸福感,即个体对生活意义和目标的判断(Steptoe et al.,2015)。总之,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多元概念,包括情感和认知两部分(Dinner,1984)。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通常反映其精神状态,是评价者根据某些自定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和认知,同样包含上述三方面的内容(王红,2015)。出于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的需要,国内外学者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通常选择其中某个方面来判断或衡量相关主体的主观幸福感。
从主观幸福感相关理论来看,按性质可以将其归纳为“自下而上”的理论和“自上而下”的理论。“自下而上”的理论基于一定假设——人们都有基本需求——认为,如果生活环境能够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人们就会感到幸福;“自上而下”的理论则关注个人内在因素,即个人如何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解释和应对生活环境及经历的事件,从而使其获得不同的主观幸福感(佩沃特,2009)。目前来看,学者们关注较多的理论主要有两个——社会比较理论和目标理论。社会比较理论是指,人们判断其满意度时,会将自身与多种标准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标准高于个人现状,则会导致个人满意度降低;如果个人现状要好于所选标准,那么个人满意度就会提升。目标理论则将主观幸福感视为结果,即是否达到目标或满足需求:个体实现较大的进展或达到目标,就会产生积极情绪;没有进展或未能达到目标,则会产生消极情绪。
(二)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主观幸福感水平与个人性格、人口学因素和文化因素等是密切关联的。研究发现,愉悦性和严谨性人格与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关联,例如,自尊和乐观的人格倾向于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佩沃特,2009)。国外研究表明,年龄和幸福感水平呈“U”形关系,中年时期人们的幸福感水平往往是最低的,而且也是处于付出最多、精神压力最大的时期(Blanchflower et al.,2008)。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低于男性老年人,她们通常会经历更多的负面情绪;随着年龄增长,主观幸福感在不同性别之间呈现显著差异(Pinquart et al.,2001)。但是Zebhauser等(2014)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相比女性老年人,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因为女性老年人更倾向于参加社会活动,从而使她们感到更快乐和放松,相比较而言,她们更擅长沟通,并能及时疏导不良情绪,而男性老年人在发展和维持亲密的伙伴关系时,相比女性老年人显得更加困难。
除上述影响因素之外,经济状况(贺志峰,2011)、身体健康状况(Shields et al.,2005)、社会关系(Shankar et al.,2015)、社会支持(方黎明,2016)等也是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此外,Puvill等(2016)发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不好并不与其较低的主观幸福感相关,但负面的心理健康却与其较低的主观幸福感高度相关。
(三)心理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综上所述: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状况与生活中的诸多方面相关,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的老年人往往拥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反过来,有较高主观幸福感的老年人也会更加注重各方面的沟通互动,且更擅长于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果缺乏不同个体特征下的差异比较和基于性别区分的心理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分析。本研究拟基于性别差异视角,探讨高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内在关系。
美国学者拉贾·切蒂认为,个人最优决策往往取决于其体验效用,体验效用的衡量指标通常采用自评幸福感(吴敬涟,2017)。如果预估某种行为会带来较高的效用水平,那么个人便会采取相应的行为来达到满意的效用水平;反之,个人就会放弃该行为或选择其他可替代的行为,以维持较高的效用水平。高体验效用的个体进行最优决策时,趋向于选择有利于其身心健康的行为,反过来,积极健康的行为也会促进个体获得更高的效用水平,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不断促进个体效用的提升。因此,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离不开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借以维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方式。Lukaschek等(2017)在探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时发现:代表精神健康的三个关键指标——抑郁、焦虑和睡眠问题——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独居仅仅增加了女性老年人出现较低幸福感的可能性。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研究较少,赵科等学者(2014)通过研究重庆市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否,与主其观幸福感评价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心理健康状况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影响因素,其外延非常广泛,它不仅指没有心理问题,而且也指要有积极向上、适应环境的能力(靳永爱等,2017)。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和米特尔曼提出了个体达到心理健康的十条标准,包括是否有充分的安全感,是否对自己有较充分的了解,生活目标是否切合实际,以及能否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Abraham et al.,1937)。日本学者松田岩南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人对内部环境具有安定感,对外部环境能以社会认可的方式适应”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栾文敬等,2012)。国内外的大量研究也表明,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与婚姻(Harootyan et al.,1994)、家庭及朋友关系(Larson et al.,1986)、生活(Cohler,1983)、社会经济地位(薛新东等,2017)、身体健康状况(Chida et al.,2008),以及社会支持(吴敏等,2016)等因素密切相关。退休后闲赋在家的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由于社会角色缺失和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主观上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波动,进而影响到其生活满意度和晚年生活质量。
遥控控制模块主要实现的控制功能包括主机启动、主机停车、主机调速和换向,主要功能流程见图7。主机正常换向时,程序控制主机降速至制动转速之后输出停车指令至电控系统DCU,待主机停机稳定之后输出启动指令至电控系统DCU反向启动主机。当主机应急换向时,与主机正常换向不同,主机转速降至制动转速以下,同时输出停车指令和空气刹车指令,快速制动主机。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年数据。该调查的基线调查于1998年进行,随后的跟踪调查分别在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年以及2011年进行。CLHLS基线调查和跟踪调查涵盖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除外)中的23个。2010年的调查涵盖区域总人口约11.56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5%。CLHLS2002年及以后的主要调研对象的年龄范围从80岁及以上扩大到60岁及以上。调查在22个调研省级行政区(不包括后来加入的海南省)随机选择约一半的市/县作为调研点,在被访对象自愿的前提下入户调查。
对于高龄女性老年人而言,心理健康变量中“感到难过或压抑”(2.839,1.980~4.072,p<0.01)以及“有睡眠问题”(1.383,1.018~1.878,p<0.05)均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是否“失去兴趣”对其幸福感水平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感到难过或压抑”对高龄女性老年人的影响程度大于“有睡眠问题”的影响程度,负面的精神健康同样会带来较低的效用水平。随着模型中变量的逐渐增加,高龄女性老年人年龄越大者,出现低主观幸福感的可能性越大,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1.016,1.001~1.032,p<0.05)。居住方式的选择不会显著影响高龄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这两点均与高龄男性老年人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措施二:对基坑周边进行限载,限制基坑两侧重型运输车辆通行;加强现场施工组织管理,合理组织施工节拍,形成流水作业,在具备基坑封底条件下,及时完成底板施作,负二层侧墙、中板、负一层侧墙、顶板施工紧密衔接。
(二)变量设置
在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针对80岁及以上的高龄男性老年人和高龄女性人分别进行逐步二元Logistic回归,其中模型1只包含人口统计学特征,模型2依次加入生活方式(由于是否吸烟、是否喝酒变量在模型中不显著且效果不佳,故不再纳入模型),模型3加入身体状况和健康保障变量,模型4加入自变量心理健康状况,以期更全面地反映不同性别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见表3、表4)。
自变量:心理健康状况,即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否对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本研究选取“过去一年中,您是否至少有两个星期一直感到难过或压抑?”,“过去一年中,您是否至少有两个星期对业余爱好、工作或其他您通常感到愉快的活动失去兴趣?”,以及“您现在睡眠质量如何?”①调查将睡眠质量划分为从“很不好”到“很好”的五个等级。出于分析需要,本研究将“很不好”“不好”两个等级定义为有睡眠问题,其他三个等级则为没有睡眠问题,分别记为0和1。等三个指标来衡量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将其中负面的心理健康状况简记为“感到难过或压抑”“失去兴趣”和“有睡眠问题”。以上每项指标均分为两个等级,回答“是”记为0,“否”记为1。
2010年7月2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加快实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加强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建立基层防御组织体系,提高山洪灾害防御能力”。按照此次会议精神和水利部统一部署,辽宁省于2010年8月启动了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完成2010年、2011年共计42个试点县(市、区)的建设任务,并在2012年汛期发挥了巨大的防灾减灾效益。
控制变量:随着年龄增长和个人所受教育不同,老年人在幸福感知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同时,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会更高(邢华燕等,2016),本研究将户籍、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②由于高龄老年人受教育年限的分布特点,将受教育年限在9年及以下的定义为低教育程度,9年以上的定义为高教育程度。和居住安排等纳入模型。收入状况也会制约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故将回答“生活在当地比较困难和很困难”的归为低收入,回答“生活在当地一般和很富裕”的归为高收入,分别记为0和1。生活方式则选取数据中的“您现在抽烟吗?”“您现在喝酒吗?”以及“您现在是否经常锻炼身体?”等三个指标来衡量。每项指标均有两个选项,回答“是”记为0,回答“否”记为1。身体状况和健康保障采用国际流行的Katz指数量表,将洗澡、穿衣、上厕所、室内活动、控制大小便和吃饭等六项日常活动能力均分为三个等级——不需要任何帮助,需要部分帮助和完全需要帮助。其中至少有一项不能独立完成则定义为失能状态(尹银,2012),记为0,其他情况记为1。健康保障采用“您是否每年进行一次常规体检?”无常规体检记为0,有则记为1。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研究在上述分析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不同特征变量上的差异以及心理健康状况对不同性别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具体方法是:首先,采用基本的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高龄老年人不同主观幸福感的人数分布,并用卡方分析来检验这些差异是否显著;其次,针对高龄男性老年人和高龄女性老年人分别进行逐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影响因素尤其是心理健康状况在不同性别之间的影响差异,以期发现提升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有效路径。
四、描述及差异比较分析
(一)高龄老年人的基本情况统计
在符合条件的样本中,处于80~85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共计1 084人,占比为28.96%,其余四个年龄段(86~90岁,91~95岁,96~100岁和100岁以上)的人数占比分别为21.3%,22.8%,12.2%和14.7%。其中,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有3 590人,占比为95.91%,教育程度较高的仅占4.10%;无配偶老年人为2 729人,占比为72.91%,有配偶老年人为1 014人,占比为27.10%;居住在城市者为1 825人,占比为48.76%,居住在镇和农村者为1 918人,占比为51.24%;从居住安排角度看,独居老年人有657位,仅占总体的17.55%,非独居(和家人住在一起或者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占绝大多数,其占比为82.45%;低收入者较少,为495人,仅占13.22%,高收入者占86.78%。
在高龄老年群体中,主观幸福感较高者居多,为3 012人,占比为80%,主观幸福感较低者为731人,占比为20%。总体而言,高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主观幸福感得分均值为10.93,高于高、低主观幸福感的临界线。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体情况(N=3 743)
?
(二)不同特征变量下高龄老年人高、低主观幸福感的人数分布和差异比较
如图1所示:不同年龄段高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均值较高,基本在10分以上,处于较高主观幸福感状态;随着年龄逐渐增长和身体各项机能的衰退,其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水平并没有呈现较大幅度下降,得分基本处于10~12分之间;从性别角度来看,不同年龄段的高龄男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均高于高龄女性老年人,相比高龄男性老年人,高龄女性老年人倾向于报告更低的幸福感水平(F=40.466,p<0.01);此外,80~95岁的高龄男性老年人和高龄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较小,95岁之后,其主观幸福感得分开始呈现波动变化且差距有所扩大,但其得分仍远远高于低主观幸福感状态的临界线8分。
图1 不同年龄段高龄男性老年人和高龄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差异比较
在不同特征变量下,通过对高龄男性老年人和高龄女性老年人的高、低主观幸福感描述分析可以发现,报告高主观幸福感的高龄男性老年人为1 393人,占83.87%,报告高主观幸福感的高龄女性老年人为1 619人,占77.76%,约是报告低主观幸福感人数的4倍。高龄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差异除了在婚姻状况、居住安排和吸烟三个特征上不显著外,其余变量均在1%~10%水平上显著;而高龄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则在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居住安排等变量上的差异不显著。报告低主观幸福感的高龄老年人中,有超过一半者教育程度较低、无配偶、居住在镇和农村,并且无定期体检。从心理健康变量来看,无论是高龄男性老年人还是高龄女性老年人,有心理健康问题者报告低主观幸福感的人数及占比均高于报告高主观幸福感者(见表2)。
表2 高龄男性老年人和高龄女性老年人高、低主观幸福感的描述统计及差异检验
?
(续表2)
?
综上,高龄男性老年人和高龄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都较高,大部分高龄老年人倾向于报告高主观幸福感。相比高龄男性老年人,报告低主观幸福感的高龄女性老年人在特征变量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劣势。
五、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回归结果及参数检验
因变量:主观幸福感。学者Lukaschek等(2017)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来衡量老年人的积极幸福感水平。借鉴上述思路,本研究运用主观幸福感得分来衡量老年人的正向主观幸福感受,选取数据中的“自评生活质量”“看待事物的积极一面”“您自己的事情是不是自己说了算”,以及“与年轻时相比,您是否觉得快乐”等四个积极指标来衡量,每项均有5个等级,将“从不”到“总是”分别赋值0~4分,得分越高,说明越积极。并且将得分范围在0~8分的记为1,定义为低主观幸福感;得分范围在8分以上的记为0,定义为高主观幸福感(Birket et al.,2009)。
对于高龄男性老年人而言,自变量心理健康“感到难过或压抑”(2.699,1.722~4.230,p<0.01)与其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精神焦虑或痛苦往往会增加他们的低生活满意度和低幸福感风险。其中,“失去兴趣”和“有睡眠问题”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但“失去兴趣”对高龄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却具有正向影响。负面的精神健康是低主观幸福感的主要风险因素,尤其是“感到难过或压抑”对高龄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最大。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年龄因素在四个模型中均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随着年龄增长,高龄男性老年人出现高主观幸福感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并且基本维持在比较高的状态,对此有学者称之为“年龄悖论”(Wettstein et al.,2016)。与其他居住方式相比,选择独居方式的高龄男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0.565,0.368~0.868,p<0.01)。此外,定期体检作为老年人自我调节和应对健康状况变化的有力手段,对于高龄男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3 不同模型中高龄男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结果和参数检验(N=1 661)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
第一,分析哲学将主客体二元对立绝对化固然错误,但雷可夫和约翰逊的体验哲学反对任何超验的东西,用绝对的一元主义经验论代替绝对的二元论,这似乎与分析哲学一样,犯了绝对化的错误。如果只有体验的现实才是真,那么现时状态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用客观的术语来界定。然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现时状态是多重现实构成的多重系统。并且如果体验理性思维植根于实在现实,又如何解释早已存在的现实的起源与定义。如果承认身体内存在不确定的现实,就不能认为现实全是体验的。另外,将真值的对应论批判为错误的,是否完全令人信服,也值得讨论。
表4 不同模型中高龄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结果和参数检验(N=2 082)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
由于该数据的高龄老年人样本占比较高且符合分析需要,故本研究选取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在选取主要变量并剔除相应的缺失值后,最终有效样本为3 743个。其中男性老年人样本为1 661个,占比44.38%,女性老年人样本为2 082个,占比55.62%。
从高龄老年人整体来看,随着模型中变量的增加,部分特征变量和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减弱,但依然在1%~10%的水平上显著。相比居住在城市的高龄老年人,居住在镇和农村的高龄老年人经历低主观幸福感的可能性更大。收入状况在高龄男性老年人和高龄女性老年人四个模型中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收入状况较好的高龄老年人相比,低收入状况会使高龄老年人面临更低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同理,不经常锻炼的高龄老年人低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概率更高,处于失能状态也会显著影响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水平。
(二)结果讨论
无论是高龄男性老年人还是高龄女性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都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影响。其中,高龄女性老年人“感到难过或压抑”对其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大于“有睡眠问题”的影响程度。相比高龄男性老年人,高龄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Abraham et al.,1937)。对于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来说,他们已经处于退休闲赋在家的状态,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渐失去,其自尊心和自我认同感也变得更加脆弱和敏感,对外界的耐受力和适应力不断下降,一旦生活中不如意的人和事出现,老年人较长时间感到难过或压抑,便会加剧其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到其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评价。高龄男性老年人是否“有睡眠问题”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而高龄女性老年人由于生命前期诸多劣势的累积,以及可能在生活中依然需要承担抚养孙辈的角色,她们的身体状况通常相对较差,进而影响到睡眠质量,导致更严重的身体不适和内在焦虑,最终会影响到其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评价。所以,睡眠问题对高龄女性老年人来说不容忽视。
此外,对业余爱好、工作或其他活动是否失去兴趣,并没有显著影响高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其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方面,高龄老年人由于受到同伴或家人影响,开始对新的事物或爱好产生兴趣,在对之前的活动失去兴趣的同时,又有新的替代物出现,例如广场舞可以消弭对从前活动的兴趣缺失所带来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此种状态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周期性,高龄老年人由于暂时的身体、外出或其他方面原因而对业余爱好、工作或其他活动失去兴趣,并不会影响到个体的整体主观幸福感。因此,积极关注高龄老年人的情感和心理健康,尤其是当高龄老年人出现难过或压抑以及有睡眠问题时,要帮助其积极调节,选择最优决策即积极健康的方式应对,提升老年人的效用水平。其中的调节措施包括加强高龄老年人与家庭成员和外界的互动,努力改善并化解其消极情绪,等等。
深圳综合指数的长期走势是一个上升通道:连接1997年5月高点,与2007年10月(或2008年1月)高点,作上轨;以2005年7月低点做下轨。此长期上升通道再分成四等分,分别标记为A、B、C及D区域。按照以前的看法,A区为低风险区,B区为偏低区域,C区为偏高区域,D区为高风险区。2015年见顶后,我之所以仍然期待还有一个第5浪,是基于再触及长期上升通道的上轨,但事实是已经不再有此机会,反映在现实上应该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未来的放缓。见顶后2015年9月及2016年出现两次短期触碰长期上升通道的中轨,引发反弹,但最终震荡后今年下破中轨,并于第三季度跌破B区下限而进入A区。
社会满意度理论指出,掌握更多资源和机会的社会成员通常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龄女性老年人在角色分工和社会资源方面存在一定劣势,在自身期望和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随着年龄增长,会进一步延续这种不利情形,进而导致较低的主观幸福感。而高龄男性老年人则相反,随着年龄逐渐增长,其出现较高主观幸福感的可能性通常逐渐增大。这一方面可通过社会情感选择理论(Carstensen et al.,2003)得到解释,即高龄老年人已逐渐适应并接受所处状态,同时其自身情感变得更加成熟,并会选择相对更积极和友好的方式来暗示自己;另一方面可通过U型理论得到解释,即45~54岁是人的一生中幸福感水平最低的时候,此时工作压力最大且收入和付出也最多,大部分个体会选择放弃目前的幸福感体验,以期获得未来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
从居住安排角度来看:是否独居对高龄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独居的生活方式不会显著降低她们的幸福感水平;而高龄男性老年人在独居方式上报告高主观幸福感的概率更高。之所以如此,其可能的原因是:高龄女性老年人在社会交往中更容易通过亲人和朋友等途径,倾诉或表露其负面情绪,不论是否与家人居住,她们的负面情绪通常都能得到有效疏导;相比较而言,高龄男性老年人则由于其本身的社会角色期望,通常不会直接表露其内在感受,为了获得较高的效用水平,他们更偏向于选择独居的生活方式来自我调节和消化。
由表1可以看出,与原矿相比,经过钠化后,APT-Na的CEC值均有所降低,当碳酸钠浓度超过0.225wt%时,APT-Na的CEC又呈现升高的趋势,这与黏度的变化趋势类似,但CEC的变化幅度并不大,经过相关性分析发现,碳酸钠浓度与 CEC并不符合线性关系,但经过平方拟合,得到的碳酸钠浓度( w N a2 CO3)与 CEC的回归公式为CEC=相关系数为0.690,说明碳酸钠浓度与CEC的关系较为明显,一定程度上证明凹凸棒石与碳酸钠悬浮液发生了离子交换。
收入状况是影响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收入较低通常意味着高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缺乏相应的经济保障,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加剧他们的焦虑和不幸福感;而且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话语权以及在代际经济支持中发挥的作用通常也较小,不利于其提升主观幸福感。
幸福感的提升离不开健康的身体,积极参与锻炼对于促进高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美国老年学家霍曼等(1992)曾指出,老年人参加锻炼和各种闲暇活动,可以为将来的生活提供新的源泉和动力,并且会使其在晚年更加自信,从而心理上更加愉悦,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更高。健康状况不佳且处于失能状态的老年人,生活上需要别人护理,依赖性较强,自我效能感往往在这个时候变得更弱。他们由于担心成为家庭负担而背负较大的心理压力,由此出现低主观幸福感的概率更高。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CLHLS2011年数据,通过比较不同性别高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发现,高龄老年群体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评价普遍较高,高龄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高龄女性老年人。在此基础上,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性别高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心理健康状况对于高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有着显著影响,其中,负面心理健康状态对高龄女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大于对高龄男性老年人的影响程度;年龄对不同性别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有着截然相反的预测作用;居住安排仅对高龄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居住地、收入状况、是否经常锻炼和失能状态等,也会显著影响高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评价。
老年期作为个体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高龄阶段更是人生的宝贵阶段。不断满足高龄老年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对其心理健康的关注。首先,要关注高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合理分配社会和医疗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日益多样化和均等化。其次,在不断完善预防治疗和护理服务的同时,要更多地关注高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加强心理辅导和疏解,并鼓励其熟悉的亲人和朋友参与其中,不断强化其积极情绪。再次,由于性别差异和角色分工等原因,高龄男性老年人和高龄女性老年人在主观幸福感评价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要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水平和生活质量,政府和社区等主体必须在居住安排、生活方式引导和情绪调节引导等方面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关注他们的个性化需求。最后,收入状况也是影响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收入来源有限的情况下,子女间的代际经济支持和政府转移收入,可以有效改善高龄老年人的收入状况,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①流量预警规则:对8:00流量超预警门槛值的设定站点,发布一次预警;以后每过2小时巡查一次,将流量与上次预警时流量比较,如增幅达到或超过预警要求,发布预警。
法律规定,对企业商品包装著作权的侵权可以根据因侵权造成的损失来确定赔偿数额,也可以将侵权所得的全部利润都上交进行赔偿。对于国家规定的赔偿制度,要按照赔偿制度的3-5倍缴纳罚款,同时也要支付其他的相关费用。
参考文献:
方黎明.社会支持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54-63.
贺志峰.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1(S1):1-3.
霍曼N R,基亚克H A.社会老年学:多学科展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2).
靳永爱,周峰,翟振武.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社区环境的调节作用[J].人口学刊,2017(3):66-77.
栾文敬,杨帆,串红丽,等.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75-83.
王红.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缘起、现状与方向[J].西北人口,2015(1):62-66.
威廉·佩沃特,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J].李莹,译.广西社会科学,2009(6):133-136.
吴敬涟.比较:第四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吴敏,段成荣,朱晓.高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支持机制[J].人口学刊,2016,38(4):93-102.
邢华燕,韩忠敏,闫灿,等.河南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公共卫生,2016(9):1141-1144.
薛新东,葛凯啸.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7,23(2):61-69.
尹银.养儿防老和母以子贵:是儿子还是儿女双全?[J].人口研究,2012(6):100-109.
张秀敏,李为群,刘莹圆.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7(3):88-96.
赵科,谭小林,文晏,等.重庆市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性研究[J].检验医学与临床,2014(18):2513-2515.
Abraham H M,James H M.Principle of abnormal psychology[J].Journal of Nervous&Mental Disease,1937(3):355.
Birket SM,Hansen B H,Hanash JA,et al.Mental disorders and general wellbeing in cardiology outpatients-6-year survival[J].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2009,67(1):5-10.
Blanchflower D G,Oswald A J.Is well-being U-shaped over the life cycle?[J].Social Science&Medicine,2008,66(8):1733-1749.
Carstensen L L,Fung H H,Charles ST.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and the regulation of emo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life[J].Motivation and Emotion,2003,27(2):103-123.
Chida Y,Steptoe A.Positive psychology well-being and mortality: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pe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ies[J].Psychosomatic Medicine,2008,70(7):741-756.
Cohler B.Autonomy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family of adulthood:a psychology perspective[J].The Gerontologist,1983(23):33-40.
Din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J].Psychology Bull,1984,95(3):542-575.
Harootyan V L,Bengston M S.Hidden connections:intergenerational linkages in American society[M].New York: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94(14):435-447.
Larson R,Mannelli R,Zuzanek J.Daily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with friends and family[J].Psychology and Aging,1986(1):117-126.
Luukaschek K,Vanajan A,Johar H,et al.In the mood for ageing:determina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older men and women of the population-based on KORA-Age study[J].BMCGeriatrics,2017(17):126.
Pinquart M,Sorensen S.Gender differences in self-concept and psychology well-being in old age:a meta-analysis[J].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2001,56(4):195-213.
Puvill M,Linfenberg J,de Craen A J,et al.Impac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n life satisfation in old age:a population based on observation study[J].BMC Geriatr,2016,16(1):194.
Ryan R M,Deci E L.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1(52):141-166.
Shankar A,Rafnsson SB,Steptoe A.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social connec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J].Psychol Health,2015,30(6):686-698.
Shields M A,Wheatley PS.Explo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psychology well-being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England[J].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s Society,2005,168(3):513-537.
Steptoe A,Deaton A,Stone A A.Subjective well-being,health,and ageing[J].Lancet,2015,385(9968):640-648.
Wettstein M,Schilling O K,Wahl H W.“Still feeling healthy after all these years”:the paradox of subjective stability versus objective decline in very old adults’health and functioning across five years[J].Psychlogy Ageing,2016,31(8):815-830.
Zebhauser A,Hofmann L,Beaumert J,et al.How much does it hurt to be lonely?Mental and phys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older men and women in the KORA-Age stud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2014,29(3):245-252.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Oldest-old:Based on Gender Differences
TAO Yuchun1,LI Weiguo1,QIU Bin1,XU Yuanchen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Jiangxi Province,China;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Jiangxi Province,China)
Abstract: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2011,this paper did research on older persons aged 80 and above,analyzed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impact of mental health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persons of different genders.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scor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oldest oldis close to 11,and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who report high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80%.And the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ly me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women.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 that mental health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both elderly men and women,and the effect on the latter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Age has totally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well-being of both older men and women,whereas living arrangements only influence older men in a significant way.
Key words:mental health;subjective well-being;gender difference;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B8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98(2019)01-0059-13
收稿日期:2018-03-26;修改日期:2018-11-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71463015)。
作者简介:陶裕春(1966—),江西南昌人,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和失能老年人长期护理;李卫国(1991—),江西南昌人,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和失能老年人长期护理。
[责任编辑:贺拥军]
标签:老年人论文; 高龄论文; 幸福感论文; 主观论文; 男性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老龄科学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71463015)论文; 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