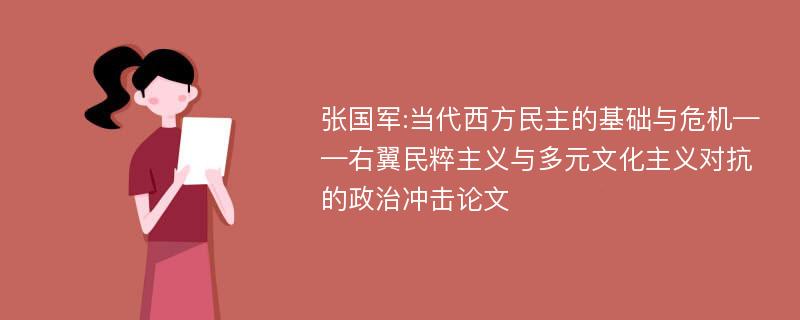
摘要:从现代国家构建历程来看,当代西方民主有效塑造合法性需要三重基础:一是从传统地域国家过渡到民族国家,二是从身份社会演化为市民社会,三是在大众崛起背景下将代议制民主改造为选举民主。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蕴于个人自由的多元主义分化为价值多元论和多元文化主义,前者主张普遍平等的个人权利,后者则追求对不同文化群体成员的差异化对待。西方的繁荣和进步助长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蔓延,使保护少数文化群体成为“政治正确”。当繁荣不再,政治正确也就成为逆向歧视,因而右翼民粹主义强势崛起。右翼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对抗将权利政治重塑为身份政治,威胁着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化个人假设,也就侵蚀着民主有效运行的基础,使西方民主体制陷入危机。
关键词:西方民主;民族国家;右翼民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
自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民粹主义强势崛起。近年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乌克兰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在总统大选中高票胜出,标志着“黑天鹅事件”事实上已变成“灰犀牛事件”。随着民粹主义的蔓延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崛起,夹杂着宗教和文化冲突的族群矛盾愈演愈烈,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发突出。就在泽连斯基大选获胜的同一天,作为对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的报复,宗教极端组织在斯里兰卡制造了伤亡重大的连环爆炸案,世界惊呼亨廷顿预言的文明冲突再次得以印证。在全球化与国家内部的多元化深度互动的背景下,文明冲突内化于国家即右翼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对抗。这一对抗不仅导致认同危机,而且正在侵蚀西方民主有效运行的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回溯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阐述民主有效塑造合法性的基础,进而分析多元文化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先后崛起的内在逻辑,以及二者的冲突对民主政治带来的冲击。
一、西方民主有效塑造合法性的基础
西方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民主,但民主塑造的合法性并非无条件的,而是以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为前提的。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民主国家数量剧增,但移植西方民主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美好生活,反而陷入持续的动荡和衰败,也就无从塑造合法性。毕竟,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服从有赖于统治的有效性,这意味着,“政治合法性需要制度化的权威(无论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进行统治的权力资源以及共同体成员间共有的规范”[1]。从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来看,民主能够发挥塑造合法性功能的根源在于,西方国家具备了有效民主的三重基础: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构建了现代国家的认同基础;通过培育市民社会构建了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通过将代议制民主改造为选举民主构建了现代国家的制度基础。
(一) 从地域国家到民族国家
国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马克斯·韦伯对其做出了经典界定,“国家是在一定区域的人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区域之内——这个‘区域’属于特征之一——要求(卓有成效地)自己垄断合法的有形的暴力”[2]。这个概念包含确定的区域、人民和统治者等基本要素,并突出强调了区域和合法垄断暴力的特征。这些要素和特征作为一个集合,适用对象是理性的现代民族国家,而非传统的封建王国和帝国。
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以及由之而来的碎片化和多元化特征。首先,王国和帝国缺乏明确边界,国家更多是一个模糊的地域,“国界只是在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才开始出现的”[3]。其次,在封建国家的层层分封中,附庸与领主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将政治认同和政治权威碎片化。即使帝国中存在基于高度集权和严密等级的君主统治,但帝国中普遍存在多个族群,“统治者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建构全社会范围内的文化同质性”,[4]因此传统国家缺乏整体性国家认同,只有狭隘的地域性族群认同。最后,在领主制分散权力之外,中世纪一直存在教权与王权的对抗,导致国家内部缺乏有效整合,各地区的文化和统治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自主性,国家对外也不具有完备的独立性,因而王国和帝国都缺乏现代的绝对主权观念。
1648年,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法国、英国、荷兰、瑞典等国和德意志诸邦与哈布斯堡王室签订系列和约,建立了延续至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该体系确立了领土界限、主权独立、平等协商等现代国际法准则,标志着民族国家形成。此后的欧洲虽然战争不断,但不再打着宗教的旗号,而是直接诉诸国家利益,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也是现代国家的标准形态。作为理想类型的民族国家意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即国家边界与民族边界相一致。与传统的地域国家相比,民族国家的首要贡献在于确定领土边界,为国家成员的共同生活提供不受侵犯的场域,同时为民众对国家的想象提供一个可视的载体,从而通过领土意识的逐渐强化构建国家认同。
其次,无论民族国家实际上由一个还是多个民族构成,国家成员都基于领土认同和政治认同而形成了统一的国族认同。国家与民族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融为一体,二者融合的必然性在于,国家构建伴随着敌我的识别和斗争,要通过塑造现实的或想象的敌人来凝聚内部成员,这就需要有效的识别和整合工具。基于血缘关系和情感归属的民族正是区分“我们”和“他们”的身份符号,民族也就为现代国家构建提供了巨大向心力。基于民族认同构建国家认同的结果是,民族国家既是政治共同体又是文化共同体,二者之间存在间隙,但包含多民族的民族国家之所以建立并持续存在的原因在于,民族成员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超越了对民族的文化认同,并将民族认同扩大为与国家边界相一致的国族认同。实现这一超越的根本在于,民族差异是自然形成并客观存在的,但将差异识别出来并用于政治动员所产生的民族归属、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却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因而安德森将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5]。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利用互联网宣传是提高潜山市的知名度极其有效的渠道。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智慧型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微博公众号以及新闻客户端进行网络宣传,开通线上旅游产品的预定销售服务,也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节庆推广、主题活动等方式开展旅游扶贫公益宣传,并加强与省内外及周边景区合作联动,积极融入省内外精品旅游线路,在重要客源地设置旅游营销机构或代理门店,实现与省内外知名景区和旅游目的地联合推介、捆绑营销。
最后,相较于传统国家权威的碎片化和多元化,民族国家则基于整体性国族认同确立了主权至上的原则。主权至上对外意味着国家独立、主权平等,相互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或藩属关系;对内意味着国家是最高政治实体,垄断暴力并享有最高统治权。民族国家初期的政治形态普遍是君主专制,在市民和大众尚未崛起的背景下,这是摆脱中世纪领主制权威碎片化和认同多元化的必然要求。霍布斯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但他通过社会契约论构建的却是君主专制政体。霍布斯认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在产生强大主权者方面并无不同,三者“向我们指明的是三种主权者,而不是三种教士;换句话说,它们所指明的是三种家长,而不是三种童蒙塾师”[6]。君主只是霍布斯构想的强大主权的完美承载者,必须如“利维坦”那般强大的不是君主,而是主权。
(二) 从身份社会到市民社会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社会分工水平极低,社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并且不同种族、民族和宗教共同体相互隔绝,缺乏交往流动。即使偶有迁徙,尤其是各共同体相互攻城略地直至建立帝国,也并未改变这一基本局面,因为多民族帝国的有效整合策略主要是因俗而治和军事威慑,同化或一体化的程度和范围非常有限。基于夷夏之辨的朝贡体系维持了中华帝国数千年的大一统局面,因俗而治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相反,曾经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却在堕落和掠夺中激起反抗,最终覆灭于蛮族入侵,并且,正是使其灭亡的蛮族入侵奠定了现代欧洲的政治版图[7]。
几近静止且相互隔离的生存状态将人们束缚于共同体,认同来源于且局限于共同体,传统社会普遍是身份社会,人们不被视为个体,而是各种团体的成员,“作为社会的单位的,不是个人,而是由真实的或拟制的血族关系结合起来的许多人的集团”[8]。身份社会的首要特征是存在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的非理性,人们盲从不可证伪的外部权威。在科学产生之前,宗教承担着解释世界和整合社会的功能。即使在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对自然神和家火的崇拜也是维持城邦凝聚力的最重要因素,由此导致城邦政治的整体性以及公民身份的狭隘性和排他性。在中世纪,信仰更是统摄一切的不可置疑的最高法则。信仰至上,且信仰赋予世俗权力以合法性,这一套秩序是既定的,任何人都只能在既定秩序内活动,否则必然遭受制裁。
其次,传统社会中的身份并非理性反思的结果,而是与生俱来的禀赋。传统社会是一种同质共同体,否定和排斥人的自由选择,共同体赖以存续的基础是滕尼斯所说的“本质意志”[9],它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并且必须从“过去”中获得解释。由于中世纪国家普遍存在国王与教会、各级领主之间的权力争夺,统治秩序极其混乱,但各种秩序最终都会施加于普通民众身上,这就将人们的身份固着于多重社会关系。多重社会关系界定的身份足够牢固且富有韧性,个体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自主探寻生存的意义。
最后,身份社会囿于各种具体的差序关系,缺乏普遍性规则。身份的先赋性意味着每一共同体都具有高度的文化同质性,但社会成员遵从的权威秩序并非一层,而是从家族、村落直至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多层级共同体构建的多层秩序。这就形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差序结构,“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10]。循着这一逻辑往下推的必然结果是,人们根据血缘—地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对待他人的标准和方式,而缺乏超越私人关系的普遍性准则。差序结构导致共同体内部的同质性与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性并存,进而使文化的封闭性与多样性并存。
由于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进,以及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巨大市场和利润的刺激,西方世界开始了快速的理性化进程。现代国家构建要形成对国家的整体性认同,身份社会中多元认同的封闭性和狭隘性成为整合社会和建构国家认同的阻碍。因此,一方面,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也是销蚀身份的过程。君主通过打击领地贵族和教会势力强化权威,加强社会政治整合,构建统一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提供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以刺激经济增长,对外则抢夺殖民地获得资源和市场,并通过民族主义动员争夺霸权。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得以建立还要归因于“以市场为领地的资本”提供的“经济暴力”[11]。在中世纪的夹缝中已经存在独立的市民阶层,但其当时尚未在政治上崛起。在早期民族国家的掠夺和征战中,君主扩大权力的欲望与市民阶层增殖资本的需求相结合,促成二者的合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脱胎于市民阶层的资产阶级逐渐壮大,传统的封建秩序和身份社会逐渐瓦解,基于契约关系的市民社会走向成熟。
传统身份社会具有非理性、群体优先性、身份先赋性、文化差异性和规则特殊性的特征,这些都消逝于市民社会之中。市民社会是理性社会,理性意味着,“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12]。基于普遍平等的个体理性,人们从群体关系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并界定其身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分工交换的社会交往和流动大大增强,群体身份差异逐渐为个体分工和选择差异替代,由此形成人与人互有差异但又相互依赖的有机团结社会[13]。理性化意味着人的本质的抽象化和普遍化,人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境遇中独立出来,成为自由主义所描述的原子式的个人,这种人学基础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构建的逻辑起点。
(三) 从代议政治到选举民主
现代国家构建包括外向和内向两个维度,民族国家解决的主要是外向的国际关系问题,这已完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理性化之后,宗教从政治领域中退出,这实现了人的解放,同时也打破了君权神授的神话,从而导致世俗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与专制王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深化,突出表现为双方在征税上的分歧,因而需要重构政治合法性。国家的根本特性是基于暴力的强制性,现代国家则要“合法”地垄断暴力,在基于分工交换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即契约关系被西方思想家引申到政治领域,社会契约论成为现代国家理论的基本模型。
成熟的思想体系都以其独特的人学作为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社会契约论的人学基础是剥离了一切社会属性的普遍的抽象的人。这种抽象人学根植于市民社会,它瓦解了传统身份社会施加于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如果身份来源于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那么身份也必然具有差异性、具体性和特殊性。构建现代国家就要消除差异身份和狭隘认同,将人还原为同质的、抽象的、一般的人,以便实现对民族国家这种缺乏文化内核的新型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和服从。由此而言,西方现代政治建构的基本逻辑就是,“将世界历史建构为一个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单向运动,进而将政治共同体建构在高度同质的人民想象之中”[14]。
抽象人学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体现即“自然状态”设定,尽管不同思想家对自然状态的想象不尽一致,但共同特征是抹去了社会和历史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基于自然状态的完全自由平等假设,社会契约论构筑了包括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治分权、有限政府、政教分离等原则的现代西方政治。为民族国家提供合法性证明的是人民主权,并且在历史上的各种国家形式中,“民族国家是唯一以人民共同意志为其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政治组织形式”[15]。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主权原则的实践又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代议制民主和选举民主。
不仅如此,生物产业产品还享受减免税(增值税)政策,生物有机肥自2008年起免增值税。2014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和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有关问题的公告》,规定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毒素、人或动物的血液或组织制成的生物制品依照3%征收率。
2016年的贵德县冬小麦种植全过程的情况为:2015年9月25日播种、2015年10月8日出苗、2015年10月20日三叶、2015年11月2日分蘖、2015年11月12日越冬开、2016年3月14日返青、2016年3月30日起身、2016年4月22日拔节、2016年5月4日孕穗、2016年5月10日抽穗、2016年5月21日开花、2016年6月22乳熟、2016年7月4日成熟。
“熵权”理论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借用信息论中熵的概念,主要是根据各指标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其权数。假设在m项指标、n个被评价对象的评价体系中,根据熵权法理论,由式(2)计算得第j项指标的熵值,由式(3)计算得j项指标的熵权(权重)。
人民主权的含义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并从中产生两种民主形态。积极含义从正面回答主权实际归属于谁,卢梭基于“公意”建立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16]正是对此问题的经典诠释。消极含义则回避实际归属,只将人民主权作为一种合法性声称,民主只能是洛克所言的“由人民的同意和委派所授权的一些人”[17]的统治。积极的人民主权过于理想化而难于实践,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向来被视为卢梭政治哲学的注脚,因而现代西方民主秉持消极民主观采取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可见,现代民主从建立之初就力图排斥、抑制大众参与政治。大众在政治上一直被视为危险因素,对“多数暴政”的恐惧从古希腊以来充斥于政治观念史。
代议制民主是代议和民主两种政治形式的结合。作为一种委托代理机制,代议制与民主并无关系,它是“人民”授权某些人作为代表组成代议机关执掌政权。代议制并非现代政治的产物,而是产生于中世纪国王为解决财政危机被迫与贵族做出的妥协。更关键的是,有资格被代表的“人民”有严格界限,绝大多数人没有选举权。出于对无产者参加选举可能威胁财产自由的警惕,“多数暴政”论者主张以财产和身份等标准限制选举资格,因此英国议会改革之前只有 40万选民,占总人口的1/60。直到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才实现普选权。
由于现代西方政治建构于抽象人学基础之上,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理性的普遍化和平等化在逻辑上必然引申出所有人都有权利参与政治的结论,西方国家无法为其限制选举权的行为进行合法性论证。普遍理性的逻辑确实导致了大众的政治崛起,1930年代欧洲各国相继爆发工人运动,一项重要诉求即普选权。社会主义理论成型之后,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对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构成了挑战。因此,开放选举权吸纳大众进入政治是必然趋势,现代政治也必然进入大众民主时代。
在大众崛起的压力之下,西方思想界从多数暴政命题转向了大众心理分析,应对大众的策略从政治排斥转向诱导控制,“要想领导他们,不能根据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是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18]基于勒庞的群体心理分析,熊彼特重构了民主理论,将民主视为政治家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获得执政地位的制度安排,民主并非人民在统治,而是政治精英的统治。将人民与政治家勾连起来的中介是选举,但熊彼特指出,“选民的选择——在意识形态上被尊称为人民的召唤——不是出于选民的主动,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对选择的塑造是民主过程的本质部分。”[19]因此,选举民主是熊彼特在群体心理分析基础上重述精英统治的结果,他通过“塑造”选民,把大众崛起与寡头统治这两个相生相克的要素捏合在一起,大众与精英的平衡也就成为当代西方民主的内在逻辑。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及其极端化
从代议政治到选举民主的演变揭示了西方政治抑制大众参与的逻辑,民主与自由之间向来龃龉不断,民主在自由主义中充其量是一个工具价值,自由才是西方文化的至上价值。基于不受外部强制的自由选择,西方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特征。问题在于,多元化是非常笼统的概念,从国家构建角度看,西方社会中存在两种既相互关联又有内在冲突的多元化,即价值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二者产生了两种政治思潮,即价值多元论和多元文化主义。
(一) 从价值多元论到多元文化主义
在除魅后的理性社会中,各种完备的宗教道德学说及其建构的等级秩序或者走向崩溃,或者被限定在纯粹私人领域,身份和文化差异或消失殆尽或隐而不显。这突出了人的价值,但也带来普遍的信仰危机。“上帝死了”之后,人们不再依循群体的既定秩序,必须自己做出理性选择,完全诉诸理性选择的秩序,必然产生茫然失措、不知所踪的恐惧。虽然现代政治建构于抽象人学基础上,毕竟人是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建构于自然状态的政治只提供了公共政治框架,并不能指导人们如何生活,如何选择。一旦行动起来,人的选择和生活仍旧受构成传统身份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传统差异性仍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场域,换了一副面孔,“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12]。
面对“诸神冲突”,以赛亚·伯林提出价值多元论进行解答,并基于价值多元这一客观现实而非虚构的自然状态对自由主义进行重新论证。价值多元论认为,社会中同时存在诸多值得追求的价值和目的,它们具有同等的绝对性和终极性,相互之间不可通约,不可公度,因此常常相互冲突;不存在能够同时实现所有价值的渠道,并且,造成巨大人类灾难的正是所有价值“最终都是相互包容甚或是相互支撑的”这种信念;因此,人类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永久性的价值冲突之中。价值冲突不可解决,人们只能做出取舍,而取舍,伯林认为只能诉诸“自由选择”。如果否定了价值冲突而认为存在某种完美的和谐状态,“选择的必然性与巨大的痛苦就会消失,自由选择的核心重要性也会随之消失”[20]。
武汉商学院与武汉中欧自贸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作顺应了武汉自贸区发展的趋势,为武汉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实现学校服务社会的职能。学校与企业相互合作、取长补短,重新整合教学资源,充分利用双方在教学和实践的优势,共同培养人才、发展企业、建设武汉。学校在合作中利用企业的实训基地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节约了教学资源,企业在合作中获得德才、技能兼备的储备员工节约了用人成本;校企合作的同时也为武汉留住人才,为实现百万大学生留汉作出努力。
在政治正确的庇佑下,多元文化主义复兴了主流文化一直试图将其同化的少数文化身份,从而将民族国家试图基于公民身份建构国族的努力付诸东流,国族重新碎片化为民族、种族和宗教群体。有学者认为,这种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可能导致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分歧的加深和潜在政治冲突的增加”[31],其实,多元文化主义只是使政治分歧和冲突成为可能,从可能变为现实必须要有与多元文化主义相对抗的力量。只要西方主流文化群体一如过去的半个世纪那样开放和包容,分歧和冲突就不会普遍发生。然而繁荣总是短暂的,随着西方世界普遍陷入债务危机或经济衰败,西方人对自己国家的世界地位产生了疑问,以前强势的、进步的心态逆转为现在弱势的、保守的心态,西方主流文化群体变得越来越狭隘和封闭。这种转折使政治分歧和冲突从可能变为现实,因为强势崛起的右翼民粹主义正是为了对抗多元文化主义而生。二者的对抗强化激活了多元文化主义以来的认同解构和异质化趋势,侵蚀着西方民主有效运行的基础。
价值多元论要求人们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自由选择,人们确实做出了选择,但选择的结果却未必符合自由主义的主流文化。多元文化主义正是自由选择逻辑的实践结果,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其选择大致脱离不了附着于原生身份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这样一来,在普遍平等的政治内部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平等政治,不过不是自由选择权的平等,而是文化认同和族群身份的平等。由于文化和身份源于先赋的差异,那么多元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异质性。多元文化主义要求少数群体身份被承认和保护,这种政治也就是身份政治或差异政治。
由图3可知,1.064 μm在平流雾中的前向散射最强.由表1和表2可知,1.064 μm在平流雾中的散射系数(4.3296 km-1)大于在辐射雾中的散射系数(3.612 3 km-1).说明1.064 μm在平流雾中前向散射大、散射能力强,多次散射对透过率的贡献较大,所以相同传输距离下,1.064 μm在平流雾中的衰减小于在辐射雾中的衰减.
与追求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均等化的权利政治不同,身份政治要求差异化身份得到承认,“普遍尊严的政治反对任何歧视,要求完全无视公民差异,差异政治则重新界定了非歧视,要求基于公民之间的差异对其区别对待”[21]。普遍平等的权利政治将个人自由视为至上价值,无论基于社会契约还是价值多元的论证,它一直秉持个人本位,多元文主义则坚持文化群体本位,将群体视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二者并存也就产生了“对群体进行区别对待的公民资格”[22]这一悖论:权利政治要求个人平等,对个人一视同仁,势必不能满足承认差异身份的诉求,甚至产生主流群体对少数群体的排斥;身份政治要求文化群体的平等,对群体平等对待,则必然导致个体层面的不平等,破坏平等的公民资格。
(二) 价值多元论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冲突
从现实来看,多元文化主义源于加拿大试图通过“同化”进行整合遭到抵制而不得不通过“有限认同”做出的妥协[23]。从逻辑来看,多元文化主义则是价值多元背景下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无论从哪个角度,多元文化主义都与价值多元论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3.1 小米的功效与作用 小米又名白粱粟、粢米、粟谷、硬粟、籼粟、谷子、寒粟、黄粟和稞子等,为禾本科植物粱或粟的种仁,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小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大量的维生素E、铁和磷等微量元素。中医认为,小米味甘咸,有清热解毒,健脾除湿,和胃安眠等功效,还具有和中益胃,滋阴养血的作用,小米表面的小米黄色素具有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作用。
3)通过收集现场相关故障信息及波纹表明,110kV那曲变#1、#2两台主变并列运行,且#1主变中性点接地运行情况下,故障当时那曲#1主变高压侧基本无3I。故障零序电流流过,那安线上流过的故障零序电流基本与当那线上流过的故障零序电流持平。
首先,二者对公民身份来源的认知不同。价值多元是在现代国家构建完成之后发现的事实,公民身份的普遍化、抽象化和平等化早已实现,其后只需人们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多元文化主义则比较复杂,一方面是基于价值多元现实的自由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拒斥西方同化而保留传统的结果,这意味着多元文化主义中夹杂着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因素。
其次,二者对公民身份的认知框架不同。在价值多元论视域中,由于普遍平等的公民身份已经实现,人们的认同具有高度同质性,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并不存在能够分散国家认同的亚国家共同体,因此,现代国家的基本关系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公民身份只是相对于国家而言。随着民权运动的深化,长期被抑制和忽略的少数群体的抗争引起人们关注和同情,这与后现代文化的反主流、反本质主义倾向相结合,使少数文化群体作为亚国家共同体分散了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因此,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身份夹杂着个人权利和群体权利,这是一种个人—群体—国家的三层结构。
两大身份阵营之间的对立是包含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对立,基于身份差异的全面对立必然会使利益分配与身份认同两种诉求相互强化,导致社会撕裂和政治分裂。有学者发现中东欧国家中存在一种“恢复性民族主义”,它试图抵制外来文化和群体的侵蚀,恢复主流文化在其辉煌时期的中心地位,“人们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反精英、反建制情绪无关,而与维护民族文化纯洁性和民族认同的中心地位的这些道德信仰有关”[34]。相较于利益冲突,基于民族文化和道德信仰的诉求更加纯粹,更易于形成长期稳定的支持,当然也因此更难以与其他文化达成妥协。
最后,价值多元,还是文化多元?这是两种多元主义冲突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界定,它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基于自由选择的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文化只是各种价值观念的排列组合,各种文化都要尊重包括普遍价值在内的多元价值,否则,“为推进文化多样性而不顾及文化的内容,就把多元论的观点降低成为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24]。这种开放的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进行了稀释化处理,文化群体被弱化为人们自由选择并可自由退出的社会团体,从而并未真正关涉当下正对西方社会整合构成威胁的多元文化冲突。封闭的多元文化主义否定价值排列组合这种弱文化概念,而认为文化是包含各种习惯、信念和制度的有机整体,尽管可以从中识别出多种价值,但它们却相互联结和依赖,不可拆解和化约,个体行为须置于文化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诠释。
与价值多元论相冲突的,只是封闭的多元文化主义,它否定文化内部的多元性,否定人的自由选择和退出,文化群体赋予个体以目的,个体依附于文化群体,从而使文化群体成为一个内卷化的封闭共同体。由于群体高居于个体之上,以群体权利为名漠视甚至压迫个体权利的现象必然会出现。由于女性在各种传统文化中普遍遭受歧视,“女权主义和少数族群的群体权利之间很有可能发生冲突,即使后者是基于自由主义论证并受其限制的群体权利,这种冲突仍然存在”[25]。否定了自由选择和退出,文化群体内部也就保持着高度同质性,多元文化之间却不存在基本的共享价值,只能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共同体,因而封闭的多元文化主义尚未脱离传统社会,或又将现代社会推回了碎片化的传统社会。
2.3 ER-β 基因Alu I 多态性与促卵泡激素、黄体生成素和雌孕激素测量结果 广西壮族绝经妇女45~50岁5个ER-β 基因Alu I 酶切基因(AA、Aa、aa、a、A)组的血清雌二醇、孕酮水平中,AA基因组、Aa基因组、a基因组、A基因组,四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aa基因组与其它4组之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aa基因组的雌二醇和孕酮血液水平明显高于其它4组(P<0.05),而aa基因组的促卵泡激素、黄体生成素明显低于其它4组(P<0.01),见表3、表4。
数学教学内容是抽象的,对于具体形象思维占优势的小学生来说,动手操作是他们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习内容及学生特点,合理选择、组织操作活动,扎实推进操作活动的开展,让学生在亲历中体验“做数学”,在体验中实现数学的“再创造”,积累扎实的数学基本活动经验。
(三) 从“政治正确”到右翼民粹主义
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多种族群,经济全球化加快了人口国际流动,更使族群结构复杂化。1970年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开始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政治鼓励更使多元文化主义得以蔓延和强化,保护少数文化群体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正确”的核心信条。相较于历史中主流文化群体对少数的压迫和排斥,这一政治正确无疑具有显著的进步性。但是,“支持‘政治正确’背后的逻辑,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没有合理的界限,也就是矫枉必须过正”[26],这意味着保护少数相对于其他理念而言具有绝对优先性,任何质疑和反对都会涉嫌歧视少数。西方社会就在这种政治正确的共识中将多元文化主义推向深入,身份政治的狭隘化和极端化日益凸显。
首先,政治正确容易将有关族群、宗教和性别等文化议题的社会事务政治化,使相关争论极端化,甚至罔顾事实,压制言论自由。这些问题在一向激进的西方校园中尤其突出,并蔓延到社会诸领域,族群问题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其次,多元文化主义要求对公民因其身份不同而区别对待以实现群体间平等,比如降低少数文化群体成员的招生和录用标准。美国很多白人学者对黑人研究不以为然,甚至认为,“美国黑人研究是一个由有罪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发明的伪学科,以便让黑人知识分子摆脱困境,使他们有机会在精英院校担任教授,而无须在数学这样非常困难的学问上证明自己的能力”[27]。对公民的区别对待必然会挤占主流群体成员的机会,造成“逆向歧视”。最后,政治正确对难民和移民产生巨大吸引力,他们却无动力融入社会,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他们也没必要融入。这就使主流文化失去了社会整合功能,导致社会结构的碎片化,并产生公民身份危机。
对立的双方都根据自己对人民概念的界定将对方称作人民的敌人,并将其妖魔化,民粹主义惯常通过污名化精英群体实现内部团结和凝聚力量,在这一层敌我区分之外,右翼民粹主义又通过更加外显的文化身份符号塑造“他者”,双重敌我意识的重叠,使右翼民粹主义获得巨大行动能力。有研究通过分析 1999年到2014年的美国主流媒体对加拿大穆斯林的报道,发现报道的基调是中立的,但普遍把穆斯林描述为“社会的外来者”,并且有的报道“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混为一谈,并认为所有年轻的穆斯林男性都是潜在的敌人”[35]。对穆斯林群体的妖魔化在西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穆斯林恐惧症”,这大大凝聚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共识,但同时也将想象的敌人塑造成了真实的对抗力量。9·11事件之后,美国大部分穆斯林认为他们作为群体而非个人受到了歧视,因此感到焦虑,这种群体焦虑使穆斯林积极行动起来抵制歧视,“他们正在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这个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统一”[36]。对于陷入恶性循环的恐怖袭击,妖魔化宣传无疑要负主要责任。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从中世纪的重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个人获得了尊重,人性得以觉醒,但人性觉醒的背面是人性的堕落。在人性觉醒与堕落的双重作用之下,理性国家要得到服从,除了依靠垄断暴力之外,还需发掘内在动因以提供情感支持。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正是人们的情感归属和精神家园,因此现代国家构建诉诸于民族情感进行政治动员,使民族和国家融为一体。如上文所述,二者具有的区分身份和区分敌我的特性也相互融合,使民族动员成为可能。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一种与胰岛素抵抗和遗传易感性密切相关的代谢应激性肝脏损伤,其可发生肝脏纤维化从而导致肝硬化[1]。目前,国内外均缺乏对NAFLD有特定疗效的药物,而且,不同的临床指南推荐的药物不同。因此,本文回顾性分析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诊的NAFLD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降糖药、他汀类、ACEI、钙离子拮抗剂是否对NAFLD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有协同治疗效果,旨在为NAFLD合并2型糖尿病人群选择合适的药物提供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工业社会中的民粹主义处于政治光谱左端,反对精英垄断资源和权力,主张平均分配和直接民主。当前这一波民粹主义左右翼夹杂,但主流是右翼,其诉求从政治经济权利平等化扩展到文化领域,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融为一体。右翼和左翼有相同点,“腐败是一般民粹主义论点的基础,‘纯洁的人民’反对‘腐败的精英’经常被民粹主义政治行动者利用,不管右翼还是左翼都是如此”[28]。当然二者的区别更为显著,右翼民粹主义的“人民”概念比传统左翼更为狭隘,它不仅将政治经济精英排除在外,还排除了“难民、穆斯林或其他文化、种族和宗教团体”[29]。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直接诱因是难民危机,这又源于西方在中东推行民主化失败而使“阿拉伯之春”蜕化为“阿拉伯之冬”。大量难民涌入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加剧了其社会异质化。由于难民中混杂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和恐怖分子无从识别,政府对暴力犯罪和恐怖袭击的严厉打击和防范容易将安全风险和文化威胁混为一谈。这必然加剧了文化冲突和族群隔阂,最终将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从国际层面转移到国内[30]。
随着社会异质性程度的提高,多元价值相互冲突的终极困境演绎为多元文化的不可通约、不可公度和相互冲突。这种悲剧性困境正在国内和国际上演,且二者相互强化。在近年西方国内的文化冲突中,颇具象征意义的是破坏雕像和教堂,美国各州已拆除了众多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将领的雕像,并由此引发了反种族主义者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冲突;法国也发生了众多针对教堂和雕像的破坏行为,黄背心运动中也出现了反犹、反穆斯林的声音。从国际层面看,文莱政府在2019年5月正式推行伊斯兰刑法,已引起西方国家和企业的普遍抵制。在该年度新西兰发生针对穆斯林的枪击事件一个多月后,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却在斯里兰卡制造了连环爆炸案,这种国际性报复袭击增加了全球安全的不确定性。
三、右翼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对抗的政治冲击
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普遍平等的自由选择权已基本实现,在大众崛起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西方国家逐步开放选举权,并将平等权扩展至社会经济领域。二战之后,西方国家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以选举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利已实现普遍平等化,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歧视也纷纷废除,普遍平等的权利政治基本实现。同时,随着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国家逐渐进入后现代社会,人们在普遍平等的自由选择基础上,开始追求独特的、差异的个性化身份。遮蔽或抑制于现代性的同一性之下的各种“差异”纷纷涌入公共领域,从而产生了1960年代以来的少数族群、同性恋、女权等社会运动,形成了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传统的强势群体、主流群体不再值得称道,备受歧视的少数群体开始对自我身份产生认同,且要求独特身份被主流群体承认。
(一) 多族群国家的认同困境
民族国家意味着国家边界与民族边界重合,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与对民族的文化认同相重合,这不会因为文化差异陷入分裂,争端只会表现为阶级阶层视域中的利益分配。然而这只是民族国家的理想类型,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个有其历史文化传统的聚居民族或移民群体组成,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的扩张,多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常态。由此,在多民族共存于一国的事实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民族国家模型之间,就产生了不能摆脱又难以解决的悖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逻辑基础是单一民族文化的同质型社会,而多民族共存却使得这种同质型社会是不现实的。这一悖论形成的根源在于,民族国家以民族身份动员建构国家认同的路径使民族“绑架”了国家。
身份政治兴起的时代背景是西方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社会议题从物质层面转向文化层面,因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新左派产生,从对西方的经济霸权批判转向了文化霸权批判。多元文化主义对承认和保护少数文化群体的诉求与反思西方主流文化的时代潮流相融合,从意识形态谱系上看,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身份政治属于左翼身份政治。与左翼相反,右翼身份政治非常保守,它的信念是抵制多元文化主义对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的侵蚀,并保护主流群体成员的利益,从而恢复西方国家的文化底色,重现主流群体的优越感。由于底层民众对逆向歧视感受更明显,右翼身份政治就与民粹主义相融合,演变为右翼民粹主义。
从国家认同建构的历程来看,现代民族国家构建遵循的是国家的逻辑,而非民族的逻辑。民族国家是以国家建构民族,民族为国家提供道德证明,民族只是国家整合的工具,“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32]通过强化民族身份认同进行国家整合的前提是单一民族,如此则民族国家构建不过是将既有的民族认同政治化。沿着这种建构论的思路来看,既然民族可以被国家创造,那么它也可以被国家的反对者或质疑者创造,正如白鲁恂所言,“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33]。如果从原生论的民族认同来看,问题就更加严重,民族与国家具有不可通约的二元性,民族是区分你我的身份符号,国家则是维持秩序的暴力机器,一旦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暴力机器往往成为或被视为主体民族进行压迫性统治的工具。
无论从建构论还是从原生论来看,民族总有可能成为国家构建的阻碍。通过民族动员构建国家,当然国家将总是受制于民族。契约社会的构建打破了个人对团体的依附,频繁的社会流动使身份对人的自由选择的限制大大减轻,但在情感归属层面,民族却是人们无法割舍的精神家园。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无论是基于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还是基于原住民族和移民对本族群文化的坚守,被冠以国族的民族或被国族抑制的民族得以复兴。因此,西方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问题是西方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后现代对现代的反对,而右翼民粹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则似乎是现代对后现代的拉扯。
(二) 从权利政治到身份政治
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是一条从左到右铺开的光谱,或可将其置于由“平等—自由”和“民主—权威”两个维度构成的二维矩阵中。在右翼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对抗中,左和右的含义都更加复杂。民粹主义一般属于左派政治范畴,如今右翼民粹主义却成为主流。实际上,在“平等—自由”和“民主—权威”这两个现代的经济、政治维度之外,又产生了“一元—多元”这一后现代的文化维度,因而普遍平等的权利政治与文化差异的身份政治相互交织,现代的意识形态谱系被彻底打乱。
与意识形态谱系的复杂化相反,西方的现实政治生态则趋向于简单对立化。右翼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对抗日益明朗,平等权利和公平分配的诉求开始以“身份”为界限分裂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主流的白人基督教群体,另一个是少数文化群体及其来自主流群体的支持者。全面兴起的民粹主义可以根据反对对象区分为左右翼,但当前已经出现左右翼民粹主义合流的趋势。在法、德等国蔓延的黄背心运动中都出现了反犹声音,英国工党及其青年组织“Momentum”也频频爆出反犹言论,由此导致部分工党党员退党。
再次,二者对多元化的诠释不同。面对多元价值相互冲突这一困境,价值多元论并没有终极解决方案,而诉诸个人自由选择。正是基于不受外界强制的自由选择,西方社会才具有多元化特征。尽管多元价值相互冲突,但价值都是选择的对象,而非选择的依据。相对于这些被选择的对象,自由是高居于其他价值之上的超级价值。而在多元文化主义视域中,社会多元性不是指可供选择的价值的多元性,而是源于不同文化身份的多元性。
在战后西方民权运动快速推进的进步时期,民权运动非常复杂,同时包含着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和少数群体权利等诉求,因而普遍平等的权利政治与文化差异的身份政治同步发展。由于物质财富极大增加,对少数文化群体的政治性倾斜被主流群体接受,并未造成被剥夺感,反而还可能迎合了他们由历史性错误带来的补偿心理,甚至满足其文化和族群优越感。但是,随着1980年代西方国家实施大规模私有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劳工流入和产业对外转移等原因,社会差距不断扩大,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数量也大幅度下滑。又由于价值多元论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冲突愈发显著,政治倾斜造成的逆向歧视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对。为了对抗政治正确,白人至上主义者诉诸宗教、民族和种族等文化差异进行社会政治动员,从而出现了一种右翼身份政治。
西方民主建立于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之上,通过理性化个人假设抹去了文化身份的差异,实现了社会的同质性,西方民主是在同质文化群体之内平衡利益冲突的机制。传统的左翼社会运动主要关注公民平权和利益分配议题,对西方民主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还不至于危及民主体制。只要认可作为民主政治逻辑前提的理性化个人假设,西方的多党竞争式民主就不会造成以文化身份差异为界的社会政治分裂,冲突只可能存在于阶级或阶层话语体系之内。西方国家已经针对这种阶级或阶层冲突做出了积极调适,比如 19世纪晚期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20世纪初期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后又实现普选权并普遍建立福利国家。正是因为这种调适的有效性,传统的左翼民粹主义在政治上并无太大影响力。
在右翼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对抗中,二者的冲突是以身份为界聚集的文化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双重冲突相互强化,这已与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阶级阶层冲突具有根本区别。一方面,群体划分和聚集的维度发生变化,从经济社会地位的纵向标准转向了身份差异的横向标准。区分了“我们”和“他们”,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化个人也就不复存在。从政治建构的需要来看,人性一旦被赋予历史性和社会性,差异化的个人必然要在文化群体中界定身份,这就破坏了社会同质性。更潜在的威胁在于,人们会根据文化传统提出不同的政治构建主张,一旦产生相互冲突,便难以达成共识。
转变临时应对的想法,完善事件舆情的预警体系,使得事件到来时有相应的应对措施引导舆论。事件管理如今应该常态化,与其在事件发生时手忙脚乱最后事件也不能够妥善解决,不如早作打算,做好事件预警工作。随着自媒体的产生,在如今自媒体也能够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舆情进行预警和检测。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已逐渐进入后现代,大量移民和难民的涌入积聚了越来越多的前现代“身份社会”特征。前现代与后现代二者叠加,促使多元文化主义蔓延并走向偏执,现代性遭到双向夹击。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隔着一个现代,政治上的根本差别在于是否承认基于普遍平等的理性的个人自由。尽管底色不同,二者却都对多元文化主义偏爱有加,一起痴迷于独特的文化群体身份。这种共性为少数文化群体吸引了大量来自主流文化群体的支持者,客观上使少数文化群体可以获得足够的力量与主流群体对抗,当然,这必定带来主流群体的分裂。将此分裂置于文化冲突视角来看,主流文化群体中的左派人士颇有“自掘坟墓”的意味,因此在中国网络上获得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贬义性称呼——“白左”,在西方也被称作“退步的左派”。
1.4 疗效评估 疗程满12周后,对患者过去30 d的性生活质量进行再次评估。ED疗效的判定: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的IIEF-5评分及其改善情况,治疗后IIEF-5评分 ≥22分视为勃起功能得到改善;并按非常满意、满意、不确定、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5个等级评价患者对勃起功能改善情况的总体满意度。PE疗效的判定:以IELT及SRSSL来评价PE的总体疗效,若经治疗IELT延长至2 min以上且SRSSL超过50%,则认为治疗PE有效;若经治疗IELT延长至6 min以上且SRSSL超过70%,则认为治疗PE显效[4-5]。
(三) 从意识形态政党到身份政党
现代国家构建完成之后,西方国家的传统政党轮流掌权相安无事,各种极端主义一直存在,不过并未汇流且并未形成全局性影响。传统政党是基于权利政治的左右划分形成的意识形态政党,遵循“合法反对原则”,在既定宪制框架内进行合法的、负责任的和有效地反对[37]。在西方政党政治尤其是两党制中,各党派为了尽量争取中间选民会将其意识形态向中间路线靠拢,从而形成关系到政体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基本共识。西方国家近年普遍面临经济衰败问题,且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金支出的扩大恶化了财政支出结构,又加剧了经济发展迟缓的问题[38],在这一背景下涌入的移民和难民已不再被视为劳动力,而成为分利者。当利益冲突被文化身份加持,社会撕裂也就更加深化。由此产生的右翼民粹主义就像一个搅局者,打破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容忍,二者的对抗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政党性质和结构,并冲击着西方的政治共识和民主框架。
冲击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意识形态政党因代表性危机而走向衰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传统政党结构发生改变。现代西方早期的代议制民主源于中世纪贵族与国王的妥协,实质是资产阶级基于无代表不纳税的理念用财产换来的政治话语权,政治合法性既然源于纳税者的授权,当然要对纳税者负责。而经过熊彼特的改造之后,代议制民主已蜕化为选举民主,由对选民负责的逻辑转变为精英自主统治。民主成为产生政治精英的方法,政党的功能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由最初的议会派别和阶级动员组织演变为通过选举产生政府的工具,政党国家化使其代表性越发模糊,从而造成普遍的“代表性危机”或“代表性断裂”[39]。
代表性危机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阶级阶层代表性的危机。选举民主通过选举构建了西方政治的形式合法性,实质是通过抽离代议责任避免西方政治一直警惕的“多数暴政”,精英统治的实质使民众对传统政党政治产生厌倦。其二是文化身份代表性危机。传统政党通过从左到右的意识形态相互区分,如今左和右的含义都发生变化,社会结构划分的标准也从阶级阶层转向了文化身份。意识形态政党面对这种变化措手不及,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和调适,必然产生代表性危机。在美国共和党的党内初选中,老派共和党人还纠缠于奥巴马的医改政策、减税这些旧话题,特朗普却以反“政治正确”而独树一帜,迎合了广大底层白人的祈求。
代表性危机带来的后果可从两个角度来看,其一是意识形态政党的衰落。阶级阶层代表性危机意味着政党远离了底层人民,文化身份代表性危机意味着政党远离了因政治正确遭到逆向歧视的主流文化群体。双重代表性危机相结合,最终结果是传统政党远离了主流文化群体的底层,尤其是蓝领白人群体。当这一群体被动员起来从沉默走向参与,意识形态政党必然会被边缘化。其二,在意识形态政党衰落的同时,民粹主义政党强势崛起。在美国政治中,传统两大党功能失调走向衰落,“以特朗普和桑德斯为代表的美国最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正在填补共和党和民主党缓慢解体留下的真空”[40]。如今西方国家的右翼政党或取得执政地位,或者支持率大增,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正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
伴随着传统政党的衰落而崛起的还有“政治素人”,最典型的当属戏剧性地当选总统的乌克兰喜剧演员泽连斯基,特朗普和斯洛伐克新当选的女总统苏珊娜·卡普托娃也都是完全的政治素人。他们毫无从政经历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面孔也越来越年轻。泽连斯基、卡普托娃、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都只有40多岁,最年轻的是已于2019年5月被罢免的奥地利前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他当选时只有31岁。西方民主政治的实质是多头精英统治,各领域精英通过相互交易妥协达成共识,这就需要谙熟政治交易的规则和手段,因而传统政治家的养成需要长年累月的历练,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成为建制派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因此,政治素人的崛起,更是反映了民众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不满。素人政治是民粹政治的一种典型,都是利用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体和社交平台进行渲染、引导和动员,而政治家则在网络上以其“表演”去迎合这些偏好。互联网在民粹主义崛起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将直接销蚀传统政党的表达和整合功能。
右翼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相互对抗,对西方民主带来冲击的突出表现之二是,政党动员手段发生巨大变化,竞争性民主撕裂社会并制造了冲突甚至战乱。在多党竞争式民主中,政党要最大限度地动员选民,动员选民就需要制造议题扩大差异,这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存在撕裂社会的问题。因此,传统的西方选举结束之后,失败方要认可选举结果,获胜方也要尽力弥合缝隙,而不是继续扩大隔阂。但在右翼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对抗中,政党却基于身份划分派别进行政治动员,那么,“政治平衡就会非常脆弱,人口结构的变化或投机的政客可以轻易将其打破”[41]。特朗普通过挑战政治正确这一脆弱共识获胜,却也对社会团结构成了伤害,因而被反对者称为种族主义者。选不赢就闹、就打的现象在第三波以来的民主化中极其普遍,但如今,这种现象已从发展中国家蔓延到了老牌民主国家。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胜利让很多美国人感到匪夷所思,他们在惊愕之余掀起一轮又一轮抗议游行,并引发流血冲突。
出于对特朗普的反对,加利福尼亚州至今还在筹划独立公投;由于对英国脱欧不满,苏格兰也在筹划着新一轮独立公投;鉴于黄背心运动愈演愈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2019年初发起了关于若干重大议题的全国大辩论。西方民主的运行方式是代议制,尽管公民具有创制权,但近年来屡屡出现全民参与的公决和讨论,证明西方民主的运行出现严重梗阻,人们希望通过直接民主来重构共识。直接民主是民粹主义的理想化民主形式,但其历史实践无不以悲剧告终。尤其有些地方的公投旨在取得独立,这已不只是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更是对公民身份和国家统一的质疑。
右翼民粹主义已经积聚了巨大力量,并在多国上台执政,更关键的是,右翼势力已经主导了议题设置,掌握了政治话语的主动权。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下,传统政党必须对这些议题做出回应,无论附和还是反对,结果都只能是继续扩大差异,撕裂社会。面对右翼民粹主义以文化身份进行动员快速获得的巨大支持,作为其对手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必须以身份进行动员,方能与之相抗衡,否则不仅会遭到对方支持者的排斥,也会失掉左翼的选民。
由于动员手段和选民基础的变化,现代意识形态政党可能会向身份政党转型,这一转型无疑会加剧西方政治生态的极端化和狭隘化。其实,尽管西方社会一直强调基于自由选择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主张道德中立和政教分离,但西方文明本身就脱胎于基督教。1960年代以前,基督教禁止同性恋、堕胎、避孕、赌博甚至饮酒等诸多教义都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用以规范公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因此,“只要西方社会的法律和政治由基督教的道德规范进行塑造,它就会彻底扼杀自由。”[42]
颇为吊诡的是,正是随着民权运动的扩展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这些源自基督教的禁令才被逐渐废除,西方的个人自由才得以充分释放。更为吊诡的是,左翼的多元文化主义势力呼吁尊重差异,宽容和解,反对歧视,但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下,多元文化主义却充满讽刺意味地抵制右派言论、集会和公共活动,甚至容不下已经建立百余年的南北战争将领雕像,这些雕像当初建立时正是被视为南北和解的标志。
四、结语:无以应对的僵局
西方民主是现代理性社会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理性意味着个人认知、改造和超越外部环境的能力,因而民主政治建立于个人达成的共识,并且现代社会必须实现永恒的进步。只要基本共识存在,社会持续进步,西方民主就能稳定运转。随着1960年代以来个人自由的绝对化,西方社会越来越陷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差异化认同渐成风尚。但由于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繁荣,社会共识仍然存在,只是往左偏移了很多,并且这种偏移具有更多的身份属性。之所以往左偏移的原因在于,西方主流群体的普遍平等自由早已实现,开始往历史上因身份遭受群体性歧视的人群扩散,比如原住民、黑人、女性和同性恋等群体,这就将社会结构划分从阶级阶层结构转向身份结构,身份意识大大强化。在永恒进步的理念之下,政治共识持续向左偏移,形成了当代西方的“政治正确”。
当西方世界因繁荣不再而无法满足进步的期待,对政治正确的有条件共识就被打破,自由、宽容和开放的西方主流文化也就趋向封闭化和狭隘化,从而形成右翼民粹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二者的对抗已构成对民主体制的冲击,如果身份群体的对立持续深化,基于理性化个人的现代性将在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夹击之下走向崩溃。届时,除魅之后的“诸神冲突”可能演变为“群魔乱舞”。西方政治一直试图将罗尔斯所说的各种宗教的、哲学的和道德的“完备性学说”[43]塞到私人领域并诉诸自由选择,通过使其远离公共政治来构建多元文化的共存框架,但西方政治本身又属于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又何尝不是一种完备性学说?面对这个无解的困境,现实政治可能有两种选择,或者依靠威权政府提供稳定的秩序,为将来的探索提供时间上的缓冲,或者转移内部矛盾和压力,并不择手段地再现国内繁荣和进步,又或者,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内外深度互动背景下,民族国家无以应对当前的僵局,它自身的存在也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当前西方的反全球化浪潮是否是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式在做最后的挣扎,也未可知。
参考文献:
[1]斯蒂文•伯恩斯坦, 威廉•科尔曼.不确定的合法性——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共同体、权力和权威[M].丁开杰, 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6.
[2]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下卷[M].林荣远,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731.
[3]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 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60.
[4]SINIŠA MALEŠEVIĆ.Empires and nation-states: Beyond the Dichotomy[J].Thesis Eleven, 2017, 139(1): 3−10.
[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4−5.
[6]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 黎廷弼,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 443−444.
[7]PETER H.Empires and barbaria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birth of Europe[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385.
[8]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21.
[9]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47.
[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38.
[11]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J].东南学术, 2006(4):18−27.
[12]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29, 41.
[13]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183.
[14]孔元.反思民族国家的内外观: 宪法和国际法的视角[J].开放时代, 2018(4): 113−128.
[15]SINIŠA MALEŠEVIĆ.Empires and nation-states: Beyond the dichotomy[J].Thesis Eleven, 2017, 139(1): 3−10.
[16]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20−21.
[17]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129.
[18]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 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7.
[19]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建,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412.
[20]以赛亚•伯林.自由论(修订版)[M].胡传胜, 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217.
[21]TAYLOR C.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C]// Gutmann Amy.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39.
[22]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M].刘莘,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423.
[23]周少青.加拿大多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国家认同问题[J].民族研究, 2017(2): 16−30.
[24]乔治•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M].应奇, 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80.
[25]SUSAN O.Femin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Some tensions[J].Ethics, 1998, 108(4): 661−684.
[26]丛日云.从精英民主、大众民主到民粹化民主——论西方民主的民粹化趋向[J].探索与争鸣, 2017(9): 4−17.
[27]MARTIN E.Reviewing black studies: Legitimacy of discipline taken to task[J/OL].Newsday, (2002-02-04)[2019-05-28].https://www.goacta.org/news/reviewing_black_ studies.
[28]SALGADO S.Where’s populism? Online media and the diffusion of populist discourses and styles in Portugal [EB/OL].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2018-01-22)[2019-05-28].https://doi.org/10.1057/s41304-017-0137-4.
[29]SCHWÖRER JAKOB.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as defender of Christianity? The case of the Italian Northern League[EB/OL].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 Gesellschaft und Politik, (2018-09-26)[2019-05-28].https://doi.org/10.1007/s41682-018-0025-y.
[30]BONINO S.The British state ‘security syndrome’ and Muslim diversity: Challenges for liberal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terror[J].Contemporary Islam, 2016, 10(2): 238.
[31]包刚升.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J].政治学研究, 2018(3): 103−115.
[32]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0.
[33]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M].邓伯宸, 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
[34]DING I, HLAVAC M.“Right” choice: Restorative nationalism and right-wing popu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J].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2(2): 427.
[35]SRDJAN V.American Images of Canada: Canadian Muslims in US Newspapers, 1999—2014[J].America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 2016, 46(1): 16−32.
[36]FARIDA J.Anxious and active: Muslim percep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treatment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he post-september 11, 2001 united states[J].Politics and Religion,2011, 4(1): 71−107.
[37]RICHARD H.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40[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4−5.
[38]程同顺, 史猛.欧洲老龄化社会的民主困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9(2): 111−118.
[39]聂智琪.代表性危机与民主的未来[J].读书, 2016(8):126−135.
[40]SEAN C.Trump, sanders and the new american populism[J/OL],Spiked-Online, (2016-02-24) [2019-05-28].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16/02/24/trump-sanders-and-the-new-american-po pulism/.
[41]RODRIK D.Is liberal democracy feasib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6, 51(1): 55.
[42]CHRISTIAN J.Islam and the legal enforcement of morality [J].Theory and Society, 2014, 43(6): 589−615.
[43]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 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0: 61−62.
Foundation and crisi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democracy: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right-wing popu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ZHANG Guojun, CHENG Tongshu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modern states, it needs three foundations for contemporary western democracy to effectively shape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first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geographic country to nation-state; the second is the evolution from status society to civil society; the third is the change from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o electoral democra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the masse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e pluralism which stems from individual freedom has been divided into value pl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The former advocates universal equal individual rights, while the latter pursues differential treatment to members of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Th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of the western world have encouraged the spread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made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minorities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But when prosperity ceases,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becomes reverse discrimination and right-wing populism thrives.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right-wing popu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reshapes the rights politics into the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reatens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ized individual as the basis of modernity, hence eroding the foundations of effective democracy and engendering the democratic system into crisis.
Key Words: western democracy; nation state; right-wing populism; multiculturalism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9)04−0116−12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19.04.014
收稿日期:2018−11−20;
修回日期:2019−05−3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党群关系视域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研究”(17CZZ003)
作者简介:张国军(1982—),男,山东滨州人,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民主理论与中国政治,联系邮箱:guojunzhang414@163.com;程同顺(1969—),男,山西闻喜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和中国农村政治
[编辑: 游玉佩]
标签: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国家论文; 主义论文; 社会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其他政治理论问题论文; 民主论文; 人权论文; 民权论文;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党群关系视域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研究”(17CZZ003)论文;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