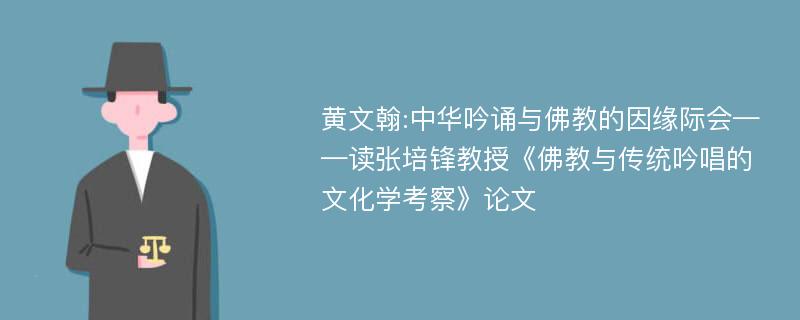
佛教与传统吟唱的关系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历史现象的错综交织,纷繁复杂,以及史料的不足等诸多因素,一直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难题。南开大学张培锋教授所著《佛教与传统吟唱的文化学考察》[1]一书,不但对华夏文化重要遗存之一的吟诵之起源和发展以及佛教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做出全面考察,而且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展示出来的方法论意义也值得认真关注。
张培锋教授在书的开篇便提出:历史如同一只瓷瓶,在悠远时空所交织的缘起缘灭中,散为万千碎片。“所谓‘还原历史’,也就是力求将这些碎片重新拼接起来。”[2]1正如千江月影,皆为月体之一分,无所谓孰真孰伪,学术研究同样不宜,也“无法根据一己之见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判断真伪”[2]3。由此,全书依据佛教的缘起史观,同时借鉴钱锺书先生拈示的“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的循环阐释方法[3],“一视同仁地看待存世的一切被人为划分为历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不同学科的材料”,[2]2从广阔宏深的“文化学”视角,对佛教与传统吟唱关系问题,做出全面、深入、细致、独到的考察,力求展现“中国佛教音声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与中华礼乐文化传统的关系”的发展脉络,并“最终揭示‘吟诵’这一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厚内涵”。[2]6
幼儿园阶段的孩子有着较强的模仿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言语行为对学生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幼儿园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心理状态,保证能在区域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将自己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另外,教师还应该对班上幼儿的心理状态有一个具体的了解,让幼儿能对教师给予自身的爱护有所感受,引导幼儿积极参与到区域活动中。同时,教师对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该给予充分尊重,不能急于否定幼儿在活动中的想法。
首先,论著揭示了华夏 “礼乐文明最深层的意义:根源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宗教理念”。[2]11对于出乎天地、平正和美、撙节人欲之乐的推崇,是华夏智慧先民共同的“英雄所见”。这种音乐即雅正之乐,其来源与作用,具有天然的宗教性质。论著揭出“华夏古乐的核心精神是源自天地人的自然和谐”之要义。[2]32华夏古乐本乎天地、贯通宇宙,具有宗教神秘性;华夏古乐带有“大道至简”般的平淡和美的音乐风格;华夏古乐是人的一颗自在、自然之心的外现。论著还对历史上所谓“礼崩乐坏”的内涵做出深刻允当的解读,指出战乱分裂中的王朝“无力维持庞大的礼乐制度,导致礼乐从朝廷流向民间,从中原流向四夷”,这是“礼崩乐坏”的本质意义。[2]22而以老子为首的古道家学派,即在第一次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携之西传,并与西域地区原有的小乘佛教融合,形成以华夏礼乐精神为核心的大乘佛教,并在第二次礼崩乐坏的东汉之时,回传中原。换言之,“礼崩乐坏绝非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的根本精神恰恰是为了挽救与弥补崩坏了的礼乐仁义”。[2]23
其中,施氮量为纯养分量(kg/hm2),吸氮量单位为kg/hm2,秸秆重、籽粒重单位均为kg/hm2,秸秆含氮量、籽粒含氮量单位均为%。
[1]该著由天津教育出版社于2016年12月出版,是叶嘉莹先生主编的“中华诗文吟诵研究丛书”之一,以下简称《考察》。
其次,论著对于佛教与传统吟唱的“源头”问题做出系统梳理。它发挥推导牛龙菲先生在《古乐发隐》一书中关于西域古乐文明与华夏音乐亲缘关系之考论,揭出西域地区在汉末中原丧乱之际,“之所以能够发挥传承华夏礼乐文化的作用,是因为在此之前早已广泛接受了华夏文化”,华夏文化“实际上主导着这一地区的文化形貌”的重要观点。[2]124其后通过对 “老子化胡说”文化意义的新探,对上述观点做出有力证明。这部分内容正是此书采用佛教缘起史观以及大乘佛教的平等观,对相关领域进行学术研究的生动写照。老子西行、化胡之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来,史不绝书。如果先验地将其仅仅看作道徒攻击佛教的捏造之言,则无法明了“这种说法之所以形成的真实历史依据和真实历史含义”。[2]126对“老子化胡说”之形成,孙昌武先生曾指出,“当时(按指东汉时期)佛教在中土扎根未稳,黄老之学盛行,老子逐渐被神化,应是佛教方面自神其教的说法,意图在表明二教的一致性,因而毋宁说是替佛教的存在作辩护的”。[6]孙先生此论值得深长思之。老子化胡等系列故事的情节与理念,在佛经中多能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学界通行观点认为,这是道经对佛经的模仿。理由是前者较后者出世时间为晚。而张培锋教授指出: “大乘佛教或道教的经典‘产生’时间,即进入人类视域的时间是一回事,其观念之根源又是另一回事。”[2]134这并非否认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考订这类问题“必须从文化理念这个角度做出大判断”,在大判断明晰的前提下方能对具体问题进行定位。否则,弟子们于佛陀在世时即讽诵经典、小乘中没有的 “分身教化”观出现在大乘佛教中等一系列“矛盾”,就无法得到圆满解答。此外,论著还以扎实的文献资料,对于阗、高昌、龟兹等地存在的大量华夏文化因素予以考察。“如果历史上没有类似于‘老子化胡’这类事情发生,华夏文化如此深入地扎根于此是很难得到解释的”。[2]145从文化意 义上考察老子化胡,这一概念“应指以道家学派为主体的华夏人种迁移至西域地区并在此地传播华夏文化,并直接促成华夏文化与小乘佛教的融合而产生大乘佛教,其最初时间大致可确定为西周末至东周初期,其所化地域主要为今新疆的于阗、龟兹、高昌等地区,亦即后来大乘佛教兴盛的地区”。[2]137论著还 指出道家的礼乐精神在于追求“希淡平和”“大音希声”,由此证明儒道佛三教对于音声问题有着大致相同的认识这一事实。[2]155
[3]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9-172.参看《考察》,第134页。
再次,论著对于佛教吟唱传统在后世发展流变的脉络做出清晰描述。比如,详尽考察了唐代华夷音声之争重新凸显的重要原因—— “当时西域地区的音声已渐受阿拉伯文化影响,逐渐失去华夏古乐风貌”[2]231,所以才有元、白起来倡导新乐府,以“魏晋以来自西域所传之‘华夏正声’”对抗“胡部新声”。[2]240值得注意的是张培锋教授指出的,唐宋以来僧人们所秉持的以华夏文化为正宗的立场,也反证中国佛教的文化根基之所在。[2]242中唐至晚唐五代,第三次礼崩乐坏出现,至北宋中期才得以重振。而重振之关键,端赖佛门之保存华夏礼乐文化,论著还提出“唐代出现的诗僧群体是将佛教梵呗、诵读转化为一般诗歌吟诵的关键人物”的重要观点。[2]255须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吟诵对于僧侣,“也是其修行实践的一部分”。二是宗教仪式化的梵呗音声“在寺院中一直代代相传”。[2]263-265华严字母与净土佛号的唱诵,即是两个重要例证。论著深入考察了禅门与吟诵之间的因缘,以有力的证据证明:古代禅僧上堂说法,往往伴以吟诵。而宗门内部不同派系之区分,亦很可能与其不同的吟诵腔调有关。此外,还揭出僧侣多善古琴的重要历史现象。“古人吟诵时每每伴随着琴声”[2]294,两者之间 是二而一的 结合,这就无怪乎僧侣中颇有兼善琴道与吟诵者的情形了。
本次监测采用高景一号卫星遥感影像,高景一号01/02全色分辨率为0.5 m,多光谱分辨率为2 m,轨道高度为530 km,幅宽12 km,过境时间为上午10:30分。监测区全域卫星影像数据获取时间为4至5月,影像地面分辨率为0.5 m,单景卫星遥感影像侧视角度≤±30°,监测区全域范围单景云量覆盖低于15%。
四是学生的能力有偏差.传统教学模式下培养的学生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有偏差,学生在课堂上感觉“学会了”,但不会把所学知识应用到自己开发的网站上.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会导致学生实践操作时完全模仿教师上课演示的网页案例,不能独立完成一个真实的有创意的网站.
要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整体,分散于不同艺术门类中。“而任一门类之技艺若能上升至道的层次,又皆是整体之体现。”[2]303这一思想是华夏文化整体观的重要观念,大乘佛教同样发挥的也是这一思想。可以说,《佛教与传统吟唱的文化学考察》一书即以“吟唱”作为一个考察角度,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不深刻理解佛教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无法真正理清佛教与传统吟唱之间的关系。
[2]张培锋.佛教与传统吟唱的文化学考察 [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6.
论著在考察佛教内部吟唱传统之时,将小乘佛教排斥吟咏唱赞,到大乘佛教接受并赞叹之这一历史过程清晰呈现。佛教对音声观念的根本转变,“是借鉴了外道的‘讽诵经典作吟咏声’的方法”,“而这里所谓‘外道’很可能即是来自华夏民族的道家学派”。[2]45“‘以音声为佛事’实为中国佛教在有着悠久礼乐传统的华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具有‘自主创新性’的理论命题”。[2]48—49其后,系统考察了华严、天台、禅宗几个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宗派对于佛教音声功德、意义之赞述的相关资料,再次证成大乘佛教音声理论,有着华夏礼乐文化深厚积淀的事实。“重声而又‘不为声迷’是佛教音声的一个重要原则”。[2]60理论上讲,“世俗一切音声皆可为 ‘佛事’”[2]64,而不为声迷的关键,则在于保有一颗澄澈之心。这颗自在、自然、澄澈的心,同样也是理解华夏古乐内蕴的锁钥。由于对“礼崩乐坏”最重要的含义重新做出楷定—— “由于后继无人,音声难以口耳相传而导致失传,而一旦失传,便难以弥补”。[2]74故而貌似崩坏的古代礼乐,恰恰由古代具有代际传承关系的僧道教团保存下来。历史上程颢过定林寺“三代礼乐,尽在是矣”的感叹[4],司马光游洛阳诸寺所说“不谓三代礼乐在缁衣中”的话[5],都不是圣贤一时兴到的偶然之论。论著由此详细论证了中国佛教音声源于华夏的基本事实,即“由于华、梵语言的不同,汉地流传的佛教音声事实上只能来源于中国本土” “自古论及梵呗者,多用中国固有音声理论来阐发”“中国佛教的音声追求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完全一致”“佛教梵呗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古乐器”“佛教梵呗的记录工具与中国传统音乐记录工具相同”等。[2]76-90
注释
在这部分论述中,论著的视角并没有局限于吟诵本身,而是扩展到整个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正是 “举大以贯小,探本以穷末”的循环阐释的需要。论著指出,大乘空宗许多基本观念可在华夏文化典籍中找到依据,这些基本观念包括缘起性空观、法身观、因果报应观等[2]158-166,“从文化解释角度上,‘三教同源说’比‘三教合流说’更为合理”[2]166,论著同时对与华夏文化精神实为一体的大乘佛教基本原则做出概括,它们分别是:“心同理同,心为万法之本;中道中观,执两端而得中;权实无定,一切皆可变通”[2]168,而其中“心同理同”的观点尤其重要,这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包容、打通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的根源所在。论著接下来便以曹植创“鱼山梵呗”之史料为缘起,通过对道教《玉音法事》与佛教《鱼山声明集》相似的“声曲折”曲谱形式,以及佛道二教对擅长歌赞咏法的梵天的共同信仰、天宝十三载佛曲名改为道曲名的考察,“充分证明着佛道音声有着完全相同的源头”[2]186。此外,针对学术界四声外来说、四声与佛教无涉说等两种对立的学说,提出更为深刻合理的看法:汉语四声之由来,是天人合一的华夏礼乐文化所孕育出的,而传播四声之说者,多为佛子;永明声律说的实质,“是诗乐分离的产物,即不再于诗歌之外寻求乐律,而就汉语诗歌语言文字本身寻求音律”。[2]212这样一来,诗歌便由歌唱而吟诵了。而吟诵的主体,则为江浙一带操吴语之僧侣文士。由此,论著对于佛教与传统吟唱的关系做出完美的解释:中国佛教中的吟唱传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但这并非否定佛教的意义,这是因为吟唱这一传统得以流传至今,佛教起到重要的保存作用,换句话说:中国佛教自其一开端直到今日,都是正宗的华夏文明的传承者。笔者认为,以上这些重要论断的提出,端赖作者在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将材料视为“具有同等地位的‘历史资源’”并进行整体把握,而非就事论事地片面考察,或者理念先行地主观臆断。“文化无非就是一种解释体系”。对历史材料的使用,更多的应该 “寻求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2]306,“唯材料之真伪乃一相对性问题”[7],绝对的真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4]参心泰.佛法金汤编(卷十二)[A].卍续藏经(第148册)[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941.
由图6可知,支架的最大位移为8.27 mm,出现在顶梁的中间部分,但最大位移与顶梁整体长度5 300 mm相比,变形量几乎可以忽略,伸缩梁的最大位移也较大,约为6 mm;支架的最大应力为737.84 MPa,出现在护帮千斤顶与护帮板的连接处,同时护帮千斤顶与伸缩梁的连接处应力也较大,约为458 MPa,两者没有超过材料的屈服强度(890 MPa)。故支架比较脆弱的部分为顶梁、伸缩梁(位移较大)和护帮千斤顶与护帮板、伸缩梁连接的部分(应力较大)。由有限元分析的结果可知,支架整体的结构和强度均能满足旗山矿的煤田地质条件,该支架能够完成综掘巷道支护任务。
[5]参志磐撰,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四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81.
[6]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353.
[7]陈允吉.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54.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
标签:佛教论文; 华夏论文; 大乘论文; 礼乐论文; 论著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6期论文; 南开大学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