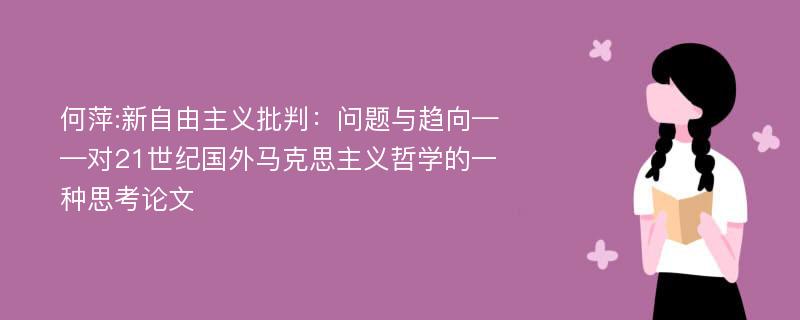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
摘 要: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时代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作为时代概念,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逻辑起点是新自由主义批判。在这个逻辑起点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分析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入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新自由主义宣扬的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新话语。在这个话语下,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宗教理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问题,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文化领域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阶级理论;劳工问题;宗教批判
研究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理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它看作一个时间概念,还是看作一个时代概念?在这里,时间概念和时代概念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时间概念指的是自然的序列,是一个同质性的概念;时代概念指的是思想的阶段性变化,是一个异质性的概念。由于这一区别,采用不同的概念进行研究所选择的材料和叙述方式也必然不同:如果按照时间概念来看,那么研究的重心必然放在21世纪以来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上,与之相适应,在叙述方式上,着重梳理和概述21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和观点;如果按照时代概念来看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研究的重心必然落在思想的变革上,与之相适应,在叙述方式上,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变化来叙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对比它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别,寻找叙述的逻辑起点,分析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点。在这两种方法中,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选取那些能够代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特征的材料进行分析,揭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和未来走向。
一、全球金融危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
以时代概念来测度,严格地说,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在21世纪的头十年,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而陷入了低谷。在这期间,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依然存在,但这些都只是在原有的理论框架下开展一些对策性问题的讨论。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出版和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文献不过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续,在理论框架上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因此,不能称之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不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起点和新视角,突破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起新的理论框架,从而显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特点、新趋向。这一事实表明,全球金融危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我们也只有在这个历史起点上,才能弄清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也才有可能知道它的问题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有什么不同,进而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及其走向。
历史地看,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里所说的一个时代的结束,特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建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这里所说的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出现的新变化。这两个时代,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以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为起点的,但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性质不同,因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构的内容及其所形成的世界格局亦不相同。19世纪,产业资本占据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从属于产业资本的。由这一经济结构所决定,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危机实质上是产业资本的危机,而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以及与之相应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成为这场危机的解药,使资本主义渡过了这场危机。在这个历史起点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开始朝着金融资本的方向行进,直至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这就是列宁所强调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1]。而在政治上,资本主义国家朝着垄断的方向发展,从资本家企业组织联合形式的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进而发展到国际垄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际霸权。与此同时,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进步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力图用社会主义力量来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强权,进而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新的文明形式代替旧的文明形态。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二元对立,其中,资本主义国家始终以建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己任,而非资本主义国家则始终以反抗、瓦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己任。这两种力量的较量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这个格局自20世纪70年代起不断地发生变化: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问题的提出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一方面要求人们共同面对和解决自然环境和国际社会的治理问题,把世界上控制和反控制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力量逐渐广泛化和多元化,尤其是文化批判力量增加了。其后是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加之互联网的出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创造了条件,使先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扼制的全球金融资本和国际霸权迅速地膨胀起来。
本研究结果表明,超声引导下甲氨蝶呤穿刺介入治疗未破裂型输卵管妊娠其治愈率和输卵管畅通率与腹腔镜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但是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等指标均优于腹腔镜组,提示超声介入治疗可以达到与腹腔镜治疗近似的疗效,且创伤小,安全性高,值得应用于临床。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运动,说到底,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凭借自己的霸权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积累资本,而新自由主义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主要手段。然而,好景不长,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就在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美国爆发,并蔓延到世界各国,演化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一历史进程表明,迄今为止,人们对金融资本的认识是十分有限的,而在这有限的认识上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与金融资本的规律是不相符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正是这种认识的有限性和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性,构成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的不仅是新的思想创造,更是社会秩序的重构。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同时是一种机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社会群体,谁抓住了这个机遇,谁就能够获得新的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自2010年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金融危机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力图通过这些探讨来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创造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此外,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阶级意识和政党理论。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危机”,即工人的阶级意识下降到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不知道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之外还有其自身的利益。费尔·赫斯指出,造成工人阶级主体意识下降的主要原因有:其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人阶级斗争的失败使工人对集体行动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失去信心,工会会员人数也大大减少;其二,这些失败导致劳工队伍改组,工人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下降,具有工人阶级组织传统的大型工作场所急剧减少;其三,社会住房计划和福利的削减迫使工人疲于寻找住所,并依靠自己的资金为养老作准备;其四,以上挫折以及对集体行动信心的逐渐下降导致工人阶级的总体意识衰退,大众文化变得沉默无语,青年对政治日益冷漠。赫斯指出,工人阶级的意识虽然下降,但并没有消亡,因此,如何提升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能力将是社会主义战略和策略的中心任务[10]。面对“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2010年接受《新左翼评论》的采访时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要取得成功,就不能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必须跨阶级发展,建立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人民政党。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今的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老一辈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甚至在政治理论上也不具备应有的政治潜力。与此同时,在当下社会中,工人阶级还存在着三大消极发展态势:一是仇外心理;二是更多的工人受雇于临时性、不固定的职业,这些人不仅更加难以组织,而且在政治上也比较无力;三是新的社会等级标准使人与人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11]。奥利弗·纳克特威在《德国左翼党与阶级代表性危机》[12]一文中分析了德国左翼党的变化,指出尽管阶级地位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不断攀升,但社会民主党对阶级话语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漠,甚至越来越脱离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形式。这就造成了一场阶级代表性的危机,即葛兰西所说的“消极革命”,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德国左翼党内的一些左翼分子只耽于激进主义的说辞,却很少积极投身于社会斗争之中,甚至不敢作为独立的参与者在这些斗争中发挥作用,从而使左翼党内陷入了“战略僵局”;而工会的战略也不确定,即目前究竟是采取继续支持竞争——法团主义的战略,还是逐渐采取斗争的战略,这个问题并不明朗。这些研究和检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欧洲左翼党的现状。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是以金融经济为主体的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投机驱动,其二是风险控制。前者来自金融经济的内在驱动的特征,后者则来自对金融经济管理的要求。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两个特征渗透到生命政治学和国际霸权政治之中,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趋向。梅琳达·库珀在《作为剩余的生命:生命技术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2]一书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对生命技术发展的消极影响。库珀吸取了福科将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思考生命问题的思路,将当代生命技术与新自由主义的权力配置联结起来,说明当前生命技术发展的特征:生命技术已经渗透了金融经济的投机驱动的思维方式,它以生命技术工业化的方式将生物学和资本再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生命的构造变成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的因素,使生命的力量和潜力变成了资本自我平衡的权力,生命变成了可利用的剩余价值,它的持续不断再生产的潜能成为经济金融化的对等物,与关于投机资本和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化产生了共鸣。由于具有这一特征,生命技术作为一种尚未开发的潜能,有可能取代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榨取和有形商品的大量生产,成为资本积累的新领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一个不曾想象的空间。兰迪·马丁在《一个冷漠的帝国:美国的战争和风险管理的金融逻辑》[3]一书中研究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状态,发现美国在反恐战争中采取了一个类似于金融管理的逻辑。根据这一逻辑,帝国主义国家不再像以往那样以主权控制来定义战争胜利,而是以维护持久战争的管理来定义战争的胜利。由于这种改变,当代反恐战争的重点不再是冷战时期采用的威慑方式,而是争夺维护风险管理的战略优先权的方式。于此一来,反恐战争通过帝国主义式的证券化将各个不同的目标连接在一起,简言之,战争将它的敌人都均质化为恐怖的威胁,然后通过“杠杆的”干预来管理非本地的风险。其实,这种思维模式不仅体现在帝国的战争上,也体现在对内的管理、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时期处理人民抗议和示威游行的机制上。阿尔伯特将这种模式称之为“前恐怖主义”,即将“危险的个体”和未来暴动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呼吁先发制人。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之中,管理者无视恐怖主义与消极怠工、工人运动之间的区别,将危机时期内的所有非法的政治表达都判定为一种恐怖主义的性质,以便将恐怖主义的威胁扼杀在萌芽状态[4]。这些考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新思路,即以金融化思维方式的渗透重新思考今日的政治哲学问题。
二、新自由主义批判: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
一张记载表。所有工作都必须作好文字记录。《思政导师工作记录表》的具体要求是:座谈会、专题讲座、谈心谈话、其他活动实施时间不得占用正常上课时间;记录表上的要素应该填写完整:列明活动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具体地点、导师和学生签名必须完整规范;记录表提交到学院办公室,记录表在提交时必须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起点和理论视角为我们思考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两点重要的方法论启示:第一,从两个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别中去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与趋势;第二,联系世界历史的变化、尤其是一个世纪以来金融资本的运动及其对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来考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问方式,从中发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的。本文正是依据这两个方法论原则来分析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与趋向的。
在政治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着重对新自由主义特有的剩余价值再分配机制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日益加深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批判。在众多的不平等现象中,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关注健康医疗资源的不平等。麦克·海恩斯在《资本主义、阶级、医药保健》[5]一文中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社会梯度(social gradient)与所有权、生产资料控制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梯度不简单是“你拥有什么”,而是控制人和资源的能力,这才是阶级分析的关键。他还用异化、剥削、阶级和阶级矛盾这几个核心范畴来分析健康医疗中的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指出造成健康、医疗上的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卫生体系,而这种体系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维方式渗透的结果。因此,要消除健康医疗的不平等现象,就必须改变以盈利为目的的法则。伊恩·弗格森和凯特·皮格特从心理方面研究了当下的不平等问题。他们在《精神维度:为什么平等对于每个人来说更好》[6]中指出,在贫富差距较为悬殊的社会,除了健康问题外,还存在着一系列广泛的社会问题,诸如暴力、吸毒、精神疾病、儿童的福利措施、社会生活的参与和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等,这些问题也是由不平等造成的。因为社会不平等造成了社会分化,于是人群中就有自卑感和优越感,有了被低估、缺乏尊重和认同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导致了暴力、吸毒、精神疾病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分析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对生产交换领域的不平等的批判扩展到对社会公共领域的不平等现象的批判。
其次,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针对金融危机的爆发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滋生的敌视移民工人的情绪,建构了一种批判的研究视角。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驳斥了美国一些书刊和影视作品中的反移民论调,即移民特别是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是导致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大卫·贝肯在2008年出版的《不法者:全球如何创造移民和非法移民》[16]一书中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移民工人所遭遇的境况并不是由他们的欲望和活动所决定的,而是受复杂的、强制力量的驱使,这种力量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全球资本的积累密切相关,简言之,全球化创造了移民;第二,移民的流入对美国的经济非常有利,所有资本家都深谙此理,在几百年的历史中,资本主义与流离失所携手并进,大量的劳动后备军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从而提高利润的重要保障;第三,在当前状况下,在政治上反对移民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因为一方面移民工人增加了国家收入却很难享受到国家福利,另一方面移民工人往往不与本地工人直接竞争就业机会。随后,大卫·贝肯在《每月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组建工会的核心问题——争取移民的平等地位和权力》[17]的文章,指出面对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联合是劳工运动赢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为此,必须组建移民共同体,使移民工人能够同本地工人团结一致行动,有效地抵抗资本和雇主的剥削,从而使工会重建获得新的生机。海斯特·爱森斯坦于2010年出版了《女权主义的诱惑:全球精英如何利用女性劳工和女性观念剥削世界》[18]一书,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分析和批判了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她回顾了近三十年来女权主义的相关著作,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本质上是“霸权的女权主义”,正是这种“霸权的女权主义”以雇佣劳动的自由来掩盖跨国公司对女性劳动的剥削,从而把女权话语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话语,女权主义也因此沦为资本积累扩张的帮凶。理查德·西摩在《不断变换面孔的种族主义》一文中指出了近十多年来种族主义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即从强调人种转向了强调信仰,从强调肤色转向了强调宗教信条和文化,而导致这种新的种族主义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反恐战争”。西摩还对当前的“文化多元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文化多元主义”的信条是一个虚伪的陈述,因为在去政治化的潮流中“庆祝”文化的多样性只会使文化从个体参与的过程变成被观察和享受的静止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它与现今的“文化种族主义”密切相连,无论是在移民问题上、还是在现今对伊斯兰的仇恨和“融合主义”的复兴上,种族主义和文化都是问题的中心。针对当前种族主义的各种新面孔,西摩指出,反对种族主义势在必行,为了击溃种族主义,我们一方面需要联合“反战”和“反种族歧视”运动中的大多数,与右翼的大肆宣扬相抗争;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重申社会的基本阶级对抗,这对于工人阶级的联合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三、对阶级和劳工问题的再思考
对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分析与批判,呈现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角。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这个新的视角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时代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进而对阶级和劳工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
从心理分析来讲,造成狂士的原因是一种自恋情结与自我亵渎。“在狂士,怀才不遇也许更带有一种风流自负的意味,它更多是一种自我伟大感”,而这种“自恋是建立在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人格基础上,所以这种自恋是最容易在现实的挫败感的驱使下走向自渎一极”[23](P79-80)。从现实层面来看,陆游一生宦海沉浮,经历丰富,深切关注国家与社会命运的儒家修行观念贯穿其一生的思想与实践[24]。狂士的心理是放翁以履践天下为己任的儒家道德观念,在不如意时精神上的创伤,这即是“儒家入世的苦行”[25](P501-511)。
(一)阶级和政党
劳工运动一直以来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因而也始终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重视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研究在21世纪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研究重心被放在了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移民劳工问题上。首先,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产品的生产向外围国家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工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今日的劳工运动研究必须有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大卫·贝肯在《当代劳工运动的激进视域:国际主义和公民权的重要性》[13]一文中指出,当我们以激进的视域来看待这个时代时,就会发现,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球化,因此,工会应当在国际层面上来反对资本主义。理查德·P.麦金太尔在《工人的权力是人权吗?》[14]中分析了当下的国际机构,诸如国际劳工组织、美国政府和各种以劳工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指出这些组织的任务应该是保护工人的人权和充分发挥他们自由结社的集体性权力,并以集体协商为工具来抵制全球血汗工资制度的不良影响。西奥多·布尔扎克不同意麦金太尔的这种观点。他在《工人需要何种权力来消除剥削》[15]一文中指出,麦金太尔强调集体性权力,是因为他怀疑个体权力能够作为一种对抗全球资本的有效力量,而这种怀疑的根据不外是自由契约中的个体权利不能成为提升劳工议价力量的有效机制。这是有失偏颇的。他认为,现在的劳动产权理论已经将工人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加入了自我管理和劳动所有权,这样一来,工人的个人权利就可以成为有效地提升工人的福利、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可以作为麦金太尔所提倡的集体性权力的补充。
从理论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全球金融危机为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进行了新的研究,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在这一研究中,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借鉴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主要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来分析金融资本的本质,预测它的未来趋势及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根据一个世纪全球金融资本的震荡来分析金融资本的经济特征和政治特征,以及它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进而揭示全球金融资本的危机机制,从而建构了从否定的、危机的视角发掘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的思维框架。
(二)劳工问题
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从总体上看,就是管理者等中间阶层发展成为阶级结构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基于这一变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突破了以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采用的工人和资本家阶级对立的二元结构框架,而将管理人员等中间阶层纳入了阶级结构之中,提出了三元结构关系。理查德·沃尔夫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学术界在对《资本论》的重新解读中提出的新的阶级概念,指出这种新的阶级概念的主要特点就是用多元决定论取代了决定论。这一新成果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提供了一个理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以及经济体内部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新模型;(2)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作了新的研究,即从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关注转移到对剩余价值论的关注;(3)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两个阶级形成的过程,并将产业工人和非产业工人的概念区分开来。沃尔夫指出,阶级结构源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由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阶级,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产业工人)、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分配者(产业资本家)和剩余价值分配的受益者(非产业工人、商人、银行家和经理)[8]。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阶级分析的三元构架,指出新自由主义建立的社会秩序是阶级、统治和妥协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而金融管理层在建立这一秩序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要研究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就必须采用这种三元的阶级分析框架。根据这种分析框架,对一个社会秩序的判断可以依据两种标准:第一种标准是对妥协的定位,这种妥协是发生在资本家阶级和管理层之间(右倾),或管理层与大众阶级之间(“左倾”);第二种标准是在上述情形中哪一种妥协的阶级居于主导地位,而真正左派的妥协只能在大众阶级取得领导权之后才可能实现[9]。
在意识形态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普世主义进行了批判。普世主义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认识论原则和道德渴望,为不少西方学者极力推崇。斯蒂芬·乔森在《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7]一文中指出,在今天,普世主义已经蜕变为一种时代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政治和公共话语日益从属于这种普世主义的霸权,这将导致社会公共领域的衰落,因为这种普世主义是把普适性建立在特定的人类主体的观念之上,忽视人类的历史性、地理性、社会性与性别的差异,而消除了差异性的普适性是一种虚假的普适性,是与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相背离的。
如果把上述研究与20世纪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作一个对比,不难看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既与20世纪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相联系,继续沿着文化批判的方向发展,又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其吸收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许多理论成果,具有了更强烈的批判性,从而展示了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和趋向。
四、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理论的再探析
自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就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有两个因素再度激发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这一课题的兴趣:一个因素是革命的主体性陷入了危机,另一个因素是拉美及其他地区的革命的基督教和解放神学的发展。这两个因素实际上提出了宗教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从而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绝不像先前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人民的鸦片”,是统治阶级在思想上压迫人民的手段,其同时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唤起群众革命、实现自己解放的一种方法。这无疑挑战了以往人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宗教理论的基本思路。根据这一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建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理论研究的新思路,即从宗教的统治和革命的双重意义上来重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在这一阐释中,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在理论上区分宗教的双重含义,即作为解放意义的宗教和作为统治意义的宗教,进而历史地考察马克思青年时期与成熟时期对宗教的不同论述,强调马克思早期的宗教批判主要是针对作为统治意义的宗教,而他成熟时期的宗教批判即对资本主义拜物教和对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则是针对作为解放意义的宗教,正是后者,成为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思想基础。通过这种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他们研究宗教与革命的关系、研究解放神学,留出了理论的空间,并沿着这一思路重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
米歇尔·罗伊在《马克思主义和宗教——人民的鸦片》[19]一文中批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警句奉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本质,指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简单化了,因为这种表述在德国其他哲学家的著作中也能找到。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马克思早期和成熟期研究宗教的不同指向,指出马克思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还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他这时的宗教批判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的”,其特点是一种历史指向而非阶级指向;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始把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来加以研究,正是这一研究建立了革命与宗教之间的复杂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不仅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过论述,而且在卢森堡、布洛赫那里得到了发展。这些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宗教与革命关系的思想资源。他还在《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本雅明与韦伯》[20]一文中系统地解读了本雅明的《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一文,并联系韦伯、布洛赫以及弗洛姆、兰道尔等人的观点,对已经沦为宗教的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罗伊认为,尽管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本雅明具有启发意义,但与韦伯的世俗化论题相比,本雅明更具批判性、更加激进。在本雅明看来,资本主义的宗教具有三个决定性特征:其一,它是一种纯粹偶像崇拜的宗教,或许是既存的最为极端的狂热崇拜;其二,这种宗教崇拜持续的时间是永恒的;其三,具有创造负罪感的特点,即资本家和穷人都是有罪的。这三个特征表明,本雅明的宗教批判,虽然是以韦伯提出的宗教资本主义产生于对加尔文主义的改造这一观点为出发点的,但赋予了资本主义一种超历史的维度。两者相比,本雅明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分析资本主义何以会陷入绝望、我们应该如何逃离资本主义等问题,则更有启发性。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这一事实揭示了全球金融资本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观念的内在联系,因此,在这个时代,要研究金融资本的内在规律及其运动方向,就必须批判地考察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与观念。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正是因此而把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的。在这个逻辑起点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分析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入手,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新话语。
阿尔伯特·托斯卡诺在《反思马克思和宗教》① http://www.marxau21.fr/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rethinking一文中对建立在商品拜物教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的宗教”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只有研究日常生活的宗教,才能认识马克思从对天国批判到对尘世批判的转换,因为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说明实质上是以资本代替了宗教的功能,是把宗教变质为商品关系,从而也把宗教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宗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的宗教”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宗教批判的终结和完成,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宗教的批判。总之,我们只有将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中的宗教连接起来,才能领会批判的社会理论中所说的“灾难的现代性的返魅”(reenchantment of catastrophic modernity)。约翰·莫利纽克斯在《不只是鸦片:马克思主义和宗教》[21]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出发,论述了唯物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指出现在几乎所有的评论和阐发马克思宗教观的著作都是从一种简单的、单一的维度来分析马克思的宗教理论,只强调马克思声称宗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而忽略了马克思对宗教的其他作用的论述,因而他们不了解马克思所批判的宗教是那种统治阶级的宗教,即作为人民精神鸦片的宗教,而现实的宗教可以是激进的、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运动。在对宗教和社会主义的看法上,莫利纽克斯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彻底反对任何禁止宗教的想法,既然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那么革命党也应该尊重信仰的差异,这样才有利于工人阶级斗争的团结。
这是一副巧用典故的趣联。据传,晋代张翰爱异乡做官,有一年秋风乍起,他忽然想起家乡苏州的莼菜和鲈鱼,于是感叹道:“人生贵得适志。”便名驾而归。为了品尝家乡风味,连官也不做了,驾着一叶轻舟返回老家,这等天真情趣不禁让人莞尔一笑。
上述这些分析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宗教与革命的关系,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批判理论研究的新向度。
“除了骗人的狗血电视剧,有男人愿意做这么幼稚的事吗?”田铭打断她的话冷冷地说。没想到范青青却十分肯定地说:“你,就是和你!”田铭看着范青青那天然自信娇蛮任性的精致小脸,就像看到了一只坏脾气的暹罗猫。
与鲁迅的刚硬文化个性相比较,茅盾的文化性格,受到浙西儒雅风尚的浸淫,明显烙有浙西文人的印记。“浙西以文”的特点,造就此地“慕文儒,不忧冻馁”,“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10]的崇文传统,于是在“儒雅”风尚浸淫下,浙西独多“清流美士”,当然也不乏对我国的文化和文学做出重要建树的饱学之士与诗文大家,例如晚近文学史上名重一时的浙西词派便出于此地。
从总体上看,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复兴是围绕着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及其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消极影响这个论题展开的。这些批判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但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问题,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文化领域发展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3页。
[2] Melinda Cooper, Life as Surplus: Biotechnology and Capitalism in the Neoliberal Era,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
[3] Randy Martin,An Empire of Indifference: American War and the Financial Logic of Risk Management,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Alberto Toscano,“The War against Pre-terrorism:The Tarnac and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Radical Philosophy, Vol.154,2009,pp.3-4.
[5] Mike Haynes,“Capitalism, Class, Health and Medicine”,International Socialism,Vol.123,2009.
[6] Iain Ferguson and Kate Pickett,“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Allen Lane,2009.
[7] Stefan Jonsson,“The Ideology of Universalism”, New Left Review,2010,p.63.
[8] 理查德·沃尔夫:《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的新解读》,《经济思想史评论》2010年第2期。
[9] 周思成编译:《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热拉尔·杜梅尼尔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7期,第12-13页。
[10] 费尔·赫斯:《全球化与工人阶级的主体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第26-30页。
[11] Eric Hobsbawm,“World Distempers”,New Left Review,2010,p.61.
[12] Oliver Nachtwey,“Die Linke and the Crisis of Class Re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009, p.124.
[13] David Bacon,“A Radical Vision for Today’s Labor Movement——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ism and Civil Rights”, Monthly Review, Vol.60,No.9,2009.
[14] Richard P.McIntyre,Are Worker Rights Human Rights?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15] Theodore Burczak,“What Kind of Rights Do Workers Need to Eliminate Exploitation?” Rethinking Marxism, Vol.21,No.4,2010, 21(4).
[16] David Bacon,Illegal People: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Migration and CriminalizesImmigrants, Boston:Beacon Press,2008.
[17] David Bacon,“Equality and Rights for Immigrants—the Key to Organizing Unions”, Monthly Review,Vol.62,No.5,2010.
[18] Hester Eisenstein,“Feminism Seduced: How Global Elites Use Women’s Labor and Ideas to Exploit the World”,Paradigm, 2009.
[19] Michael Lowy,“Marxism and Religion: Opium of the People”, New Socialist,2005,pp.19-23.
[20] Michael Lowy,“Capitalism as Religion: Walter Benjamin and Max Web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2009,pp.60-73.
[21] John Molyneux,“More than Opium: Marxism and Relig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008,p.119.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1-00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01)
作者简介:何萍,1953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骆中锋,1983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 磊]
标签:宗教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世纪论文; 哲学论文; 世界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论文; 《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01)论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