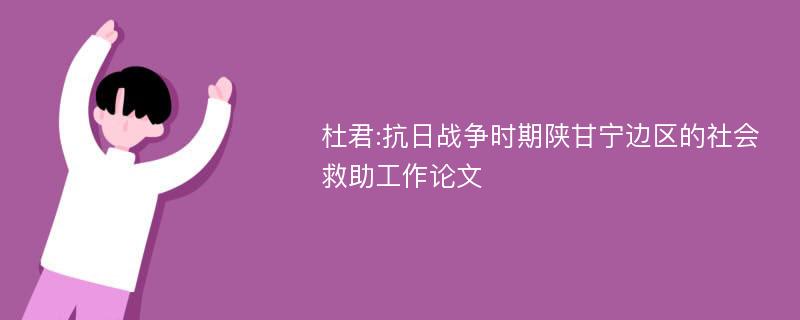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难民、灾民、烟民、赌民、“二流子”、老弱病残者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救助工作。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工作的特点是实行分类救助原则、注重培养被救助群体的自救能力、形成了多元化救助体制。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取得了明显成效: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民众思想观念变革和社会风气改善。
[关键词]抗日战争;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
近年来,史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机构、社会救助方式、社会救助经验教训等诸多社会救助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做好新时代的社会救助工作,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本文在此基础上,对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对象、社会救助特点、社会救助成效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一、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工作的对象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工作的对象为各阶层的弱势群体。
(一)对难民的救助
政府积极安置难民,解决其基本生存问题。抗战初期,众多难民开始涌入边区。截至1939年1月,“从山西、绥远以及冀、晋、豫各省流入边区之难民,前后为数在三万以上。”[1]14对这些难民的救助,边区政府主要先从解决他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入手。民政厅建立难民收容所,解决难民途中的食宿问题。难民到达边区后,政府制定了具体的救助政策,如在1940年颁布的《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中,规定难民“得请求政府分配土地及房屋;得请求政府协助解决生产工具;得免纳三年至五年之土地税(或救国公粮);得着量减少或免除义务劳动负担”[2]283等。为帮助解决难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边区政府发放了紧急救济粮款,发动群众调剂住房、粮食,使难民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此外,政府还积极组织难民进行生产自救。对于难民来说,政府的紧急救济只能解一时之困,再加上边区经济基础薄弱,依靠紧急救济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必须生产自救。为此,边区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帮助难民自谋生路。难民到达边区以后,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帮助难民,鼓励难民自谋生路,并根据难民自身的特点,帮助介绍工作,有的介绍到农村种地,有的介绍到工厂做工,还有的介绍到学校读书后再返回家乡参加抗战[1]14。其次,创办难民工厂。此办法,既可吸收难民参加劳动,以资赈济,同时又能促进边区工业发展,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边区的难民工厂主要有难民纺织厂、难民农具厂和难民硝皮厂。仅1939年8月至12月共5个月,这3个工厂除解决难民生活、工资外,还盈余6 402.55元(法币)[3]184-185。再次,鼓励难民垦荒。边区荒地多,政府便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难民开荒生产,以此解决难民的生存问题和边区农业发展问题。1943年3月,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其中规定:经移民难民自行或雇人开垦之公荒,土地所有权归移民或难民,且3年免收公粮及其他义务劳动;开垦之私荒,3年免缴地租,且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移民、难民在政治上同边区老户享有同样的权利;难民无力治病的,享受公共医院免费医疗优待,子女入学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等[2]305-306。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促进了移难民工作的开展和边区农业的发展。最后,组织群众互相调剂。边区政府积极动员老户给移难民打窑洞、盖房子,帮助难民开荒,实行赈济互助。许多老户都将多余的农具、籽种、土地挪借给难民使用、耕种。如华池县群众1944年就给移难民调剂了429亩土地、10.8石粮食、9.52石籽种[4]320。
(二)对灾民的救助
陕北地瘠民贫,加之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的影响,经常发生灾荒,有“三年两头旱”之说。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至1944年受灾面积共计7 649 607亩,损失粮食576 820石,受灾人口1 055 470人[4]204。对于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边区政府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救助:放赈、发放农贷、以工代赈、设立义仓。
至于“一鹤冲天”,张三爷则说:“当时我急中生智,用尽平生之力蹬踏坐马,借劲上蹿,抓住一块突出的岩石,脚蹬手爬,爬上山顶的。当时腿也撞伤了,手也磨破了。”
对于蛋鸡料,适宜的粒度为7~18目。经改进后对辊粉碎机粉碎的玉米粒度(61.22±2.44)%远远高于理想粒度的基本要求,而经锤片粉碎机粉碎的玉米粒度在7~18目的比例平均仅达到(30.67±1.30)%,不能达到理想粒度的基本要求。因此,本试验中,改良对辊粉碎机对玉米粒度有显著影响,值得在饲料生产中推广应用。
在对边区灾民的社会救助中,政府也非常注意贯彻“自救”方针。针对边区经常发生自然灾害这一特点,政府除了发放赈济粮款外,还采取了以工代赈、领导人民创办义仓等以人民群众“自救”为主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各地普遍实施后,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一积极的救助理念不仅符合当时边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是现代社会救助工作的核心理念,即“助人自助”,有利于调动被救助者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促进施救主体和救助对象的交流,不仅使边区的社会救助工作顺利进行,也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这种因群体而异、因个体而异的救助方法,有利于发挥个人特长、潜能和主观能动性,保证了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提高了救助工作的效率,也发展了边区经济,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
2.以工代赈。主要是指遭受自然灾害以后,安排灾民参加国家或社会举办的工程劳务,增加收入,解决生存和生产困境的办法。这种办法边区政府在社会救助中也经常采用。如1940年在绥德和陇东各地,实行了修路和建筑水利工程,作为以工代赈,支出法币5万余元,得以代赈的灾民达3 000余人[4]211。1941年三边地区发生灾荒时,边区政府民政厅除了拨救济粮外,还拨给2万元的救济款,并给定边专署发指示信,要求本着以工代赈的原则,动员灾民修筑定边至寺台大车路一段,这样“尚可将赈款作为发工资之一部,以利达到经费节省,民困解决,并迅速修成该段道路,以利盐运之目的为要”[5]330-331。以工代赈既能救济灾民,使其摆脱生存困境,又能兴办公益事业,推动边区建设,是一举两得的救助措施。
品牌需要场景“引爆”,即流量全面跟随场景流行。场景成为消费者商业需求新的入口和渠道。场景营销需要更多的流行细分,以促进渠道与用户可持续融合与发展。
3.发放农贷。1941年12月,边区政府成立农贷委员会,各县成立农贷办事处,负责监督农贷发放和还款事宜。1943年,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农业贷款章程》,规定贷款对象为勤劳的贫苦农民、灾难民。贷款按照用途的不同分为农业生产贷款、农业供销贷款、农村副业生产贷款和农田水利贷款,且以农业生产贷款为主,主要包括耕牛农具、籽种肥料、棉花及各种青苗等。且贷款分为长期和短期,利率分别为年利1分和月利1厘[6]116-117。发放农贷既减轻了政府救助的压力,又可促进灾民发展生产,是一种积极的救助方式。
4.创办义仓。义仓在组织上由政府直接领导,从义仓所辖区域的群众中推举出热心公益并素有威望的人士成立义仓筹委会,群众选举代表5—7人组成义仓管理委员会,负责募粮、入仓、查仓、放粮和保管事宜。在平年或丰年发动群众在自愿乐施的原则下进行募捐,遇到灾年则开仓放粮。义仓带有防灾备荒的救济性质,同时还刺激生产发展。自1939年新正县共产党员张清益在其所在乡雷庄首创义仓之后,义仓即在边区普遍推行起来。据1944年5月中旬的调查统计,延属分区仅富县一县就开义田2800亩,成立义仓93处[7]。
(三)对烟民、赌民和“二流子”的救助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在制定对各类群体的救助政策时,立足于当时边区经济基础差、生产力低下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时更注重培养被救助群体的自救能力。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对各类群体的救助过程中,而且始终是社会救助工作的灵魂。其中,最富有成效的就是对烟赌民、“二流子”这些生活困难的社会闲散人员的救助与改造。对于这类群体,政府先从思想上教育他们,让他们认识到劳动光荣;继而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工具、资金方面的实际困难,使他们摆脱过去沾染的不良习气,都能够靠劳动来维持和改变自己的生活。
制定法律,坚决禁止赌博、吸贩毒。为了禁止赌博,边区政府制定了大量法律条例。在1938年5月和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曾先后两次布告全边区军民:“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8]61,并公布了要取缔的数种行为,其中就明确规定:“抢占民房,聚众赌博,包庇或贩卖鸦片者,无论任何机关与人员,均得以法令惩处之。”[8]114对于禁烟,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查缉毒品办法》等,从法律上对吸、贩毒人员进行了界定并制定了惩罚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10月份开始,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调研疫情时曾表示,要加速猪肉供应链由“调猪”向“调肉”转变。这也被业内解读为今后生猪流通格局和猪肉供应链将有重大调整。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工作取得了如下成绩。
在对烟民、赌民、“二流子”思想改造的同时,边区政府对这部分人进行了生活救助。例如对于从事农业生产有困难的“二流子”,政府发动群众给他们调剂土地、农具、籽种,组织他们与其他村民一起互助劳动。还有一部分“二流子”,政府则帮助找工作或借给资本,以便摆摊、做小买卖等。这些措施使不少“二流子”摆脱了过去沾染上的不良习气,能够靠劳动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
(四)对老弱病残的救助
对社会上一些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进行救济,是社会救助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也受到了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颁布了相应的法令法规来展开救助工作。
由上可知,COPD合并肺心病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与其血清炎性细胞因子、BNP水平呈正相关,临床中在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时需把握其内在联系。
2.对老弱孤寡、生活无法维持者的救济。为实现老有所养,边区政府民政厅设立了养老院,并于1941年6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养老院组织规程(草案)》,其中规定了进入养老院的资格,即60岁以上的无法继续服务革命的同志以及无法维持生活的抗属或有功于国家的边区老人,且规定入院老人的衣、食、住等方面需求均由院方负责,革命退职者仍享受原津贴,抗属及其他有功于国家的老人按月酌量发予津贴;入院老人享受一切公民权利并享受免费医疗,这就较好地保证了老人的基本生活,实现老有所养。随后,还在绥德、陇东分区设立分院。社会上的老弱残疾孤寡等生活无法维持者,都得到了政府的救济,政府每月供给他们粮食、救济款,对于有些老弱孤寡者,能工作的也尽量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据1939年延属、三边、关中三个分区的统计,共为社会上残疾老弱、孤寡无依者发放救济粮713石,救济款2 745元;1943年靖边、延长、延川三县的统计数字为救济粮150石,救济款1 142元[4]214-215。
二、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工作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工作具有如下特点。
(一)实行分类救助原则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弱势群体涉及各个阶层,且人数众多,情况错综复杂,每一群体又具有自身特点,需要的救助内容各不相同。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救助弱势群体工作中一直坚持分类救助的原则。
救助移难民主要立足于发展边区经济的需要,对其采用救济和安置相结合,鼓励难民垦荒等办法,先解决难民的生存困难,再帮助难民发家致富;救助灾民,主要以生产自救为主,发放赈济粮款与发放农贷相结合;救助烟民、赌民、“二流子”等,则重点是对他们进行生活和生产上的救助,培养其自身生存能力,最终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对于无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则由政府来负担,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即使是同一类救助群体,也根据个体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救助方法。比如对难民的救助,政府并不是一刀切,而是根据个体差异分别对待。对于那些想从事农业生产的,政府和当地群众向难民提供各种帮助,使其能够建立家庭;对于有一技之长的难民,政府则安排其进难民工厂做工,到机关工作,或为其提供贷款做小买卖等,充分考虑到难民的个体特点和需要。
市场行情的好坏决定着生猪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规模养猪场的经济效益。精明的养殖户,要随时把握好这个关键。行情好时,加大投入,尽快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及时扩大销量,减少库存量。行情不好时,及时调整优化猪群结构,缩小育肥猪群,增加优良繁殖猪的头数,等待养殖周期回转,以备东山再起。但是,一些缺乏远见的养殖户,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行情好时,一味扩大养殖规模,惜售产品;行情不好时,不惜血本全部抛售存栏,转产转业。从而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二)注重培养被救助群体的自救能力
陕甘宁地区历来自然环境恶劣,社会闭塞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封建迷信较为盛行,烟民、赌民、“二流子”等寄生群体人数众多,他们是无序社会的受害者,因染上恶习生活贫困潦倒反过来又危害社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解决边区经济发展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以及移风易俗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群众对这部分群体进行了救助,主要是改造思想,强制劳动,使他们过上自食其力、丰衣足食的生活。
在对边区移难民的救助工作中,边区政府也很成功地实践了这一原则。边区政府对移难民发放必要的粮款,组织当地群众调剂解决困难,尤其注意发动移难民生产自救。政府负责给移难民介绍工作,安排他们到工厂做工,鼓励移难民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并给予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还给移难民发放农贷。许多移难民都得到了益处,这也促使他们努力生产。通过政府的救助,尤其是移难民们自己的努力,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有不少移难民通过辛勤劳动发家致富。
1.放赈。主要是在遇到灾荒时边区民政厅发放救济粮款,解决灾民的穿衣和吃饭问题。1940年3月边区党委和政府发出《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县组织赈济委员会,并选派得力干部进行深入的调查统计工作,对每一个救济者都需经过群众的讨论,确定必要及救济数量后,再以区为单位经过赈济委员会核查后,发给民政厅印发的救济三联赈票,方可到指定机关领取救济粮款。遇到紧急情况时,也可先发放粮款。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至1942年,边区政府共发救济粮7 227.4石,救济款809 746.80元[4]208。边区政府的赈济措施在救助灾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拨发的数额有限,但对于灾民们来讲却如同及时雨一般,短期内解除了灾民的生存困境,暂时得以温饱。
(三)形成了多元化救助体制
抗战时期边区建设面临着很多严峻的问题和考验,而边区政府的力量又是有限的,若单靠政府的力量,难免顾此失彼,因此在社会救助工作中边区政府形成了多元化的救助体制,发挥了党、政、军、民的合力作用。
如果说外观包装的设计升级只是产业升级的常态动作,那么包装材质的升级则更加深入到企业的生产核心。“我们从传统的透明塑料纸包装升级为纯铝锁鲜装,可以避免光及空气的进入,使紫菜的保质期得以延长,鲜美度得以保持。”阿一波紫菜的负责人李志江说,这也是为消费者营造更好消费体验的必要升级。另据了解,此前包括达利集团、盼盼食品等企业也与当地的科技型企业对接,利用科技助力提升外包装阻光固鲜的功能作用。
在边区政府的号召与影响下,边区的八路军对社会救助工作给予了积极的帮助,如在救助难民工作中,八路军保护难民逃入边区,解决难民逃难途中的食宿问题;当难民来到边区后,一些地方驻军帮助安置难民,与难民共同生产;军队主动招待难民,与难民联欢等,密切了军队和百姓的关系。这样既能分担政府救助工作的压力,也有利于边区民众与政府、军队拉近感情。
1.对儿童的收容和救济。1937年边区政府建立了托儿所,1938年与边区儿童保育会合并,改称为边区儿童保育院,截至1939年就收容了全国各地的三百多个儿童。儿童保育院设有两个班:婴儿班,收托6个月以上至3岁以下的婴儿;幼稚班,收托3岁以上至6岁以下的幼儿。进入儿童保育院的主要是抗日将士和工作人员的孩子,以及东北流亡的孤儿。保育院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救助边区内外的难童,作出了很大贡献。
边区社会救助工作的一大特色,就是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其中,进行互济。“一夫不获,时予之辜”,互相救济是人类中的最高道德。边区的群众间互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抗战时期,尤其是1940年以后边区外援断绝,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困难,这种救济方式更是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在全边区广泛推广。调剂的作用大,解决问题也快。在具体的救助工作中,边区民众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帮助移难民建立家务,到各地普遍设立义仓,从动员全边区禁毒禁赌,到改造烟赌民、“二流子”,边区群众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工作在党政部门的领导下,在边区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尤其是开展了互济的救助方式,使得边区的社会救助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合力作用,在边区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使政府能够用较少的投入做了较多的工作。
三、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工作的成就
对烟民、赌民、“二流子”进行思想改造。如边区政府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村民大会、烟民座谈会,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使其在认识到烟毒的危害后,主动劝说烟民戒烟,并监督烟民参加劳动,此外还在烟民之间发动戒烟竞赛,成功者给予表彰奖励。对“二流子”的思想改造方式较为多样,包括群众座谈会、领导干部的劝诫、乡村中有威望人士的劝说、家人劝说以及劳动英雄的模范作用等,让他们深刻体会到劳动光荣,懒惰可耻,实现思想上的转变。比如延安市政府在召开劳动英雄大会时,专门找了几个“二流子”旁听,并像招待劳动英雄一样招待他们。看到英雄们所享受的荣耀,他们很是羡慕和感动,并下决心进行改变,还当场宣布自己的生产计划。
(一)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前,边区是一个农业和工商业经济落后的区域。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社会救助活动,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边区社会救助政策促进了边区人口增加,从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由于实行了优待移难民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移民、难民,边区的人口大大增加。这虽然增加了边区的经济负担,但同时也为边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边区政府鼓励开荒生产,积极帮助移难民解决生产中普遍存在的耕牛、农具、种子等问题,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写道:“最近四年中耕地扩大237万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土地多的区域大批地吸收了移民,增加了人口。例如:延安在1937年只有人口3.4万,现有人口7万左右(延市在内)。因此该县的耕地,由30万亩左右,增至70万亩左右。”[9]755此外,边区通过禁烟、禁赌和对“二流子”进行改造,促使其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边区的经济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据统计,抗战几年来边区收获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1936年收获1 034 301石;1937年收获1 116 381石;1938年收获1 211 192石;1939年收获1 754 258石[10]40。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分析……………………………………………………… 刘洋(10-267)
边区的社会救助工作促进了边区工业的发展。抗战前,边区工业十分落后,几乎没有近代工业。抗战爆发后,为解决就业问题,边区逐步建立起工业和商业贸易体系,实现自给自足。边区建立的难民工厂,不仅解决了一部分难民的生存问题,还促进了边区工业的发展。例如难民纺织厂在创办之初只有8架纺织机和10个工人,“1943年有工人161名,设备有铁织机52台,木织机15台,年产土布7 524匹”[11]132,发展成为边区纺织业的中心工厂。
利用区位商来衡量我国水利产业集聚水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法律环境指数(包括律师、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服务条件,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帮助程度,对生产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
抗战前,边区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很落后。截至1936年底,延安全县仅有工商业和服务业128户,从业人员456人(其中学徒、店员205人,占从业总人数的44.9%);手工业年产值只有2万元左右(法币下同),商业资金总额也不过13.6万元上下[12]146。为了发展手工业,同时也为了解决一部分难民、生活困难者的生活来源问题,政府在农村经济中大力提倡发展各种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作坊。对于那些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移民、难民和“二流子”,政府帮助借贷资本,让其从事手工业生产或商业贸易。这些民众的参与,给当地市场增添了活力。农村的手工业从业人数大增,1944年,延安市的私营商户已有401家,商业资本达22 000万元(边币)[13]25。
随着社会救助制度的不断完善,边区贫困人数大大减少,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于商品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边区的消费合作社在抗战期间有了长足的发展,县、区、乡均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合作社在边区民众生活中起到了供给群众日用品和帮助群众调剂交换、互通有无的作用。边区的集市贸易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有大量移难民迁入的地区,如关中的马栏区,由于河南、大关中等地移来难民,人口由500户激增至1 200余户。这些难民经过政府救助和生产自救,一般生活已达到温饱,购买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仅马栏合作社一家,每日销货在万元以上。由于商贸繁荣,马栏镇设立了逢四、逢十日的集期[14]。这都从侧面反映了边区商业的快速发展。
(二)促进了边区民众思想观念的变革
边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人们思想蒙昧落后,抗战前虽受到一些新思想的影响,但大多数地区人民仍然思想保守,民族意识淡漠。抗战期间,边区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民众的思想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完善的社会救助工作,使民众切实体会到新旧社会制度的不同。通过他们自身生活的变化,使他们对抗战、对国家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感受,这对边区民众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得到进一步发扬。在边区,抗日救亡思潮高涨,从政府到民众,从难民到妇女儿童,都被这股浪潮卷入其中,成为抗战不可或缺的力量。从国统区、沦陷区逃往边区的难民,一路上亲眼看见日本帝国主义暴行,对抗日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对于边区内的民众来说,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改变也是深有感触:发生灾荒有政府及时发放赈济粮款;烟赌民在边区已经绝迹,“二流子”经过改造和救助,已经完全靠劳动解决了温饱问题;老弱病残得到政府的救助,生活有了保障。这些变化与他们在旧社会的黑暗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事实使边区民众深刻认识到了国家与民族的观念,他们自觉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党、军队、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边区民众的这种思想上的认识表现在行动上,则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去,每次征兵任务都提前并超额完成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抗战期间,边区民众民族意识的提高还表现在他们在人力、物力上对抗战的支持。为了支持抗战,边区民众省吃俭用,积极交纳救国公粮,给军队送粮草、做鞋袜、送慰问品等。据统计,全面抗战八年,边区人民共交纳救国公粮101.48万石[15]115。虽然负担加重,但他们却心甘情愿,甚至还要求多出公粮。如延安西区劳动英雄田二鸿不仅自己多出公粮,并且号召全村多出公粮,他说:“多出公粮是为了保卫边区,保卫自己的家乡!”在他的影响下,全村人民争先恐后地提出了自己的出粮数目[16]。通过这些认识和行动上的表现,可以看出保守、封闭的边区,农民思想意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发扬。
Atmospheric-oceanic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large-scale SST anomalies over the North Pacific in winter
(三)改善了边区社会风气
抗战时期,边区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整个边区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边区政府通过颁布法律和实施相应的救助工作,改变了边区吸毒、赌博、游手好闲等不良习气,而劳动光荣、抗战光荣则成为边区民众新的追求。在边区生产劳动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劳动英雄和模范。1943年11月,边区举行了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表彰了各行各业的劳动英雄,如移民英雄冯云鹏,工厂劳动能手赵占魁,农业劳动英雄吴满有,妇女中的英雄郭凤英等。当地政府把这些劳动英雄的模范事迹通过奖励、登报、演戏、互相参观及请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讲话等适合当地群众的形式进行宣传,使许多群众受到了感染,纷纷向劳动英雄们学习,开展劳动竞赛,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高。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劳动光荣、艰苦奋斗的观念深入人心,过去那种“劳动者卑贱”的旧思想已经被取代,使边区完全呈现出一片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社会新观念和新风尚,也使陕甘宁边区成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工作对象广泛,特点突出,成绩显著。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2] 雷志华,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资料选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3]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5]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6]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7] 富县县府指示各区及早成立义仓管理委员会[N].解放日报,1944-06-01.
[8]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9] 毛泽东选集[M].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
[10]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1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12] 延安市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市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13]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14] 关中人民购买力提高,马栏设立集市[N].解放日报,1943-10-21.
[15]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16] 群众热爱边区,星夜碾米赶送公粮,田二鸿自动要多出[N].解放日报,1943-12-17.
SocialAssistanceintheShanxi-Gansu-NingxiaBorderRegionDuring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
DU Jun,OU Rui
(School of Marxism,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extensive social relief work for disadvantage group such as refugees,victims,the elderly,the weak and the disabled and even the good-for-nothing guys including smokers,gamblers,and loafers in 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assistant work are as follows: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classified relief,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their self-help ability and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social aid mechanism. With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this social assistant work,its achievements should not be ignored. It not only promotes 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border areas but also refreshes people’s thoughts and improves social morality.
Key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Social Assistance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9)03-0105-06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9.03.015
[收稿日期]2018-06-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DJ014)。
[作者简介]杜君,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欧瑞,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哲 文]
标签:边区论文; 陕甘宁边区论文; 难民论文; 政府论文; 社会救助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DJ014)论文;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