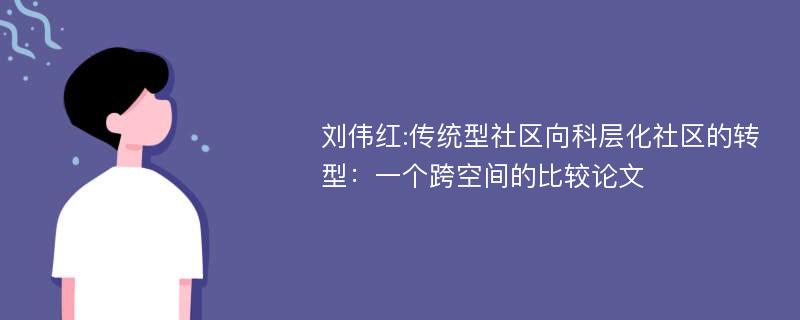
摘要制度变迁带有明显地路径依赖特色,但内外环境的变化又会促进制度要素的多重更迭,从而使制度演化表现出继承性与更替性的双重特点。作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社区形态之一,农转居社区在我国北方生发出一种既承接历史又融合当代特点的传统型社区治理形态,这种治理形态以纵横结合的方式表现出权威的二重性与内部自治的贯通性特性;而在同期的苏南一带,其社区治理则突破传统迈向科层化的社区治理形态,这种形态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权威的二重性,但权威的实现形式与内部自治的横向贯通都发生了明显的裂变。在中观治理结构上,科层化社区治理的转型并未产生明显的制度创新,却在微观层面上瓦解着社区自治的生态循环,如果被其短期效益吸引而扩散其应用范围,则会对其他地区的自治制度创新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应引起各方的关注。
关键词传统型社区;科层化社区;权威;自治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概念在我国大陆学界引起广泛共鸣始于1986年民政部倡导的“社区服务”,1996年,全国范围广泛开展的社区建设运动以及1999年第一批社区建设实验区的建立则进一步推动了理论界对社区发展的关注。在社区服务与社区发展的框架下,上海、青岛、武汉、深圳等地的治理创新实验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关注,但是在实验之后,社区治理的效果如何却不甚明了。正如田毅鹏、吕方等人所言“与经济发展的繁荣局面不同的是,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由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始终步伐缓慢,难以形成稳定成熟的模式”。[注]田毅鹏、吕方:《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0页。从路径依赖的视角看,这种困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与原来“街居制”的“剩余组织”身份有关,按照早期新制度主义的观点,社区组织的“脱胎换骨”需要强烈的外部压力方能达成,[注][韩]河连燮:《制度分析:理论与争议》,李秀峰、柴宝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8页。而这种压力显然不是政府单方作用的结果。
当下,社区自主治理实验的高潮似乎已经过去,而政府基层治理的压力却没有消减,这种压力试图从各方突围,但效果并不明显。在制度创新走入困局之时,一种新的社区形态——农转居社区,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突现。这种社区形态不同于原农村社区,亦迥异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国内学者对这种新生事物保持了高度的兴趣,研究成果陆续呈现。但当前的研究成果多隐含着城市社区优于乡村的理论预设,在经验研究上,缺乏对社区治理阶段性发展价值的重视,强调农转居社区中庇护关系负面价值,[注]卢俊秀:《村落社区被动城市化的庇护关系逻辑》,《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1-14页。而忽视其社区安全阀功能对于社会稳定的价值;[注]刘伟红:《边界模糊的治理:集中农转居社区的类单位化自治之路——基于对山东省的调查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55-62页。倡导一元化的制度改革,希望通过严格、规范的统一管理,将社区纳入制度化发展的轨道,[注]马光川、林聚任:《分割与整合:“村改居”的制度困境及未来》,《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第82页。而忽视了社区自治创新的根基并不在同一性上;将基层社区实践中的“变通式”落实简单视为“制度粘性”所致,[注]李棉管:《“村改居”: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广东省佛山市N区的个案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第1期,第13-25页。而没有看到制度变革中的要素重组带来的影响;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反思农转居改革的目标是否就是城市社区居委会的问题,[注]张丽琴:《从“村改居”看村委会的改革走向》,《理论月刊》2008第9期,第174-176页。并对建立在大量政府投入基础上的“村改居”社区秩序建设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注]吕青:《“村改居”社区秩序如何重建——基于苏南的调查》,《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第6期,第54页。但是却没有相关的研究,对农转居社区的制度创新给予合理的认定,从而影响了其制度发展的生命力。
例7 (2008年全国理科2卷)从20名男同学,10名女同学中任选3名参加体能测试,则选到的3名同学中既有男同学又有女同学的概率为( )
社区自主治理制度的发展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社区内外各种要素相互接触、竞争、协商、合作而建构起来的。但是制度发展的路径不是随意搭建的历史形成的惯性、制度内外的结构性动员与制约、偶发性因素的呈现时机等都会对具体制度的发展产生影响。本文试图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下,从制度发展的连贯性入手,探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型社区与科层化社区建构的内在逻辑及结构性影响,期望能够为社区自主治理理论的探讨增砖添瓦。
二、社区治理制度的自然建构:传统轨迹的当代重组
作为一个学术名词,社区是近代以来学界对工业化进程展开理论反思的产物,但作为一个历史现实,社区却具有久远的实践性。中国的传统村社即可视为滕尼斯笔下“共同体”的现实映射之一。按照孔飞力的归纳,我国传统的村社治理中包含两种基本形式:一为军事化村社,一为非军事化村社。军事化村社与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其村社组织形式与成员的身份归属高度国家化,村社与国家的连接是直接而连续的;非军事化村居,则以士绅、宗族及县政府在基层的代理人为基本治理主体。其中政府代理人的主要治理功能是社会控制及资源汲取,而士绅和宗族的治理功能则在于社区纽带的维持、公共事件的处理及基层需求的上达。上述两种治理形式在封建王朝逐步走向衰弱的过程中最终完成了融合,而融合的结果就是地方士绅影响的进一步扩大,这一点在孔飞力对清末地方团练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注][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1-128页。但是士绅并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体系之外,根据瞿同祖等人的研究,士绅的权威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家选考制赋予士绅的身份权威,二是士绅身份网络所形成的“上达”能力,即士绅为村社谋取资源的能力所带来的事实权威。[注]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29-231页。对于后一点,费孝通先生曾冠之以“双轨政治”之名。[注]费孝通:《乡土重建》,香港:香港文学出版社,1947年,第46-47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以来,我国村民委员会产生的合法路径就是村民民主选举,这一点,已作为社区治理的基本原则得到各界的确认。但是作为形式与实质的结合体,村居权威来源的构成并不仅仅指向居民选举,政府的认可是社区自治组织获得完整权威性的另一重要环节。没有政府支持的社区自治组织,不仅在政府看来是不适当的,在居民看来亦是不合理的。这一点虽然在具体的文本制度中没有具体的表现,但是在实践中却达成了共识。另外,在村社治理中,村委会只是社区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村社党组织是社区权威构成更为重要的一环。党组织的权威来源,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其一为村社内党员选举产生的权威,其二为镇街党组织及政府的支持而产生的权威。党组织权威来源的双重性比村居自治组织更为明显。
金振口服液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其由山羊角、黄芩、青礞石、石膏、平贝母、大黄、人工牛黄、甘草等组成,具有清热解毒,祛痰止咳之功,临床上用于治疗小儿急性支气管炎所致发热、咳嗽、咳吐黄痰、咳吐不爽、舌质红、苔黄腻,符合本次临床试验的适应症,相关临床研究表明[3,10‐11],其对小儿急性支气管炎痰热壅肺具有很好的疗效,作为阳性药,同类可比,安全有效。
后期体温正常,但排便干燥、食欲不好的猪可用柴胡、白术、苍术、陈皮各15克,山楂、大黄各30克,芒硝60克,麦芽、神曲各20克,甘草、木通各10克,水煎喂服,每天1剂,连服3剂[4]。
在传统型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内部治理的横向贯通使社区保持了“块”上的相对完整。但是在科层化社区治理模式下,这种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制度转化:一,社区经济自主权退化;其二,社区监督权退化。
这种因“路径依赖”而重生的“传统型社区治理形态”出现在笔者调查的山东省中部地区,作为传统的孔孟之乡,社区治理的“自发色彩”在政府的“放任”下发展得更为“温和”,表现出更多“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体特性。
(一)社区组织权威的双重来源
社区以“高信度的规范、互惠、关系纽带、声誉系统以及权威的横向延展行为为基本标志”。[注] Dahlander, O’Mahony. “Progressing to the Center: Coordnating Progressing to the Center: Coordinating Project work”. OrganizationScience,July 22, 2011, P.961-979.在村社治理上,我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治理框架是一种纵向与横向整合相结合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国家的纵向权力下行到县为止,但国家权威却是直接渗透到村社的,这种权威渗透以士绅为基本的传达导体。[注]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0页。在垂直权威渗透到村社之后,其在村社内部的运行则是横向延展的,这种横向延展表现在社区权威对社区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社会纽带、价值认同等领域的全面渗透上。这种横向的全面渗透使村社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封闭性自治色彩。
传统型社区治理形态并不单纯存在于我国北方地区,2004年前后,在笔者对苏南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基层治理变迁的调查中,亦曾观察到这种形态在苏南一代的广泛存在。而今,这些已经成为历史,苏南的农转居社区已经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我们把这一发展阶段称为科层化社区治理。这种称谓来源于科尔曼对权威关系的划分,科尔曼曾将权威关系划分两种基本的模式,一种是共同权威关系,一种则是分离的权威关系,前者的典型表现形式为公社,在此系统中支配者的命令与被支配者的利益一致;而后者则表现为科层组织与代理关系,在这一系统中,只有额外的补偿才能保证被支配者的利益获得满足。[注][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7-89页。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居民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是一种近似的共生权威关系,当社区组织日渐转化为政府“下级”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准科层关系,我们称之为科层化社区。
中山市副市长高瑞生介绍,在共建过程中,中山市结合实际,制定了“平安西江”建设的“五大发展目标”,发改、经信、教体、交通、环保、国土、海渔等部门以及各镇区形成工作合力,努力实现水上综合治理、智慧治水能力、协同管理水平、水域环境保护、城市文化多样性“五个再上台阶”。
(二)社区内部自治的横向贯通
在传统型的农转居社区中,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虽不完全是法定的“指导关系”,但是社区自治的横向延展保持了相对的完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社区集体经济的空间延展
此种纵横结合的治理架构在建国后以单位制的方式重现,国家权力深入到各个单位,而单位内部呈现出政治宣讲、价值建构、身份建构、经济生产、社会保障同体的结构。虽然理论界很少将单位作为自治体看,但是众多的单位理论学者却是将单位当作“共同体”来看的,而共同体在本质上是自治的。当下,随着单位制的逐步解体,基层治理再次发生了制度构成要素的更迭,而新制度主义高度青睐的“路径依赖”现象则在集中农转居社区中获得了“重生”。
在村庄时代,虽然土地等主要经济资源的产权是集体性质的,但是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个体行动者采取了更加原子化的社会行动模式,而单家独户的居住空间也为这种模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拆迁后,集中化的居住模式、分享式的公共空间使个体分散经营的弊端充分暴露,而聚集所产生的商业机会也使得“兼业化”的居民无暇顾及“成本—收益”比过低的碎片化的“土地”,双重压力的存在催生了社区重新整合“集体经济”的需求。社区组织成为承接这些需求的应然主体,并通过社区内人力、财力的再组合建构起新的“复古式集体经济”。这种集体经济较为普遍地采取了外方内圆的“公司型”建构模式:社区对外表现为市场型组织,按照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模式运行,对内则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共享,以平等共有的方式推动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福利分配。与分散居住时代的经济形态相比这种“复古式的集体经济”亦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色:分散居住时代村社经济的发展是个体直接对接市场,个体经营者之间没有风险及责任共担机制,个体对集体的诉求少,集体归属感弱;拆迁后,个体的部分利益聚结到集体,集体风险共担及责任共担趋势走强,个体对集体的诉求变多,集体归属感与监督力同步增强,从而使社区内部的团结纽带得以强化,社区组织的对内责任性得到普遍提升。
察尔汗地区的盐岩中大都以层状似层状产出,但其的杂质含量不一,泥质夹层分布不均匀[12],得到的试件中的夹层也不能保证夹层大小一致且分布均匀。在试验中选取试样时从同一块岩石中钻取岩芯,这样得到试验结果只能表明试样表面的泥质夹层的含量及厚度大致一样。且目前的技术手段很难判别试样内部夹层的具体分布[13-14],无法研究夹层厚度对盐岩力学特性的影响程度,这也是目前研究的难点所在,因此本文假定内部泥质夹层是均匀分布的。通过对野外采集的两类盐岩进行单轴压缩试验,天然和卤水饱和两种状态下盐岩的破坏过程、全应变-应力曲线、强度特性、质量差与强度的关系等方面研究与分析,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第二,社区共同价值与社会纽带的再显性化
社区共同价值与社会纽带并不是因为集中居住而重新建构起来的,在分散居住的村庄时代,这些社会性的要素就一直存在,只是更多地处于治理功能的隐形状态,而农转居的发展则为这些社会性要素的显性化提供了空间支持。农转居社区共同价值与社会纽带的显性化是规划性制度变迁与生成性制度变迁合谋的产物。在社区集中化完成之后,随着集体性事件的增多,社区共享利益的分配逐渐促成了居民认知上的“内外”之别,这种内外区分的优越感类似于单位时代“单位人”因独享的单位福利而产生的优越感,其产生过程并不源于个体的努力,而是来源于“身份”的差异。这种不能通过个体努力改变的差异对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个体而言,更具有诱惑力,也更容易产生优越感,从而推动居民身份认同的显性化。这种身份认同的显性化会进一步密化社区内部的交往频率,而使社会纽带的连接韧性和强度得到提升。社区共享利益分配不仅以其形式要件推动了社区居民身份认同与价值体系的再建构,还以其现实触感推动着社区内各个领域透明、公正制度建立的可能性,在公平理念日渐深化的当下,居民对收益的分配已不再单纯纠结于分得多少而更注重分配是否公道,而公道与否则是制度如何发展的问题。
传统型社区治理形态在治理结构上更多地传承了历史性的要素,社区权威既承接了来自政府的权威渗透,协助政府完成其基层指令;又发展了社区内部横向贯通的治理生态,发展出相对独立的“自治王国”,表现出明显地纵横结合的结构性特征。
三、传统型社区治理向科层化治理的转型
在传统型社区内部,社区组织候选人来自本社区,在利益认同、关系纽带、价值认知上与社区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其选举过程虽然是在基层政府组织的引导下完成的,但是基层政府并不能直接决定其结果,当选团队的授权根源在社区内部,这种权威来源使社区组织与居民间的监督关系得以确立。而政府对选举中的组织引导及其对选举结果的公布则使社区组织的权威地位得到更广义的合法性认可。社区组织权威的双重性特点,具体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居)民委员组织法》中关于社区组织协助政府完成相关行政任务的法规条文,使政府众多政策、法令没有止步于政府基层部门,而是通过社区组织的力量得以执行。在政府没有过度介入社区具体运作的情况下,社区内部横向贯通的自治机制得以自然的建构。
目前绥中县工业总产值173.22亿元,预测在2020~2030年期间,其年平均增长率5%,因此2030年绥中县年总产值可达282.16亿元。而在这10年期间,工业用水指标平均为4.0m3/万元,因此预测2030年绥中县工业用水量0.512亿m3。
“支配乃是共同体行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注][德]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而历史形成的惯习、外部强加与内部建构的制度则是影响支配结构的重要条件。[注]同上,第51页。传统型社区治理向科层化社区治理的转变既表达了对传统社区治理制度的部分替代又表达着社区内外制度因素的重新组合。在此,笔者将使用同样的分析框架探讨科层化社区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一)社区组织权威来源的结构转化
科层化社区的组织权威仍然保持了双重权威来源的特点,选举和政府授权是社区组织权威获得的两个主要来源。但是,在具体运行上却发生较为普遍的功能异化。这种异化与国际上有关社区治理建构基础的争论有一定关联,其争论的核心是:社区发展应由专业化的服务人员支撑还是由社区内部产生的领导者支撑。其中领导者支撑论更加强调民主参与,而专业化服务则强调经济效率。[注]Sue Kenny,“Chang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Roles: the Challenges of a Globalizing World”. In Rosie R.Meade, Mae Shaw , Sarah Banks, Politics,PowerandCommunity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P.47-57.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一带,政府主导的社区发展基本上是沿着专业化的方向推进的。这种发展路径以村(居)委会为平台,不区分政府公共服务与社区服务的差异,更强调管理向服务的转型,这种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科层化社区建构的步伐。
在乐曲风格上,《巴斯蒂安钢琴基础教程》也比传统的钢琴教程有了很大的扩充,包含了古典、民歌、童谣、流行及现代等风格,让学生接触到丰富多样的音乐风格。但《巴斯蒂安钢琴基础教程》没有涉及巴洛克时期的复调作品。
调查发现,苏南一带许多农转居社区都有形式不一的以公务员考试或组织选调生的名义进入社区的社工。这些社工往往是在社区初建阶段以政府委派的方式进入并主持社区工作,村居原来的两委成员只是发挥协助作用。这些以政府委派方式进入社区的社工并不是政府在社区的独立性机构,他们在居委会工作两年之后,必须按照相关政策与程序参加居委会的“两委”选举,如果不能在选举中“留任”,就可能被“清退”。这意味着,这些“社工”的权力来源也是双重的,虽然其初始的权威来源于政府委派,但是其工作的长期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居民选举的“授权”之上。与传统型社区明显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委派而来的“社工”是先主持工作而后获得“基层授权”,这种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社工”的留任。用老百姓的话说,“不是特别不行,就是他了。”加之苏南一带“多村并居”、“拆村并居”模式的助力,“先工作后授权”的模式往往能获得平稳的过度。
社区监督权是指社区内居民、组织相互监督的权力,这种监督权的最终落脚点是社区治理的现实效果,即社区治理的绩效。农转居完成编制改革之后,在组织机制上的重大转变就是镇、街对社区的考核机制开始真正地发挥作用。拆迁前及安置初期,社区对镇、街的考核并不是特别看重,特别是那些经济发展较好的社区更是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社区两委的工作津贴及奖金发放主要是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政府发放的工作津贴在两委工资收入中占的比例较小。但是在转型之后,居委会对于考核的重视则会大幅提高,原因在于:居委会的工资、奖金的相当一部分是依据考核成绩由镇、街财政发放的。平时发放的工资在年度总工资中的比例仅在60%左右,而剩余40%左右的收入要看年度考核的情况,如果年度考核成绩满分,则发放全额工资、奖金,在各类考核指标中每扣一分,则减去一部分工资、奖金。在苏南大部分的农转居社区中,社区组织成员的年工资、奖金额平均在10万元左右,书记主任则在14万元左右,40%的考核绩效,则意味着年终4—6万的经济收入。年终考核的主体是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社区居民打分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在实现了农转居编制转化之后,居民组织向政府靠拢的特点就更加明显。
(二)社区内部的自治功能退化
山东运河区域,一般是指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流经山东境内的部分州县及其辐射地带,大致包括今天的枣庄、济宁、聊城等3个地级市,包含德州的德城、陵县、武城、夏津、平原等县级地区,以及菏泽市东部单县、巨野、运城,泰安市的东平县,济南市的平阴县等近40个县市。明代以前,在京杭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会通河”疏浚之前,山东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临近的华北地区差别不大。随着几代统治者的大力开凿、疏浚和重整,从元末明初到之后将近400余年的时间里,随着运河航运的便利,山东运河区域的烟草生产、棉花种植、果品栽培等活动也因大运河的南北通达、易于转售而促使地方经济获得了结构性的调整和跃升。
第一,社区经济自主权的退化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有权管理本居民委员会的财产,但按照既存的城市社区惯例,居委会的职责不包括社区集体经济的经营权,因此,在城市社区建设早期,不少地市皆将原属于居委会的集体产业收归地方政府管理。这种政经分离的治理模式,近年来有逐步增强的趋势。在笔者的调研中,苏南许多集中农转居社区皆以股份公司改革的方式,将集体经济管理权从自治组织分离,这种分离不是像通常的模式那样在社区内部另建集体经济组织,而是将集体经济转移到了市、镇经营的股份公司,在村居实现编制转型之后,社区组织无权管理集体经济,居民则直接领取其股息红利。科尔曼认为,个体的权利转让以其拥有这项权利为基本前提,[注][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第71页。但是拥有权并不是权利转让的充分条件,特别当所有权具有集体特性时更是如此。在村庄时代,村民对集体资产拥有支配权,并以村委会为代理人,而当集体所有权转移给更大的组织,村民成为分散的股东之后,个体化红利更倾向于以原子化的形式将集体组织排挤出利益分享的领地。社区资产的集体所有,最终演化为实质上的个体所有。集体被还原为个体之后,个体的综合已经不是原来的集体。
第二,社区监督权的退化
因而从形式上看,科层化社区的权威仍然是双重的,基层授权与政府授权并存,但是政府授权却是实实在在的,基层授权明显地受到程序设定与搭便车心理的影响。正如布迪厄所言,效率和技术并不直接产生权威,[注][法]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68页。这些能够操作电脑,并能及时处理网络信息的“社区新人”并不比原村两委更能团结社区的力量。同时,“若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的管理人员是由社会招聘而来,居民对其容易产生不信任感,容易出现村改居社区居委会工作不能落实的局面 ”。[注]梁慧、王琳:《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分析》,《理论月刊》2008年第11期,第172页。种种困难的存在,使这些“空降”的社区组织人员更容易在麻烦面前沿着路径依赖的方向垂直向上寻求支持,从而使社区更深地嵌入到政府的科层结构中。
“制度建构个体的目标”,[注]Orfeo Fioretos, Tulia G.Falleti, Adam Sheingate, TheOxfordHandbookofHistoricalInstitutional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23。当社区组织的活动结构由政府的考核制度严格限制时,社区组织的集体目标已经发生了转移。
制度贷款是由政府制定的一种长期低息贷款方式,其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农业生产。该贷款方式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将银行中的一些资金用于农业生产;二是由政府进行担保和支付相应的利息费用,调用农协的资金;三是直接利用国家金融机构进行财政资金贷款。
四、科层化社区治理转型的结构性影响
从社区内部的治理结构看,传统型社区治理向科层化社区的转型的确引发了治理内部制度要素的替代,但是从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来看,这种变化却是十分微小的,因此,并没有引起明显的制度抵制,但是这一看似微小的变化却在制度层面上瓦解着社区自治制度创新的根基。
(一)科层化社区治理的转型并未改变政府与社区的发包关系
在科层化社区治理的合理性解释上,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读,即认为科层化社区治理结构更有利于社区治理的专业化,并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对此笔者不以为然。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形式与内容看,科层化的社区治理并未改变政府与社区的发包关系,社区仍然是一个综合性的微型治理机构,专业性服务供给能力非常有限。
政府与社区的发包关系是通过上文所述的纵横结合的整合方式实现的,在这种方式下,政府将社会需要的某些公共服务的主体环节全部打包下放到基层某一单位,该单位负责完成这一包裹中的所有任务结构。其典型特点是:政府以统一的方式打包,基层单位以统一的方式接包,政府与基层单位内部很少发生直接的联系;政府打包下放的任务以地域或服务对象为边界而不以接收单位的职业能力为边界;基层单位在打包任务面前有多少自主性取决于任务结构对基层单位的激励能力。这种发包关系不仅体现在政府与社会的协作上,[注]刘伟红:《AR测试在英美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争论及启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11页。亦体现在教育、金融等公共领域。
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村社在内部治理上拥有较多的自主权,但是村社并不排斥政府的任务发包。镇街发包给村社,往往以具体事项是否坐落于村社的地理范围以及人员归属是否为村社居民为准。因此,在任务类型上,政府发包的内容往往包含了经济发展、土地整理、住房改造、环境治理、青少年教育、老人照看、居民娱乐等纷繁复杂的种类,结构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包裹”的处理是否附带着政府的财力、物力支持,而在于政府把这社区放在了“包裹”的任务承担者位置,而不管这些“包裹”的公共产品属性如何。因此在基层治理的运作上,社区组织就演化为政府各类公共事务的代言人,即多元任务的承担者。但是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空间,因此,社区在“接包”的过程中能够利用内部的各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将外部任务转化为内部团结的纽带。
在科层化社区治理模式下,虽然社区组织的人员结构及权威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政府与社区的连接方式并未发生改变,政府仍然是打包下发任务,社区仍然是多元任务的承担者,政府非但没有因为社区的科层化而使其走上专业化的道路,相反,这些任务承担者因更加关注多元任务的完成效率,而逐步丧失了专业化发展的各种机会。在这种格局下,科层化社区治理根本无法倒逼政府职能的转化。因此,科层化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并没有改变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治理架构,对政府治理形态的影响几乎是微不可查的。
(二)科层化社区治理转型解构了社区较为完整地自治生态
社区完整的自治生态包括三个主要的内容:一,社区成员的多维认同与责任体系的共存;二,社区组织的对内忠诚;三,社区集体资源内控性。传统型社区治理结构较为完整的维护了上述三大生态要素,而科层化社区则不同。科层化社区治理结构首先侵蚀的是社区自治组织的对内忠诚,这种侵蚀对社区自治生态的发展来说是结构性的,这种侵蚀一旦形成就会强力约束、影响其他生态要素的发生、发展路径,分散、弱化其他要素聚合到自治生态循环中的几率;科层化社区治理结构以监督权上收的方式弱化了社区自治组织与居民间的相互监督,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组织需要监督,社区居民同样需要监督,学者们基于对强权监督的理论偏爱而更容易强调居民对社区组织的监督,但是就我国社区发展的现实看,社区组织对居民的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居民的公共意识尚未建立的阶段更是如此,相互监督方能促进社区治理制度的有效建构,并推动价值认同与利益认同的显性化。相反,仅以政府或居民监督社区组织,社区组织的角色就会退化为简单的服务供给者,而社区居民就发展为社区的“顾客”,这种关系无助于社区公民责任的建构,会进一步侵蚀社区自治发展的根基;科层化的社区治理模式隔离了社区组织个人收益与集体资源发展的关系,使社区组织成员与社区居民同等程度的发展为社区集体资源收益的“散户”,使社区成员直接面对政府与市场,从而加剧了社区内部成员的原子化趋势。
(三)短期治理效果引发的同类模仿容易造成局域范围的治理雷同
模仿是人类学习的重要路径,学习更为先进的技术是组织发展的重要策略。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使富有短期效益的治理策略更容易被周边或相对落后的地区模仿。苏浙沪一带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更容易成为其他地区模仿的“典范”,相对传统型社区治理而言,科层化社区治理更具规范化、专业化、福利化共存的特点,这些特点极易成为其他地区模仿的识别标杆。
采用如图所示的传统模型标定模板时,由于椭圆柱体与圆柱体的投影相互重叠,对其进行投影数据的分离困难。另一方面,若原模板的旋转中心与椭圆和圆的中心共线,特别是如果旋转中心靠近椭圆或圆的中心时,相当于在所有投影角度或部分投影角度产生了模板旋转角度信息的缺失,形成了确定投影角度的盲区。在这种情况下,为求解所有的投影角度序列,需要对模板进行建模,采用解析方法或者数值方法求得。但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都比较复杂,而且无法体现这种模板的优势。
从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看,政府主导的规划性制度变迁只能解决规范化的问题,却不能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而农转居社区面临的问题则各具特点,其产生的原因与可资利用的资源亦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自治”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史看,其着力解决的是“独特性”背景下的治理秩序问题,其目的是“求同存异”。虽然我国的社区规模相对较小,但是“存异”仍然是社区自治创新的重要发力点。笔者比较担忧的问题是,随着各地经济力量的发展,地方政府财力的增加,科层化社区治理成为其他地区学习的典范,而扼杀多元化社区治理制度创新的突破,若如此,我国社区自治发展的道路将更加迷茫。
五、结语
农转居社区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的社区治理形态,在人口结构、经济结构与组织机构上都与农村社区、城市社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从国家与社会自治的连接方式看,它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纵向整合与横向整合相结合的治理格局。这种治理格局既不排斥政府的任务委托,亦不排斥社区内部自治要素的多元重组。此种状态为政府重组社区内部的制度要素留存了较大的空间。
当政府无力承担社区内部自治要素的全部成本而放任社区自然发展时,传统型的社区治理模式就会在基层土壤中生发出基于经济自治的社区团结要素,使社区保持较多的自治空间。但是,当政府的财力足够强大时,社区内部的自治要素也极容易被政府收购,使其发展为科层化的社区。但是科层化的社区治理模式并未改变纵横结合的中层治理格局,社区依然是各类政府职能下发的“沉淀所”。
科层化社区治理说到底是地方政府懒政的一种表现,是其试图利用政府的强大财力收购基层治理的力量,达到提升政府基层工作效率的目的。但是地方政府推动的这一社区改革运动,并不符合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目标,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居民的自我建设能力逐步增强的当下更是如此。
制度变迁并不以年为衡量单位,而是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跨度来衡量。皮尔逊说,因为种种压力的存在或对自身长远规划的不自信,人们更容易采取一些短视的制度规划策略。[注]保罗·皮尔逊、瑟达·斯考克波尔:《当代政治科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何浚志、任军锋、朱德米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6页。笔者以为当下正是农转居社区自治发展的关键节点,这一节点是新制度发展“路径依赖”的起始点,在这个起始点上,政府、学界、社区各方都应以历史的眼光对待自治路径的选择,而不是盲从于“普遍规律”的随波逐流。
TheTransformationfromTraditionalCommunitytoBureaucraticCommunity——AComparisonacrossSpace
LiuWeihong
Abstract:Community, as a basic system of first-level social governance,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the progress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a special community for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Farmer-to-resident community in north of China creates a traditional community governance form which undertaking history and confusing some kind of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with double source of authority and self-government system cross several levels within the community. Meanwhile in Suna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structure has breakthrough traditional and go forward to the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double source of authority do not change, but the function of the authority has changed and lead to the loss of ability of self-govern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community do not make much more difference to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n middle-level, but it is truly make much difference on the ability of community self-government. So scholars should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on the study of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governance to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Keywords: traditional community; bureaucratic community; authority; self-government
中图分类号C91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9)02-0106-11
作者简介:刘伟红,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行政管理系主任、副教授,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地方治理实验室访问学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集中农转居社区变迁与治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5BSH1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城镇进程中的新型社区公共治理体系重组——基于对山东省的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4YJC840018);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政治制度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4BTYJ13)”;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利益型群体性事件化解机制研究:基于社区治理结构重塑的视角”(项目编号:J13WC01)。
责任编辑:郭洪
标签:社区论文; 政府论文; 组织论文; 制度论文; 权威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兰州学刊》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集中农转居社区变迁与治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5BSH1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城镇进程中的新型社区公共治理体系重组——基于对山东省的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4YJC840018) 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政治制度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4BTYJ13)” 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利益型群体性事件化解机制研究:基于社区治理结构重塑的视角”(项目编号:J13WC01)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行政管理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