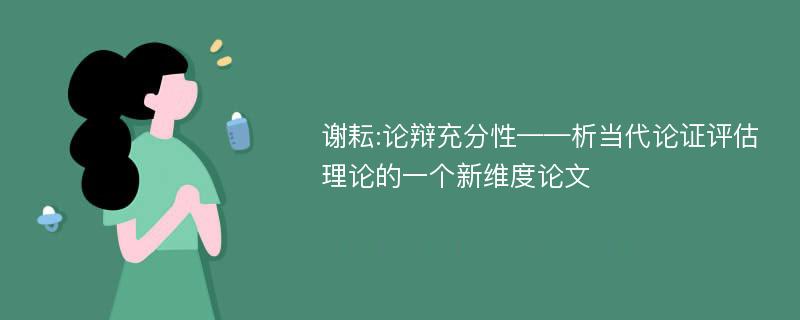
[摘 要]“论辩充分性”标准是当代论证评估理论的一个新进展。它通过对论辩术理论视角的借鉴与整合,从而成功突破了仅关注“前提—结论间推论关系”的传统论证评估维度。论辩充分性标准要求论证者恰当地应对与其论证相关的论辩性素材,因而,其理论阐发既需要指明论证者所具有的特定论辩性义务,也需要澄清成功履行该义务所对应的具体标准。约翰逊对于论辩充分性理论做出了实质发展,他既着力坚持逻辑学的成果性论证研究对象,又试图维系其普遍主义的论证规范理想。从更广的当代论证理论领域来看,论辩充分性标准展示了逻辑学论证研究进路革新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也明确呈现出其理论建构目标与论证实践情境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关键词] 充分性标准 非形式逻辑 论辩充分性 论辩性义务 论证理论
在当代论证研究兴起之前,论证的分析与评估一直是逻辑学的研究主题。受其形式化研究范式的影响,逻辑学提供的论证规范以“有效性”标准为核心,注重从论证结构的形式特性来评估论证的好坏。但这一评估理论在应用于实际生活中时却饱受质疑,因为“对于日常论证的分析与评估而言,有效性这一要求既不充分也不必要。”① R. H. Johnson & J. A. Blair, Logical Self-defense, New York: Idea Press, 2006, p.xiii.因而,当代论证学者一直致力于探求区分论证好坏的全新标准,来革新论证评估的规范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当代论证评估研究形成了三分进路的理论格局:一个好的论证在修辞学进路中意味着“在说服听众时成功取效”,在论辩术进路中指的是“在解决争议时恰当展开的言语行为”,而在逻辑学进路中则是“为结论成立提供了合理依据的命题组合”。但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成熟后,近年来不同进路的理论之间开始产生冲突与争议。同时,对复杂论证实践形态的分析,也使得学者们日渐意识到结合不同研究进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探索恰当的方式来对它们加以整合创新,正成为当前论证评估研究的前沿发展方向。而新近由非形式逻辑学家约翰逊(R. H. Johnson)提出的“论辩充分性”(Dialectical Adequacy)理论,正是在这一方向上极具代表性的一次理论拓展。
一、从充分性标准到论辩性义务
约翰逊是非形式逻辑的创始人和最有力的理论推动者,他提出的以“展示理性”(manifest rationality)为标识的论证理论,是当代非形式逻辑的代表性理论。在其中,约翰逊开创性地建构了一个全新的论证评估理论体系,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突破了逻辑学仅关注“前提—结论间推论关系”的评估维度,进而为论证好坏增加了“论辩充分性”这一规范标准。藉由对该标准的辩护与发展,约翰逊既充分拓展了非形式逻辑研究的理论领域,也给出了一种整合三分进路论证评估理论的特定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约翰逊就和布莱尔一起提出了论证评价的“RSA三角标准”:相关性(Relevance)、充分性(Sufficienc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即,一个好的论证意味着其每个前提都可接受和与结论相关,并且一并为结论提供了充分的支持。①“RSA三角标准”最早出现在R. H. Johnson & J. A. Blair的Logical Self-defense(Toronto: McGraw-Hill Ryerson,1977)一书中。RSA三角标准成功革新了原来的“有效性”标准,开创了非形式逻辑的发展。该理论自提出以来,深受论证学者的认可,并在许多逻辑教科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进而成为了非形式逻辑的标志性理论特征。但显而易见,这三条标准仍然还是针对论证中“前提—结论间推论关系”的规范要求。随后,约翰逊和布莱尔通过进一步将“充分性”标准加以拓展,从而彻底突破了传统的逻辑学论证评估理论进路。
依其之见,论证者在建构论证时还需要“保卫自己的论证”(defending your argument),即还要主动“考虑一个理性的批判者可能针对你的论证和立场所提出的反对意见”。② R. H. Johnson & J. A. Blair, Logical Self-defense, Toronto: McGraw-Hill Ryerson, 1983, p.195.这一论证建构要求的合理性,来自于论证评估的“充分性”标准:“在最弱的要求下,论证者也必须揭示反对意见是不相关的或不妥当的。一个未能对这些反对意见做出回应的论证‘违反了充分性标准’”。同时,“论辩性义务”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充分性标准的这一方面,可以被称作论证者的‘论辩性义务’”,换言之,“论证者有义务针对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为论证的前提或结论做出辩护。”③ J. A. Blair & R. H. Johnson,“Argumentation as Dialectical”,Argumentation, vol.1, no.1, 1987, p.54.由此,充分性标准得到了拓展:“体现在前提中的证据充分性是局部充分性(local sufficiency),但从论证的论辩本性中,还产生出一种全局充分性(global sufficiency)。……如果你的论证要成功地、理性地说服对方,仅仅提供那些使你自己接受结论的理由是不够的。你必须回应那些竞争性的观点,以及那些可能使别人不认同你的理由。你可以论证那些可替立场是有缺陷的,或者它们不如你的立场优越,你需要识别那些重要的反对意见并进而说明他们是错误的。一个未能应对竞争性观点或论辩性议题的论证,没有满足全局充分性的要求。”④ R. H. Johnson & J. A. Blair, Logical Self-defens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4, p.75.
2组患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苏醒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PONV评分、补救镇痛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其次,约翰逊的整合方式也体现着他坚持普遍主义论证规范理想来限制修辞学视角的基本特征,并以对“听众”的拒斥为其基本策略。如前所析,在阐发论辩充分性标准时,最棘手的难题是“指定问题”,即,哪些论辩性素材是论证者有义务在论证中去加以回应的?实际上,对此问题的一种清晰简明、且为其他论证学者所推崇的解答方式,是论证者应当回应其论证对象所实际知晓或真正提及的那些论辩性素材。这一解答方式援引了“听众”来作为论辩性义务的决定因素,因而展现着当代论证研究中修辞学进路的理论取向,即强调和凸显听众在论证分析与评估中的重要角色和功能。由此而言,论辩充分性评估维度同样也为修辞学研究进路预留了理论渗透的空间。然而,约翰逊却清楚地表明,“我不乐意接受任何一种过多依赖于听众概念的解决方式。”在他看来,听众对象始终体现着某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既不可知,也无法被预知,因而并不能得到准确的把握。其次,论辩性素材的价值也并不依赖于听众,“很可能存在着很有价值的反对意见,但它却并不为某些特定的听众所知晓”,② R. H. Johnson, Manifest Rationality: A Pragmatic Theory of Argument, p.333.所以听众并不能为论证评估议题提供规范标准。
2018年调查显示,感到抑郁情绪的医生认为在对待同事时他们会更少地投入工作(42%),更容易被激怒(42%),对周围表达不满(37%),更难表达友善(36%),只有不到22%的医生认为沮丧没有带来这些影响;同时,感到抑郁情绪的医生在对待患者时会更易被激怒(33%),更少投入(32%),导致医疗差错(14%),甚至已经造成差错(5%)。
复位不良4例,1例行开放手术翻修,其余患者延迟下床锻炼时间,术后支具辅助固定6个月,症状均缓解满意,骨折愈合可,短期内无明显相关并发症出现。
综上分析,边坡稳定性影响的主控因素是人类工程活动、降雨,诱发因素为地形条件和地震。以上因素综合作用,促进滑坡的形成、发展与发生。
二、论辩充分性标准
当然,作为针对论辩性外层的评估标准,论辩充分性具体对应何种论证规范要求,这无疑还需要进一步阐明。而且对一个论证而言,显然可能存在许多与之相关的反对意见和可替立场,论证者无疑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要求去对它们都加以回应。因此,约翰逊将对论辩充分性标准的解读更明确地区分为两个问题。首先是“指定问题”(The Specification Problem),即论证者的论辩性义务是什么?换言之,哪些论辩性素材是他有义务从而必须去回应的?其次是“论辩优越性问题”(Dialectical Excellence),即论证者怎样才算是充分回应了论辩性素材?或者说,他成功与适当地履行其论辩性义务,需要满足什么标准?在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约翰逊主要以“反对意见”为分析对象,来探讨和解答这两个问题。
由此来看,早期体现为“全局充分性”的那些要求(在论证建构中对论辩性素材加以回应),其实也并不是论证本身的优劣标准,而是针对论证者而设定的行为规范。换言之,它们更多体现为论辩术进路的评估规范,而不是逻辑学进路的论证标准。可是,约翰逊随后即通过一个革新的二维论证概念,把对反对意见、可替立场的回应内嵌于论证构成当中,而这一做法正是为了使论辩充分性要求真正转变成论证本身的优劣标准。从实质而言,约翰逊是用“论辩性外层”这一概念来巧妙地捕获了动态论辩过程中的理论议题,然后又将它们转化到一个静态的成果性论证概念之中。这一策略使他既为其理论的拓展引入了论辩术视角的全新议题,同时又得以坚守逻辑学研究的成果性论证对象。
可见,无论是全局充分性还是论辩性义务,它们都源自于对论证做“论辩化”解析,体现着当代论证研究的论辩术理论进路。更明确而言,只有将论证分析置于其发生发展的论辩情境当中,才会使得反对意见、可替立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因而,通过在非形式逻辑理论中拓展“论辩充分性”这一评估维度,既成功突破了传统逻辑学论证评估进路的局限,又巧妙实现了对论辩术研究视角的借鉴与整合。
对于论辩优越性问题,约翰逊则提出了“3A”标准来作为其理论解答:适当性(Appropriateness)、准确性(Accuracy)和充分性(Adequacy)。依他所言,“‘准确性’意味着论证者回应的是他人真正持有的观点,而不是对之的某种曲解,也就是说,论证者(在应对论辩性素材时)不应犯稻草人谬误。‘充分性’即论证者做出回应时所用到的论证应当同样满足推论性核心的规范标准”,而“‘适当性’则意味着论证者不能不应对他应当要回应的反对意见。”⑥ R. H. Johnson,“Anticipating Objections as a Way of Coping With Dissensus”,H. V. Hansen et al. (eds.), Dissensus and the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p.14.论证者要适当地履行其论辩性义务,就必须对那些应当回应的反对意见无一遗漏地加以处理,同时,他也需要公正、准确地处理每一个反对意见,并对它们做出恰切的回应。
三、固守逻辑学的论证规范理论整合
从实质而言,“论辩充分性”是通过援引“论辩术”理论视角才得以揭示的论证评估维度。但作为一名非形式逻辑学家,约翰逊却完全采用了逻辑学的理论进路来对之加以阐发,这其中也展现着他整合逻辑学、论辩术和修辞学三分进路的独特方式。
从更实质的层面而言,听众所对应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正是由论证实际展开的具体情境所决定的,因此,修辞学进路中对于听众的重视,也即意味着在论证分析与评估上的实用化和情境化导向。而约翰逊之所以对之加以拒斥,正是因为这一导向与逻辑学进路中对普适性论证规范的追求相冲突。如他所坦言的,“在我看来,非形式逻辑部分地保留着形式逻辑的普遍主义倾向,它试图给出一种普适的论证价值理论。”③ R. H. Johnson,“Making Sense of Informal Logic”,Informal Logic, vol.26, no.3, 2006, p.251.揭示出这一普遍主义的论证规范理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约翰逊始终都致力于以“标准反对意见”来澄清论辩性义务和阐明论辩充分性标准。从他对标准反对意见的阐释来看,尽管最初曾一度包括了“听众想了解的反对意见”,但到最后仍然归结为以“强度”“迫近性”“显要性”来进行界定,这一转变也正是为了使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进而,论辩性义务也即与论证的听众对象失去了实质性关联,“纵使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听众提出反对意见,论证者也需要自己预见与回应反对意见。”① R. H. Johnson, Manifest Rationality: A Pragmatic Theory of Argument, p.171.显然,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约翰逊是逐步地剥离了论证情境中听众的作用的。而这一做法就是为了抵制修辞学进路对论证规范的情境化解读,从而保证其论辩充分性标准始终都具有逻辑学品性。
对于指定问题,约翰逊一度认为“论证者必须回应与其论证相关的‘标准反对意见’(The Standard Objections),此外,他还应当回应那些在标准反对意见以外的,但却是听众想要他回应的,或者他知道如何应对的反对意见。”其中,“标准反对意见”指的是“那些在论题的相关论域中频繁出现的和典型的、具有显著重要性的反对意见”。① R. H. Johnson, Manifest Rationality: A Pragmatic Theory of Argument, p.332.显而易见,这个以标准反对意见为主,以论证者能力和听众期望为辅的义务清单略显庞杂,但是,它却充分体现出论辩性义务中不得不涉及的情境性考虑。正如约翰逊所言,“要理解论辩性义务,我们既需要考虑到论证者的认识能力与局限,又需要考虑到修辞性因素,即听众的期望”。② R. H. Johnson,“More on Arguers and Their Dialectical Obligations”,C. W. Tindale et al. (eds.), Argumentation at the Century's Turn, CD-ROM, Windsor, ON: OSSA, 1999, p.12.然而,在随后几年中,约翰逊结合论证实践的不同阶段,重新为论辩性义务问题给出了更为明确的解答。在他看来,论证实践的过程可划分为“建构论证阶段”与“改进论证阶段”。基于两个阶段的不同特征,论证者具有不尽相同的论辩性义务。总体而言,“在建构论证阶段,论证者应当回应已有的和可以预见到的反对意见;在改进论证阶段,他应当回应实际遇到的反对意见”。但更具体来看,在建构论证阶段,“论证者需要履行的论辩性义务是回应那些标准反对意见”。③ R. H. Johnson,“More on Arguers and Their Dialectical Obligations”,C. W. Tindale et al. (eds.), Argumentation at the Century's Turn, p.6,13.并且,它们可进一步展开为三个特征维度。(1)强度(strength):反对意见越强,越需要对之做出回应。(2)迫近性(proximity):反对意见越接近论证者的立场,越需要对之做出回应。(3)显要性(salience):反对意见在论题的论辩环境中越是突出,越需要对之做出回应。④ R. H. Johnson,“Anticipating Objections as a Way of Coping With Dissensus”,H. V. Hansen et al. (eds.), Dissensus and the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CD-ROM, Windsor, ON: OSSA, 2007, p.13.在改进论证阶段,论证者需要应对的是在论证提出后所实际遭遇到的反对意见。其中,他尤其应当回应那些“严重的反对意见”,也就是那些针对论证中关键前提、背后有论证所支持的强反对意见。⑤ R. H. Johnson,“More on Arguers and Their Dialectical Obligations”,C. W. Tindale et al. (eds.), Argumentation at the Century's Turn, p.10.
首先,“论辩充分性”评估维度的拓展,实际上展现着逻辑学论证研究进路变革发展、回应冲击的一种理论尝试。纵观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现状,日渐强盛的诸种论辩术与修辞学理论,早已将逻辑学论证研究进路冲击得单薄而式微。若历数近年来关于论证研究进路的专门探讨,相比于论辩术与修辞学进路的炙手可热,逻辑学进路几近无人问津,而且,甚至已开始有学者仅以“论辩术”与“修辞学”来作为论证研究的理论基础。当然,造成逻辑学论证研究进路这一理论困境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当代论证研究的兴起是以对形式逻辑论证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为起点的,这本身即是对逻辑学进路合法性的巨大冲击。甚至可以说,正是逻辑学作为唯一合法论证理论的地位被动摇,才开启了众多当代论证理论的新生,而它们都力图回避、替代或超越逻辑学的研究进路。另一方面,当代论证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革是以现实情境中的论证为对象,注重论证分析的语用和实践维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论辩术和修辞学论证研究进路的理论优势。简言之,逻辑学进路历来注重从语境中抽离出成果性论证来加以分析,但论辩术和修辞学进路则更关心在具体情境中对论证行为和互动加以探讨,这无疑也注定了它们更能与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相契合,也能为之提供更好的理论视角和拓展方向。
随后,以“论辩性义务”概念为基础,约翰逊进一步构建了其完整的论证理论体系。其中,鉴于论证建构中所要求的不只是提供支持理由,约翰逊提出了一个革新性的二维特质论证概念:论证既包括一个“推论性内核”,同时还具有一个“论辩性外层”(dialectical tier),论证者在前者中提供理由来支持论题,而在后者中履行相关的论辩性义务。如回应已有或可能的针对论题的反对意见,以及批驳关于论题的可替立场。⑤ R. H. Johnson, Manifest Rationality: A Pragmatic Theory of Argument,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0, p.168.相应地,他也发展出一个更为全面的论证评估规范体系,其中既包括评估推论性内核的“推论充分性”要求,也包括评估论辩性外层的“论辩充分性”标准。由此,“全局充分性”也正式转变为“论辩充分性”标准,成为了论证评估中的一个全新维度。
首先,这一整合方式体现出约翰逊固守逻辑学进路来归并论辩术视角的根本思路,并以坚持“成果性论证”对象为其基本策略。事实上,在当代论证理论中,论辩术进路以“论证的论辩化解读”为特征,将论证看做“一种言语行为间的论辩性互动”。这一研究视角会带来两个理论导向:一是论证本身在更广的交际语境中被“言语行为化”,二是论证的优劣评判将依赖于整个论辩互动的总体目标。进而,论辩术进路的评估理论将关注整个论辩进程的整体目的与互动规范,探讨协调论证参与者合理行为的程序规则。但与之不同,逻辑学进路一直以来都以一种已经完成的成果性论证作为研究对象,而不关注一个互动展开的论证过程。正是受此理论传统的影响,约翰逊不断坚持“我的论证理论的建构明确地以书写的论证(written argument),即成果性论证为关注重心。”论辩术进路的两个理论导向在他看来都不可接受,因为逻辑学论证研究不是“为理性对话中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做出规定”,而是“为论证本身的评估提供标准”,其论证评估理论关注的也应当是“一个论证是否依其自身是一个好论证(a good one in itself),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好论证(a good one simpliciter),或者是一个客观上好的论证。”① R. H. Johnson, Manifest Rationality: A Pragmatic Theory of Argument, p.319, 291, 194.
四、逻辑学论证研究的革新与困境
可见,约翰逊所提出和发展的“论辩充分性”标准是一种逻辑学进路的论证评估理论,其中,他接纳和归并了论辩术进路的洞见,却疏远和限制了修辞学进路的渗透。这一理论拓展既开启了当前论证评估研究的一个新维度,也引发了论证学界持续的理论反思和争议。然而,只有在更广的当代论证理论论域当中,我们才能对之做出一个深入而恰切的评析。
边坡工程按持久工况(天然工况)和短暂工况(暴雨工况)两种工况利用理正软件进行计算设计。本次稳定计算及边坡设计安全系数具体取值为表2。
一直以来,作为当代论证研究中逻辑学进路的代表,非形式逻辑既需要对饱受批评的形式逻辑论证理论加以反思和变革,也需要在当代论证领域中坚守和拓展逻辑学品性的论证研究。早期非形式逻辑学者以RSA三角标准为标志的评估规范革新,成功地实现了对于形式逻辑论证理论的变革和超越。但在面对论辩术与修辞学进路的强势发展和冲击时,他们也不得不主动迎合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方向。这既需要通过借鉴与整合其他进路的洞见来突破自身传统的理论界限,又需要敏锐而审慎地保持其逻辑学论证研究的理论特质。由此,我们可更准确地解读论辩充分性评估理论的特定价值。显然,约翰逊看到了论辩术进路能为非形式逻辑带来实质性拓展,因而主动借鉴了其理论视角来揭示论辩性素材、论辩性义务等新内容,并拓展出论辩充分性评估的新维度。随后,他又借助一个二维特质的论证概念,来坚守逻辑学研究的成果性论证对象,进而将这些新的理论拓展都化归为逻辑学领域中的研究议题。约翰逊也看到了修辞学进路的渗透会为非形式逻辑带来难以调和的理论危机,因而选择不从听众的角度来阐发论辩充分性标准,以避免对其作情境化的解读,并由此来确保其逻辑学论证规范的理论品性。可以说,论辩充分性评估理论的拓展就是非形式逻辑在三分进路中借鉴发展、革新突围的一次理论尝试。
其次,“论辩充分性”评估维度的拓展,也明确揭示出逻辑学论证研究进路的理论局限,以及它由此而陷入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纠葛困境。事实上,只有当论证被放回实际论辩语境中去考察时,才会彰显出论辩性素材的合法性以及对它们加以应对的重要性。然而,约翰逊却采取“论辩性外层”的方式,来将这些实践情境中的动态素材硬性固化于论证概念之中,使它们上升为论证对象的构成性要求。同时,从最初对应于充分性标准的“论辩性义务”要求,到最终发展完善的“论辩充分性”维度,约翰逊也从一开始就把应对论辩性素材的重要性上升为了论证规范层面的必须性。他继而以标准反对意见来阐发这一规范维度,其目的也在于追求某种客观性和普适性。如前所析,坚持静态的成果性论证、普遍主义的论证规范理论,是约翰逊固守逻辑学论证研究进路的基本策略,而它们所体现的也正是逻辑学一直以来的学科特性:是关于论证本身好坏的规范性研究,而不是关于实际论证行为的描述性研究。显而易见,逻辑学研究的这一理论导向也意味着它需要脱离对实践情境的依赖,力图建构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论证理论。但是,论辩性素材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都根源于具体的论辩实践情境,它们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求着、甚至只能够以情境化的方式来加以解析和探讨。由此,这种一般性理论与情境性实践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也注定将为论辩充分性理论带来诸多的争议和批评。
隔一年,我和妻子离婚了。妻子不愿意离婚,法官不愿意判决。我和妻子先后去法院纠缠半年多时间。我恳求法官看一下妻子膝盖和胳膊肘上的刀疤与鳞屑。我说,我担心哪一天妻子的刀片会划在我的脖子上。妻子坚持说,我这是刺血治疗皮肤病,我的心理没问题。我说,你的心理没问题,我的心理有问题,我跟你过日子早已失去了安全感。
一方面,对于论辩充分性的阐释,同样可选择完全依赖于论辩实践的情境化理论方向。如同语用论辩术学者的看法,“论证者所需应对的只是他想要说服的对手所知道和提出的反对意见”,因而对于论辩性义务的复杂探讨似乎并无必要,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真正基于论证实践。”① M. A. van Rees,“Book Review on Manifest Rationality”,Argumentation, vol.15, no.2, 2001, p.234.另一方面,纵使充分承认在论证实践中应对论辩性素材的重要性,也并不必然能导出在理论建构中相应的义务与职责要求。阿德勒(J. Adler)就曾指出,论辩性义务的要求“太过苛求,满足它所必需的时间与智识上的消耗将使之变得难以施行。而且,履行它而付出的努力也将减损论证实践与探究活动本身的生命力。”② J. E. Adler,“Shedding Dialectical Tiers: A Social-Epistemic View”,Argumentation, vol.18, no.3, 2004, p.284.确实,约翰逊也承认,通常只有哲学家才会在其论证建构中主动回应标准反对意见等论辩性素材,而这并不是实际生活中论证的常态。有鉴于此,费诺切罗(M. Finocchiaro)就曾建议以相对较弱的“论辩性美德”(dialectical virtue)来替代约翰逊的论辩性义务要求,以使之不要上升到论证理论的规范性维度。③ M. Finocchiaro,“Commentary on Johnson’s Anticipating Objections as a Way of Coping With Dissensus”,H. V.Hansen et al. (eds.),Dissensus and the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pp.1-6.
进而,在一般性理论与情境性实践之间如何才能恰当均衡的问题,也将约翰逊及其论辩充分性理论推到了一个令人纠结的理论困境。他既需要向情境性要求做出适当妥协,却又始终不乐意放弃其一般性理想。正如他所坦言,“近年来我在论辩性议题上被以美德为基础和以义务为基础的两条进路所拉扯。我现在倾向于认为同时存在论辩性义务与论辩性美德,尽管至今为止它们都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④ R. H. Johnson,“Response to Maurice Finocchiaro’s Commentary”,H. V. Hansen et al. (eds.), Dissensus and the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p.3.同时,他也开始做出让步,“可能我需要调整我的理论……不再将(论辩性义务的)问题理解为哪些反对意见是论证者必须回应的,而是将之理解成哪些挑战是他选择要去回应的,以及哪些挑战是他有兴趣从而愿意去回应的”,因此,“论证者对于所需回应的素材的选择,也可以合法地依赖于自己的兴趣”,换言之,“关于论辩充分性的原则将需要同时关注义务与兴趣。”⑤ R. H. Johnson,“The Dialectical Tier Revisited”,Frans H. van Eemeren et al. (eds.), Anyone Who Has a View: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Dorc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50.从实质而言,关于论辩充分性理论的争议,呈现的也正是当代论证理论中逻辑学进路在变革拓展中所面对的难题:那些在真实论证实践的描述性研究中所呈现的情境性素材,到底如何能够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转换为逻辑学规范性研究中的理论议题,并进而导向某个具有普适性、一般性的论证理论?与此相应,近年来约翰逊所做出的这种折中与妥协,或许也昭示着逻辑学论证研究在未来发展中不得不采取的理论态度。
“论辩充分性”理论标识了当前非形式逻辑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也开启了当代论证评估研究的一个全新维度。通过借鉴论辩术的理论视角,约翰逊将非形式逻辑的理论论域进行了实质拓展,同时也成功突破了传统逻辑学的论证评估维度。论辩充分性理论展现了约翰逊固守逻辑学、归并论辩术和限制修辞学的特定理论整合方式。其中,他既着力坚持逻辑学的成果性论证研究对象,又试图维系其普遍主义的论证规范理想。而从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一整合方式代表着逻辑学论证研究进路革新发展的重要方向,但同时也展示出其理论建构目标与论证实践情境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因此,通过充分关注和探讨论辩充分性理论的发展和争议,我们也能够恰当地审视当代论证研究的前沿动向。
〔中图分类号〕B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9)03-0032-0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义论证理论研究”(16JJD720017)、2016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耘,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广东 广州,510275)。
责任编辑:罗 苹
标签:进路论文; 理论论文; 约翰逊论文; 逻辑学论文; 形式逻辑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逻辑学(论理学)论文; 形式逻辑(名学论文; 辩学)论文; 《学术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义论证理论研究”(16JJD720017)2016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中山大学哲学系论文; 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