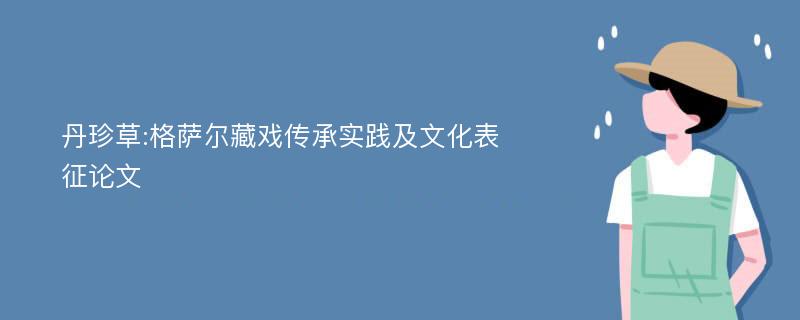
[摘要]格萨尔藏戏将口头诗歌中的“歌”化为具体的表演行为动态实践,集声音、舞蹈、仪式和群体互动等多种形式于一体,是历史悠久、别具特色的藏戏剧种。格萨尔藏戏表演通过对古典时代民族民间文化的重构与想象,构成格萨尔史诗更丰富宽广的表达。作为文化象征的表述符号,格萨尔藏戏是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表演民族志,其歌舞形态为本的言说系统,更贴近格萨尔史诗说唱本体,并重新廓清格萨尔史诗口传与书写之间复杂的关联,还口头说唱以本原。格萨尔史诗戏剧化表演实践与创新中的复合性、融合性、新生性特征和带有实验性的探索,使格萨尔藏戏经历新的蜕变。
[关键词]藏戏说唱 ;格萨尔藏戏;传承实践;文化表征
格萨尔藏戏是在传统藏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演唱格萨尔史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艺术,其唱腔、舞蹈、面具、服饰等戏剧元素与传统藏戏一脉相承。格萨尔藏戏因表演形式、风格、场地、道具等的不同而分为寺院格萨尔藏戏、舞台格萨尔藏戏、马背格萨尔藏戏、广场格萨尔藏戏、傩面格萨尔剧、现代格萨尔歌舞剧等。早期格萨尔藏戏只在宁玛派寺院和民间个别地区演出,内容主要以雄狮大王格萨尔的戎马生涯和征战传奇为主。作为藏族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传承过程中,格萨尔藏戏既保持了传统藏戏艺术风格,又不断受到其他民族戏曲艺术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为藏族地方特色浓郁、流传较广的民间文艺戏剧形式。
格萨尔藏戏以舞蹈、面具、唱腔、服饰等“身体表述实践”为核心,展开动态的文化演述,传达民族历史、集体记忆和文化意象,强调在特定的地域和文化范畴、语境中理解“表演”,在行为动态中将文本与语境重新结合起来,表现出程式化、神圣性、世俗性相互交织的特征,内部却蕴藏着各种微妙繁富的文化信息和生命镜像,同时具有口语诗学的回归意义。格萨尔藏戏之于民俗文化新生与重构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帮助那些沉浸在书写和文本中的学者们,使他们通过对民族和文化的宽阔谱系形成总体性认识,进而领会和欣赏其间诸多非书面样式的结构、原创力和艺术手法,重新发现那最纵深也是最持久的人类表达之根”。[1]
人两眼重合视域为124°,越接近人眼极限视域角度越会带来更强的观影体验感,所以很多消费者喜欢去影院观影,而近年VR、AR技术的兴盛也正是因为其视野的大幅提升,而带来更深的代入感。随着大屏化趋势,电视产品的观影距离不断提升,以及电视产品尺寸的增加,大屏彩电已经能够基本达到“影院”级观影效果。
顶层设计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某项任务或者某个项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
一、藏区说唱传承与藏戏
说唱在藏区的绵延传续和不断丰富,对藏戏以及格萨尔藏戏的产生、发展与完善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早在苯教时期,王宫里的“仲”(grung)(说唱神话)就非常兴盛,已有职业从事说唱的故事师和说唱家。民间说唱也十分流行,有“白”(勇士出征歌)、“夏”(对歌)、“仲鲁”(故事歌)和“岭仲”(格萨尔说唱)、道歌说唱、“堆巴协巴”(祝福赞词)等。这些说唱,从内容到形式,对后来藏戏的唱腔以及格萨尔藏戏产生了直接影响。据文献记载,“摇鼓做声”的巫舞和载歌载舞的“鲁”,在囊日松赞时代就已经流行开来。《西藏王统记》记载,松赞干布颁发《十善法典》庆典会上,“令戴面具,歌舞跳跃,或饰嫠牛,或狮或虎,鼓舞曼舞,依次献技。奏大天鼓,弹奏琵琶,还击铙钹、管弦诸乐……如意美妙,十六少女,装饰巧丽,持诸鲜花,酣歌曼舞,尽情欢娱……驰马竞赛……至上法鼓,竭力密敲……”[2]藏史文献《巴协》中记载,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修建桑耶寺时,为调伏魔道,莲花生大师在所行仪轨中跳的舞蹈就是寺院“多吉嘎羌姆”(金刚舞,简称羌姆)的起源。羌姆是原始苯教巫师以祭祀仪式为基础,结合民间的土风舞演变而来的宗教舞蹈。开始,羌姆只在寺院里由僧人表演,后来传入民间,僧俗人众,均可观看,是具有一定娱乐性的宗教舞蹈。桑吉嘉措的藏医著作《亚色》记载,桑耶寺竣工,人们欢庆寺院落成,载歌载舞,跳“阿卓”(鼓舞),唱“鲁(歌)”,表演“鲜”(哑剧舞蹈)。西藏乃东县哈鲁岗村现今依然保留着“阿卓”鼓舞的娱乐形式,领舞师所戴面具与藏戏山羊皮面具基本相同。民间早期的热巴舞也为后来的藏戏奠定了基础,如藏戏开场演出的猎人舞与热巴舞中的猎人动作完全一致。民间的山歌、牧歌、劳动歌、弦子、箭歌、酒歌、对歌、情歌等皆成为藏戏唱腔和格萨尔藏戏的源泉之一,如“达仁”(长调)和“达通”(短调)都已融入藏戏曲调。
佐钦寺一直以来被称为格萨尔羌姆(格萨尔藏戏)的发祥地。该寺地处四川甘孜州德格县,是宁玛派寺院,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笔者曾两次到佐钦寺调研。佐钦寺的格萨尔藏戏由该寺第五世转世活佛白玛仁真土登·曲吉多吉初创。白玛仁真土登·曲吉多吉曾撰写格萨尔史诗中的《分配大食财宝》《雪山水晶宗》。佐钦寺格萨尔藏戏既与宗教仪轨相协,又与悬挂风马旗、赛马、招福、烟祭等各种民俗活动相表里,表现出神圣性、世俗性的相互交融。各寺院表演的格萨尔藏戏,在服装和道具上有一定的区别。大多数寺院表演格萨尔藏戏时,演员都戴面具;有些寺院,演员却不戴面具,而是以服装和演员的佩饰区分角色。佐钦寺的格萨尔藏戏,所有角色,都由男性喇嘛饰演。演员的角色人选,主要看表演技能,不分高低贵贱。格萨尔王一般由演技最好的青年僧人扮演。佐钦寺格萨尔藏戏的面具最为齐全,该寺现存的八十多具格萨尔藏戏面具,神态各异,独具匠心,有很高的权威性。演员阵容也十分强大,达一百八十多名。传说,格萨尔藏戏面具是土登·曲吉多吉活佛在梦中得到格萨尔大王的亲临指教而创制的,因此,佐钦寺格萨尔藏戏面具成为藏区其他寺院格萨尔藏戏面具制作的经典样式。《赛马称王》是佐钦寺最为精彩的传统保留节目,融舞蹈、对歌、说唱于一体。全剧由七个部分组成,格萨尔王的出场亮相最为出彩,威风凛凛,气势不凡。主要情节是演述格萨尔王与母亲郭姆一起经历艰难困苦,顽强不屈,一往无前的精神,以及格萨尔对待爱情的真挚热烈,面对超同的阴险、巫咒、迫害如何足智多谋等。这些故事已经成为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
据笔者调查,德格现有的14座寺院,每年都在固定时间展演格萨尔藏戏。除了格鲁派寺院,宁玛派、萨迦派和噶举派寺院都有格萨尔藏戏演出,《赛马称王》《岭国三十员大将》《霍岭大战》《岭·格萨尔王、王妃珠姆和十三威尔玛战神》《岭国统帅格萨尔、七大勇士、十三位王妃》是主要表演剧目。佐钦寺格萨尔藏戏传承有序,百年不衰,演出面具种类繁多,有雄狮、鱼、猴、蛇、雕、老鹰、大乌鸦、虎、狼、仙鹤、马等各种动物面具,制作生动有趣。佐钦寺每年举行金刚橛修供大法会,法会最后一天、藏历新年或者每年五六月份,寺院藏戏团必定会为僧俗民众表演格萨尔藏戏。史诗中的英雄群体,他们独特的生命情态、内在的精神品质,以及性情各异的个性气质,在戏剧表演中被反复演述,向观众展示着具有唤醒性的生活情境,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审美补偿体验。
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错对藏戏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清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率众三千进京,期间,看到汉族、蒙古族、满族等不同民族的舞蹈、戏剧、杂技、音乐等艺术表演,很受启发。返藏后,即对从拉达克传入的具有西域风情的歌舞进行了改编,组织成立了由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的专业歌舞队——江噶尔巴,同时邀集一些享有盛名的民间藏戏班子进入哲蚌寺演出,并因此开创了在哲蚌寺表演和观摩藏戏的惯例。“寺院羌姆”与宗教仪式开始逐渐剥离,藏戏成为独立的戏剧形式,并允许民间艺人公开演出,半职业化的藏戏戏班在民间广泛出现,职业藏戏剧团开始正式演出,从此,唱、诵、舞、演浑然一体的戏曲表演程式基本形成。藏戏原系广场剧,只有一鼓一钹伴奏,并无其他乐器。藏戏唱腔高亢雄浑,因人定曲,每句唱腔都有和声帮腔。藏戏演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顿”,开场表演祭神歌舞;第二阶段为“雄”,表演正戏;第三阶段为“扎西”,即尾声,意为祝福和迎接祥瑞。藏戏的传统剧目有“十三大本”之说,如《日琼娃》《云乘王子》《敬巴钦保》《德巴登巴》《绥白旺曲》等。传统藏戏的服装,从开场到结尾,只有一套,演员并不化妆,主要是戴面具,特别是戴蓝面具表演。 20世纪,藏戏出现了水准较高的戏曲文学剧本和一批优秀的传统剧目,著名的“八大藏戏”②正式形成,藏戏趋于完善。2006年藏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美国民俗学家鲍曼将“表演”在本质上理解和界定为一种交流的方式,一种言说。毫无疑问,藏戏也是藏区民间文化精神的一种“言说”。由于西藏及四省藏区自然条件、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方言语音的不同,藏戏的剧种因而十分丰富,出现了不同的艺术种类和流派,如白面具戏、蓝面具戏等。仅就蓝面具戏而言,在传承过程中,因地域不同,形成了觉木隆藏戏、迥巴藏戏、香巴藏戏、江嘎尔藏戏四大流派。卫藏藏戏作为藏戏的艺术母体,经朝圣的僧侣、民众远播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藏语地区,形成了四川德格藏戏、色达藏戏、嘉绒藏戏、昌都藏戏,以及青海黄南藏戏、华热藏戏、果洛藏戏,甘肃甘南的“南木特”藏戏等分支。印度、不丹等国的藏戏亦随藏族聚居地的迁移而如影相随,传承至今。
二、格萨尔藏戏传承实践
格萨尔藏戏将口头诗歌中的“歌”化为具体的行为动态实践,集声音、舞蹈、仪式和群体互动等多种形式于一体,成为历史悠久、别具特色的藏戏剧种。在格萨尔藏戏中,史诗已从单纯的艺人说唱、文本阅读延伸到以史诗为题材的多样性戏剧化表演,“以文本为中心”已逐渐走向“以表演为中心”的回归。如鲍曼所言,“表演”除了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性的言说方式,有时还包括了更广泛的“文化表演”,还可以理解为对口传史诗诗性功能的展演。在史诗流布的不同地域,格萨尔藏戏的传承实践,具有不同的语言文化表征和“地方性知识”特征,已然是基于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一种动态的民俗生活事项和文化表述。格萨尔藏戏主要有佐钦寺格萨尔羌姆、果洛马背格萨尔藏戏、甘南“南木特”格萨尔藏戏、色达格萨尔藏戏,以及现当代语境下的格萨尔歌舞剧等。
(一)佐钦寺格萨尔藏戏
传统的“折嘎”说唱,是藏区民间最古老的说唱曲调之一。“折”,意为米、果实;“嘎”,意为洁白。每逢藏历新年或喜庆欢乐的场合,民间都会有折嘎艺人的演唱。演唱折嘎,有送吉祥、转好运之意。折嘎分为说、唱两部分。先说后唱,并穿插一些简单的形体动作。说唱者身着白色氆氇袍,肩搭白面具,项挂白哈达,手持白色木棍。折嘎艺人说唱,不仅要吐字清楚、口齿伶俐,而且唱词要根据时间、地点、观众的不同即兴发挥。这一说唱形式至今依然广泛流传于藏区。
在雨季来临之际,突降暴雨或阴雨持续不停的情况下,居民对内涝的发生是否有心理准备对防灾减灾也很重要。在接受访谈的人群中,有62%的居民表示没有心理准备,仅有38%的居民由于经历过多次的内涝灾害,一旦有类似降雨情况出现便有很强的心理暗示,因而会相应地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比如时刻关注天气情况,关掉电器,叮嘱亲朋好友出门时做安全防护等。对于大的内涝灾难来临时,70%的居民第一反应是先跑到高处,保护生命,但仍有30%的居民认为内涝灾害不会伤及生命,最重要的是抢救贵重物品,然后再躲避到安全区域。可见,大多数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能够做到爱护生命,但仍有少数居民缺乏自保意识。
“格萨尔达羌姆”,意为“格萨尔马背藏戏”,是在马背上表演格萨尔史诗的藏戏。果洛格萨尔藏戏,最具地方性特质的是马背藏戏和广场藏戏。从古至今,马与藏族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紧密相联。果洛牧区广阔的草原和自然地理空间,非常适合马背藏戏演出。果洛被认为是格萨尔赛马称王崛起之地,是果洛民众特定地域、特定族群的集体记忆。这里的人们深信,果洛的土地就是岭国的遗址,果洛的每一顶帐篷里,都有格萨尔的故事在传唱。据调查,果洛格萨尔藏戏最早始于甘德县夏仓地区。史诗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其在当代语境下有了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在果洛,格萨尔藏戏的演出非常活跃,有传统格萨尔藏戏、马背格萨尔藏戏、广场格萨尔剧、傩面格萨尔剧和现代格萨尔舞台剧等。果洛马背格萨尔藏戏于2008年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甘德县夏仓格萨尔马背藏戏团”的瓦泰·普尔多成为马背格萨尔藏戏的国家级传承人。
“喇嘛玛尼”和“折嘎”说唱一样,也是一种流行于藏区民间的说唱曲调。“喇嘛玛尼”,“喇嘛”,意为僧人,“玛尼”,意为念经。但作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喇嘛玛尼,并非念经,而是佛教诵经曲调中的一种玛尼调式。艺人演唱时,挂一幅绘有故事内容的唐卡,一边指着画面,一边讲唱故事。“喇嘛玛尼”有许多固定的调子,在说唱开始、中间、结尾处,会时不时插诵“六字真言”,说唱内容往往是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说唱最多的历史故事有《朗萨雯波》《文成公主》《洛桑王子》《嘎玛旺宗还魂记》等等。王尧先生在《西藏文史考信集》中记录他的所见:“提到西藏一种说唱形式的表演艺术——‘喇嘛玛尼’。这种演员用比较简单的道具,挂上一幅唐卡,用一根木棒指着画上的人物,一边讲说,一边歌咏,表演其中的故事。艺人唱到动人之处,声泪俱下,听众也跟着唏嘘不止,得到很好的共情反馈。这种艺术形式对藏戏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至少也可以看出藏戏演员的‘说唱’基本功训练,从‘喇嘛玛尼’得到帮助和启发。”[3]在西藏,说唱喇嘛玛尼的民间艺人被称之为“喇嘛玛尼哇”“嘛尼巴”或“洛钦巴”(即善说者)。关于喇嘛玛尼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吐蕃时期,唐朝皇帝派高僧到西藏传播佛教,用变文或者变相的形式演唱佛经故事,这种说唱形式被传承了下来。一种认为是噶举派高僧、藏戏创始人唐东杰布所创。据《唐东杰布传》记载,噶举派高僧唐东杰布主持修建西藏铁桥的过程中,发现了七个能歌善舞的姐妹,七姐妹天生丽质,舞姿优美,歌声动听。为了募集资金修桥,唐东杰布在白面具戏的基础上,吸收佛经故事和民间传说中带有戏剧因素的内容编排节目表演,并设计唱腔、动作和鼓钹伴奏,指导七姐妹演出。①“喇嘛玛尼”说唱的故事脚本,对藏戏的影响非同寻常。
(二)果洛“格萨尔达羌姆”
“岭卓”是迄今发现的记载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格萨尔舞蹈。“岭卓”,即“岭卓极乐金刚乐曲舞”(格萨尔舞蹈),民间称其开创者为康区宁玛派高僧居·米旁嘉措大师。“岭卓”将偈颂唱词和民间舞相结合,是寺院和民间均可表演的大众化舞蹈。“岭卓”演员一般为十六男十六女或八男八女,舞蹈动作和唱腔均可改变,但舞蹈的结构程序和唱词须遵循原创的排演。“岭卓”共有四个舞段。第一段迎请舞,第二段礼赞舞,第三段征战舞,第四段妙音舞。“岭卓”的表演程式几乎与藏戏相同,每段均有较长的唱诵和舞蹈,表演时边唱边跳,动作都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段与段之间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表演岭卓舞,首先讲究其完整性,四个舞段的创作主题、意境设计和精神引导,皆围绕岭·格萨尔王、三十员大将、诸战神护法以及众王妃展开,将肢体行为语言内化为优美的史诗意境,诠释深藏在舞蹈背后的史诗文化语境,充满象征、隐喻、欢乐、吉祥。表演者与观众彼此呼应,心领神会,于欣赏中获得感悟和愉悦。
“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作力。”[7]同样,格萨尔藏戏的传承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情境中,处于不断创新和重构的动态过程中。今天的藏区,民间文化生活已变得丰富而多元,呈现出强大的扩容状态,民间日常生活选择已经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多变性和现代性。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用一种或两种形式来传承英雄史诗。在族群和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中,格萨尔史诗已成为文化生活的活态样本。在现代性进程中,格萨尔藏戏传承表演实践也进入了“新时代”,表现出丰富复杂的多元化取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消融性和包容性。人们“逐渐对旧习俗的溃决习以为常;努力抗争以把新事物整合进来,调整以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8]
马背格萨尔藏戏,表演者多为寺院僧人。表演分两种形式:仪式性表演和戏剧性表演。仪式性表演要举行隆重的格萨尔煨桑仪式,三十员大将、王妃等飞身上马,手持兵器或风马旗,英姿勃发,围绕烟祭台,口诵祭词,祈祷世界和平,人间安乐,众生吉祥。果洛甘德县龙什加寺的“马背格萨尔藏戏”非常注重展示格萨尔史诗所谓“原汁原味”的场景,可谓独树一帜。风驰电掣的马队,雄浑有力的马蹄声,明快嘹亮的鼓乐声,呈现出旌旗猎猎、樯橹灰飞烟灭的格萨尔古战场。这样的情境性表演,充分表现出戏曲艺术最古朴的原初形态,保留着民间艺术真实稚朴的风格。祭祀仪式、乐器伴奏、特定角色、民歌曲调、歌之舞之……几乎包含了藏族戏剧艺术早期的所有元素。果洛格萨尔藏戏《英雄诞生》《赛马称王》《十三轶事》《霍岭大战》《天岭卜筮》等剧目,多是由寺院的高僧上师依据书面文本的《格萨尔故事》《格萨尔王传》等进行节选创编。戏中角色都由寺院僧人饰演,扮相漂亮的年轻喇嘛会扮演剧中的女性角色。
“格萨尔达羌姆”往往在开阔的草地上演出。一般会根据格萨尔史诗的叙事设置多个剧情演出场地。在旷野上搭几顶漂亮的帐篷作为岭国营地或魔国营地,帐篷内表演的多为史诗开篇“天界授记”,或者部署作战计划等戏分。史诗情节的展开过程,如行军、作战都在马背上表演,跨马骑战是马背格萨尔藏戏的重头戏,双方勇士、大将手持兵器冲出营区,在马背上表演各种难度系数较强的技术性动作。表演首先会以传统的程式化说唱方式对话、论辩。舌战后,双方才兵戎相见。马背格萨尔藏戏每年在果洛民间演出,除了重要的节日法会期间演出外,藏历六月四日,即世界公桑日,祭奉神山如阿尼玛沁雪山、年宝玉则、玛域上部十三岳、玛域下部九神山等,活动期间,各个寺院都会就近诵念祈愿经、煨桑,然后举行格萨尔藏戏表演,悦神山,娱民众。草原上,骏马长鬃飞扬,四蹄翻腾,人声鼎沸,桑烟缭绕,非常壮观。这种古老传统的当代传承和马背藏戏已日趋成熟完整,宏大史诗已被微观化处理,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民俗文化新生事项。
甘南藏戏“史诗剧”《阿达拉姆》为最受欢迎的剧目。《阿达拉姆》依据格萨尔史诗中《地狱救妻》一章创编而成,以格萨尔王勇入地狱、智救王妃阿达拉姆的故事为线索,演述了阿达拉姆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将驰骋疆场、战功赫赫的传奇经历和身世故事,以及阿达拉姆与格萨尔王的战地浪漫爱情。《地狱救妻》将格萨尔王的英勇无畏以及18层地狱的阴森恐怖、善恶报应、因果轮回作为主题。《北方降魔》将神话、历史、现实融于一体。主人公格萨尔王出击北方,拯救被掳王妃梅萨,与魔王斗智斗勇,刀光剑影,终于战胜邪道魔王鲁赞,救得梅萨王妃。这部戏的很多场景、情节、唱词,对传统藏戏都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甘南格萨尔藏戏非常重视刻画戏剧人物性格,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取象非常广泛,除了形象地表现史诗众多人物的形象和各色神态,还有很多神祇鬼灵形象,以及对各种飞禽走兽形态的模仿。剧中,格萨尔王雄才大略,气贯长虹,既有神性的无所不能的,又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格萨尔与王妃珠姆、梅萨之间爱恨嗔妒缠绵悱恻的情绪交织、情感纠葛,通过唱词、唱腔、韵白表达得十分精彩,具有明显的甘南格萨尔藏戏特征,独具魅力,自成一家。
选取2018年1月~2018年7月我军队医院老干部科收治的老年糖尿病的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均符合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参照组,各40例。其中,参照组男22例,女18例,平均年龄(53.21±2.17)岁,平均病程(7.1±2.2)年;观察组男23例,女17例,平均年龄(52.39±2.21)岁,平均病程(7.3±2.2)年。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三)甘南“南木特”格萨尔藏戏③
“南木特”,意为“传记”。“南木特”藏戏诞生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与甘南拉卜楞寺嘉木样五世活佛丹贝坚赞有关。上师21岁时赴拉萨学法讲经,多次观看藏戏。三年后返回拉卜楞寺,向朗仓活佛讲述西藏藏戏。朗仓活佛学识渊博,曾在北京居住近20年,常与京剧大师梅兰芳交往,熟悉了京剧。经过汉藏融合创新,甘南藏戏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征。除了传统的八大藏戏剧目外,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以甘南藏区民间口头流传的格萨尔故事为内容的具有甘南藏区本土化特色的“史诗剧”。甘南藏戏首次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格萨尔史诗列入藏戏剧目。《罗摩衍那》是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部分叙事篇章改编的藏戏。格萨尔史诗中的《阿达拉姆》《霍岭大战》《北方降魔》等藏戏由夏河县拉卜楞红教寺院(宁玛派)演出。1986年甘南格萨尔藏戏《北方降魔》参加了拉萨“雪顿”藏戏艺术节,因演出别具一格,故事生动,大受欢迎。甘南格萨尔藏戏,重视将历史与神话融为一体,以甘南、青海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安多方言演出,地方性说唱特征非常突出。
“格萨尔广场藏戏”,舞台虽然设立于空旷广场,但并不以草地雪山为背景,也没有骏马利刃做铺陈,而是具有“虚拟性”戏剧表演特征,全凭演员个人演技的展示,进行虚拟、幽默、夸张的形态表演。这种虚拟化的舞台表演与内地京戏表演十分类似。如《赛马称王》,舞台上的道具,只有一条长凳,这条唯一的长凳也是少年格萨尔赛马称王后的象征性宝座。表演骑马作战的大场景戏,主要靠演员的平日素养与精湛技艺。演员虚拟的骑马征战表演,已成为格萨尔藏戏的程式化动作。格萨尔广场藏戏的“舞、做”表演,本就来源于现实生活,“舞、做”与曲词、唱腔相配合,优美和谐,表演风格既豪放又典雅。格萨尔广场藏戏表演,演员一般不戴面具,而是根据角色需要在演员面部用色彩一笔笔勾描,一点点勾画,形似京剧脸谱。果洛当地有24家格萨尔藏戏民间表演艺术团,他们的格萨尔藏戏表演,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区文化事项,寄寓着民众情感生活的欢乐和悲伤,引导着民众对民族历史文化诸多意义系统的追忆和理解。
甘南格萨尔藏戏是舞台剧而非广场剧,是最早普遍运用布景、道具、服饰、灯光的藏戏。布景的使用和转换,既说明了剧情的发展,又交代了人物活动场所的转换,环境的变化。其次,甘南格萨尔藏戏的剧本、剧目、表演、伴奏甚至演出场地,与其他地方性藏戏迥然不同。甘南藏戏中的神怪角色都要戴面具,其他角色不戴面具。演员的造型、服装、头饰十分讲究,道具也新颖别致,与西藏藏戏差别很大,但与传统藏戏的表演程式并无不同。甘南藏戏的三个部分:开场,正戏,结尾。正戏部分一贯到底,剧情连贯。戏中专设一名“解说人”或“旁白者”,以吟诵形式解释剧情,说明前因后果,穿针引线,引人入胜。“演员上场前,有乐器伴奏,比如会有札木聂、牛角胡、骨笛、胡琴、海螺等烘托气氛。演员出场后,进入剧情,伴奏逐渐消失,由演员随着剧情的推进发展变化,注重如何细腻地表达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节奏。甘南格萨尔藏戏,属于格萨尔史诗说唱的原本体形式,皆采用‘连珠韵白’加诵唱……韵白通常是从念诵佛经的声调借鉴而来,连珠式的歌词,并不押韵,散文与偈语句共用,祝词、赞词以及民间唱词、道白速度非常快,妙趣横生。演唱或道白抑扬顿挫、妙语连珠。有些剧目还有念诵加‘拜歌日’的说唱形式,语言朴素,比喻生动。”[5]这种戏剧化形式,再通过采用一系列的象征符号和舞蹈动作,使他们的“表演形式更倾向于一种有意识的传统化,即人们会意识到表演是‘重复以往已存在过的东西’。”[6]
甘南格萨尔藏戏,表演细腻,韵白清晰,唱腔时而高亢爽朗,时而低缓悲凉,民间说唱特征尤其突出,延续了格萨尔史诗初始本体的说唱,既具有戏剧演述形态的完整形式,又有其独特的戏剧审美风格,其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浪漫主义色彩在格萨尔藏戏艺术中别具特色。
(3)降水对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影响,降水量多的时候,空气中污染物的质量浓度较小,这是由于降水加速了空气中污染物扩散,空气质量较为优良。而在无降水天气,污染物容易堆积,空气质量较差。因此,在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天气,可以通过增大降水量来改善空气的质量。
三、格萨尔藏戏的创新与重构
马背格萨尔藏戏的表演不受空间、角色、唱腔的束缚,各种舞蹈动作,如圆场、绕场、过场,以及马上马下的高难度戏分,都在宽广的露天草原上进行。江河雪山是背景,广阔草原是舞台,场面宏大,气势恢弘,深受民众喜爱。“从传承人走向受众,强调的是把史诗演述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过程进行观察的取向。受众的作用,就绝不是带着耳朵的被动的‘接受器’,而是能动地参与到演述过程中,与歌手共同制造‘意义’的生成和传递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环节。”[4]表演者和观众实际上正是在这种社会性实践的重复交流互动中,共同完成了一个个意义的生成。
随着藏民族对现代戏剧理解的不断深入,古老的艺术形式正以人们不易察觉的动态方式发展、变化、创新。传统与现代并存,史诗中的英雄主义篇章,民歌的谚语对唱,旁白的幽默哲思,格萨尔王恩怨纠结的爱情,以及终得善果的理想主义气息,洋溢着一种浪漫、唯美和自由。格萨尔藏戏丰富的文化内涵、包容多元的表演,已经逐渐传播延伸到史诗流布区域以外,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被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了解、认同、喜爱,表现出传统与新生既守正又创新的实践形态。格萨尔藏戏传承与表演的这种新生性、复合性、融合性特征和带有实验性的探索,使格萨尔藏戏正在经历新的蜕变。
布恩(James Boon)认为符号是意义的学科,符号的系统和意义的系统联系起来即可解释与理解社会、个人和文化。格萨尔藏戏的声音、造型、歌舞等符号同样能够阐释民族、个人、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界限。近年来,四川甘孜州已有50个“格萨尔藏戏”团,色达县格萨尔藏戏团尤为突出,他们表演的《英雄诞生》《赛马登位》《霍岭大战》剧目,已走出国门,蜚声海外。色达县格萨尔藏戏团的“格萨尔宫廷舞”在塔洛活佛的倡导下,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同时结合藏区北派藏戏的表演风格创立的别具特色的格萨尔藏戏,成为格萨尔藏戏新“范本”。这种对传统藏戏推陈出新的“范本”,首先保持了传统格萨尔藏戏叙事的诗性结构和唱腔多变的音乐结构,以及念白少、曲调多的演唱特色,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其次,写实布景、各色灯光、不同道具的大量运用,呈现出民间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相得益彰,使格萨尔藏戏的表演观赏效果更具戏剧化特征。笔者参加了两次 “格萨尔故里行”学术考察,在色达县调研,并曾经随同色达县格萨尔藏戏团赴杭州展演。雪域藏地的格萨尔藏戏在西子湖畔、江南水乡受到了同样的欢迎。理查德·鲍曼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认为,“从根本上,表演作为一种口头语言交流的模式,存在于表演者对观众承担展示自己交流能力的责任。这种语言交流能力依赖于能够用社会认可的方式来说话的知识和才能。从表演者的角度说,表演要求表演者对观众承担有展示自己达成交流方式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展示交流的有关内容;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表演者的表述行为达成的方式、表述技巧以及表演者展示的交际能力是否有效等等,将成为被品评的对象。此外,表演还标志着通过对表达行为本身内在品质的现场享受而使经验得以升华的可能性。因此,表演会引起表演行为的特别关注和高度自觉,并允许观众对表述行为和表演者予以特别强烈的关注。”[9]31-35格萨尔藏戏正是在其动态行为“表演”的言说方式中,与观众、听众和参与者进行“文化表演”的交流与互动。
式中:分别对应的是温度为T0、T时的k阶Stokes波中心频率。可以看出,k阶Stokes波相对于BP的中心频移量是1阶Stokes波的k倍,即前者的温度灵敏度系数是后者温度灵敏度系数CT的k倍。这也意味着,利用Brillouin多波长输出可以实现更高的温度灵敏度系数,如果Stokes波达到10阶或以上,则理论上可以使温度灵敏度系数提高一个数量级。
戏剧形态的创新目的在于其价值化提升。随着全国藏区各地文化事业的推展,以及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高度重视,格萨尔藏戏传承表演实践日益走向多样化。近几年,青海果洛、四川甘孜开始以电影胶片的形式记录现场格萨尔藏戏表演。同时出现了“老戏新唱”的现代格萨尔歌舞剧,以及实景拍摄的马背格萨尔电视剧。拍摄的记录片已有《姜岭大战》《丹玛王子传》《多岭之战》《赛马称王》《降伏北妖》《霍岭大战》等剧目。大型现代歌舞剧有《格萨尔》《天牧》、“果洛森姜珠姆女子格萨尔藏戏团”创编表演的《赛马称王》多次赴港澳台、国外演出。色达格萨尔藏戏团参加波兰“第37届国际山丘民俗节”,获得大赛金奖、优秀奖等5项大奖。一届民俗节,一个国家同时获得5项奖,是37届以来的第一次。格萨尔藏戏团以“西藏传奇岭国王格萨尔”为主题,赴英国巡回演出,其中《赛马称王》《霍岭大战》最受欢迎,西方观众以这种特定的戏剧化形式近距离接触了解中华文化。格萨尔藏戏传承所呈现出的这种开放姿态和融汇众流的特质,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创新与实验。但创新必然受到事物本质属性的制约。京剧大师梅兰芳曾就戏曲创新提出过一个原则:移步而不换形。“移步”,是指要向前走,不要固步自封;“不换形”,即不要粗暴地将原戏曲改得面目全非,导致京剧不像京剧。格萨尔藏戏的当代传承与创新,面临同样的问题。
四、结语
格萨尔藏戏表演通过对古典时代民族文化的重构与想象,构成格萨尔史诗更丰富的表达。格萨尔藏戏传承作为文化象征的表述符号,也是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表演民族志。表演的象征形式、艺术形式,已构成社会生活资源本身,具有其相应的能指和所指。能指是格萨尔藏戏符号性表征的外显形态:脸谱、服装、武器、战马、唱腔;所指,即其背后所指涉的意义和观念。作为行为表述实践,格萨尔藏戏,无论演员或观众,在耳听目视的观赏愉悦中,接受着这些符号象征是如何重述、演绎记忆深处的“过去”与“传统”。借助唱腔、舞蹈、服饰、道具、旁白,唤醒集体的共同记忆,诠释个体的生命意义,以及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特定的语言和身体行为表述,格萨尔藏戏背后隐含着多民族文化融汇的线索引导,以及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提供给我们文化符号系统新的知识,帮助我们对自己、他者文化更客观、更深入的理解,从而重新廓清言说与书写之间的复杂关联,还口头说唱以本原。
注释:
经过与其他供暖方式的对比(见表3),超低温CO2空气热源热泵供暖的节能效益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1)具有较高的系统综合能源利用效率;(2)运行调节灵活,使单位供暖面积耗能量降低。
①老百姓以为她们是仙女下凡,赞其为“拉姆”(仙女),以后藏戏被称作“拉姆”亦由此而得名。
(1)打破行政边界,推进跨区域旅游合作。河南省旅游经济网络空间结构不均衡。随着全域旅游战略的提出,河南省旅游经济的跨区域合作成为必然,在合作空间的选择上,必须要打破行政边界的限制,重点加强中东部旅游经济的区域合作,提高西南部旅游经济的连通能力,最终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均衡化发展。
②“八大藏戏”:《文成公主》《诺桑王子》《智美衮登》《苏吉尼玛》《百玛文巴》《顿月顿珠》《卓娃桑姆》《朗萨雯波》。
③ 2003年12月玛曲地区藏剧演出主要组织者咚仓·嘎藏赤列活佛,以及拉卜楞寺主持法舞演出的高僧桑热布和嘉样彭措,曾就甘南藏戏交换意见,指出甘南藏戏中的《格萨尔·降魔》和《朗萨雯波》《阿达拉姆》不被尊为“南木特”,其中的原因在于剧中有杀戮、不是先贤大德的传记,剧中人不是藏传佛教的佛陀、法王。甘南“南木特”藏戏已被列为甘肃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48.
[3]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60.
[4]朝戈金.朝向21世纪的中国史诗学[J].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10(1).
[5] 索代.夏河史话[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227.
[6] [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5.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总则,第二条,定义一)[Z].2003(10).
[8] [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M].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
[9] [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1-35.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1-0057-08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9.01.007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优势学科“中国史诗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丹珍草(杨霞),藏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藏族文学研究、格萨尔史诗研究。北京 100191
收稿日期:2018-11-19
责任编辑:杨新宇
标签:藏戏论文; 格萨尔论文; 甘南论文; 说唱论文; 史诗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民族学刊》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优势学科“中国史诗学”阶段性成果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