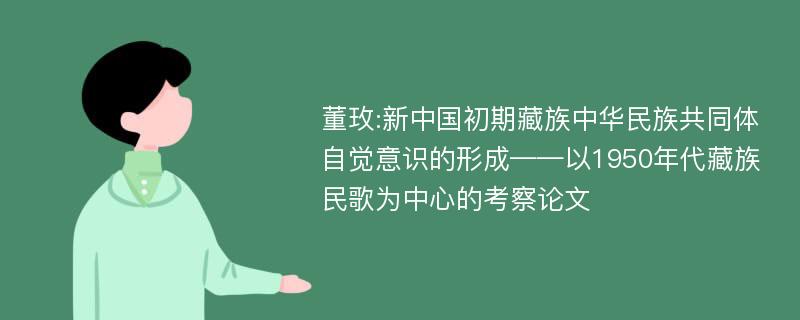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建构,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内忧外患条件下“独立富强”之追求。但中华民族由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转变的“共享”观念,并不因其出现而被广大民众,特别是少数民族民众所接受。相对而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成为广大藏族民众的自觉意识。1950年代的藏族民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形成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形成的动力。
关键词:共和国初期,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藏族民歌
一、民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的概念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初的产生,意味着在“瓜分豆剖”的国家危机历史条件下,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我觉悟。蕴涵在梁启超欲 “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1]中的则是中华民族建构中的同一性逻辑①,同一性为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建构与强调民族的自觉提供了支点。然而,这些共同与共有的一致性,与其说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自觉,倒不如说是共同意识建构者的主体自觉的结果。在以往的研究中,实则多聚焦于精英分子的言说,或国家与政党之经营,强调的是建构者的主体性,而对其客观效果,即中华民族民族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范围内被接受,多所忽略。②
取一定量的样品置于样品盘中,设置升温程序为:30~510 ℃,10 ℃/min,吹扫气体为氮气,流速 20 mL/min。将所得的 TG曲线进行一阶求导得到 DTG曲线,并利用软件标示热失重速率曲线的Peak温度。
首先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同一性,能否为下层民众,那怕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民众所接受?正如彭南生先生所强调:“我们的研究应注重老百姓自己的真实故事。只有把老百姓的故事讲清楚了,才能揭示一部真实的中国近代史。”[2]下层史研究强调史料上拓宽视野,因而有关层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就需要关注非主流的报刊、私家笔记、家传家谱与野史资料,特别是作为下层民众心声表达的民间文艺等形式。
正如许纪霖先生强调的“一个国族是否获得公共的、普遍的认同,关键不是看主体民族的认同,而是看少数民族与族群是否承认”[3]。中华民族建构的出现,并不会因此直接导致各少数民族特性的消失,相反更需要的是如何在此巨大的差异中确立能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性。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同一性的建构不乏各少数民族上层的参与,也不难进行考察。③但对于一般的少数民族民众而言,如何考察并发现蕴涵在其中的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主导力量?同样需要采取下层史研究的视野,从民间文艺,特别是从民歌这种内心流淌出来的最能表达下层民众淳朴真挚感情的艺术形式中去寻找。从这个角度而言,天生的歌唱民族——藏族及其民歌,无疑为进行此项研究,打开了一扇绝好的窗口。
近年来,藏族民歌的研究日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总体而言,学术界关于藏族民歌的研究,多侧重于藏族民歌的艺术形式④,略及藏族民歌中蕴涵的政治性内容⑤、宗教性内涵⑥等,而从思想史、社会心理方面,特别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对藏族民歌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与著作尚未发现。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藏区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区域自治、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等等,不仅揭开了藏族人民的历史新篇章,其影响所及包括藏区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藏族人民的社会心理、对政治国家的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导致下层民众以热切的民歌唱出自己的心声,亟待加强发掘。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元素,针对数据处理方面的网站也较为广泛,数据演化的形式也随着不同领域的特点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
二、共和国初期藏族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费孝通先生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历了几千的时间,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实现的”[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1年5月23日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不仅使西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宣告帝国主义制造“西藏独立”图谋的破产,也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在普通藏族民众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首先,祖国大家庭的共同体意识深入藏族民众心中。随着西藏和平解放,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各项规定,打破了藏族民众的思想禁锢,使之亲身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藏族民众发出久已埋藏在内心中的呐喊:“西藏是中国的土地。”[5]他们歌唱祖国的壮丽河山:“我们祖国的江河,象波纹一样多,我们祖国的草原,象镜子一样平,我们祖国的城市,象海洋一样大。”[6]中国各族人民就是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天上有朵乌云,遮住了金色的太阳,谁拉走了我心爱的牛羊?——是那比狐狸还狡猾的管家,谁拆散我心爱的人儿?——是那比豺狼还凶残的土司头人。金光灿嘴的太阳,赶走了那朵乌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为我们夺回了失去的牛羊,我那心爱的人儿也脱离了虎口,回到了我的身旁,我深深感谢世间的 “活菩萨”——伟大的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13]
这种共有家园意识,自然也就使藏族民众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他们不仅将祖国大家庭比喻成为花园,“中国各民族有六七十,一齐团聚在一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没有高低呵,好好守护咱们的大家庭吧!”[8]守护家园的意识,进一步使藏族民众认识到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翻身的藏族人民呵,决不能离开祖国的大家庭;否则,除险的反动派,又会把毒药倒在我们口里!”[9]由此可见,对中国共有家园的意识,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已经成为藏族普通民众共有的社会心理认知。
其次,各族人民血浓于水的共同体意识成为藏族民众普遍的认同。藏族与中国其他各民族间早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连着心的交融关系。在藏族民众的心中,藏族与汉族就是“同一父母生下来的孩子呀,本来就是亲兄弟”[10],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离、民族歧视等政策与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却阻断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推翻了压在藏族人民头上的大山,民族平等观念及其政策的实施,则为各族人民的团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汉族老大哥也不自大,藏族小弟弟也不自卑了,大小民族主义都取消,大家永远团结在一道。 ”[11]
藏族民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进一步增强,他们将各族人民比作“云”、比作“星”、比作“水”,虽然各在一方,发源不同,都是紧紧地团结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是灌输式教学,在课堂中滔滔不绝,从未考虑学生对物理是否理解.最终教师讲了很多,学生听了很多却没有实际的意义.探究性一部分内容要求的也是学生的自主性,在新的课堂教学中学会转换角色,让学生成为教学的重点,给学生空间去探究和解决物理难题,教师则担任从旁指导的角色,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去探究物理,去发现物理,去理解物理.给学生一定的思考空间,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双手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物理,吸引学生对物理学科的兴趣.
在整个藏区未解放前,藏族民众未能将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变为自觉意识,同样源自于国家的淡漠以及国家效能的缺失。此正如顾执中、陆诒所言:“游牧生活本无定处,一切行动,均受制头目或酋长的命令,而且宗教的信仰,已成为牢不可破的势力,此所以番民只知寺院,只知服从头目土司。然而官厅方面,不能循善道诱,长官不能深入番民,联络头目,未尝不是政令不通行的最大原因。”[40]一语道破民国政府在藏区政令不通的关键所在,即政府未能对藏区采取积极措施,如何能让一般藏族民众认可政府,进而认同国家呢?深谙边疆民族问题的马鹤天指出:“在边疆民族复杂之地,融洽各民族感情,固为必要,但尤应泯除各民族界限,使各民族文化渐趋平等,生活渐趋一致,如普设学校,讲求卫生,改良生活,增进常识,使知世界情形,国家现状,同为国家一份子,利害相同,福祸与共,久之自忘其个人之利益与民族之差别。”[41]明确指出国家认同的前提在于文化平等与共同富裕。
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生活在中国这个共有家园之内,要紧密团结,守卫祖国,共建美好幸福的生活,成为了那个时代藏族民众心中的最强音。
再次,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空前强烈。随着西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领导核心,开始出现在藏族民众眼前。感受到解放前后的变化,藏族民众以神性与诗意的歌声,赋予了中国共产党高度认同:
海子上游的是鸳鸯,海子底游的是金鱼;玩耍虽不在—起,大家都生活在海子里。平原上住的是汉人,高原上住的是藏人;住家虽不在—起,大家都生活在大家庭里。[7]
曾经无比虔诚信仰佛爷、崇拜神灵的藏族民众无由表达自己的感激,用其所能想到的所有能够表达自己感激与崇敬的词汇,赞颂中国共产党。党的领袖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化身,被藏族民众讴歌为太阳,比作活佛、众神之神,将藏族民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毛主席有如众神之神,看出西藏众生的痛苦,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14]由此,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同与祝福:“雄伟的人民中国,耸立在南瞻部洲的东方,献给她真情的颂歌——愿她百劫永存,万寿无疆!”[15]
2018年家道家政与各地人社、工会、妇联、商务等单位合作,将高频率举办家政服务(育婴师)培训暨就业安置行动作为人力资源拓展的主要渠道。培训内容包括:母婴护理常识、产妇保健与日常生活护理、母乳喂养与人工喂养、新生儿洗澡、新生儿抚触实操技能指导及训练、新生儿护理与保健基础知识及异常情况的鉴别处理等。
北京是个金子的城,据说那里有个金子的太阳,那不是金子的太阳,那是毛主席温暖的阳光。北京是个银子的城,据说那里有一座银子的宝塔,那不是银子的宝塔,那是革命英雄纪念碑。北京是个珊瑚的城,据说那里有个珊瑚的号角,那不是珊瑚的号角,那是党中央洪亮的声音。[16]
藏族民众将北京比作 “金子的城”、“银子的城”、“珊瑚的城”,是因为那里有作为地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更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所在。这是他们心目新的圣城,更是以歌声表达自己迫不及待前往“朝圣”的心情:“北京吹起的金唢呐,吹的人我还没有看见过。不是我不想念北京,是嫌马的脚步太慢了。孔雀!你懂得我的心意,快送我飞到北京去。 ”[17]
从已有可见的1950年代藏族民歌来看,彼时藏族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已经具有了非常明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家园意识、各民族大家庭意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国家意识以及政治核心意识。这些内容均从相当程度上表征着藏族民众发自内心地的声音,已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转向自觉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最后,首都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成为藏族民众心目中的圣城。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也就具有了政治上作为国家中心与权力中心的象征意义。在相当程度上,人们对于首都的认可与否,也就是对政治国家的认可与否。原本,在藏族民众心中,所谓的圣城就只有被藏传佛教格鲁派三大寺所在地的拉萨。随着广大藏区的解放,首都北京在藏族下层民众心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并超越了拉萨。在他们的心中:
销售赠送有偿取得赠品,其赠品在取得时,其采购成本已计入“销售费用”账户,因此在赠品发出时只需要填制销售出库单即可;对原已计入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三、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的核心力量
依据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从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转变的理论,郑汕、赵利峰等人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自觉过程,从民族意识觉醒的角度划分为分别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等为标志的几个阶段。[18]然而直至1950年代,广大藏区仍未摆脱落后封闭的状态,导致藏族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未踏上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变之路。暂且不论西藏,即以民国时期甘青川藏区而言,“居民亦只知服从本属之酋长,不知其他,俨若另一个世界,所谓国家民族,内乱外侮,固不与彼等关也”[19],“土官和土司所辖的范围,截至今日政令仍不能及,边胞无知无识,根本没有国家观念,更无所谓民族意识”[20]。即使藏族上层,也难说得上真正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卓尼土司杨积庆,“对藏人之统治,则采完全封建的、神权的方法,毫无近代有力的政治机构,更毫无民族主义之意识”[21]。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及建立新型民族关系的前提和不可缺少的条件。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才“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平等时代”[22]。透过藏族民众的欢歌,即可发现蕴含在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自觉的核心领导力量。
由表2可知,以脱水量(λ)为因变量,微波作用时间(χ1)、微波功率(χ2)、物料量(χ3)对本实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拟合得到脱水量的二次多项式回归方程,见式(3):
藏族民众称“民主改革是最大的佛爷”,其实他们所称颂的“最大的佛爷”又何尝不是带来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呢!正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下的广大藏区的变化,最终促使藏族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他们在新社会的阳光中,在新社会的幸福生活中,热情洋溢地唱出了民族团结的欢乐颂章:“夏天,草原上多美丽,因为遍地开满了鲜花。冬天,寨子里多温暖,因为天空照耀着阳光。现在,全国各地多快乐,因为各族人民团结成一家。 ”[38]
甘巴是个好地方,只是乌云遮住了太阳。想从地上走吧,地上有很多刺巴;想从草原上走吧,草原上又有豺狠。[23]
在这乌云的笼罩之下,“家乡的牧主不倒,草原上听不到欢笑”[24],“穿西服的‘假巴’,象骑马一样压着我们”[25],“马家的苛捐杂税像刀插在脊背上,只得离开了亲爱的家乡”[26]。
解放军来了,藏区和平解放了,家乡的乌云被驱散,豺狼被赶走,家乡变了模样。如马尔康的藏族人民在歌唱:“马尔康是我美丽的家乡,从前这里一片荒凉,没有我立脚的地方。东风卷走了乌云,彩霞里出了太阳,我歌唱新的生活,热爱自己的家乡。”[27]如德格的藏族人民在歌唱:“德格是美丽的家乡,从前是一片荒凉,自从得到解放,德格变成了天堂。”[28]正是由于对家乡的热恋,藏族民众才会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家乡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而由衷地感动。正是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使藏族人民认识到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会产生对祖国大家庭的认同:
我们祖国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各族人民有如同胞的兄弟;伟大的理想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互助互敬永远不分离。我们祖国象一座美丽的大花园,香气馥郁充满着春天的阳光;各族人民都是勤劳的园丁,共同的劳动,散发着友爱的芬芳。[29]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族人民凝聚的核心力量。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历史上就与其他各民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具有了朴素的共同体意识。此正如民歌所唱:“白河,黑河,红水河……虽然流的方向不同,但总是要流进天湖!汉人、藏人,各族人民……虽然语言不同,但却是最亲的弟兄!”[30]然而最亲的兄弟,却因为历史上种种的原因,未能团结在一起。现在有了解放军,有了共产党,各族人民打破重重阻碍,欢聚在一起:
太阳、月亮、星星,在不同的时候出现,现在有了毛主席,他们在天上聚会了。马鹿、麂子、崖羊,在不同的山上吃草,现在有了共产党,他们在山上聚会了。汉族、藏族、蒙族,生长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有了解放军,他们在城里聚会了。[31]
藏族民众深刻地体认到,各族人民能够团结在民族大家庭中,完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汉藏人民消除隔阂,实现了空前的团结。这就不能不使藏族民众由衷地决心要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身旁:“东边的银星,西边的银星,四面的银星围着月亮。藏族人民,汉族人民,各族人民团结在毛主席的身旁。”[32]
再次,中国共产党在藏区推动经济的复苏,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了幸福安康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藏区的基本原则,避免了战火、硝烟与伤亡,赢得了藏族民众的普遍拥护:“西藏和平解放啦,毛主席的政策放光芒,西藏人民齐欢唱!”[33]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积极恢复与发展藏区经济的措施,特别是积极的经济救济,赢得了藏族民众的赞扬:
小学生年龄小,对游戏具有天生的喜爱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用游戏的方式刺激学生对色彩的感知。比如,教师可以设计“连一连”的游戏,将相同的玩具用不同的颜色表现出来,然后引导学生对这些进行辨识,之后将他们联系到一起。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美术色彩教学中,还能够刺激学生对色彩的认识,使学生从游戏中感受到色彩感知的乐趣。
共产党功德无量,毛主席是金子太阳。我不是空口赞扬,良心要我歌唱。旧社会里的贫苦牧民,像春天的瘦羊一样。共产党却给穷苦牧民,救济、贷款买牛羊,住上了崭新的帐房。什么人给我们衣裳和口粮,是照耀我们的金子太阳,解放的故乡,——河卡草原上年轻人到处欢笑又歌唱,老年人也穿起了节日的盛装。翻身的牧民,在一起组成了“年来康”。[34]
中国共产党给藏族民众带来的美好幸福生活,使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化为响亮的歌声:“严冬的冰雪化了、脸上的愁容散了,吹起我的牧笛吧,唱一曲快乐的歌。不唱佛爷不唱天,不唱牛羊和草原,歌唱恩人解放军,帮咱庄民把身翻。”[35]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改革,使藏族下层民众摆脱人身束缚,实现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初,藏族民众已经切身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温暖:“提起解放前的日子,头人对我们象对待犯人,看看今天的幸福时光,党对我们象对儿女一样;提起解放前的日子,强盗到处横行,看看今天的幸福时光,人民的歌声夹着欢笑。”[36]民主改革以后,藏族下层民众第一次抬起头、挺起胸来,获得个人的公民权利。他们的心中从未有如此的欢畅:
民主改革是最温暖的太阳,融化了压在我们心上的冰雪。民主政革是最宝贵的春雨,浇活了垂死的藏金花到青棵麦。民主改革是最有力的闪电,击毁了统治草原的奴隶制。民主改革带来了人民的法律,埋葬了吃人的账册利刑具。民主改革是最伟大的佛爷,赐给了藏民帐篷、牛羊租和歌声![37]
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藏区获得了解放,绽放出美丽的光芒。没有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人们就不可能有对祖国大家庭的热爱。可是,在旧时代的重重束缚之下,家乡笼罩在重重苦难之下,藏族民众感受不到家乡的美好:
四、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变的动力
诚如许纪霖先生所言:“国族的产生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内部拥有共享的族群记忆、历史、语言和文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近代国家所创造的统一的民族市场、独立的国家主权以及共同的法律政治体系。”[39]国家在多民族国家的“共享的国族认同”的塑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否产生,并成为自觉意识的关键。
随着原材料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降,劳动力成本和运输费用提高,促使生产企业成本急剧上涨,利润空间大幅缩水,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成为企业扩大利润空间的必选方案。然而,对生产企业来说,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关键还是提升企业工业化生产水平,用高生产效率获取更高利润。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数学活动,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活动中提高自主意识,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现教学目标。因此在教学中教师需要加强对教学活动的重视,学生只有通过亲身的体会和实践,才能够实现对学生的有效培养,适应小学生的个性特点,组织学生主动进行探索,积极进行对学生的有效培养,推动数学课堂的教学发展。
来自于专业脚手架承包商的正式雇员,全过程监督指导脚手架工进行脚手架搭设及拆除等相关作业,检查验收脚手架是否符合要求,同时负责作业过程安全。脚手架主管必须经过阿美认证,其证书有效期为三年。脚手架主管分为三种类型。
国家应如何创造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李自发认为,“民族意识之形成,基于历史背景与夫现实之同情心”,因而“欲彻底解决蒙藏问题”,首先要 “解除蒙藏人民目前所受之痛苦,引起好感”,并“扶助蒙藏人民求得物质生活之满足,取得信仰”。[42]卫惠林强调边疆政策应以“促进边疆之现代化为最高目标”,“一切边疆建设计划,应以国家利益与边疆民族利益密切配合,以增进边民福利,扶植边疆文化经济之健全发展为基本目的”。[43]这些规划和设想,无疑是推动国家认同,推动各少数民族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在转向自觉的正途。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却根本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不具备高效能的国家以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领导核心。
封建农奴制、军阀统治以及国家的不在场、不作为,除了在藏族下层民众中制造痛苦、制造仇恨,还能制造什么呢?他们用歌声控诉旧的社会制度:“主人的狗天天吃着牛奶,有时候还要喂几块拉夏,但是,我们这些奴隶们,却顿顿吃着曲拉。”[44]他们用歌声发泄对军阀统治的仇恨:“害人的三代马家呀,你们比豺狼虎豹还凶猛,你们把草原上的牧民,都拖进了很深的火坑。”[45]他们并没有就停留在对农牧制度、农牧主和军阀的控制之上。不是有国家吗?因而他们要追问:“收起的青稞粒粒是血汗,老鼠是黑夜把它往洞里搬;这种冤枉有谁知道谁可怜,唉,累死累活只剩下辛酸。我们的皇帝他不管,他不管。”[46]因而,藏族民众在诅咒“老鼠呵,可恨的老鼠呵,什么时候你才能死光!”之时,又何尝不是对封建国家的绝望!藏族民众转而求助于神佛。神佛不是解救众生的“怙主”,引导众生走向终结解脱的导师吗?因而他们追问:“菩萨!你当真没有听见,还是受了兴人的贿赂?穷人受苦你就不管。”[47]这种追问戳破了笼罩在藏区政教合一制与封建农奴制外衣上的宗教圣神性和虚假性,因而也是某种意义上对自以为已经为藏族民众套上了教民身份的宗教上层的否定!
无论统治者再怎么花言巧语宣称为人民谋福利,无论宗教对未来世界描绘的再怎么美妙,都是无源之水,都不可能获得人民最终的信仰和信赖。他们最终也不会将人民真正地凝聚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讲:“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48]正是这可见的好处,使藏族民众看到了新旧社会的对比:
毛主席——常碧的青海湖,草原上千万的人民牛羊靠它活。马步芳,一个朵(应为尕——引者注)唠池,只肥饱了他和他周围的几个人。[49]
东边的云,南边的云,西边的云,北边的云,虽然各飘一方,但都围绕着太阳。启明星,宿昴星,南斗星,北斗星,虽然各在一方,但都围绕着月亮。沟里的水,溪里的水,江里的水,河里的水,虽然发源不在一个地方,但都汇聚在海洋。蒙族人,维族人,藏族人,汉族人,虽然民族名称不同,但都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12]
财务预算管理作为一项极具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管理工作,其中包含了预算编制、执行考评等一系列内容。在国有企业战略发展布局中科学、合理的应用财务预算,能够最大限度的规避经营风险,提高管理效率,从而促进国有企业的全面发展。
藏族民众以通俗晓畅的对比,揭示了两种统治的差异。前者只是为了少数统治者及其走狗,而中国共产党则带给了藏族人民实实在在的好处:
Section 3: Theoretical derivation of the imaging principles
以前穷人也唱歌,净唱苦歌没甜歌,唱着唱着心酸痛,歌声中断泪珠落。如今来了共产党,翻身农民唱甜歌。一唱有了房和地,二唱有了牛马骡,三唱有了粮和面,四唱有了碗和锅,五唱有了新衣裳,六唱有了新被窝,七唱废除高利贷,八唱再不受奴役,九唱不把乌拉支,十唱当家作主多快活。唱了一支又一支,翻身农民歌儿多,谢过恩人毛主席,再唱改革胜利歌。[50]
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使藏族人民深信中国共产党是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的政党。他们歌唱:“索呀拉索,藏族老百姓的痛苦,共产党深知道。索呀拉索,藏族老百姓的痛苦,毛主席深知道。索呀拉索,藏族老百姓要笑行民主改革,共产党、毛主席来领导。”[51]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关怀,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可见的种种福利,藏族人民才由衷地感激中国共产党,热情地赞颂中国共产党。他们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比如活佛,比作大救星,比作赐福神:
四柱八梁的官厅里,住着伟大的人民领袖,在西藏人民的头上,放射着扎西的慈光。毛主席,你是我们的活佛!铁兔年的和平三月,从此西藏人民永远解放,藏民在欢欣鼓舞中,到处是翻身的歌唱。毛主席,你是我们的大救星!水龙的幸福年头,奠定了如意的丰收,马儿肥,羊儿壮,家家粮食堆满仓。毛主席,你是我们的赐福神!祖国有了大救星,拨开了苦难的乌云,驱逐了帝国主义妖魔,我们获得了自由平等。毛主席,你的恩情如海深。[52]
由感激而生信仰,由信仰中国共产党而认可、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隐含在其中的内在逻辑,就是促使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在转向自觉的内在动力:以民族平等为前提,以经济发展与人民福利提高为支撑,以个体权利的解放为粘合剂,就会推动藏族民众在自信的基础上,与其他民族生出互信,进而达成各民族间的共信。
五、小结
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任何共同体间所有可见的差异都“可以产生人以群分的意识”[53]。这种差异在族群间、民族间,因为文化与族性的差异,往往会形成明显的区隔。这是在多民族国家凝聚同一性的障碍所在。然而,正如论者所言:“一个民族的复兴,更非有严密地组织不可,要使整个民族,有严密地组织,必须民族各份子,能够各个把他们对于民族的自信结合起来,构成互相信赖的道义关系,然后才有组织与力量的可言。有了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目标,然后便生出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便是共信。有了自信、互信与共信,然后才可以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54]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各民族间的共信,并不因政治国家的存在,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具有统一的共同体意识。藏族民众的心声,清晰地揭示出,“自信、互信、共信”的确立,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采用正确的路向:“世上最好的地方,是北京城,那里发射出金光,照耀着各民族团结,毛主席领导着我们,朝着那幸福的路上走。”[55]共和国初期藏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在转向自觉,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藏区发展为中心,以藏族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的真实写照。
注释:
①所谓同一性,就是在建立在各民族差异性之上的共享的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对这些要素的共享的历史记忆与认可、认同,即是共同体意识。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相关成果可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4页;孟真:《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1935年第181号;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第1-11页;顾颉刚:《中华民是一个》,《西北通讯》1947年第1期;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2编,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56页;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②相关研究可参见:罗福惠:《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演进》,《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关健英:《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船山学刊》2016年第1期;沈桂萍:《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俞祖华:《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长》,《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③参见喜饶尼玛:《论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 2期;周晓艳:《身份与意义——藏族精英贡觉仲尼国家认同论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刘永文、李玉宝:《近现代藏族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李双、喜饶尼玛:《民国时期康区藏族精英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实践——以第三次康藏纠纷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④这方面的研究文章相对较多,如张莉、张超:《稻城亚丁区域藏族民歌的形态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4期;魏晓兰:《论四川康巴安多地区藏族民歌的音乐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4期;赵维峰:《安多藏区民歌》,《中国音乐》1993年第4期;才让措:《安多藏族民歌——以青海安多方言区为例》,《大众文艺》2010年第19期;仓央拉姆:《安多地区藏族民歌及其音乐特点》,《西藏艺术研究》2000年第4期;冯坚:《阿坝藏族“草地牧歌”旋律形态研究》,《民族音乐》2009年第4期;应秀文:《青海玉树藏族民歌音乐特点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尕藏:《藏族拉伊浅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宋志端:《藏族“拉伊”初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王双成:《藏族“拉伊”的特殊唱词及其成因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中国工会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困难职工帮扶和脱贫攻坚工作。分类做好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推进困难职工帮扶与政府救助、公益慈善力量有机结合,推动建立低保与扶贫有序衔接机制,实现帮扶送温暖常态化、经常化、日常化。把提高解困脱困工作质量放在首位,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让困难职工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⑤专题性论文仅有胡文平:《金色的太阳:1950年代藏族民歌中的中共政治形象》,《江汉论坛》2017年第2期;张小芳:《〈北京的金山上〉:西藏人民唱给毛主席的祝酒歌》,《湘潮》2013年12期。
⑥专题性论文主要为夏敏:《藏传佛教世俗化与藏族民歌》,《西藏研究》2002年第1期;李晓丽:《原始崇拜及环境保护在藏族民歌中的体现》,《西藏艺术研究》2001年第2期;夏敏:《歌谣与禁忌——西藏歌谣的人类学解读之一》,《中国藏学》2000年第2期;周金菊:《藏族民歌与宗教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8年第2期;张敬:《青海藏族民歌中的藏传佛教及其功能》,《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力人.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A]//癸卯新民丛报汇编[C].1903:130.
[2]彭南生.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J].史学月刊,2004,(6).
[3][39]许纪霖.国族、民族与族群: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如何可能[J].西北民族研究,2017,(4).
[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特点[J].群言,1989,(3).
[5][10][49][52]苏岚编.藏族民歌[C].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9.24.27~28.12~14.
[6][27][35][50]中国少数歌谣编选组编.中国少数民族歌谣[C].中国少数民族歌谣编选组,1960:46.47.44~45.49.
[7][38]蒋亚雄编译.藏族民歌(第2集)[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5.4~5.
[8][11]王沂暖编译.玉树藏族民歌选[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21.17.
[9][13][30][37]四川藏族新民歌选(汉文版)(第2集)[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60:50~51.14~15.51.29.
[12][29]开斗山编译整理.西藏新生曲[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38~40.41.
[14]苏岚辑译.藏族民歌(第1集)[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10.
[15]庄晶编译.藏族民歌(第3集)[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2.
[16][24][26][34][44][45]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青海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青海卷[C].中国 ISBN 中心,2008:236.229.230.238.226.273.
[17][32][42]芦笛辑译.哈达献给毛主席:四川藏族民歌[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15.8.18.
[18]郑灿,赵利峰主编.边防民族宗教概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132~133.
[19]陈言.陕甘调查记[Z].北方杂志社,1937:9.
[20]王钧衡.四川西北区之地理与人文[J].边政公论,1945,[4](10、11、12):42.
[21]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天津大公报馆,1936:76~77.
[22]费孝通.代序:民族研究[A]//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4.
[23][46][51]乐安等搜集整理.从黑夜唱到天明:四川藏族民歌选[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56:25.8~9.22.
[25]李刚夫整理.康藏人民的声音:藏族民歌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12~13.
[28][36]四川藏族新民歌选(汉文版)[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58:44.44.
[31]中央民族歌舞团创作研究室编.金沙江藏族歌谣选[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8~9.
[33]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西藏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青海卷[C].中国ISBN中心,1995:205.
[40]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10~111.
[41]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1编)[M].商务印书馆,1947:60.
[42]李自发.青海之蒙藏问题及其补救方针[J].新青海,1933,(12):8~9.
[43]卫惠林.如何确立三民主义的边疆民族政策[J].边政公论,1945,[4](1):4.
[48]杨春贵等选编.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 乙种本[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587.
[5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11.
[54]刘宗基.中华民族应一致团结起来[J].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35,(2):5.
[55]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藏族民歌选[C].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37.
Tibetan’s Chinese Nation Self-awareness Formation in Early New China Stage--Investigation on Tibetan Folk Songs in 1950s
DONG Mei
Abstract:The forming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cept reflects Chinses people’s ideal for independence and prosper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mestic strife and foreign aggression.The share idea from existed entity to self-aware entity would not be directly accepted by the public,especially the ethnic minority public.Relatively speaking,the aware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as not accepted by Tibetan unt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The Tibetan folk songs of 1950s deeply reflected the core function and power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self-awareness.
Key words:Early Republic;Tibetan Public;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wareness;Tibetan Folk Song
中图分类号:C958.1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3-0179-07
本文系甘肃省高校科研项目《洮岷河“花儿”与甘南藏族“拉伊”之比较研究》(批准号:2017A-125)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3-12
作者简介:董 玫(1976-),女,甘肃临夏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文理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音乐交流史、音乐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张 科]
[责任校对 张 科]
标签:藏族论文; 民众论文; 共同体论文; 中华民族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甘肃省高校科研项目《洮岷河“花儿”与甘南藏族“拉伊”之比较研究》(2017A-125)论文; 兰州大学论文; 兰州文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