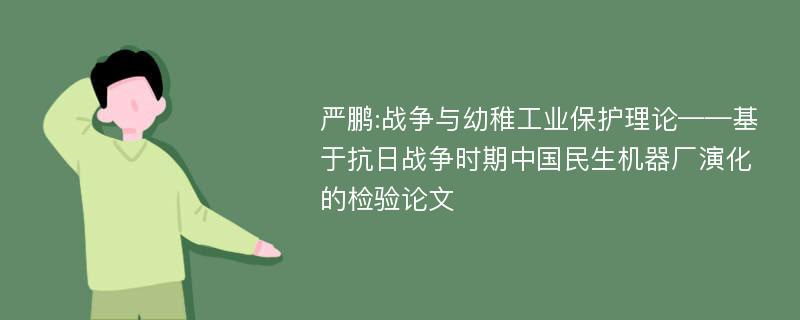
摘要: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的提出与欧洲的战争经验有密切关系,本文则试图通过一个中国工业史的案例予以进一步的检验。抗日战争爆发前,作为中国西部的一家企业,民生机器厂仅具备修理能力,属于典型的幼稚工业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东部工业企业、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内迁,被民生机器厂吸纳,充实了该厂的技术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后方航运业的需求激增,促使该厂学习制造轮船,实现了由修配到制造的跨越;同时后方进口国外设备困难,民生机器厂自力更生学习制造核心部件,并由此提升了技术能力。民生机器厂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了真实的能力积累,但企业的发展并非拜战争所赐,只是战争这一历史偶然因素为民生机器厂等落后地区的企业创造了适宜的供求条件,诱导其由低级产品市场进入高级产品市场,进而推动了工业化。
关键词:幼稚工业保护理论;战时经济;工业化;技术能力;抗日战争
战争对于工业化的影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较少涉猎的主题。然而,在充满偶然性和意外性的真实的历史中,战争是考察经济演化时无法忽略的变量。一般而言,战争扭曲了经济发展的既有道路,并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创痛。但是,实际情况远为复杂。李斯特[1]根据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指出战争会迫使交战国不得不争取自给自足,这将鼓励工业落后国家在工业上获得相当进展。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构成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的立论基础之一。维斯和霍布森[2]则进一步指出战争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乘数效应。就中国经验而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下简称“战时”),翁文灏[3]已观察到战争刺激了大后方工业的兴起,尤其强化了战前极为薄弱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对此现象之成因,郑友揆[4]给出了接近于李斯特的解释。然而此前卞历南[5]与张守广[6]对战时工业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本文拟以民生机器厂这一个案,具体剖析战争刺激后发地区工业化的机制及相关企业发展的原因,进而对幼稚工业保护理论进行检验。
一、幼稚工业企业:战前的民生机器厂
民生机器厂是卢作孚主持的民生公司的附属企业,学界对卢作孚与民生公司的研究[7]相当丰富但鲜有成果专论民生机器厂。抗日战争爆发前(以下简称“战前”),民生机器厂只是中国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一家幼稚工业企业。民生公司是教育家卢作孚于1925年在重庆筹建的企业,主营业务为川江航运。晚清开埠通商以后,中国逐渐走上了经济现代化道路,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资源禀赋优越,却受制于“蜀道难”的地理条件,长期依赖危险的水道与外界贸易往来。因此,自轮船引入长江上游后,川江航运逐渐成为中外企业争夺激烈的市场。1922年海关报告称:“新造轮船加增于扬子江上游者,为数殊多,其吨位供过于求”。到了1926年,川江航运市场进入到竞争最激烈时代,外国资本公然表示“务使华轮不能支持”[8]。此时,在合川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等,最初的计划“只在办一航行合渝之小船,与在合川办一电灯厂”。由于经营得当,民生公司稳步扩张。1926年公司运客1.4万人,1936年则增为41万人,货运吨位则由1926年的500吨增至1936年的80 000吨[7]。战前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7艘,共20 409吨,在长江航线中已可与太古、怡和、日清和招商局这四大航业巨头并驾齐驱[7]。在经营航运主业的同时,民生公司还广泛投资于机械、纺织、煤矿和铁路运输等领域,其中民生机器厂即为民生公司投资于机械工业的附属企业。
船舶是航运企业从事经营的主要工具,购买及维护船舶也就成为航运企业重要的投资和经营活动。由于本地工业不发达,长江上游航运业所需的轮船,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是从国外进口,就是依赖长江下游上海等地的工厂制造。例如,从1923年起,在工程师叶在馥的主持下,上海的江南造船厂设计并制造了一系列适合航行于长江上游的特种轮船。由于川江水急滩高,普通轮船航行于此必须绞滩,既浪费时间和金钱,又很危险,叶在馥设计了一种浅水轮船,一方面马力大而不怕川江急流,另一方面吃水浅而不怕川江滩石[9]。江南造船厂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国营造船企业,川江轮船的设计与制造,体现了该厂较强的技术能力。除江南造船厂之外,上海还聚集了一批中、外资造船企业,为重庆等他埠所无。因此,在民生公司开办之初,卢作孚只能不远万里奔赴上海购买轮船,他在上海接洽9个船厂,最终与合兴造船厂“议妥船价全部24 500两,约合35 000元”[10]。1926年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民生在上海建造完成,公司由此迈出了经营川江航运的第一步。
然而,位居长江上游的民生公司要向长江下游的上海厂家购买轮船,甚至要将船舶开到上海中修和大修,势必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更有甚者,公司“每遇机器损坏,皆向他厂配制,遂每受其要挟,且不能按时交械,以致营业深受影响”[11]。为了解决船舶供应和维修瓶颈,民生公司采取了纵向一体化战略,[注]一般而言,企业采取纵向一体化战略的投资动机是防御性的,民生公司的决策亦具有这一特点。关于纵向一体化的更多分析详见钱德勒[12]的研究。向产业链上游的资本品部门扩张,于1928年创办了民生修理厂,后改名民生机器厂。由于西南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加上民生公司自身亦为新创企业,故民生机器厂成立之初,亦极为幼稚,资本才两万元,“仅小屋一橼,车床4部,刨钻床各1部,发动机1部,职工亦系十余人耳”[7-11]。可以说,民生机器厂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仅为民生公司附属的船舶修理部门而已,对外部市场的参与度不高,甚至因为产能有限而谢绝外来订单[11-13]。 1932年民生机器厂的制造收入,总计对内收入152 284元,对外收入14 735元[14],后者仅为前者的1/10,这反映了民生机器厂的特性。随着民生公司业务的扩张,民生机器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例如,1932年因为“公司所有各轮,无船不修”,导致机器厂修理能力出现严重缺口,“冷作两起,工徒百余,均不敷用”[15]。在这种形势下,民生机器厂于1933年购买了地皮扩大厂基,新建了翻砂间,购买了龙门大刨床等新设备,生产设备总数达到30部,动力设备则有7部共52匹马力,职工总人数亦增至165人[16]。短短几年间,民生机器厂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这自然得益于母公司的扩张。
从技术能力的角度看,民生机器厂是有实质性进步的,从一个小修理间发展到对千吨级轮船实施大修,而这种修理工作在此前的西南地区没有企业可以办到[7]。民生机器厂技术能力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修理活动中的经验积累和有意识的人才培养。由于西南地区机械工业落后,早期进入民生机器厂的工人,多数不识机械图样。为此,民生机器厂从1933年起招收学徒,采取半工半读模式,对受过初级教育以上的青年施以机械教育,将其培养为合格的技术工人,这一计划带有速成性质[11]。截至1936年,民生机器厂已招收学徒3批,这些学徒日后都成为了厂中的技术骨干[7]。但是,总体来看,战前民生机器厂的技术能力还是极为幼稚的,停留在修配水平,未能发展出实质性的制造能力。战前民生机器厂的主要任务还是民生公司所属船舶的修理和改装。例如,1933年2月卢作孚就曾直接致函民生机器厂,称“希速将民江轮引擎改为烧柴油者”,以便在修好该船后,可以将其“改为拖驳”[17]。值得一提的是,民生机器厂逐渐掌握了一些小型机械如水车打谷机和油漆机等的制造能力,并对外营业。但这种业务数量有限,且亦包含修理成分[11]。因此,战前的民生机器厂虽然解决了民生公司的船舶修理瓶颈,但尚不能为母公司直接供应船舶。
作为一家在战前只具备修理能力的幼稚企业,民生机器厂既不能造船,也难以制造较复杂的船机。民生机器厂制造第一艘新船民文时,船上所用的两具锅炉,仍“购自英商固敏洋行”,因每具重达18吨,故“经多方设法,始克运至内地”[22]。进口机件如此大费周章,自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负担,故新船建造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定下了自主制造核心部件的方针。例如,对于木壳机动船的锅炉,新船建造委员会决定“用港购之4、5分钢板自造”。对两艘80呎新船的机炉,新船建造委员会也决定“由民生厂制造100马力之蒸汽机2对,利用旧通管制造水管锅炉2只,装入此2船壳”,并规定“尽4个月内完成之”。此后,新船建造委员会一度决定造三联式150马力引擎,后又决定缓造,改造7部450—550马力引擎,后又改为400—500马力,由叶在馥“负责计划”[21]。当然,由于起点较低,在开始为新船造配套的船机时,新船建造委员会仍不得不将部分机件的制造工作外包给其他厂家,或继续从市场上采购现成产品。例如,80呎新船所用的240马力引擎,虽然设计绘图工作由民生机器厂完成,但制造工作外包给了重庆的大鑫厂,限其3个月内完成。再如,新船建造委员会于1938年底开会讨论购买机件和材料事宜时,曾议决一条船上的胀炉通滚筒向外厂购买,理由是“不必因节省千余元导致误事”[21]。这反映了民生机器厂制造船机同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从修配到制造:民生机器厂的技术跨越
1939—1943年民生机器厂共制造新船19艘,平均每年制造3.8艘。考虑到该厂造第一艘船民文费时近一年半,可以认为其制造能力是有所进步的。因此,在战前仅仅具有修船能力的民生机器厂,在战时实现了“从修配跳到专造”的技术跨越。由于民生机器厂在战时制造新船极度依赖内迁后方的周茂柏和叶在馥等技术专家,客观地说,其技术跨越离不开战时特殊环境下东部地区技术人员的向西迁移。但是,即使在接纳了东部技术人员的条件下,民生机器厂若不付出相应的努力,也无法实现从修配到制造的技术跨跃。民生机器厂刚开始尝试造船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阻力,周茂柏[19]曾对民生公司的同仁说:“现在连一根铁钉都要发生困难,但我们决不退馁,依然要鼓勇负起我们的责任,尽力做去”。这种迎难而上的企业家精神[23],是推动民生机器厂实现技术跨越的内在动力。
除了能够制造交通运输装备上的动力设备外,民生机器厂在战时技术能力的发展还体现为制造水轮发电机[30],这显然也是掌握船用核心部件制造能力后的一种外溢。必须要指出的是,大后方工业企业是在电力企业进口外国货困难的背景下从事水轮发电机等装备的试制的[31],具有典型的战时特征。因此,民生机器厂对于船舶核心部件的自制,以及衍生而来的对于其他装备的制造,均属于战时环境下的自力更生。从这个角度看,战争对于后发地区的幼稚工业确实起到了李斯特所说的保护与促进作用。当然,战争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为企业制造复杂技术产品的动机提供了强劲的激励,企业技术能力的发展,仍取决于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
在改造旧船的同时,民生机器厂着手制造新船,新船建造委员会从一开始就积极推进80呎新船的建造。民生制造厂完成的第一艘自造轮船为叶在馥主持设计的民文,该船为客货两用轮船,因专门用于行驶川江,故“船壳之建造,系根据川江之湍急水流狭窄之河床,以及其他特殊因素,为设计之标准”,而尤其注重“船身之坚固性与横稳点等”,使其在洪水期和枯水期均能畅行无阻[22]。对叶在馥而言,设计此类川江轮船可谓驾轻就熟。但是,对民生机器厂来说,将设计蓝图落实于制造过程,还是花费了时间的。1939年1月民文动工,在制造过程中,民生机器厂遇到了缺乏工程人员的困难,直到1940年6、7月间才基本完工[22]。建造民文所耗费的时间,反映了民生机器厂为掌握造船能力而付出的学习成本。有理由推测,在完成民文等早期船舶的建造后,民生机器厂的制造能力得到了提升。1942年民生机器厂竣工新船10艘,几乎平均每月完成1艘,达到了其最佳水平[7]。
与东部技术人员涌入民生机器厂相应的是,战时运输扩大了对船舶的需求,激励了民生机器厂通过造船来增加运力,而这又使该厂实施了组织变革。据周茂柏[19]回忆,1938年至1939年初,民生机器厂“工作激增,组织丕变”。从造船方面看,最重要的组织变革是民生公司设立了新船建造委员会,作为民生机器厂从修配到制造过渡阶段的统筹管理机构。1938年冬,民生公司决定在重庆建造新船,考虑到“一切设计及工程等事宜,皆极繁重”,成立了新船建造委员会,由公司经理郑璧成、襄理张挽澜、厂长周茂柏和工程师叶在馥担任常务委员[20]。1938年11月29日通过的《民生实业公司新船建造委员会简章》规定,新船建造委员会系“为添造新船”而成立,共有委员9人,其中民生公司8人,民生机器厂1人。新船建造委员会下辖设计室和监工室,分管新船船形、轮机之设计及监造事宜,而船、机设计须照公司要求办理,设计完成交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方能发包施工建造[21]。1939年1月新船建造委员会决定新船设计室与民生机器厂的设计股合并。尽管新船建造委员会是民生机器厂母公司的组织,但由于公司本身是机器厂的出资人和最大客户,[注]实际上,尽管战时民生机器厂的组织机构日益完善,并成为独立核算的单位,但该厂仍不能自负盈亏,资金、福利和工资等一应事务全由民生公司统一管理[7]。故新船建造委员会的设立是有利于民生机器厂向造船迈进的组织变革。与此同时,在周茂柏的领导下,以前“事权既不统一,处理亦乏效能”的民生机器厂,也于1939年进行了组织改革,将全厂分为3课10股,“以厂长总其指挥监督之权”[19]。民生机器厂的组织变革也是与该厂规模扩大化和业务复杂化相适应的。
1938年10月3日新船建造委员会召开了第1次会议,会上讨论的议案主要是对长江、巴渝和民彝等既有船舶的改造。例如,会议责成叶在馥研究长江和巴渝的“旧船壳可否改作货驳”[21]。民彝原名宜昌,1929年建于上海,原属美商捷江公司,1935年卖给民生公司后更改了名字,1937年8月遭火焚毁。由于该船容量大,在川江已被列为第一级轮船,故民生公司决定将其“重行建造”[22]。战前民生机器厂已经能够从事船舶改装工作,改造民彝等船仍是该厂既有能力的扩展。但是,由于叶在馥等高级技术人员的加入,民生机器厂的船舶改造能力也在技术上有所跨越。例如,民彝即按照叶在馥所绘图样修复,而重新设计的方案对原船结构进行了大的改动,如将前后货舱口设计为极长,以使其能够装入钢轨和汽车。对长江和巴渝的改造亦由叶在馥计划决定,改造方案包括将无线电杆撤去和新造船壳等[21-22]。这样的大规模改造,其工程量和难度或不亚于新造轮船,对于民生机器厂是极好的锻炼。因此,民生机器厂改造轮船的周期并不短。以民彝为例,1939年1月正式开工,先进行冷作工程,9月将烧坏的铁板拆除后重新装配,10月将全部机器拆卸后修配安装,1940年2月着手木工工程,9月方全部完工[22]。民彝的修复改造工作耗时近两年,这充分说明修造大型船舶的不易。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发动进攻,一大批东部地区的工业企业为避免沦于敌手,向西南和西北地区搬迁转移。其中机械制造类企业为数众多,约占内迁企业总数的40%。与此同时,一批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背井离乡前往西部地区。在工业内迁过程中,民生公司不仅有力地组织了物资和人员的运输,而且协助一批东部企业在重庆安顿下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民生公司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为民生机器厂补充了来自东部地区的技术力量。其中对民生机器厂技术跨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一为该厂与来自武汉的周恒顺机器厂合营,二为该厂对江南造船厂技术人员的吸纳。武汉的周恒顺机器厂诞生于清末,技术力量较强,能制造煤气机等动力装备。该厂企业家周茂柏曾留学德国,是国内声望很高的机械专家。但抗日战争爆发后,周茂柏不得不设法将自家企业和家族成员迁往西南后方。民生公司对周家企业的内迁予以了帮助,但也借机提出了联营的条件。因此,一方面,周茂柏被聘为民生机器厂厂长;另一方面,1939年4月迁至重庆的周恒顺机器厂以大部分机器、材料抵作股本,由民生公司投资,双方合作成立恒顺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达100万元,由卢作孚任董事长。由此,民生机器厂与原本技术实力更强大的周恒顺机器厂在战时形成了共生关系。此外,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南造船厂的工程师叶在馥带着27名熟练技工退往汉口,也被卢作孚网罗进民生机器厂[13]。除了周茂柏和叶在馥等技术专家,民生机器厂还大量聘用同济大学和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来厂工作,先后达92人之多[7],这就巩固了该厂的中层技术力量。这些来自东部地区的技术人员进入民生机器厂工作,对该厂在战时实现技术跨越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民生机器厂也注重对生产第一线的工人进行技能培训,“在各种工作中,尽量予以探讨之机会,增加其经验,并当召集训话或作个别谈话,纠正其思想,奖励其工作”,对学徒则“其训练视工人尤重”[19]。总之,民生机器厂在战时扩充了从企业家到基层工人的各个层次的技术力量,积累了强大的人力资本。
民生机器厂在后期造船时速度提升,除了能力有所扩展外,船型的变化也是重要原因。民文为钢壳船,而新船建造委员会从成立伊始即致力于研发木壳船,1938年10月21日决定木壳船船长应为80呎左右,使用蒸汽动力,引擎由恒顺机器厂制造,锅炉由民生机器厂自制,炉通则在香港购买。由叶在馥负责锅炉制造计划,并提供机器图样。新船建造委员会并议决“将来恒顺厂搬渝开工时,可商造船用瓦斯机1对装船试验,如成功即多造”[21]。因此,木壳船的制造在开始带有技术试验的性质。木壳船虽采取了木质外壳,但仍然使用机器动力,与传统木船有本质差异。之所以采用木壳,是因为考虑到后方钢铁材料日趋缺乏。实际上,民生机器厂在战时造的19艘新船,除4艘为完全钢壳外,其他15艘均采用木骨或木壳。这些木壳船具有川江轮吃水浅的特点,制造成本显然低于钢质船,故能较好地适应金属原料紧张的战时环境。在造船过程中,民生机器厂采用四川柏木来代替进口木料,而对新原料的特性,该厂“曾经深刻之研究方予解决”[7]。这表明即使是制造相对简单的木壳船,也需要民生机器厂付出相当的努力。
参考译文:高水平的展品、高质量的观众、广泛的国际参与度和鲜明的时代感将有力烘托CIMT2009的展会主题。
作为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附属单位,民生机器厂的主营业务理所当然应为船舶修造。战前民生机器厂已经开始了缓慢的技术能力提升进程,但尚未从修配过渡到制造。战时民生机器厂实现了从修配到制造的跨越,而这一演化过程的提前完成具有非自然的性质,是东部工业企业和技术人员内迁大后方的结果。由于技术人员的流入和充实,民生机器厂在战争初期极短的时期内就完成了技术跨越。
就制造核心部件来说,人才之外,专用设备也是必不可缺的,这就需要企业投资购置。民生机器厂在战时的设备扩充也颇有力度。1939年当民生机器厂从修配开始向制造过渡时,周茂柏[19]指出:“本厂工作机件,年有增加。去年统计,共有131部。近因工作加多,工作机件,不敷分配,已委托本市各厂家代制大小工具机40余部,一切图样模样,均在赶制中。至各项器材,本厂存蓄尚富,近又向香港订购器材800吨,用应急需”。据时人评述,民生机器厂所用机床的特点不在于精确,而在于重型。1939年该厂购置了最初的重型机床,使得此后能自造许多种重型工作机。此外,该厂还购买了中华造船厂湘厂的全部冷作工作机,而这批机器正是用来制造锅炉和船壳的[13]。民生机器厂制造川江轮船的关键在于自行制造战时难以进口的高压水管锅炉[7]。实际上,“这种高压水管式锅炉,是体积最小、而效力最大的最新式锅炉,在战前上海也没有人制造过,民生厂因为有重型工作机设备,有全部冷作机,又有优秀技师,所以才能冒险去仿造高压水管式锅炉”[13]。进一步说,民生机器厂为了造高压水管锅炉,曾花下相当资本去扩张设备。因此,与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样,物质资本的积累也是民生机器厂能够自主制造核心部件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民生公司的航运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以货运量来说,1936年仅8万吨,1941年达到17万吨的巅峰,此后每年货运量保持在16.7万吨左右的水平,是战前货运量的两倍。客运人数的增长更为惊人,1945年运输人数488.4万人,是1936年41万人的11.9倍[7]。如此巨大的战时运输需求,自然是推动民生机器厂从修配到制造的动力,而民生机器厂对于造船能力的掌握,也为满足战时运输需求尽到了自己的力量。1945年民生公司共有船舶84艘,总吨位26 000余吨[7]。民生机器厂战时新造的18艘运输船占船舶总数的21.4%,吨位共计1 720.9吨,占公司船舶总吨位的6.6%。由于民生公司认为战时“不需要添造大轮”,而着力建造“小型川江轮船”[13],故民生机器厂所造船舶对民生公司运力的价值,不能由吨位大小来判断,其对于公司运输事业的实际贡献更大。进一步说,民生机器厂造船能力的发展,也为战时大后方交通运输的改善作出了贡献。
三、技术能力提升:民生机器厂制造核心部件
机械产品是由各种零部件组合在一起的,最终产品的组装固然体现为一种能力,核心部件的制造尤为考验技术。战前中国造船工业技术较落后,即使是最先进的江南造船厂,也不能充分实现船机等零部件的国内自制。[注]比较而言,战前以三菱长崎造船所为代表的日本造船企业的技术进步,体现为船机制造能力的逐渐提升[24]。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下,零部件进口困难,迫使民生机器厂在制造整船的同时,设法自制锅炉等核心部件。民生机器厂相关能力的提升,使其向造船之外的领域拓展制造活动。
总体而言,战前民生机器厂发展迅速,却仍然是一家仅具备修理能力的幼稚企业。在近代中国,上海的大隆机器厂被认为是规模最大的民营装备制造企业,而大隆机器厂也是由轮船修配起步,逐渐发展出制造能力的。这一技术能力提升的过程并不简单,大隆机器厂的经营者曾感慨“修配工作人少易为,专造工作人多难治”,而“从修配跳到专造,中间设施,千条万绪,树机之难,安得若修配之易哉”[18]。民生机器厂想要“从修配跳到专造”,也不会那么容易。民生机器厂的幼稚更与整个西南地区工业的落后状态相符合。[注]例如,民生公司投资的三峡染织厂也发展成为战前四川最大的棉染织企业,但在使用相同原料的情况下,其出品品质仍远不如武汉的企业,调查者认为“当是技术上关系”。但是,作为民生公司的附属企业,依托于母公司的扩张,民生机器厂有稳定的市场,应当足以支持其走上大隆机器厂的道路,即“从修配跳到专造”。只是在市场的自然条件下,这一渐进演化过程将耗费较长时间,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意外地加速了这一进程。
民生机器厂掌握船机制造能力的原因有二:一为东部地区技术力量的注入,二为对生产设备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大。就东部地区技术力量注入而言,民生机器厂在船机制造方面的发展机制与整船制造相同,都依赖于周茂柏和叶在馥等技术专家。具体来说,民生机器厂船机制造能力的快速进步得益于与周恒顺机器厂的联营。早在清末,汉阳的周恒顺机器厂就曾向四川市场出售蒸汽动力装备,其制造能力较强且技术经验丰富。因此,民生机器厂在开始尝试造船时,也曾请周恒顺机器厂制造配套的动力设备。两厂的这种协作关系,在战时一直持续。民生机器厂是在制造民捷和民悦时,与恒顺机器厂合作,“由前者制造笨重之锅炉,后者代造精细之轮机”[13]。1940年恒顺机器厂代民生机器厂制造4部120匹马力蒸汽机主机时,本应由恒顺机器厂自行解决生铁原料,但因“市面生铁缺货,无法补充”而导致停炉,恒顺机器厂只好请求民生机器厂“先拨5吨以应急需”,而产品生铁部分的价格按民生机器厂拨价计算[25]。民生机器厂并非单纯地依赖恒顺机器厂代制轮机,它从一开始就介入到了轮机制造过程。以前述民捷和民悦的140匹马力蒸汽机来说,虽由恒顺机器厂代造,但制造机器所要用到的木样是由民生机器厂自己提供的。木样的制造工艺简单,体现的却是设计能力。再如,1943年恒顺机器厂制造250匹马力蒸汽机时,汽缸交给了民生机器厂代为镗制。这对于民生机器厂的制造能力有很大的促进,因为民生机器厂必须“新制工具3件”,方能完成任务[26]。因此,民生机器厂虽然委托恒顺机器厂代为制造复杂的轮机,但在设计和生产的部分环节均有参与。民生机器厂能与恒顺机器厂形成良好的关系,是由周茂柏同时执掌两厂决定的。总之,在周茂柏主持下,1942年民生机器厂已能自制两部300匹马力的三联式蒸汽机[7],这是民生机器厂轮机制造能力的显著进步。
从式(17)可以看出,W1的计算需要未知的目标位置真实值.因此,在计算过程中,首先令W1=Q-1,计算θ1,而后利用θ1中目标位置估计构建更加准确的W1,然后用W1得到更加准确的θ1.
民生机器厂制造核心部件能力的形成和提升,也使其制造活动得以向船用动力装备之外的领域拓展,其中最著名的是民生机器厂为天府煤矿制造蒸汽机车锅炉。天府煤矿也是因为战争导致“海运阻滞,外货无从购买”而决定自造机车[27],带有典型的战时进口替代色彩。天府煤矿将机车锅炉的制造外包给了民生机器厂,双方于1943年2月3日订立合同,规定民生机器厂按照天府煤矿送来的图样制造两座机车锅炉,此后又追加一座,共计101万元,锅炉所需钢板及炉通管均由天府煤矿供应并负责运至民生机器厂内,其他工料和燃料则由民生机器厂自行解决[28]。因此,民生机器厂代造机车锅炉属于典型的来图、来料代工,不触及设计。然而,即使只是代工,对民生机器厂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民生机器厂后来承认:“机关车锅炉,本厂系第一次制造,工具之添配甚多,制造上亦较生疏,故不能早期完工,应该公司(天府煤矿)急需”。这再次表明任何企业初次制造某项产品都要付出巨大努力和产生高额成本。民生机器厂不能如期完成工作,除了缺乏经验外,还因为天府煤矿不时改变设计以及江北停电等意外。因此,应于1943年7月底完工的第1座锅炉一拖再拖,直到8月29日才在民生机器厂验收装船,9月5日运至天府煤矿矿厂内。为了慎重起见,锅炉完成后,按合同规定只需“试水压每平方吋225磅”,而民生机器厂“为使用安全计,试至250磅”。经1943年10月装车使用,天府煤矿自制的机车行驶“甚为良好无何故障”。[注]1943年3月初天府煤矿曾致函民生机器厂,谓锅炉的上水门位置因系“利用旧上水门模型”,拟“稍事变更”,并附上了《机车锅炉修正图一》。1943年6月中旬和6月底,民生机器厂又曾两次接到天府煤矿关于设计更改的通知,第二次涉及更改前管板眼的直径,但“是时管板眼子已钻妥,正待装铆”,于是“改孔增加钻工12工”,使工期延迟了4天。民生机器厂的制造技术欠缺和经验不足体现在:“原订8月8日完工之第1座锅炉,发现炉壳铆钉与炉通管相撞,须拆换铆钉约30只,延期7天”。第1座锅炉完工后,天府煤矿派员验收,要求“将汽包法兰拂平,出汽管加铜垫,开车凡而加钢圈”,遂又拖延数日[29]。民生机器厂初次制造机车锅炉即获得了成功。实际上,尽管先后有别,但民生机器厂是在同时制造3座锅炉,而第1座锅炉率先完成后,该厂便认为“图样上与制造上之一切问题既告解决,2、3两部当可顺利进行”。后来,装载了第2、3座锅炉的蒸汽机车分别于1943年12月14日和1944年1月17日试车,结果均运行良好。由此,民生机器厂掌握了制造蒸汽机车锅炉的能力,而装载了民生机器厂所制锅炉的国产机车担负了当时天府煤矿铁路运量的73%以上[27],为大后方缓解能源供应紧张问题作出了贡献。
公元 160 年前后,关羽出生在今河北运城。他的身材非常高大,面庞如大枣一样红润,一双丹凤眼,英俊潇洒;两条卧蚕眉,乌黑浓重,更显英姿,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美男子。十九岁之前关羽一直在运城做小生意,后来因为当地的盐商欺负老百姓,他实在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不料失手将盐商打死,之后就逃到河北涿()州,结识张飞,再遇刘备。三人亲若兄弟,金兰结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桃园三结义”。从此他就追随刘备,为匡复汉室南征北战。四十岁的时候,关羽被封为寿亭侯,四十九岁时又被封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
臭氧关节腔注射:患者取仰卧位,患侧膝关节常规皮肤消毒,铺无菌巾。以髌骨外上缘为进针点,1%利多卡因浸润麻醉,用7号针穿刺入关节腔内,若积液较多则先抽出积液,然后注入30 μg/mL的臭氧20 mL,每周注射1次,连续注射3次。
遂感六天魔王,引諸鬼衆,肆諸凶虋,傷害無辜,怨氣盤結,上衝太霄。(《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六,《中华道藏》30/573)
展会期间,林德(中国)叉车的精彩呈现,众多客户、合作伙伴纷至沓来,与林德就进一步携手推动科技创新与智能化、数字化、新能源转型升级,推进仓储物流发展,展开深入探讨。
四、总结:虚假繁荣还是能力积累?
战时民生机器厂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资产由1937年的47万元增为1944年的34909.6万元,厂房面积由4 400平方米扩为312 015平方米,设备由最初的不到10台增加到395台,职工人数也由战前的403人增至2 200人[7]。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企业,民生机器厂的技术能力也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不仅迅速实现了从修船到造船的过渡,而且学会了制造船上的核心部件,还发展出了制造机车锅炉和水轮发电机等复杂技术产品的能力。因此,民生机器厂在战时获得了全面的、实质性的发展。
民生机器厂的战时经历,是当时中国工业企业尤其是大后方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的一个缩影。[注]类似的企业还有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上海机器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和新中工程公司等。部分企业的案例可参考张柏春访问整理的《民国时期机电技术》[32]。对比战前与战时民生机器厂的发展,可以说战争确实加速了该厂技术能力的提升,使其由战前所处的低级产品市场进入高级产品市场,这与李斯特的理论是一致的。战争对民生机器厂产生了以下正面作用:其一,从供给层面看,战争促使东部地区的技术力量直接注入民生机器厂,使其人力资本积累意外地实现了扩充,奠定了战时技术发展的基础,即战争使东中部地区的先进生产力实现了空间上的横向转移。其二,从需求层面看,一方面,战时需求为民生机器厂提供了稳定的复杂技术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传统进口渠道被切断又使民生机器厂在这一市场上摆脱了国外先进厂商的竞争。民生机器厂既感知到了进入高级产品市场的信号激励,又不会因为产品受到挤压而萌生退意。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有利条件因战争而偶然地结合在一起,促使民生机器厂实现了在和平年代难以想像的跨越式发展。因此,与其说是具有破坏性的战争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还不如说战争改变了部分企业面对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条件,使要素流动趋向于促进特定企业的发展。
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战争带来的条件改善都具有偶然性,早在战时即有人指出大后方的工业化是不正常的或虚假的。赫克歇尔在分析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工业化时就持这种观点,并举战争结束后受战时环境保护的企业大量破产为例,反证战时工业发展是失败的[33]。民生机器厂在战争结束后,即遭遇周茂柏等去职、与恒顺机器厂联营结束、东部技术人员返乡和战时市场需求消失等打击,失去了战时的繁荣景象,员工减至1947年的800余人[7]。这似乎又印证了赫克歇尔的理论,而与李斯特相左。然而,李斯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战争对后发工业的保护机制在于战争所引起的隔离状态,而“在和平恢复以后,这种隔离状态如果能仍然继续一个时期,对这类工业将有很大好处”[1]。所谓的“隔离状态”,实际上就是指有利的供求条件。李斯特与赫克歇尔的区别在于,李斯特看到了演化具有时间性,工业企业的技术和制造能力积累需要较长的时间。民生机器厂在战时形成的能力,在战后确实有所保留,并能继续满足和平时期西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需求。[注]此外,重庆地区战前机械工业极端落后,战后至今却成长为装备工业重镇,其中不乏战时的积累,这是包括战争在内的历史偶然性因素给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留下的显著印迹[34]。因此,民生机器厂在战时的能力积累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但这种能力的稳固化同样受历史偶然性因素的左右。进一步说,既然战争这种偶然性因素只不过是通过改变市场条件而发挥正面激励作用,那么大可不必讴歌战争带来了发展,在和平时期采取适当的政策去改变市场条件,也能诱导同样的工业进步。
参考文献:
[1]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93.
[2] 琳达·维斯,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M].黄兆辉,廖志强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95.
[3] 翁文灏.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M]. 北京:中华书局,2009.540-543.
[4]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138-139.
[5] 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M].卞历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6] 张守广.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7] 凌耀伦.民生公司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50-372.
[8] 聂宝璋,朱荫贵.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上册)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75-376.
[9] 佚名.江南造船厂的回忆[J].新世界,1944,(5):44.
[10] 卢作孚.本公司是怎样筹备起来的[J].新世界,1934,(56):1.
[11] 张华.民生机器厂之现状及其将来[J].新世界,1934,(20):43-45.
[12] 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M].张逸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34.
[13] 佚名.后方最大的机器造船厂——民生机器厂[J].新世界,1944,(5):46-49.
[14] 民生机器厂廿一年度制造进款收入统计表[J].新世界,1933,(20).
[15] 杨锡蕃.民生机器厂二十一年度工作状况[J].新世界,1933,(20):37.
[16] 李劼人.民生机器厂一年来之概况[J].新世界,1934,(41):65-66.
[17] 民生实业公司事务所通知船字第108号[Z]. 重庆档案馆藏档0207-4-2201,1933.
[18] 严庆祥致李淇华、严庆瑞函[Z].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459-1-503,1930.
[19] 周茂柏.民生机器厂一年来扩充与整顿[J].新世界,1939,(4-5):42-44.
[20]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字第691号[Z].重庆档案馆藏档0207-1-1602,1938.
[21] 新船建造委员会会议录[Z]. 重庆档案馆藏档0207-4-0200,1938-1939.
[22] 民生机器厂建造民彝、民文两轮述略[Z].重庆档案馆藏档0067-2-73, 1940.
[23]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易家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91.
[24] Fukasaku,K.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War Japan: Mitsubishi Nagasaki Shipyard, 1884-1934[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1992.12.
[25] 民生机器厂文件 [Z].重庆档案馆藏档0207-1-22302, 1940.
[26] 民生机器厂民二第2973号[Z].重庆档案馆藏档0207-1-2510,1943.
[27] 天府煤矿矿厂.仿制蒸汽机车说明书[Z].重庆档案馆藏档0240-15-06900, 1944.
[28] 民生机器厂文件[Z].重庆市档案馆藏档0207-1-4570, 1943.
[29] 天府煤矿矿厂.天府字第9880号[Z].重庆档案馆藏档0240-14-03200, 1943.
[30] 富源水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卅四)富字第0403号文[Z].重庆档案馆藏档0207-7-2190, 1945.
[31] 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工程处龙机(卅一)字第7389号文[Z].重庆档案馆藏档0207-1-4060, 1942.
[32] 张柏春.民国时期机电技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2-93.
[33] Heckscher,E. The Continental System: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2.279.
[34] 民生机器厂致富源水力发电厂函[Z].重庆档案馆藏档0220-1-0184, 1946.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9)01-0020-08
收稿日期:2018-1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及资料整理”(14ZDB047)
作者简介:严 鹏(1984-),男,湖北武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E-mail:pengyan831@163.com
(责任编辑:孙艳)
[DOI]10.19654/j.cnki.cjwtyj.2019.01.003
[引用格式]严鹏.战争与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基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生机器厂演化的检验[J].财经问题研究,2019,(1):20-27.
标签:机器厂论文; 民生论文; 战时论文; 能力论文; 公司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及资料整理”(14ZDB047)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