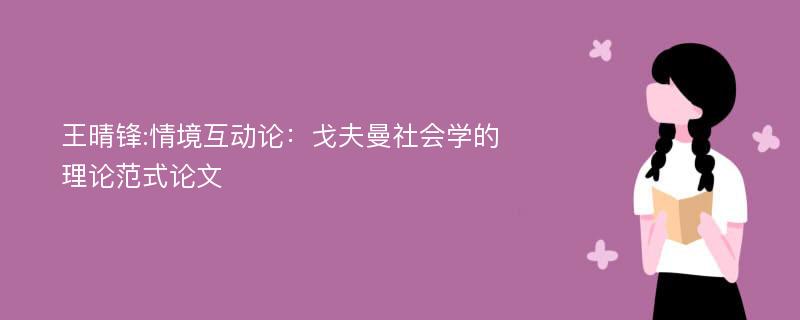
[摘 要]欧文·戈夫曼以微观互动为研究对象,而情境则为基本分析单元。纵观戈夫曼毕生的研究,他的社会理论体系可以冠之为“情境互动论”。戈夫曼对公共秩序的研究重点关注情境秩序,互动卷入的形态与分布体现出特定的情境结构。管控个体卷入配置的规则丛构成了情境礼仪,它包含着对情境参与者的依附、忠诚和尊重以及对包容性社交场合的承诺。戈夫曼以情境性的视角讨论精神病现象,认为精神病症状是一种情境失当。情境互动论是戈夫曼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他运用该理论探讨了拟剧论、污名、框架分析、性别设置以及会话分析等。情境互动既是研究主题,亦是研究内容,它是戈夫曼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与阐释范式。
[关键词]情境互动论;面对面互动;情境礼仪;互动仪式;情境秩序
与很多社会思想家一样,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也很难被确切地加以归类。尽管他以面对面互动作为研究对象,却不是符号互动论者;尽管他经常谈及结构,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结构功能主义者;尽管他剖析日常生活现象并解构习以为常之事物,却不是常人方法学者。本文认为,戈夫曼首先是一位互动论者,他强调微观的人际互动组织,聚焦于印象管理、面子工夫等互动技术。即使在抨击西方住院治疗制度并提出“全控机构”思想的《收容所》(1961)和更具一般化、形式化逻辑的《框架分析》(1974)等著作里,戈夫曼的阐述也是以人际互动研究为基础的。其次,戈夫曼社会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情境的重要性,并视之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因此,面对面互动和社会情境是戈夫曼的两大研究主题。鉴于此,本文提出的一个观点认为:戈夫曼的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情境互动论”(Situational Interactionism),以区别于“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因而,戈夫曼是一位“情境互动论者”,他探讨的是情境互动,不是社会互动;是情境化自我,不是社会化自我。情境互动论与符号互动论的核心区别在于:符号互动论没有将情境作为互动的核心变量加以探讨。本文从情境在戈夫曼社会学中的地位、情境卷入与互动秩序、情境礼仪与互动仪式以及情境失当等角度阐释情境互动理论。
一、情境在戈夫曼社会学中的地位
戈夫曼关于情境的观念深受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赫尔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等符号互动者和社会建构主义者彼得·伯格(Peter L.Berger)等人的影响。在戈夫曼的社会学里,“情境”是指这样一种整体性的空间环境,个体进入它内部的任何地方都成为(或即将成为)在场的聚集之成员。情境始于参与者发生相互监视之时,并一直延续到倒数第二位参与者离开[1](p18)。在《被忽略的情境》一文中,戈夫曼对社会情境的定义强调彼此监控和可进入性的特征,即它是“一种相互不断监控各种可能性的环境,在它的任何地方,个体会发现他自己可以接近所有‘在场’的其他人,而其他人也同样可以接近他”[2](p135)。十多年后,戈夫曼在《谈话形式》(1981)里对情境作了更加宽泛的定义,认为社会情境是“一种物理区域,在它里面的任何地方,两个或以上的个体彼此处于视觉与听觉的范围之内”[3](p84)。戈夫曼认为,当社会生活中使用“社会情境”的表述时,它并不是指各种沟通可能性的环境,而是指由在场的个体共同维持的小型社会系统和社会实在,或者是他们当下感知的正在发生的具有主体性意义的互动[1](p243)。互动参与者通过举止和外表时刻进行着信息交换,正是可广泛获得的沟通途径以及控制这种沟通而产生的规则将原本仅仅是物理性的区域转换成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实体场域,即“情境”[1](p154)。戈夫曼还将相对封闭、自我平衡的和自我终止的互依性活动循环称为“情境性活动系统”[4](p96),它区别于由个体单独完成的活动(无论是否有他人在场)和由诸多亚群体在不同空间中共同展演的“多重情境性”活动。
戈夫曼尤为强调面对面互动的情境特征。个体情境性呈现的最明显方式莫过于管理个人仪表或“个人门面”,也就是通过着装、化妆、发型以及其他外表修饰进行印象管理。情境不仅为个体交往提供了可能性,它本身亦形塑着互动的特征以及进程。在戈夫曼看来,情境是一种迪尔凯姆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它构成“自成一体的实在”[2](p133),应如同分析其他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那样研究情境自身的特性。社会情境是相互监控的场域,人们正是在社会情境中进行各种沟通与互动,他们利用表情、身体以及情境材料在更大的社会框架内调控自身,呈现社会性的自我肖像,向他人表明自己的社会身份以及当下的意图和感受。总之,社会情境是观察整个社会生活的“天然制高点”。社会情境中大量微不足道的细节能够反映出隶属与支配关系,它们不仅仅是社会序列和等级结构的描摹、象征、镜像或仪式性的肯定,这些表达构成了等级序列本身,它们既是影子又是实物[5](p6)。在《互动仪式》(1967)序言的最后,戈夫曼特意强调“不是人及其时刻,而是时刻及其人”[6](p3),这正是凸显出互动情境的重要性。但是,戈夫曼并不提倡“毫无约束的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m)”[7](p4),因为运用于特定社会情境的规则与期待几乎不可能完全在“当下”产生。戈夫曼承认,“任何一个进入社会情境的参与者都携带着之前与其他参与者——或者至少与他们类似的参与者——的交往而已经确立成型的个人经历;并且具有诸多共享的文化假定”[7](p4)。
戈夫曼区分了“情境中”(situated)和“情境性”(situational)两种不同的现实维度。“处于情境中”是指“发生在某个情境之物理边界内的任何事件”[1](p21)。在由两人构成的情境中,第二个人将他自身和已先在的他人完成的一切转换成“处于情境中的”活动,事实上,新的加入者将一个单独的个体和他自身转变成了聚集(gathering)。情境活动的某些要素可能发生于情境之外,即没有人或只有一个人在场。也就是说,这些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可以延绵至情境外,或者是情境外活动的延续,它们在情境内外会产生类似的效果。这些活动的构成要素也可能发生在情境内,但它们不是“关于情境的”或者“情境关联的”,它们仅是恰好发生在特定的情境里,但是事件本身的属性(其过程与结果)与该情境并无直接的关联性。这种现实构成是情境活动之“仅仅处于情境中”的维度,它的活动要素受到规范性管控,由此,我们得以谈论各种义务和冒犯。情境活动要素中的“情境性”维度不会发生于情境之外,它内在地依赖于情境内诸条件[1](p22)。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戈夫曼举例进行了对比。譬如,当遭遇持枪抢劫时,被害者的身体风险是“情境性的”,而财物损失则是“仅仅处于情境中的”。会话中话语传达的某些含义是“仅仅处于情境中的”,而通过身体表达的情绪赋予这些话语的渲染效果则是“情境性的”。又如,人们期待工具书阅览室里的读者进行的是查阅书籍及相关行为,而不是利用阅览室的空间做其他与查阅无关的、影响公共秩序的事情,这是行为的“情境性”维度;而个体具体选择阅读哪一本书、他的阅读技能、从阅读中的获益以及是否有人给他布置了阅读任务等等,这些都是其阅览室活动的“仅仅处于情境中”的要素。戈夫曼采取“情境性的”视角,并试图将“情境中的”维度转变成“情境性的”维度进行分析。例如,他明确表示关于框架分析的视角是“情境性的”[8](p8)。在探讨自我的领地时,戈夫曼也主要关注情境性的领地和自我中心主义的领地。
戈夫曼认为,互动情境系统是一种实体,在其中可观察到个体进行的各种卷入管控及其功能。戈夫曼视聚集为“社会单元的自然类别”[1](p198),支配情境内参与卷入的各种规则是聚集的一般性结构特征,这些规则责成个体将自身交付于情境性的彼此参与。情境现实中的忠实、阻碍、间距以及游离等是可进入式参与的基本问题。大致而言,戈夫曼探讨的情境性活动系统至少具有四个特征。首先,可进入性。通过向所有的在场者呈现出或维持可进入性和开放性,个体表明聚集本身已经赋予任何参与者都有获得被关注的权利和给予其他参与者以关注的义务。其次,情境忠实。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他都应对社交场合保持适当的敬意。再次,情境的紧密性与松散性。周末公园里的懒散、慵倦和葬礼上的肃穆、哀恸,这是个体面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情境呈现为一个从紧密(严格)到松散(宽松)的连续系统,个体根据不同的需要遵守不同的行为规则以及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情境及其社交场合的尊重。也可以用正式与非正式、拘谨与随意、彬彬有礼与不拘礼节等来表达情境规则系统的两端。在行为定义较为宽松的环境里,制度化的卷入结构会降低某些行为的不当性。最后,情境效应。社会情境是一种身居其中的个体彼此共同在场而形成的社会设置,观察者对情境的解读端赖于个体呈现出的外部特征以及施展出来的能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在实际的社会情境里,个体正是运用这些信息传递关于自身的叙事,并获知和习得他人的叙事,这便是情境性的社会效果。若将社会情境中琐碎的、微不足道的细节统合起来,将产生巨大的总体性效应。
二、互动卷入与情境秩序
公共秩序领域中的社会情境并不仅仅是遵守或破坏规则的场所,而且是“急速地经历整个微缩型司法程序的场景”[9](p107)。在这些场合中,居于核心的并不是遵从与违犯,而是各种补救性工作,尤其是提供纠正性的解读,以表明可能的冒犯者实际上与规则有着正当的关系。微观互动产生的冒犯主要与自我领地的宣称有关,并且这些宣称是对尊重的期待,因此相应的补救工作是仪式性的,旨在表达冒犯者对作为终极价值的被冒犯物之悔恨态度。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对违犯者的惩罚及其内疚等情感并不是参与者首要的关注点,他们共同关注的是如何继续维持互动。每一位参与者彼此之间都达成某种默契与心照不宣的合作,随时准备对违犯行为进行补救。补救性交换将反身性引入情境性互动系统,如果没有这种设置,公共生活将会无望地充塞着各种细微的领地侵犯及其裁定,自我领地的清晰划分也将难以实现[9](p108)。
制造故意性会计信息失真的行为,就其萌芽状态时,涉及的人数较少,易于控制;如果任其自流且形成规模,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这就使得那些原来就参与会计造假的人更变本加厉。当会计故意性信息失真现象频频出现后,信用将不复存在。
与其他社会秩序类型不同,互动秩序包含的卷入义务具有(或需要)非理性的、受情感驱使的成分[6](p115)。个体有义务保持自然的参与卷入,当他无法维持互动位置或执行特定的互动角色时,其他共同参与者会提供援救以恢复仪式秩序。也就是说,个体不仅自身必须保持适当地卷入,而且也必须适时采取行动以确保他人的适度卷入。这是一种交互式支持的共同卷入。戈夫曼认为,即使在不属于社会情境的状况下,也可能产生情境性行为。因此,为了防止出现无意的冒犯而带来的尴尬,如令人猝不及防地突然闯入某领地,个体即使在独处的时候,也会保持他的“在场性”或“呈现性”[1](p41)。例如,如厕者通常会故意地发出干咳声,即使他无法判断是否有人进来,以表明他正在厕所的隔间内,或者表明他不想听到或见到某些事情和行为。在日常的互动过程中,有些行为被定义为附属性的、次要的,即“附属性卷入”,它们在情境中不会被完全禁止,因而可能对义务性行为构成潜在的威胁。情境中的附属性卷入亦具有历史变迁性、文化异质性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因此,一个孩子被允许的附属性卷入或次要举止,诸如在公共场所吮拇指、舔吸管、吹泡泡糖等,倘若这些举止同样发生在精神病院里的成年人身上,那么它们会被认为“症状性”的表征形式。另一方面,当支配性卷入对情境中的个体及其自我控制构成威胁时,个体会发起附属性卷入以彰显他是情境的掌控者。
戈夫曼用于分析互动系统的总体性思想框架是微观的结构功能主义,他探讨情境礼仪的结构与功能,但是填充该框架的材料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行为细节。不同类型的情境礼仪和互动规则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例如,互动参与者遵守进入边界性区域的规则并尊重其边界范围,这体现出对聚集本身的尊重;对外部关注、“玄秘”卷入和各种类型的“离场”等的制止性规则确保个体不会专注或沉溺于情境外的事物;对不符合场景的主要卷入或过度投入次要卷入的制止性规则使个体不会过于分离性地陷于自我指涉;对多重卷入的管控同样规范着情境中的小群体行为;诸如此类。总之,为了限制个体的情境外卷入和情境内疏离,互动参与者必须表明他留意和专注着由整个情境所共同维系的社会生活系统。个体通过各种微观的方式,如身体面朝其他参与者、抑制生物性释放、时刻检视卷入强度、克制过度卷入情境性任务等,以表明他在情境中正处于适当的卷入状态,充分意识到情境中的聚集并以之作为首要关照对象。
图3为热解不同质量浓度(简称浓度)重镁水溶液所得产物的XRD图,图4为热解不同浓度Mg(HCO3)2溶液所得产物的SEM图。
如果参与卷入难以持续,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是个体主动离开互动系统,即情境撤离;另一种情况是出现情境崩溃,这时会产生愤怒、窘迫和尴尬等各种负感经验。个体也有可能出现“过度卷入情境”的状况。然而在戈夫曼看来,这种表面上的“过度卷入”恰恰是卷入不足的表现,因为行动者过于依赖与情境性的主要卷入相关的选择性象征符号,也就是说,符号和标识僭越了真实的情感和实际的行动。而“情境穷尽”则是指“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参与”,也即情境中的所有人都聚焦于同一个关注点,这时再也没有其他主要卷入活动,但可能会伴随着诸多次要卷入和附属性卷入,但它们不足以对支配性卷入构成危险。这是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点之后,面对面参与或情境的性质会发生变化,也就是情境的“再结构化”,它从复焦式情境参与转化为单焦式情境参与,此时发生的行为和言语针对的是整个情境。当生活中出现的某些紧急情况、意外或危机引起个体全神贯注于情境性活动时,该事件本身可能会掩饰原本可能是情境性的违犯行为,并为之开脱。例如,行人在泥泞的路上摔了一跤,他可能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迅速站起来,稍作整顿之后继续前行,以此表明他并没有完全投入于该失态行为,而仍然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情境礼仪。这便是“情境性脱卷”。因此,通过对情境化卷入进行调适,它表达的可能并不是卷入本身,而是个体对情境的依附感和归属感产生的尊重和敬意[1](p196)。
三、情境礼仪与互动仪式
互动规则管控着情境中个体卷入的配置,这种配置使个体必须恰当地处理诸如主要卷入、隐蔽卷入、自主卷入、共同卷入以及脱卷边界等。在他人在场的情境中,个体受到特定规则丛的引导和支配,这些规则丛便是情境礼仪[1](p24)。面对面互动的微小社会系统,即情境性聚集,由符合情境礼仪规范的各种行为构成。情境礼仪包含着对情境参与者的依附、忠诚和尊重以及对包容性社交场合的承诺,如果参与者未能遵循或违犯这种仪态和风度,将被视为对情境本身及其他参与者的疏远、脱离和敌意。情境礼仪赋予由聚集维持的共同社会生活以具体的形态,并且将聚集本身从仅仅是集合在一起的在场个体转换成类似于小群体的、自主性的社会实在。
戈夫曼从两个分析性的角度来探讨情境礼仪:非焦点式互动和焦点式互动。前者关注个体之间仅是基于同一情境中的共同在场而如何进行沟通;后者关注集合在一起的特定个体彼此给予“沟通许可”(communication license),并维持某种类型的共同活动,这种共同活动将情境中在场的其他人排除在外[1](p83)。戈夫曼阐述了情境礼仪和举止得体的一般性要素。特定情境中的个体需要克制自我,并表明有能力应付在他面前发生的任何面对面互动。这种在情境中自我控制的警戒与机敏(规训化的身体)可能意味着抑制或隐藏个体在其他情境中被期望展现的能力和角色。无论个体的其他关注点如何,即他“处于情境中”的兴趣如何,他必须投入于情境活动并保持这种状态直到他离开,也就是说,他必须保持“互动紧张”[1](p25)。戈夫曼认为,即使是在缺乏实际物理边界的情况下,也存在“惯例性的情境闭合”[1](p151)。因此,我们不能随便往别人家的窗户里张望,即使是进入敞开着门的房间也要象征性地敲一下门,以表明正式进入并请求得到允许。在某些场合下,自言自语是被容忍的,如当个体表现笨拙时,他可能会咒骂自己,以向他人表明这种无能或冒犯行为连他自己都无法接受,并且表明这并非他一贯的风格,从而挽回失去的脸面。
精神病学家在这些失当行为上投入大量的精力,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研究这些行为所需要的定位和观察技巧,对其进行详尽的描述,设法理解它们对病人的意义并且获得授权在学术出版物中对其进行讨论——这种授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些不当行为大多是琐碎的、令人难堪的,或者是杂乱的[1](p3)。
任何社会必须动员和组织其成员,使之成为日常接触中能够自我管控的参与者,这其中的一种重要组织方式是仪式。在以仪式作为组织原则的社会系统里,互动参与者被教导“要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具有依附于自我的感受和通过面子表达的自我,有自豪感、荣誉感和尊严,懂得机智圆通和镇定自若”[6](p44)。在戈夫曼看来,经过充分社会化的个体是“仪式性雅致的客体”,[6](p31)他能够并愿意遵守社会互动的基本规则。为了保全自身与他人的面子,参与者之间还会默契地相互配合。无论个体在社会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会通过“无视、将信将疑、幻想和合理化”等方式将自身与特定的情境隔离开来。个体还会通过他人适当的支持进行行为和观念的调适,从而相信自己就是想成为的人[6](p43)。总之,戈夫曼认为,仪式秩序的主要原则“不是公正,而是面子”[6](p44)。社会生活是整齐有序的,个体主动远离和规避那些不需要他的或者不受欢迎的甚至可能遭歧视的人、事件和场所,他们恪守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并且相互合作以保全彼此的脸面。
戈夫曼对公共秩序的研究重点关注那些彼此在身体上可接近的陌生人或仅仅是点头之交的人们构成的情境,此类情境中的秩序才是核心问题。个体的行为片段锚定于其周围的环境之中,每一位参与者面向在地的(local)和当下的情境,并且这种情境随着参与者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日常互动中的个体具有情境分辨能力,他们不断地通过各种生理感知警觉地观察、读取情境信息并随时进行监控。在惯例性的、秩序井然的情境里,个体可以继续着他的“例行公事”,此时事物的表象对他而言是“自然的”或“正常的”。“正常的表象”意味着可以心安理得地从事当下的活动,个体只需对环境的稳定性状况稍加关注即可。他们能够根据当下的情境信息预料即将发生的事情,可以不假思索地进行行动展演。此时,警惕仅是一种次要的投入,并且可以忽略情境中偶尔出现的警告信号。然而,当个体突然感知到某些事物变得不自然或出现失范的时候,也即当即时的情境出现了危机时,他必须全力以赴地去应对,这时犹如平稳运转的机器突然开足马力进入高速挡,需调动所有的注意力并采取适应性行动。个体并不需要在每一个场合都保持这种反应态势,否则他将负重不堪,连普通的基本活动也将难以为继。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只需通过寻常的规范性管控就能够维持正常的表象、继续进行日常活动。
也就是说,在理念上,个体即时性的情境结构可以分成两个世界:一个可以很容易地维持控制,另一个则需要完全投入自我保护性行动;一个是平静安宁的,另一个则是紧张冲突的。个体秘密地监视和戒备各种警戒性符号,以便及时作出符合情境的反应策略。但是,现实中个体对情境的关注和反应并非如此断然分明,平静祥和的情境可能离剧烈动荡和骚乱性的情境仅一步之遥。个体的客观世界呈连续谱状态分布,即从自由自在地与自我和他人相处直到人人自危、高度紧张,个体所处的情境可能是该连续谱中的某个位置。戈夫曼区分了警告的可能性及其结构可行性,他试图探究那些安全而平静的情境如何被扰乱和破坏,因为这能够更好地了解个体客观世界的结构。情境中的个体行为受关于卷入的社会价值或规范的约制,这些规定包含了卷入的强度、主要卷入与次要卷入的分配以及将个体带入某种程度的参与之倾向。个体的卷入会呈现出类型化的配置,从作为整体的情境视角来看,可以将每位参与者的卷入配置与其他人维持的卷入配置相联系,通过这种方式统合而成的模式被称为“情境的卷入结构”[1](p193)。卷入的形态与分布体现出特定的情境结构,反过来,情境的卷入结构可以作为指涉框架描述某个场合或交遇(encoun⁃ter)中的个体行为。
一是部分报账人员不熟悉财务报销业务处理流程,容易出现业务分类错误;报销总量庞大,报账排队的等待时间过长,甚至部分报账人员在在经历各部门签批手续后,仍无法在财务部门完成报账,因此,问题和意见集中在财务部门爆发。
四、情境失当与精神病行为
精神病学对情境失当性的研究主要关注情境触犯者,而不是被触犯的规范和社会。对精神病人而言,情境失当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情境失当”这一概念工具,戈夫曼阐释了精神病人可理解的行为,即特定情境下的行为礼仪和策略选择,以表达个体与在场他人或社会设置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那些“外行的精神病学家”所无法认识到的。在戈夫曼看来,仅凭情境行为本身无法判断和区别某种“症状”是由于个体的器质性障碍还是功能性障碍导致的。精神病学通常假定器质性精神病人的行为失当完全是症状性的,然而,它没有解释这种基于心理的疾病如何能够引发与器质性障碍相似的一切行为类型[1](p237)。因此,戈夫曼认为器质性行为与功能性行为的一致性仍有待商榷。无论偏常行为是基于何种原因(社会的抑或机体性的),无论它是否为症状性的,只有当它违犯了既定情境中的特定规则丛时,它才会被感知和定义为“偏常行为”。跨文化的医学认知实践可能被人误解,以为精神病是一种“文化无涉的”或不受文化制约的病症。与之相反,戈夫曼认为之所以在跨区域的比较研究中能够发现这些类似的“病人症状”,这正是由于许多不同文化的社会聚集中具有基本相似的情境礼仪规则。戈夫曼由此探讨了情境失当的症状性意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情境失当行为都被视为精神病的表征,精神病症状是冒犯者没有侥幸逃脱的情境性冒犯,他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既无法强迫他人接受冒犯,也无法让他人相信其他的解释[1](p240)。在精神病人被机构化的过程中,医生与病人家属(串通者或勾结者)之间会形成共谋性的联合,以遏制第三方(病人)的情境定义,或者说秘密操控其情境定义。同时,戈夫曼认为,个体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情境性失当行为表达对在场他人或社会设置的不满、敌意甚至进行攻击。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我国花卉生产体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已经成为世界花卉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国内花卉产业起步相对较晚,同时基础设施缺乏完善性,故此园林花卉在发展期间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具体如下:
情境要求具有道德特征,互动参与者有义务维持这些要求。作为日常互动之主体的个体须熟悉情境义务,否则可能出现各种情境失当。通过对公共场所的行为进行情境分析,戈夫曼试图表明不能以某种道德规范作为手段将世界二元划分为相互对立的维护者和冒犯者。他以情境互动论的视角讨论越轨与失范现象,认为污名并非对规范的偏离和逾越,而是个体与社会之间情境互动的结果。在《公共场所的行为》的开篇,戈夫曼即以精神病学家的研究作为破题,认为精神病症状是一种“情境失当”[9](p355)。在他看来,精神病学家诊断精神障碍的典型方法是引证病人的情境失当行为,这些特殊类型的不当行为被认为是提供了“精神病”的明显症状:
精神病学家对症状性和非症状性的行为失当之区分也促使我们反思镶嵌在社会中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使我们以类似的二元对立的方式划分任何情境失当的行为,罔顾其内在的关联性,而制度化的设置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对立的趋势。在《公共场所的行为》的最后论及“情境失当的症状性意义”时,戈夫曼对美国当时的精神病学诊断和治疗模式提出了质疑:“我们需要考虑情境冒犯者是病态的;有时毫无疑问可以证明他们是不正常的,但是即便如此,这种论证可能性不应该成为我们如此看待他们的理由。”[1](p235)情境分析为重新审视精神病学及其治疗实践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它强调医学模型的社会管控功能。在戈夫曼看来,精神病学和精神病患者的住院治疗制度与其说是对病人本身的治疗,不如说是社会对遭受威胁的礼仪进行纠正。然而,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社会自我治疗,不仅提供治疗的社会机构(精神病院)负荷沉重,而且作为冒犯者的精神病人经历了各种“非人”的遭遇,他们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与市民生活脱位、与亲友疏离、在严密的组织和监控下不得不过的屈辱生活以及出院后的永久性污名等。总之,戈夫曼认为精神疾病更多地与公共秩序的结构有关,它不是本质性的精神错乱,各种形式的非机体性“功能”障碍并非病态,而是情境冒犯的类型。然而,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性条件下,它们却被归罪和污名化为精神疾病而加以收治、施以惩罚。
五、总结与讨论
情境与互动是戈夫曼社会学的两大重要主题。本文将戈夫曼的社会理论体系概括为“情境互动论”,它强调自我、行为和秩序的情境性,同时又强调微观的人际互动,尤其是各种精致的互动技术。情境互动论基本涵括了戈夫曼社会学的内涵,也表明了他的社会研究方法。倘若从情境互动论的角度讨论戈夫曼的整个社会学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将它置于实证主义范式下进行考察,那么个体主义与社会决定论、行动与结构、场景与能动性之间的传统张力与不可调和性可以迎刃而解。另一方面,尽管戈夫曼强调情境意识,尤其是行动者对情境的感知与定义,但他并不是情境决定论者。行动确实嵌入于情境之中,但依然存在超情境的管控机制,行动者之间的认知期待以及共享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情境。
以“情境互动论”命名戈夫曼的社会学,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基本涵括戈夫曼所有论著的主题和内容,避免了以“拟剧论”这样的单一标签来狭隘地定义和概括戈夫曼一生的研究。其次,它概括了戈夫曼一以贯之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戈夫曼是在情境互动论的范式下研究拟剧论、框架分析以及性别、会话等。再次,情境与互动是戈夫曼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关键主题,而情境互动论也是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阐释范式。最后,它突显出互动研究、甚至社会研究中“情境”的重要性,情境之于戈夫曼犹如文化之于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情境不只是分析性的背景、环境或外部变量,它是影响面对面互动模式的自成一体的社会事实。“情境互动论”这一观念的提出也能够化解戈夫曼在符号互动论中的尴尬处境。符号互动论聚焦于互动却没有发展出关于符号的理论体系,而戈夫曼的情境互动论则兼顾了“情境”与“互动”。情境互动论与其他互动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许多互动论者并不认为互动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秩序,他们通常研究互动中的制度再生产,或者通过互动实现的制度再生产[10](p145)。而戈夫曼认为存在自成一体的互动秩序。
因为在设计时便考虑到“多用途”,所以通过系列化发展和改进改型,“鲲龙”AG-600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加改装必要的设备,满足执行岛礁补给投送、海上缉私与安全保障、海上执法与维权等多任务需要。
情境互动论实质上阐明了冲突与共识、失范与规范是如何得以共存的。情境化的互动系统通过转换规则与更广泛的社会相联系,因此,它不是像帕森斯的模式变量那样聚焦于系统内交换。戈夫曼社会学中的情境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情境抽样,而不是个体抽样。由此,情境互动论也可以成为民族志实践的理论基础。此外,对心理人类学家而言,情境互动论的贡献在于它否定了人类行为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假定[11](p17)。戈夫曼的情境阐释机制还影响了不少学者。例如,“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提出者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解释暴力时得出结论认为:导致产生暴力的是暴力情境,而不是暴力个体或暴力文化[p12]。最后需指出的是,虽然戈夫曼也采用了非西方社会中情境行为的文献,但他的论述主要适用于“美国中产阶级的行为”[1](p5),或者说,他的视角和立场是以美国的中产阶级白人为参照点的。
不久,那个一杭在医院里遇到的墨镜男匆匆进来,把一个皱巴巴的记事本和一个U盘双手递给范坚强。范坚强点了点头,那人出去了。范坚强翻开记事本,走到一杭面前,念了起来:“9月23日,早上发生了一起车祸……9月25日,有个穿警察制服的人来找我……9月27日,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来找我,……临走,给了我一万块钱。我请他放心,我绝不会出卖范老板……”范坚强抬头看了一眼一杭,说:“你看看,是这个记事本吧?”
参考文献:
[1]Erving Goffman.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J].New York:Free Press,1963.
[2]Erving Goffman.The Neglected Situation[J].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64,66(6).
[3]Erving Goffman.Forms of Talk[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
[4]Erving Goffman.Encounters: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M].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1.
[5]Erving Goffman.Gender Advertisements[M].New York:Harper&Row,1979.
[6]Erving Goffman.Interaction Ritual: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M].New York:Pantheon,1967.
[7]Erving Goffman.“The Interaction Order.”[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1).
[8]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New York:Harper&Row,1974.
[9]Erving Goffman.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M].New York:Basic Books,1971.
[10]Anne Warfield Rawls.The Interaction Order Sui Generis:Goffman’s Contribution to Social Theory.[J].Sociological Theory 1987,5(2).
[11]Philip Bock.The Importance of Erving Goffman to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J].Ethos 1988,16(1).
[12][美]兰德尔·柯林斯.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M].刘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1.020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1-0138-07
作者简介:王晴锋(1982—),男,浙江绍兴人,社会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 幸
标签:情境论文; 互动论文; 个体论文; 社会论文; 参与者论文; 《理论月刊》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