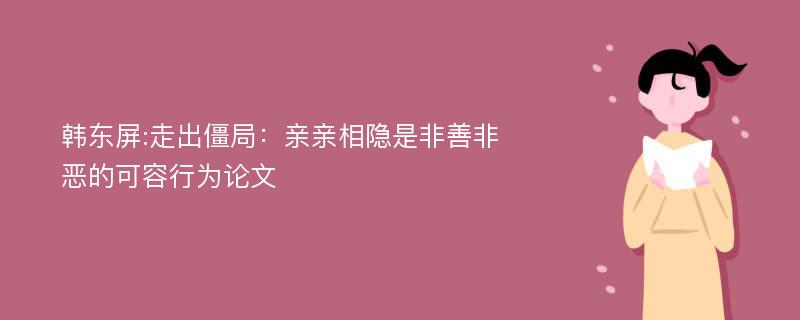
摘 要:我国学界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很久,却仍未解决。关键在于,对亲亲相隐行为的价值定性要准确。不仅否定派对亲亲相隐是恶的不义行为的论证不能成立,肯定派对亲亲相隐是善的美德行为的论证也不能成立,这就需要另行定性。对行为在价值上的划分,道德不同于制度的两分法,即不当与正当的两分,而是四分法,即不当、守当、欠当和应当。据此分析,在知亲犯事情境中,助亲为虐属于恶的不当行为,大义灭亲属于善的应当行为,亲亲相隐则属于非善非恶的欠当行为。这里的“欠当”不是指行为违反了底线道德,而仅指行为没有响应道德中高线规范的倡导,达到“应当”的美德,因而亲亲相隐也就没有善恶可言。对这种行为,法律上自然不可入罪惩罚,道德上则默许之,既不谴责也不赞扬;对社会而言,亲亲相隐属于可容行为。
关键词:亲亲相隐;价值属性;恶善;非善非恶;欠当
由刘清平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引爆的亲亲相隐问题之争①,在我国理论界已经持续了17年之久,可问题至今依然存在。不论是报刊上的公开讨论,还是网群中的私下交流,都在时不时地进行,并且每每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亲亲相隐问题的含义已经不用多说,就是指在知亲犯事情境中,即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亲人做了不当之事(包括于法不当和于道德不当)时,如果隐瞒不报,社会该如何看待和处置?这一所指表明,亲亲相隐是一个现实性极强的问题,与个人实践和社会实践都密切相关。个人实践方面关乎陷于此情境中的当事人该如何选择行为,社会实践方面关乎社会公权如司法机关该怎么判定此类行为的性质,并为之预设何种社会规范,如立什么样的法。显然,这里无论是要说明该如何选择行为,还是要说明该预设何种社会规范,都需要有法理学和伦理学方面的充分论证为支持,这就使得该问题同时成为了一个具有学理性的问题。
正因亲亲相隐问题首先并主要是实践问题,而不是纯粹的学理性问题,所以与一般的学术争鸣的悬而不决也无伤大雅不同,这个问题的久拖不决绝不是什么好事,理论界应继续努力,尽早了断这一悬案。学界这些年参与亲亲相隐问题争鸣的人士众多,主要为哲学界和法学界的学者,其争论焦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为亲亲相隐这种行为的价值属性是什么?二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是否相互排斥?三为孔子、孟子和苏格拉底等谈过亲亲相隐话题的先哲,究竟对之持何态度?四为自古至今的中外法律都是怎么处置亲亲相隐的?显然,其中第一个焦点才是关键所在,因为只要我们能正确确定亲亲相隐行为的价值属性,就能知道该在道德和法律上如何处置它,继而也能推出大义灭亲行为的价值属性以及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究竟是什么关系,该如何处理。而先哲由于也会出错,其对亲亲相隐的态度就无关紧要。至于既往法律对亲亲相隐的有关认定,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判据,仍然有赖于对亲亲相隐的价值定性是否准确。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策略是不讨论后三个焦点问题,只思考第一个焦点问题,并在得出结论时顺势解决同样具有实践紧迫性的第二个焦点问题。
在对亲亲相隐的价值定性上,人们经过讨论大致形成的是两种相互反对的派别,一是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的否定派,认为亲亲相隐是恶行,应受法律惩罚。属于这一派的学者主要有刘清平、邓晓芒、黄裕生等;一是对亲亲相隐持肯定态度的肯定派,认为亲亲相隐是善举,不仅应当享受法律豁免,还应赞赏鼓励。属于这一派的学者主要为郭齐勇、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刘水静等。这两派观点的论证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导致了亲亲相隐问题争执不下和久拖不决。若想打破这种僵局,自然也应从弄清两派究竟有何不妥开始。
一、否定派的观点和问题
否定派认为亲亲相隐为恶行的观点,主要由否定派的首要代表,也是率先向亲亲相隐行为发难的刘清平论证的,其他否定派人士都支持其观点。刘清平对亲亲相隐的否定有两个层面的论证。一是特定层面的论证。这就是当亲亲相隐的行为者是如舜这样的“公职人员”,其行为方式是对自己犯罪父亲的“窃负而逃”和对自己犯罪弟弟的“封象有庳”时,就是“无可置疑的腐败行为”,因为前者属于利用职权“徇情枉法”,后者属于利用职权“任人唯亲”①。一是一般层面的论证。即当亲亲相隐的行为者是没有特定身份的一般人时,如《论语》中“攘羊案例”的“子为父隐”时,该行为与腐败虽然已经扯不上直接关系,但本质上还是属于恶行。因为“不可坑害人”是“大多数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共识”,也是人的“正义感”所在。根据这种共识,不仅“攘人之羊”的父亲干的是坑害人的事,并且“努力隐瞒父亲的犯罪行为,乃至设法帮助父亲秘密潜逃”的儿子所干的事,也会造成坑害人的后果。这就是,一方面隐而不报等于拒绝帮助受害者及其亲属,这就“导致他们难以找回自己正当拥有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通过隐瞒父亲罪行、帮助父亲潜逃的举动,使父亲摆脱了由于从事不义行为理应受到的道德谴责和法律惩罚,最终为父亲谋取了保存名声、逍遥法外的不正当私利……不但进一步坑害了受害者,而且还破坏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1]。邓晓芒也认为,亲亲相隐是把家庭关系凌驾于法律之上,把亲情看得比正义更重要,具有“冲击法律、侵犯人权、解构制度、导致腐败的消极作用”[2]b58。
在上述观点的论证中,否定派将特定人物的亲亲相隐,即作为公职人员的舜的“窃负而逃”和“封象有庳”指认为腐败行为,在假定当时事实确实如此的前提下,是可以得到认同的(道理后面说);将“不可坑害人”作为正义的界限,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否定派关于亲亲相隐行为也是坑害人的恶行的论证,不能令人信服。
亲亲相隐实际上存在消极亲亲相隐和积极亲亲相隐之分。消极亲亲相隐只是隐而不报,其他一概不做,既不帮助犯事亲人隐匿犯事证据,也不帮助其逃匿。积极亲亲相隐则不同,不仅隐而不报,还做帮助犯事亲人逃匿追捕或隐匿犯事证据的事情。然而,否定派在对亲亲相隐作不义论证时却没有加以区分,完全以积极亲亲相隐说事。因刘清平为攘羊案例中子为父隐是坑害人行为的论证所预设的具体前提,就是儿子“设法遮蔽父亲的邪恶举动,乃至帮助父亲潜逃”的积极亲亲相隐,这就在方法上犯了从特殊推定一般的以偏概全的错误。先不管否定派关于积极亲亲相隐是不义行为的论证是否成立,这里至少可以判定,仅仅是隐而不报的消极亲亲相隐,既不等同于“默许”家人坑害人的态度,也肯定不属于坑害人的行为。因为,隐而不报也完全可以是在否定亲人犯事行为的态度下所做的行为选择。此其一。其二,隐而不报并没有使受害者增加新的损失。如果这里我们不是如此认定,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目睹有人作恶而未报的在场者,都将被视为做了坑害人的事。甚至,那种受到当事恶人威胁而不敢举报的在场者,也要被认为是做了坑害人的事。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也都要为之受到社会的惩罚。但这个推导结论,显然在社会历史中从未变成过现实,这就足以说明,它实际上是被古往今来的国家或人们所共同否认并排斥的观点和做法。同时,我相信否定派的诸位,也不会对之表示赞同。
以郭齐勇为代表的肯定派不但强烈反对否定派对亲亲相隐的不义定性,而且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行为。郭齐勇说亲亲相隐或父子互隐“是一切正面价值的源头”,“在孔子的时代,父子互隐恰恰是正义、正直、诚实的具体内涵与意义之一”[3]。龚建平说亲亲相隐“是君子自美而美人之美的处世方式”[4]。并且两人还共同认为“亲亲相隐”是人类“共通具有的普世性伦理”[5]。肯定派之所以说亲亲相隐是美德,在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亲情和‘四端之心’等道德情感,正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的发源地”[3]。并且,“‘亲亲’的人格成长和发展,有利于‘仁民’的人格成长和发展;‘齐家’能力的增长,也可以促进治国能力的增长”[6]。因此,“亲亲相隐不为罪有利于维系整个社会道德体系正常发展,并在协调人际关系、梳理人伦道德,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7]。也就是说,从个人、家庭、国家的角度来看,亲亲相隐有利于修齐治平[8]。
但是,能否提高破案率这一点根本不能成为立法的决定性因素,最多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参考因素。因为立法的目的从来都不是破案率,而是对代表社会正常秩序的社会公正的维护。社会公正作为立法的首要价值,要远大于破案率的价值。因此,倘若亲亲相隐不利于社会公正,那么法律对它的禁惩,即便无助于提高相关破案率也不能由此放弃。何况,效益论证者“对提高破案率很少有帮助”的这个用语已然表明,他们还是承认这一法律规定对提高破案率并非绝对没有帮助。还有,效益论证所做的所谓“经济学分析”也完全不能成立。因为这个需要以一系列变量因素为前提条件的复杂分析及逻辑推导过程存在诸多破绽。只要其中一个前提有问题,就足以使整个推论毁于一旦。例如,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说,当公安机关和犯事者亲属信息不对称时,犯事者亲属对犯事亲属被抓获的“预期破案率通常低于实际破案率”。因为他“信息匮乏,再加上不希望甲(指犯事亲属——笔者注)被抓获的心理倾向和通常普遍存在的侥幸心态”,“仍然会认为公安机关根本不可能发现甲作案”。但是,将“不希望”和“侥幸心态”这种主观愿望作为犯事者亲属计算破案率的根据,纯属非理性的掩耳盗铃,只有傻瓜才会这样想。因而,此时犯事亲属的预期破案率究竟是低于还是高于实际破案率,在没有任何客观根据的情况下,实际上只能是各占百分之五十的概率。由于每个正常社会的破案率实际上都会超过百分之五十很多,因而犯事者亲属即便所预期的破案率比实际破案率低,一般仍然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于是会不敢为亲者隐[9]。
二、肯定派的观点和问题
其实,即便是对积极亲亲相隐,以“坑害人”相指责也是牵强的,因为在知亲犯事情境中,无论是帮助犯事亲人隐匿犯事证据,还是帮助犯事亲人逃匿,都直接属于在做有益犯事亲人之事,即增加其利益。而增加一个人的利益,并不必然等于损害另一个人的利益。如果由于认定帮助犯事亲人的行为,在客观上间接不利于受害人及时找回损失而将其定性为坑害人,那就还是会由此推定隐而不报的消极亲亲相隐者也属于坑害人,因为它同样不利于受害人及时找回损失。于是,这就又要回到那种需要惩罚所有知恶未报的在场者这种不可取的结论。实际上,很多行为在客观上都会间接不利于某个人或某些人,如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竞争谋利行为,客观上都会有优胜者间接损害失败者之利益的效果,因为市场份额、社会财富总量、好的职位之类,从来都不是无限多的,这就必然存在胜者多得而败者就会少得的普遍性因果关系。可我们能由此说这些竞争获胜行为都是坑害人的行为吗?这就说明,判定一种行为的价值属性,一般只能以它的直接效果进行价值定性,而不可根据它的间接效果。综上可知,否定派关于特定亲亲相隐是恶行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而关于一般性亲亲相隐是恶行或不义行为的观点及论证,是不能成立的。
经过以上两个部分的论述,现在得出结论:在对亲亲相隐的价值定性上,一方面,否定派关于非特定含义的亲亲相隐是恶的不义行为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另一方面,肯定派关于亲亲相隐是美德行为和无罪行为的立法论证,也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对亲亲相隐还存在其他价值定性的可能吗?如果存在,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这个回答将基于道德对行为的价值划分给出。之所以要选择“基于道德”给答案,不仅在于目前法律方面关于亲亲相隐不为罪的立法论证不能成立,更在于法律乃至所有制度的价值都不是自足的,而是要以道德为价值来源和价值基础,并都要与该社会的主流道德的价值取向保持一致[12]。因此,我们本来就应该首先从道德的层面开始分析亲亲相隐行为的价值。
从性质上说,亲亲相隐这类特殊性的爱亲行为与一般性的爱亲行为也存在质差。这就是,后者没有包含“不当”的因素,前者则有“不当”的因素在内,因为亲亲相隐是为做了不当之事的亲人进行隐瞒,而一般的爱亲则没有亲人做了不当之事这一前提。一般情况下,当发现陌生人做坏事时,我们都知道,及时阻止或举报他是善行义举,而帮其隐瞒则肯定不是善行义举。现在,同样的情境中,只不过是将做坏事的陌生人换成自己的亲人,同样的隐瞒怎么就会立刻出现质的跳跃,变为善行义举,即肯定派所说的美德行为?这其中的道理何在?没人否认,凡是美德行为都属于值得社会加以鼓励和提倡的行为。如果亲亲相隐也被归为美德行为,就也会在被鼓励和提倡之列。那么,在知亲犯事的情境中,是不是越能有效地帮助犯事亲人隐瞒坏事和逃避社会惩罚的人,就越有美德,越该表彰?这自然只能是一个十分荒唐的谬论!因为这种激励的结果,只能是让大家比谁更会帮助恶人对抗社会公正。因此,亲亲相隐这类性质的爱亲行为,根本就不配称美德行为,也不可能成为“一切正面价值的源头”。
娱乐会带来更自我、更封闭的满足感。那是不是幸福的巅峰?我不知道。但如果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以后,我们对于幸福的定义来看的话,这似乎是幸福的巅峰。
肯定派除了往上对亲亲相隐作美德论证外,还从下为亲亲相隐作合法论证。就是通过全面考据中西法律史,证明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法律都有容许亲亲相隐或“亲亲相隐不为罪”的法律规定。然而,即便全部中外法律史都是支持亲亲相隐的规定,也不能证明我们现在的法律也应该支持亲亲相隐。因为不仅从“是”并不能直接推出“应当”,而且谁也不能保证以往的传统做法必然都对。因此,这里的要害不在于以往有多少支持亲亲相隐的法律规定,而在于支持亲亲相隐的既有立法理由能否成立。幸好肯定派中还有人记得要提供立法理由,基本上为两类,即法理论证和天理论证。法理论证包括必要性原则论证、可能预期性理论论证、社会效益论证和经济效益论证。由于社会效益论证同样是将一般爱亲的社会效益,偷换成亲亲相隐的社会效益而不能成立,可能预期性立论论证实质属于第二类的天理论证,因而法理论证方面现在只需分析剩下的必要性原则论证和经济效益论证。必要性原则是指,若要将某种行为立法入罪,必须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由于法律“即使对亲亲相隐的行为给予了一定的处罚,也不能杜绝此类行为的发生”,“就不应该再将相隐的行为列入处罚的范围”。问题是哪一种惩罚某种犯罪的法律能完全杜绝这种犯罪的发生?所以这个立论明显不行。效益论证是运用经济分析法,得出法律容忍亲亲相隐的效果优于不容忍亲亲相隐的效果,因为不容忍亲亲相隐的法律规定,“对提高破案率很少有帮助”[9]。
MCN-nIC与MCN-IC两组患者糖尿病和急性胰腺炎病史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MCN-IC组患者腹痛和食欲减退发生率显著高于MCN-nI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1)。
然而,天理论证的立法理由似是而非,实经不起推敲。所谓“我们天性中最深刻、最合理的原则”就是指亲人相爱的原则或天理,这种源自家庭关系的原则,虽可说“构成了我们文明社会的基础”,但它显然不是文明社会的唯一基础,并且更不是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它在重要性上,显然比不过社会公正原则。相反,如果颠倒这两个原则的重要性排序,将爱亲原则置于公正原则之上,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变成每个家族反对每个家族的激烈战场。因此,只要亲亲相隐是属于不利于社会公正的行为,那么这时那个维护家庭关系的“伟大原则”就得让位于维护社会公正的更为伟大的原则。由此可知,立法在毫不考虑亲亲相隐行为是不是违背其他社会原则的情况下,仅凭一个爱亲原则就支持它,至少存在不完全论证的缺陷。此其一。其二,根据这套立法理由,大义灭亲反将被推定为恶行,因为它就属于“破坏或削弱这些保护夫妻间关系的伟大原则”或“天理”的行为。既然如此,大义灭亲就需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可是,法律应该惩罚这种实质上具有舍己为人的大义灭亲行为吗?显然,只有坑害人的行为才属于恶,才需要被惩罚,而大义灭亲行为不仅是谁的利益都没损害,反而牺牲自己的亲情以维护社会公正,这样的行为何恶之有?显然,一个会引出荒谬结论的立法理由,本身也一定是荒谬的。所以,即便“法律是低层次的”,也不意味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服从于爱亲这一所谓的“天理”或“伟大原则”。
其中,Xi,t表示第i城市在t期的地价、房价和物价;σt表示为n个样本城市在t期的地价、房价和物价的标准差。若σt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则表明地价、房价和物价存在σ收敛。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
效益论证不行,天理论证又如何?天理论证的基本逻辑是:出于父母子女之真情的亲亲相隐“是符合天理的,符合人性的……天理、人性、人情是高层次的,法律是低层次的,法律不能有悖人性、人情,更不能违背天理”[10]。这个逻辑还从国外找到了共鸣,这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阐述亲亲相隐之法律规定时的一段话:“这一规则是以我们天性中最深刻、最合理的原则为基础。这些原则源自我们的家庭关系,并且构成了我们文明社会的基础,它们对于那些为生活中最亲近、最珍贵的关系所联结在一起的人形成信赖关系至关重要。破坏或削弱这些保护夫妻间关系的伟大原则,将会破坏人类生活的最佳慰藉。”[11]
白酒品评是判断酒质优劣的重要检测技术,具有快速、准确的特点,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被分析仪器所替代[6]。由公司的2名国家评委和4名省评委组成原酒质量鉴评小组,对试验组和对照组的118个酒样进行品评分析,品评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使用清洁稻壳所产原酒具有醇厚干净,糠味、土腥味、涩味、霉味等异杂味小的共性特点,其质量普遍优于对照酒样,实验组原酒质量评分比对照组高11.64%。
三、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及解释
但是,肯定派在这里明显是搞错了一件事情,就是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种一般意义的爱亲行为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社会功效,也当成了亲亲相隐这种特殊意义的爱亲行为所具有的。可是,如果去掉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所有一般意义的爱亲内容,仅剩亲亲相隐这一点时,它还能有那些积极意义和社会功效吗?而被肯定派当作理论根据的传统儒学实际上也从无这样的意思,当年孟子只是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的开端,而没说亲亲相隐是仁义礼智的开端。
在对人的行为的价值划分上,法律、政策、纪律等制度,全是两分法,都是将行为分为正当和不当的两类,如法律的正当和不当就是合法和违法;政策的正当和不当就是合策和违策;纪律的正当和不当就是守纪和违纪。既然如此,从制度方面说,一个行为在价值上就存在两种可能,或是不当的或是正当的,而不可能既不是正当的,又不是不正当的。而道德对行为的价值划分则不是这样。表面看,道德好像也是两分法,是将行为分成了合乎道德的“正当行为”与不合乎道德的“不当行为”这两类。其实是四分法,是将行为的价值从低到高区分为四个层次,即不当、守当、欠当和应当。其中,不当行为属于恶行,应当行为属于善行,而守当行为和欠当行为则都是在善与恶之间的非善非恶的行为[13]96。正因道德对行为的价值划分是四分法,所以关于亲亲相隐的价值定性,在肯定派和否定派的两种定性之外,还存在其他可能。道德之所以能将人的行为做出四种层次的价值划分,在于社会规范中,道德规范与制度规范存在大的不同。所有制度规范作为对人行为的固定指令,在宽松度方面没有任何差异,全都是必行指令这一种形式。所谓必行指令,是指任何一条制度规范,不管其指令内容是要求行为人做什么还是禁止行为人不做什么,都必须得到行为人的严格遵守,这样其行为才具有正当性,否则就都属于违反制度的不当行为,都要受到惩罚。因而,由制度规范给人形成的义务,全都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讲的绝对义务。如不论是禁止坑蒙拐骗的法律规定,还是要求依法纳税的法律规定,都是行为人必须履行的绝对义务,不容一点儿通融。
而道德规范作为人的行为指令则不同,由于它在宽松度方面实际上存在低线规范和高线规范的差异,使得道德规范除了有必行指令之外,还有非必行指令。道德规范中的必行指令,是由低线规范构成的,而非必行指令则是由高线规范构成的。从指令的导向看,所有低线规范都属于不准人做什么的禁令性规范,如勿说谎、勿偷盗,不要骂人打人,不要随地吐痰,不要趁人之危,等等。而所有高线规范均属于提倡人去做什么的倡导性规范,如应当助人为乐,应当扶贫济困,应当见义勇为,应当大公无私,等等。于是,两种道德规范给人形成的道德义务也是两种,一种是由必行指令形成的绝对义务,一种是由非必行指令形成的相对义务。就绝对义务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而言,相对义务则是可以履行也可以不履行的义务,这就意味着道德在此给人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正因道德规范有高线和低线两种,所以它才能将行为分出四种类型。具体说来,“不当行为”与“守当行为”是依据低线道德即禁令性道德规范划出的,而“欠当行为”与“应当行为”则是依据高线道德即倡导性道德规范划出的。其中,所谓“不当行为”是指违反了低线道德即禁令性道德规范的行为,亦可称“败德行为”,即突破道德底线而对道德造成破坏的行为;所谓“守当行为”,是指未违背禁令性道德规范的行为,亦可称“守德行为”,即守住了底线道德的行为;所谓“应当行为”,是指响应了高线道德即倡导性规范的行为,亦可称“美德行为”,即值得赞美的行为;所谓“欠当行为”,是指未响应倡导性规范的行为,亦可称“欠德行为”,即欠缺美德的行为[13]96-97。
同时,由于被道德的低线规范亦即通常所说的“底线道德”禁止的行为,一定就是被道德认定的坏行为,这才需要通过禁令性规范将其排除掉,而被道德的高线规范提倡的行为,一定就是被道德认定的好行为,这才需要通过倡导性规范促其出现。所以,凡是违背了低线道德规范的不当行为都属于恶行,凡是响应了高线道德规范的应当行为都属于善行。因而,道德的低线规范就是划分恶与非恶的标准,道德的高线规范就是划分善与非善的标准。从利益关系上说,所有被低线道德规范禁止的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类似“以邻为壑”的损人利己性;而所有被高线道德规范倡导的行为,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类似“雪中送炭”的损己利人性。因此,在道德上从行为的实质内容说,损人利己就是确定和识别恶行的标准,损己利人就是确定和识别善行的标准。而余下的守当行为和欠当行为,即那些既没有被道德禁止也没被道德提倡的行为,由于都既没有损人利己也没有损己利人,因而根据已知的道德善恶标准判断,它们就都属于非善非恶的行为。有鉴于此,我们也可以将这两种行为合称为“正当行为”。于是,道德对行为价值的四分法也可变成不当行为、正当行为和应当行为的三分法。
从数量上看,与恶的不当行为和善的应当行为相比,非善非恶的正当行为才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最大量存在的行为,也是人一生中的绝大多数行为,不仅个人日常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自理行为属于这样的行为,而且社会交往中的所有平等交易或等价交易的行为也属于这样的行为。前一类行为的性质是利己不损人,后一种行为的性质是利己也利人。两者都与损人利己的不当行为和损己利人的应当行为不同。有了这种道德对行为的价值分析框架,再回到亲亲相隐的问题上就可以给出这样的回答:亲亲相隐属于非善非恶的欠当行为。这是因为,在知亲犯事的情境中,作为犯事者亲人的当事者,存在三种行为选择,即大义灭亲、助亲为虐和亲亲相隐。助亲为虐是指参与或协助干了坏事的犯事亲人继续干坏事,具有违反低线道德规范的损人利己性质,是恶行,也是需谴责的卑鄙行为;大义灭亲是指为了维护社会公正,不惜牺牲亲情而检举、举报、举证干了坏事的犯事亲人,具有响应高线道德规范的损己利人性质,是善行,也是值得赞扬的高尚行为。而亲亲相隐,一方面没有越过低线道德规范做损人利己之事,即助亲为虐,另一方面也没有响应高线道德规范做损己利人之事,即大义灭亲,因而它就属于在不当行为和应当行为之间的正当行为。确切地说,是正当行为中的欠当行为。同时,也是在恶行和善行之间的非善非恶行为,既不高尚也不卑鄙,既不需要赞扬也不需要谴责。
东川的绿色之变是云南绿色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从理念到行动,在云岭大地上绿色发展日益成为与传统工业化增长模式相竞争并获胜的另一种发展模式,成为消费升级的新动能、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既然亲亲相隐不属于损人利己的恶行,法律自然就不应该将其入罪进行惩罚,因为法律只应惩罚干坏事的人,而不应惩罚没干坏事的人,否则就是恶法,将导致无人不受法律惩罚的状况出现。由此可知,我们其实只能根据法律不可惩罚没干坏事的人这种理念,证成亲亲相隐不为罪的立法理由。同时可知,法律对亲亲相隐不为罪的认定,并不意味对大义灭亲的否定,因为大义灭亲属于被社会道德所倡导的应当行为,也是一种高尚的美德行为,它的价值地位,比法律乃至所有制度都不禁止的正当行为还要高一个层次,更不可能被禁止。
还能知道,从伦理上说,在知亲犯事情境的三种行为选择中,不可取的行为是助亲为虐,不然就会滑向反道德的恶,并意味行为人自愿作恶人。而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则都属于可取的选项,都在道德为人留下的自由选择空间之中。其中,大义灭亲行为的选项又更可取,因大义灭亲也正是这一情境中的高线道德规范亦即倡导性规范,因而它是高尚行为,体现的是善和美德。尽管这种有益于实现社会公正的行为选择也要同时付出一种较为沉重的代价,就是牺牲个人亲情,但这个选项在价值上,仍然要高于非善非恶或说既不高尚也不卑鄙的亲亲相隐。因为前面已经论证,社会公正的价值,是先于和大于个人亲情的价值。当然,如果有人不情愿为社会公正付出亲情的代价,而要选择亲亲相隐这种无碍亲情也无益社会公正的行为,道德上也是容许的。有点奇怪,不仅视亲亲相隐为美德的肯定派学者必然会反对大义灭亲,反对亲亲相隐的刘清平也将大义灭亲说成“邪恶原则”。他这个观点有失偏颇,仍是从特殊中推出的一般,因为他是以“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义灭亲是邪恶的为前提,得出大义灭亲作为一种原则也是邪恶的结论[1]。
背着母亲,我偷偷到父亲出事的现场去了几次,每次都待上很长的时间。父亲在我心中的无名英雄形象,变成了一个用白色漆线勾勒在柏油路面上的空白轮廓,肢体虽然扭曲,但是依然完整。南来北往的车辆不断地从父亲的轮廓上压辗而过,每压一回,关于父亲的生前种种便更加清晰起来。父亲依旧活在我的心中,依然继续为我增添新的记忆,只是不再与我分担新的悲伤。蹲在父亲的身旁时,我不止一次地想起那个在夜市口卖蒸饺的老人。有时,我甚至有一个冲动,想要把父亲的死讯告诉他;我知道这一切都与他无干,我只是想看看他听到我的述说之后,在一阵阵的白色蒸汽包围下,依旧两眼茫茫,仿佛世事原本并无可喜,亦无甚可悲的模样。
既然大义灭亲和亲亲相隐都是道德为人们留出的自由选项,那么,出于对更好结果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当知亲犯事情境出现时,无论是决意选择大义灭亲还是决意选择亲亲相隐的人,都还要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良善预案。就选择大义灭亲的人而言,只有当犯事亲人准备继续干坏事时,才需要立即制止或举报。除此之外的情况,都应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主动自首,仅在劝说无效后再行举报。这样做的优点是,如果劝说有效,就无须举报,也就不会伤害亲情。而劝说无效后的举报,因为已有前面的情理沟通为铺垫,其对亲情的伤害度也会减弱,低于未情理沟通的直接举报。令人惊诧的是,出于儒家立场认定亲亲相隐为美德的郭齐勇竟然也有关于大义灭亲的主张。这就是,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都是儒家提出和提倡的原则,“但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用于对待“寻常之过”即私人事务或民事的行事原则,后者是用于对待“大恶”即公共事务或刑事的行事原则。是故他的实际主张是,只有在亲人所犯之事是事关公共事务或刑事的“大恶”之时,才需要贯彻大义灭亲的原则,其他情况则都适用亲亲相隐原则[14]。然而这个方案根本不好用,试问:攘人之羊是民事还是刑事?而且也无法自圆其说:舜父瞽瞍杀人、舜弟象总想要谋害于舜,这两个哪一个不属于刑事上的“大恶”?哪一个不需要大义灭亲?可郭齐勇为何又在此前的论辩中支持得到孟子肯定的“窃负而逃”和“封象有庳”?[15]
就选择亲亲相隐的人而言,同样应该先行劝说主动自首之事,在劝说无效后,再选择以消极性亲亲相隐行事,即只是隐而不报,再不做其他。前一种做法的道理是,如果劝说有效,就会有益于实现社会公正且无须亲亲相隐。后一种做法的道理是,如果不是选择消极亲亲相隐而是选择积极亲亲相隐,那么相比消极亲亲相隐,客观上就会增加实现社会公正的难度和时间,有间接损害社会公正的作用,具有一定的负面道德价值。由此可知,每一种可取选项的具体做法若不同,也会影响其价值。尽管从价值分析看,积极亲亲相隐行为在客观上有间接损害社会公正的负作用,但从立法上说还是不必区别对待,仍可同样以不为罪待之。一个现实的考虑是前面说的,不可依据间接的危害为某种行为定性入罪;另一个现实的考虑是司法在现实中很难求证一种亲亲相隐的具体情况,究竟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既然不举报犯事亲人的亲亲相隐不为罪的立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不可让犯事者亲属根据司法需要举证犯事亲人的立法,就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种行为同样属于非善非恶的欠当行为。而且,既然既有法律中都会有回避规定,即犯事者亲属不能成为犯事者的有利证人。那么,与之同理或根据对等原则,犯事者亲属也同样不可以成为犯事者的不利证人。否则,就成了在此搞双重标准。不过,亲亲相隐不为罪的立法,不会包括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人,亦即不意味法律也能容忍类似舜的“窃负而逃”和“封象有庳”。因为舜作为社会管理者和执法者,在知亲犯事情境中,只能依法回避,让其他执法者来进行处理,而不可利用自己所握公权之便,或对其父“窃负而逃”,或对其弟“封象有庳”。试想,一般的人有条件这样做吗?所以,凡有如舜的这类作为,不仅渎职,而且是以权谋私,确实属于不义恶行,当受法律惩罚。
结 论
在知亲犯事情境中会出现的亲亲相隐行为,从价值定性上说,既不是肯定派说的善的美德行为,也不是否定派说的恶的不义行为,而是非善非恶的欠当行为。由于这个“欠当”,仅指未能响应高线道德规范的倡导和没有达到应当如何的美德行为水平,效果上并不存在损人利己的性质,也与底线道德无关。因而,对社会来说,它属于可以容许的行为,于是在法律上不可将其立法入罪惩罚,在道德上不可进行舆论谴责。换言之,它属于被道德默许的行为。在此情境中,需要被道德谴责乃至被法律惩罚的行为,是助亲为虐的行为;需要被道德赞扬的行为,是大义灭亲的行为。
注释
①具体论点参看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做过婚前检查吗?”“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我是说去医院。”女青年脸红了,小声回答:“查了,是个男孩。”
参考文献
[1]刘清平.论“亲亲相隐”扭曲正义感的负面效应[J].栗谷学研究(韩国),2015(31).
[2]a邓晓芒.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J].学海,2007(1):5-24;b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3]郭齐勇.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兼与刘清平先生商榷[J].哲学研究,2002(10):27-30.
[4]龚建平.“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J].学海,2007(2):23-32.
[5]郭齐勇,龚建平.“德治”语境中的“亲亲相隐”[J].哲学研究,2004(7):59-64.
[6]郭齐勇.“亲亲相隐”[N].光明日报,2007-11-01.
[7]李晓君.从《孟子·尽心上》第三十五章解读“亲亲相隐不为罪”[J].贵州文史丛刊,2009(2):57-61.
[8]罗晓丹.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损益解读[J].法制与经济,2015(7):95-96.
[9]蔡昱,龚刚.“亲亲不能相隐”的经济学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8(2):144-153.
[10]汪袅袅.儒家伦理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J].当代贵州,2018(3):56-57.
[11]于宵.“亲亲相隐”在美国[J].检查风云,2011(5):6-7.
[12]韩东屏.论道德文化的社会治理作用[J].河北学刊,2011(5):7-12.
[13]韩东屏.人本伦理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14]郭齐勇,肖时钧.“门内”的儒家伦理:兼与廖名春先生商榷《论语》“父子互隐”章之理解[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31-136.
[15]姚源清.“亲亲相隐”思想的法理资源[J].当代贵州,2015(8):54-55.
A Tolerable Action Irrelevant to Goodness or Evil:A Reevaluation of Kin Concealment
Han Dongping
Abstract:The controversy concerning kin concealment has been going on for a long time in the academic circle.However,we have not got a definite conclusion yet.The point is to make a precise evaluation about kin concealment action.Neither the argument of the proponents of kin concealment who regard it as good,virtuous action nor the argument of the opponents of kin concealment who regard it as unjust evil action is valid for their unawareness of this point.So we need a reevaluation of kin concealment.As to the division of human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moral values,a tetrachotomy is more practical than the dichotomy in legal realm which divides all activities into justice and injustice.The tetrachotomy this essay proposes divides all human activities into four classes,which are unjust action when violates the bottom line morals,ordinary activity when obeys the bottom line morals,sub-just activity when doesn’t conform to the high-line morals,and just activity when conforms to the high-line morals.According to this division or classification,in the situation of knowing some kin has violated the law,helping this kin commit crimes belongs to evil unjust action,placing righteousness above family loyalty belongs to good just action,and concealing the misconducts of the kin belongs to the sub-just action which is neither good nor evil.Here“sub-just”does not mean that the action violates the bottom line morals,but only that the action does not respond to the high-line moral principles.This kind of action should not be criminalized and punished legally,but tacitly accepted morally.It is neither to be condemned,nor is it praiseworthy.And for society,it is a tolerable action.
Key words:kin concealment;value attribute;good and evil;irrelevant to goodness or evil;sub-just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9)02-0035-08
收稿日期:2018-11-22
作者简介:韩东屏,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4),主要从事伦理学、价值哲学和社会历史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 齐]
标签:大义灭亲论文; 道德论文; 社会论文; 价值论文; 法律论文; 《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