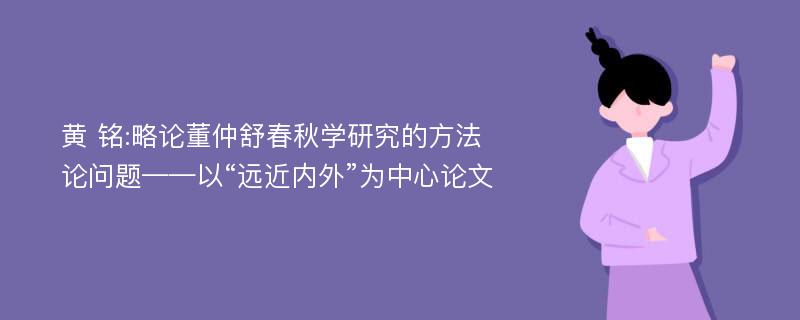
[摘 要]通过何休来解释董仲舒的春秋学,是历代注释者共同遵循的方法。近来有学者从学理上否定了这一路径,认为董学未明的症结正在于此,力图突破何休的框架另立新说,并举“远近内外”问题为例。本文从该例证出发,阐述新旧两种解说,分析出新说错误的原因在于误解了何休的“义例”。以此广论何休的“义例”与董仲舒“《春秋》无达辞”观念之间的关系,重申“以何解董”的方法论问题。
[关键词]以何解董;义例《;春秋》无达辞
董仲舒与何休,是公羊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位经师,被后人称为通向《公羊传》的阶梯。尽管两人在诠释《公羊传》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同时在师承关系上,何休承接的是胡母生的学脉①关于何休学脉远承胡母生,段熙仲有详细的考证,参见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3页。,而非董仲舒的后学,但后世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董、何视为一体,或者即便在某些内容上有所保留,但在经典解释中,也经常用何休的《公羊解诂》去注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如凌曙《春秋繁露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都是如此。
分别以0和T表示计算的基期和计算期,根据Ang and Liu(2003)LMDI加和分解方法[20],对式(3)进行因素分解得到:
以何解董的诠释方法,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即董、何对于公羊学核心概念的认识基本一致。具体而言,何休概括的“三科九旨”,在董仲舒那里也能找到根据②如魏源《董子春秋发微序》,康有为《春秋董氏学》,都以何休的条目整理董仲舒的思想,认为何休所言三科九旨之类的核心观念,在董仲舒那里已经有相关的内容了。。当然,也有学者因为政治原因,强行区分董、何③例如苏舆针对康有为借董子言变法,攻击康有为而曲解董仲舒的微言、改制、王鲁等观念,并归罪于何休。另一方面,何休的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也有重大的义理失误,关键在于用何种理路去质疑何休,可参看黄铭:《何休〈公羊解诂〉质疑略说》《,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47-53页。,但以何解董的诠释方法是没有变的。近来有学者试图从学理上否定这种诠释方法,如杨济襄教授认为:“(《春秋繁露》的注释者)之所以‘于理仍多未明’,最主要的症结,便是由何休《解诂》与董氏之学的扞隔而来。”④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551页。具体来说是“掣肘于何休在《公羊》经传‘字面用语’所构架出的‘义例’,无视于董氏所倡‘《春秋》无达辞’的治经方法,以致于不仅在《公羊传》的注解释义上无法得到通贯,对董氏春秋学义理之发凡,也往往有错误的理解。”⑤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第387页。纠偏的方式是“援引《公羊》经、传原文去破解何休《解诂》所带来的迷思。”⑥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第387页。这种思路无疑是新颖的,是否能够成立,还涉及到对于公羊学整体性的理解。下面笔者就从“远近内外”问题来具体分析。
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发展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石。父母是学生的第一任教师和榜样。作为家长,应该时刻关心子女的身心成长状况,要科学合理地解决家庭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创建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与成长环境,既不能溺爱子女,也不要对子女提出不合理的期望,要及时疏导他们的心理问题,使他们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
(1)供应链过长,全面了解信息成本过大。从全链的角度考虑,关键企业和少数的一二级企业获得了资金帮助。解决了融资困难。但是全链的效率没有那么高,整体授信变得困难。银行作为服务机构,获取全部信息成本很高,很难。从收入成本角度考虑,鉴于信息获取的难度考虑,商业银行没有动力去全部兼顾信息。
一、以何解董之旧说
这种新解存在很大的问题。从文献的角度讲,将“哀”字改为“衰”字,没有版本上的根据。然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讹误颇多,经过清代学者的整理改定,方勉强可读,那么杨氏运用“理校”改字,也不能简单地判定为非法,还是需要从学理上进行考察的。
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大国齐宋,离(不)言会⑦“离不言会”,凌曙、苏舆皆以为当作“离言会”,文献上的根据是天启本注云“一无不字”,当从无“不”字本。。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①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0-281页。
这段材料的主旨是《春秋》缘鲁以言王义,而王义在时间上有远近之别,故而以“隐桓”与“定哀”对举。那么“大国齐宋”以下,是何含义?与上文是否有关联?凌曙与苏舆都认为这些与“远近”有关,故以何休“张三世”之说注释“大国书离会”等内容②如注释“大国齐宋,离言会”,则引用隐公元年何注云:“于所传闻之世,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注释“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则引用哀公三年何注云:“哀公治著太平之终,小国卒葬极于哀公者,皆卒日葬月。”注释“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则引用昭公十五年注文“戎曼则称子,入昭公见王道太平,百蛮贡职,夷狄皆进至其爵”。注释“鲁无鄙疆”,则取隐公元年何注“至所见之世,治著太平,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之意,认为哀公八年“吴伐我”,十一年“齐国夏帅师伐我”,而不言“伐我某鄙”,是因为“王化所及者远”。,认为这些是“三世说”的具体书法。为了具体分析,我们先来看一下何氏的“三世说”。
《春秋经》(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
《公羊传》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再次,“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也是哀公篇的书法。“录而辞繁”,指国君死后,《春秋》既书其卒葬,又在时月日例中,卒书到日,葬书到月。《春秋》大国之君,都是卒日葬月。而小国之君的卒葬,随着三世例有一个递进的过程:传闻世例不书小国卒葬;所闻世方书之,然卒月葬时;至哀公之时,小国才能都达到卒日葬月的标准。
由上可知,何休的“三世说”,包括两个部分,一为立意,一为书法。其一,《春秋》假托鲁国言王者之道,王者治世有先后次序,故治乱之法分三个阶段,即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世依次递进,先治大恶,再治小恶,再到纤细之恶;王化所及,由鲁国至诸夏,再到夷狄。其二是具体书法,如离会、名号等等,在三世之中有不同的表达。从这两点来考察《奉本》篇“大国齐宋”以下,实际上是讨论三世的书法问题。
首先,是书法时限的确定。“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哀”指鲁哀公,时间上属于所见世之末。当时理应治著太平,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故而之前鲁国被伐,《春秋》要记录鄙疆,如庄公十九年“齐人伐我西鄙”;而至哀公则不书鄙疆,如八年“吴伐我”,十一年“齐国书帅师伐我”。
第一,“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衰者皆言我”,这样的句读以及理解,是否有内在的矛盾?按照杨氏的解释,“衰”泛指“衰世之事”,然而结合上下文,应该专指外国战伐之事,否则“伐”字无处安顿。但是杨氏新解最后的落脚点在“缘鲁以言王义”,这个说法包含甚广,整个《春秋》中的史事,皆属于“衰世之事”,如篡位、弑君、出奔、外淫等等皆是“王心”应该关注的,所以具体的“伐”与广义的“衰事言我”始终无法统一。而且“当此之时”,按照杨氏的新解,指代整部《春秋》跨越的二百四十二年,既然是整部《春秋》,何必单言“当此之时”?更为重要的是,杨氏对于“《春秋》缘鲁以言王义”的理解有偏差。杨氏以为,《春秋》本来只记录涉及鲁国之事,以鲁为“我”;之所以记录外国之事,因为《春秋》是王者,对于整个天下,都有“我”的担当。然而在董仲舒的理论中,“缘鲁以言王义”并非只是“记录外事”,而是假托鲁国为“王者”,阐发王义。重点在“王”,而不在“鲁”。《春秋繁露·王道》篇云:
何注: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欑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③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注,徐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最后,“远夷之君,内而不外”,也是哀公篇的书法。《春秋》讲究夷夏之辨,内外之别,体现在名例上,诸夏之君称爵,而夷狄之君则有“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称谓,“子”为爵称,同于诸夏。至哀公时,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无内外之分,故而夷狄之君皆称爵,与诸夏无别。
以何休三世例解《奉本》篇的关键,是对于“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的理解,“哀”指鲁哀公,则“大国齐宋”以下皆为哀公时的辞例。杨氏从这一点突破,认为“伐哀者皆言我”,并非专指哀公,相关的论据,是《春秋》经文言“我”、言“伐”者,不限于哀公篇,并总结了《春秋》经文言“我”、言“伐”者的例子,制成一表(见表 1)②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第398页。。
《春秋经》(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本课程共有12名教师,全部为双师素质教师,专兼职各占50%,形成了学历、学缘、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学梯队。课程负责人是本校护理专业负责人,教学实践经验丰富,教研科研成果丰硕。
二、杨氏新说辨正
所以从何休“三世说”的角度解释董仲舒此段文字,是完全合法的。而且董仲舒也有“三世”之说,如《春秋繁露·楚庄王》篇云:“《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①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9-10页。董子既提出了三世的断代,又提出三世的文辞有变化,而《奉本》篇恰恰是三世异辞的具体化,则董、何之“三世说”若合符节。
表1 《春秋》经文言“我”、言“伐”者一览表
《春秋》纪年 三等庄公九年 所传闻之世经文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传)内不言败,此其言败何?伐败也。曷为伐败?复雠也。庄公十年庄公十九年僖公二十六年文公十四年文公十七年成公二年襄公八年襄公十年襄公十二年所传闻之世所传闻之世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所闻之世所闻之世所闻之世所闻之世所闻之世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传)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则其言次何?齐与伐而不与战,故言伐也。我能败之,故言次也。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夏,齐人伐我北鄙。邾娄人伐我南鄙。齐侯伐我西鄙。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莒人伐我东鄙。秋,莒人伐我东鄙。春,王三月,莒人伐我东鄙,围台。襄公十五年 所闻之世襄公十五年襄公十六年襄公十六年襄公十七年襄公十七年襄公十八年襄公二十五年定公七年定公八年哀公八年哀公十一年所闻之世所闻之世所闻之世所闻之世所闻之世所闻之世所闻之世所见之世所见之世所见之世所见之世夏,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公救成,至遇。(传)其言至遇何?不敢进也。邾娄人伐我南鄙。齐侯伐我北鄙。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成。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洮。齐高厚帅师伐我北鄙,围防。冬,邾娄人伐我南鄙。秋,齐师伐我北鄙。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夏,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吴伐我。春,齐国夏帅师伐我。
据此,杨氏云:“言‘我’记‘伐’之事,遍布于《春秋》三世之中,并非仅见于哀公,而何休所言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根本不见于《公羊传》,更非董氏春秋学之内容。既然,董氏认为‘王道’之义遍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而言‘我’记‘伐’之事多列于哀公以外之经文,董氏实无必要强调‘诸侯伐而皆言我者’皆哀公之事。”①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第340页。否定了哀公之事,则“大国齐宋离言会”以下的文字,也失去了三世辞例的含义。
OSCE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考核方法,只是提供一种客观的、有序的、有组织的考核框架,在这个框架当中每一个医学院、医院、医学机构或考试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加入相应的考核内容与考核方法。OSCE是通过模拟临床场景来测试医学生临床能力,是一种知识、技能和态度并重的临床能力评估方法。考生通过一系列事先设计的考站进行实践测试,测试内容包括标准化病人、在医学模拟人上实际操作、临床资料的采集、文件检索等。考站设置分长站、短站,时间从5分钟到20分钟不等。由主考人或标准化病人对考生进行评价。
那么,“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应该怎么解释呢?杨氏认为“伐哀”当作“伐衰”,“衰”指代“衰世之事”。同时“我”字也有新的含义,杨氏云:
“我”字在经文中专指“鲁国”,除非事关鲁国,否则,经文不会以“我”行文。我们由上述《春秋》言“我”记“伐”之事看来,众多的战伐,鲁国并非皆为当事国。那么,此处的“诸侯之伐衰者皆言我”,应该不是指经文在字面上以“我”字行文的意思。否则,这句话与经文实际的记载情况就有出入。“诸侯之伐衰者皆言我”,应该是指《春秋》经文在书写“战伐”史事时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致使经文的陈述,透露出“我”的责任与使命。由于《春秋》是以鲁史记为示范,示范出一个王朝的礼制与气象;所以,放眼天下以为视野,去关怀诸侯之间的伐战,于《春秋》经文来说,毋宁是对王者的期待,期许王者以天下为己任。《公羊传》屡番感叹“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也是这样的一种情愫。事实上,“皆言我”,对“我”的期许,便是董氏所言“缘鲁以言王义”。②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第401页。
杨氏将“伐我”二字拆开,认为“我”字并非是鲁国,而是《春秋》书写的原则,即以“我”之使命感记录本不该记录的外国战伐之事。并列举“莒人伐杞(隐公四年经)、楚人伐郑(僖公元年经)、齐人伐山戎(庄公三十年经)、秦师伐晋(宣公二年经)、吴伐越(昭公三十二年经)等”,皆属“伐衰言我”的范畴。而这种书法与董氏所云“缘鲁以言王义”是符合的③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第402页。。
《春秋繁露·奉本》篇有这么一段文字:
整本书阅读虽然由来己久,但真正进入教学领域还是近几年的事,这虽然是目前新课改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由于此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教学研究并不完备,因此,本论文在充分认识整本书的提前下,尝试将其纳入语文课程视野,为一线教师提供一个可供教学使用的视角。
其次,“大国齐宋,离言会”,也是所见世的书法。因为离会属于小恶④桓二年何注云:“二国会曰离,二人议,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决事,定是非之善恶,不足采取,故谓之离会。”据此,离会为小恶。,在传闻世,以鲁国为内,以诸夏为外,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故齐宋等国的离会是不书的。至所闻世,以诸夏为内,亦书其小恶,故书齐宋离会。所见世的情况,何休未有说明,苏舆云:“所见世,远近大小若一,当书外离会。”⑤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80-281页。则齐宋离会,亦是哀公篇的书法。
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
来曰聘。王道之义也。④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16页。
这段文字中,董仲舒将“缘鲁以言王义”表述得非常清楚。首先,《春秋》假托鲁国为王者,故而朝见鲁国的诸侯能够得到褒奖,如滕本为子爵,而褒为侯爵。可见重点不在记录外事,而在于王者的褒奖。其次,通过内外异辞的方式,彰显鲁国的王者身份。例如,同样是外交事件,诸侯称“朝聘”而鲁称“如”。落脚点都在“王”字上,显示鲁国被赋予的王者权力与地位,远非“书外事”那么简单。如此,则杨氏新解在学理上不能自洽。
第二,杨氏批评何休三世例最主要的论据,是对“鲁无鄙疆,诸侯伐哀者皆言我”的质疑,认为经文书“伐我”,不仅限于哀公篇,且找出了很多例证,之后才有改“哀”为“衰”的说法。然而这种批评是建立在误解何休辞例的基础上的。何休认为,至哀公朝的时候,王化遍及天下,故而鲁国没有鄙疆,诸侯来伐哀公,经文仅书“伐我”。这种书法针对的是“有鄙疆”的情况,即表1中的“伐我东鄙”“伐我西鄙”“伐我南鄙”“伐我北鄙”等书法。所以不书“伐我某鄙”而书“伐我”,证明了哀公时期的鲁无鄙疆,而表1中的经文,完全可以支持这个观点。杨氏的错误,在于混同了“伐我”和“伐我某鄙”两个辞例,单就“伐我”二字进行检索,忽视了“鲁无鄙疆”四字。既然何休之说能够成立,那么改“哀”为“衰”等讲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三、《春秋》之例与《春秋》无达辞
由上可知,杨氏质疑以何解董的诠释方式,是从“例”的批判开始的,又认为何休之例与董仲舒“《春秋》无达辞”的观念冲突,从而否定以何解董的合法性。那么就有必要重新审视“例”与“无达辞”两个观念。应该怎样看待何休的义例呢?
第一,要明确何休之例的确切所指。以上文提到的“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为例,指的是“伐我某鄙”与仅言“伐我”的比较。不能简单地以“伐我”二字检索经文,否则会泯灭何休的问题意识,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如表1中第一、二条,“伐”“我”二字本不相连,又第一条“伐败”之“伐”乃“夸伐”之意,与“战伐”无关,都不应纳入。
第二,要明确何休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如“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中对于“微国”的界定。从何休的角度来看,“微国”基本上与“小国”相同,而与“大国”相对。区分的标准是爵制,即公、侯为大国,伯、子、男为小国①这是大体的判分,微国的概念比小国更广,包括伯子男以下的国家,但与大国的区分是明显的。另外,郑国属于特例,虽为伯爵,但属于大国。。这与《公羊传》隐公五年“二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之文相合。然而杨氏认为:“董氏所言之‘微国’,应是泛指国力衰微之国,亦或许是相较于霸主国而言。”并将卫、陈、蔡三个侯爵之国视为小国②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第417页。,据此立论,破解何休小国之君的卒葬条例。这是不恰当的。
第三,要明确“正例”与“变例”的区分。这种区分不是何休开创的,《公羊传》中早已有之。
大量的运用对偶,在形式上音节整齐匀称,节律感强;在内容上,凝练集中,概括力强,使“嘎花”富有音律感,便于人们唱和记。
《公羊传》继弑君,不言即位,此言即位何?如其意也。③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注,徐彦疏,第117页。
选取2017年3月~2018年5月离休老干部病房收治的老年患者84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护理模式分为两组,各42例。其中,对照组男30例,女12例,年龄61~89岁,平均(73.19±3.72)岁;研究组男29例,女13例,年龄61~90岁,平均(74.05±3.11)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经伦理委员同意。
其中“继弑君不言即位”就是《公羊传》的条例。条例本身是一套书写规则,用来彰显微言大义,但并不是说,所有内容都必须符合条例,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的义理是从变例中求得的。如上文,按照条例,鲁隐公被杀,桓公即位属于“继弑君”,本不应该书“公即位”的,可因桓公弒隐自立,书了“公即位”,反而表达了“如其意以著其恶”的义理。由此可知,以例解经,正例当与变例相表里。对待何休的条例,也应该注意这一点。如何休论述曹君之卒葬。
据安徽省水利工作会议消息,淮水北调工程已获安徽省内立项批准。淮水北调工程属南水北调东线安徽配套工程,也是皖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区域调水工程。该工程自蚌埠五河站从淮河干流抽水,经淮北市濉溪县黄桥闸向北至宿州市萧县岱山口闸,调水线路总长266km,估算投资10.3亿元,主要保障淮北、宿州两市工农业生产用水。前期工作目前正加快推进,计划2012年4月底前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及部分泵站单体工程的初步设计,并报安徽省发改委批准,力争上半年开工建设。
《春秋经》(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十一年)夏,五月,葬曹桓公。
何注:小国始卒,当卒月葬时,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来朝,《春秋》敬老重恩,故为鲁恩录之尤深。
在种植玉米之前,我们需要做土地整理,主要是去除去年在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的根部,或者完全粉碎[1],以避免影响玉米的正常种植或影响其产量。事实上,粉碎去年作物的根部更有利于作物栽培,因为粉碎的材料可以用作肥料来提高土壤肥力。然而,由于玉米高产的需要,土壤肥力仍然不足。因此,还需要在播种前施用基肥,才能有效地保证玉米的产量和收入。
徐疏:所传闻之世,未录小国卒葬。所闻之世乃始书之,其书之也,卒月葬时,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者是也。今卒日葬月者,正以敬老重恩故也。④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注,徐彦疏,第167页。
按照徐彦总结的何氏条例,传闻世不录小国之君的卒葬,至所闻世方录之,且卒月葬时。然而桓公十年属于传闻世,曹伯终生却卒日葬月,属于变例,为的是表达“《春秋》敬老重恩”的义理。可以说,正例确定书法原则,变例揭示义理,这在何休的理论中是自洽的,且《春秋》据乱世而作,不可能没有变例。然而杨氏云:“如果,何休所言,曹国国君卒葬之‘时日月’条例是真实的;那么,就不应该有例外,方可称为书写‘条例’。”⑤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第456页。笔者认为,这种僵化的条例观,不符合《公羊传》以例求义的精神。
(二)根据流行程度推断 暴发性发生腹泻,传播迅速,一般与病毒性腹泻有关;隐性发生,传播缓慢,渐进性加重,多由细菌性、寄生虫病或营养剂应激因素引起。
以何解董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何休的义例与董仲舒“《春秋》无达辞”的观念是否矛盾?很多学者将“《春秋》无达辞”视为董仲舒反对条例的证据,关于此说,需要重新考察。“无达辞”之说见于《春秋繁露·精华》篇。
难晋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称子,盖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杀奚齐,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何也?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仁人录其同姓之祸,固宜异操。晋,《春秋》之同姓也。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为为之者,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辞,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谓奚齐曰:嘻嘻!为大国君之子,富贵足矣,何必以兄之位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尔。录所痛之辞也。故痛之中有痛,无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齐、卓子是也。①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94-96页。
由上可知,董仲舒是根据僖公九年“晋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齐”,来论述“《春秋》无达辞”的观念的。推寻董氏的逻辑,奚齐为未踰年君,本应遵循“未踰年之君称子”的书法,《春秋》却书“君之子”,是为奚齐明义,认为奚齐为大国君之子足矣,不该居兄之位。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无达辞”,并不是抛弃条例,而是在条例的基础上进行变化,说明微言大义。如果没有条例的规范,则无法“从变”以“从义”。可以说,“《春秋》无达辞”实际上与变例的概念相同,与何休以例解经的方法并不矛盾②除了“《春秋》无达辞”之外,董仲舒还有“《春秋》无通辞”的说法。《春秋繁露·竹林》:“《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这与条例也不矛盾,“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是《春秋》的常辞,也就是常例,以此为基础,才能偏然反之,从邲之战的文辞中看出夷夏关系的倒转。所以无论是“无通辞”还是“无达辞”,都不是脱离条例任意解说的。。
综上,我们认为,如果从公羊学的理路出发,从内部理解董仲舒与何休的学说,以何解董的诠释方式是合法的,可能还是必要的,因为董仲舒后学的著作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与其另立新解,不如从时代相近的《公羊解诂》去诠释董仲舒的春秋学,不必刻意夸大董、何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董、何具体的学说确有差异,例如上引奚齐称“君之子”的问题。董仲舒认为称“君之子”是变例,而何休以为正例,但这属于具体的师法差异,不影响以何解董的诠释方法,只是在诠释过程中需要仔细辨别③关于董、何的差异,可参看黄铭《:〈春秋〉学中的董何之异》,见干春松,陈壁生主编:《经学与建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186页。。
On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 in Dong Zhongshu’s Study of Chunqiu:With the Relation of Near-Far and Inner-Outer as the Center
HUANG Ming
(Institutefor Advanced Studiesin Humanitiesand Social Sciences,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Dong Zhongshu’s study of Chunqiu was interpreted with the aid of He Xiu,which was a common method adopted by the annotators in the past dynasties.However,some scholars,having denied this approach in the academic respect,attribute the crux of implicit studies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 to it.Focusing on the issue about the relation of near-far and inner-outer,these scholars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new approach to breaking through He Xiu’s framework.Starting from this example,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old and new interpretations,and concludes that the causes for their errors lie in their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application of prime purport and principles adopted by He Xiu to historical narratives.Accordingly,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e Xiu’s application of prime purport and principles to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Dong Zhongshu’s ideas of no thoroughgoing diction in Chunqiu or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s widely discussed,and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 is restat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ong Zhushu with the aid of He Xiu.
Key words:interpretation of Dong Zhongshu with the aid of He Xiu;prime purport and principles to historical narratives;no thoroughgoing diction in Chunqiu
[中图分类号]B 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9)01-0003-06
[收稿日期]2018-04-12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18QNZX5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106112016CDJXY470010)
[作者简介]黄铭(1985-),男,江苏常熟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春秋学、礼学研究。
[责任编辑:严孟春]
标签:董仲舒论文; 春秋论文; 公羊论文; 之世论文; 公羊传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汉代哲学(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论文;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18QNZX5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106112016CDJXY470010)论文;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论文;
